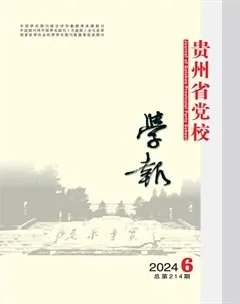“兩創”視域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闡釋的三重內在張力
摘 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日益成為全社會的共識。然而,在“兩創”過程中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絕不可能不受約束地隨意加以改造、任意加以創新,必然會受到一系列張力性因素的內在制約。文化主體的“進步預設”、“理性自負”和“歷史局限”使得傳統文化的闡釋主體存在“劇作者”與“劇中人”的張力性結構;傳統文本的“非確定性”、“良莠混融”和“意義域界”決定了傳統文化存在“開放性”與“確定性”的張力性對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極作用的邊界性、轉化方向的規定性以及闡釋方式的特定性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闡釋存在“自在性”與“自為性”的張力性因素。梳理和分析“兩創”過程中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闡釋的張力和邊界,從而更加自覺、更加辯證地處理文化闡釋過程中的兩難困境,是推動“兩創”走向深化的必經環節。
關鍵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文化闡釋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5381(2024)06 - 0040 - 11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下簡稱“兩創”),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化傳承問題的一個原創性觀點。經過十余年的理論詮釋和實踐探索,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日益成為全社會的共識。然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絕不可能不受約束地隨意加以改造、任意加以創新,必然會受到一系列張力性因素的內在制約。習近平同志指出:“故步自封、陳陳相因談不上傳承,割斷血脈、憑空虛造不能算創新。要把握傳承和創新的關系,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1]。在這里,習近平同志對“割斷血脈、憑空虛造”的揭示和“破法不悖法”的警示,實際上點明了文化傳承創新的張力問題。張岱年基于辯證法的基本精神指出:凡立論須自審其適用之限際或范圍[2]68,如不自知其限際,便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2]69因此,只有歷史地、客觀地承認和澄清這種內在張力,才有可能科學合理地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如果不對其邊界和張力進行清晰地認識和前提性反思,在理論認識層面可能會導致人們將“兩創”隨意運用于關涉文化傳承的所有問題之中,從而使“兩創”思想淪為一個任意搬用、裝點門面的裝飾物;在實踐層面可能會導致人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闡釋缺少理論規范,從而誤解或曲解當代中國的文化政策。因此,有必要從主體、文本和價值三個維度對傳統闡釋的前提和界限進行反思和批判,從而更加自覺、更加辯證地處理文化闡釋過程中的兩難困境,這是推動“兩創”思想研究走深走實的重要環節。
一、“劇作者”與“劇中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闡釋的主體張力
思想闡釋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過程中必經的邏輯環節,而任何闡釋必然是特定文化主體的闡釋,而任何文化主體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對于文化主體的理解首先關涉這樣一個問題:文化是“自身發展”的,還是由人來推動發展的?斯賓格勒認為:文化發展的全部過程表現出自己對于人的真正獨立性……文化是自身發展的,與人無關,與人民無關。[3]斯賓格勒從抽象理性出發探討文化發展問題,認為文化是與人無關的自我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則認為:“人們的觀念和思想是關于自己和關于人們的各種關系的觀念和思想,是人們關于自身的意識,關于一般人們的意識(因為這不是僅僅單個人的意識,而是同整個社會聯系著的單個人的意識),關于人們生活于其中的整個社會的意識。”[4]可見,一方面,人是文化的創造者,即任何文化都是人的對象化活動的產物,人是文化的實踐主體和創造主體;另一方面,人也是文化的創造物,即文化反過來又塑造主體甚至創造作為主體的人。作為文化主體的人體現為一種“主—客”統一性。在這個意義上,文化主體的價值和意義正是在文化的發展和創造中獲得彰顯,而文化的發展和創造則表征為新的具有嶄新精神內核的文化主體的形成。文化的每一次發展既依賴新的主體又創造新的歷史主體。文化的這種塑造者與被塑造者的統一性決定了主體在文化轉化和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的內在張力。
(一)文化主體的“進步預設”制約了對傳統文化的全面認識
在作為主體的人的意識深處,常常潛藏著某種價值預設。近代以來,在進步主義和理性主義的雙重驅動下,生活于現實世界的人總是傾向于將過去的時代理解為荒蠻落后的時代,從而下意識地拔高當代人所生活的時代意義。自覺地分析和反思作為“兩創”主體的當代中國人潛意識之中的這種價值預設是認識傳統文化主體張力的重要方面。有學者指出,人不僅是文化的創造者、繼承者,而且是文化的載體或文化本身。[5]張岱年在分析文化主體性的時候也曾指出,任何主體同時也是一種客體。[6]因此,在“兩創”過程中,傳統文化的傳承主體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這種現實境況很容易掩蓋或者忽視對自身缺陷的深刻反思和前提批判,從而難以分析和辨別傳統文化當中隱藏的“劣根性”,進而影響傳統文化轉化發展的效果。當代人似乎總是擅長于批判和審視過去的人和傳統文化所具有的缺點,而容易忽略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這種思想傾向容易導致這樣的潛意識和無意識:似乎作為理性主體的現代人,在對傳統文化進行思想批判和道德審視的過程中已經先行地將自身設定為“進步的”,從而可以居高臨下地評判過去的一切。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進行道德敘事的人似乎自身就具有了先民所具有的德性;揭示古人的“劣根性”就是張揚現代人的“優越性”。[7]這是一種嚴重的遮蔽現象。不管作為傳承主體的現代人是否意識到,傳統文化中的“劣根性”同“優秀因素”一樣,客觀而隱蔽地存續于現代人的身上。比如,來自傳統社會的以權力為中心的政治觀,不僅仍舊存在于當代中國人的身上,甚至被現代技術時代所放大。如果忽視了對這種政治觀念進行深刻的前提反思和徹底的自我批判,從而改造傳統以權力為中心的政治觀,進而改變圍繞著“權”“術”“勢”而展開的思維方式,我們對傳統政治文明優良成果的傳承和弘揚就會淪為一種毫無意義的“形式”。因此,我們應該自覺以冷峻的態度對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進行客觀審視,對傳承主體的立場方法進行深刻反思。
(二)文化主體的“理性自負”制約了對傳統文化的客觀理解
在以理性為人類一切知識和價值源頭的現代社會,似乎人在“理性”的加持之下可以做到想做的一切事情,這構成了現代人的“理性自負”。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的過程中,生活于現代社會的文化主體,很容易對自身的理性籌劃能力過度自信,導致面對存在于過去的傳統文本,難以深刻理解其本真意蘊和深遠意涵,進而影響傳統文化轉化發展的效果。比如,“邏輯與歷史統一”的方法論是闡釋歷史文本的基本要求,如果人們對于自身的理性籌劃能力過度自信,盲目地以“邏輯”因素對“歷史”過程進行肆意“侵犯”,就不可能真正做到本真地呈現“思想的歷史”,也就難以突破所謂“解釋學循環”的桎梏。在這個意義上,實現對傳統文化“兩創”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突破和超越這種“解釋學循環”,徹底貫徹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理念。正如馬克思所說:“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8]182超越“解釋學循環”也只能在“解釋學循環”的過程中找到讓文本自己說話的真正出路。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任何文本的意義,始終是和特定闡釋者綁定在一起的,而任何文本闡釋者必然存在其特有的思維“前見”。傳統文化的闡釋者應當客觀地闡釋文本,但由于闡釋者的先入之見,決定了他不可能做到絕對客觀,而是根據自己的“前見”對文本進行闡釋和解讀。因此,所謂“文本的意義”是文本與闡釋者的“思維前結構”相互作用的結果。就“兩創”的主體而言,在深入文本進行解讀和闡釋之前,首先應該對解讀文本的“思維前結構”或者“前見”進行必要的前提反思,即引入“第二個自我”,從而形成“真正的經驗”。在對解釋學的前提性問題進行謀劃的過程中,伽達默爾明確指出,真正的經驗就是這樣一種使人類認識到自身有限性的經驗。在經驗中,人類的籌劃理性的能力和自我認識找到了它們的界限。[9]這種深刻的認識對當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兩創”具有重要的啟迪。
(三)文化主體的“歷史局限”制約了對傳統文化的內涵闡釋
文化闡釋必然是一定主體的闡釋,任何文化主體都不可能超越其生活的特定時代和歷史條件的限制,因而文化闡釋具有其特定的主體性意蘊。馬克思指出,社會生產中的個人都是現實的個人,“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8]524。因此,每個參與文化傳承的主體,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原子個體,而是具體地、現實地生活于特定時代之中的社會的個體,不可能擺脫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個時代歷史條件的限制。作為處于特定社會生活之中的文化傳承主體,其對傳統文化所做的解讀和闡釋必然打上時代和社會的烙印。闡釋者所處的時代格局、時代問題、時代需求以及闡釋者個性化的知識結構、認知方式、情感關懷、生存體驗都必然會影響對傳統文化要素的理解和闡釋。因此,針對同一傳統文化要素,不同時代的文化主體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理解。在推動傳統文化“兩創”的過程中,文化闡釋的這種主體性意蘊決定了對傳統文化所作的歷史闡釋應該進行合理的辨識與考量,即辨析清楚在多大程度上歷史事實的事實是關于個人的事實,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關于社會事實的事實[10]。同時,文化闡釋的主體性絕不等同于主觀性,即虛無和否定文化內涵的客觀性。因此,在“兩創”過程中,對傳統文化要素的闡釋必須首先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還原概念的原初語境。這種客觀性內涵成為闡釋主體性發揮的合理邊界和基本前提。主體無法超越特定的時代和歷史條件,并不意味著人只能完全消極被動地接受時代和歷史條件的限制,而是可以積極主動地根據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去彰顯自身的主體性,從而在歷史創造中進行文化創造。因此,在“兩創”過程中,由于主體的歷史局限,傳統文化闡釋的深度和準度可能會受到一定影響,但絕不會徹底影響對傳統文化闡釋的創新性和創造性。
二、“開放性”與“確定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闡釋的文本張力
“兩創”不是外在于文化傳承過程的原則性規定,而是體現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容進行思想加工和內涵闡釋的具體過程之中,這種思想加工和內涵闡釋都需要通過以文字為載體表現出來。任何思想一旦通過文字的形式記錄下來,就具有了天然的意義開放性。這種開放性因每個歷史時代解釋者的生存狀態和價值追求的不同而開顯出不同的意義空間。這種意義空間的展現是立體多元的動態性存在,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視角會對同一文本做出不同的闡釋。同時,任何文本的思想內涵在特定歷史語境和特定時代場域之下又具有其確定的意義空間,否則就會失去文本基本的作用和價值。洪漢鼎十分形象地指出,對作品真理內容的理解不是在昔日的黃昏中,而是在來日的晨曦中。傳統繼承是通過作品的語言中介或構成物對作品在當代視域下進行闡釋,作品的語言中介或構成物的抽象觀念性或意象性既規定了闡釋的界限,使得傳統繼承不是任意的繼承,同時又使繼承不囿于原先的意蘊,使得傳統繼承成為創造性的繼承。[11]因此,文本的這種“開放性”與“確定性”存在的張力性結構,導致對文本內涵的闡釋具有特定的邊界和限度。
(一)文本的“非確定性”導致文化信息損耗
就表現形態而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浩瀚典籍;二是以非文本形式存在的文化要素。這兩種存在形態都具有非確定性的文本特征。就前者而言,古代典籍在幾千年的流傳過程中,經歷了復雜的版本變換、內容變遷和內涵變化,難免會出現漏字、衍文、錯簡等各種具體情形,從而難以直接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因此,通過考鏡源流、辨章學術,以專業的溯源、考證與校勘最大限度地把握傳統文本的準確內涵成為必經環節。經此環節,典籍之中的傳統文化要素才真正實現“文本化”,成為“兩創”的真正對象。否則,對經不起基本學術考驗的傳統文化內容進行的“兩創”是難以真正開發其思想價值的。同時,那些存在于文化典籍之中的價值理想和道德范式,實際上絕大多數只是停留在理念層面的精神境界,只是在應然層面作為人人須遵守的“道德范型”或“道德律令”而存在。在實然層面,這些法則和律令從未完全展現自身,并沒有真正成為古人在現實生活中所達到的精神境界,也并沒有完全存在于古人的德性結構之中,從來沒有真正做到過和實行過。古今中外皆如此。陳先達曾提出,“傳統不等于文化典籍”[12]73。基于此,就不應該把圣人、先賢所倡導的“道德范型”視作古人實際具有的德性結構,這就決定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辯護應是適度的,而不是過度與不足的。[7]因此,不能機械地將古代的文化典籍視為不可超越的范本,更不能將“兩創”窄化為對古代典籍文本所做的當代注腳。因此,傳統文本的這種“非確定性”成為傳統文化內容闡釋的重要障礙性因素,成為制約“兩創”的重要方面。就后者而言,許多傳統文化要素是以非文本的形式存在的,或者寓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風俗習慣和心理結構之中,或者以文學、繪畫、建筑、雕塑、音樂等形式寓于傳統藝術作品和文化遺產之中。這些文化要素都無法直接進行“兩創”,要在相關領域專業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文化整理、思想加工和精神提煉,從而提煉出某一領域的相關文化命題,進而實現其傳統文化要素的“文本化”。例如,蜚聲中外的敦煌文化之中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存在于洞窟壁畫之中的各式各樣的飛天形象是以藝術的形式存在的文化表征,我們無法直接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需要敦煌學專家對其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思想加工,從而實現其“文本化”,即將敦煌飛天形象的歷史溯源、流傳演變、形態分類、代表意涵等研究清楚,并以敦煌學研究成果的形式呈現出來,成為進一步研究其藝術價值和哲學價值的文本基礎。在此基礎上,可以根據時代需要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開發其唯美風姿所具有的美學價值和藝術價值,探究其所包含的精神自由的哲學意蘊,深挖其與中國人“天人合一”的價值追求具有的內在契合性,等等,從而推動其創新性發展。然而,在正本清源的過程中,傳統文化文獻載體的數量十分龐雜、形式復雜多樣、時間悠久綿長、思想浩轉流變,導致對歷史本來面目的徹底還原、歷史文化內容的客觀審視困難重重,很可能存在對文化內容的誤讀、轉化效能的損耗、文化信息的失真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成為制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的重要方面。
(二)文化內容的“良莠混融”導致文化甄選困難
郭齊勇指出,在理解文化傳統的優長與價值時,又必須深具自我批判的精神,正視并檢討中國文化自身的缺失、缺弱與缺陷,這恰好是中國文化“兩創”課題的題中應有之義。[13]中華傳統文化不是凝固的死的存在,而是流淌在思想的時間隧道中的活的存在,不是一堆死寂的思想化石的堆砌,而是一條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之川。這條思想河流之中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問題在于“水”與“泥沙”并非涇渭分明,而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式摻雜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是一體兩面、相互涵攝的關系,很難簡單地加以區分和剝離,它的特點、優點和缺點很可能就是一個“點”,甚至它的精華很可能正是它的糟粕。同時,隨著歷史的變遷和場域的轉換,傳統文化的某些要素也會發生變化。有些文化要素在過去起過很好的歷史作用,現在卻走向了反面;有些文化要素在今天看來不合時宜,在將來可能會受到重視;有的文化要素在某一文化場域失去了效力,在另一文化場域卻可能發揮奇效。五四時期的部分知識分子曾主張丟掉傳統的“包袱”。在這里,以“包袱”作喻,其實既不全面也不深入,是非批判的、直觀的、機械的。因為,當我們說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已經融入每個中國人血脈的時候,有些糟粕性的東西可能也融入了每個中國人的血脈之中,而很難將其當作“包袱”加以簡單拋棄。因此,關鍵在于我們應該基于什么樣的立場去“審視”傳統文化,應該運用什么樣的標準去“揀選”傳統文化,應該如何在“返本”中開新,應該如何將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要素合理地契入社會現實、融入人民生活等。文化是作為整體存在的,任何外在的批判和反思,試圖通過“外科手術式”的方式都無法解決對傳統文化價值的準確認知。將傳統視為發展的“包袱”,并不是由于我們充分認識到了傳統的消極作用,而恰恰是由于我們對傳統的認識不夠深刻,即沒有認識到傳統的消極因素其實同積極因素一樣,已經滲入我們的骨髓和血液里,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我們不可能簡單地將其拋棄。因此,只有對這個文明中間最精華的東西進行全面的開發,才可能對它糟粕的東西進行轉化。[14]杜維明的這一認識頗為深刻,為我們開發傳統文化當代價值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啟示。這種客觀境況導致我們對傳統文化價值的全面理解和準確體認異常困難,這種困難性決定了當代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創”必然會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制約。
(三)文化內涵的“意義域界”導致文化闡釋困境
所謂闡釋不是對文本簡單復誦或機械注釋,而是要在文本中不斷開拓出新的意義空間。“注釋”意味著一種崇圣性的解讀,這種解讀可以看作原初意涵的另一種表達,帶有一種天然獨斷性。“闡釋”意味著一種自否性的解釋,這種解釋必然不是原初意涵的重復和再現,而是在把握古代文化命題原初內涵的基礎上,充分參照當代社會發展需要、轉換其思想語境、擴大其適用范圍、豐富其思想內涵。因此,我們所理解的文本“闡釋”既不是迷信經典、崇拜權威,從而陷入原教旨主義的泥淖,也不是隨意闡發、任意解讀,從而陷入相對主義的陷阱,而是根據時代需求、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對傳統文化進行前提批判和思想改造。經典之為經典,并不在于其內容上的包羅萬象,而在于它作為思想種子的孕育力和理論假設所開啟的可能性和開放性。因此,在承認對傳統文化進行“見仁見智”的全方位解讀的同時,也必須承認文本闡釋所具有的特定限度。然而,闡釋的創造性再強大、再突出,也不能突破來自“文本”所提供的意義的可能性空間的限度,否則就是一種“非法”的“誤讀”。[15]這就是文本闡釋的意義限度。有學者指出,“這個限度就是該經典文本所給出的‘意義域’”[16]。只有在這一意義域之內的闡釋才是合法而有效的,一旦越過了這一意義域,就會演變為對文本的“借題發揮”和“過度闡釋”。在對傳統文化資源進行現代闡釋的過程中,要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對傳統文化資源進行辯證分析、全面認識,這種科學的方法論是把握傳統文化命題“意義域”的關鍵。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概念、命題和范疇具有模糊性、多義性的特點,若缺乏嚴格的學術規范和嚴謹的治學精神,很容易產生對文本內容的臆解和誤讀。張岱年先生曾指出,我們考證歷史事實,要嚴守史料所證明的限度,超過這限度,應該闕疑。[17]因此,學者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態度,不能根據自己的解釋需要任意虛構聯系、妄加演繹、臆解材料,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闡釋的任意性和主觀性。只要我們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將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精神之文字符號載體的典籍與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的現實實踐真正地融為一體,就不會越出這一“意義域”的邊界。此外,一種觀點認為,闡釋意味著運用純粹客觀的立場審視文本,從而追求徹底回歸作者原意。其實,如果深究一下到底何謂“作者原意”,就會發現這是不可能實現的。面對某一文本化內容,“作者原意”意味著作者的原本意圖,即作者在特定時代背景、特定語言環境、特定理論視域下通過特定文字所要表達的意圖,因此闡釋者很難精準、完全把握作者的意圖。同時,作者一旦通過文字的形式表達某一思想,就意味著作者思想的凝結,作為語言符號的文字本身就會彰顯出自身的文字意圖。因此,文本之中所體現的作者意圖、文本意圖、文化政治意圖、讀者闡釋意圖等之間處于復雜交叉融合,必然影響對傳統文化內涵的闡釋。
三、“自在性”與“自為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闡釋的價值張力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兩創”還關涉這樣一個問題: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如何在現代中國的現實場域中彰顯出來,進而在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發揮作用。整體而言,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存在于傳統的農耕社會、基建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依附于嫡庶分明的宗法倫理、服務于皇權專制的文化存在,它同中國傳統社會獨特的問題機制、內在結構、制度運行和演變邏輯相嵌套,決定了中國文化獨特的時代風貌,決定了傳統中國人認識和把握世界的獨特方式,決定了傳統中國社會獨特的制度選擇和價值取向。這些價值支柱形成了一套邏輯自洽、具有很強的自我保護能力的文化系統。有學者感嘆:文化傳統的更新與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脈的溝通,如同給心臟病人做“搭橋手術”,那是要慎之又慎的。[18]與傳統社會相比,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結構、政治架構、價值目標都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因此,中華傳統文化時代價值的彰顯具有天然的歷史間隔性,必然要面對傳統與現代所產生的抵牾與沖突。禁錮于時光之中的傳統文化精髓,要想跨越古今之障,成為靈動鮮活的民族生命之源,還需要經歷文化結合、轉化的鍛煉。傳統文化與歷史語境之間的這種命運性關聯勢必制約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構成了當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價值張力。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定向,規定了傳統文化積極作用發揮的基本邊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底色,規定了傳統文化轉化發展的基本方向;古今中西之爭的時代觀照,規定了傳統文化轉化發展的闡釋方式。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極作用的彰顯具有邊界性
面對當今世界面臨的發展危機、治理危機、生態危機、道德危機、和平危機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無疑蘊藏著豐富的解決危機的智慧啟示,具有特殊的時代價值。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19]譬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對西方二元對立、宰制自然的形而上學的頡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倫理、崇道德的傳統對西方工具理性張揚而道德理性缺失的補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追求對西方現代性文明的警示;等等。同時,習近平同志對中華文化負面價值的認識是清醒而深刻的:“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20]313傳統文化中這些陳舊過時的糟粕性要素具有頑固的生命力,絕非輕易就能消除,一旦具備一定的條件,就會死灰復燃,成為影響和制約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創新的因素。換句話說,傳統文化天然的內在矛盾制約著其價值彰顯,這一認識前提決定了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無限度地拔高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中華傳統文化,哪怕是其中的優秀文化的價值都是有其邊界的。因為,文化的價值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文化觀念發揮作用離不開其所依存的社會結構,離不開經濟基礎的制約和政治制度的約束。文化觀念本身并不是自足的,它本身無力承擔起現代性危機這樣重大的歷史責任。[21]現代性危機和問題根源于文化表現背后的社會關系和經濟基礎,文化層面的反思可以為發現和解決現代性危機提供致思路徑和思想資源,但是如果僅僅從文化觀念層面進行渲染、推演和論證,就會陷入“概念拜物教”的錯誤邏輯。例如,僅依靠“天人合一”的中國觀念能使人類社會走出生態危機嗎?這顯然不是一個認識問題。正如恩格斯所說:“要實行這種調節,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22]521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只能被定位為“為解決世界難題提供有益啟示”,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思想資源和價值尺度,而并不能徹底解決世界難題,更不可能使中國超越現代化發展階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提醒我們:發展的緊迫性不允許中華民族再用道德尺度的固執和浪漫情調,企圖超歷史階段去揚棄工業文明的一切弊端而享受它的一切優秀成果[23]。我們堅決反對西方文化沙文主義,但也絕不主張走向“東方文化主導論”。任何文化危機都是社會危機的反映,并不存在純粹的文化危機。沒有任何一種外來文化能使西方社會擺脫困境,解決問題的鑰匙和手段存在于西方社會自身[12]25。因此,現代性危機根植于資本邏輯展開過程之中,呈現于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方方面面,其解決和克服只能依靠變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反思資本主義制度所確立的文化基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反思西方現代性的價值就體現為在思想層面提供思想資源和價值尺度,進而指導現實層面的社會實踐化解矛盾和重建秩序,而不可能代替現實層面的社會實踐。因此,在“兩創”過程中所進行的文化闡釋面臨著天然的價值限度和意義邊界,不能任意、無限地拔高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發展的方向具有規定性
“兩創”文化觀代表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化傳承問題的政治高度和科學態度,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為其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基調和理論底座。馬克思早就指出:“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是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的。”[24]也就是說,任何觀念、思維或者精神都是具體的、歷史的,都只能是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任何文化創造與文化創新,都不能離開社會現實的基礎。因此,在“兩創”過程中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絕不能突破當代中國社會和文化性質的價值規定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轉化發展只有立足當前的社會現實和經濟基礎,緊扣我國新的歷史方位,順應時代發展的新要求,才能在時代的風云變化中熠熠生輝。具體而言,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必須突破概念的束縛,立足新時代的社會現實和經濟基礎,浸潤到真正的“時代問題”之中,圍繞著時代需求的滿足和時代精神的塑造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對于當代中國而言,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最大的時代主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25]這種對中國式現代化社會主義性質的明確界定,為傳統文化現代闡釋指明了基本發展方向。對此,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20]340這里明確提出“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的基本要求,本質上就是為了彌合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鴻溝,限定傳統文化現代轉換的方向。所謂“與當代文化相適應”意味著傳統文化的闡釋必須充分考量當代中國文化的現實境遇、根本性質、文化精神、價值追求等因素,并在實踐中不斷激活自身的當代生命,有機融入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實踐之中。所謂“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意味著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必須充分考量當代中國正在堅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過程人民民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等因素,從而在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斷構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同時,對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任何形式的文化虛無主義和文化復古主義錯誤傾向,擺脫“激進-保守”的文化困境。
(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闡釋的方式具有特定性
近代以來,眾多先賢圍繞“中華文化的現代轉換”問題,進行了蔚為壯觀的思想探索。尤其是現代新儒家通過吸收改造西方思想的精髓對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化進行思想重構。比如熊十力受柏格森哲學的影響,綜合儒佛,改造佛家的唯識論,創立以“體用不二”為精髓的“新唯識論”;賀麟基于德國古典哲學的基本觀點對陽明心學的理論闡釋,創立了以“心物合一”為精髓的“新心學”;馮友蘭基于英美新實在主義的理論視域對宋明理學進行重新詮釋,創立了以“共殊關系”為核心的“新理學”。正如馮友蘭所揭示的:現代化的中國哲學,并不是憑空創造一個新的中國哲學,那是不可能的。新的現代化的中國哲學,只能是用近代邏輯學的成就,分析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確起來。[26]這種認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一代學人所作的主要的學術努力,從而也反映出近代中國文化所面對的最重要的時代命題:以西化中,古今貫通。毋庸置疑,現代新儒家所作的理論探索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和當代中國文化的時代建構具有重要的思想啟迪和理論借鑒意義。然而,由于他們囿于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試圖通過抽象的理論闡釋和體系化的文化重構解決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問題,從而忽視文化與經濟、政治之間的深層次關聯。在我們看來,“兩創”絕非以傳統文化為衡量標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揀選與審視,從而將馬克思主義肢解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注腳,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和觀點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審視、批判和重構,從而超越了現代新儒家的致思邏輯。正如有學者主張的,傳統文化只有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才能把其中囿于封建時代的東西剔除出去,把超越其時代的精神解放出來。[27]從而將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為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文化要素。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而言,“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我們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因此,對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應該在“結合”范式的統攝之下,朝著造就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方向而奮斗,最終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造就成為現代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以上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闡釋的三重張力并沒有囊括所有方面,但可以幫助我們深度理解“兩創”所蘊含的辯證精神,進而既可以為理論化梳理解讀習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一種思想范式,又可以為踐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傳統文化觀提供理論借鑒。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1-12-15(2).
[2]張岱年.天人五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7.
[3]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13.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99.
[5]張志宏.中國文化發展論要:從“人文化成”到“和而不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11.
[6]張岱年.文化與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85.
[7]晏輝.辯護與批判:傳統文化現代轉換的雙重邏輯[J].學術界,2020(5):43-55.
[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2.
[9]伽達默爾.詮釋學1:真理與方法[M].修訂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505.
[10]卡爾.歷史是什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23.
[11]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M].修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13.
[12]陳先達.文化自信中的傳統與當代[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13]郭齊勇.中國文化的“兩創”[J].孔學堂,2021,8(3):4-8.
[14]杜維明.否極泰來:新軸心時代的儒家資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94.
[15]何中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亟待澄清幾個模糊認識[J].理論導報,2017(4):28-30.
[16]張曙光.現代性論域及其中國話語[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351.
[17]張岱年.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M].北京:中華書局,2012:105.
[18]劉夢溪.中國文化的張力:傳統解故[M].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303.
[19]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4-09-25(2).
[20]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1]豐子義.馬克思現代性思想的當代解讀[J].中國社會科學,2005(4):53-62+206.
[2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3]衣俊卿.評現代新儒學和后現代主義思潮[J].教學與研究,1996(2):8-12+80.
[2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25-226.
[25]習近平.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8.
[26]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200.
[27]丁立群.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基本路徑[J].哲學動態,2016(6):12-19.
The Triple Internal Tension of Interpre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Two Innovations”
Li Xinchao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Gansu,China)
Abstract:Promoting the“two innovations”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consensus in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in the process of“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the interpret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nnot be arbitrarily transformed or innovated without constraints,and will inevitably be constrained by a series of tension factors. The“progressive presupposition”,“rational arrogance”,and“historical limitations”of cultural subjects result in a tense structure of“playwright”and“character”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The “uncertainty”,“mixed quality”,and“domain of meaning”of traditional texts determine the tension between“openness”and“certainty”in traditional culture;The boundary nature of the positive rol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prescribed direction of transformation,and the specific interpretation methods make the interpret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ve tension factors of“freedom”and“autonomy”. Streamlining and analyzing the tension and boundaries of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two innovations”is a necessary step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two innovations”,in order to more consciously and dialectically deal with the dilemma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creative transformation;innovative development;cultural interpretation
責任編輯:劉有祥 邱春華
收稿日期:2024 - 09 - 02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兩創’重要論述的邏輯體系與內在機理研究”(項目批準號:23CKS015)、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研究”(項目批準號:2022YB002)、2023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研究專項重大課題委托項目“大中小學‘四個自信’教育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挖掘與應用研究”(項目批準號:23ZKJFZ04)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李新潮,男,山西臨汾人,法學博士,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