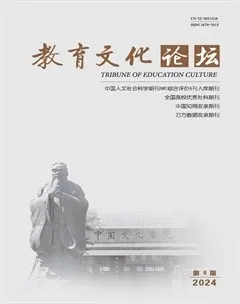兒童敘事的特征、傾向及內容
摘" 要:
兒童寫的詩歌有別于成人為兒童創作的兒童詩,它不僅直觀地反應出兒童敘事的主要特征、基本傾向和核心內容,也為了解兒童的視角,進入兒童生活世界提供了路徑。兒童的敘事在內容上具有自傳性,是他們本人的生活史以及關于過去、可能的現在、未來的反事實,構建出關于自己和家庭的檔案;在方式上具有具身性,兒童用身體、動作感受并描述世界,以己度人、推己及物的思維方式使兒童寫的詩呈現出萬物一體且有靈的特征。兒童敘事表現出三種傾向:表象即本質,韻律先于意義,敘述先于邏輯。這些傾向不僅使兒童的敘事呈現出鮮明的詩性,也反映出他們極佳的美學表現力。兒童敘事圍繞事物如何誕生、世界如何運轉、我們如何生活這三個核心內容而展開。兒童易受到暗示和引導的特征,使其詩中并非完全保留了自身的感受和表達,因而完全的兒童視角只能是一種理想化的研究方法。
關鍵詞:
兒童寫的詩;兒童敘事;兒童的視角;敘事特征;敘事傾向;敘事內容
中圖分類號:I0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615(2024)06-0089-10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4.06.010
收稿日期:2024-05-07
基金項目:
作者簡介:梁昱坤,女,甘肅蘭州人,貴州大學學報編輯部編輯。
敘事是人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文化活動,即通過語言或其他媒介敘述事情,簡言之就是講故事。美國認知心理學家、教育學家杰羅姆·S.布魯納認為:敘事是一種思維模式,是一種意義生成的承載工具。敘事有利于兒童創建一個關于世界的版本,其中兒童在心理上為自己構思一個位置,建立一個關乎個人的世界[1]。近年來,我國學者也開始關注兒童的敘事研究,但研究成果較少且集中在繪畫、游戲、閱讀以及相關課程教學等方面,關注兒童敘事能力的動態變化,以及如何通過敘事教育引導兒童在語言表達、道德認知等方面的發展,多為基于教育目的的質性研究,少有從兒童的視角出發對其敘事特征作一般性的考察,總體而言兒童敘事研究仍處于起步探索階段。兒童的思維更多表現為一種敘事性思維,敘事在幼兒認知、情感和社會發展方面具有核心作用[2]。兒童不僅能夠通過圖畫、游戲和講故事實現敘事,詩歌也是兒童敘事的重要形式。正如有論者所指出:兒童的敘事本身就是詩性敘事[3]。
詩歌作為人類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是人類抒發情感、表達意志最原始的路徑之一,所謂“思無邪”“詩以言志,故曰緣情”皆是此意。詩之形式起源于自然而健康的韻律,詩之內容則直指人類的精神世界。凡能言語者皆能言詩,兒童的詩是進入兒童生活世界的重要路徑。中國歷來就有詩教的傳統,但這一教育傳統在文化形式日漸豐富的時代已然失落,詩歌教育被并入語文教育之中,成為整個文化教育的一小部分。兒童寫的詩并未真正進入學術研究領域,甚至沒有明確的定義和概念。當談及兒童畫、兒童歌曲、兒童游戲,聽者皆能明白這些表述指向由兒童作為主體并主導的活動,它們分別對應兒童畫的畫、兒童唱的歌、兒童做的游戲,然而兒童詩或兒童文學的概念卻并不與此相同。無論在文學領域還是教育領域,“兒童詩”這一概念從誕生之初直到現在,其定義始終是成人為兒童創作的詩歌或者成人從兒童視角出發創作的詩歌,本質上仍是成人精神活動的產物。在文學領域,兒童創作的詩歌尚未被視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在概念上往往與成人創作的兒童詩混為一談;在教育領域,兒童創作的詩歌則幾乎從未被正視。因此,為與原有的“兒童詩(歌)”概念相區別,本文在論述中使用“兒童寫的詩”或“兒童的詩歌創作”這一明確的表述展開討論。
兒童寫的詩在形式上表現出新的社會現實和關于兒童的情感生活[4],但所謂的“新”是基于成人視角的判斷,對兒童來說不過是“本來如此”的事實。兒童詩與兒童寫的詩體現出兒童視角與兒童的視角的區別:兒童視角是成人由外向內地盡可能真實地重建的兒童的視角,而兒童的視角則是由內向外運用兒童自己的語言、思想和形象來表達的視角[5]1。成人研究兒童,往往是出于如何更好地教育兒童、規訓兒童的目標,卻不一定真正在乎兒童本身如何。例如:在教育學領域,兒童的繪畫長久以來與美育的目標、標準密不可分,教師關注如何通過教學使兒童掌握繪畫的技巧,使之更加符合成人審美的標準;在心理學領域,兒童的繪畫則被用來分析年齡與記憶、敘事、藝術表現的關系,或者通過作品中表現出的無意識,將其運用于問題兒童的治療,如治療語言障礙或者適應困難[6]。這些研究的出發點,表面上看是為了兒童,實則是為了使兒童達到成人為其制定的標準。兒童之為兒童,必然有其本質,了解兒童本身應該成為一種目的。正如蒙臺梭利所言:成人對于兒童仍是一知半解。“他們的身上藏著太多待解的謎題,我們必須懷著滿腔熱忱和犧牲精神踏上探索之旅,如同那些遠涉未知之境的淘金者一般,去尋找兒童靈魂中潛藏的秘鑰。”[7]
敘事是一種思考探索、分享經驗和賦予意義的方式。無論是對成年人還是對孩子來說,敘事都同樣重要。孩子世界中的見解和圖像有助于我們用孩子的眼睛來看待他們是如何思考生活和構造“另一個”世界的[8]38。正如有論者所指出:要想走進兒童生活世界,就要把握兒童的共時性,對兒童當下狀況及體驗——“兒童如是”進行描述[9]。兒童的視角總是在兒童自己的語言、思想和形象中呈現出來,代表了兒童在其生活的世界中的經驗、感知和理解[5]2。因此,孩子和成人一樣,都會用敘事來構造他們內部的心理世界,從兒童寫的詩入手,進入兒童生活世界與精神世界,是從兒童的視角探索兒童世界的路徑之一。
一、兒童敘事的一般特征
(一)敘事的自傳性
兒童發展心理學已經指出:兒童在幼兒時期即能形成自我的概念[10]381。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認為自我包含主我與客我兩個部分,其中客我在2歲左右形成[10]380-381。主我包括自我意識和個人能動性,客我包括性別、年齡等自我定義的范疇。兒童寫的詩中充滿了關于個人的敘事,他們不僅能夠講述“我”如何出生、成長,也能夠想象關于“我”的過去和未來,這使他們的敘事表現出鮮明的自傳特征。敘事的自傳性是一種對于個人生命的重新組織,創造出關于個人的前后連貫一致的故事。一方面,表現為以“我”的視角講述關于“我”的故事,展現兒童生活中的真實事件;另一方面,敘事的自傳性也不可避免地帶有關于“我”的想象與虛構。與成人的自傳性敘事往往出于一種對過去的干預和糾正不同,兒童則更多地描述關于其本人的“真實”,包括所謂的“反事實”。在兒童生活的世界中現實并不具有唯一性。“現實的世界真實地發生在過去、現在,并即將發生在未來,但是,我們并不僅僅生活在這個世界里。相反,我們生活的宇宙中存在著許多可能的世界,未來的世界可能有很多種,過去或現在的世界也可能有很多種,這些希望和想象的產物的世界即為‘反事實’。”[11]34孩子的詩中有大量關于過去、可能的現在、未來的反事實。
你問我出生前在做什么∕我答我在天上挑媽媽∕看見你了∕覺得你特別好∕想做你的兒子∕又覺得自己可能沒那個運氣∕沒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已經在你肚子里[12]12(《挑媽媽》,朱爾,8歲本文中標注的年齡均為兒童創作詩歌時的年齡。)
兒童很早便能夠大致理解關于出生的事實,但他們仍會對這一神秘的現象做出各種想象,描述一個可能的世界。“我”之所以是現在的樣子,之所以生活在現在的家庭中,原因為何?朱爾的回答是:因為我覺得媽媽特別好,所以想成為她的兒子。兒童也能夠想象自己的死亡:
一百歲我死亡了/我的兒子是老警察/我的兒子的兒子是警察/我的兒子的兒子的兒子想當警察[13]56(《一百歲我死亡了》,劉芝宇,9歲)
死亡往往意味著生命確定性的消失,其不確定性構成了哲學上關于這一話題的永恒探討。然而在孩子的詩中,不僅死亡的時間是可以確定的,死后的生活也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被預知:一代又一代的兒子都將成為警察。“警察”這一特殊的身份與職業也體現出兒童敘事的個人性與家庭性。
若對具體的兒童敘事進行分階段的考察,會發現其所記錄的內容恰好構成了本人的生活史,構建了一部關于自己和家人的檔案。如關于自己的成長:
突然發現我長胖了/但是/不用擔心/因為我同時又長高了[14]260(《我長胖了》,張澤林,8歲)
在沈熙雯的詩中,母女兩人的對話構成了其詩歌的基本形式,家庭在敘事中凸顯出重要性。
“媽媽∕坐好∕我給你∕拍張照”∕“我這么胖∕不要拍我”∕“沒事∕大海∕比你∕胖多了”[14]218(《海邊,母女倆的對話》,沈熙雯,9歲)
對話這一自然形式在兒童敘事中表現出整體傾向,這表明在兒童的敘事中存在與個人性相對應的“底層敘事”,即兒童在敘事中展現的是自己原原本本的生活世界[3]。但兒童的生活并非全是幸福與快樂,兒童寫的詩同樣記錄了生活的悲傷與殘酷。
我去爸爸家玩兒/多玩了一天/回到家/媽媽說/你這個叛徒/我很委屈/你是叛徒的媽/所以我們是一家[14]39(《叛徒》,江睿,10歲)
留守兒童、單親家庭等特殊身份形成的特殊經驗,在兒童的敘事中留下深刻的痕跡。
(二)敘事的具身性
具身認知或具身化指的是思想的身體化,即身體與心靈之間的關聯[15]。具身認知理論認為:人類的決策和行為密不可分,而人類的思想和感受與身體的感覺–運動經驗同樣緊密關聯。對于這一理論更具體的解釋是:脖子以下進行的動作會對脖子以上進行的思考造成強烈的影響[16]。葉浩生將具身認知的性質和特征總結為三個方面:身體參與認知,知覺是為了行動,意義源于身體[17]。兒童通過身體、動作感受與認識世界,這一點清楚地反映在他們的詩歌敘事當中。
1.以兒童之五感
我很多時候∕腳疼的時候∕都有像星星的感覺∕一閃一閃[14]140(《星星》,海菁,7歲)
莫里斯·梅洛-龐蒂援引塞尚的話說明人類五感之關聯:“我們看到物體的光滑、堅硬、柔軟甚至氣味。因此,我的知覺不是視覺、觸覺、聽覺材料的總和,我連同我的整個存在,以一種渾然未分的方式進行感知,我把握到事物的獨一無二的結構、獨一無二的生存方式,它同時對我的所有感官發話。”[18]在孩子的敘事中,視覺、嗅覺、聽覺、味覺、觸覺并非截然分開的領域,它們相連相通,共享路徑,最終匯合于他們的大腦,得出融合性的結論:腳疼的身體觸覺,是星星一樣“一閃一閃”的視覺感受。當4歲的孩子因結膜炎而第一次體驗滴眼藥水的經歷時,她形容藥水進入眼睛的感覺就像是大人牙膏的味道除引用公開發表的作品外,本文未注明的其他兒童敘事均來自作者的家庭教育實踐。。在這里,藥水接觸眼睛的感覺被形容為一種味覺。兒童的敘事體現出“以己度人”“萬物有靈”的傾向[3],當敘述的對象非人甚至是沒有生命的無機物時,兒童仍以身體去感受事情的發生與事物的變化:
老師在黑板上寫字/我能感覺到/黑板有些痛[13]25(《黑板》,曹宇萱,10歲)
僅僅是寫的動作,不足以讓人產生痛的感覺,兒童之所以感受到痛,其實是源于粉筆在黑板上劃過時發出的刺耳聲音。
2.以兒童之動作
春天來了∕我去小溪邊砸冰∕把春天砸得頭破血流∕直淌眼淚∕到了花開的時候∕它就把那些事兒忘了∕真正原諒了我[12]8(《原諒》,鐵頭,8歲)
土是花兒成長的家∕摸一摸∕這個字軟軟的∕春天∕這個字長出了頭發[12]27(《土》,曹世武,8歲)
如何感受春天?一個孩子的答案是“去小溪邊砸冰”,另一個孩子則選擇“摸一摸”。“砸”與“摸”的動作具有明顯的年齡特征,同時反映出孩子傾向于用身體探索世界的思維方式。“土”這個字摸起來是軟的,春天的時候還會“長出”頭發。摸是觸覺,長出頭發是視覺感受。春天不僅會長出頭發、頭破血流,也會原諒“我”傷害它的行為。事物不僅具有人的面貌,也有人的感情。兒童并非通過語言知道這一點,而是看到、聽到、感知到。兒童不僅以動作認識世界,還通過動作認識事物之間的聯系,并由此建立起自身與世界的聯系。
我想做一棵樹∕我學著一棵樹的樣子∕把腳丫踩進泥巴∕把手臂伸向天空∕哦,我發芽了∕哦,我開花了∕哦,我結果了[12]46(《我想做一棵樹》,李雨融,11歲)
樹不僅是地面上能夠看到的部分,它的“腳丫踩進泥巴”“手臂伸向天空”,如果“我”像樹一樣做出相同的動作,那么“我”就能跟樹一樣發芽、開花和結果。
兒童“萬物皆人”的思維特點,亦反映在他們關于其他客體的敘事中,形成一種“推己及物”的取向,與王陽明所謂“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不謀而合。也就是說,不僅兒童本身通過身體感知其他客體,在兒童的視角中,其他事物亦以自己的“身體”感受、對待另外的事物。
燈把黑夜∕燙了一個洞[12]14(《燈》,姜二嫚,7歲)
光是什么?是燈對黑夜行為的結果,正如香煙會將紙燙一個洞。在兒童的敘事中,萬物皆是主體,與“我”本身具有同樣的性質和地位,并不存在所謂的主客之分。“相對于主體性哲學而言,現象學認為并不存在真實客觀世界與心理主觀世界的二分,而認為只有一個世界,一個真正存在的世界,它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19]。兒童敘事中反映出的認知特點,在某種程度上與現象學的觀點具有奇妙的耦合。
二、兒童敘事的基本傾向
(一)表象即本質
我們的骨頭∕穿上了人肉∕我們一笑它就笑∕我們哭了它也哭∕我們的心里有神秘∕我們的骨頭會和我們一起生活[12]23(《骨頭》,董其端,6歲)
表象即本質,意味著對過程和邏輯的忽略。在《骨頭》一詩中,我們和骨頭始于“穿上人肉”,終于“一起生活”,中間的內容并非對肉與骨頭如何結合的過程的描述,“哭”“笑”指向一種對狀態的描述。在6歲兒童的眼中,人之所以是現在的模樣,是因為骨頭穿上了人肉。3歲的女孩看到宣傳高空墜物危險的海報上示意死亡的骷髏圖案時,認為人從高樓墜亡即意味著身體變為骨頭。兒童無法理解人體運轉的機理,卻本能地察覺到其中有“神秘”。但兒童敘事中的神秘并不導向成人所謂的神秘主義,正如這首詩最終描述的仍是樸素的結果:我們的骨頭和我們一起生活。兒童敘事的這種傾向,天然地帶有一種詩性。即便在家庭教育實踐中,也能觀察到兒童自發的詩性敘事,如4歲的女孩會說:“媽媽是香香的,寶寶也是香香的。媽媽干什么,寶寶就干什么。人生就是這樣。”這種表達并非孤例:
我基本上就是媽媽/媽媽基本上就是我/你摸我的肉/就是摸媽媽的肉/因為我是媽媽生的[20]173(《我基本上》,姜二嫚,6歲)
人生的本質正如兒童眼中所見到的,是一種對父母的傳承和復刻。但這一忽視邏輯和過程的傾向并不具有絕對性,兒童畢竟是成長中的生命,隨著年齡的增長能夠逐漸理解抽象的邏輯或者潛藏的因果關系。即便在相同的年齡階段,也有兒童能夠先于同齡人理解因果關系,并進行具有邏輯的推論:
要是笑過了頭∕你就會飛到天上去∕要想回到地面∕你必須做一件傷心事[12]70(《回到地面》,朵朵,5歲)
笑過了頭的結果是飛到天上去,因此回到地上必須要做一件傷心事,其中的邏輯固然不具有科學的意味,但能夠自圓其說。
(二)韻律先于意義
一下子∕扯開夜∕這個黑色大睡袋∕的拉鏈∕飛快地∕就像做錯事的孩子∕就是這樣∕就是這樣∕流星慌慌張張地逃跑了∕黎明從拉開了的睡袋中伸出頭來∕沒看見什么∕縮回腦袋∕睡袋關上了拉鏈沒拉開∕沒拉開∕沒拉開[12]29(《黎明》,易海貝,12歲)
兒童的詩歌在形式上經常表現出重復,如《黎明》一詩中“就像做錯事的孩子∕就是這樣∕就是這樣”“拉鏈沒拉開/沒拉開/沒拉開”。成人有意識地使用重復的手法,往往是為了強調某種感情或者造成某種效果。但對并未掌握文學理論的兒童而言,重復首先表現為一種節奏和韻律,這種韻律本身就是一種意義。“在嬰幼兒的世界里,人類的話語是有旋律和節奏的,長大后才認為話語是有指示性和邏輯性的。”[21]94嬰幼兒時期,成人為了達到使幼兒盡快入睡的目的,會在哄睡時哼唱句法單一但在結構上循環往復的兒歌或童謠,可以說兒童與詩最初的接觸即始于節奏與韻律。布萊恩·薩頓-史密斯在論述兒童的敘事時提到一個5歲男孩講述的內容:“然后這個從前死了∕然后這個結局吃了這個結局∕這個結局∕這個結局∕然后這個結局死了∕然后這個結局死了∕然后這個結局死了……這個結局有一個結局∕這個結局∕這個結局。”[21]99重復帶來的韻律,讓兒童的詩歌體現出一種意猶未盡的情緒,很難說清楚其中有怎樣的深意。作為詩歌形式的韻律自有其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它與詩歌想要傳達的意義相比具有獨立性和優先性。然而,無論孩子所使用的韻律是出自本能還是對成人的模仿,其中的意義始終來自兒童的心靈,反映出存在于他們天性中極佳的美學表現力。
(三)敘述先于邏輯
今天天氣真不好∕一天都沒出太陽∕我的金魚在水里全淹死了∕我的小鳥飛到天上給摔死了∕我那只九歲的母獅子被兩個月的小白兔給吃了∕我那兩只企鵝和北極熊被凍死了∕我那只猴子蕩秋千時不小心掉到天上撞上云朵死了∕我的飛機在零下給化了∕媽媽的手機一夜都在充米,結果沒米了∕唉,今天可真是開心的一天啊[12]126(《今天天氣真不好》,劉海荃,9歲)
敘事心理學家認為:成人互動的主要類別是“閱讀或詳述文本”,而孩子的互動方式中,最常見的是“玩笑式的主題轉換”[21]89。“玩笑”或“搞笑”在孩子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兒童敘事的內容和結構,就其方式而言與成年人差別很大。兒童對想象世界的描述更多是出于玩耍或游戲的目的,而不是要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他們的敘事不一定遵守某些規則或講故事的“普遍形式”,即“有一個開頭,確定一種期待,中間使其復雜化,最后滿足這種期待或解決問題”的形式[8]39。詩歌對他們而言亦是游戲的一種形式:“寫實就像是一場游戲,而我,就是那個參與的人,偶爾想要玩一下,就寫下一首”[14]70,“寫詩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是一件自由的事,可以讓我天馬行空地想象”[14]259 ,甚至是“我喜歡這樣說,不管它是不是詩”[14]199。因此,在兒童寫的詩中,詩歌的結束往往并不是出于敘事結構的需要,而是心靈獲得滿足之處。游戲的性質也使孩子寫的詩中經常出現反復的主題,他們“癡迷于某種特殊的,也許是失衡的人類行為”[21]92。如在另一首關于開心的詩中,孩子這樣寫道:
和姐姐走在路上∕突然特別開心∕好想把姐姐扔到樹上(《開心》,姜二嫚,11歲)[20]43
對于兒童來說,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游戲都可以進行。在充滿幻境與想象的游戲世界里,孩子可以毫不費力地隨意出入[22]。正如英國教育家尼爾認為:游戲在童年早期是第一位的[23]。
三、兒童敘事的主要內容
兒童不僅比成人所認為的學得更多,而且幻想得更多、關心得更多、經歷得更多。在某種意義上,年幼的孩子實際上比成人更加聰明,更富有想象力,更會關心他人,甚至更為敏感。在兒童的敘事中,充滿著成人不曾注意到的經驗和感受。從兒童敘事的特征和傾向能夠看出:兒童感知世界的方式是發散式、流動式的,他們并不會固定地僅體驗周圍世界的某個部分,而是同時以自己的身體生動地體驗著所有事物,就像佛陀一樣,是身在斗室、心在四野的旅行者[11]224。若成人認為他們對于世界的描述已經窮盡,那么重新認識和了解兒童則可以為之打開全新的大門。
(一)事物如何誕生
兒童關注事物如何產生:宇宙、星星、月亮,這些東西是怎樣出現的?孩子的詩中有大量的想象,比如關于星月的由來:
太陽是個火球/她吐出火苗蒸干了銀河/河里的魚兒跳上岸/變成了星星。在夜里/許多流星坐滑梯/有些滑走了/有些困住了/就這樣/許多困住的星星擠呀擠/慢慢地/他們變成了月亮[13]29(《擠呀擠》,饒堃鉅,10歲)
在詩人顧城12歲寫下的詩中,星星和月亮是這樣來的:
樹枝想去撕裂天空/但卻只戳了幾個微小的窟窿/它透出天外的光亮/人們把它叫做月亮和星星[12]17。
星星既可以是河里的魚兒變的,也是來自天外的光亮。又如關于宇宙的誕生:
宇宙像一個沒有點著的煙花∕沒人愿意給他一點火光∕他生氣了 憤怒了∕把自己點燃了∕宇宙煙花爆炸了∕宇宙誕生了[13]52(《宇宙的誕生》,黃柳,10歲)[7]
年紀的增長和來自學校、家庭、社會的教育終會讓兒童從科學的角度理解事物產生的原因,但這并不代表他們關于事物起源的敘事就不重要。相反,成人能夠從中了解兒童如何構建世界以及萬物之間的關聯。葉嘉瑩回憶兒時學詩的經歷時說:“小時候讀詩,我就用我的想象,把它們都做成一個個故事,就藏在我的腦子里。”[24]詩與想象密不可分,兒童敘事的詩性不僅表現在詩歌創作的形式與內容之中,也表現在以故事記憶詩、表達詩、理解詩的思維方式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詩的功能對于兒童而言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言事”的需要,而非古典詩教所注重的“言志”或“抒情”傳統。兒童的詩歌固然也是他們抒發情感的媒介,但這種情感的抒發是在敘事的過程中自然地體現出來:
我發現/有好多顏色/都還沒有命名/還有好多聲音/也沒有命名/甚至/有好多字/還根本沒有發明出來[20]8(《我發現(之一)》,姜二嫚,7歲)
“我發現”這一兒童敘述中經常出現的表達,既表現出認識新事物的驚訝與新奇,也突出了發現的主體“我”之驕傲與喜悅。兒童感知到的世界遠比成人更加廣闊、深邃,他們不僅看得到已經存在的事物,也知道還有好多字根本沒發明出來。
(二)世界如何運轉
兒童看待世界的方式與成人不同,他們有自己看待世界、社會與自然的方式,并產生相應的理念[25]。兒童是天生的哲學家,而詩性的敘事方式又使他們成為天生的詩人。兒童描述世界的方式并非是通過物理公式或者數學運算,而是通過兒童的思考工具:一是身體以及動作:
我揮揮手/就有很多手/我跑步/就有很多腳/小狗朝我搖尾巴/就有很多尾巴/然后/我打秋千/就有很多我[12]52(《很多》,姜馨賀,4歲)
二是想象以及虛構:
大地寶寶/是天空寫給/莊稼的信件/大地寶寶是/太陽和月亮的/小球場/每到黃昏/太陽和月亮/都要進行一場激烈的比賽[26]33(《比賽》,張璘,11歲)
“我”與世界是一體的,我的動作使世界發生變化,我與世界的互動,其結果仍作用于“我”:我打秋千/就有很多我;而大地上光線和顏色的變化,是因為太陽和月亮的比賽:
在黃河入海口/黃河與大海/被夕陽/一刀/兩斷(《一刀兩斷》,黃豆逗,9歲)[26]15
自然界中事物的分界源于自然的力量,而人類的社會生活也被人類的創造物所區隔:
我和媽媽之間/隔著被子/我的房間和爸爸的房間之間/隔著客廳/家和學校之間/隔著道路、店鋪、樹木/我和路之間/隔著鞋子/寧德和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之間/隔著飛機……[14]25(《隔》,游若昕,7歲)
正如兒童哲學家所指出的:兒童并非用事實和規律來認識世界,他們眼中的世界是具有他們個人興趣的個人世界,其主要特征是感情和同情[27]。兒童敘事的重要不在于其是否正確,而是其中的啟發意義:成人可以借此了解他們如何努力理解這個世界,以及兒童如何確定他們在世界中的位置。意義生產作為一種結果,貫穿于兒童敘事的文學作品中[28]。
(三)我們如何生活
兒童的詩歌中充滿對生活的觀察和思考,這種觀察并非簡單的記錄,而是凸顯出共性與個性,以及社會的或生理的區別:
爺爺小時候/流行放牛、放羊/爸爸小時候/流行玩打仗游戲/沖啊/噠噠噠/我們現在/流行養倉鼠/養烏龜/我們班上/男生大都養烏龜/女生大都養倉鼠/而我/既養倉鼠/也養烏龜[14]21(《流行》,游若昕,11歲)
但生活并非總能如愿,兒童對生活的變故與“不可承受之重”更加敏感:
小時候/你說/月亮是太陽的孩子/后來/你說/星星是天空的眼淚/上學了/你說/想你想到心痛的時候就會走走/因為/你說/走著走著就累了/想著想著就忘了[13]40(《你說》,洪婉仟,13歲)
死亡不僅意味著身體的靜止,也意味著能與逝去的親人相見:
奶奶帶我去看外婆最后一面/那天我哭了/像被大火燒壞了眼睛/但/外婆這次沒有哄我[13]37(《清明》,粟楊欣,10歲)
你的籠子還在淘寶的路上/可你卻上了天堂/去見我的爺爺[14]31(《致小皮》,游若昕,11歲)
兒童的敘事中不僅有關于自身及家庭過去、現在、未來的描述與想象,也有關于人類整體生存的思考:
在大家的/掌聲中/一個人/走了進去/不知過了/幾千年/幾萬年/這個人/再也沒有/走出來[12]40(《黑森林》,游若昕,9歲)
“黑森林”仿佛人類生存的隱喻,人在掌聲中進入,最終消失在其中,體現出無盡的哲學遐思。兒童善于用想象虛構一種結論或邏輯,對于他們無法解釋的事情也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媽媽,你看星星/它是眼睛人/在傳說中才有的,你沒有聽說過/我是在一本書上看到的……[12]78(《眼睛人》,李彤遙口述,3歲)
兒童不能洞悉世界的全部奧秘,他們深知這一點,才會有沒完沒了關于“為什么”和“后來呢”的追問。然而在他們眼中,成人亦非無所不知、全知全能。星星是“在傳說中才有的”,而媽媽是不知道的。骨頭為什么和“我們”一起生活?因為“我們”的心里有神秘,然而知曉秘密的人卻是兒童自己。在他們看來,世界的秘密最終仍掌握在他們手中。如《我有千萬種語言》《秘密》:
媽媽/你都不懂/你也不相信/我會玩具的語言/我會天鵝的語言/我會蹦蹦床的語言/我會外星人的語言/我也會自言自語/我還有秘密的語言/那是只能在心里說的話/我對誰也不說……[26]30(《我有千萬種語言》,魯詩語,5歲)
有一只大肚子鳥/它的肚子很大很大/因為它把很多想說的話都憋在肚子里/這是個秘密/誰也不知道[13]42(《秘密》,向雅婕,9歲)
《秘密》的作者說:“我總是有很多話想說,卻又總是往肚子里吞……一次,我在無意間發現鵪鶉有著大大的肚子。我想,它是不是也有很多話憋在肚子里沒有說,所以肚子才會那么大。那樣的話,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秘密了。”[13]42
四、結語
兒童有一百種語言,一百個兒童就有一百顆童心及其存在的世界。兒童的詩本應引起文學、教育學、心理學等諸多領域的關注與討論,但事實并非如此。究其原因,一方面,如本文開篇所述,在文學領域兒童身為作者的創作并不在傳統兒童文學的討論范圍內;另一方面,教育學領域對兒童敘事的關注則多強調教育的目標和兒童的發展,對兒童正在經歷的、直觀的“生活世界”缺乏尊重和理解。兒童不僅是天生的哲學家,亦是天生的詩人,兒童寫的詩是了解兒童、認識兒童的重要途徑。然而,從兒童寫的詩中考察兒童敘事,即便對兒童的視角有所發現,也不得不依靠業已成型的觀念、價值進行描述,遑論兒童的詩歌還會經過成人的選擇、編排乃至修改。因此,完全的兒童視角仍然是一種理想化的研究方法, 成人可以無限接近卻無法抵達兒童的世界。但正如有論者指出:對于本質問題的追尋將賦予我們改變的力量,指引我們找尋有關童年本質的最佳答案,更深入地去了解童年、探索童年的秘密和價值[29]。
參考文獻:
范燕瑩.布魯納[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289.
[2]" 楊寧.敘事:幼兒教育的基本途徑[J].學前教育研究,2005(Z1): 14-17.
[3]" 錢慧.論兒童敘事及其繪畫載體[J].陜西學前師范學院學報, 2019(2): 12-15+45.
[4]" 吳曉,田麗君. 論當前兒童詩的審美趨向[J].浙江學刊, 2005(3): 215-219.
[5]" 迪翁·薩默爾,英格瑞德·普拉姆林·塞繆爾森,卡斯滕·亨代德.兒童視角與兒童的視角:理論與實踐[M].杜繼剛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
[6]" 徐靜茹.看畫識童心:兒童繪畫心理解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20.
[7]" 蒙臺梭利.童年的秘密[M].李依臻,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8.
[8]" 蘇珊·賴特. 繪畫,開啟兒童創造力[M].謝岫岫,魏旭輝,遲劍鋒,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9]" 李旭,梁文昕,康佳琦.兒童生活世界的“蒙蔽”與“敞亮”——繪本《公主的月亮》中兒童視角的方法進路[J].教育文化論壇,2022(4):107-114.
[10]瓊·利特菲爾德·庫克,格雷格·庫克.兒童發展心理學[M].和靜,張益菲,譯.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11]艾莉森·高普尼克.孩子如何思考[M].楊彥捷,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12]果麥.孩子們的詩[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
[13]“是光”的孩子們.大山里的小詩人[M].果麥,編.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0.
[14]馬非.孩子們自己寫的詩[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
[15]露特·E.施瓦茨,弗里德黑爾姆·施瓦茨.具身認知[M].李雪,余萍,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23.
[16]西恩·貝洛克.具身認知:身體如何影響思維和行為[M].李盼,譯. 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3.
[17]葉浩生.“具身”涵義的理論辨析 [J]. 心理學報, 2014 (7): 1032-1042.
[18]莫里斯·梅洛-龐蒂. 梅洛-龐蒂文集:第4卷:意義與無意義[M].張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19]黃進,趙奇.“兒童的視角”:歷史生成與方法論探尋[J].學前教育研究, 2020(8): 3-11.
[20]姜二嫚.姜二嫚的詩[M].小里予,繪. 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
[21]西奧多·R·薩賓.敘事心理學:人類行為的故事性[M].何吳明,舒躍育,李繼波,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22]勞倫斯·科恩.游戲力:笑聲,激活孩子天性中的合作與勇氣[M].李巖,譯.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
[23]龔兵,李慧萍.兒童的自我教育:百年夏山的價值探尋[J].教育文化論壇, 2022(4): 9-15.
[24]陳曉耘. 葉嘉瑩:詩不遠人" 終身為教 [J].中國基礎教育, 2024(3): 6-10.
[25]成尚榮.兒童立場[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26]張心馨.孩子選孩子們的詩[M].銀川:陽光出版社,2020.
[27]吳國平.課程中的兒童哲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27.
[28]帕特里特·M·庫珀.小小孩都需要的教室[M].孫莉莉,譯.昆明:云南晨光出版社,2021.
[29]羅瑤.何謂遵循兒童天性的教育?——基于裴斯泰洛齊的兒童天性觀解讀[J].教育文化論壇, 2023(1): 27-36.
Characteristics, Tendencies, and Content of Children's Narratives: a Study Based on Children Poetry Creation
LIANG Yuku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China, 550025)
Abstract:
Children poetry written by children differs from children poetry created by adults for children. It not only vividly reflect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basic trends, and core content of children's narratives but also provides a pathway to understand the children's perspective and enter their world of life. Children's narratives are characterized by autobiographical content, encompassing their personal life history and counterfactual narratives about the past, potential present, and future, constructing archives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In terms of approach, children's narratives exhibit embodiment because they perceive and describ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bodies and actions, utilizing a thought process of self-comparison, self-projection, and anthropomorphism, presenting their poetry with a holistic and spirited feature. Children's narratives demonstrate three tendencies: appearance equals to essence, rhythm precedes meaning, and narration precedes logic. These tendencies not only endow children's narratives with a distinctive poetic quality but also reflect their excellent aesthetic expression. Children's narratives revolve around three core themes: how things come into being, how the world operates, and how we live. Children are prone to be implied and guided, which leads to the result that their poetry does not entirely preserve their own feelings and expressions, thus a fully authentic children's perspective can only be an idealized research approach.
Key words:
children poetry; children's narratives; children's perspectiv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narrative tendency; narrative content
(責任編輯:楊" 波" 郭" 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