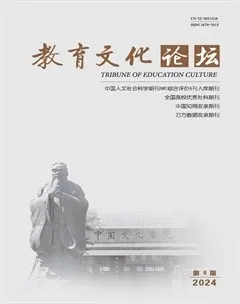集體記憶建構:青少年學生公共關懷的興發路徑及其優化
摘" 要:
個體成員對所屬共同體的公共關懷是共同體存續與發展的必要條件。處于人生“拔節孕穗期”的青少年學生的公共關懷狀況,直接關系中華民族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命運。學校是培養青少年學生思想品德的主陣地,理應承擔起培育青少年學生公共關懷的重任。公共關懷是一種兼具公共性、實踐性、關系性和向善性的態度和行為。就此而言,集體記憶的建構是不容忽視的公共關懷促發因素,它賦予個體成員特定的身份,為個體成員提供踐行公共關懷的體驗情境與實踐機會,從而實現共同體的凝聚和團結。這為學校教育興發青少年學生的公共關懷提供了新思路。時下,集體記憶異構,模糊的敘事文本框架、隨意化的敘事主體和繁蕪的敘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解構了公共關懷的生發基礎,強烈沖擊著學校對學生公共關懷的培育。對此,學校教育需要從把關敘事文本框架的內容與基調、消除敘事主體的隨意性、規范敘事方式等方面采取措施,更好地實現集體記憶建構對青少年學生公共關懷的興發價值。
關鍵詞:
青少年學生;集體記憶;建構框架;公共關懷;興發路徑
中圖分類號:G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615(2024)06-0078-11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4.06.009
收稿日期:" 2024-02-06
基金項目:
作者簡介:
蔣紅斌,女,湖南雙峰人,博士,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面對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基于促進民族團結和世界和諧的目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兩大重要命題。他強調:共同體的構建就是人們在共同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1]。個體必須具有將自身與其所屬共同體聯結起來的興趣與情懷,才能將共同體當成行為目標,并為之付出努力。這種興趣和情懷就是公共關懷。共同體成員的公共關懷,是共同體建設不可或缺的基礎,深刻影響著共同體的建設。人是一種社會性存在,每個個體在社會中都歸屬于至少一個共同體。在特定時間與情境下,個體一定是作為某個共同體的成員而存在,也正是在對其所屬共同體及共同體中其他成員的公共關懷中,個體才能獲得清晰的自我認知和準確的自我定位,從而獲得自我發展的可靠依憑。因此,個體成員的公共關懷既是共同體存續與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個體自身的存在需要與價值體現,具備良好的公共關懷素質已然成為國家對當代公民的基本要求。青少年學生正處于人生的“拔節孕穗期”,他們的公共關懷素質不僅影響自身的發展,更關涉中華民族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命運。正因如此,教育部在2022年專門將加強學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列為工作重點之一,強調以增進共同性為方向[2],并在《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代中小學思政課建設的意見》中再次強調要落實相關課程內容,有針對性地進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3]。這些無疑都包含著對培育與提升學生公共關懷素質的重視。
每當社會出現道德缺陷時,人們總是會將其與學校教育聯系起來,并寄希望于學校,盼望學校能加強、補充學生所接受的抑或沒有接受的教育。時下,社會公共關懷狀況堪憂,青少年學生的公共關懷素質亦不容樂觀。學校是培養青少年思想品德的主陣地,理應擔此重任,加強對青少年學生公共關懷情意與實踐能力的培育。那么,究竟是什么導致了公共關懷的失落?表面看來,社會環境的復雜變化難辭其咎。然而,社會環境必須通過必要的中介和路徑才能對個人產生影響。在所有的中介和路徑中,集體記憶的建構是不容忽視的一個方面。不同的社會環境因素不斷充斥到公共關懷集體記憶之中,或興發公共關懷情感與實踐,或解構人們的公共關懷情懷,誤導人們的公共關懷行為。厘清這一點,重視對集體記憶特別是公共關懷集體記憶的建構,無疑是紓解當前青少年學生公共關懷困境的新思路。
一、集體記憶建構:興發青少年學生公共關懷的可能路徑
簡而言之,集體記憶即關于集體的記憶,是集體成員通過共同活動形成的關于集體、旨在發展集體的共同意識的過程與結果。正如涂爾干所指出:集體不是個人的簡單集合,它擁有一種與其成員的個體特征不同的特征和靈魂,有著自己特有的思維方式、感覺方式和行動方式,有一種超越個人的特殊同一性,因而具有比個體更大更高的價值性和更豐富多彩的要求[4]。集體既需要其成員的公共關懷,又能成為一種仁愛的保護力量,反過來為其成員提供庇護。共同體在本質上就是人們在共同條件下結成的集體,因此,“共同體”與“集體”在概念上是同質的,其核心要義就是個體成員聚合以后產生的一種精神共同性和同一性。如此,集體記憶的建構其實就是賦予個體成員特定的身份,促使個體成員形成共同性認同,從而實現共同體凝聚和團結的過程和結果。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個體成員逐漸產生和形成了基本的公共關懷品質。也因此,集體記憶建構能夠成為興發公共關懷情懷、促生公共關懷行為的一種可能路徑。
(一)公共關懷的時代構架
1.公共關懷的時代含義
公共關懷并不是一個新話題,學者們已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廣泛分析,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公共關懷是以利他的方式關心公共利益的態度和行為,即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時期,社會成員在公共生活中對人們共同生活的行為準則、規范的主觀認同以及自覺體現于客觀行動上的遵守、執行[5]。這一概念界定強調公共關懷關乎公共生活,具有“公共善”性質,且是一種情感與實踐的結合。當今時代,人們的利益關聯越來越緊密,人際互動的理性成分越來越高,關系性特征凸顯。因此,公共關懷的內涵與外延都有了新的發展,既包括共同體成員對所屬共同體公共秩序的遵守、公共價值的認同和對公共事務、公共利益的關注和維護,也包括個體對共同體其他成員的事務與利益的關注和維護。關懷的對象不再限于共同體,而是同時包括了共同體內的每一個成員,是關懷者與被關懷者共同構成的關懷關系,以公共善為目的。公共關懷內化于個體是一種態度和情懷,外顯于實踐則為一種行為體現。這一界定同樣適用于青少年學生,只不過他們的關懷發生場域以學校為主,在一定程度上輻射家庭與社會公共生活。從以上界定可知,公共關懷至少包括了公共性、實踐性、關系性和向善性等時代要素。
公共性是公共關懷的基礎要素,一是指公共關懷源于公共生活的需要,為了公共生活的可能,是成員之間共生共享、共同發展的黏合劑;二是指公共關懷最終關涉的不是單個個體的利益——既不是“我”的個人利益,也不是“我”以外的任何單個個體的利益,而是對共同體的共同事務和利益的認同與維護。那些看似對單個個體的關懷,實則具有公共意義,構成公共關懷。正所謂“德福一致”,當人人相善其群時,真正的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便得以實現。
實踐性是公共關懷的關鍵要素。單純的理性思量或情感牽動既不能實現對他者利益的維護,也無法實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和對公共利益的關懷。公共關懷終究要落實到具體的實踐行動中才具有現實價值,個體的公共關懷情意也只有通過具體實踐行為才能得以體現,否則就會淪為紙上談兵式的形式主義,或者是葉公好龍式的虛假關懷。
關系性是公共關懷的核心要素,也是當前社會背景下凸顯的特性,對公共關懷的有效性和持續性至關重要。內爾·諾丁斯特別強調:在本質上,關懷“意味著一種關系,它最基本的表現形式是兩個人之間的一種連接或接觸。兩個人中,一方付出關心,另一方接受關心。……任何一方出現問題,關心關系就會遭到破壞”[6]。公共關懷更是如此,是個體在公共生活中與他人交往時,一方發出關懷信號與行動,另一方真實感受到關懷并給予相應的回應,從而主動建構的雙向良好互動關系。共同體成員和共同體之間同樣如此,個體成員通過公共關懷維護共同體的發展,共同體則為其成員提供歸屬與庇護。單向關懷通常“受外在環境和因素的影響比較大,也有可能形成被關懷者的主動依賴,關懷者的主觀強制,并以關懷的名義越界和越權”[7],因而可能不是真正的關懷,也難以持久。當下,陌生人社會取代熟人社會,血緣親情締結的人身依附紐帶越來越松弛,公共關懷的關系性特征更加凸顯。在共同體中,將成員聯結起來的正是由彼此相互關懷形成的共同感。
向善性是公共關懷的價值底線要素。一方面,這意味著公共關懷是一種倫理關懷,具有性質上的向善性;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公共關懷以公共善的實現為價值歸依,具有目的的向善性。內爾·諾丁斯將關懷分為自然關懷和倫理關懷,自然關懷是不需要做出道德努力的關懷,幾乎是人的天性,倫理關懷則不同,是以關懷者的道德為基礎、需要做出道德努力的關懷[8]。公共關懷的利他屬性決定了它是一種典型的倫理關懷,離不開關懷主體的道德支撐。而且,公共關懷不僅指向公共善,以增進公共福祉為優先追求,其本身也是公共善的組成部分。
2.公共關懷的興發機制
公共關懷既是一種對共同體及其成員的關心、關注、愛護的情懷,又是一種將之付諸實踐的行為品性,其興發離不開必要的認知基礎、情感驅力和現實觸發條件。
公共關懷的興發以公共認同為認知基礎。公共認同即個體與其所屬共同體之間“相互認可的一種主觀性態度、認知與情感依附”[9],既包括個體對自己作為共同體成員的身份與角色的確認,對公共規則和公共事務的理解與支持,以及對增進公共福祉的內在把握,也包括共同體對其成員特定身份的賦予與承認。這種雙向認同使個體與共同體中其他成員產生情感聯系,進而為生發公共關懷行為提供了必要的認知條件。它讓共同體成員意識到“自己的利益與社會的繁榮休戚相關,他的幸福或者生命的維持,都取決于這個社會的秩序和繁榮能否保持。因此,種種原因使他對任何有損于社會的事情都懷著一種憎恨之情,并且愿意用一切方法去阻止這個令人痛恨和可怕的事情發生”[10]。
對共同體的歸屬感及由此而生的責任感,是公共關懷生發的情感驅力。歸屬感是個體對所屬群體及其從屬關系的劃定和維系的心理表現,是個體感覺被團體認可與接納時的一種感受。責任感則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以集體為優先的情感體驗與感受。“一個生命的存活繁衍,是需要有一個生命系統來支撐,……,比如說,一只螞蚱需要一塊草地,一只青蛙需要一片池塘”[11]。人更是一種需要歸屬感的生物,歸屬于至少一個自己能愉悅地認同的共同體,幾乎已成為人的一種自然需求。如果能獲得一種雙向認同,則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有了公共認同和歸屬感,人便成為“相互義務的對象”,進而產生一種自覺維護共同體的責任感,這便為公共關懷的發生提供了強大的內源性動力。反過來,公共關懷又正是歸屬感得以獲取和滿足的條件。
特定情境場域的出現,是公共關懷實踐的現實觸發點。公共關懷是基于具體情境的道德自愿,只有在真實的交互境遇中,關懷行動才可能發生,關懷關系才能建立。具體情境和場域的出現,使得公共關懷成為一種可操作性品質,這是公共關懷發生的現實條件。經驗亦證明:公共關懷一定是發生于具體情境之中,是人們在特定情境下所懷有的特定之情與作出的特定之行。在不同情境下,關懷者的關懷表達必有不同,并不存在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模板。
(二)集體記憶的建構對公共關懷的興發
1.集體記憶及其建構框架
人們對集體記憶的探討始于20 世紀初。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于1925 年提出了集體記憶理論。他認為,集體記憶是集體中的成員基于當下公共利益與需求,對所在集體的共同經歷進行回憶與重構,最終形成共同價值觀念的過程和結果,“在本質上是立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12]59。集體記憶的內容是某種社會內容的凝固,借助各種媒介保存和流傳,在特定社會群體內共享共存,起著溝通個體與集體,聯系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作用。
莫里斯·哈布瓦赫強調:集體記憶的建構必須置于一定的社會框架之內才能實現。特定的社會框架決定了哪些材料能進入集體記憶系統以及如何進入集體記憶系統,構成了集體記憶的材料及其演化方向。“在每一個時代,這個意象都是與社會的主導思想相一致的”[12]71,只有那些符合現實需要的質料,才會被篩選出來,成為集體記憶的源泉,同時也為集體記憶的建構劃定邊界。當然,這一社會框架絕不只是靜態的記憶素材,“因為我的記憶對我來說是‘外在喚起’的。我生活其中的群體、社會以及時代精神氛圍,能否提供給我喚起、重建、敘述記憶的方法,是否鼓勵我進行某種特定形式的回憶,才是至關重要的。”[13]也就是說,集體記憶的建構框架實際上可拆解為三個方面,它們彼此結合,共同完成對集體記憶的建構:一是哪些材料能納入集體記憶,這決定著集體記憶的內容和價值導向,可稱其為敘事文本框架;二是這些材料由誰來決定與傳承,這是建構集體記憶的人物中介,可稱其為敘事主體;三是敘事主體通過何種方式完成對敘事文本的傳承和傳播,可稱其為敘事方式。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敘事文本框架的確定、敘事主體的產生以及敘事方式的選擇都有不同。
2.集體記憶建構興發公共關懷的基本機制
集體記憶的建構以群體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經歷為基礎,在成員之間的交互活動中完成,其本身及其建構過程“是凝聚社會共識、獲取集體認同、培育價值導向、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途徑和有效形式”[14],這與公共關懷的生發具有很強的機制共契,以公共關懷為素材的集體記憶及其建構過程更是公共關懷的直接促發因素。
首先,集體記憶建構過程在生成公共認同和形成良好公共關系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專門的公共關懷集體記憶建構更是如此,這為公共關懷的生發提供了良好的基礎。集體記憶本身就是關于共同體的記憶,是公共認同的核心,其建構過程也是公共認同形成的過程和公共性、關系性的生成過程。在集體記憶建構活動中,共同體通過吸納等方式賦予其成員特定的身份,并在記憶的反復重現中確證和固化這一身份。特定身份的確證與固化,使得共同體成員將自己與共同體緊密聯結起來,成員之間也逐步形成共同的理想與信念:自覺認可公共價值,產生公共認同,結成良好關系。在集體記憶的不斷復現中,這種認同被不斷激發和強化,由此生成的關系也被不斷鞏固,成為良好的興發公共關懷情懷與激發公共關懷實踐的認知基礎與環境條件。
其次,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是歸屬感與責任感的產生過程,為公共關懷的生發提供情感驅力。集體記憶天然地具有滿足個體歸屬感、促生責任感的優勢。在集體記憶建構過程中,個體深刻感受到彼此之間的緊密團結,感覺到有一種來自共同體的情感和力量將自己包裹其中,為自己提供精神定位和行為方向。這種體會使其對共同體的信任感和依賴感油然而生,形成歸屬感,并產生自覺維護共同體的責任感。在集體記憶的反復重現中,這些情感與意識被反復喚起與強化,成為強大的公共關懷情感驅力。
最后,集體記憶建構過程還為公共關懷提供情境體驗與實踐機會,實現對公共關懷的觸發。莫里斯·哈布瓦赫認為:“進行記憶的是個體,而不是群體或機構,但是,這些植根在特定群體情境中的個體,也是利用這個情境去記憶或再現過去的。”[12]40事實上,記憶總是依賴于一定的情境,正是在各種具體情境中,共同體成員通過敘事的一致實現對集體記憶的建構。這一過程通常是通過各種具象的儀式慶典或其他形式的共同活動營造的特殊情境氛圍而完成,個體只有參與到這些互動中才能獲得集體記憶。加之集體記憶本身就是關于共同體的記憶,集體成員切身參與的建構過程本身就具有公共關懷性質。因此,集體記憶及其建構過程既為共同體成員的公共關懷提供了切實的實踐場域與體驗,其本身也是公共關懷的動態實踐過程。
集體記憶與公共關懷的共契機制分析同樣適用于青少年學生,為培養與提高學生的公共關懷品質提供了新的思路。只不過對于青少年學生來說,他們的心智尚處于成長過程中,他們的生活具有特殊性,關涉的共同體主要是班級與學校,其公共關懷對象也主要是班級、學校及其成員。但青少年學生走出學校時,需要承擔一定的社會公共責任,需要有超出學校范圍的公共關懷情懷與行為。因而,在以建構集體記憶為路徑培養他們的公共關懷情懷與實踐行為時,在記憶框架的選擇及其教育應用方面都要考慮針對性和適應性。
二、時下集體記憶的異構對公共關懷的銷蝕:青少年學生公共關懷培育面臨的新困境
公共關懷對個體幸福和公共福祉都非常重要。當下,社會公共關懷狀況堪憂,公共性隱退、關懷關系脆弱、公共關懷實踐缺場和公共善乏弱等現象比比皆是。這些現象在青少年學生群體中也有相應的表現,他們在公共關懷方面無知無行、有知不行等現象隨處可見,且年級越高公共關懷越淡漠,冷漠甚至不文明行為越嚴重。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集體記憶特別是公共關懷集體記憶的異構,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這也是學校公共關懷教育面臨的新困境。
(一)模糊的集體記憶敘事文本框架對公共關懷生發基礎的消解
在應然意義上,集體記憶的敘事文本可以為公共關懷的形成提供認知基礎和價值引導。但是,“沒有記憶能夠在生活于社會中的人們用來確定和恢復其記憶的框架之外存在”[12]76。時下,我國已逐漸進入“陌生人社會”,傳統“熟人社會”里緊湊的圈層關系和共同精神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競爭和個體化的盛行。“人們視陌生者為一種不相關的存在……陌生人被分配在不被關心的范圍。”[15]在陌生人社會里,人們的公共關懷行為承擔著巨大的道德風險,如幫助摔倒的老人反被訛,特殊時期好心分享藥品反被毆打辱罵等,都是令人痛心的例證。如此情形下,集體記憶的建構框架受到強烈沖擊,建構集體記憶的材料和價值導向也隨之改變。加之創傷性事件往往更容易讓人“長記性”,進而造成阻礙性集體記憶。這種情形必然會造成公共認同危機和歸屬感、責任感的缺位,導致公共性迷惘,最終阻擋關懷行為的發生。于是,許多情況下,“個體對公共領域中的公共角色持否定或消極的態度,他們傾向于以逃避公共責任的方式來追求自我中心的身份認同以及私人利益的滿足”[16],對公共利益漠不關心,對他人充滿懷疑甚至心懷警惕。“精致利己”“道德冷漠”比比皆是,不知關懷誰、不知如何關懷的尷尬時常發生。公共關懷的不足反過來又加劇人際冷漠,對集體記憶的敘事文本框架產生不利影響,形成惡性循環。
身處學校“小社會”的學生,激烈的升學競爭消解了他們本就脆弱且不成熟的公共情懷。雖然學校教育中的教育內容和方式都是經過篩選后確定的,但學校不是一座孤島,信息時代學生獲取信息的渠道與速度已難以控制,社會消極事件不可能被阻攔于校門外。況且,從心理視角而言,越新奇的、越不被允許的事物反而越能勾起學生的好奇心。這些價值模糊的敘事框架極易侵入學生的心靈,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
(二)隨意化的集體記憶敘事主體對公共關懷倫理底線的挑戰
敘事主體堪稱集體記憶建構過程中的“意見領袖”。拉扎斯菲爾德曾將意見領袖定義為:“活躍在人際傳播網絡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觀點或者建議并對他人施加個人影響的人物”[17]。在傳統社會中,能成為意見領袖的人,一般都具有較強的思考能力、邏輯能力和表達能力,并掌握了信息渠道,其人其意見被視為社會代表和權威。在集體記憶建構過程中,敘事主體充當了這一角色,他們通過自身魅力以及對敘事內容和敘事方式的選擇與詮釋,既決定記憶什么,也決定如何記憶以及記憶的演化方向,影響著其他成員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在他們對敘事內容的重復言說中,他們的權威性不斷得到強化,共同體成員對他們的附和與服從心理越來越強。
在傳統社會里,敘事主體一般由國家代表和社會精英承擔,他們所擇取的敘事內容與方式較集中,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清晰,與主流高度一致,具有明顯的正向引導作用。如今,個體化凸顯,傳統意見領袖的權威性被解構,網絡技術的加持更加劇了這一情勢。“互聯網初步實現了‘人人皆可發言’的技術民主,集體記憶也進入了大眾書寫時代”[18] ,集體記憶敘事主體框架隨意化,官方檔案記錄和精英主體言說的權威屢被挑戰,個體敘事者在不斷流轉的視聽信息中選取自己感興趣的焦點隨意刻寫,特別是網絡“大 V”的嵌入。他們以超乎想象的影響力左右著龐大的粉絲群體,一些根據他們自己的喜好隨意制造的話題進入記憶框架,影響人們的記憶走向。人們甚至為了快感罔顧真實,集體記憶被輿論主導。人工智能的發展,更是對真人敘事主體發起了挑戰,在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上感染著特定且廣泛的受眾。因此出現了文本紛亂、價值多歧的情境,既有的集體記憶不斷被改寫和解構,附于其上的公共情懷和價值被不同程度地消解,正在生成的集體記憶變得紛雜,公共認同和公共價值屢現危機。更有甚者,他們傳播的一些內容甚至是反公共關懷的,其沖擊力度強大,極易走進人們記憶系統,導致集體記憶價值失魅。
如此,敘事主體框架的隨意化正在形成一種巨大的消解力量,解構傳統集體觀念,銷蝕集體記憶的凝聚功能,進而造成公共價值迷亂、公共性流失、公共關懷的倫理底線一再降低。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對青少年學生造成影響。在學校教育中,雖然敘事主體依然以教育者為主,但學生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家長,以及一些社會人士、網絡人物也進入敘事主體群,將良莠不齊甚至反公共關懷的各種信息傳遞給學生。而青少年學生對一切都心懷好奇,他們精力旺盛卻又缺乏足夠的價值判別能力,一旦接觸到這些內容,其價值觀念極易被誤導。
(三)繁蕪的集體記憶敘事方式造成公共關懷實踐疲軟
記憶具有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哪些信息會被最終留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敘事方式。在傳統社會里,各種面對面的紀念儀式和其他共同活動是集體記憶的主要建構方式。這些活動通過營造“集體歡騰”(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和公共空間凝固公共內容,為集體記憶的建構提供情境與場域,同時也為公共關懷提供體驗場景和實踐機會。如今,集體記憶建構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網絡通信、智能終端讓視聽影像紛呈,視聽沖擊力越強的信息越能進入人們的記憶體系。這在利好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公共關懷實踐疲軟,對公共關懷而言是非常致命的。
在集體記憶的建構中,具身實踐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方式。現實場域中的實踐體驗與學習更為真實與深刻,公共意識也需要在實在的公共生活中形成。如今,網絡世界已成為人們的重要生活場,信息便捷且瞬息變幻,往往等不及人們的反思便已消失。虛擬世界中人與人的“相遇”看起來越來越頻繁、便利,但彼此只是相逢不相見更不相知的過客,這成為公共關懷具身實踐的直接阻滯。同時,各種智能存儲設備的出現,大大降低了記憶的重要性,導致了記憶惰性,弱化了人們的記憶能力。沒有了共同記憶和公共交集,實在性的公共空間被解構,必要的實踐場域缺失;沒有了具體關懷對象,不知該如何關心,也不知關懷效果,公共關懷無法被激活。這一過程歷經多次反復后,失敗的關懷體驗進入記憶系統,并通過網絡傳播給他人,引發蝴蝶效應,導致人們的公共關懷積極性被消磨。
這種情形同樣發生在學校教育領域。網絡信息技術的應用使得許多傳統教育活動都以虛擬形式進行,或以模擬情境代替部分真實情境,師生們在這些情境中沉浸式地“扮生活”。這樣的操作雖然便利又省力,但虛擬形式具有短暫性和淺表性,模擬的情境終究無法激發學生的長久關注。“扮生活”時人人毫不猶豫地關心集體、幫助他人,一旦遇到真實情形,還是不知所措、猶豫不決或冷漠以待,公共關懷實踐疲軟。這樣的信息充斥于記憶系統,對學生公共關懷集體記憶的建構造成難以逆轉的傷害。
三、改善集體記憶建構框架:青少年學生公共關懷興發路徑的優化
現代人原本就具有在社會困境中共同承擔責任的傾向[19],優化集體記憶特別是公共關懷集體記憶的建構,是興發學生公共關懷的積極路徑。當然,集體記憶的重建不是“動物化石中保存完好的脊椎,可以憑之就能重建包含它們的整體”[12]82,而是“重新合成這個場景,并將新的要素引人其中,這些新的要素是從當前所考慮的這一場景之前或之后的不同時期轉借而來的”[12]106。為此,需要基于現實需要把握好集體記憶的內容和意義,以實現其對青少年學生公共關懷的興發價值。
(一)把關敘事文本框架,錨定公共關懷的認知基礎與價值導向
敘事文本框架通過對敘事內容的選取和敘事基調的確定實現對集體記憶的定位,進而為公共關懷的生發提供認知基礎和價值導向。《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代中小學思政課建設的意見》提出:“持續深化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革命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各類主題教育;充分利用新時代的偉大實踐成就和時政要聞、重大活動、鄉村振興、抗擊疫情、奧運精神等方面形成的教育資源”[3]。這為青少年學生公共關懷的興發提供了思路。
在學校教育中,我們可以直接開展公共關懷主題活動,將與公共關懷密切相關的內容充實到記憶體系,指導學生的行為。在其他公共活動中,也要有意識地納入有利于促生公共關懷的內容。我國有著豐富的公共關懷傳統資源,儒家的仁愛思想、墨家的兼愛思想、道家的泛愛思想,都富含推己及人、由私及公的公共關懷意蘊。佛家悲憫蒼生的慈愛,也蘊有一種宏達天下的關懷。遠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0]的大同關懷,近至眾志成城、共同奮斗、共克時艱的大愛精神;大至舍小家保大家的舍生取義英雄事跡,小至互幫互助、團結友愛的具體行為,特別是那些和學生生活貼近的榜樣與示范,都應該被納入集體記憶建構的文本框架。
從敘事基調上彰顯這些內容的價值導向尤為重要。無論什么內容,首先,要確保其能匡正認識,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有利于公共價值的養成,以點燃學生公共關懷的“靈魂蠟燭”。其次,要盡力消除消極內容的負面影響。在教育實踐中,試圖圍堵、隔離學生的視聽已然不可能,一些負面事件對公共關懷的破壞力大,尤其容易對處于成長中的青少年學生產生消極影響。此時,更需要我們堅持正向敘事基調,消除可能的“負能量”,防患于未然。
(二)消除敘事主體的隨意性,強化其公共關懷引領作用
在集體記憶的重構過程中,敘事主體是非常關鍵的因素。“正是敘事人的身份及其在敘述文本中所表達的方式和參與程度,決定著敘事文本的基本特征”[21]。敘事主體通過對文本框架內容的抉擇,敘事方式的選取與詮釋,以及他們自身的榜樣引領,既決定了記憶的內容,也決定了敘事的方式以及記憶的價值屬性。敘事主體本身就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影響著共同體中的其他成員。對于心智仍在發展中的青少年來說,這種影響更為明顯也更為重要。
因此,在建構公共關懷集體記憶時,要消除敘事主體的隨意性,強化敘事主體的引領作用。一方面,在學校教育中,敘事主體應該以教師為主,對個體化敘事主體進行話語引導,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引領學生,及時匡正隨意化引發的問題。必要時可以通過制度賦權,穩固他們的話語權與話語體系。另一方面,為適應科技的迅猛發展,敘事主體還需掌握必要的言說技巧,甄選恰當的敘事方式,為自己的敘事提供足夠的技術、關系和情感支撐。
(三)規范集體記憶敘事方式,優化公共關懷的實踐場域
集體記憶依賴媒介、圖像或各種集體活動來保存、強化或重溫[22]。在學校教育中,相關社會實踐、志愿服務等活動依然是構建公共關懷集體記憶的主要途徑,可以為學生提供公共關懷實踐機會。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重大的公共事件,在直接參與者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特別是在他們還處于成年身份形成的早期階段,在他們還是年輕人的時候。”[12]52對于青少年學生來說,在專門組織的周期性的集體活動中,他們可以獲得持續的教育影響,相互之間的接觸頻率也會提高,一種更親近的師生、同伴關系得以建立,有利于他們公共關懷素養的提升。加強活動的儀式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充滿儀式感的活動可以更好地讓學生在身體參與和情感激蕩中生發公共關懷情感,形成積極且正確的公共關懷態度,自覺踐履公共關懷。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隨著科技的發展,學校教育中集體記憶的敘事方式也實現了符號、物質、儀式等象征系統與互聯網技術的疊加并存[23]。因此,對魚龍混雜的傳播媒介從方式到內容進行甄選、規范尤為必要。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第一,融合現代信息技術,利用紀錄片、主題影視、場館研習等方式,建構場景或還原情境,傳遞情感,強化認同,激發共鳴;第二,利用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及地方教育資源平臺服務功能,發揮“電子儀式”的作用,邀請相關專業權威人士形成輿論合力,有效引導話題,指導和規范學校教育中的集體記憶刻寫;第三,引導學生正確識網用網,利用大眾傳媒,搭建話題式、氛圍式場景,發揮學生的悟性思維[24],鼓勵和肯定學生思考;第四,打造積極向上、格調高雅、團結友愛、嚴肅活潑的校園文化,實現公共關懷集體記憶的建構。通過這些途徑規范集體記憶建構的敘事方式,打動學生心靈,最終興發學生的公共關懷情懷與行為。
四、結語
“訴諸族群過去的方法,無論怎么空洞含糊,都能激勵其‘我們的人民’為共同的民族作為自我犧牲的愿望和意志,很少有其他意識形態能在這方面與之匹敵。”[25]在對青少年學生公共關懷的興發中,集體記憶正是這樣的一種路徑,以其特有的方式促生公共認同、形成良好公共關系,并為公共關懷的生發提供情感驅力和情境體驗與實踐的機會,實現對公共關懷的觸發。面對歷史文化的豐厚饋贈和集體記憶異構的時代困境,我們需要具備超強的敏感力和恒久性,優化集體記憶的建構框架,充分發揮集體記憶對青少年學生公共關懷的興發價值。
參考文獻:
新華社.習近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上的講話[EB/OL].(2021-10-25).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25/content_5644755.htm.
[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點[EB/OL].(2022-02-08).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2/t20220208_597666.html.
[3]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代中小學思政課建設的意見[EB/OL].(2022-11-08).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2211/t20221110_983146.html.
[4]涂爾干.道德教育[M].陳光金,沈杰,朱諧漢,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6-67.
[5]常楷.公共關懷視閾下的新媒介傳播[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5(11):74-77.
[6]內爾·諾丁斯.學會關心:教育的另一種模式[M].第2版.于天龍,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4:33.
[7]常楷.馬克思主義公共倫理關懷思想及其在中國的實踐探索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20.
[8]內爾·諾丁斯.關心——倫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路徑[M].第二版.武云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34.
[9]王毅杰,倪云鴿.流動農民社會認同現狀探析[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49-53.
[10]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M].蔣自強,欽北愚,朱鐘棣,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08.
[11]魯樞元.文學藝術與社會生態[J].東方文化,2000(1):79.
[12]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2.
[13]陶東風.記憶是一種文化建構——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J].中國圖書評論,2010(9):69-74.
[14]李保森.《國家相冊》與集體記憶的建構[J].電視研究,2018(3):47-49.
[15]齊格蒙特·鮑曼.后現代倫理學[M].張成崗,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182.
[16]葉飛.公共參與精神的培育——對“唯私主義綜合癥”的反思與超越[J].高等教育研究,2020(1):18-24.
[17]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209.
[18]胡百精.互聯網與集體記憶構建[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3):98-106+159.
[19]琳恩·斯托特.培育良知[M].李心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78.
[20]孟子.孟子·梁惠王上[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9:14.
[21]何純.新聞敘事學[M].長沙:岳麓書社,2006:19.
[22]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5.
[23]龍柏林.集體記憶構建之當代變遷的哲學思考[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8(1):49-54.
[24]杜尚榮,羅凱戈,朱艷.基于感悟教學的創新型人才培養機制研究[J].教育文化論壇,2022(6):105-111.
[25]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M].葉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7.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The Path and Its Optimization to Stimulate the Public Care of Adolescent Students
JIANG Hongbi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410081)
Abstract:
The public care of individual members towards the community they belong to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The public care status of young students in the crucial growing stage of lif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fat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even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chools are the main battlefield for cultiv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character of young students, and shoul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public care for young students. Public care is an attitude and behavior that combines publicness, practicality, relatedness, and goodness. In this regar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s an undeniable factor in stimulating public care, which endows individual members with specific identities, provides them with experiential situations and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public care, thereby achieving community cohesion and unity. This provides new inspiration for promoting public care for young students in school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heterogene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fuzzy narrative text frameworks, arbitrary narrative subjects, and cumbersome narrative methods have largely deconstructed the foundation of public care, strongly impacting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care for students in schools. In response to this, school education needs to take measures such as controlling the content and tone of narrative text frameworks, eliminating the arbitrariness of narrative subjects, and standardizing narrative methods to better realize the value of collective memory construction in promoting public care for young students.
Key words:
young students; collective memory;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 public care; stimulate path
(責任編輯:梁昱坤" 郭" 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