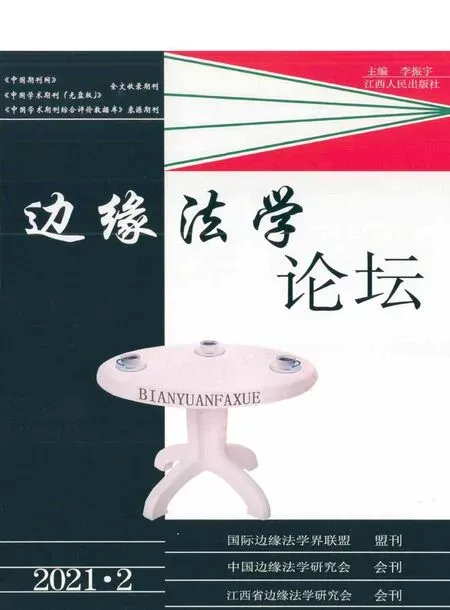恩格斯與麥金農女權思想的比較
焦祎婕 (重慶 400045)
[內容提要]
在本文中,筆者通過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的女性主義和麥金農《邁向女性主義的國家理論》中的馬克思主義進行分析后認為,單純將以麥金農為代表的激進女性主義法學總結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借鑒或者批評都是不全面的,激進女性主義法學在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之上已經發展出了自己獨立的理論。
激進女性主義法學 馬克思主義 理論比較
女性主義法學是關注女性法律問題并從女性角度審視法律和法律體系的一個法學流派。它是批判法學發展至后期的一個主要分支。斯坦福大學的法學教授凱瑟琳·麥金農是激進女性主義法學的杰出代表。麥金農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同時,又批判馬克思主義關于女性主義的立場和觀點,提出了自己獨立的女性主義理論,為女性主義法學的傳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麥金農的激進女性主義法學理論之所以被自詡為“獨立的女性主義理論”,是因為這一理論不是在平等條件下所進行的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的聯合,而是在吸收和超越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基礎上,保留自由主義的一些有價值的理論,通過分析法律上的靜態權力和把國家權力的本性界定為男性,使這一研究擺脫了傳統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而走向了獨立的女性主義。在麥金農看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為理解和解釋女性的從屬而作出的最原始的馬克思主義的嘗試。
一、恩格斯:回到公共事業的女性
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二部分“家庭”中,恩格斯先是細數了巴霍芬的四項偉大功績。巴霍芬的第一個偉大功績是認真對待部落盛行毫無限制的性關系這一原始狀態,并且到歷史的和宗教的傳說中尋找這種原始狀態的痕跡。第二個偉大功績是發現了母權制,巴霍芬把只從母親方面確認世系的情況和由此逐漸發展起來的繼承關系叫做母權制。發現婦女占統治地位。第三個功績是在共產制家戶經濟中,大多數或全體婦女都屬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則來自不同的氏族,這種共產制家戶經濟是原始時代普遍流行的婦女占統治地位的客觀基礎。第四個偉大發現是廣泛流行的從群婚到對偶婚的過渡形式。恩格斯還列出了摩爾根劃分的家庭形式。從雜亂性關系的原始狀態中,逐漸發展出了以下四種家庭形式,即血緣家庭、普那路亞家庭、對偶制家庭和專偶制家庭。恩格斯最后總結,群婚制對應的是蒙昧時代,對偶婚對應的是野蠻時代,而以通奸和賣淫為補充的專偶婚則對應的是文明時代。
在時代更迭中,婦女被剝奪了群婚性自由而男子沒有。在家庭形式的演進過程中,影響女性地位變化的重要事情是母權制推翻父權制的確立。父權制的確立是指男性氏族成員的子女留在本氏族內而女性成員的子女應該離開本氏族轉入他們父親的氏族。恩格斯“母權制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上的失敗。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了。”恩格斯認為,專偶制是只對婦女而不是對男子的專偶制。專偶制的婚姻關系比對偶制牢固的多,但通常只有丈夫享有單方面的婚姻解除權。在恩格斯看來,專偶制家庭中的妻子將自己身體一次出賣永生為奴。“歷史上出現的最初階級對立是和個體婚制下夫妻間對抗的發展同時發生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又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同時發生的。”專偶制以經濟條件為基礎而非以自然條件為基礎,是私有制戰勝公有制的第一個家庭形式。專偶制建立在丈夫對妻子的統治之上,是文明時代開始的標志之一。但是,專偶制絕非是個人性愛的結果,不以自然條件為基礎,而是以經濟條件為基礎。對恩格斯來說,女性群體被壓迫,是由于階級社會中特殊的家庭形式而造成的。并認為女性的經濟依賴性是剝削階級關系和基本家庭結構之間的聯結點。
恩格斯“現代的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家務奴隸制之上,而現代社會則是純粹以個體家庭為分子而構成一個總體。現今在大多數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須是掙錢的人,贍養家庭的人,至少在有產階級中間是如此,這就使丈夫占據一種無須任何特別的法律特權加以保證的統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資產者,妻子則相當于無產階級。”在恩格斯看來,個體婚是女性作為被男性的奴役對象而出現的。同時,他又表示無產者的家庭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專偶制家庭,男子的統治地位在無產家庭中喪失。恩格斯認為女性之于男性乃至社會的“從屬性”是可變的,可變的途徑就是改變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女性被劃分進“資產階級家庭”和“無產階級家庭”,女性成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私人生活”的反映。實現女性解放是要從社會入手,改善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社會本身,而非簡單地將無產階級女性提升為資產階級女性。恩格斯甚至認為,在無產階級家庭中的女性享受的是性愛,而資產階級家庭中的女性受到資本和丈夫(男性)的雙重壓迫,只是“不道德的”維護著形式上的一夫一妻制。
恩格斯“在現代家庭中丈夫對妻子統治的獨特性質,以及確立雙方真正社會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當雙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時候,才會充分表現出來。那就可以看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而要達到這一點,有要求消除個體家庭作為社會經濟單位的屬性。”恩格斯想要女性從家中的“私人”領地進入到社會的“公共”場域中,通過打破資本主義之下私密和公開的劃分,消除階級割裂和壓迫,從而達成女性解放的基本條件。女性受壓迫的地位和現狀應當得到改變。
李進超認為,恩格斯的婦女解放思想第一次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把女性解放問題納入社會解放這個大問題中來思考,拓展了未來婦女解放運動的視野。筆者認為,恩格斯主張男女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應有之義。在談法律主體地位平等的時候,經常被忽略掉的就是性別平等這個前提條件。性別平等應當成為法律平等的基石而非圍場。在法律的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關系方面,恩格斯更重視和強調法律的實質平等性。“在婚姻問題上,法律即使是最進步的法律,只要是當事人讓他們出于自愿一事正式記錄在案,也就十分滿足了。至于法律幕后的現實生活發生了什么事,這種自愿是怎樣造成的,法律和法學家都可以置之不問。”兩性的平等問題具有多元性,性別平等關涉法律平等、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多方面的問題。恩格斯強調,兩性之間的經濟地位平等決定了法律地位平等,進而決定了他們社會地位平等。女性實現平等的前提是個體家庭作為社會經濟單位的消亡。女性實現平等的途徑則是要從家庭中回到社會公共事業中去。
二、麥金農:對非批判性的再批判
激進女性主義法學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多于吸收,麥金農將恩格斯的女性主義批駁為唯物主義實證論導致的性別歧視錯誤;兩性平等、女性曾具有最高地位的事實假象錯誤;無產階級女性沒有因其是女性而受到壓迫的理想化錯誤;因果關系的、單向的和片面的社會解釋方法錯誤。
麥金農在《邁向女性主義的國家理論》中談到:“恩格斯試圖在階級關系的語境中,在家庭的歷史發展的理論框架內解釋女性的從屬。……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都把兩性之間關系的重要特征看做是當然的:馬克思的理由是,女性是自然的(產物),自然是天定的;恩格斯的理由是,女性是家庭的,并且恩格斯對女性在家庭中的勞動和性別角色主要持非批判的立場。”麥金農指出了恩格斯理論上的矛盾之處。一方面,恩格斯認為改變女性的從屬地位要通過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來實現。另一方面,恩格斯又說女性受壓迫的情形先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出現而存在,它是隨著階級的出現而出現的。那么,就不能將反抗和改造資本主義制度當做女性解放的當然徑路了。在麥金農看來,恩格斯不僅在解釋母權制的時候沒有論證它的真實性,而且他的專偶制婚姻中男性占支配地位的特征也是被假定的,恩格斯的觀點只有在被假定的情況下才會起作用。麥金農認為恩格斯在階級分析范圍內,通過把女性的利益隸屬于他的階級分析模式之下,而使其獲得合法性。恩格斯在解釋女性狀況方面的努力之所以是失敗的,更多的是因為他唯物主義的特性,而非他的性別歧視傾向。麥金農進一步認為是恩格斯的客觀唯物主義實證論決定了他的性別歧視。恩格斯的錯誤在于他把“存在的”直接界定為了“必要的”,沒有解釋為什么是此一事物存在而非其他事物。麥金農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批判是因為,她認為恩格斯所假定歷史上的性別平等狀況,甚至女性曾具有的最高地位未曾存在過,或者說恩格斯并未能給其所主張的存在性提供充分且排他的證明理由。麥金農評價恩格斯未能把握整個女性階級和階級劃分本身之間關系的影響,沒有注意到女性的家庭義務和公共生產之間的緊張狀態跨越了階級。恩格斯在家庭內部討論女性的地位問題沒有看到性別歧視是一個社會性問題。區分家庭領域內的“私密”和家庭領域外的“公共”對于女性地位問題的分析和女性地位提升本身并無助益,將女性限制在家庭內部本身就是一種性別歧視。
萬希平認為,麥金農以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觀為理論研究基礎,從社會性別視角通過以女性地位為中心的性別批判,揭示在父權制下被制度化了的國家權力機制,在建構其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國家觀理論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刻的探究分析。邱昭繼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麥金農女權主義法學的理論起點。女權主義法學從馬克思主義那里獲得了方法論的啟示。從馬克思主義法學的階級分析到女權主義法學的性別分析是分析對象和視角的轉變。女權主義法學繼承并發揚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批判和解放精神。劉莉等將麥金農對恩格斯的批評總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對實證主義方法的批評,二是對私有制壓迫起源的批評,三是對性別壓迫歸結為階級壓迫的質疑。
筆者認為,麥金農的理論是對恩格斯觀點的批判而非批評。批判包含了吸收和重塑、借鑒與升華,若只是批評的話則只是一味否定并未重建新的立場和陣營。在筆者看來,麥金農所指的“性”是區別于生理性別的社會性別,她認為社會性別是建構出來的,其中暗含了男性的權力即統治。麥金農不認為“階級權力創造了社會性別權力”,她批判了恩格斯階級差別是性別壓迫基礎的理論,并非只有那些握有階級權力的男性才能夠在家庭中壓迫女性。女性和階級本身是具有交叉重疊的部分。很難講是資產階級的女性受到了壓迫而無產階級的女性沒有受到壓迫,即使是資產階級女性也不能決絕的說是只受到了資產階級男性的壓迫。“女性和階級的關系是以她們和男性的關系為中介的。”從麥金農的立場來看,男性充當了女性跨越階級的“中介”。那么不禁要問,充當“中介”的男性如何統治著把他們當成“中介”的女性?麥金農借鑒了馬克思、恩格斯階級分析的方法,并將之用于性別分析當中。麥金農認為女性是因為其性別本身而遭受到壓迫而非私有制的壓迫或階級的壓迫,女性受壓迫的狀況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麥金農強調社會性別和性別政治的獨立女性主義理論,并不是意味著完全忽視了階級。她想要回答的問題是:女性不平等的根源是性別的原因還是階級的原因?麥金農始終堅持一種以女性為中心地位的性別批判,她通過把女性主義對女性從屬的解釋和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階級被剝削的解釋相比較,嘗試在認識論層次上重構女性主義。麥金農是把社會性別理解為一種權力的形式,并把權力放到其社會性別形式中去理解。性既是社會的也是政治的。
比較而言,恩格斯的女性觀具有家庭性、從屬性和私密性,麥金農的女性觀具有社會性(政治性)、獨立性和公共性。如果說恩格斯女性主義理論中的女性還沒有邁出家門,那么麥金農所言說的女性已然通過男性的“中介”經由家庭步入社會并且即將邁向國家,試圖建構女性主義的國家理論了。而恩格斯所指的女性還在想象著如何擺脫摩爾根界定下第四種家庭形式——專偶制的束縛,通過從“私密”家庭走向“公共”社會來實現自身的平等和解放。這其中,資產階級的女性遭受雙重壓迫,地位比無產階級女性低下的多。恩格斯和麥金農所處不同時代,理論建構的場域頗為不同。
三、在馬克思主義“邊緣”的激進女性主義法學
女性主義法學將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運用到了性別分析上,馬克思主義看到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女性主義法學家則看到了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女性主義是資產階級的,而在女性主義的眼中馬克思主義是男性的。激進女性主義批判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依然是男性的視角,并沒有從女性立場出發關切女性問題。依照男性統治所構建的社會秩序、法律規則和國家制度都體現男性的權力,保護著男性的利益,“女性所謂的權力不過是無權的另一面”。麥金農在書中關于“家務工資”和“意識覺醒”等的論述,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啟示和影響。一通分析下來可以看出,激進女性主義法學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吸收和借鑒是方法論層面上的,激進女性主義法學針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則是在認識論層面上的。
激進女性主義法學已然發展出了自己獨立的女性主義理論,即將脫離原先界定的女權運動核心問題——家庭、家務勞動、性別、生育、社會化、個人生活——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之內展開,而具有其獨立的理論意義。“激進女性主義法學提倡和發展獨立的女性主義理論,并不意味著對原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借鑒論意義上的否定,而是表明女性主義法學正積極尋找依靠自身觀點證明自身正當性的理論依據。
在此情境下,激進女性主義法學不再單純扮演馬克思主義運動的角色,正在逐漸演進出第三條道路——認識論層次上的性別政治。激進女性主義法學之所以有這樣的嘗試是因為,其認為馬克思主義將階級的劃分運用到女性問題上不足以解釋女性分歧的、多樣的和共同的經驗。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意識變革本質上不是社會變革的形式,而對于女性主義而言卻完全是一種社會變革形式。女性主義強調女性對她們狀況的自我感知是重要的。激進女性主義特別主張性別既在分析中又在現實上劃分了階級,而馬克思主義還停留在女性主義運動只為受教育的女性爭取利益。此類和而不同的觀點已經充分表明激進女性主義法學在自身理論演進的過程中,即將催生出自己獨立的女性主義理論。任何片面地將激進女性主義法學歸于對馬克思主義的吸收或者批評都是難以成立的。
就激進女性主義法學代表人物麥金農的理論來說,她是在何種程度上吸收和批判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一直沒能得到很好的澄清。通過對文本的對比和梳理,可以發現激進女性主義法學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多于吸收,麥金農將恩格斯的女性主義批駁為唯物主義實證論導致的性別歧視錯誤;兩性平等、女性曾具有最高地位的事實假象錯誤;無產階級女性沒有因其是女性而受到壓迫的理想化錯誤;因果關系的、單向的和片面的社會解釋方法錯誤。激進女性主義法學在批判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還受到了自由主義的影響,試圖通過自由主義的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改造,從而發展出獨立的女性主義理論。
在當下深刻反思女性主義法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在關系問題有著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價值。恩格斯和麥金農分別在各自所處的時代背景下提出了女性平等的實現路徑——回到“公共事務”和“意識覺醒”方法,都有一定的理想主義和局限性,在借鑒的同時也要注意對理論本身的二次揚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