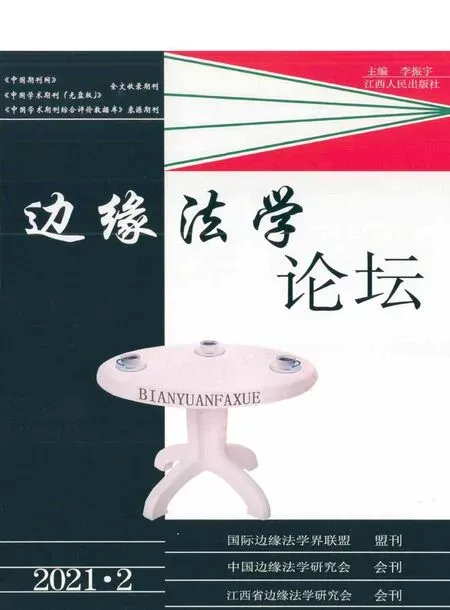人類血性對法治建設(shè)的積極意義
吳 琪 (江蘇 太倉 215000)
[內(nèi)容提要]
法律的產(chǎn)生、發(fā)展、運(yùn)作和流變是各種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因?yàn)楹魡菊x、追求正義和捍衛(wèi)正義的人類血性,我們才選擇了法治。法治社會需要血性,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究古代法律和現(xiàn)代法律如何看待這種血性,如何規(guī)范這種血性。
人類血性 弘揚(yáng)正義 法律制定
通過網(wǎng)站搜索,可以看到以“血性”為題的幾篇相關(guān)文章,但這些大多是面對當(dāng)前社會道德淪喪的現(xiàn)狀,從而批判法律缺乏血性,呼吁法律直面?zhèn)惱怼7膳c血性,應(yīng)該從法律制度本身去解決,人的血性不能被法律閹割,法律也不可能磨滅人的血性,法治社會的目的絕不是把人當(dāng)作法律的附屬物,而是充分尊重人的欲望、人的情感、人的需求,使人的價值在自由社會里得到充分發(fā)展。因而,法治建設(shè)更需要民眾的正氣來支持,這也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一、人類血性的社會認(rèn)知
在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血性被定義“指剛強(qiáng)正直的氣質(zhì)”。在現(xiàn)代文明社會,血性應(yīng)該表現(xiàn)為堅(jiān)守它們的勇氣和正義感。它可以是為了個人正義而“挺身而出”,也可以他人的正義而“仗義執(zhí)言”。從法律誕生的那刻起,血性就成為法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因子。
(一)血性與道德的異同
談及血性,總會與道德發(fā)生一定交集,但血性同道德既有聯(lián)系,又是不同的東西。人們有基于血性而要求伸張正義,這與道德主張的善惡美丑、維護(hù)正義的要求有相同之處,可以說,從產(chǎn)生方式和價值層面看,人們的血性要求在道德中得到了表現(xiàn)。當(dāng)然,道德與血性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1、性質(zhì)上
血性是一種人出于心理情感而產(chǎn)生的朦朧心理狀態(tài)、情感氣質(zhì),而道德是人對生活中善惡好壞的一種觀念及其建立其上的規(guī)范。
2、形式上
血性只是一種不成熟的感性化情感、氣質(zhì),而道德是一種較為成熟的觀念,甚至更多表現(xiàn)為對社會中美德的弘揚(yáng)、丑陋的批判的一種制度,其人為形塑的作用大一些。
3、程度上
血性是一種性格氣質(zhì),它相對模糊、抽象,而道德因?yàn)樯鐣浾撚绊憣ζ滟潛P(yáng)和否定的東西有更強(qiáng)的觀念和規(guī)范,所以更清楚。
(二)人類血性的重要性
人類血性在自然意義上,有自保的本能;在精神意義上,意味著人格和尊嚴(yán)。一個集體、民族和社會本身是有一群具有血性的人組成的,人們在長期的交往中形成了自身的“民族精神”,這是社會的凝聚力,也是社會追求正義的力量源泉。
二、法律與血性的理論維度
法律是人類走向文明的產(chǎn)物,其產(chǎn)生是社會綜合因素的結(jié)果,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論述法與其他社會現(xiàn)象時,他這樣寫道:“法律應(yīng)該與國家的自然狀態(tài)產(chǎn)生聯(lián)系;與氣候的冷、熱、溫和宜人相關(guān);還與土壤的品質(zhì)、位置和面積有關(guān);法律與諸如農(nóng)夫、獵人或者牧民等各種人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guān)。法律必須與政體所能承受的自由度相適應(yīng);還要以居民的宗教、性癖、財富、人口、貿(mào)易風(fēng)俗以及言談舉止發(fā)生關(guān)系。”
(一)法律與血性的關(guān)系
血性體現(xiàn)在人類樸素的道德情感中,是一種捍衛(wèi)權(quán)利,鋤強(qiáng)扶弱,打抱不平的心理,從法律產(chǎn)生的那一刻起就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血性在起初的表現(xiàn)為格斗和血親復(fù)仇,而這與法律的產(chǎn)生有著密切關(guān)系。在最開始的時候,人們依靠自身的道德約束來互認(rèn)利益。隨著權(quán)利客觀性的增強(qiáng)和權(quán)利數(shù)量的增加,利益的捍衛(wèi)、糾紛的解決完全依靠個人的自力救濟(jì),社會處于相對混亂的時期。為了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又解決利益歸屬,人們把習(xí)慣總結(jié)為習(xí)慣法,并由氏族中的社會權(quán)威(酋長等)主持。由此產(chǎn)生了相應(yīng)的裁判機(jī)制、執(zhí)行機(jī)制和具有相當(dāng)程度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的規(guī)則,法也隨之產(chǎn)生。但畢竟此時社會權(quán)力主導(dǎo)的法在強(qiáng)制性上仍有缺陷,所以仍保有格斗和血親復(fù)仇等形式。當(dāng)法律進(jìn)一步完善,社會機(jī)構(gòu)專門化而由此進(jìn)入國家時代時,法律逐步去除非文明殘酷的糾紛解決方式,由此格斗和血親復(fù)仇被國家的權(quán)利救濟(jì)途徑所替代。
事實(shí)告訴我們:法律必須體現(xiàn)人的情感、人的需要和人的欲望。法律源于社會,必須對社會中的個人血性和民族血性有個明確地判斷,既著眼于現(xiàn)實(shí),又能以法律激濁揚(yáng)清,推動社會發(fā)展。血性中捍衛(wèi)正義的本性是好的,但其形式不一定就是文明的,法律在面對血性的時候,是趨善去惡。因此,法律在鼓勵人們血性的時候,以權(quán)利為立足點(diǎn),嚴(yán)格遵循法律程序的確認(rèn)權(quán)利和保障權(quán)利,是以正義的方式去實(shí)現(xiàn)正義。
(二)法律對血性的理性規(guī)范
血性中這種朦朧的正義感,促使人們?nèi)ヤz強(qiáng)扶弱,捍衛(wèi)正義,這對法律是積極的推動,但是血性始終只是一種潛意識中樸素的道德情感,在實(shí)體上有時候背離正義走向,在程序上往往沒有合理的形式。因此,法律對血性必須正確看待,趨利避害,采取制度化的方式對血性進(jìn)行規(guī)范。
1、血性追求的是實(shí)體正義
對于個人而言,這種正義是得其所得。對于集體而言,這種正義是人際關(guān)系的合理安排。
2、血性需要程序上合理
正是因?yàn)榉沙绦虻暮侠砘沟萌祟悢[脫野蠻殘酷的暴力。血性是人類是非感的體現(xiàn),需要充滿人文關(guān)懷,彰顯人性尊嚴(yán)的形式去體現(xiàn)。
3、血性要求法律制度保障
法律對待血性的態(tài)度是將人的愿望設(shè)計為一定的法律原則和規(guī)則,用具體化的制度去規(guī)范和維護(hù)它,這是法律進(jìn)步的表現(xiàn)。這既能增加法律的認(rèn)同感,又在一定程度上強(qiáng)化了法律信仰。
利科教授在《公正與報復(fù)》中提到一個悖論:“人們尋求公正很大程度是基于報復(fù)精神,但公正的目的是要超越報復(fù)。”具體到法律上,人類血性是人的一種基于義憤而產(chǎn)生的樸素的正義感,而這些正義感本身存在太多的報復(fù)情緒,事實(shí)上與公正的要求相悖。法律是關(guān)于正義的規(guī)范,它是一種制度正義的體現(xiàn),所以法律必須在時間和空間上減少報復(fù)情緒,增強(qiáng)理性指導(dǎo)下的正義。在時間上,法律往往規(guī)定舉證期限;在空間上,把公正實(shí)現(xiàn)的地方由案發(fā)現(xiàn)場轉(zhuǎn)到法庭,這些都是消解被害人、法官的義憤情緒,使得法律能夠公正地對待雙方當(dāng)事人。
幾年來日益頻發(fā)的見死不救案件,法律面對血性喪失,該如何處理的問題值得思考。見義勇為只是道德義務(wù),在不傷及其他的時候,如果將其納入法律,既提升了對普通人的要求,也可能使法律實(shí)效大增。
三、法律與血性的現(xiàn)實(shí)維度
(一)古代法律中血性的制度設(shè)計
“在古代社會,先民們的直覺經(jīng)驗(yàn)與對自然的神秘感奇特得結(jié)合在一起,其思想和行為很大程度上受到直覺情感的支配……古代社會中的人們很大程度上生活在‘情感的荊棘叢’。人們情感化對待事物的姿態(tài),在古代法中留下深了深的印記。”
1、血親復(fù)仇與同態(tài)復(fù)仇
復(fù)仇是一種原始的自衛(wèi)方式,也是具有直覺的報復(fù)情感對侵害者施加的一種懲罰。在東西方文化里,這種基于血緣的文化現(xiàn)象是共通的:人們“總是為了懲罰而懲罰,為了使罪人受苦而使罪人受苦,而且他們給別人強(qiáng)加痛苦的時候,自己并沒有指望獲得任何利益。古代社會人們最重要的社會關(guān)系是家族血緣關(guān)系,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對某一個人的人身傷害,被認(rèn)為是對一個家族全體成員的侵害;對一個人身傷害行為的報復(fù),針對的是加害人的家族成員,由此產(chǎn)生血親復(fù)仇。
血親復(fù)仇表現(xiàn)為:“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除此,還提出了復(fù)仇的第四個原則:“父不受誅,子復(fù)仇可也。”意思是如果父親是被冤枉處死的,兒子可以向法官甚至君主復(fù)仇。
中國早期的法律也是允許私人復(fù)仇的,儒家經(jīng)典《周禮·秋官》稱西周時,朝廷司寇處有一個叫“朝士”的機(jī)構(gòu),如果自己的父兄為人所殺,就可以到這個機(jī)構(gòu)登記仇人的姓名,以后就可以殺死仇人而無罪。在朝廷的司徒處又有一個“調(diào)人”的機(jī)構(gòu),凡發(fā)生殺傷行為,就要把仇人互相調(diào)開來“避仇”。不愿離開的就要抓起來,防止冤冤相報。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復(fù)仇,就以一次為限,不許雙方再行復(fù)仇,導(dǎo)致仇殺不已。
古代阿拉伯世界、歐洲及其他的一些地方法律也有關(guān)于血系復(fù)仇或者同態(tài)復(fù)仇的規(guī)定。其中關(guān)于復(fù)仇的最典型的表述如《舊約全書》記載的古希伯萊人的法律原則:“以命還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在具體的法律規(guī)則中,《漢穆拉比法典》作為迄今發(fā)現(xiàn)最早最完整的成文法典,其中規(guī)定“倘自由民損毀任何自由民之子之眼,則應(yīng)毀其眼”(第196條)、“倘彼折斷自由民[之子]之骨,則應(yīng)折其骨”(第197天)、“倘自由民擊落與之同等自由民之齒,則應(yīng)擊落其齒”(第200條)。
血親復(fù)仇打破了罪責(zé)自負(fù)的原則,把個人和家族聯(lián)系在一起,甚至在家國一體的統(tǒng)治模式下成為解脫個人的枷鎖,這種原始野蠻的報復(fù)形式是對生命的極端蔑視,更是對個人自由選擇的不尊重,而且它嚴(yán)重破壞社會秩序,這種非人道的落后制度在法律中逐步去除。
春秋時期的法律對復(fù)仇不多加干涉,但戰(zhàn)國的法律就開始禁止私人復(fù)仇,強(qiáng)調(diào)一切殺人行為都必須由國家刑罰進(jìn)行嚴(yán)懲。最典型的是法家的觀點(diǎn):私人之間的復(fù)仇是影響統(tǒng)治秩序的大罪,要予以嚴(yán)懲。商鞅入秦,實(shí)踐法家理論,開始禁止私人的復(fù)仇,使復(fù)仇的風(fēng)氣有所收斂。韓非指責(zé)當(dāng)時社會上的“五蠹”之一,就是“立節(jié)操”而帶劍的俠客,“俠以武亂禁”,替人復(fù)仇,破壞法制。復(fù)仇是一種基于人倫產(chǎn)生的,在人倫與社會秩序的博弈當(dāng)中,法律戰(zhàn)勝了野蠻。在唐代也有關(guān)于血親復(fù)仇的禮法之爭,使中國古代“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的觀念根深蒂固,或許是因?yàn)橹袊糯茉缇徒⒘溯^為強(qiáng)大的國家政權(quán)機(jī)構(gòu),所以原來的血親復(fù)仇、同態(tài)復(fù)仇演化為由國家政權(quán)來代替進(jìn)行這種復(fù)仇。
霍姆斯在《普通法<責(zé)任的早期形式>》中專門論述了西方法律在傷害方面的進(jìn)化:眾所周知,法律程序的早期形式是基于復(fù)仇。現(xiàn)代作者認(rèn)為羅馬法源于血仇,而所有的權(quán)威都同意日耳曼法也是這樣起源的。世仇導(dǎo)致了由選擇性到強(qiáng)制性用以收買世仇的和解協(xié)議。和解協(xié)議的逐漸發(fā)展可以在盎格魯-薩克遜法中被溯及,而到了征服者威廉時代,世仇雖然沒有滅絕,但基本上已經(jīng)被解決掉了……早期法律的一個特點(diǎn)是不能穿透外部的可見事實(shí),有形的損害即實(shí)際的補(bǔ)償……曾經(jīng)是特權(quán)的通過協(xié)議收買復(fù)仇、付出賠償而不是讓與損害實(shí)施者的身體,無疑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普遍性的習(xí)慣。
霍姆斯的觀點(diǎn)可以從不同時期不同法典的規(guī)定證明:《十二銅表法》第二條規(guī)定的“如果故意傷人肢體,而未與受害者和解者,則他本身也亦應(yīng)遭受同樣的傷害”表明羅馬時期的法律雖然仍規(guī)定同態(tài)復(fù)仇,但已以未能和解的條件限定適用;日耳曼法的代表《薩利克法典》中關(guān)于殺害自由人統(tǒng)一適用罰金,只是數(shù)額的多少。
從復(fù)仇到賠償再到國家刑罰,霍姆斯關(guān)于責(zé)任的論述和法典的發(fā)展歷史告訴我們:在法律的原始階段,傷害行為作為一種有形損害,無法實(shí)際賠償,只能同態(tài)報復(fù)或者血系復(fù)仇。未造成死亡的傷害行為就要實(shí)行同態(tài)復(fù)仇,再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就是將這種私人的復(fù)仇改換為使用財產(chǎn)賠償,強(qiáng)迫加害人拿出所謂“血金”來抵償傷害。最后,在國家觀念得到強(qiáng)化后,才逐漸確立把所有的暴力侵犯視為犯罪的概念。
2、司法決斗制度
決斗曾經(jīng)在歐洲盛行,源于法律上的承認(rèn)。由于當(dāng)時人的認(rèn)知水平較低,在證據(jù)認(rèn)定上往往依據(jù)神明裁判,對于疑難案件采用火審水審等裁判制度,其中決斗也被列為一種糾紛的解決方式,而日耳曼法則是最早確立了歐洲的司法決斗制度。根據(jù)規(guī)則,決斗中獲勝一方的陳述被認(rèn)為是事實(shí),而敗北一方或不敢參加決斗一方的陳述則被認(rèn)為虛假的,其依據(jù)是神會保佑說真話的人。
司法決斗制度自從被勃艮第國王確立后,逐漸被日耳曼諸國普遍仿效,在以后約600年間成為歐洲一種重要的司法手段。但10世紀(jì)以后,羅馬天主教逐漸取得對世俗的領(lǐng)導(dǎo)地位,一些神學(xué)家認(rèn)為,司法決斗違反了基督教非暴力與和平原則,不符合基督教教義,而且憑武力定訴訟勝負(fù),對弱小者不公平,于是教皇多次提出禁止司法決斗。與此同時,隨著社會的進(jìn)步,世俗君主們也開始改革訴訟制度,12世紀(jì)后半葉,英國國王亨利二世進(jìn)行司法改革,禁止司法決斗,而代之以宣誓作證的方法。此后,其他西歐國家也相繼進(jìn)行改革,司法決斗制度逐漸衰落,但其徹底退出歷史舞臺仍經(jīng)過漫長的發(fā)展歷程。英國直到1819年才正式廢除司法決斗。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法制史上,決斗制度從未被法律確認(rèn)過,也沒有成為解決爭端的民間流行方法。決斗在東西方法制中命運(yùn)不同。私力救濟(jì)與當(dāng)時歐洲的政治社會體制是相符的,而我國古代社會高度專制,在統(tǒng)治者眼里,民間逞勇斗狠無疑是對統(tǒng)治秩序的蔑視,會對社會安定造成極大威脅,因而絕對不允許當(dāng)事人自己捋起袖子進(jìn)行所謂“私力救濟(jì)”。
(二)現(xiàn)代法律中血性的制度設(shè)計
古代法律中血性的制度設(shè)計,多少是出于人的本能、認(rèn)識水平低和神靈崇拜,其中不合理,暴力化的因素太多。現(xiàn)代法律在理想建構(gòu)和經(jīng)驗(yàn)進(jìn)化作用下,法律日趨合理,在摒棄格斗和血親復(fù)仇等非人道的血性表現(xiàn)形式之下,做出了更合乎人性,又保障社會安定制度安排。
1、良心拒絕和非暴力反抗
法律本身具有效力,但實(shí)效如何則是關(guān)系到法律實(shí)現(xiàn)時能否達(dá)到法律預(yù)設(shè)的效果問題。法律是否應(yīng)該被遵守,特別是當(dāng)法律嚴(yán)重違背人們的道德倫理,出現(xiàn)不公正時,公民的守法義務(wù)和守法道德是否仍舊存在,主張正義自由是社會第一價值的羅爾斯對“良心拒絕和非暴力反抗”有獨(dú)到的見解。他認(rèn)為,“一般來說,正如一種現(xiàn)存憲法所規(guī)定的立法合法性并不構(gòu)成承認(rèn)它的一種充足理由一樣,一個法律的不正義也不是不服從它的充足理由。當(dāng)社會基本結(jié)構(gòu)由現(xiàn)狀判斷是相當(dāng)正義時,只要不正義法律不超出某種界限,我們就要承認(rèn)它們具有約束性。”當(dāng)法律不正義時,他認(rèn)為人們可以依照良心自由取得“非暴力反抗”的權(quán)利。這種非暴力反抗從人的血性和尊嚴(yán)角度,從為緩解社會張力的功利角度,從維護(hù)權(quán)利、控制權(quán)力的角度,從維護(hù)憲法權(quán)威的憲政角度看都具有積極意義,但它同樣會對現(xiàn)有的法律權(quán)威和社會秩序帶來沖擊。
2、正當(dāng)防衛(wèi)
在刑法中,判斷一個理性人的標(biāo)準(zhǔn)是刑事責(zé)任能力,而刑事責(zé)任能力的衡量尺度是融合了年齡、智力和精神狀況在內(nèi)的因素,主要包含辨認(rèn)和控制能力。正當(dāng)防衛(wèi)是指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chǎn)和其他權(quán)利免受正在進(jìn)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行為。對正在進(jìn)行行兇、殺人、搶劫、強(qiáng)奸、綁架以及其它嚴(yán)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wèi)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屬于正當(dāng)防衛(wèi),不負(fù)刑事責(zé)任。從針對一般侵權(quán)行為的正當(dāng)防衛(wèi)到針對嚴(yán)重危及人身暴力犯罪的特別防衛(wèi),各個國家的刑法,即使是在古代,像宋刑統(tǒng)中都已列入非犯罪化是由當(dāng)中,要么不認(rèn)為是犯罪,要么不予處罰。相比于緊急避險,正當(dāng)防衛(wèi)刑法采取的是一種鼓勵人們同違法犯罪作斗爭,以捍衛(wèi)權(quán)利捍衛(wèi)正義的態(tài)度。
3、緊急避險
緊急避險是指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chǎn)和其他權(quán)利免受正在發(fā)生的危險,不得已采取的緊急避險行為,造成損害的,不負(fù)刑事責(zé)任。緊急避險采用損害一種合法權(quán)益的方法以保全另一種合法權(quán)益。有“緊急情況”、“別無他法”、“迫不得已”和“保護(hù)大于損害”等詞語或詞組限定。相比于正當(dāng)防衛(wèi),其在危險來源、情況緊迫性、避險限度和特殊主體的禁止限制條件更嚴(yán)苛,這也體現(xiàn)了比例原則,反映出法律在無法同時保全多種利益時,不得已得選擇保護(hù)較大利益的權(quán)衡。
4、自助行為
“無救濟(jì)就無權(quán)利”,救濟(jì)是權(quán)利三項(xiàng)權(quán)能之一。古典自然法學(xué)家洛克將權(quán)利和權(quán)利救濟(jì)看得很重,認(rèn)為盡管在和平安定的自然狀態(tài)下,權(quán)利仍然受到危險,而作為個體的人靠自力救濟(jì)很難,以此構(gòu)建他的社會契約論,主張大家讓渡權(quán)利救濟(jì)的執(zhí)行權(quán),以獲取的公力救濟(jì)。現(xiàn)代法律與古代法律相比,在救濟(jì)上的一個重大差別就是由專門的機(jī)關(guān)承擔(dān)權(quán)利救濟(jì)責(zé)任,盡量減少權(quán)利自我救濟(jì)的空間,這既是從整體上維護(hù)社會秩序的考慮,也是對權(quán)利最好的救濟(jì)方式。盡管如此,但因權(quán)利自身的性質(zhì)、受侵害程度、緊迫性,獲取公力救濟(jì)的可能性和及時性,權(quán)利人有親身感受和選擇能力,這就給權(quán)利的自我救濟(jì)留下了空間,因此各國立法對自助行為都留有缺口,同時為自主行為限定了出現(xiàn)的條件:(1)為了自己的合法利益;(2)在不能及時取得公力救濟(jì)的情況下;(3)迫不得已;(4)采取合理的手段,沒有超過限度;(5)事后及時請求有權(quán)機(jī)關(guān)處理。
5、見義勇為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被視為中華美德。然而在社會轉(zhuǎn)型時期,由于原有的道德規(guī)范受到?jīng)_擊,幫助他人之后反被訛上不斷發(fā)生。尤其是“小悅悅事件”給人們很大沖擊。事實(shí)上,從各國的立法實(shí)踐來看,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強(qiáng)制人們“見義勇為”,比如德國刑法第330條C款規(guī)定:“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險或急難時,有救助之必要,依當(dāng)時情況又有可能,尤其對自己并無重大顯著危險而且不違反其他重要義務(wù)而不救助者,處一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罰金”,法國、意大利也有類似規(guī)定。英美法系基于人與人之間的自治一般不強(qiáng)制“見義勇為”,但是從側(cè)面對見義勇為行為提供保護(hù),比如加拿大安大略省2001年頒布的《見義勇為法》規(guī)定“無論習(xí)慣法如何規(guī)定,自愿且不求獎勵報酬的個人,不必為施救過程中因疏忽或不作為所造成的傷害承擔(dān)責(zé)任”;新加坡公民在實(shí)施見義勇為時,對反咬一口行為予以懲罰,也免去了好人被訛詐的顧慮和擔(dān)憂。
6、幫助行為
幫助行為也是法律對血性外在面向的保護(hù),畢竟人生活不僅僅是個人,也需要在與他人的交往中相互照顧,形成共同體,為此各國立法都對此有所規(guī)定。例如《民通意見》第157條規(guī)定“當(dāng)事人對造成損害均無過錯,但一方是在為對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進(jìn)行活動的過程中受到損害的,可以責(zé)令對方或者受益人給予一定的經(jīng)濟(jì)補(bǔ)償。”
四、余論
人類血性是出于維護(hù)正義的沖動,更少的計較個人利益,而更多的是朦朧地非理性地行為。其實(shí)是個人看不下“不正義”的現(xiàn)象。法律是人性化的,法律在對血性的吸收、規(guī)制和保護(hù)中得到進(jìn)化。高鴻鈞教授在《中國法治的出路》里這樣寫道:“近代以來,法律中的情感因素被不斷剔除。……不過,當(dāng)法律剔除了情感因素之后,也帶來了某些負(fù)面的效應(yīng):法律漸趨成為一種脫離日常情理的理性條文,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生硬推行的強(qiáng)制律令,成為一種遠(yuǎn)離民眾生活的官方規(guī)則。”誠然,近代化法律在科學(xué)的推動下朝著更加精確、更加理性方向發(fā)展,反倒缺乏了人的情感等因素,但相比于西方,我們走得更遠(yuǎn)。
自古中國就是個人治的社會,統(tǒng)治秩序至上的國度里,人民為血性而追求公平正義既缺乏超驗(yàn)的理念,又缺乏制度規(guī)范,以至于磨滅人性,漠視人權(quán)。在西方,從柏拉圖的人治到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穿越了黑暗的中世紀(jì),法律終成為最有權(quán)威的社會規(guī)范,法治終也成為現(xiàn)行最佳的社會狀態(tài)。生活在法律社會中的人雖然聰明有理智,但他們同樣是有感情的,人與人相處之間會產(chǎn)生不正義,會有正義的呼喚,人類社會,法律不是無情的,必須回應(yīng)人因血性而做出的感性舉動,趨利避害,設(shè)計制度,合理規(guī)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