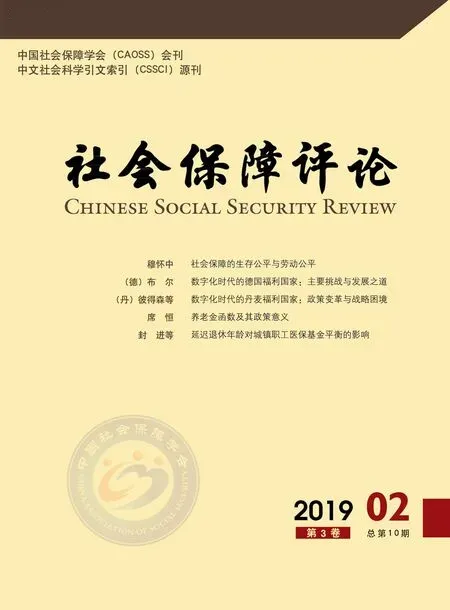全球競爭下社會保障支出的地區差異:基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較
李 雪
一、引言
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在經濟全球化和市場轉型的背景下建立和完善的。作為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的代表,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對外貿易國和第一大吸引外資國。積極參與全球競爭一方面給我國帶來了更多的資本和機會,另外也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政策越來越受到國際經濟政治局勢的影響。與此同時,隨著原有計劃經濟下單位制的瓦解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以往由工作單位全部承擔的職工醫療、養老等保障功能轉型為政府、單位、個人按一定比例分擔的新型社會保障制度。其中政府社會保障支出主要承擔無穩定工作的居民保險、社會補助和社會救助①政府社會保障支出中,有時也涉及對職工社會保險基金的財政補貼。。有穩定工作的職工社會保障則由雇主和個人按一定比例承擔。在政府社會保障支出中,地方政府承擔了總支出的90%以上。大量研究發現,經濟全球化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社會保障支出規模,因為這些國家為了爭取更多外資和提高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盡可能降低企業的稅收負擔,從而縮小了財政收入規模以及社會保障支出規模②Robert Kaufman, Alex Segura-Ubiergo, "Globaliz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 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 1973-97," World Politics, 2001, 53(4).。然而,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不斷發展完善、政府社會保障支出規模穩步上升。那么,我國政府社會保障支出規模不斷擴大的動力何在?
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是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也是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增長最快的地方。僅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地25 個城市,就貢獻了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和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總額的一半以上。由圖1可見,2000—2014年這15年間,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對外貿易額分別占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5%—50%和25%—35%,這兩地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則占據全國的25%—35%和15%—25%。

圖1 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經濟全球化水平(2000—2014年)
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積極參與全球經濟的同時,其社會保障支出規模也不斷上升。圖2分別描述了兩地平均每個城市和平均每人的社會保障支出數額③這里以戶籍人口作為分母,因為社保的政府開支部分主要是針對戶籍居民的。。可以發現,2000年以來,兩個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均實現穩步增長,其中從2006年開始則實現跨越式發展,從2005年每城市不足4 億元,分別迅速上升到2014年的83 億元和48 億元。城市層面的社會保障支出中,長三角要顯著高于珠三角,但個人層面則相反。這是由于長三角戶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較高導致的。

圖2 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社會保障支出(2000—2014年)
那么,為什么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出現了和理論預計相反、與多數發展中國家現實相悖的情況——社會保障支出在面臨全球化壓力時不降反升?有觀點認為,地方社會保障支出的上升完全是中央推進的結果。固然,社會保障制度在全國各地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央政府要求的結果,那為什么中央能推進地方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卻無法推進其他公共服務性支出,如教育支出①在政府各項公共服務性支出中(如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的支出),從2000年到2016年,僅有社會保障支出在GDP 占比和人均數額方面均實現了顯著增長。?“教育經費占GDP 的4%”這一目標不但被寫進《教育法》和《中國教育發展綱要》, 科教興國還被立為“基本國策”,可到2016年我國各級政府教育支出合計也僅占GDP 的3.7%②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計算所得。。也有觀點認為,地方社會保障支出增加是個別地方官員偏好的結果。然而這無法解釋為何各地官員都一致地偏好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并且不約而同地選擇從2006年開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在學術研究中,已有不少學者認識到我國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全球化的相關關系③關信平:《世貿組織、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社會福利改革》,《社會福利》2002年第1 期。,但目前尚缺乏系統考察社會保障支出與全球性和地方性經濟、社會因素關聯的經驗研究。
探討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的影響因素,特別是它與經濟全球化及國內經濟、社會因素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首先,它有助于進一步發展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更重要的是,政府社會保障支出是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國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①國際勞工組織:《全球社會保障的最新動態與未來展望》,《社會保障評論》2018年第2 期。。它是國家將稅收進行再分配,用以保障國民在市場能力受損(如退休、失業、生病、傷殘、生育、遭遇災害)時的基本生活,從而降低社會不平等和實現社會公平。系統評估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的動力及其與全球化的關系,不僅有助于理解國家的再分配功能及其與社會不平等的關系,而且可以借此探討全球化下國家自主性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可能這一理論問題②Peter Evans,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s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1997, 50(1).。
本研究以2000—2014年我國長三角16 個城市以及珠三角9 個城市的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為研究對象,運用政治社會學的福利國家理論和經濟全球化理論,通過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描述并比較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政府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的差異及其決定因素。研究發現,盡管經濟全球化進程對人均社會保障支出有負效應,兩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政府財政能力和勞動爭議數量構成促進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的重要動力。繁榮的經濟和充盈的政府財政使政府有能力增加社保支出。勞動爭議作為信訪的最大來源之一③孔令明:《集體性勞動爭議實證研究——基于某省D 市近十年3110 宗爭議原始資料》,《社會科學論壇》2016年第10 期。,在2005年后實行“信訪一票否決制”的官員考核背景下,推進地方政府發展與勞動權益直接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社會保障開支(見圖3)。長三角和珠三角社會保障支出的發展模式有所不同(見圖4A 與圖4B)。在長三角,地方性因素——勞動爭議數量、地方財政能力和經濟實力——顯著促進了社會保障支出,經濟全球化的效應則并不一致。在珠三角,地方性因素和全球因素的交互作用,連同地方經濟實力,共同促進了社會保障支出。值得指出的是,經濟全球化對兩地社會保障支出的作用方式不同。長三角的地方政府更能抵御經濟全球化的壓力,而珠三角的社會保障支出則顯著受到全球化的抑制作用。這部分可由兩地卷入全球化的不同模式來解釋。珠三角作為我國最早開放的地區,其外貿依存度(對外貿易占GDP 百分比)一直遠高于長三角,吸引外資水平直到2003年后才微弱低于長三角。換言之,珠三角參與全球經濟的深度和廣度要高于長三角。

圖3 長三角和珠三角社會保障支出決定因素

圖4A 長三角社會保障支出的決定因素

圖4B 珠三角社會保障支出的決定因素
本研究的貢獻有三:第一,本文采用經驗數據,系統探討了影響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的國際和國內因素,為政治社會學中福利國家研究提供了發展中國家視角;第二,本文探討了長三角和珠三角這兩大外向型區域經濟體的異同,并發現珠三角地區全球因素的作用取決于地方因素的水平,為理解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區域差異提供了新的全球化的解釋路徑;第三,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地在面臨全球化壓力時社保支出仍不斷增加的現實,為“全球化下國家自主性”的理論論爭提供了新的例證:盡管國家面臨更多來自國際的壓力,但它亦有能力做更多。
二、全球因素、地方因素與社會保障支出
(一)經濟全球化與社會保障支出
經濟全球化意味著貿易和投資這兩項最常見的經濟活動越來越多地跨越國境進行。在全球化時代,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個人和組織之間發生經濟活動的頻率和規模都越來越大①Stephan Haggard, Robert Kaufman,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Welfare States: Latin America, East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25-128.。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成為經濟全球化時代最主要的經濟活動類型。對外貿易包括進口和出口,即貨物、產品的跨國界流通。對外投資則意味著資本的跨國界流通,包括外國對本國的投資,即外商直接投資(FDI)以及本國對外投資。高額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意味著一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高度依賴。
1.對外貿易與社會保障支出
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分工和資源配置,從而能充分利用各國比較優勢,生產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的產品。但一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也意味著經濟運行越來越受到國境之外的難以預料且不可控制因素的影響,從而也帶來了更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導致更多的失業、下崗事件和更大規模的困難群體。同時,對外貿易使得市場競爭擴展到全球層面,全球競爭迫使企業以更大的力度控制生產成本,以便以較低的價格在全球競爭中占得先機。
對外貿易的這兩個特征對社會保障支出產生了顯著影響,學者將其分別稱為“補貼效應(compensation effect)”和“競爭效應(competition effect)”②Alexander Hicks, Social Democracy and Welfare Capitalism: A Century of Income Security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1-23.。根據補貼效應,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高風險和市場劇烈波動,政府會增加社會保障開支,以補償市場競爭中的失敗者和缺乏市場能力的人,如發放食品券(food stamps)和各種最低生活救濟(如最低生活保障金),以便換取這些人繼續支持國家開放市場的政策③Dani Rodrik,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pp.15-17.。研究顯示,那些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歐洲發達國家,社會保障水平往往很高。那些西北歐的小國,如比利時、奧地利和瑞典等,其社會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例在發達國家中居于前列④Peter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12-122.。這些國家國內市場狹小,因而對國際市場依賴很深,面對國際市場的不景氣、不確定、高風險時首當其沖,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的情形日益常見。市場競爭的失敗者和困難人群通過民主政治途徑要求政府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這也是其外向型經濟得以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社會保障支出的上升不僅緩解了全球化的負面效果,從長遠看,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公共開支還有利于培養和維持一支高質量的勞動力隊伍,有助于推進產業升級和提高國際競爭力。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研究者對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則發現社會保障支出隨全球化程度加深而遞減的效應,即競爭效應⑤Robert Kaufman, Alex Segura-Ubiergo, "Globaliz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 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 1973-97," World Politics, 2001, 53(4).。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多以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生產為特征,這類生產形態利潤微薄,因而對成本非常敏感。為了在國際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廠商拼命壓低勞動力成本和稅收責任,政府出于發展經濟的考慮,也往往滿足企業訴求,盡可能降低企業稅負。由于稅收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在稅收規模有限的情況下,政府的社會保障支出也隨之受到消極影響。可見,由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分工中所處的位置不同,國內的制度設置不同,對外貿易對其社會保障支出的影響也就不同。
2.FDI 與社會保障支出
FDI 即外商直接投資,它是外國資本為獲得某個本國企業的利益進行的投資,目的在于在該企業管理中具有有效的發言權。世界體系理論認為,FDI 會加劇邊緣國家(the periphery)對核心國家(the core)的依賴,從而邊緣國家制定的政策只可能對核心國家有利,而對本國的勞動者不利。在這個意義上,FDI 同樣會降低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FDI 的大量流入會不斷蠶食侵占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性,加強外國資本對國內政策制定的控制力。和本國資本相比,外國資本并不愿意為公共財政做貢獻,也不太可能將所獲利潤回饋給該國或進行再投資。外國資本還有可能破壞本國較為脆弱的工業體系①Glenn Firebaugh, "Growth Effect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2, 98(1).。外國資本進入本國經濟的規模越大,越可能影響本國的政策制定過程,越可能促使本國政府制定對外資友好(foreign capital friendly)的政策,如低稅收、低關稅政策②William Dixon, Terry Boswell, "Dependency, Disarticulation, and Denominator Effects: Another Look at Foreign Capital Penet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102(2).。
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同樣認為FDI 會降低社會保障支出,但他們認為這一結果會惠及各方。各國為爭奪外資而競爭會促使外資流向生產成本(包括稅收)最低、最具比較優勢的國家,從而使資本的使用更有效率。這一過程盡管可能導致國家財政支出和福利支出減少,但它提高了市場效率,會使資本和勞工同時受益,因而是個“雙贏”的過程。
也有學者認為FDI 會導致社會保障支出增加。對外投資只有當其在流入國的收益大于在流出國收益時才會發生③Alwyn Lim, Kiyoteru Tsutsui, "Globalization and Commitment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ross-National Analyses of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Economy Effec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2, 77(1).。這對流入國的政府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法治、高質量的勞動力等,這些都需要大量的政府公共投入④Evelyne Huber, et al., "Politics 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08, 70(2).。因而,FDI 會促進流入國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包括社會保障上增加投資。
3.小結
在經濟全球化與社會保障支出的關系這一問題上,學者們觀點不一,這也意味著經濟全球化的效應取決于具體國家的制度環境。針對發達國家的經驗研究多顯示,經濟全球化對社會保障支出的水平并無顯著一致的影響⑤David Brady, et al.,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Affluent Democracies, 1975-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5, 70(6).;而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則表明,經濟全球化導致了全球范圍內發展中國家社會保障支出下降⑥Nita Rudra, "Openness, Welfare Spending, and Inequal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4, 48(3).。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實力較弱、國家治理水平較低,抵御國際市場風險的能力較低,更容易受到跨國資本和企業的左右。它們多涉足于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產業,這對當地的勞動力質量、營商環境等的要求也較低。各種因素導致發展中國家在面臨全球化挑戰時,其政府公共性開支包括社會保障支出出現縮減現象。
(二)國家、階級政治與社會保障支出
與全球化理論相對,強調國內政治因素的學者認為強大的國家能力、左翼政黨和工會是推動社會保障支出的兩大動力。國家中心論(state-centered)認為,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ies)是決定社會保障水平的重要因素①Margaret Weir, Theda Skocpol, "State Structures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Keynesian' Responses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Swede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eter Evans, et al.(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國家能力包括國家的行政能力(administrating capacities)、發現并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以及國家繼承的統治遺產(policy legacy)和已有政策的后果(policy feedback)等②J.Craig Jenkins, et al., "Class Force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Intervention: Sub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1-199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6, 111(4).。國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與政府的組織樣式(organizational forms)有關。權力相對集中(state centralization)的政體樣式——如議會制,相比權力分散的政體樣式——如美國式的參眾兩院制加多次否決權(veto points)的制度設置,由于其動員社會財富的能力更強、決策效率更高,因而更能促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③Evelyne Huber, et al., "Social Democracy, Christian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Welfare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9(3).。因此,是鐵血宰相俾斯麥治下獨裁的普魯士德國,而不是權力分散、政府規模小的民主制美國,最早建立了現代意義上針對勞工權益的社會保險制度。政策后果和政治遺產同樣能塑造國家結構和其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能力。不少學者在解釋美國福利水平較之西歐發達國家顯著較低的現象時指出,1935年美國社會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塑造了美國福利國家的格局。由于當時沒有將醫療保險法案包括在內,導致國家機構圍繞其他類型的社會保險進行組織和發展,這給醫療商業保險利益集團以可乘之機,它們的發展壯大進一步抑制了國家為全體國民提供全民醫療保險的可能④Edwin Amenta, Bruce Carruthers, "The Formative Years of U.S.Social Spending Policies: Theories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American State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8, 53(5).。
關注階級政治(class politics)的學者則多認可權力資源理論(Power Resources Theory),他們認為左翼力量是推動社會保障支出的重要力量。左翼力量包括左翼政黨(如工黨)和工會等群體。權力資源(power resources)與市場資源相對,資本家擁有較多的市場資源,如資本、財富等;但民主政治下“一人一票” 的設置使絕對力量占多數的工人和底層群體擁有更多的權力資源。通過民主政治,工人階級支持的左翼政黨上臺,他們作為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更傾向于通過有利于工人階級的擴大社會保障支出的法案,從而以再分配的方式修正市場分配⑤Walter Korpi,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pp.3-10.。需要指出的是,社會保障制度是一個整體,工人的訴求不僅直接推動和其自身直接相關的社會保險建設,也推動國家層面的社會保障支出,包括針對無業者、退休者、學生、幼兒等的社會保障。當“為公民提供各類社會保險和保障以應對市場風險”成為社會共識,并最初以員工社會保險的形式固定下來后,社會保障制度會逐步擴展到整個公民群體(從員工本人、員工家人擴展到公民整體),而不再以是否有固定工作作為獲取的門檻,因為人人生而平等并擁有同樣的公民權利是現代國家的共識和基本原則。
近來,這兩種觀點則出現整合的傾向,即學者們開始關注階級政治在何種制度環境下能促進社會保障支出。左翼力量起作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的制度設置。有些學者強調階級政治的核心地位,如“階級中心的國家中介理論”(class-centered and state-mediated approach)①Alexander Hicks, Joya Misra,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the Growth of Welfare in Affluent Capitalist Democracies, 1960-1982,"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9(3).;有些則更為強調國家結構(constitutional structure)②Evelyne Huber, et al., "Social Democracy, Christian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Welfare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9(3).,如政體中心理論(politycentered approach)③Theda Skocpol,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27-28.;還有的則認為國家制度結構與階級政治同等重要,如制度政治理論(institutional politics theory)④Edwin Amenta, Bold Relie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n Social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8-9.。
總之,強調政治因素的學者認為,國家與左翼力量的互動——更具體的說,國家如何響應來自工人群體的訴求——是理解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重要角度。這一視角亦可解釋為何獨裁國家普魯士德國最初建立了現代意義的社會保險制度。盡管獨裁國家缺乏制度性的利益訴求渠道(如民主政治下的選舉),但當時緊張的勞資關系、層出不窮的工人罷工給政權合法性帶來嚴重威脅。由于不能通過政府下臺疏解工人不滿和反抗,國家轉而通過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維系合法性。換言之,獨裁國家和民主國家一樣具有響應社會訴求的能力,只是響應方式有所不同。
(三)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支出
工業社會理論(Industrial Society Theory)認為,現代國家的社會保障功能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后果。在農業社會,個人因年老、疾病而喪失工作能力后,是由當地社區——家庭、村莊、教會——等提供各類福利救濟。工業社會的發展要求大量農民遷移到城市變成工業生產的勞動力,他們與原有的社區失去聯系,市場帶來的風險此時只能由現代國家承擔。同時,市場經濟也需要一支可持續的高質量的勞動力隊伍,這也刺激國家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⑤Clark Kerr, et al.,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66-68.。
根據工業社會理論,工業社會相比農業社會其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要高很多,工業生產帶來大量剩余。這導致工業社會的國家有財力為公民提供各種社會福利和保障。換言之,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社會保障支出的規模。
三、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社會保障支出
(一)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
社會保障制度服務于經濟發展模式,當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并積極融入全球市場時,原本的國家-單位保障制隨著單位制的瓦解逐步發展為國家-社會保障制⑥鄭功成:《從企業保障到社會保障: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遷與發展》,中國勞動保障出版社,2009年,第17-25 頁;童星:《社會主要矛盾轉化與民生建設發展》,《社會保障評論》2018年第1 期。。社會保障制度一般滯后于經濟制度的變革。盡管1978年就開始實行對外開放、引進并允許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的存在,但直至1986年七五計劃國家才首次明確提出社會保障概念,并將“社會保障社會化”作為國家-單位制的對立制度正式載入國家發展規劃。這是我國當代社會保障制度的起點。同年,國務院發布《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明確規定了合同制工人退休后養老保險實行企業與個人分擔交納保費的社會統籌,以及企業破產和失業職工的社會保障問題。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明確指出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系的支柱之一,提出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目標。1998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建立則意味著社會保障成為一項基本的社會制度。國家隨之出臺了一系列社會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法規,促進社會保障制度全面走向社會化和去單位化。
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的一大特點是地方政府承擔了絕大部分支出責任。2002年到2014年,中央政府的社會保障支出從58 億元上升到700 億元,地方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則從1331 億元升至15269 億元。地方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從2002年占總體的95.8%下降到2004年的90.2%,隨后便一直穩步上升到2014年的95.6%。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的內容上,如表1所示,二者的功能高度重合,均集中于社會保險、社會補助和社會救助三方面。主要區別在于,地方政府承擔了城鄉居民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的大部分支出責任,在經濟發達地區尤為如此①例如上海的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就全部由市政府承擔。上海市也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首創者。。
由于地方政府的財力不同、面對的經濟結構不同,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一直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發達地區如長三角珠三角,不但社會保障水平高,而且由于大量年輕勞動力參與,出現養老保險金大量結余的現象;相反,東北老工業基地由于退休人口多,導致待遇低、負擔重,甚至出現收不抵支的財務危機②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2016)》,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8-99 頁;郭林:《中國社會保障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思路與主要方向》,《社會保障評論》2017年第3 期。。

表1 中央和地方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內容③表中加黑的內容為支出較大的幾類。以中央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為例,2015年用于社會保險方面的支出占總支出的56%,用于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為總支出的10%。

資料來源:中國財政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財政年鑒(2016)》,中國財政雜志社,2017年,第259-269 頁。
鑒于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支出中起到關鍵作用,本文把關注的焦點放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社會保障支出上。表2給出了這兩個地區2014年的基本經濟指標。可見,長三角較珠三角面積更大、人口更多、戶籍人口占比更高。傳統上長三角包括16 個城市,即江蘇省的南京、泰州、南通、蘇州、揚州、無錫、常州、鎮江8 市和浙江省的杭州、寧波、湖州、嘉興、紹興、舟山、臺州7 市以及上海市;珠三角則包括廣東省的9 個城市,即廣州、深圳、佛山、中山、惠州、東莞、珠海、江門、肇慶。長三角的常住人口比珠三角高46%,戶籍人口則是其2.7 倍。兩地均是我國經濟繁榮富庶之地。2014年我國人均GDP 為47202.8 元,長三角和珠三角分別是這一全國水平的2.1 倍和1.9 倍。

表2 2014年長三角和珠三角基本狀況
(二)經濟全球化與兩地社會保障支出
珠三角和長三角是我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地區,也是受全球市場影響最深的地區。1980年至1990年,我國先后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5 個經濟特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洲為沿海經濟開放區,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旨在吸引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對外貿易逐漸成為拉動經濟增長、提高就業水平的重要工具,出口導向型戰略得以確立①袁欣:《中國對外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鏡像”與“原像”的背離》,《經濟學家》2010年第6 期。。
長三角和珠三角參與全球經濟的方式有所不同。圖5、圖6分別比較了這兩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方式。總體規模上,珠三角略高。其對外貿易占GDP 的百分比超過長三角30%以上,FDI 占GDP 之比也只是在2003年后才微弱低于長三角。珠三角經濟的外貿依存度更高,而長三角則在大部分時間內更依賴外商直接投資。
在全球經濟分工中,中國的情況是勞動力充裕而資本和技術相對稀缺,因此中國的比較優勢在于生產和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的產品,進口更多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都體現了這一特征,即均集中于勞動力密集的加工裝配行業。研究發現,對外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具有相互替代性①張軍、郭為:《外商為什么不以訂單而以FDI 的方式進入中國》,《財貿經濟》2004年第1 期。。無論外商是以訂單的方式(對外貿易),還是以投資的方式(外商直接投資),其對象都是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別是加工型的制造業。即使出口產品中機電產品的比例越來越高,其中相當一大部分也是針對零件的加工裝配組裝行業,而非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原創機電產品②郭克莎:《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研究》,《管理世界》2000年第2 期。。

圖5 對外貿易占地區GDP 百分比(2000—2014年)

圖6 FDI 占地區GDP 百分比(2000—2014年)
具體到長三角和珠三角,由于其在全球經濟中以低勞動成本、低技術含量位于產業鏈的低端,因而對勞動成本非常敏感。這兩個地區的對外貿易以制造業的加工貿易為主。盡管我國的勞動力價格低廉,但在國際市場上也要面臨其他低勞動成本國家如墨西哥、菲律賓、柬埔寨的競爭,因而會盡可能地降低勞動成本包括稅收負擔才能在國際競爭中取勝。根據“競爭效應”,對外貿易會對政府的稅收規模產生抑制作用。當政府的稅收收入有限,又面臨是將財力投入于經濟發展(如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公共服務(如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的權衡時,地方政府往往傾向于前者。在這個意義上,對外貿易會降低社會保障支出。
與此同時,對外貿易也可能會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對外貿易的繁榮意味著經濟規模擴大和政府稅源增加。即使外貿企業稅率有所降低,由于外貿企業的增加和產量的上升也會導致政府稅收收入的增加。另外,人民政府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為人民服務、關心人民幸福是人民政府的宗旨。以長三角的核心城市上海為例,盡管面臨全球競爭的壓力,上海市還是早在2003年起就建立了“小城鎮社會保險制度”(即鎮保制度),針對被征地農民以及未征地但土地被鄉鎮企業占用的農民,由政府、征地企業出資提供社會保障。2006年起,上海市還將無保障老人納入社會保障,由政府出資為其提供養老和醫療服務①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口述上海——社會保障改革》,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16-127 頁。。這里則體現了對外貿易的“補貼效應”,即政府增加支出保障那些因市場風險和制度變遷而難以維持體面生活的人群。
因而,對外貿易對社會保障支出有如下作用。
假設1:對外貿易對地方政府社會保障支出有顯著效應。
假設1a:對外貿易能顯著降低地方政府社會保障支出。
假設1b:對外貿易能顯著增加地方政府社會保障支出。
FDI 在一定條件下也會抑制社會保障支出。FDI 即外商直接投資,它是外國資本為獲得某個本國企業的利益進行的投資,目的在于在該企業管理中具有有效的發言權。國際上一般將外國投資者的股份超過10%作為界定FDI 的標準。在中國,FDI 的標準更高,即當外國資產股份占到25%以上時,外國資產資本的流入才被計入FDI。這一標準使我們更能考察到FDI 的本質,即外國資本對本國企業的管理和控制能力②黃亞生:《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5-18 頁。。FDI 流入我國目的在于通過管理控制合資企業,占領中國市場獲取更大利潤。他們傾向于盡可能減少上交的稅收,并且也不像本土企業那樣愿意為當地公共事業和民生事業付出。同時,由于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處于國際分工的產業鏈低端,對技術工人和高技術員工的要求不高,難以刺激地方政府出于發展經濟的考慮而進行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如對失業工人提供技術培訓等。這些都導致FDI 對社會保障支出的負效應。
然而FDI 也可能成為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力量,進而促進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FDI不僅意味著來自外國的資產和資本,它意味著我國與資本流出國因為這一資本流動建立了一種社會關系,包括制度關系、文化關系、經濟關系等方面①Nina Bandelj, "The Global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The Case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9, 74(1).。外資流入的過程因而是個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過程,它首先表明外資在我國獲得合法性,同時也說明隨外資流入的先進技術和相對規范的管理模式,包括簽訂勞動合同、提供社會保險、保障員工福利等都獲得了合法性。這被稱為FDI 的“溢出效應”②李金昌、曾慧:《基于金融市場發展的FDI 溢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省際面板數據研究》,《統計研究》2009年第3 期。。FDI 的不斷擴大促成了我國幾部勞動法律的頒布,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勞動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勞動法》。這些法律的出臺既是出于吸引外資的需要,也吸收了外資企業的一貫做法和習慣。法律規定了職工各項勞動權益包括參與社會保險、簽訂勞動合同的權利③Mary Gallagher, "Reform and Openness: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Delayed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2002, 54(3).。員工社會保險的穩步發展推動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促進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針對長三角的一項研究表明,以外資為主的某市社會保障支出顯著高于以內資為主的某市④葉靜、耿曙:《全球競爭下的“競趨谷底”?發展路徑、政商關系與地方社保體制》,《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 2013年第1 期。。
因而,FDI 對社會保障支出的影響既可能是消極的,也可能是積極的。
假設2:FDI 對地方政府社會保障支出有顯著效應。
假設2a:FDI 能顯著降低地方政府社會保障支出。
假設2b:FDI 能顯著增加地方政府社會保障支出。
(三)地方政府、勞動爭議與社會保障支出
改革開放以來的地方政府具有相當的財政支配權和自由裁量權,并且承擔了絕大多數公共服務,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因而,地方政府的社會保障支出規模不是單純由中央政府決定的,而是受到全球因素以及地方政治、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這構成本研究的出發點。
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是決定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的動力之一。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經濟發達,地方財政收入連年實現兩位數增長,使擴大社會保障支出規模成為可能。以長三角的蘇州和珠三角的東莞為例,2012年和2000年相比,兩地的GDP 分別增加了7.79 倍和6.14 倍,財政收入則增加16.19 和25.54 倍⑤據各市統計年鑒計算。。財政收入增速顯著高于GDP 增速,為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提供充分的經濟支持。但經濟發展也意味著政府在培育市場、促進民生方面的職責越來越重。如果財政支出的需要大于財政收入,社會保障支出的規模也不會迅速擴大。因而,財政盈余能力與社會保障支出是正相關。假設3 如下。
假設3:財政盈余越高,政府社會保障支出越高。
地方政府的社會保障支出規模還受到中央對其考核標準的影響。長期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使地方官員的考核標準集中于GDP 等經濟指標上。在這一制度環境下,地方官員將財政收入集中投向經濟發展方面,如培育市場、基本建設、產業升級等。他們開展橫向的“GDP 錦標賽”,通過做出最好的經濟政績實現個人的職業晉升①周黎安:《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與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5-62 頁。。相形之下,地方政府在民生方面投入不足,社會保障支出偏低。
2006年以來,隨著維穩成為一票否決的高壓線, 信訪一票否決制成為地方官員的考核標準②周黎安:《行政發包制》,《社會》2014年第6 期。。勞動爭議作為一種制度化的處理勞資糾紛、維護職工權益的機制,同時也是信訪案件的重要來源。地方官員為“消滅”信訪,尤其注重整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并大規模地提高社會保障支出。2005年10月,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 并將促進社會公平、完善社會管理作為地方政府社會治理的要求之一。在此基礎上,2005年重新修訂了《信訪條例》,并對各地進行信訪工作排名,實行信訪一票否決制。
在歷史上,勞動爭議是作為信訪制度的補充機制存在的。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勞動爭議被當成人民內部矛盾一律訴諸勞動信訪處置。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企業改制、工人下崗、失業激增,信訪制度已經無法容納工人的各種訴求,中央遂重啟勞動爭議。勞動爭議主要涉及員工合同、社會保險、員工工資等各項勞動權益,采取“一調一裁二審”模式,發生爭議時先由企業調委會調解,失敗了可以申請勞動仲裁,仲裁不服的再向法院起訴③莊文嘉:《“調解優先”能緩解集體性勞動爭議嗎?》,《社會學研究》2013年第5 期。。在這相對較長的時間里,提起勞動爭議的職工往往同時采用多種行動模式。據針對某市3110 宗集體勞動爭議的分析,其中1192 宗勞動爭議都采取了信訪,占總數的38.33%,居五大行動模式——信訪、罷工、舉報投訴、堵路、堵廠——之首④孔令明:《集體性勞動爭議實證研究——基于某省D 市近十年3110 宗爭議原始資料》,《社會科學論壇》2016年第10 期。。
勞動爭議案件是信訪案件的重要來源,也是一地信訪風險的重要指標。對地方政府而言,勞動爭議案件越多,發生信訪案件的可能性就越大。從而在“信訪一票否決制”的壓力下,地方政府就越可能通過增加社會保障支出、促進社會保障制度發展來減少勞動爭議案件、降低本地發生信訪案件的數量和可能性。例如,上海的鎮保制度通過解決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從根本上解決了此類信訪問題⑤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著、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口述上海——社會保障改革》,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76 頁。。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勞動爭議案件本身針對的是職工的勞動權益和社會保障,但政府對此類問題的關注不但會促進職工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也會相應帶動居民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和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
地方政府對勞動爭議的響應取決于中央考核這一制度環境。這也解釋了為何2006年起隨著“信訪一票否決制”納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標,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各城市也都出現了顯著的社會保障支出增加的現象,而其他類型的公共服務支出——教育、醫療等,由于其較難納入簡單的指標體系,仍停留在相對穩定的水平。因而,假設4 如下。
假設4:勞動爭議越多,地方社會保障支出越高。
(四)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支出
根據前述“工業社會理論”,隨著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以往承擔社會保障功能的傳統家庭、親族、共同體逐漸解體,這些功能轉而由現代國家承擔。這種觀點認為,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國家能提供的社會福利的內容、覆蓋面和規模。
假設5:人均GDP 越高,地方社會保障支出越高。
假設6:經濟增長速度越快,地方社會保障支出越高。
四、數據與方法
本研究分別選取長江三角洲16 個城市和珠江三角洲9 個城市從2000年到2014年共計15年的數據進行歷時性分析。這種數據是時間序列的截面數據(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al Data),又稱面板數據(Panel Data),研究單位是市-年。例如南京市在2014年的數據構成了一條記錄(observation)。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各城市統計年鑒。
將研究起點設置在2000年有以下幾點原因。首先,截至2000年,我國初步建立起市場經濟下的社會保障制度。1998年以前,社會保障由多個部門分管,管理體制混亂無序。如社會保險即由勞動部、人事部、民政部以及鐵道、交通、銀行等10 多個部門分別管理;社會救助雖然由民政部負責,但城鎮職工卻被排除在外;在醫療保障方面,公費醫療與勞保醫療一直被分割管理。1998年3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成立標志著權責分明的統一社會保障體制的確立。民政部負責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則專門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負責。具體到各項社會保險,1997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1998年12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1999年1月國務院頒布了《失業保險條例》,1999年9月國務院頒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2000年以來,我國進一步頒布了《工傷保險條例》,發展了農村社會保險,并啟動了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第二,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中國在更深的程度上參加全球競爭。經濟全球化對社會保障支出的影響較之以前更為顯著,對勞資關系的影響也更為深遠。第三,數據的限制。2000年以前由于社會保障制度政出多門,數據統計口徑不一且分散在各處,難以進行跨地區跨時間的比較。
本研究采用廣義線性回歸(GLS)中針對面板數據的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模型進行分析①對本研究來說,統計分析的內生性主要源于遺漏變量偏誤,即影響社會保障支出的因素可能是未被控制的城市其他特征或高于城市的某些宏觀因素(如金融危機等)。解決方式如下:第一,本研究采用追蹤面板數據,從而控制了城市層面差異;第二,通過控制年份固定效應,排除了宏觀因素可能的干擾。。首先,面板數據的特點是數據之間具有高度相關性,如南京市2012年的人均GDP 與2013年的數額必然高度相關。這違背了OLS 回歸中關于樣本獨立的假設,從而不能使用一般的回歸方法進行分析。其次,面板數據的另一個問題是需要保證該數據是平穩的時間序列,對于存在單位根(unit root)的非平穩序列需要用差分(difference)等方法進行處理,否則會產生偽相關。本文對存在單位根的變量進行差分處理后再進行回歸分析。第三,在采用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還是固定效應(fixed effect)模型上,本文選用了隨機效應模型。這一方面基于Hausman 檢驗不顯著的判斷,另一方面本研究使用的數據特征使隨機效應模型比固定效應模型更具有統計優勢①Hugh Ward, et al., "State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Gap in Authoritarian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2, 45(9).。本文數據共涉及25 個城市(N=25)的連續15年(T=15),即每個城市只具有14 個自由度。由于面板數據自變量的滯后效應②即某年的人均GDP 只能對次年及之后年份的社會保障支出產生影響,難以對當年的社會保障支出產生影響。,對自變量滯后一年處理后會減少一個自由度,而固定效應估計時又會使用一個自由度,這樣帶來大量信息丟失會使標準差增加,從而導致估計有偏。另外,固定效應模型難以處理自變量對時間不敏感的情況,而本數據中若干個城市的城市化、老齡化水平在2000—2014年都變動極小。綜上,本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并對自變量做滯后一年的處理。這也符合福利社會學研究的常規。回歸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β0是整個模型的截距,βi是每個單位(城市)截距,它服從正態分布。Xβ是自變量矩陣,εi,t是殘差。
因變量。本研究將人均社會保障支出作為因變量,其中戶籍居民數量作為分母。因為政府社會保障支出主要是針對戶籍居民的。具體操作中對這一數值取對數,以避免估計中產生的偏誤。由于各城市規模不同,社會保障支出總額難以反映該地對每位居民的保障水平。而社會保障支出占GDP 的百分比或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僅能反映社會保障與經濟規模和財政規模的關系,難以體現它對個人的保障程度。所以,本文采用人均社會保障支出是合理的。
自變量。自變量首先包括經濟全球化的兩個變量:(1)對外貿易總額占GDP 百分比;(2)外商直接投資(FDI)占GDP 百分比。這兩個變量也是最常用的測量經濟全球化對本國影響程度的變量。
第二組自變量是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及其對社會訴求的響應。分別采用(3)該地某年度的財政盈余(取對數)和(4)每百名工人中勞動爭議的數量來衡量。財政盈余等于財政收入減去財政支出,正值說明出現財政盈余,負值則意味著財政赤字。
第三組自變量是該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分別采用(5)人均GDP(取對數)和(6)GDP 增長率來衡量。
控制變量。在對社會福利支出水平的解釋中,本文控制了(1)社會平均工資水平。政府對社保基金的注資、城鄉居民養老、醫療保險的水平等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的項目都與社會平均工資的水平有關,因而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在一定程度決定了社會保障支出的規模。接下來是描述本地人口狀況的兩個變量:(2)老年人口比例;(3)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基本假定是,老齡化會拉動社會保障支出特別是養老和醫療方面的支出。城市化中帶來更多城市貧民和失業人口,也要求政府增加社會保障支出。
以下是主要變量的描述統計:

表3 各變量描述統計
五、分析與討論
分析發現,經濟全球化對人均社會保障支出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體現了全球化的“競爭效應”。在此背景下,地方財政能力、勞動爭議數量和經濟發展水平構成地方社會保障支出的主要動力。財政盈余越高,政府越可能擴大社會保障支出。勞動爭議數量作為潛在信訪風險的指標,推動政府擴大社會保障開支以免被“信訪一票否決”。人均GDP 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顯著促進了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總之,如果說經濟實力和財政能力為政府擴大社會保障支出提供“可能性”,那么勞動爭議水平在“信訪一票否決制”的制度框架下,則提供擴大社會保障支出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比較長三角和珠三角可以發現,長三角的地方政府更能抵御經濟全球化對社會保障支出的抑制作用。相比之下,珠三角則體現了鮮明的“競爭效應”。政府的支出動力來自勞動爭議的壓力,并且這種壓力緩和、扭轉了“競爭效應”。長三角社會保障的動力是財政能力、勞動爭議和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全球化的效應并不一致:FDI 體現為負效應,但對外貿易在一定情形下則體現正效應。在珠三角,經濟全球化具有顯著的一致的負效應。有意思的是,這一負效應的規模取決于勞動爭議的數量。當勞動爭議超過每百人一件,負效應消失,并進而轉變為正效應。假設1、2、3、4、5 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驗證。
(一)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社會保障支出決定因素
表4報告了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地社會保障支出的決定因素。模型1 放入所有自變量,包括全球化、地方政府財政能力與勞動爭議以及經濟發展指標。模型2 在模型1 的基礎上增加了3個控制變量,分別是社會平均工資、老齡化和城市化程度。

表4 長三角和珠三角社會保障支出的決定因素
對外貿易體現了競爭效應,抑制了地方政府社會保障支出。根據模型2,對外貿易占GDP百分比每上升一個單位,人均社會保障支出下降0.1%(=1-e-0.000999)。在這一背景下,社會保障支出的促進因素主要是勞動爭議數量和經濟發展水平。每百人勞動爭議數量每上升一個單位,人均社會保障支出上升94%①每百人勞動爭議數量取值范圍為[0.17,1.71],即勞動爭議最多只能上升1.54 個單位。換言之,每百人勞動爭議數量上升1 個單位是很大的范圍,因此這里的94%只在極少數情況下才出現。(=e0.664-1)。在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中,人均GDP 顯著,即人均GDP 的對數值每上升一個單位,人均社會保障支出上升87%(=e0.631-1)。GDP 增速則不顯著。財政盈余促進了社會保障支出。它的對數值每上升一個單位,人均社會保障支出增加6.4%(=e0.0064-1)。
在控制變量中,城市化促進了社會保障支出,社會平均工資也與人均社保支出體現正向顯著關系。另外,老齡化對社會保障支出有消極影響,這符合威權主義的邏輯,即在威權體制下,福利支出對選民的特征并不敏感,這也與學者對拉美國家的研究相一致①Nita Rudra, Stephan Haggard, "Globalization, Democracy, and Effective Welfare Spend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5, 38(9).。
表4說明,盡管經濟全球化對人均社會保障支出有抑制作用,地方財政能力、經濟發展水平和作為信訪風險信號的勞動爭議數量都推動政府擴大社會保障開支。那么長三角和珠三角有沒有以及有什么區別?表5、表6分別考察了長三角和珠三角社會保障支出的決定因素。
(二)長三角社會保障支出的決定因素
表5模型3 放入所有的自變量和控制變量,模型4 至模型6 則分別添加了勞動爭議與FDI、勞動爭議與對外貿易以及所有交互效應。模型顯示,經濟全球化在長三角地區不具備顯著一致的作用模式。對外貿易和FDI 的作用方式相反,并且在多個模型中不具有一致的作用方向。對外貿易盡管在模型3—4 體現正效應,但在模型5—6 則失去顯著性;FDI 在模型3 和模型5 體現負效應,但同樣在模型4 和模型6 不具備顯著性。在國內因素中,勞動爭議數量和人均GDP、GDP 增速均系促進社會保障支出的作用力量。財政盈余在模型3 和模型5 顯著。在控制變量中,社會平均工資是正向關系,老齡化作用并不顯著,城市化則僅在模型4 和模型6 體現顯著的正效應。

表5 長三角社會保障支出的決定因素

注:1.括號內是標準誤;2.*p < 0.1,**p < 0.05,***p < 0.01(雙側檢驗)。
總之,構成長三角社會保障支出動力的主要為國內因素,特別是勞動爭議數量和經濟發展水平。全球化的作用則不夠一致和穩定。也可以說,長三角地方政府較能抵御全球競爭以及外資的各種壓力。這部分上可由該地區較強的政府管理能力和關注民生的傳統解釋①萬向東等:《工資福利、權益保障與外部環境——珠三角與長三角外來工的比較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6 期。。研究發現,長三角地區針對勞工權益(如勞動合同簽訂等)開展過多項整治行動②劉林平等:《勞動權益的地區差異——基于對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外來工的問卷調查》,《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2 期。,切實保障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推行。另外,部分城市如上海,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一直走在全國前列。上海于1993年在全國首創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即“低保”),并向全國推廣;上海還早在1996年就頒布了《上海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屬于全國最早、保障水平最高的機制。關注居民社會保障的傳統使該地區在面臨負面壓力時仍能延續并擴大既有的社會保障水平。
(三)珠三角社會保障支出的決定因素
表6按照表5的思路,在分析珠三角社會保障支出的決定因素時,分別將主效應與交互效應放入模型。和長三角不同的是,經濟全球化在珠三角地區顯著抑制了社會保障支出。其中對外貿易體現了鮮明的“競爭效應”,它在所有4 個模型中都表現負向的顯著效應。這也與珠三角卷入全球化的方式一致,即以對外貿易為最主要方式。FDI 只在模型8 中體現負效應。與長三角一致,勞動爭議和人均GDP 同樣構成社會保障支出的動力。但不同的是,勞動爭議與對外貿易和FDI 的交互效應均顯著。這表明,勞動爭議的作用規模取決于經濟全球化的水平,或者說經濟全球化的作用規模取決于勞動爭議的水平。在控制變量中,與長三角一致,社會平均工資與社會保障支出正相關,城市化水平不顯著,老齡化則為負顯著。
勞動爭議與經濟全球化的交互效應可以用邊際效應圖來表示。圖7和圖8分別描繪了對外貿易與FDI 的邊際效應如何隨勞動爭議數量的增加而變動。圖7表明,當每百人勞動爭議數量大于0.8 時,對外貿易的負效應消失,并隨勞動爭議的增加進而變為正值。這說明,勞動爭議能緩和、扭轉甚至改變對外貿易的“競爭效應”,將其變成“補貼效應”。但在336 個樣本中,只有29 個樣本的邊際效應值為正,占總數的8.6%。也就是說,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外貿易的邊際效應仍為負值。這也就是為什么95%置信區間的下端值(虛線表示)一致處于0 刻度以下。圖8報告的FDI 邊際效應則顯示,當每百人勞動爭議數量大于0.3 時,FDI 的負效應被抵消,并隨之變為正效應。在336 個樣本中,有306 個樣本的邊際效應為正,占總數的91%。總之,FDI 的邊際效應在大多數情況下為正。

表6 珠三角社會保障支出的決定因素

圖7 珠三角地區對外貿易的邊際效應

圖8 珠三角地區FDI 的邊際效應
勞動爭議能改變經濟全球化的抑制作用,這一方面表明珠三角地方政府較之長三角更容易受到全球經濟的左右,更容易按照外資的需求和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降低社會保障支出。另外,勞動爭議的積極作用也顯示,隨著地方官員考核標準的變動,地方官員開始真正著力解決民生問題和勞動者的權益問題。
六、結論
經濟全球化對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s)的影響是政治社會學中的重要議題。這不僅因為福利國家的水平關系到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市場產生的不平等、促進社會公平。更重要的是,這一議題涉及現代國家的核心功能——為國民提供社會福利和保障。本研究是一次系統地采用經驗數據,對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社會保障水平決定因素的考察分析。與國際上多數對發展中國家社會保障支出的研究不同,本研究發現,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我國仍能實現社會保障支出的連年增長。支撐這一快速增長的動力主要是地方政治、經濟因素。一方面,“信訪一票否決制”新增為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標準之一,這要求地方政府從片面發展經濟的“GDP 錦標賽”中走出來,開始關注社會穩定和民生問題,并進而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和支出的穩步增長。另外,地方經濟繁榮、財力充足也為社會保障支出規模的擴大提供經濟基礎。本研究的發現為福利國家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證,即深受全球化影響的發展中國家仍能實現社會保障支出的增長,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可以并行不悖。
通過進一步比較長三角和珠三角,本研究發現,兩地參與全球化的方式不同,這部分解釋了兩地社會保障的支出模式。珠三角作為我國最早開放的地區,對外貿易一直都高于長三角,FDI 也是2004年后才被長三角超過。因而,它的社會保障支出顯著受到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并且對外貿易呈現一致的顯著負效應。長三角的開發開放比珠三角略晚,它以1984年上海開放、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為標志,在參與全球經濟中更注重吸引外資。盡管我國的對外貿易和FDI均高度集中于利潤低的加工制造業,但相比之下,FDI 意味著對合資企業的管理權,涉及的產業層次、企業規模、技術水平都較高;而對外貿易則涉及各類企業特別是較小的民營企業規模大小不一,技術水平參差不齊。總之,FDI 對成本控制的要求沒有對外貿易那樣嚴苛。這也使得長三角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不太容易受制于全球競爭的抑制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巨大,各地無論是參與全球化的程度,還是社會保障支出的水平都差別巨大。本文基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研究發現并不一定適用于其他地區。這個缺憾有待于基于全國數據的進一步研究來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