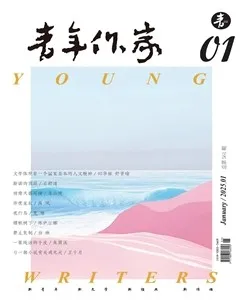君從故鄉(xiāng)來
在籍貫一欄,我填的是廣西凌云縣,那是我祖輩生長生活的地方,有許多與我血脈相連的人居住在那兒。談到故鄉(xiāng),很多時候我便默認(rèn)是凌云。但有一個小城,我離開幾十年從未踏足,可它的街道屋宇山頭樹木與人,細(xì)節(jié)豐富固執(zhí)鮮活地印在我的腦海,正如昨日重現(xiàn),讓我發(fā)現(xiàn)在血脈傳承的鏈條之外,故鄉(xiāng)更應(yīng)該是記憶的源頭。
如今記憶力一直在衰減,許多人與事不知不覺被拋在腦后,就算是拼命想記住的內(nèi)容,也扛不住腦細(xì)胞的衰敗與死亡,好在抓住當(dāng)下才是最實(shí)際的修行,過去與將來都是虛妄。在記憶自行斷舍離的過程中,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我最好的記憶有相當(dāng)一部分是九歲以前的生活。我的出生地是一座叫西林的小城,歷史上著名的“西林教案”的發(fā)生地,號稱廣西的省尾,與貴州接壤。九歲之前我就生活在那兒,那以后我隨父親回到凌云,待了兩三年,又遷到別處。從離開西林那日起,幾十年飛逝,我沒回去過,但是,不需要閉上眼睛,我輕而易舉就能讓這個小城當(dāng)年的模樣浮在眼前。
西林縣城的四面都是土山,幾乎一個單位占據(jù)一個山頭。每一個山頭上有彎彎曲曲各種走向的水泥或磚頭臺階,通往家家戶戶。商業(yè)系統(tǒng)占據(jù)的山頭是我最常去的地方,有好幾位同學(xué)的家在上頭,我不懼爬坡爬臺階,和伙伴們玩得天昏地暗。偶爾我們爬到靠近山頂?shù)牡胤剑灰娨黄艿臉淞衷陲L(fēng)中搖曳,以那種會脫皮的桉樹居多。
我的家很長一段時間安扎在縣城的電影院旁邊,縣城中心位置,相當(dāng)于電影院的耳房,一大家子人住的地方比麻雀窩大不了多少。因為屋子和電影院連成一片,院門朝向大街,每逢圩日,四方來人當(dāng)中有一部分人內(nèi)急時會竄到我家的院子里解決問題,我家搭的簡陋洗澡間變成了藏污納垢之地,怎么掛牌寫字警告都不起作用。電影院有兩扇側(cè)門與我家院子共一堵墻,從門縫或是窗戶都能偷看電影。我的父母是禁止我和哥哥這樣做的,但他們防不勝防,有那么多扇窗戶,有那么多道門縫,我們總能偷看電影,只是角度讓我們的脖頸和身體不太舒服。當(dāng)我們的眼睛嵌在門縫聚精會神地觀影時,拿著電筒來回走動的工作人員會用手電筒照向我們,呵斥我們,我們扭身閃開,他們一走,我們的眼睛又扒到門縫上了。當(dāng)然,更多的電影是我們買票進(jìn)去看的,扒著門縫看的電影有我們看過無數(shù)遍的,例如《閃閃的紅星》《地道戰(zhàn)》,也有像《一江春水向東流》《畫皮》《紅蝙蝠公寓》這類父母覺得兒童不宜,大人自己買票去看根本不帶上我們的電影。我們只能選擇偷窺,反反復(fù)復(fù)看上幾場,內(nèi)容基本掌握,和同學(xué)伙伴們針對故事情節(jié)侃侃而談時,總能勝人一籌。書非借而不能讀,影非窺而不能銘,頗有點(diǎn)這個意思。
郵局也在縣城的中部,電影院的對面。我有兩個同學(xué)家在郵局的宿舍區(qū),其中一個是班長,學(xué)習(xí)特別好,一個是我的好朋友,我經(jīng)常繞彎到她家,叫上她和我一道去學(xué)校,我們有一路的天好聊。我們還一塊種過蓖麻,上山摘過蓖麻。當(dāng)時學(xué)校號召學(xué)生種蓖麻,每人發(fā)了一把蓖麻籽。我們在屋前屋后開荒種蓖麻,整個電影院的四周都被我們種上了。我們眼盯著一窩的蓖麻發(fā)芽抽條開花結(jié)籽,我們熟悉每一棵蓖麻的生長情況,成熟的蓖麻被我們及時摘取,我們還到附近的山上去搜尋野蓖麻,也會摘到一些。我們的蓖麻合到一塊兒勉強(qiáng)夠一斤,那時我們非常誠實(shí),不飽滿的蓖麻我們都會扔掉,認(rèn)為收購站是不會收的。收購站一斤給價四毛二分,我們每人分了兩毛一。小伙伴用錢買了餅干水果糖,我買了連環(huán)畫,我們實(shí)現(xiàn)了共享,精神口腹皆愉悅。我們討論說種蓖麻來錢太慢,我們收集了一年才收獲一斤,不如收集鐵和銅。我們經(jīng)常到垃圾堆和各種工地上翻找,螞蟥釘鐵線弄到一些,鐵鍋舊刀具這些很少能弄到,主要是競爭對手太多,我們搶不過男生。金屬類物品收購站給的價格更低,一大堆換回幾分錢,吃幾根雪條就沒了。沒隔幾天伙伴在垃圾堆尋找廢鐵時,腳底被銹鐵釘扎穿,被大人送到醫(yī)院打破傷風(fēng)針,我們賺大錢的計劃無限期擱置了。
后來我家搬到縣城的南邊,算是比較偏遠(yuǎn)的縣政府家屬大院,房子寬敞多了。離家不到五十米就是客車站,客車站后面是一條河,我和車站員工的孩子經(jīng)常中午不睡覺到河邊用泥箕捉魚,把捉回來的小魚放進(jìn)一家人用水的大水缸,不幸死去的魚讓那一缸水變得腥臭,我少不了又被大人數(shù)落。過了河是縣醫(yī)院,很偏遠(yuǎn),我在那住過院,急救,差點(diǎn)沒搶救過來。有一次我哥哥的腦袋被人開了瓢,也是在那做的處理,我臉貼在窗戶上,看到醫(yī)生用一團(tuán)一團(tuán)的藥棉在傷口上蘸血,鮮艷艷的,我想吐,手腳冰涼,那時候我就知道我做不了醫(yī)生。
平時看病我們更喜歡選擇八達(dá)鎮(zhèn)醫(yī)院,它在縣城的中心位置,我在那兒拔過牙、開過中藥治百日咳,還被針挑手指頭治過疳積。好多醫(yī)生認(rèn)識我這只小藥罐,我只要路過有事沒事會進(jìn)去轉(zhuǎn)上一圈,守中藥柜那個老中醫(yī)偶爾會塞給我一小節(jié)甘草。甘草撕下一絲放進(jìn)嘴里,能讓嘴甜上半天。有一個醫(yī)生留著長發(fā),臉是男相,說話也是男聲,身材高大,抽煙,可她偏偏是女身。在孩子口中傳說她長了兩套性別系統(tǒng),我無法分辨,卻被這個傳說震撼。我進(jìn)入醫(yī)院經(jīng)常看到她在過道上用鍘刀切藥,我能看到的是她的力氣很大,手起刀落,一捆草藥顆粒狀滾落。我試過靠近鍘刀,也想試一試,每每被她厲聲呵斥,讓我離遠(yuǎn)一點(diǎn),否則手指頭保不住。她的聲音又粗又硬,見到她我總不自覺離開兩尺遠(yuǎn)的距離,但我一直在暗自觀察,想看出除了長發(fā)以外,她身上哪兒還有女人的特征。
縣城有兩所小學(xué),縣一小和八達(dá)小學(xué)。八達(dá)小學(xué)離我家近,但父母讓我上的是一小,說一小教學(xué)質(zhì)量更好。那年月沒有拐賣兒童一說,孩子們上到幼兒園大班都是自行走路上學(xué)。一小好遠(yuǎn)啊,從我家到學(xué)校,幾乎是從縣城的一頭走到另一頭,那時候不覺得遠(yuǎn),一路上和同學(xué)打打鬧鬧就到了。我們放學(xué)時跑到馬路上,偶爾見到一輛馬車,跟車夫打聲招呼,他們會載我們一程。放學(xué)回家必經(jīng)過糧所,糧所有一間間的倉庫,倉庫門經(jīng)常是敞開的,晾曬谷米還有面條,有時還會拋出一窩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老鼠和老鼠崽。我和同學(xué)的愛心泛濫成災(zāi),我們義不容辭地把老鼠帶走搶救,用磚頭給它們搭建新屋,給它們喂水和青草,抹上清涼油,直到它們真的死透,再給它們建上一個小墳。在放學(xué)的路上,我們還禍害過無數(shù)的蜻蜓,我們捉住蜻蜓,把蜻蜓的尾部扯斷,插上棍子連上細(xì)繩做成一架架飛行器。孩子們的殘忍和善良一樣,都在那里。
我還有一個好朋友住在文藝隊的宿舍區(qū),那個地方我一直覺得聚集了全世界長得最好看的人,那些姐姐長得跟天仙一樣,各有各的美。看著她們,我雖說還未了解自卑的內(nèi)涵,但那時我已確定,我永遠(yuǎn)長不成像她們的樣子。我的好朋友長得也很美很美,難道是近美者美?我經(jīng)常進(jìn)入文藝隊的練功廳看美麗的姐姐們劈腿下腰,更驚奇于一些小哥哥們的腰也如此柔軟。我看他們排演各種節(jié)目,我的好朋友偶爾會在一些劇目中客串角色,她真是太幸福了。我父親寫的一些本子后來也被這些美麗的人兒排演著,在禮堂演出時我坐在第一排,我無比光榮,跟我搭訕的人都被我一一告知,舞臺上演的劇是我爸寫的。
我在一小上到三年級就隨父親的工作調(diào)動離開了西林。我清楚地記住了許多班上同學(xué)的名字和他們的長相。多年以后,我已在省報工作,有一次觀看本單位與外單位的羽毛球賽,一個剛上場的男生被我認(rèn)出來了,我認(rèn)出他是我的小學(xué)同學(xué),坐在我的前一排,他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冬天一直掛著兩條黃鼻涕,被老師叫起來回答問題十有八九不會。那時還封建,男女生互相不說話。我認(rèn)出他后上前問他是不是姓石,他點(diǎn)頭。我說,我是你的小學(xué)同學(xué)。我把名字說出來他一臉懵然,完全不記得有我這樣一個人了,畢竟我們只同學(xué)三年多,還是小學(xué),又分開了將近二十年,記不住正常。但他相信我是他的同學(xué),因為他也有他的記憶,在講述的過程中,那個時間那個小城我們記憶的背景板是一樣的。
四十年過去,我知道我記憶中的小城早已面目全非,甚至可能讓我一點(diǎn)蛛絲馬跡都找不出來。我不止一次接受邀請,讓回西林看一看,感覺就是差點(diǎn)動力,一直沒有成行。
機(jī)緣來時是不需要什么準(zhǔn)備的。2021年7月,女友歐潔要到西林辦事,將自駕前往,邀我同行。“兩天時間要扔在路上。”我給女友這么說,卻又像顯示自己的俠義,同意與她一道同行。嘴上是答應(yīng)了,我心里頭莫名煩躁,仿佛一個重要的行程不應(yīng)該是這么個開啟的方式。
從南寧自駕一天到西林對女司機(jī)來說是不理智的,我們先到百色歇了一夜,第二天再從百色前往西林。坐在車上,車子朝百色的方向前進(jìn),我還是有點(diǎn)不太確定,懷疑我是否花上幾個小時就可以回到遠(yuǎn)離了四十年的地方。
在路上,我給西林的文學(xué)愛好者羅皓宇發(fā)了信息,告訴他我要到西林的消息。在這之前我沒有與羅皓宇見過面,他是早年通過一個群加了我的好友。每年西林砂糖橘成熟的季節(jié)他都問我要地址,要給我寄水果。我每次都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我相信以他的性格每年都要往外頭寄不少砂糖橘,對于一個基層作者來說,怕是不小的負(fù)擔(dān)。我也怕欠人情,不知道如何還,我天生不愿與人太熟絡(luò)的性格在很多人看來是高傲,自以為是,其實(shí)我是太缺乏與人交往的能力,退縮罷了。如果不是這方面能力有欠,我怎么在西林只識得羅皓宇一人?
羅皓宇和另外一名文學(xué)愛好者黃仕偉在那勞鎮(zhèn)迎接我們,請我們吃飯,并帶我們參觀宮保府建筑群。宮保府為清代云貴總督岑毓英所建。岑毓英為那勞人,他的兒子岑春煊也出生在那勞,后來任過兩廣總督。岑春煊少年時曾就讀于泗城(凌云)云峰書院,后隨岑毓英赴任地讀書。凌云縣博物館里有好幾塊牌匾與岑春煊有關(guān),這位名人將西林與凌云兩個縣城關(guān)聯(lián)起來了。
吃飯時聊天我才知道羅皓宇他們今天和縣里的一幫文學(xué)青年有外出采風(fēng)活動,臨時聽說我來,就提前結(jié)束那邊的活動過來接我們。從那勞往西林,不過半個小時的路程,這段路程于我就是入西林城的一個鋪墊。我關(guān)注自己的內(nèi)心,激動是沒有的,反倒漫上來一種無所適從的茫然。路兩邊的景致像水一樣滑往身后,縣城的街道突然呈現(xiàn)在我面前,人來人往,店鋪林立,車輛穿梭。我像闖入一個秘境,這里的生活與我無關(guān),我來與不來,一切都按部就班上演。有時候成為旁觀者,心態(tài)會特別安逸,不參與其中,沒有壓力,不被牽扯。但現(xiàn)在的我卻有一種不甘,這里怎么就讓我置身事外了?
羅皓宇的車在前頭領(lǐng)路,我們到達(dá)入住的酒店,與兩位男士告別。羅皓宇約晚上一起聚餐,我極力推辭,因為中午已經(jīng)吃過人家一頓,實(shí)在不想再勞煩別人,但羅皓宇十分堅持。我們稍事休息,下午歐潔出去辦事,我也與她一道跑了一些地方。她這一趟來主要是考察西林某行業(yè)的行情,沒有非做成生意的壓力。期間接到一個侄兒的電話,說聽說我到西林來了,他在西林工作,要請我吃晚飯。我父親有六個哥哥,我有二三十個堂哥堂弟,侄兒多得記不住名。但這個侄兒我是有些印象的,讀完大學(xué)后來考公務(wù)員到一個鄉(xiāng)里當(dāng)警察,原來是到了西林的古障鎮(zhèn),最近調(diào)到縣里來了。我來西林這趟跟父母提了一嘴,他們馬上傳聲給這個侄兒了。凌云的孩子跑到西林當(dāng)警察,在西林娶妻生子,成西林人了,感覺他替我做了些什么,說不清楚,我總不能認(rèn)為他是替我活在西林吧。我說晚飯已經(jīng)答應(yīng)別人了,他又約了夜宵。
天還很光亮,羅皓宇來了電話,說晚上吃牛肉火鍋。我和歐潔無所事事,驅(qū)車往飯店。羅皓宇和黃仕偉已經(jīng)在候著,菜都點(diǎn)好了。中午吃得太飽,沒有太多食欲,隨便吃了一些。歐潔認(rèn)識的朋友從外地回來,一個又一個電話催我們換場去吃夜宵。羅皓宇當(dāng)場做主,把所有人召集到一個大排檔上,包括我的侄兒。南方的夜宵是一種值得研究的文化現(xiàn)象。聚在一起吃夜宵的一般交情都好,性格也隨意,也不會有人真正是餓了肚子找吃來的,大家腹中已經(jīng)有晚飯墊底,到了夜宵場上就放開以啤酒為主,燒烤為輔,聊些雞零狗碎事,很少談?wù)隆F【葡碌每欤辉幌湎洌詈鬀]有人記得聊了啥,圖的就是純樂。過了午夜,夜宵攤生意依然紅火,一個小城有許多晚睡且快樂的人。
喝了酒不能開車,我和歐潔在我侄兒的護(hù)送下乘三輪車回酒店。睡下前,我跟歐潔說,一整天都沒認(rèn)真瞧一瞧西林。
第二天早上由西林縣文聯(lián)安排,做了個文學(xué)講座。我擔(dān)心文聯(lián)方面要給我講課費(fèi),先表明自己多年未回家鄉(xiāng),到這做的都是公益講座。文聯(lián)主席很開心,說當(dāng)?shù)氐奈膶W(xué)愛好者很多。果然,一個小會議室都坐滿了,我拿昨天黃仕偉發(fā)給我的一篇小說做范文,談了一些小說的敘事方法。更多的文學(xué)愛好者關(guān)注散文寫作,我也借此談了基層作者散文寫作同質(zhì)化的問題,寫散文不要拘于寫游記,寫父母往事等等。
很多很多年前,我的父親就是西林縣的一個寫作者,他一個農(nóng)村的孩子因?qū)懽鞲淖兞嗣\(yùn),而我的命運(yùn)自然也與此關(guān)聯(lián)。所以,我尊重一切基層的寫作者。
下午,羅皓宇與黃仕偉帶我游西林,我們穿街走巷,沒有一處能喚起我的記憶。我說了幾個我原先熟悉的單位,都不在原址了。從我記事起,我在西林有過三個家,最早一個是文化館,文化館的地勢也是很高,要爬高高的臺階,那一處的整個山頭好像都蕩平了。第二個家在電影院旁邊,電影院是在的,電影院整個規(guī)模都變大了,周圍干凈整潔,沒有什么住家了。當(dāng)我放棄去尋找熟悉的內(nèi)容時,卻認(rèn)出了第三個家的周邊。第三個家應(yīng)該是政府各部門工作人員的宿舍區(qū),格局是一排住人的平房,有兩間房,對面再有一排小房子做廚房和洗浴間用。這個小區(qū)地勢也是很高的,從馬路邊出出進(jìn)進(jìn)都要上至少有十級的臺階,我家是挨著馬路邊最近的這一排。廚房后頭臟水往外排的一個區(qū)域,各家大都圍起來種菜,菜園子與馬路的落差至少有五米左右。我有一次與大院的孩子捉迷藏,為了不讓人找到,異想天開地掛在圍墻邊上,果然無人發(fā)現(xiàn)我,可我后來體力不支,自己都覺得馬上要摔到馬路上去,要摔死了,也不知是不是內(nèi)在小宇宙爆發(fā),手一撐腿一蕩人又爬了上來。我認(rèn)出了這一條我差點(diǎn)要摔下去的路,它沒有變,馬路邊上的小區(qū)地勢也還是高的,修起了高墻。這附近全改造過了,唯有這一處保留了原來的格局,街道沒有拓寬,地沒有鏟平,就像一頁紙被不經(jīng)意折疊的一個小地方,重新把它攤平時,發(fā)現(xiàn)它看起來特別新,就和它被折起來那日一樣新。
羅皓宇他們帶我游月亮山山體公園,公園地勢高,能俯瞰整個西林城。從高處看,西林還真是個小小的山城,它周邊的輪廓可以用眼睛畫出來。那條我游過泳捕過小魚兒的馱娘江卻能逃過我的眼睛,我望不到它最終的流向。
第二天一早,我們離開了。說實(shí)話,當(dāng)我一離開這個小城,我就不記得它的樣子了,一兩天的觀看全如夢幻泡影,一點(diǎn)不留,我的西林還是四十年前的樣子,在我腦海里那么清晰那么完整,更可能的是我不愿意讓記憶受到任何覆蓋和修改。這把年紀(jì)了,經(jīng)常想留住那些舊時光,不去動,不去想,想讓它們保持原樣,在那樣的圖景當(dāng)中,我永遠(yuǎn)是少年。
重回故鄉(xiāng)的意義是什么?有些人消解了鄉(xiāng)愁,有些人錦衣榮歸。于我來說,重回故鄉(xiāng)更像是一個儀軌,離開多少年總有回來的時候。西林是我的生長之地,是我人生的起點(diǎn)和源頭,更是我一生性格稟性的造就之地。回鄉(xiāng)是一次溯源而上的旅程,在這里即便找不到一絲熟悉的痕跡也無大礙,所有能看到的實(shí)相總會朽壞,看不到的才是永恒。
2023年的春節(jié)剛過,羅皓宇的死訊突然傳來,令我震驚不已。我一直以為他比我年紀(jì)大,看了他的訃告,才知道他比我小一歲。再多的嘆息也喚不回離去的人。春節(jié)期間他還給我拜了年,短短幾天時間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經(jīng)打聽,他是突發(fā)腦梗,后來看一些寫他的悼念文字,又知道他平時過于勞累。他是一名警察,參與辦過不少案子。前兩年我寫一個懸疑小說,與他語音聊了幾次,咨詢他一些破案的技巧和常識。他寫的很多小說在未發(fā)表前都讓我看過,我覺得他和黃仕偉都是西林優(yōu)秀的作家。
出門在外,有時候聽某某人說是西林人,一陣驚喜,說我也是那個地方的,對方或是也有一份驚喜。所謂的同鄉(xiāng)之誼應(yīng)該是越小越偏遠(yuǎn)的地方更能講究起來吧?小地方更聚氣,這氣有力氣、心氣、骨氣,等等,相遇的人都知道。
君從故鄉(xiāng)來,應(yīng)知故鄉(xiāng)事。我跟西林聯(lián)系靠的還是人,像羅皓宇這樣的人。
【作者簡介】楊映川,作家;作品發(fā)表于《人民文學(xué)》《當(dāng)代》《十月》《花城》等刊,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魔術(shù)師》《淑女學(xué)堂》《我記仇》《狩獵季》等,曾獲人民文學(xué)獎、百花文學(xué)獎,廣西獨(dú)秀文學(xué)獎、文藝創(chuàng)作銅鼓獎等;現(xiàn)居南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