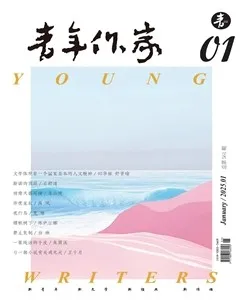續(xù)命術
【作者簡介】先志,1998年2月出生于湖南湘潭,廣西師范大學法律專業(yè)在讀,小說發(fā)表于《當代》《上海文學》《天涯》《青年文學》《西部》《文藝風賞》等刊,現(xiàn)居湖南湘潭。

行差踏錯一步,可不得了啊。在高樓上,連華生嘖了一聲,抿了抿嘴,食指的指甲刮掉,拇指的指甲一彈,碰到了防盜窗上已積滿泥的不銹鋼桿。底部鋪著的三塊木板已經(jīng)腐朽,花盆底部黑乎乎的東西從排水孔鉆出來,黏黏的,不知是什么。本來好好的月季也不知為何不再開花。屋內污濁的空氣讓人難以忍受。連華生踮起腳,從欄桿與欄桿的縫隙間,好不容易看到一個賣西瓜的小販經(jīng)過。住在高樓上的連華生已經(jīng)數(shù)年未見過陌生人了。小販戴著一頂鴨舌帽,坐在賣西瓜的三輪車上四處張望。連華生不喊,這車就要顛顛簸簸地走了。他知道這車是要去青云市場路口的,很少經(jīng)過這個年代久遠的小區(qū)。恐怕小販對這里還不熟悉。于是,連華生敲著窗邊的水管大聲喊道:
“別走,別走!我要買西瓜!”
賣西瓜的小販好不容易剎住車,過了好一會兒,才從頭上找到了連華生的位置。連華生的臉藏在兩叢干枯的月季之間。
小販說:“老爹爹,我等著你,你下來吧。”
連華生說:“你上來,我自己挑一個。”
“什么?”樓層太高,賣西瓜的小販聽不太清楚,“我挑一個,給你帶上去?”
“我腿腳不便啊,”連華生叫道,“我下不了樓。你上來,讓我自己挑一個。西瓜很難挑的。我老了,現(xiàn)在眼睛也看不太清了,不過還好,西瓜只要聽聲音。我一個一個敲,總能挑到好的。你這里有一車的西瓜。難道這一車里就沒有一個不壞的嗎?肯定有的……”
賣西瓜的小販聽到一半,吐了一口痰,吐到裂開的花壇中,罵罵咧咧地走了。連華生望著車噴出的稀薄尾氣,慢慢地說完,又哀嘆了幾聲。
下午,連華生將上午遇到賣西瓜的事講給兒子聽。時間已將近四點,兒子剛從武漢回來。他穿著西裝,在昏暗的客廳中感到悶熱難耐,于是解開了領扣,拎起沙發(fā)上干癟的襯衫、外套,或許還有一兩根從河邊撿來的荊條。他撿起荊條丟到了防盜窗上,又抖去灰塵,整理好坐墊,才坐下。他問:“怎么沒有水?”他干渴至極。然而,連華生一心一意地講述賣西瓜的事,還沒講完。
兒子說:“買西瓜也不是什么難事。你先給我拿杯水喝。”
“難道很簡單嗎?西瓜不用挑嗎?”連華生一直站著,“我也是很合情合理的。我挑過了,那么西瓜再有什么問題,也與他無關。現(xiàn)在西瓜里注水的可多了。一敲,聲音悶悶的。我聽說水還會養(yǎng)蟲……”
“好了,我?guī)湍闾粢粋€就是了。又何必去刁難人家。”
連華生被打斷,一下子默默的,好半天才說:“但我在這里活了很久。”
“什么?”
“恐怕,我快要死了。”
“什么死不死的!”兒子不耐煩地拭去額前耳后的汗水,從公文包里拎出一捆藥包,幾只炙蜈蚣被擠出來,落在了茶幾上,“正好,我剛從中藥鋪回來。于清蓮說,你現(xiàn)在正是該喝藥的年紀。”
十多年前,連華生有一個老相好在中藥鋪工作。那時他身體還好,腿腳也便利,常折了幾朵樓下隨風而生的野雛菊送給華容清。鋪子里除了華容清,還有一個老媽媽,是華容清的母親。她整日像塊檀木坐在鋪子里頭的竹椅上,夏天腳邊也點了小小的炭盆烘烤。誰能想到鋪子里還有一位老媽媽呢?連華生與華容清已經(jīng)夠老了。那老媽媽該有八十多了吧。連華生最喜歡看華容清制作炙蜈蚣的過程:先將蜈蚣們各自串在一根根竹簽上,去掉頭和尾,搓掉足,再澆上點黃酒在盆里拌勻,開小火在一個銅鍋里慢慢烘干。烘好的炙蜈蚣像是先秦的竹簡。華容清束好幾十根蜈蚣干,放入墻上的小柜,又挑出兩根,和一些用戥子稱好的白芍、川芎、郁李仁、柴胡、白芥子、香附、甘草及白芷等,分成兩個藥包,掛在連華生的指頭上:“好了,把藥送給于清蓮。她就住樓上,是203,還是 303……你反正知道的。她家也不會關門。”
幽暗的病房總讓人感到膽寒。于清蓮的家與這棟樓的其他房間構造并無不同,只是她常年敞開門,門內的過道和走廊仿佛連成一體,側邊的廁所、廚房以及餐廳都顯得幽深,仿佛藏著什么。另一側的墻上掛了幾幅從青云市場廉價買來的油畫,其實只是為了遮住墻上漏水的痕跡。對此,華容清也曾抱怨過,因為如果水侵蝕到中藥柜,那就麻煩了。不過,于清蓮其實是個陽光的姑娘。當她聽見連華生上樓時沉重的腳步聲,立刻從病榻邊的小板凳上一躍而起,在門框邊等待連華生。
“大伯,你來啦,”她接過連華生手里的藥,“進來坐坐吧。我把藥燒上。我外公也在等你呢。”
連華生小心翼翼地順著甬道前進。好像一段很長的旅程似的。到了盡頭的客廳豁然開朗。客廳十分亮堂,大概因為一整面都是落地窗。窗簾畏縮地候在角落。太陽真是明亮,卻又虛晃晃的,直叫人感到刺眼。連華生一下子就不自在了。于清蓮中途蹩入了廚房,此刻他聽見她揭開藥罐蓋子,擰開龍頭接水,又點燃煤氣,把藥包倒進去烹煮的聲音。他摸著還有余溫的板凳坐下。那病榻上垂下的毯子正巧輕輕磨蹭連華生的膝邊。
病床上的老伯瘦得驚人,宛如一副骨架。他半張著嘴,干裂的嘴唇顯得像一個干燥的草圈。喉嚨里不時發(fā)出咕嚕咕嚕冒泡的聲音。偏偏毯子又是這樣厚重!混著毛氈制成的床墊,像餃子一樣將老伯包裹得嚴嚴實實。連華生輕輕拎起膝邊毯子的一角,便覺得無比沉重,立刻悔得撒手。
于清蓮從廚房出來,她盤腿坐在連華生腳邊:“你坐,你坐!我沒關系的。”她又按住正欲起身離開的連華生,“吃了送來的藥,他頭痛確實好多了。”
“他還病著嗎?”
“是啊,晚上他頭痛得厲害!”于清蓮似乎終于找到了傾訴的對象,“一痛他就大叫,叫得像動物園里的獅子,像外面的雷聲。他說他嗓子里有東西要爬出來。奇怪吧,痛的卻是腦袋。別看他白天安靜得很,晚上可精神極了!為了這個,我還特意買了盞燈。但我也不能整晚開著,開著我睡不著。白天我還得學習呢。”
她往后一指,連華生才看見窗簾后立著一盞落地燈。于清蓮走過去插上電,忽然之間,燈泡亮得如同太陽,照得連華生趕緊用雙臂遮擋。
“夠亮了吧,”于清蓮關掉燈,“如果不是這么亮,也騙不了他。”
晚上,連華生躺在床上,盯著漆黑的天花板,手抓著薄毯總也睡不著。廁所里的水管一直在響。他打開燈,嫌燈光不夠明亮,又從中藥鋪后頭找出兩盞落滿灰塵的臺燈,可惜插頭已經(jīng)歪了。于是他又把老媽媽房里的小太陽燈偷搬過來。小太陽燈像一架落地風扇,一插上電,嗡嗡地亮起橘紅色的光。不一會兒,連華生就被烤出汗了。他忽然心慌得很,但并不覺得不舒服。華容清剛清點完傍晚送來的藥材,洗了手腳,還沒爬上床,瞧見連華生像蜈蚣干一般汗涔涔地壓在毯子上:
“你這是做什么!大夏天的不嫌熱嗎?”
“你聽到什么沒有?”
華容清伸手去扯毯子,被連華生壓住手腕:“別說話,你聽。”
幽暗的天花板上,傳來像猴爪撓樹般的咔嘶啦咔嘶啦聲。聲音是從廁所里的水管傳來的。華容清走進廁所,拉開窗,窗戶正對中藥鋪后頭的小垃圾場。垃圾場前的民房里有人在打麻將。麻將碰撞的聲音嘩啦——嘩啦——,像流水緩慢地滲入地下。
“你聽到了沒有?”連華生恍惚地說,“這是于清蓮家在叫啊。”
“我該找除蟲隊來了,”華容清關上窗,又湊近角落里的水管,貼耳聆聽了一會兒,“幾十年了,這些白蟻要把我家的天花板都蛀空了,還好中藥柜提前做了防蟲。”
“那叫聲叫得我心痛得很!從今晚就……”
“你年紀大了,”華容清輕拍水管,那頭也回聲似的咕嚕幾聲。她轉身回到床邊,聲音漸小了,“明天,我給你開幾服解心慌的藥。”
“你多大了?我今天剛算了,我是五十九歲六個月零三十天。”
“算這么仔細做什么!”
“于清蓮的外公多少歲了?”
“他啊,”華容清慢慢脫掉褲子,躺到連華生身邊,“我媽跟他分開之后,我們就不計他的歲數(shù)了。”
“別打岔!”
“大概是九十三,或者九十四了吧。”
“九十三!”連華生沒想到他這么大年紀,坐起來盤腿望著華容清,“難道你也七十多了?”
“他老來得子嘛!”
“九十三了還沒有去世……人很少活到九十三。”
“可能是喝中藥的緣故,他四十三歲起就喝中藥了,”華容清掰掰手指,沒想到已經(jīng)過了五十年,“當然,這也是我媽的意思。”
“但他并不健康,”連華生被拽著又慢慢躺下,“我今天去瞧了。他比以往病得更重了。他都起不來了,喉嚨里像壓著塊石頭。晚上,又死命地叫!你聽——”
“哎呀,這都是可以想見的。他老了。”
華容清對樓上順水管重新傳來的嘶啞吼叫聲充耳不聞,轉身抱著連華生一只干瘦的手臂,不一會兒就睡著了。
翌日,華容清打發(fā)連華生去一趟青云市場。她需要一些新鮮的蓮蓬、蓮子,還有剛從東湖挖上來的粉藕。華容清的那位老媽媽想吃這些,每個月她就惦記著這么一點食物。連華生不清楚華容清是怎么得知這些信息的。每當他拉開簾子,小心翼翼地經(jīng)過中藥鋪后面去廁所時,那位膚色黝黑、身體干瘦的老媽媽總是緊閉雙眼,躺椅微微搖晃。華容清用勺子舀起蓮子湯遞到她嘴邊,她的眼睛依舊閉著。好在她能吞下,這證明她還活著。現(xiàn)在,連華生更相信蓮子和粉藕是她的保命之物,否則她怎么能活到九十歲呢?他懊悔自己以前為何視而不見,并抱著學習的態(tài)度接下了這項任務,這讓華容清感到好奇:“你今天怎么了,心情不好?”
從中藥鋪到青云市場需要穿過平安街。平安街原本有一些賣舊家具和宣紙毛筆的店鋪,后來又增加了賣羊奶粉、燈具和漁具的店。最近還新開了一家網(wǎng)吧。每次連華生去找孫子時,總會對那網(wǎng)吧的招牌感到不滿:青云網(wǎng)吧。似乎開網(wǎng)吧的人與青云市場有某種聯(lián)系。但連華生對青云市場的底細了如指掌:很久以前那里有一口古井,井水下連著某種物質,使井水熱騰騰的,后來才知道這叫溫泉井。熱氣蒸騰,藍色和紫色的磷光像青云一樣從井口蔓延。連華生還特意去看過,井已經(jīng)被石板封死,只留下一塊模糊不清的碑。他趴在地上想聽聽石板縫隙下是否有水聲,一雙手將他拉起來:“老伯伯,行個方便,讓一下。”一個賣燒雞的女人將一鍋廢棄的鹵水潑在了石板縫上。
連華生走進了網(wǎng)吧。一個戴眼鏡的男人正盯著藍幽幽的顯示屏,不停地點擊鼠標。他抬頭看了連華生一眼:“要開幾個小時?”
“我來找人。”
“我這兒可沒有學生。”
“我沒說找學生。”
“那你找誰?”
“我找我孫子。”
那男人推了推眼鏡,好奇地湊近連華生半禿的白發(fā),藍幽幽的光映在他的臉上:“老伯,您今年多大了?”
“問這個做什么!”連華生突然緊張起來,“跟你有什么關系!”
“我看您今年不超過70吧?我爸今年68歲,比您稍微年輕一點。但我的兒子才十六歲,他在縣三中讀書,每周才回來一次。您孫子成年了嗎?我說過了,這里沒有學生。”
連華生氣得手直發(fā)抖:“我孫子九歲。”
“好了,那更沒有了。”男人走出柜臺,把連華生推到門外,“要么您打電話,要么就在門口等。總之,我這里沒有學生。”
連華生站在門前的三級臺階上,頭暈目眩,腳步不穩(wěn),誤踏了兩步,暈頭轉向地滑進了一旁的小門面。他進去后才看清這里賣的是什么。三面墻上掛滿了花花綠綠的壽衣,一個抹了發(fā)膏,白發(fā)梳得服服帖帖的老人迎上來,燈光下他的腦門油亮亮的:“您是給自己買,還是給別人買?”
等連華生到了青云市場,早市已經(jīng)熱鬧了一陣子。人們提著塑料袋,反方向擠得連華生快要被推了出去。連華生只好繞了一小段路,找到一個無人小巷拐進市場。這里倒有幾輛滿載泥藕的三輪車,還有坐在路邊掰蓮蓬的婦女招呼他。連華生嫌賣得不夠便宜,走到市場里才發(fā)現(xiàn)價格都一樣。他隨便撿了些蓮蓬、蓮子和泥藕,匆匆忙忙又往來時的小巷走去。他進來時,看到巷口有一個推三輪車賣舊書的,他好奇地翻看了一會兒,卻背著手裝作很嚴肅,忽然拿起一本。
這本線裝書的名字叫做《如死真經(jīng)》。牛皮紙封面上灑了幾滴油漬,頁邊也已經(jīng)卷起。單單只是名字就吸引了他。好像還有一本假經(jīng)似的!連華生以為里頭是什么奇門秘術,至少是一些畫了圖譜的氣功書。更年輕的時候他也聽廣播練過,他還記得些拳腳功夫,一想到此便忍不住合指并掌,暗自演練起來。他真翻開,才發(fā)現(xiàn)這是一本藥方,或許是關于養(yǎng)生的,每一個藥方還配有草藥的圖。這是華容清感興趣的東西。他本來興趣索然,但又瞥到目錄最后一個藥方叫做“續(xù)命術”。
“這本書三塊錢,”賣書的人赤腳坐在三輪車上看《楊家將》,湊近指點,“喜歡就拿回去。”
“再看看,”連華生依依不舍地將書放回,發(fā)現(xiàn)只剩這一本,“我先去買東西,待會兒再來。”
連華生拎了一袋藕和一袋蓮蓬,穿過中藥鋪的前廳和后房,將藕倒進黑魆魆的廚房里的籃子。華容清正在后房扶著人換燈泡。踩在人字梯上的是連華生的兒子,他見連華生剛進了廚房又出來,燈泡擰到一半時叫住他:“爸,蓮藕洗了嗎?”
“唔,啊,還沒有,”連華生低頭哼哼,“等會兒再洗。”
“你又想讓華阿姨洗吧?”兒子擰好燈泡,又用一塊小小的麂皮細細擦了一遍,“我說,華阿姨都累壞了,她要管這個中藥鋪,又要照顧她的父母。華阿姨的女兒也辛苦得很啊,她放假了還得照顧外公。哎,我怎么沒見到于清蓮?她還在樓上嗎?”
連華生拉拉華容清的衣角:“你讓他來做什么?”
“我讓他來除蟲啊,”華容清扶好梯子,待人下來,“再不除,這個房子都要成爛殼子了!”
連華生不知道兒子在中藥鋪后頭干什么。他倒是像模像樣的,背著個裝藥水的氣罐,手里提著個連在罐上的管子,就像吸塵器的管子。他還戴上了把整個頭都包住的面具。這下他更聽不清連華生說什么了。這是他從朋友那借來的。連華生只聽到后頭一陣陣噗呲噗呲的聲音。可是這中藥鋪里真的有蟲嗎?他聽說山里長草藥的地方,蛇啊,毒蟲啊都不敢靠近。能受得住的都要成仙了。或許他兒子正順著吱呀作響的樓梯殺滅墻壁里的“仙人”。他才想起二樓夾層里還放了東西,但已經(jīng)晚了。
兒子坐在樓梯的最高階,把一件件物品丟下來,其中夾著一只死老鼠。除了這些,還有一些舊得已經(jīng)爛成棉絮的被褥,一個癟了的舊沙發(fā),一堆舊衣服。
“這都是什么呀,怎么藏了這么多垃圾!”
華容清在柜臺稱好藥給顧客,也跑過來看:“難怪!有這些東西,墻里怎么會不生蟲!”
連華生無地自容。兒子戴著手套,毫無顧忌地拆開那些破爛的布和棉絮:“我本來想讓你和華阿姨住在一起,想著正好能改掉你的毛病。很多東西該丟的時候就丟了。”他拆開一包衣服,掉出一個沉甸甸的塑料袋,袋子里是好幾盒藥。兒子撿起來看了看,又盯著側面的說明小字費力地認了一會兒:“西地那非……哎呀,你現(xiàn)在怎么還吃這種藥!”
連華生羞得手足無措:“這是很久以前的了……”
華容清戴上眼鏡接過藥:“這種藥吃了不好啊,傷身體。你是什么時候吃的?”
“二十多年前吧……”
“難怪!”兒子憤憤地從樓梯上跳下來,“我媽那時候不會是因為這個去世的吧?”
“不至于,”華容清拆開藥盒,“那倒不至于。主要是這藥吃多了,傷身體。你現(xiàn)在還在吃嗎?”
“沒,沒有,我現(xiàn)在吃了干嗎呀。”
濕漉漉、軟綿綿的藥盒被拆開,里頭竟掉出一些干死的蛆和結塊的頭發(fā)。
于是直到晚上,連華生才鼓起勇氣將書拿給華容清看。華容清坐在昏暗的燈光下,提著戥子,小心而迅速地稱好各種藥材,并用油紙包好。明天早上有一批中學退休教師來取藥,她們大多患有關節(jié)炎和嗓子病。等最后一包藥稱完,華容清將三十多個藥包整齊地壘在柜臺后,連華生將書翻到最后的“續(xù)命術”一頁給她看。
“這些藥材倒是不難找,”華容清用指尖點著字念過去,“黃芪、當歸、葛根、真菊、肉桂、細辛……可是這是用來治什么的呢?既不是清熱,也不是散風寒,我沒見過這種方子,只怕吃了不上不下的,寒熱交加,對身體不好啊。”
“這是續(xù)命的方子,你當然沒見過了。”
連華生好說歹說,華容清終于同意了:“好吧,隨便你。但是劑量先少一些,三天服用一次,先試試看,如果不舒服就停。”
過了幾天,連華生的兒子又來了。他剛剛從車站換班回來,制服還穿在身上,剛坐下就忍不住分享:“今天站臺差點出人命呢。”
“怎么回事?”
華容清隨口一問,同時忙著把炒藕尖、蓮子炒豬肝,還有一大盆熱騰騰的粉藕湯端上桌。
“有位老太太沒站穩(wěn),可能是因為年紀太大,看不清楚。車來的時候,她差點掉進軌道。”
“太危險了!這么大年紀,她不應該一個人出門坐車。”
“是啊,還好我眼疾手快拉住了她。她兒子當時去洗手間了,回來后弄清楚情況,就一直感謝我。他兒子是個大老板,在武漢有公司。他叫我跟他去上班。”
“你沒答應吧?”
兒子得意揚揚地說:“我當然要考慮一下。”
“哎,”華容清擦干手,叫連華生也去洗手,然后招呼大家吃飯,“你可要考慮清楚啊,不要上了別人的當。”
“是啊,”連華生洗完手坐下,“我們年輕的時候,到處都是陷阱。等你去了武漢,就不知道他要怎么對你。”
兒子沒理連華生。這幾天,連華生神采奕奕,坐著也挺直了腰桿,像是在尋找觀眾。但兒子只轉頭看向華容清:“華阿姨,這幾天還有蟲子嗎?”
“嗯,沒了,”華容清吃了一口飯,又夾起一塊粉藕喂給身邊閉眼沉默的老媽媽,“但是,你爸爸總說他睡不著覺,說天花板上還有聲音。我倒是沒聽見。”
“不是啊,”連華生為自己辯解,“那是于清蓮的外公在叫。”
兒子瞥了他一眼:“我看他挺精神,說明睡得很好!”
連華生無意與兒子解釋續(xù)命術的作用。畢竟續(xù)命術的功效不是誰都能明白。他自從服下兩服藥之后,感覺好多了。下腹部的位置似乎燃起了一股火。年輕時,連華生還做過鍋爐工,現(xiàn)在他感覺自己就像加了煤的鍋爐,燒得熱氣騰騰,蒸汽從鼻子、眼睛、耳孔、指尖四處溢散,帶動這具服役多年身體的關節(jié)又生龍活虎起來。他兒子倒是早忘了他做過鍋爐工的事。小時候他貪玩,他們一家都是這樣。兒子總是跑到鐵軌邊摘狗尾巴草、豬尾巴草,還有蒺藜,躺在鐵軌邊玩游戲。每天連華生下班都要膽戰(zhàn)心驚地沿著鐵軌尋找被隱藏的兒子。真是不把生命當一回事!想到這里,連華生問兒子:“我孫子呢?他是不是又去網(wǎng)吧了?”他重重地嘆氣,“唉,你要注意啊,網(wǎng)絡對他眼睛很不好!”
“什么?”兒子狐疑地回頭看他,“你老糊涂了。前陣子,他跟他媽媽早回娘家去了。我不是說過了嗎?我都愁死了!”
飯后,華容清叫連華生跟著兒子把剩下的粉藕湯送到樓上。兒子阻止過,但華容清還是把藕湯倒入保溫桶,一個不夠,又倒了兩個。明明他端著那個大盆上去就好了。為此,上樓時兒子一直數(shù)落連華生:
“你要是有個定心,就跟華阿姨好好過,平時有什么事幫她多做點。她老了,你也是……不要發(fā)呆!這不是以前了,還總是到處閑逛。要是我真的去了武漢,起碼我能安心……你聽到了沒有!”
連華生只顧數(shù)腳下的步子。這樓梯原本有十七階,可今天十六步就走完了。連華生心里墜墜的,他想重新走一遍,但一抬頭看到兒子嚇人的怒容,只能膽戰(zhàn)心驚地作罷。
于清蓮早早地站在門口等候,她接過兩只保溫桶:“好香啊,是藕湯吧。”她看到兒子身后的連華生,眼睛一亮,“哎呀,大伯,您今天精神怎么這么好?”
連華生受寵若驚:“真的嗎?”
“真的呀,”于清蓮提著保溫桶,用手肘輕輕碰了碰連華生,轉了一圈仔細打量,“真的,我覺得你變年輕了。”
連華生飄飄然。屋里彌漫著藥湯的味道,沉悶而污濁,令他的手指不自覺地蜷縮。他悠然自得地在靠近門邊的餐椅坐下,隔著幾步遠的地方就是床上的老伯。今天是個陰天,薄毯一蓋,他仿佛就消失了。連華生端起桌上半涼的茶水抿了一口,仿佛沒有看到那張床,仿佛一切都未曾發(fā)生,不停地側耳偷聽兒子和于清蓮在廚房里的談話。
“你畢業(yè)了準備去哪兒啊?”
“還不知道呢,”于清蓮似乎揭開了藥罐的蓋子,咕嚕咕嚕地將藥倒進碗里,“這么大的事,我總得找人商量商量。”
“總不能照顧你外公一輩子吧。”
“這也是個去處,”于清蓮拿起抹布,抹干凈碗沿的藥漬,捧著還冒熱氣的藥碗走出來,“跟著他我確實學到了不少東西呢。”
于清蓮小心翼翼地將藥碗放到床頭柜上,又揭開老伯身上的厚毯。原本毯子遮住了他一半的臉。兒子躲得遠遠的,往連華生身后擠,直到把連華生擠得站起來,不自覺地移到床邊。那老伯臉色蒼白得可怕,臉上的皺紋仿佛要讓皮肉從骨頭上融化下來。他那薄薄的嘴唇似乎已禁止氣流通過,實在很難相信他還活著。
“外公,喝藥了。”
于清蓮舀起一勺滾燙的藥,湊近嘴邊吹了幾十次,小心地抵著老人的牙關倒進去。老人沒有回應,藥水仿佛順著水管自然流淌。連華生還能聽見藥水在老人肚子里翻轉的聲音。藥似乎迷了路。于清蓮繼續(xù)舀起第二勺、第三勺……就這樣幾勺下去,老人臉色竟?jié)u漸紅潤起來,臉上的皺紋也隨著復蘇的呼吸緩緩翕動。等到藥水見底了一大半,老人終于睜開眼睛,被喉嚨里的藥水嗆得重重咳嗽。于清蓮扶他坐起,攪拌開碗底的藥渣,端過來,讓老人順著碗沿一口氣喝完。
“今天是粉藕湯呢,”于清蓮接過碗放下,又打開保溫桶,低頭陶醉地聞了一會兒,手掌扇動香氣送到老人鼻尖,“可惜少放了一味料,我也說不上是什么。聞起來讓人饞得不行。以前的湯,是叫人節(jié)制的。”
“哎,可能是華阿姨光顧著和我說話去了,”兒子走過來,有些懊惱,“她說,你已經(jīng)一年多沒出過這個屋子的門了,我嚇了一跳,以前怎么沒注意到呢?這是真的嗎?”
于清蓮收拾好藥碗起身:“是真的。”
“那你怎么上學呢?”
“上學總有辦法的,你看我住的那個房間里,不也有一臺電腦嗎?我可以上網(wǎng)課。”
“那總不算是真正的上學。”
“哎,所以我今年起申請了休學,我已經(jīng)休息好一陣子了。”
兒子長嘆了一口氣:“我還跟華阿姨說,等你畢業(yè)了,和我一起去武漢上班呢。”忽然,他抓住于清蓮的手腕就往外走,“所以華阿姨才跟我說,你一年沒出過門。我今天來,就是要幫你解決這個問題的。”
“什么?我不要!”
于清蓮驚恐萬分。可能由于長期未出門,蒼白細瘦的手腕如稻草般被兒子的手指緊緊抓住。她拖鞋底的紋路早在日復一日的室內跋涉中磨平了。這么一扯,她便摔倒了。她雙腳亂蹬,拒絕連華生兒子的攙扶。她過長的指甲緊扣著臟黑的木地板,摳得地板縫中的污垢都嵌進了指甲,摳得指甲邊緣盡數(shù)磨損,摳得綿軟的地板發(fā)出尖銳的撕裂聲。但連華生的兒子還是拖著她到了門邊。她死命抓住搖搖欲墜的門框,木裂中的尖刺扎破虎口流出血來。連華生拽扯她帶動整扇門如狂風驟雨般咣當作響。她手指深陷彎曲的門框里,一點點被拖下樓梯,聲嘶力竭地呼喊:“救命啊!救命啊!”
那老人似乎沒聽見。他專心致志地品嘗著那碗粉藕湯。藕塊切得太大,他還要用一雙筷子,笨拙地將藕搗碎,搗小。
連華生望著地板上指甲留下的痕跡,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餐椅離得太遠;剛剛于清蓮坐的椅子被老伯擺上了粉藕湯。他光是站著就汗如雨下。等于清蓮的呼救聲微不可聞了,他才訕訕開口:“伯,你外孫女喊你呢。”
老伯吸溜了一口湯,抬頭問:“在哪里呢?”
“她剛剛還在這兒呢!”
“噢,那是在喊我嗎?”
“是的,”連華生滿頭大汗,不停用手背擦拭額頭,說完他倒不確定了,頭皮像上了發(fā)條越來越緊,緊得他整個人都快中暑了,“應該是的。”
“你不要緊張。”老伯仿佛看出了什么,拍拍腿邊床鋪的凹陷處,“我聽華容清提到過你,說你是個好人。”
“她說我是個好人?”連華生受寵若驚地坐下,但沒有坐到老伯拍的位置,而是保持了一臂寬的距離,出汗的問題漸好了些,“我以為她早就和樓上不聯(lián)系了。”
“是的,是這樣的,但是……”老伯放下碗,像牛一樣緩慢地,若有所思地咀嚼著,“這都是她媽媽的主意……但每天晚上我們都通過水管說話。水管方便得很,直上直下。耳朵貼在水管上,遠處的人說話好像近在眼前。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有人可能偷聽。你偷聽過嗎?”
“沒有,”連華生沒想到懷疑到他身上,慌張起身擺手,“真的沒有!”
“你坐下!”老伯咚咚猛拍床鋪,“我說了,不要緊張!你有沒有去過這里的二樓、四樓和五樓?華容清的媽媽原先在每一層都有房子。”
“沒有!我和她都沒說過一句話!”
“我想也是,”老伯咧嘴露出牙花,緩緩說道,“畢竟,華容清跟我說,你最近也在研究續(xù)命術。”
連華生心頭一驚:“續(xù)命術!”這三個字如久遠的哀樂如雷貫耳。那小半本的東西已是他心頭之秘。他沒想到華容清竟如此松懈,通過水管告訴了別人,更別說還有人可能在偷聽!老伯轉身半趴下,在床與墻的縫隙里死命摳著些什么,先摳出兩條油膩膩的枕巾,又是一架小玩具車,最后才翻出一本殘破的冊子。它毀了一半。老伯吸了吸鼻子,隨手拈開最后一頁丟給連華生看,那上面赫然印著“續(xù)命術”。
“這些都是沒用的東西,我都不知道它們壓在床下多少年了。”老伯慢慢地回憶道,“我還記得我剛拿到的時候,哎,那時候,我喜歡在床上邊翻書邊吃東西。華容清的媽媽不知道說了多少次我這個毛病,但我總是改不過來。”
連華生來回翻了幾次,確認無誤這就是他的《續(xù)命術》:“你怎么會有這本書?”
“我怎么會有?哎……”老伯的語氣似乎越來越緩慢,“這不是什么稀奇的東西。”
“難道它有很多本嗎?”
“很多本?是的,每個人都有一本……到時候了就會有。”老伯又慢慢躺下,蓋上毯子,“不過它沒什么用,什么用都沒有!好了,你是個好人,于清蓮不在,還得麻煩你把保溫桶帶下去給華容清了。”
老伯說完,靜靜地閉上了眼睛。剛剛臉上紅潤的氣色漸漸褪去,氣息也隨著呼吸逐漸減弱。仿佛他一直就是這個樣子,從未活過來。連華生下樓時碰到于清蓮正一瘸一拐地上樓,他還想問問她,但于清蓮抱著胳膊,傷痕累累,頭發(fā)也披散著。連華生覺得很過意不去。她甚至沒注意到連華生手上拿著的那兩個不銹鋼保溫桶。她“砰”的一下關上了那扇殘破的房門。連華生頭一次見到這條走廊真正封閉的樣子。
晚上,華容清搬起老媽媽的竹椅,送她到中藥鋪后面的小院子里曬月亮。按照華容清的說法,太陽光太強了,月亮才適合這么老的人。華容清在一旁檢查簸箕上晾曬的人參、黃芪、當歸、薄荷等。十幾個圓圓的簸箕擠滿了小院子,連華生幾乎無從下腳。他像是和老媽媽一起被困在了簸箕之海的孤島上。他只能看著華容清像魚一樣靈活地在簸箕之間穿行。
“那個續(xù)命術的方子,你覺得有什么問題嗎?”
“怎么啦?”
“我是問你有什么問題沒有?”
“我早就說過了,我看不出來,也不知道那是治什么病的!”華容清直起腰,說道,“我說了要你吃了,不舒服了再告訴我。你現(xiàn)在不舒服了嗎?”
連華生不知如何作答。他忸怩地細細察覺了一下身體的觸感。他判斷不準。他茫然地望向華容清:“但你告訴了你的父親。”
“是的,我告訴了他。不然我跟誰說呢?于清蓮老也不下來,我媽媽整日像塊木頭一樣坐著。至于你,你就是那個研究續(xù)命術的人!我已經(jīng)不年輕了!我老了!我又要跟誰去說呢?”
華容清叉腰站在簸箕之海的另一端,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委屈得胸脯一上一下,洶涌的淚水都被她強壓下去了。她和連華生之間隔了七八個堅硬的簸箕。那些飄浮其上的人參干和皺縮的薄荷葉顫顫巍巍地抖動。
連華生沒想到她如此激動地指責自己,一下口不擇言:“但你沒告訴我你父親早就研究過續(xù)命術!還有那藥!”
“他研究過續(xù)命術嗎?”華容清按下胸口,擦干溢出的一點兒眼淚,慢慢平復,驚訝道,“他沒跟我說過呀。我和他說的時候,他還問我續(xù)命術是什么呢!”
連華生當晚沒有睡好。第二天、第三天也都沒有睡好。華容清倒還是老樣子,日復一日地進藥材,稱藥材,賣藥材,顧客也還是那些老顧客。連華生無所事事地坐在中藥鋪前廳里,焦慮得一根根反復查看自己的手指:手指沒有什么變化,這種沒有變化反而讓他感到心驚。哪怕多年存在的手癬換個地方生長也好。他已經(jīng)吃了好幾服藥了。他突然想起,應該去修復與于清蓮的關系,應該讓她與自己以及自己的兒子重歸于好。于是,他趁著華容清跟隨送藥材的人去藥材廠辦事的時候,偷偷溜上樓。華容清臨走前囑咐他:
“我出去一會兒,可能暫時回不來。你把店看好,我就不鎖門了。如果有人來買藥,你就讓他們下午或明天再來,聽到了嗎?”
連華生點頭表示明白。等華容清匆匆忙忙地走后,他便上了樓。他敲響了于清蓮家的門。于清蓮開門一見是他,很是驚訝:“老伯,您怎么來了,這個時候……”
“怎么了?”
“我沒有提前得到消息。”
“難道你以前知道我會來?”
“當然了!媽媽通常會提前通過水管告訴我們。不過沒關系,”于清蓮高高興興地把連華生請進門,“我好幾天沒見到別人了。正好,老伯,您能和我聊聊天。”
她想讓連華生坐到床邊的椅子上,但連華生這次執(zhí)拗地拒絕了。他坐到靠門邊的餐椅上。于清蓮只好搬了床邊的凳子過來坐下。床上的毯子黑黢黢的,遠遠看去很難分辨下面是否有人。連華生看著仿佛什么也沒發(fā)生過的于清蓮,問道:“你的傷好了嗎?”
“好了呀,吃了藥就好了。”
于清蓮坐在低矮的腳凳上,仰頭仔細地看了看連華生:“老伯,你這幾天身體不太好啊。”
“怎么?”
她站起來捧著連華生的腦袋左右看:“要是我是像媽媽那樣的醫(yī)生就好了。我什么也說不上來。不過,可能只是單純沒有睡好。”
窄窄的方形餐桌上擺了一壺茶。連華生倒茶給于清蓮和自己。他進來前斟酌了許久,心里不安得很,不知道如何向于清蓮道歉。如此倒是煙消云散了,仿佛一直無事發(fā)生。兩人靜靜地喝茶,廚房里沒了中藥烹煮的聲音,連華生還不習慣。他試探性地咳嗽了兩聲,于清蓮就說:“老伯,我要向你袒露一個秘密。”
連華生感到詫異:“什么秘密?”
“我也不好說,說起來總是覺得愧疚。你知道青云市場里的那口井吧?”
“知道。”
“前些日子,市政不是請人來疏通了嗎?井水又渾又黏,早就不能用了。他們在里面挖出了好多東西,有炒菜的鍋、燈泡、電池,很多亂七八糟的,還有一只死貓!”
“啊,我沒聽說過。”
“怎么會沒聽說呢?就是一年多前的事,你仔細想想。”于清蓮前傾身子,抓住連華生干瘦的腿,有些著急,“你想起來了嗎?那只貓就是我丟進去的!”
“啊,”連華生推拒著于清蓮的手,“那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那只貓是媽媽的貓。”
連華生半晌沒說話,過了好一會兒,看著低下頭的于清蓮說:“是之前養(yǎng)的那只花貓嗎?不見的時候,她確實找了很久。不過她怎么不知道貓已經(jīng)死了?”
“她認不出來了。那天我和她一起去買菜。她經(jīng)過的時候都沒有認出來,只是捏著鼻子看了幾眼就走了。畢竟,死了就是這樣的。”于清蓮低頭抽泣著,“我嫌它平時晚上太吵,趁它不注意,把它塞到井里去了。”
“唉,”連華生嘆了口氣,“這實在不是什么大事。”
于清蓮送連華生離開時,倚在修補好的門框上說:“老伯,今天跟你坦白了,我心情好多了。殺了媽媽的貓之后,我就不愿意出門。但現(xiàn)在我相信過不了多久,我就能走出這扇門了。”她的眼眶還紅著,讓連華生產(chǎn)生了憐憫之情。回想剛剛和于清蓮的親密對話,他輕快地下樓,腳步越來越輕快,甚至在走進中藥鋪的時候哼起了歌。歌是他很小時母親教他唱的:“清泉水,水清泉,泉水清又響。”他剛進門時還沒發(fā)現(xiàn)有什么不對,直到踏上通往二樓的樓梯,才一側頭發(fā)現(xiàn)一樓簾子背后似乎有一個陌生人站在老媽媽跟前。
他走過去掀開簾子:“你是誰?”
那是一個介于青年和中年之間的男人。他的臉色模糊,穿著一件墨黑的夾克和牛仔褲。他蹲在老媽媽的膝前,扶著老媽媽放在躺椅扶手上的手,只抬眼看了一下進來的連華生。連華生又問:“你是誰?”
他沒有回答連華生,只匆匆結束了與老媽媽的對話。好像他剛剛和老媽媽說了很多話:“……好了,我就說這么多,你自己選擇吧。”
連華生有些膽怯地走近:“你在做什么?”
那男人沒有回答他,繞過連華生,掀起簾子匆匆往門外走。連華生慌忙跟上,在后頭一直問:“你是誰?你是來拿藥的嗎?華容清今天不在,你下午再來吧!”可他說晚了。那男人一步也沒回頭,走得很快。黑色的身影仿佛一陣青煙繞過中藥鋪的柜臺,飄忽而去。連華生追到了大街上。迎面走來兩個說笑的扛扁擔的小販。一個賣綠豆沙,一個賣豆腐花,見到連華生都緩慢地壓低了聲音,似乎提防他偷聽到什么。那個男人不見了。太陽是如此刺眼,連華生張望了一會兒,就回了鋪里。
他擔心藥鋪里少了什么東西,但柜臺后包好的藥包數(shù)量他記不清,柜子里的藥材他也一概不知。房間里的燈泡和墻壁都還完好無損,椅子也仍在。藥鋪里還有什么值錢的東西呢?他惴惴不安地回到了中藥鋪后面。剛才那個男人似乎和老媽媽說了很多話。他從未和老媽媽說過話。他硬著頭皮掀開簾子,走到老媽媽面前:“媽媽,剛才那個男人跟你說了什么?”
他小心翼翼地摸上老媽媽的手。手硬得像塊炭,冷得像塊鐵。寒意令連華生一陣哆嗦。老媽媽沒有說話。他順著手臂一路摸到老媽媽的臉。她一直戴著一頂沉重的、如同苗族頭飾一般的帽子。他探查了一下老媽媽的鼻息,發(fā)現(xiàn)她已經(jīng)去世了。
等華容清回來,只看到連華生如同一條喪家犬般蹲坐在中藥鋪門口的臺階上。他順著眼前的陰影抬頭望見華容清:“老媽媽她,她去世了。”
華容清放下手中的塑料袋,匆匆走入后室,不一會兒又匆匆出來,揪住連華生的背。連華生將下午那個來去無蹤的男人告訴了華容清。
她一邊哭一邊責罵:“我不是說了嗎!叫你好好看著店,要是有人來,就說我不在,讓他下午來,或者明天再來。我就讓你做這么一點小事,你怎么還搞砸了!”
她撿起地上的塑料袋,從里面翻出茼蒿、芹菜、圓白菜、蕹菜,一樣樣扔在連華生身上。連華生來回躲閃,最后躲到了大街上。大街上此刻空無一人,婦女們站在居民樓的入口處呼喊她們的兒女。一聲又一聲的名字接續(xù)回響,連綿不絕。連華生漲紅了臉,慌不擇路地逃到一個安靜的巷子。他挑了一個由紙箱圍成的小窩坐下,它的主人應當有事外出了。畢竟,流浪漢也有自己的忙碌。他心靜了片刻,又開始不安:憑什么這又是他的責任!他抬頭張望了片刻,又瑟縮地坐下,因為他聽到了什么聲音。他半邊身子貼在巷子的墻上,墻冰涼涼的。一絲若有似無的音樂隔著圍墻從遠處傳來。會是哀樂嗎?這個念頭一起,連華生就漸漸有些傷感。他貼在墻上的手指不自覺地摳弄堅硬的磚塊。他才發(fā)現(xiàn)磚塊上已經(jīng)滿是指甲的劃痕,仿佛之前就有人經(jīng)常坐在這里聽音樂。
等到深夜,連華生才鼓起勇氣回到中藥鋪。藥鋪的門大開著,里面還亮著燈,在蕭瑟黑暗的古街上顯得格外醒目。他悄悄走進臥室,發(fā)現(xiàn)里面空無一人,只有華容清曾用來研究藥方的小桌上亮著一盞臺燈。連華生在大廳里呼喊:“華容清!華容清!”但沒有人回應。他費了很大的力氣,把臥室和大廳里的各種抽屜和藥柜都翻遍了,卻什么也沒發(fā)現(xiàn)。最后,他一步一步,膽戰(zhàn)心驚地掀開通往中藥鋪后面的簾子。
華容清正閉著眼睛躺在原來老媽媽常躺的那把躺椅上。黑暗中,躺椅微微搖晃,寂靜無聲。連華生焦急地蹲在華容清面前:“媽媽呢?”
“她啊,”華容清輕輕嘆了一口氣,“她下葬了。”
“哪有那么快就下葬的!”
“她之前就有過交代。有交代自然就快些。”
連華生不信。他起身,來回走了一圈,沒有發(fā)現(xiàn)老媽媽。那躺椅微微搖晃著,仿佛黑暗中有什么東西在推著它。連華生用力按住,但堅持不了多久就筋疲力盡地癱坐在地上。
他摸著華容清的膝蓋:“你坐在那里干什么!”
但華容清沒有回答他。她變得漆黑而干硬,仿佛融入了夜色。夜深了,她閉上眼睛,仿佛睡著了。
連華生垂頭喪氣地拖著腳步走出中藥鋪的后室。大廳里,于清蓮正在柜臺后撥弄算盤。三只垂掛的燈泡散發(fā)出昏暗的光。算盤邊還有華容清原先用的戥子,中藥柜的幾個抽屜也打開著。
于清蓮見連華生如行尸走肉般顯現(xiàn)在燈光下,開心地招呼他:“老伯,不知怎么的,今天到了晚上,我就特別有精神,精神一來,也有了勇氣。”她走到大廳中央,轉了個圈,“你看,我走出來了。我思來想去,還是要感謝你。”
連華生勉力打起精神:“你走出來了就好。”
“老伯,你臉色很不好啊。”于清蓮扶住連華生耷拉的雙肩,十分擔憂地打量他,“我給你開服藥吧。”
連華生看她如旋風般從那幾個打開的中藥柜里揀出一些藥材,又快速地用戥子稱好。她折起一張油紙,想了想,又撿出幾根炙蜈蚣,混在一起,熟練地將藥打成幾個包,然后揮手越過連華生的腦袋:“哎!慶東華!把咱爸送回家去,”她推推連華生,叫他轉身向后,“這么晚了,他一個人不安全。”
連華生見兒子不知從何處睡眼惺忪地走來。兒子仿佛已經(jīng)對這里很熟悉了,變得更高大、更健壯。他不滿又無奈地接過那一大摞藥包。他一拉起連華生的手,連華生便抵觸地大叫:“我不要回去,我不要回去!”
“這么晚了,你還想干什么!”
連華生經(jīng)這一吼,氣力明顯衰弱,但一想到家所在的高樓便一陣膽寒:“我不要回去!”
“好了,不要置氣了。”
兒子像收攏晾衣架一樣,輕而易舉地將連華生背到背上。連華生在兒子臂彎的禁錮下徒勞掙扎。于清蓮又回到柜臺后繼續(xù)打算盤。她打得有些著急,打錯了好幾次,還有那么多的藥材等著她重新清點。連華生微弱的呼叫隨著兒子的漸行漸遠而趨于無聲。夜重歸于靜。她抬起頭,悵然若失地想了一會兒,似乎聽見外頭蛐蛐的叫聲,走過去關上中藥鋪的門,又走到簾子后頭,呼喊了一聲:“媽!”
沒有人回答。廁所里的水管又響了,好像有人用手指一下一下敲擊別人的名字。她又回到大廳,在幾個柜臺和臥室的衣柜里翻來翻去,不知為何越翻越亂。床上還有連華生的一些物品,她用床單卷好,準備一齊丟到藥鋪后頭的垃圾場去。扯床單時,床縫掉出一本寫有續(xù)命術方子的書。于清蓮翻了頭幾頁,這些看不懂的方子令她皺眉。她把書夾進床單,打成一個包袱堆在門邊。最后,她從藥柜下翻出了一件薄毯,在這個漸涼的夏末夜晚,肘靠柜臺思考了一會兒剛剛那個陌生的方子,那張續(xù)命術,忽感風從門縫中吹進來,又腳步匆匆,掀起簾子來到藥鋪黑暗的后頭,將毯子蓋在躺椅上的媽媽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