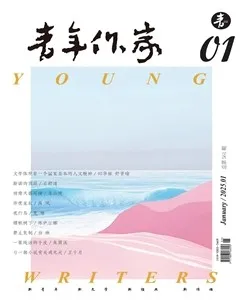怎么了
文惠收到了一條短信。
怎么了
由于沒有標點符號,這可能是個問題,怎么了?也可能是個過程,怎么了……也可以是個結局,怎么了。
發出這個“怎么了”的人,好些年沒見過了。
多年不出現的人,怎么突然就出現了呢?往上翻一下,上一條訊息已經是十年前,對方發來的是一句:我刪你了!感嘆號!可見其情緒激烈。
文惠沒回,十年前就沒回,十年后才知道沒回,沒回的原因可能是忙,也可能是根本沒看到。可是,既然都刪了,怎么又出來了?文惠一直搞不清楚微信的功能,文惠懷疑對方只是拉黑她,又把她放出來,但是他拉來放去,好像也就是他自己拉來放去。文惠都是不知情的。
文惠這次馬上就回了。文惠說,我怎么了?反問的問號。
你遇到什么事了?
文惠說,我遇到什么事了?
你要有事,告訴我。
文惠停頓了一下,說,那你告訴我,二十年前,你為什么一直擦你的腳踏車?
因為車是新的,他說。
文惠只好說,哦。
我想見你,他又說。
文惠笑了一笑。見不見的,文惠要想一想。
文惠很快就回家鄉了,倒也不是真要見誰,本來就要回,交通發達了,故鄉不再是回不去的故鄉。不像古人,離鄉就是永別。
十幾個小時的飛機,足夠文惠把往事再想好幾遍。窗外云層蓬松,如幻影如泡沫,都似是假的。
二十年前,文惠有個男朋友,男朋友有一輛腳踏車,每天傍晚騎來文惠家,第一件事情,要一塊舊布擦車,擦來擦去,連輪胎都擦。
你是喜歡腳踏車還是喜歡我呀?這是文惠當年的問題,可能也是很多年以來的問題。
當年的男朋友說,這是山地車,21級變速的,不是腳踏車,腳踏車只有一個速度。
文惠和男朋友分手了一年都沒有緩過來,初戀,緩不過來。現在看來,二十年都有點緩不過來。
文惠去買山地車,店里沒有21級變速的款式,家里人認得車廠廠長,自己去廠里提。
取了車,騎回家。車廠遙遠,預計需要兩個小時,可是四個小時都沒能騎到。山地車竟然很難騎,變幾個速度都沒有用。上橋的時候,終于哭出來,實在騎不動了。下了車,坐在橋沿,才發現輪胎是癟的。車廠出來的新車,沒有氣,也沒有人提醒她要先充氣,就這么騎了一路。
文惠找了個工作,與前男友的單位在一個大院,一個大門。可是再也沒有互相碰到過。文惠只在車棚里看到他的車,她把自己的車停在那輛車的旁邊,經過車棚打水的時候也會看一看那兩輛車。整個大院僅有的兩輛,21級變速的,山地車。
前男友被單位派出去進修,三個月,車棚里只有一輛山地車了,文惠的。
文惠時常加班到半夜,漆黑的夜,昏黃燈光,車棚里最后一輛車,開鎖的聲音都顯得凄涼。一天又一天。前男友回來的那一天,文惠突然提出辭職,徑直走下樓梯,進車棚,推了自己的車,出了大院門。文惠騎車騎得飛快,頭都沒有回。山地車果然是可以加速的。
文惠換了個工作,唯一的不便是要搭班車上班,從家里到班車站點,騎車三分鐘。單位實在太空,同事實在熱心,都要給文惠介紹對象,前程一個比一個好。文惠只是笑笑。前男友提分手的理由就是前程,領導說的,還年輕,心思不要放在兒女情長上,要奔前程。
早晨的站點,一個人都沒有,文惠把車停在一間沖印店的門前,與一棵樹鎖在一起。班車到達的時間是七點,沖印店開門的時間是十點,可是也沒有別的選擇,沒有別的店,也沒有別的樹。
每天傍晚從班車上下來,文惠第一眼就會看到自己的車,與一棵樹鎖在一起。文惠開鎖,騎車回家。一天又一天。直到有一天,下了班車,車不見了,繞著那棵樹轉了一圈,車真的不見了。走路回家,騎車三分鐘,走路也不過六七分鐘。文惠竟然如釋重負。
文惠為什么也要買車呢?明明并不喜歡騎車。
這個問題,也有人問過。這個人,還是前男友的一個同事。
分手不久,前男友的同事就來約她,這就有點戲劇了。
文惠還應了約。為什么?只有文惠自己知道。
看到他推著車過來,文惠還是愣了一下,因為一眼看到,那是前男友的車。
同事的。他說,到單位附近吃點什么,所以跟同事借來用。
文惠說,哦。
我住得遠,上下班騎車可是到不了的,他又說。自己倒笑了一聲,盡顯尷尬。
文惠不說話,不知說什么好。
有一間湯圓店,很近。前男友的同事說,我們就去吃湯圓吧。
文惠說,好。她當然知道那間店,前男友帶她去的,一對老夫婦的小店,不賣別的,只賣湯圓。他總是要鮮肉湯圓,她只吃白糖小圓子。也有可可圓子,文惠總會去想,那會是什么味道?
店卻關了。
咦?前男友的同事說,前些天還來過呢,怎么就關了?
文惠看一眼門上貼的通告,結業了。
怎么說關就關了?同事說。
文惠說那就不吃了吧。
去吃別的。同事說,然后看電影。
文惠看了一眼車,前男友的車,突然就說,這個車好看嗎?
同事也看一眼車,說,還好吧。
有人覺得這個車很好看。文惠說,有多好看呢,那個人每次到女朋友那兒,都問女朋友要一塊布擦車,一擦就是半天,擦完之后就一直盯著車看,女朋友心里面想你盯著我都沒有看過那么長時間。
前男友的同事說我才不會去看一個腳踏車,我只會盯著女朋友看,如果我有一個女朋友。
文惠笑了,說,所以那個人的女朋友成了前女友。
同事愣住,不知說什么好。
就這樣吧。文惠說,飯就不吃了。
電影也不必了,文惠又說。
那么有沒有再見?文惠與前男友。
見了,一面。文惠說,前男友訂了個私房菜館,小包廂。
太戲劇了吧。
是挺戲劇的,比他的同事來約我還要戲劇。文惠說。
他說,見你是要告訴你,愛過你。
不知道如何回應的情況下,只能問,那你為什么老是擦你的車?
你還記得那輛車?
我只記得那輛車,文惠說。
記不記得我們的第一面?他說。
文惠搖頭。
他一笑,酒窩縱深了許多,落在法令紋的紋腳,顯老了許多。
我們的第一面。他說,我差一點撞到你。
文惠說,這就有點驚喜了。
我從來沒有提到過這個第一面。他說,那天我騎著我那輛12級變速的,是12吧……
21。文惠糾正他。
……我騎著我那輛21級變速的山地車,速度太快,差點撞到你。
完全沒有印象,文惠說。
你抬了抬眼,但是完全沒有看我,你沒有看任何人,眼神是散的,可是太打動我了……我四處打聽,打聽到你……
一定要文惠回憶一點什么,如果正在街上走,很規矩地走著,卻差點被很不規矩的車撞到,對方還很沒有禮貌,竟然還扔了句“怎么了”過來……她也只能懶得理,略一抬眼,走人。
文惠說,哦。
一時冷了場。
還記得我那個時候的主任嗎?他又說,也是見過幾次的。
文惠說,記得,她那么不高興,所有的不高興都掛在臉上。
他也只能笑笑,因為文惠說得都對。
你那時要上夜校,要拿文憑,考編。文惠說,那些對你來說太重要了。而且我們也太年輕了。
你后來消失了,不見了。他說,去哪里了?
文惠笑笑。
我也買了輛山地車。文惠說,跟你的一樣,21級變速。
我知道你那輛車。他說,見過。
我找了個工作,自己找的。文惠說,上了三個月班,有一天突然就不想上了,家里安排我去了一個機關上班。
那不挺好?他說。
挺好?文惠笑了,說,對很多人來說是挺好的,都被安排好了。
他不說話了。
單位有點遠,要搭班車上下班。文惠說,每天早上我都是騎車,再轉搭單位的班車上班,每天早上我都是把車停在一間沖印店的門前,和一棵樹鎖在一起。每天傍晚從班車上下來,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車,車還在,和一棵樹鎖在一起,那就開鎖,騎車回家。一天又一天,好多天。
他說其實做公務員真的挺好的,挺安穩的。
是啊,好安穩。文惠又笑了一聲,說,可是我不要啊,我不要那樣的安穩,我只要出去,我要去外面的世界,世界多大啊。
他望著文惠,其實他眼里的文惠,也很陌生,好像從來就沒有理解過。
終于有一天,從班車上下來,沒有看到自己的車。文惠說,繞著那棵樹轉了一圈,又轉一圈,真的沒有,真的被偷掉了。我就走路回家了。我也不難過,我一點兒也不難過。我一路走,一路笑,一路笑到家。我很快就離了職,離開了,就是你說的,消失了,不見了。我從這個城市徹底消失了。
他停了好一會兒,終于說,你要自由。
文惠說,對,你終于有一句話講對了,我要自由。
所以我離開的時候就沒有打算再回來。文惠又說,如果編制這種東西都能戰勝愛,如果奔前程都成為了一個理由。
我愛過你。前男友說,真的愛過。
謝謝。文惠說,我也只能說謝謝。
前男友的擁抱突如其來,文惠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文惠僵在原處,驚嚇之外,唯有厭倦,深深的厭倦。
后來呢。
文惠家鄉的一個朋友告訴文惠,前男友換了輛囂張的越野車。
文惠說,知道,見過一次,他從那車上跳下來,很是風光。
也許用囂張這個詞更精確。朋友說,有一次,在一條窄巷,我與他迎面對上了,一眼認出來他的車,但既是后來進來的,退讓是應該的,他偏不,對峙在那里,也是自以為有了點權勢。
后來呢。
朋友下了車,直向他走過去,他一見,馬上滿臉堆笑,將自己的車退了出去。
幾次交道打下來。朋友說,此人重利,不可交。
文惠不說話。喝茶。
還有那個約過你的,前男友的同事。朋友說,文惠你這些年不在,可知他已是本城網紅?
文惠一笑,說,我都離開了,還去管什么網紅。
人家粉絲成千上萬,怎么當年就沒有火花?
文惠喝一口茶,說,火花這種東西,也真是玄妙,有時候有,有時候就是沒有。
真是想不到。朋友說,他有一天會成為網紅。
文惠笑起來,說,網紅也不是天生的,多少網紅在成為網紅之前,就是一根草。不過也是一種自我突破吧,就這一點,真心佩服。
【作者簡介】周潔茹,作家,出生于江蘇常州;著有長篇小說《島上薔薇》《小妖的網》,小說集《我們干點什么吧》《你疼嗎》等;現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