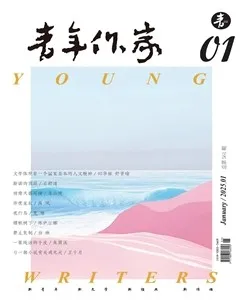斯諾的預旺
【作者簡介】石舒清,小說家;本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出生于寧夏海原縣,1989年畢業于寧夏固原師專英語系;著有小說集《伏天》《苦土》《開花的院子》《暗處的力量》等多部,曾獲魯迅文學獎、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莊重文文學獎等;現居銀川。

預旺行
有了寫這篇東西的念頭時,我就決定找機會去預旺一趟。這實際是再容易實現不過了,我是寧夏人,預旺就在寧夏同心縣。從我老家到銀川,同心是必經地。說來是這樣,但實際上預旺在同心的東南部,預旺古城距離同心縣城72公里,也就是說,許多年來,我在銀川和老家往來之際,無數次經過同心,但沒有一次經過預旺。要去預旺就得專門去,而我近年來的頭暈毛病讓我不敢獨自遠行。但想寫這篇東西的念頭促使我想去預旺看看,看看當年預旺在紅色政權中為什么會有那么重要的位置和分量,看看國際知名人士斯諾先生在預旺的行蹤遺跡。我小區樓下有一家同心人開的飯館,我和老板打問過去預旺是否有直達班車,說有的。后來他再見到我時,就問我去了預旺否?我說還沒有,他就用特別的眼神看著我,好像在說,這是多大的事呢?費得著做這樣的準備和熱身么?我也覺得自己實在是一個缺乏行動力的人。作為一個喜歡寫作的人,行萬里路方面我是做得遠遠不夠的,我縣的一些鄉鎮至今我還沒有去過。記得三十多歲的時候,我陪江西的一個作家去寧夏有名的旅游景點須彌山,我作為土著導游,結果是讓她沒能看到須彌山大佛,因大佛在一個拐角處,我們沒走到拐角那里去。那是江西作家第一次到須彌山,不好意思,我這個導游也是第一次到須彌山。帶朋友游須彌山卻錯過了北魏大佛,那當時我們在須彌山究竟看了些什么?這簡直就是一個笑話,多年來成為我的一個心結,覺得辜負了江西文友。至于名播天下的六盤山,就在寧夏隆德縣境內,就在固原市,我這個年過半百的固原人竟然沒有去過,說來真是沒人能信。但這次去預旺的念頭格外強烈,我要去預旺看看,我要去斯諾去過的地方看看。斯諾的名著《西行漫記》封面上的小號手照片,就是他在預旺拍攝的。我準備買周日的班車票。周六,銀川海寶小區會有很多的舊書攤,是我常去的地方,那天和朋友同去轉書攤,我告訴他次日我要去預旺。他說,你小心一些。他知道我頭暈的毛病。但沒想到我的頭暈病忽然就發作了,而且是多年來比較嚴重的一次。我當時在一家書攤前蹲著看書,忽然就感到頭暈眼花,因常常是這樣,我也不是很緊張,靜靜地等待著眩暈過去,然而顯然這次不同往時,往時暈暈也就過了,這次卻是久暈不過,而且我覺得雙眼鼓脹,臉頰也麻木起來,緊跟著上嘴唇也麻了,好像無形中腫起老高。我暗想不好,不得已說給一同逛書攤的朋友,我們就打車去了醫院。
長話短說,結果沒什么打緊,但后來的幾個月我一直在吃藥調理,預旺行只好擱置。有時候躺在床上,我想著預旺,想著斯諾在預旺的見聞經歷(都是我通過讀資料或聽人講述得來的),我這樣想著,就奇怪地覺得斯諾在預旺的種種經歷在我這里清晰起來,倒好像我和他一同經歷了似的。這樣一種形式的預旺行,說來也是夠特別了。
特別的預旺行,借重種種可靠資料提供的方便,記在下面。
騎兵隊長
那時候我們海原縣還屬甘肅管轄,紅軍在與馬家軍的作戰中繳獲了不少戰馬,使騎兵隊的力量得以壯大。騎兵隊隊長是一個二十六歲的干瘦小伙子,他愛馬愛得有些過分了。他慷慨地分配給斯諾一匹好馬,配著西洋鞍子。但是他要求騎兵們騎上一段,就要下馬來走,以防把馬累著。往往是騎上一公里,下馬來陪馬走上三公里,這算什么騎馬。因為大家都這樣,斯諾不方便搞特殊,但是從馬上下來陪著馬走時,斯諾就走了一肚子的不愉快,照這個樣子,還不如沒有馬,直接步行來得痛快。見到時任紅十五軍團團長徐海東時,斯諾把對于騎兵隊隊長的不滿婉轉地表達了出來,惹得徐海東大笑,于是讓斯諾把那匹只能陪著走不能騎的馬還回騎兵隊長,另給了斯諾一匹強壯的寧夏馬。這一次斯諾算是騎美了,寧夏馬像強弓射出的箭似的,在開闊的平原上奮蹄奔行,五十里的路程中間只歇了一歇,同行者被寧夏馬紛紛甩向身后,當斯諾一人一騎出現在預旺城時,那馬還像剛剛出發時一樣充滿勁頭,一氣跑到司令部門前才不得不停下來,意猶未盡地搗騰著前蹄,噴著響鼻。斯諾從馬上下來,撫摸著汗津津的馬臉表示著贊賞和感謝。他決定親自找點好飼料喂喂這馬。這樣一次酣暢淋漓而又愉快的騎行之后,對于騎兵隊隊長的不滿,好像也給丟在身后很遠處不再受影響了。
賣西瓜
賣西瓜的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回民老漢(斯諾稱其為老漢,其實五十歲上下還算不得老漢,也許是那時候人的壽命普遍不高的原因吧),他有著一面坡的西瓜地。圓滾滾的西瓜看起來像閱兵時綠油油的地雷。從眼神和面部表情看,回民老漢就像是駕在獵人手上的一只勁道十足的鷂子,但是他和你眼對眼時,眼神就柔和起來,顯露出足夠的善意,像是忽然間認出了老朋友似的。讓斯諾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他的女兒,十五六歲的樣子。那女孩好看得讓人心生憐惜。但是她躲閃著不讓人看她。她側身站著或背過身去時,身影也是很耐看的。她的好看使整個環境和氛圍都有些異樣。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好看的女孩讓人感到一種莫名的不安和擔心。斯諾心情復雜地覺得,有些時候有些地方,美好像顯得不合時宜。
不知怎么一來,回民老漢就說起了馬鴻逵,他一時氣憤得好像不會說話了似的,他說他三個兒子,其中兩個兒子讓馬鴻逵抓去當兵,給他馬家當兵,娃娃的衣服食糧還要兵娃子家里供給,一年就這個花銷,也得幾十塊啊。一個老鄉提醒說,你這樣說馬鴻逵的不好,傳到人家耳朵里夠你受的。回民老漢就顯露出了鷂子一樣的眼神,說,我不怕,我當著他馬主席的面都是這話。
這時候走來幾個小紅軍,前面的一個懷里抱著只兔子,兔子的紅眼睛寶石似的,不知道在這樣的眼睛看來,世界又是什么樣的。總覺得這樣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和我們眼里的世界不盡相同。幾個小紅軍嘁嘁喳喳合計了一番,就由抱兔子的小紅軍和回民老漢說,他們想用這只兔子換西瓜吃,不知道能換不能換?如果能換,怎么換合適?回民老漢同意換,兩人商量了一陣,終于敲定,一換三,這兔子可換三個西瓜。小紅軍們留下兔子,抱著西瓜走了,好像他們在議論著這個買賣他們吃虧不吃虧。回民老漢把兔子給女兒抱著。一會兒工夫,那幾個小紅軍又返回來,看來西瓜已經被他們吃掉了,但他們支支吾吾地說,兔子是司務長派他們來山里捉到的,要給戰士們打牙祭用,現在可怎么著是好。聽口氣他們是想討回兔子。回民老漢說,可以,把我的西瓜拿來。那幾個頭又碰到一起悄悄嘀咕什么。還是那個先前抱兔子的向前靠靠,挨近回民老漢,難為情地低聲對他說,嘴饞想吃西瓜,沒忍住把兔子用來換了,回去沒辦法給司務長交待了。他又說,能否先記賬,過幾日有錢了就把西瓜錢還了。女孩抱著兔子背對他們站著,但顯然她是聽到了小紅軍的話。她的背影的樣子說明她是聽到了。小風把她的衣裳的后背吹出細微的水紋一樣的動靜來。回民老漢說,你們要是馬鴻逵的兵,我啥話不說,把兔子給你們,但你們說你們是馬鴻逵的兵么?那幾個又是一番嘁嘁喳喳,先前抱兔子的小紅軍偏頭看了看女孩不為所動的背影,就互相勸說著那樣離開了。回民老漢望著幾個小紅軍的背影,有一刻他好像要對著他們的背影喊一聲,但還是改了注意,向立在一邊的斯諾等人神情復雜地笑笑,斯諾也表示理解和支持地對回民老漢笑笑,然后自己掏錢買了幾只西瓜,幾個人各抱一只西瓜離開了。斯諾們走出老遠,那女孩才偏頭看他們,從側面看到小風吹動著她的劉海,像高妙的手指輕輕拂動著琴弦似的。
收稅員
斯諾在預旺時,極受觸動的一件事是,當地人民用極端的方式處置了一個國民黨的收稅員,把他捉來公審后槍斃了。
是這樣的,這個人確實是國民黨的一個收稅員,就是預旺城附近某個村子的人,原本是種地的,后來因為某種關系成了國民黨的收稅員。國民黨的稅多。老百姓對收稅員的印象向來就是惡劣的。尤其這個收稅員,他不只收稅,還吸大煙,每到一個地方,派稅的同時,還要求村長、保長給他弄一點大煙來供他吸食。又不敢不滿足他。所以就算是村長、保長們對這個收稅員的印象也不好。預旺被紅軍接管后,這個收稅員消失了一陣子,忽然又出現了,這次他宣稱說他不是國民黨的收稅員了,他宣稱說他已經正式接受了紅軍的任命,負責給紅軍收稅,他現在的正式身份是紅軍收稅員。老百姓是誰收稅都不敢不繳的,這就讓他得逞了。他故技重演,照慣例要求盡快給他提供一份大煙來。這就讓一些覺悟高的農民起了疑心,當他蹲在一個墻根里曬著太陽吸大煙時,被四處尋他的農民堵個正著,問他說,紅軍沒有收稅員,他收了稅,是繳給了哪搭的紅軍?這一問就問出了收稅員一臉的緊張,他說,你們先不要急,等我吸罷煙和你們說。農民們劈手奪了他的大煙讓他趕緊說個清楚。他無法說得清楚。幾個農民就把他結結實實綁了,交給了剛剛成立的臨時蘇維埃政府委員會。一時群情激憤,要求讓這個大煙鬼吃槍子兒。幾天后經過公審,果然就把這個收稅員槍斃了。臨刑前收稅員要求給他一頂新的白帽子戴著好上路,大家紛紛痛斥他說,你一個大煙鬼戴啥白帽帽,再不要丟你先人的臉了。
斯諾在《西行漫記》里就這件事這樣寫道:“我認為這是對這邊農民最重要的一件事。”
小紅軍
斯諾在《西行漫記》里專門就小紅軍寫了一節,寫到多個小紅軍。斯諾對小紅軍們有一個整體性描述:
他們大多數人所穿的衣服都太大,袖子垂到膝頭,上衣幾乎拖到地上;
他們吃得很多,每個人都有一條毯子,他們的領袖甚至還有一支手槍;
他們纏著紅布,戴著多少嫌大一些的破帽子,上面綴著一顆紅星;
他們的出身都很模糊。有許多記不清自己的父母;
有許多是逃亡的學徒,大多數是從人口過多,不能過活的小屋里逃出來的;
而他們全體是自己決定加入紅軍的,有時候成群的少年逃到紅軍里去;
他們的神情不像孩子;
他們之所以喜歡紅軍,大概是他們在紅軍里第一次受到了人的待遇的緣故。
……
斯諾寫到,有許多小紅軍實際上都打過仗,甚至是和敵軍拼刺刀,斯諾寫到一個細節,小紅軍和白軍拼刺刀的時候,白軍把小紅軍們上了刺刀的槍奪過去,然后笑著把他們推入旁邊的戰壕里去。由此細節可以看出孩子們就是再勇毅,也還是越不過作為孩子在體力方面的上限。
有一個從福建來的十五歲的小紅軍對斯諾說,他加入紅軍已經滿四年了。斯諾吃驚地說:“那說明你加入紅軍的時候才十一歲?”“是啊,我現在算是一個老紅軍了。”十五歲的孩子老練地意氣洋洋地說。
小紅軍里有不少人在認知和才干方面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實際年齡,有一個小紅軍,是小紅軍的一個小領導,也才十五歲,但是他跟著大部隊走過了萬里長征,當斯諾問他:“這是(指長征)很辛苦的吧?”這個十五歲的少年是這樣回答的:“不辛苦不辛苦,與同志們在一起走什么長征都不辛苦。我們革命的少年不能夠想到事情的辛苦不辛苦,我們只能夠想到我們當前的任務。如果它要我們走一萬里,我們就走一萬里,它要我們走兩萬里,我們就走兩萬里!”
接下來斯諾問他是他的老家江西好還是現在他所在的甘肅好。
小紅軍回答說:“江西是好的,甘肅也是好的。有革命的地方都是好的。我們吃什么,我們睡在什么地方,都是不重要的,只有革命是重要的。”
這段對話后的第二天,斯諾驚訝地發現,在千百人的紅軍大會上,站在前面分析政局、慷慨陳詞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前一日和他對話的少年。斯諾對他有一個由衷的評價:“他天生是一個宣傳家。”
一個叫向季伯的小紅軍給斯諾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
在《西行漫記》這樣一部重要的著作中,斯諾拿出了幾乎一頁多的篇幅寫了這個小紅軍。
向季伯是所有斯諾見過的小紅軍里,衣著最干凈最合身的小紅軍,斯諾說,不要說小紅軍,就是那些顧不上收拾自己的紅軍領導人,和向季伯一比,也像是一些流浪漢。斯諾對向季伯的描述是:“他是鎮上最漂亮的一個士兵。”
但是有一天,向季伯卻來到斯諾的小房子里,首先給他敬禮,那是斯諾見過的最為標準的軍禮,他稱斯諾“斯諾同志”,他顯得過于鄭重地說,他要來給斯諾同志澄清一件事,也許斯諾同志早就知道了,是這樣的,他名叫“向季伯”,但在某些方言里,“季伯”容易被誤讀,說到這里,孩子顯現出很痛苦的樣子來,他對斯諾說,斯諾同志,“季伯”實際上是很好的名字,他為自己有這樣的名字而驕傲,有些同伴喊他的綽號,使他很痛苦很熬煎,同伴們也許是故意這樣叫的,就算不是故意,就算確實是口音的原因,這樣叫也會讓他難堪,一個人的尊嚴是受不了這個的,他思慮再三,覺得還是找找斯諾同志的好,所以今天他特意來找斯諾同志,就是要澄清這一點,要斯諾同志不要聽信那些烏七八糟的話,要斯諾同志知道他有一個很好的中國名字“向季伯”。說得斯諾也鄭重起來,斯諾發誓一樣對眼前站得筆直顯得痛苦的孩子說,他只叫他向季伯,要是他叫了另外的什么,那么,向季伯同志可以拿刀殺死他斯諾,或者用手槍打死他。
向季伯好像還不能完全放心,他從口袋里拿出一張紙條,紙條上就寫著他的名字“向季伯”,是他自己寫的,他把紙條給斯諾看,一個字一個字給斯諾指點著讀著讓斯諾聽。他說,斯諾同志,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名字,假如您寫了書,在外國出版,假如外國的同志知道中國有一個小紅軍叫那個混蛋名字,那事情就太大了,這是我特意來找您的原因,您能明白么?斯諾對向季伯保證說,他在書里只寫“向季伯”這個很有中國味道和中國深意的名字,別的名字不用向季伯說,他自己這里都不能通過的。得到這個保證后,向季伯長舒了一口氣,像完成了一項任務似的。他給斯諾深鞠一躬,又是一個標準敬禮,像個真正的軍人那樣走出去了。
斯諾說,原本他沒有打算寫向季伯的,但這樣一個經歷后,他覺得如此一個儀容整潔、護守尊嚴的中國孩子,應該在自己的書里有著一個特別的位置。
贅語
雖說有如上形式的預旺行,但我去預旺實地看看的念頭還是有的,我對老婆說,等我吃藥調理得好些時,我們一起去預旺吧,去住上三天,好好看看。老婆說,好。其實向來皮實的老婆近期身體也出了點小毛病,年歲如此,也屬正常,我們的預旺行看來還得往后推推。好在現在信息獲得方便了,網上有不少關于預旺的小視頻,總有千百個之多,足夠看的。但我覺得不看還好,看了之后,好像對我想象中的預旺造成了一個大的干擾和破壞,反而變得沒激情,沒心思了。我想象中的預旺,紅色重鎮預旺,斯諾在《西行漫記》里重重落過一筆的預旺,全然不是小視頻里所呈現的預旺。看景不如聽景,難道總是這樣?一天在單位的一個攝影家那里,很偶然地看到兩張關于預旺的老照片,是對同一個堡子門不同時間的拍攝,一張拍攝于20世紀30年代,一張拍攝于20世紀80年代。兩張照片的重要區別是,30年代照片門額上的幾個大字,到80年代已經看不到了,我想問問常常采風的攝影家,80年代的這個堡子,現在還在么?還是80年代的樣子么?話到口頭,又沒有問出來。記得有資料說,魯迅先生原本有寫楊貴妃的打算,于是去西安實地考察,結果是,魯迅先生后來并沒有寫出楊貴妃來,據傳魯迅先生有感慨云:“連天空都不是唐朝的了。”如此說來,去不去預旺,已經是沒有那么要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