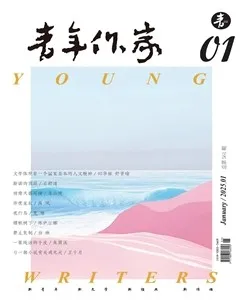文學體現著一個國家基本的人文精神
多和少的體悟是寫好短篇小說的關鍵
舒晉瑜: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創作的?短篇小說在你的創作中占有很大比重?
邱華棟:最早的一個短篇小說《永遠的記憶》寫于1984年,那年我十五歲,寫的是一種感覺和心理狀態,很短,現在看來應該算小小說,也就兩千多字。我進入到大學之后,寫了關于少年記憶的系列短篇《我在那年夏天的事》。這些小說表達的,也都是關于青春期成長和窺探世界的那種惶惑、煩惱和神秘感。每次寫短篇小說,我都把結尾想好了,因此,短篇小說的寫作,對于我很像是百米沖刺——向著預先設定好的結尾狂奔。因此,語調、語速、故事和人物的糾葛都需要緊密、簡單和迅速。
大學畢業后來到北京,我感受到城市的巨大張力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的投射,于是,大概花了七八年時間,我寫了《時裝人》系列小說,一共有五十篇。這些短篇的篇幅也不長,每篇都有一個詩歌意象在里面,比如《重現的河馬》里面有河馬,《刺殺金槍魚》里面有金槍魚,《時裝人》里面有時裝人和大猩猩,而《蜘蛛人》里出現了城市蜘蛛人。這些短篇都有詩意的追尋和城市異化帶來的那種變形,小說故事本身不是寫實的,而是寫意的,寫感覺、象征和異化的,并帶有成長后期的那種蒼茫感。
舒晉瑜:你的短篇有怎樣的特點?
邱華棟:比如《十三種情態》是十三篇與當代情感、婚姻、家庭、外遇、戀愛有關的短篇小說。這些小說的題目都只有兩個字:《降落》《龍袍》《云柜》《墨脫》《入迷》《禪修》等等,每個短篇的篇幅在一萬五千字左右。
我寫短篇小說,從二十多年前的一兩千字,寫到了如今的一萬五千字左右。我也在思考為什么我經歷了這么久,才把小說寫到了一萬五千字。我覺得,對于我來說,如何寫短篇小說,一直有一個“多”和“少”的問題。一萬五千字的短篇,時間的跨度和人物的命運跌宕都有很大的空間感。比如,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說,是“少”的勝利。我覺得他的簡約和“少”,是將一條魚變成了魚骨頭端了上來,讓你在閱讀的時候,通過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想象力,去恢復魚骨頭身上的肉——去自行還原其省略的部分,去自己增添他的作品的“多”。這對讀者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此,顯得非常風格化。
但雷蒙德·卡佛不是我很喜歡的短篇小說家,因為“少”使他顯得拘謹,小氣。我還是喜歡骨肉分配均勻的短篇小說,比如約翰·厄普代克、約翰·契弗、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莫言、艾麗斯·芒羅(我不喜歡她的名字被翻譯成“門羅”)的短篇小說,他們是我最喜歡的,將“多”和“少”處理得非常好的短篇小說家。所以,寫短篇小說,就應該在其篇幅短的地方做長文章,在多和少之間多加體悟,可能是寫好短篇小說的關鍵。
舒晉瑜:《十一種想象》是一部很有創意的歷史小說集,你的每一篇、每一部作品都在出新。
邱華棟:《十一種想象》是歷史小說系列,一共十一篇,我取材于各個國家的歷史和人物故事,出現的歷史人物有成吉思汗、丘處機、韓熙載、玄奘、魚玄機、李漁、利瑪竇、埃及法老圖坦卡蒙和他的王后安克赫森阿蒙等等。面對歷史展開想象,是我的新嘗試。
我平時喜歡讀閑書,亂翻書,其中就讀了不少歷史書。二三十歲的時候,心態比較浮躁,寫了不少當下都市題材的小說。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心慢慢靜下來了,讀書也更加雜亂。在閱讀歷史著作的時候,我時常會萌發寫些新歷史小說的念頭。這本書可以說就是這樣一種心態下的產物。我不喜歡重復自己,每次寫個小說,總要稍微有些變化,或者題材、或者結構、或者敘述語調等等。十多年下來,我寫的歷史小說中有幾部是長篇,如《中國屏風》系列四部,以近代歷史上來到中國的外國人為主角。現在這一本則是十一篇中短篇小說。其中,有三部中篇小說《長生》《安克赫森阿蒙》《樓蘭三疊》,其余八篇是短篇小說。
舒晉瑜:從題材上看,中外都有,不同歷史時期都有,都是依據一些史實所展開的關于歷史的想象?
邱華棟:是的,比如收在小說集里的《長生》,寫的是13世紀初期,丘處機道長應正在成為人間新霸主的成吉思汗的召請,不遠萬里,前往如今的阿富汗興都庫什山下面見成吉思汗的故事。我在上大學的時候,讀了丘處機的一些詩作,非常喜歡,就對這個人物產生了興趣,何況他又是中國道教的著名人物。因此,才有了《長生》的中篇版和長篇版。其實,假如今后有時間,我還想再把《長生》的小長篇擴展成大一點的長篇,類似吳承恩的《西游記》那樣,虛構出丘處機帶著十八個弟子,一路上與妖魔鬼怪斗法的故事,這樣是不是更有趣呢?
我在寫這些小說的時候,有意地、盡量地去尋找一種歷史的聲音感和現場感,去繪制一些歷史人物的聲音和行動的肖像。這可能是我自己的歷史小說的觀念吧。比如,我一直很喜歡《韓熙載夜宴圖》這幅畫,最終導致了《三幅關于韓熙載的畫》的寫作。我想象了歷史上失傳的、關于韓熙載的另外兩幅畫的情況,以及韓熙載和李煜之間的關系。《色諾芬的動員演說》取材自色諾芬本人的著作《長征記》,色諾芬是古希臘很有名的作家,他的多部作品被翻譯成了中文。我一直對希臘羅馬時期的歷史著作有興趣,這篇小說不過是隨手一寫。我曾經做過一個夢,夢見我在一座古城里醒來,一個古代的人在我的耳邊說:“這是亞歷山大大帝所征服和建造的城市,它是亞歷山大城!”眾所周知,亞歷山大很年輕就去世了,死之前他已經建立了很多亞歷山大城,他的遠征路線一直到了印度。我不知道我今后會不會寫一部關于亞歷山大大帝的長篇小說。我覺得是有可能的,因為我對他的生平特別有興趣。《利瑪竇的一封信》則是我有一天去北京市委黨校,看到利瑪竇的墓地之后,產生了寫一篇小說的想法,取材于他的《中國札記》和史景遷的研究著作《利瑪竇的記憶之宮》。讀了這篇小說,你一定會對利瑪竇有一個基本的了解。這十一篇小說,于我是一種題材的拓展和大腦的轉換,假如能給讀者帶來一點對歷史人物的興趣和會心的微笑,我覺得就很好了。
寫記憶容易,寫今天很難
舒晉瑜:《來自生活的威脅》和《可供消費的人生》延續了你“與生命共時空”的文字風格。和所經歷的時代如此近距離的表達,你覺得有何利弊?
邱華棟:書寫眼前和當下是十分困難的。我覺得對眼前萬象的文學捕捉,讓我感到刺激而新鮮。寫歷史是容易的,寫記憶也是容易的,可寫今年和今天呢?很難很難。而我卻在把小說寫新,我也常常覺得很難,就像是你以為你抓到了一條魚,可是你一看,它已經跑掉了。
舒晉瑜:《來自生活的威脅》把故事集中到了高檔社區,在閱讀的時候,感覺似乎是要刻意營造一種社區環境和背景。是有這樣的用意嗎?
邱華棟:不是刻意的。這個系列我從2000年一直寫到了2010年,十年的時間寫了六十篇小說,一開始是按照單篇的短篇小說寫的,可我寫著寫著,覺得可以把很多小說像串糖葫蘆那樣,把它們都串起來,形成新的結構。這樣,這些小說之間就有著松散的聯系了。比如《騎兵軍》《都柏林人》《小城畸人》《米格爾大街》,都是類似的作品。
舒晉瑜:為什么關注社區文化?
邱華棟:北京不就是由一個又一個的社區構成的都市嗎?社區將是都市人生存的最重要的環境。但新的社區文化卻還沒有定型,我通過這個系列的寫作,來探討當代中產階層面臨的困境,試圖尋找新道德和新的價值觀定型的可能。一個文明的復興,關鍵還是要看你能輸出什么樣的價值觀。其他都是空談。
舒晉瑜:《來自生活的威脅》反映了不同家庭的形形色色的故事。聚焦社區其實也是你的作品對城市文化的表現之一。
邱華棟:當然首先是題材的突破。我自己曾經當過編輯,看到百分之七十的稿子題材依舊是農村題材的,很多寫作者的技術含量也不高,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民大國,作家多出自農民,大作家更是農民。我是少數書寫城市的都市作家,從觀察對象是中國的中產階層這一點上,我的這個“社區人”系列也是很有意思的。
舒晉瑜:有時候感覺你講故事的愿望特別明顯。
邱華棟:1993到1999年,我寫了一個五十篇短篇小說構成的系列“時裝人”,那個系列是變形、夸張和意象化、碎片化的有后現代意味的小說系列。而這個“社區人”系列六十篇,我有意識地在找講故事的感覺,寫得比較老實。我想,講故事就類似繪畫里的素描,是一個基本功。
左手當代,右手歷史
舒晉瑜:你寫了大量的城市題材,從短篇、中篇到長篇《北京傳》,多數是關注當下,描寫現實生活的作品,《空城紀》的創作題材在以往的延續中又有變化。你怎么看這些年的創作?
邱華棟:年輕的時候創作量很大,每年能寫十幾個短篇。30歲以后,慢慢地有一些歷史感,就逐漸形成一種狀態:左手寫當代題材,右手寫歷史題材。中間寫了一組“中國屏風系列”(《賈奈達之城》《單筒望遠鏡》《騎飛魚的人》《時間的囚徒》)、長篇小說《長生》,由此延伸下來,我現在的寫作習慣就是有意地讓自己調整,保持新鮮感。比如左手寫完一個當代題材的《哈瓦那波浪》,右手就寫一個歷史題材的短篇小說集《十俠》。下一步也許我寫個科幻題材的作品,讓自己的寫作保持創造的快樂,不重復自我。
舒晉瑜:16歲發表作品,18歲出版第一部小說集并被武漢大學破格錄取,大學階段的教育對自己的人生有很大影響吧?
邱華棟:在大學期間我去拜訪原武大校長劉道玉先生,他的一席話對我有很大影響。他說,到大學來讀書最重要的是自我發現,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是最關鍵的,不要期待老師給你多大引領。一定要樹立目標,持之以恒地頑強奮斗,成就你自己,這是教育的根本。那時候我就明白,想要成為好作家,最重要的就是志存高遠,要多讀書,想盡辦法積累生活、積累知識、積累經驗。從那以后我的目標從來沒有變過,而且幸運的是,我的愛好和職業完美結合了。寫作40年,我嘗試過十多種文體: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文學隨筆、評論(包括電影評論、建筑評論)、詩歌、小劇本、非虛構作品……文體龐雜。
武大給我的第二大影響是文史哲的打通。很多年以后我覺得當時無論是聽鄧曉芒先生講康德,還是聽易中天先生講中西比較美學,或者去旁聽考古系的課,對我都有一定的作用。《空城紀》的結構跟讀《史記》有一定關系。上大學的時候老師就督促我們讀《史記》,說《史記》是文學作品,學中文的應該讀一讀。現在看《史記》就是很有意思的一部結構主義作品——我上大學的時候好老師比較多,幾句話就能點醒。
舒晉瑜:同樣的教育環境培養出不同的學生,這和個人的悟性和天賦有關,你特別善于吸納各方所長。
邱華棟: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曾經談到,他有一個創作計劃表,未來五年要寫什么,十年要寫什么。我也制定了寫作計劃,經常把靈機一動的構思寫到筆記本里。我也經常和作家們聊天,很多優秀的作家都給我啟發。創作到一定程度我們要問自己:一個作家到底要創造什么樣的文學世界?你的符號是什么?你的創作整體上是不是有文化的、文學的貢獻?現在碎片化的時代很難聚焦,想明白自己的目標,你才能有辨識度。
前段時間我到魯院講課,提到《德里克·沃爾科特詩集:1948—2013》。德里克·沃爾科特是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歲的時候出版第一本詩集,雖然寫得比較稚嫩,但已經顯現出文化的縱深和方向感,一看這株苗你就知道他未來會是一棵大樹。我想如果15歲時我讀到這本詩集,我的詩一定不是今天的樣子。
舒晉瑜:從16歲起就開始發表作品,你的寫作體裁寬泛,詩歌、小說、隨筆、評論幾乎無所不能。你覺得,這樣的多面手對于自己的創作有何益處?
邱華棟:寫詩讀詩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開會后寫,在飛機上寫,在外地賓館睡不著起來就寫。為什么?一是詩歌便捷短小,二是詩歌可以保持你對母語的警覺與敏感。其他文體的寫作是跟著興趣走的。比如,我還寫有電影研究《電影作者》、城市建筑隨筆《印象北京》、20世紀西方小說家評論《靜夜高頌》(三卷)等多部,都是跟著當時的興趣在走。
《空城紀》的靈感來自一只石榴
舒晉瑜:《空城紀》體現出詩性的語言風格。這部作品你經歷了長達30年的準備,動筆是出于怎樣的契機?
邱華棟:莫言、賈平凹、遲子建、畢飛宇……很多作家都有文學的故鄉,我沒有。我父母是河南人,我在新疆長大、在內地求學,沒有文學意義上的故鄉。小時候每天抬頭就能看到白雪皚皚的天山主峰,周圍就是沙漠、戈壁灘,風吹過來,一團團的駱駝刺在滾動,那種荒涼、開闊的成長環境對我的心靈世界有很大影響。多年來我一直想無論如何應該寫一本書獻給自己的出生地,但是怎么處理這種經驗和資源,我一直沒找到感覺。
我是一個“資料收集狂”,收集了許多關于西域歷史地理、文化宗教、民族生活方面的書籍,包括近代以來外國探險家在西域的考察,像斯文·赫定、斯坦因……我經常翻一翻。還讀了幾十位學者的相關著作,石云濤的《漢代外來文明研究》、還有榮新江、孟憲實的著作……我腦子里盤旋的素材和原料慢慢被激活。直到有一天我切開一個石榴,突然想到這石榴是當年張騫從安息國帶到長安的,我一下找到了《空城紀》的結構。石榴有六個子房,我就把整部小說分為六章:龜茲雙闋、高昌三書、尼雅四錦、樓蘭五疊、于闐六部、敦煌七窟,寫六座古城廢墟遺址的故事。
舒晉瑜:你曾經給這部書起名《流沙傳》,聽上去也不錯。
邱華棟:紀和傳都有時間感。這個題材其實始終在我腦子里不斷地變化。我最開始構思是想寫一個漢代背景下的小說,比如說有一個人跟著張騫出使西域,張騫被扣留了,但他一直走到羅馬,一路上遇到各種事情……后來一想這不是《西游記》嗎?我去過二十幾處古城遺址,這些廢墟不應該是一座空城,曾經有哪些人走動,他們的聲音、形象經常會在我腦子里浮現。當你積累了足夠多的材料,當你找到了恰當的結構以后,寫的過程是很愉快的。
舒晉瑜:但是《空城紀》跨度如此之大,七個洞窟橫跨一千多年的歷史,駕馭起來也有難度吧?能否舉例談談?
邱華棟:敦煌學已經成為全球顯學,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學術命題。寫敦煌的作家不少,學者更多,比較有名的我都看過,比如井上靖的《敦煌》、葉舟的《敦煌本紀》、陳繼明的《敦煌》……看得越多越感覺怎么寫敦煌對作家來說是巨大考驗。
敦煌七窟的選擇是有用意的。我多次去敦煌實地看過,家里也有很多關于敦煌的畫冊,一個窟一個窟地看過去,最開始挑了30個窟,覺得體量太大。我突然想起卡爾維諾的《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又名:《寒冬夜行人》),我讓國王、士兵、殺人犯等七個不同時代的個體命運跟具體的洞窟聯系起來。每個洞窟的壁畫都有一定的佛教寓意,也反射著現實的生活。比如“一個國王”寫的就是于闐國王死后回憶在敦煌的生活、到于闐的生活等等,這樣整個歷史就活了。幾個洞窟把1300年的敦煌史串起來,有代表性的石窟和歷史都融入其中了。
舒晉瑜:看了那么多相關的著作,寫的時候會不會有一種壓力?
邱華棟:恰恰給我提供了不一樣的思路。文學的創造性最重要,每個人的見識、修養和眼界不一樣,我們在處理同一個題材的時候也不會碰撞、不會沖突,相反,可以豐富讀者對敦煌這樣一個偉大寶庫的認識。以歷史文化遺產作為寫作對象,這是中國當代作家的使命,同時也體現著一個作家的能力。
歷史小說也是當代小說
舒晉瑜:一般長篇小說從頭到尾貫穿一個人物或事件,但《空城紀》采取了散點透視的方式。
邱華棟:我最開始對這種結構還有點狐疑,反復琢磨,覺得石榴籽式的結構是成立的:30個短篇構成6個中篇,散點透視又聚合為一部《空城紀》,仍是完整的一個石榴,但又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長篇小說。每一部分我都對涉及的歷史元素有所側重,比如龜茲最有名的是龜茲樂,我就寫細君公主的女兒弟史和龜茲王絳賓都喜歡音樂,他們到長安去學習音樂,把長安音樂帶到龜茲,回到龜茲后又把龜茲音樂帶到長安,反復交流。在寫龜茲雙闋的上闋時,我寫了解憂公主、細君公主和她的女兒弟史,還有統率幾萬兵馬的馮夫人。從漢武帝時期到漢宣帝時期,她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在西域影響很大,非常了不起,但是這些人物淹沒在歷史的長河里。細君公主遠嫁馬孫國,漢武帝曾經送給她一把琵琶,她想念中原的時候就彈琵琶寄托思鄉之情,有一首《悲愁歌》特別感人: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愿為黃鵠兮歸故鄉。
舒晉瑜:女性人物描寫在您三十多年的創作中還是有變化的。
邱華棟:早年寫小說時總覺得城市里物質女孩太多,有一些批判的眼光,實際上不是這樣,男性女性都一樣有物質需求。《空城紀》里的女性就不同了。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歷史文獻中的中國女性很少,傳記也少,李清照、魚玄機、薛濤……數不出多少。我的小說復原歷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實際上也是對當代女性主義的一種呼應。
舒晉瑜:那么如何處理虛與實、歷史和當下的關系呢?
邱華棟:小說里確實出現了只有在當代才能夠定位和辨識的一些符號。這么寫是為了符合當下的閱讀。歷史學家不能這么寫。小說不是歷史學的論文,就像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么歷史小說也是當代小說。當然小說家不可能完全復制還原當時的歷史境遇,只能進行創造性想象,用現代漢語的語調陳述。
舒晉瑜:小說的敘事視角在不斷變化,尤其讓物在說話,引人入勝。“于闐六部”中的錢幣部,有一枚漢佉二體錢(身上有兩種文字,一面是漢文,一面是佉盧文),學者對錢幣反復論證,年代、內容、適用范圍……信息含量很大,故事也很動人。
邱華棟:第一人稱“我”在小說里不斷變化,從人到物有無數個化身,比如在“龜茲雙闋”中上闋是用第一人稱,到了下闋就變成了白龜茲的王子白明月,在外篇就變成了當代人李剛。越往后越“神乎”:到“于闐六部”里,簡牘敘事是“我”,錢幣敘事、雕塑敘事也是“我”……“我”作為一個敘述主體是有限的,但同時它又特別飽滿,我自己投入其中,容易讓讀者有一種代入感。
寫作的時候,錢幣敘事首先打動了我。當時于闐國遭遇大旱,按照他們的規矩,要向上天貢獻人祭,還必須是尉遲氏王族才可以。沒有人站出來自愿作為祭品。這時候有一個已經出家的王子說我愿意還俗,這樣就可以獻祭。小說里的獻祭儀式也是學者研究過的,要喝一種液體叫蘇摩汁,產生幻覺后就不太疼了。然后王子就咬著這枚錢幣,錢幣感受到蘇摩汁的香氣和口腔的溫暖;王子的生命開始燃燒,錢幣的身體開始變得灼熱,被一股火焰吞沒,感覺到王子華美的靈魂就像是一股煙一樣緩緩騰空。王子用他的犧牲拯救于闐擺脫了災厄。
舒晉瑜:小說還涉及了很多典故,比如中原和西域的“三絕三通”、傅介子刺殺樓蘭王的歷史事件,在小說中都通過合理想象呈現得非常清楚。
邱華棟:小說里班超的投筆從戎、漢代的“三絕三通”,還有李隆基給楊玉環排演霓裳羽衣舞的過程,我仔細閱讀相關的唐代文化,很多歷史故事在史書中也就一句話。所以既不能寫得太實,也不能寫得很虛。怎么讓班超和班勇父子以對話的方式呈現歷史?怎么體現父子復雜的情感關系?班勇的母親是誰?我認為是龜茲王族的一個女兒,那么她和班超怎么相見?我去過喀什和田,在疏勒見過一些古老的杏樹,又粗又大。春天杏花開的時候,古老的杏樹伸出一條很粗的橫枝,上面站了兩三個漂亮小姑娘,杏花在她們的晃動下飄然落下,在我心中留下了特別美好的印象。班超和姑娘(小說中就是疏勒王親弟弟的女兒西仁月)在杏樹下第一次相遇了……這就是我的合理想象。那些情景特別有質感,來自我對新疆的觀察和經驗,那些語言也只有在新疆生活過的人才會有。
奇妙的想象:一匹穿越千年的馬
舒晉瑜:小說里有很多神奇的呼應,比如敦煌七窟的第七窟和第一窟的故事剛好呼應。細君公主的漢琵琶一直流傳到了當代,2020年被“我”在新疆木合塔爾的作坊后院里發現了。
邱華棟:為這事我也咨詢了一些朋友,他們認為漢琵琶在新疆流傳2000年是完全可能的。這種呼應我覺得挺有意思,有時候你就得創造一點小小的奇跡。
敦煌七窟的第一窟里寫了令狐安一定會出家,原因是樂尊(左亻右尊)和尚摸過他的頭,說:“你會繼承我的衣缽,今后你會出家為僧。等到有人讓你來敦煌千佛石窟找我,就是我的圓寂之時,也是你的出家之時。”果然過了20年,令狐安和趙娉婷結婚的時候,有一個和尚走來對他說“師父樂尊和尚派我來,讓我把缽交給你……”令孤安就跟他走了。趙娉婷后來找去,每天住在洞窟外面,希望丈夫回心轉意。再后來趙娉婷爬進洞窟,發現她的丈夫已經坐化為石頭禪者。
第七窟寫到主人公“我”喜歡的姑娘趙娉婷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我”想去看看她,趙娉婷就帶“我”進了285窟,在285窟里“我”入定了,跟洪辯和尚對話,包括王道士如何發現藏經洞,日本敦煌學家藤枝晃的《敦煌寫本概述》是如何寫的,把伯希和、斯坦因、張大千、常書鴻和敦煌的交集捋了一遍。“我”一覺醒來后,就對趙娉婷說:“我想到敦煌研究院來和你一起工作,把自己的下半生獻給敦煌研究。”另外小說里有很多“剛”:吳剛、王剛、李剛、陳剛……其實是“金剛不壞之身”的一種隱喻,也是呼應著某種堅定的信念。
“于闐六部”中簡牘部一節,我讓漢簡、直體佉盧文陀羅語木簡和于闐語木牘講了一晚上的故事,講龜茲女賊的故事,講生命死亡的故事,最神奇的是其中于闐語木牘在哭泣,其他簡牘問你為什么哭呢?然后簡牘就開始講亨舉的故事……講到最后天亮了,他們又復歸原位。然后一個媽媽帶著叫亨舉的孩子來博物館,少年亨舉穿越了一千二百年,和古老的木牘對視。寫到這里我自己都覺得是神來之筆。也顯示了我們文化中千年不絕的相互呼應。
舒晉瑜:簡牘部一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博物館奇妙夜》——不管是士兵、學者,還有國王的敘述,你的寫作里都暗含著家國情懷。
邱華棟:1941年張大千來到莫高窟,在清理一個洞口的積沙時,忽然發現沙堆中有一個袋子。打開后滾出來一顆殘缺的頭顱骨,還有功勛證明和身份證明。這人原來是大唐軍驍騎尉張君義,在西域戰死后,他的遺骨最終回到故鄉。我覺得剛好呼應了沈從文的那句話:一個戰士,不是戰死沙場,便要回到故鄉。《空城紀》里的戰士不僅戰死沙場,最后也回到了故鄉。
舒晉瑜:閱讀的過程中,無時不感佩作家豐富的想象力和對細節的把控能力。比如《霓裳羽衣舞》中有個細節,演出結束后舞女們掉落在地上的珠玉和環佩,很有畫面感。
邱華棟:我也寫得挺興奮。當然要投入全部的情感、對整個史料的爬梳、辨識、取舍,確實有一定難度。比如關于尼雅四錦,很有名的一塊叫錦護臂,上面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五個字。發生了什么故事?錦帛為什么是在男人的左胳膊上裹著,他是什么人?我反反復復構思了幾個方案,考量了好長時間。但是一旦確定,寫起來就像創造游戲般的快樂。再比如《雕塑部:佛頭的微笑》,斯坦因他們挖出來的一個兩米多高的佛頭,佛頭從被挖出來的那一刻,見識過多少來來往往的人,我通過佛頭的眼光看世間,這么一來中西交流史中的人物都囊括其中了。
舒晉瑜:所以小說背后也隱含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觀念?
邱華棟:我圍繞六個古城遺址重新建立關于漢代和唐代的想象空間,所有這些內容都佐證了中華文明的特性,中國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在書寫歷史主人公的時候,我更側重于描繪人物內心的聲音,那些背景式的、脆薄的、窸窣的、噪鈍的、尖銳的聲音,讓位于鮮活的歷史人物,以此表達出他們在漢唐盛世中發出的元氣充沛的初始強音。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是作品要表達的主題。當然在小說中我們不能做簡單的政治圖解,我也不是為此而寫,是寫完以后發現《空城紀》完成了一種使命,確實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交流、交往、交融,以及文明之間的互相借鑒,能夠讓讀者更充分地了解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而且無論在藝術還是小說語言上,《空城紀》都是我深受世界現代文學影響的一個寫作,很容易被翻譯、被交流。小說一開始就是漢代的公主遠嫁烏孫和親;然后張騫出使西域,出現了花斑馬,這匹馬最后出現在北宋畫家李公麟的《五馬圖》里,叫滿川花,時間已經過了一千多年。諸如此類,小說的敘述在時間和空間上一直流動,這片土地在流動中變得更加豐沛。
石榴籽結構適應碎片化閱讀
舒晉瑜 :關于創新,在你這里好像不是問題。
邱華棟:人類的文學藝術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游戲,一個是勞動。猿人在山洞里面教孩子唱歌畫畫,就是一種游戲。游戲是文學藝術的一個來源之一,所以說我們作家要有創造性游戲的能力。
當然好作品還是得經過多年的孕育和積累。最近幾年我出版的《北京傳》《現代小說佳作100部》和《空城紀》都有30年以上的積累。有一些作家跟我講,怎么寫都不如經典。有個觀念叫“遠香近臭”,但凡100年前都是香的,有些研究古代文學的看不起研究現代文學的,研究現代文學的看不起研究當代文學的……“遠香近臭”就是一個自然的形態,但是我們創造著的此刻的個體生命是無法復制的,你觀察到的一切都是有價值的,那么你就寫個體生命的這種獨特性。至于能不能經得起時間的淘洗和檢驗,那是以后的事情,但你首先要有信心。
舒晉瑜:出版之后緊接著面臨的問題是,多元化的網絡時代,該如何有效閱讀。關于《空城紀》你有什么建議嗎?
邱華棟:我最開始想寫成七卷本,寫成七卷本誰看呢?現在是碎片化的時代。我采取石榴籽式的結構也有這個考慮。這部長篇應該怎么讀?我覺得可以有三種讀法:第一種讀法就是從頭開始讀。第二種讀法是先看目錄,挑選感興趣的內容,比如說你對樓蘭感興趣,看樓蘭就行了,樓蘭一疊、二疊……實際上就是時間和歲月的疊加;如果你對敦煌感興趣,就讀最后一部分;如果你僅僅對我寫了一部什么樣的小說感興趣,讀后記就可以了。第三種讀法,可以隨手把這本書翻開,就從那一頁開始讀其中的一節,把它當成短篇,相當于剝開石榴吃了一把籽。簡而言之,讀《空城紀》跟吃石榴的道理一樣,第一種吃法是直接啃;第二種吃法是把它掰開,選擇其中一部分子房;第三種就是嘗嘗,撥拉十幾個籽吃。這樣的結構其實適應了今天碎片化的閱讀時代。
舒晉瑜:看完整部作品后,確實感覺空城不空,所有的人物都撲面而來,非常生動鮮活。你是不是也覺得達到了理想狀態?
邱華棟:我覺得達到了。我的寫作完全是業余的,客觀上來講寫作是很受限的。曾有人質疑說這人寫過什么代表作?當代作家寫出代表作要經過時間的檢驗。那么現在我覺得有幾部作品可以拿得出手了:《北京傳》《現代小說佳作100部》和《空城紀》。前兩年《北京傳》出版,朋友說你已經有代表作了,我說還不算,我給自己打70分。《北京傳》是大眾讀物,如果說有價值,主要在于記錄當代。《空城紀》是個藝術品,一方面動用了我的出生地經驗,另一方面集合了我三四十年的閱讀和寫作經驗,還有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像是吸取了很多精華長成的一棵靈芝,最終凝結成《空城紀》,我還是挺滿意的。
舒晉瑜:這也和作家的天賦有關。
邱華棟:首先你要確立當一個更好的作家,有天賦也必須要勤奮。外部環境對文學也產生挑戰。傳媒在變化,整個時代在變化,文學的地位也在變化,起起伏伏。但是文學畢竟還是人類精神生活最重要的一個領域。文學體現著一個國家基本的人文精神,體現著人類的最高精神追求,有一份光榮在其中,文學事業還是值得付出的。
我對詩歌心存敬畏
舒晉瑜:練武術的人都知道一句話:“一寸長,一寸強,一寸短,一寸險”,說的是長有長的特點、好處,短有短的優勢和長處。既有過曾在武術隊訓練六年的體驗,又在文學戰場上南征北戰四十年,你作為年輕的“老作家”自然知道短篇“險”,亦知道長篇之道。你的城市題材小說也被同道看好,認為你作為“城市闖入者”,已成為都市文學新的代言人。作為新生代作家群體中的佼佼者,你創作伊始就把目光投向日益豐沛的城市生活,捕捉和描摹現代都市的生存景觀,著墨于“新的邊緣群體與都市新人類”,體現出作家對城市的獨特理解與深刻把握。正如莫言所說,“他是距離都市現實最近的作家”。你的枕邊書有哪些?
邱華棟:枕邊書不斷在變化,我喜歡同時閱讀好幾本書,哪本書讀得快就先讀完哪一本。床頭柜上總是放著二三十本書。純粹的枕邊書對于我并不存在。
不過,有一類書是我經常翻閱的,那就是書目類的圖書,或者是一些關于書的書。比如,我18歲的時候讀到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現代主義代表作100種/現代小說佳作99種提要》,是英國作家安·伯吉斯參與編寫的,這個作家寫過小說《發條橙》,從此,我就喜歡上了閱讀書目類書籍。再比如,法國人皮沃先生編寫的《理想藏書》,最早由余中先翻譯過來,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我翻了好多遍。前幾年,余中先和女兒一起又增訂了新版。我又翻閱了好幾遍。最近,在翻閱《501位文學大師》《有生之年一定要讀的1001本書》《東大教授世界文學講義》(5冊)等書,涉及到大量世界文學作品。我讀這類書,潛意識里是一直在把中國文學放到世界文學的視域里進行比較和衡量,因為,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舒晉瑜:你的文學起點很高,是否與童年時期的閱讀有關?
邱華棟:有關系呀!我小學五年級就讀了《紅樓夢》。看不懂也讀了,不過,我在初中的時候通過很多文學雜志,讀了很多當代作家寫當代生活的小說,這是我開始寫作的最初動力。
舒晉瑜:你在大學時期就出版小說集《不要驚醒死者》和詩集《從火到水》,獲得武大“紀念聞一多文學獎”“湖北省大學生科研成果創作”一等獎等。你現在還寫詩嗎?你最喜歡的詩人是誰?
邱華棟:一直在寫,從1990年到現在我已出版了6本詩集,今年出版了詩集《編織藍色星球的大海》,不過收錄的都是舊作。我對詩歌心存敬畏,詩是語言中的黃金,是純粹和高級的文學體裁。更多的時候我寧愿做一個詩歌的閱讀者和愛好者。寫出好詩太難了。就我個人的趣味,我喜歡埃利蒂斯、聶魯達、帕斯、艾青等現代詩人的作品,寬闊、大氣、清澈、豐富、闊朗。當然,我喜歡的詩人太多了,家里有四個書柜,裝滿了古今中外的詩人詩集,可能至少有三四千種。
舒晉瑜:為什么如此看重詩歌?
邱華棟:我把讀詩當作錘煉語言的方式,詩歌是語言的閃電,詩歌是語言的黃金,必須要閱讀詩歌,才能保持對漢語的敏感,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習慣。有時候覺得自己的語感不太好,就讀一讀詩,讀一讀先秦散文,再找找古代漢語的感覺,詩歌閱讀還是挺重要的。
舒晉瑜:熟悉的朋友都知道你“文武雙全”,既作詩文也習武術,并先后出版《刺客》《十俠》。你一定也喜歡武俠小說吧?寫好武俠小說最重要的是什么?
邱華棟:我從初中開始,在業余體校練了幾年武術,也迷過金庸、古龍、梁羽生的武俠小說。但我知道,武俠小說在現代科技社會肯定是要衰落的。因為,那是冷兵器時代的傳奇。我在2020年出版了武俠短篇小說集《十俠》,其實就是在梳理俠的精神在中國歷史中的流變。我覺得徐皓峰是當代武俠文學的新發展。他更多地寫到了近代武師們的實戰和技藝,而這才是現代體育精神之下的搏擊精神體現。
舒晉瑜:多年前你曾出版《挑燈看劍》,所涉及的書籍與話題都是閱讀熱點,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等。以你的閱讀分析,諾獎得主和他們的作品有沒有共同的特點?
邱華棟:不可否認,諾貝爾文學獎是當今世界影響最大的文學獎。但他們的視線還是從歐洲來看世界的,有歐洲中心論的潛在心理在起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獲獎者變得全球化,很多邊緣國家和地區的作家獲獎。其實作家存在的價值就是其差異性和獨特性,每個好作家都是獨特的。
當然了,這些獲獎作家最大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很勤奮,平均每人都有二三十種著作,都把文學創造和寫出杰作作為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標。近些年,我不怎么關注這個獎了。因為我喜歡的一些大作家,像是卡洛斯·富恩特斯、翁貝托·埃科、阿莫斯·奧茲接連去世,再也沒機會獲獎了,這個獎錯過的大作家也有很多很多。
每個好作家都是獨一無二的
舒晉瑜:《小說家說小說家》刻畫了王蒙、劉心武、賈平凹、莫言、余華、劉震云等30位當代小說家的文學肖像。寫當代的作家,你會有什么顧慮嗎?既是朋友、同行,又是你的評論對象,你覺得這種關系是否更有助于深入了解他們的作品和內心世界?寫的時候是否有可能自動屏蔽掉缺點?
邱華棟:我當了很多年的編輯,一直就在當代文學生產的現場,這些當代作家是我平時接觸的師長、同行和朋友,所以,我寫起他們來駕輕就熟,沒有任何顧慮,相反,我還有向這些作家致敬的心態。要知道,小說家都是創造一個個獨特世界的人,每個好作家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的艱難跋涉,我是最能體會的。
舒晉瑜:你對于外國文學的涉獵與閱讀在當代作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社區人》的創作就融會了對約翰·厄普代克等人作品的學習和感悟。那么你覺得,作為60年代末的青年作家,與5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比如莫言、韓少功、閻連科等相比,有哪些優劣?他們當年熱衷于外國文學的學習最終似乎又回到了傳統,你這么認為嗎?
邱華棟:傳統本來就在我身上。我是讀四大名著、唐詩宋詞,聽奶奶講故事和評書長大的,傳統從來都在血液里。我現在依舊熱衷外國文學,這主要在于你要隨時找到鏡子來看你自己。漢語小說最近三十年的發展特別巨大,但是,從寫作技巧、價值觀、容量、深度上,還沒有做到當年拉丁美洲文學反過來影響歐洲美國文學的地步。所以,持續地向外國文學學習,是一個作家必需的功課。你小學沒畢業,就宣布回歸傳統了,那怎么行?當然,對于一些中國作家,比如莫言,我想也就是那么策略性地說說,人家天天在家里研究全世界的同行呢,可不能狹義地解讀。假如簡單來比喻的話,也許莫言、閻連科、韓少功他們是威廉·福克納、加西亞·馬爾克斯和胡安·魯爾弗,我和李洱、張者、王剛等人,可能會成為約翰·厄普代克、索爾·貝婁、菲利普·羅斯那樣的作家。
舒晉瑜:你本人也是小說家,博覽群書又閱人無數,高屋建瓴是否有助于你的創作?
邱華棟:隨著年歲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加之不斷的閱讀,這非常有助于我的寫作。也許我正在進入一生中能寫出最好作品的時期,我得把握住這個階段。
舒晉瑜:你有一篇文章《書越讀越少》,能否具體談談你的理解?
邱華棟:我的意思是,隨著大量的閱讀,會建立一個閱讀的標準。在這個標準之上的書會變少。就像是《史記》《論語》,千百年來有大量關于它們的解讀、闡釋、白話翻譯等著作,一旦你的閱讀水準建立,你就直接去閱讀它們的原文,后來衍生出來的大量讀物都可以不用看。這樣的話,書是越讀越少了。
舒晉瑜:你有什么樣的閱讀習慣?
邱華棟:現在,由于平時工作忙,我的閱讀都是以碎片時間來進行的。把碎片時間利用好,就能獲得一個完整的閱讀結果。另外,讀書也有方法,有的書精讀,有的書泛讀,有的書瀏覽,有的書買來暫時不讀。這樣一年下來,我好像能閱讀一千種書。
舒晉瑜:你也是文壇有名的藏書家,現在藏書量多少?有什么珍本?是不是多數藏書后都有動人的故事?
邱華棟:我大約有三四萬冊書,放在超過40個書柜里。我不覺得我是藏書家,這些書都是我曾萌發興趣翻讀的書。也沒有什么珍本,也沒有什么藏書故事。不過,我專門搜集了《金瓶梅》和《紅樓夢》的各種影印本和翻譯本,對這兩部明清小說杰作的印刷、傳播很感興趣,也和其他藏書家合寫了《金瓶梅版本圖鑒》和《紅樓夢版本圖說》這兩本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些讀者很喜歡。
舒晉瑜:藏書的標準是什么?會定期清理藏書嗎?
邱華棟:我藏書的標準,就是我自己感興趣的書。而我感興趣的書特別蕪雜,也很難形容。比如,我最近買了一冊《人體解剖與手術圖譜》,是漢英法拉對照本。我在搬家的時候才整理書,書一般按照作者來擺放,這樣就很容易找到要找的書。馬未都曾經給我說過“百年無廢紙”,這使得我很難扔掉任何一本書。所以,我常有一種歡喜,叫做“聚書的快樂”。
舒晉瑜:有什么不為人知的閱讀趣味愿意分享一下嗎?
邱華棟:我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打開書,聞一聞到手的書的味道。書香這個詞可不是假的,書的味道也是各種各樣的,無論是線裝還是印刷體的書,總體說起來是一種香味。不信,你也聞一聞?這可能是我的不為人知的“閱讀趣味”了。
舒晉瑜: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你會選哪三本?
邱華棟:嗯,我想想,要是只帶文學書的話,我覺得我得帶上《詩經》《紅樓夢》和《尤利西斯》。
西方文學已經祛魅了
舒晉瑜:《現代小說佳作100部》中的100部是怎么確定的?
邱華棟:還是跟閱讀經驗有關。我讀了三四十年的世界文學——我不喜歡用外國文學這個詞,外國文學和中國文學有可能形成對立,而世界文學包含了中國文學,所以書里也收錄了中國作家莫言、中國臺灣作家李永平,還有中國香港作家董啟章等等。我在讀世界文學作家作品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已經形成了一個判斷力:特別是和當代同齡的西方作家相比,中國作家是很棒的。《紐約時報》評出“21世紀最佳書籍100本”,我一看里面沒有中國小說就很生氣,起碼應該放上5~10部中國作家的作品。當然它主要評選以英語為主的作品,稍微兼顧一點其它語種。
舒晉瑜:你認為哪些作品可以收入?這么判斷的依據是什么?
邱華棟:在我這樣的資深讀者看來,西方文學已經祛魅了,20世紀80年代我們讀到馬爾克斯、普魯斯特恨不得頂禮膜拜,這種心態現在沒有了,既不仰視也不俯視,我以平視的眼光看待世界文學,這種判斷力就在于我閱讀了大量的作品后形成了一條文學水平的經線。
舒晉瑜:從收入書中的作品構成中,讀者大致可以發現文學在地理意義上的轉變。那么這種寫作方式是如何確立的?
邱華棟:我寫這本書有一個潛在的想法,就是體現時間和空間的變化。我后來觀察,無論是二戰以后還是各種文學爆炸現象,比如說福克納的寫法跟尤利西斯、跟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意識流、跟普魯斯特都是有聯系的。福克納影響了馬爾克斯,馬爾克斯影響了莫言,莫言影響更年輕的作家,比如我。這種影響是連續性的。
我的電腦里積累了很多作家的讀書隨筆和書評,成千上萬冊圖書讓我擺脫了某種憂慮,我逐漸萌發了寫一本《現代小說佳作 100 部》的念頭。我邊轉動地球儀,邊想著活躍在地球表面上的各國各種語言的作家,先確定了大約300位作家和他們的小說代表作,然后做刪減,范圍逐漸縮小到100位作家的100部小說。當然,小說世界中的生命都互有輻射,實際上,這本書涉及的作品有好幾百部。我割舍了不少自己喜歡的作家作品,重點選擇了一些在100年小說發展史上起到作用和影響力的作家。當然不是說獲諾貝爾文學獎或者獲布克獎就是最好的,100個人里70%都沒獲過諾貝爾文學獎。
舒晉瑜:優秀的作品和獲獎并不是完全畫等號。你剛才提到這部作品體現“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能具體談談嗎?
邱華棟:時間是100年,空間的變化是,第一部分是歐洲作家,歐洲作家最重要的是從1922年到1945年前后有一批優秀的、最有創造力作家出現;第二部分是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作家的作品;第三部分是亞洲、非洲作家的作品。1945年到1965年,是北美文學的天下,美國從麥卡錫時代到了1960年代,黑人文學、猶太文學、女性文學、科幻文學……從1965年到1980年前后拉美文學爆炸,所以地理上也在轉移,在《現代小說佳作100部》里顯示從歐洲到北美,從北美到南美,80年代以后到2000年左右,亞洲和非洲作家又崛起了,這批作家有的叫“無國界作家”,有的叫“離散作家”,有的原來生活在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后來通過文學進行了反擊。比如說薩爾曼·拉什迪、石黑一雄、奈保爾……這本書描繪了文學創新點在空間地理的轉移。
不同語言的文學是一條條大河
舒晉瑜:《現代小說佳作100部》一開始選了300部,后來減少到100部,應該也是基于你的閱讀經線?而且最關鍵的一點,你確立了1922年這個時間點。
邱華棟:1922年是現代小說的一個起點,有人把現代文學的起源追到波德萊爾《惡之花》的出版,我更贊同埃茲拉·龐德的判斷,現代文學的元年應該在1922年,1922年的2月2日,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出版是決定性的,同樣那一年出版了艾略特的《荒原》、馬塞爾·普魯斯特的《去斯萬家那邊》(第一卷)。同樣這一年,卡夫卡在寫他的長篇小說《城堡》,弗吉尼亞·伍爾夫完成了長篇小說《雅各的房間:鬧鬼的屋子及其他》,勞倫斯寫完了《長篇袋鼠》,福斯特寫完了《印度之行》,勞倫斯的《智慧的七大支柱》也是那年出版的,魯迅連載完了他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隨口一說,我能說出30部以上的1922年出現的重要作品,每個月都有新作品。所以說1922年是現代小說的元年,之后文學發生巨大變化,而此前是19世紀的寫法,包括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是19世紀的家族史小說,到了《浮士德博士》就有了心理小說的深度。
舒晉瑜:你的全球視野和開闊的寫作格局在這本書里具有充分的體現。分卷好像沒有完全按照作家的國籍,也不按照語種或年齡來編排?
邱華棟:是按照我的寫作順序進行排列的。進入21世紀后,作家作品的選擇上我體現了在地性,比如理查德·弗蘭納根是澳大利亞人,他寫過《深入北方的小路》《顧爾德的釣魚書》《河流引路人之死》,最近又出了本新書《第七封信》,他寫的塔斯馬尼亞島帶給我們地方性的陌生經驗,也包含著現代的眼光。法國的勒·克萊齊奧跑到非洲南部的小島,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跑到西南邊城,挪威作家克瑙斯高在斯科納鄉間……他們的筆下很多作品題材都和祖國原鄉故土密切相關。這樣的分卷,更能體現出21世紀世界文學的“小說地理學”全球性的新文學景觀。
舒晉瑜:在閱讀書寫的過程中,你發現當代有經典嗎?寫作中是不是也有引領讀者閱讀的意味?
邱華棟:克瑙斯高《我的奮斗》(6卷本)就是。我已經讀了3卷,很厚,但是很好讀。如果說不同語言的文學是一條條大河,那么,這些小說就是文學之河邊醒目的航標,顯示了里程和方位,指引后來者能找到自己的目標。航標的出現對于行路之人是十分親切的,就像當年 19 歲的我從書店捧回一本《提要》的心情。當時我還是武漢大學的本科生,學校郵局旁一座綠樹掩映的山坡上有一家書店,就在那里,我買到了一本書:《現代主義代表作 100 種 /現代小說佳作 99 種提要》。大學期間我就按圖索驥,讀到了書中提及且已被譯成中文的小說。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也注意到文風的樸實,希望在每一篇三五千字的篇幅之內,把這個作家的基本生平信息說清楚,把他的代表作的主要內容大致勾勒出來。
閱讀什么樣的文學,就是召喚什么樣的心靈
舒晉瑜:《現代小說佳作100部》這部作品原來的名字叫《航標:現代小說佳作100部》?
邱華棟:就是說這些作家作品起到了航標的作用,但是后來我把“航標”刪掉了。寫作這本書,我的確有一個基本的設定,每本小說都要有簡體中文譯本,這樣讀者就能找到原著去閱讀。其中唯獨印度作家維克拉姆·賽斯的《如意郎君》不是全譯本。這部小說英文版厚達1400多頁,由劉凱芳先生翻譯的一部分發表在《世界文學》雜志2001年第1期上,全譯本我尚未見到。但我特別欣賞這本書,它有資格排進這個書目里。
舒晉瑜:這些作家里有沒有情感上比較親近的?
邱華棟:我喜歡意大利的兩個作家:卡爾維諾和翁貝·托埃克。卡爾維諾的每一本書都是獨特的,他的想象力特別輕盈,讓我們脫離了沉重的大地,還體現了文學想象的甜蜜。
翁貝·托埃克在社科院開講座時,我拿本書在大堂找他簽名,他問你是什么人?我當時是記者,他說我的讀者呢?我說我也是讀者。他既是一個學者,同時也是一個小說家,他的《玫瑰的名字》把對中世紀的研究裝到偵探小說的外殼里,那本書在全球賣了四千萬冊。
舒晉瑜:無論是《空城紀》還是《現代小說佳作100部》,其實你的很多作品都體現了百科全書式的特點,這樣的風格是如何形成的?
邱華棟:我受翁貝·托埃克影響很大,一直把他視為榜樣,但我永遠成不了他。他是個大學者,研究領域很廣,家里有50萬冊的藏書。我手機里有一個關于翁貝·托埃克的視頻,他帶著一個電視臺記者跟著他拍攝書庫,像迷宮一樣地走了十幾分鐘。
有兩類作家我特喜歡,一類是想象力發達,像薩爾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寫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以后孩子們的不同命運,有一些細節很生動。比如說寫到有一個從英國回來的男醫生去看女病人,兩個女仆用床單罩著女病人,需要看身體的哪部分,就挖個洞移到什么地方。醫生并沒看到病人的臉,就喜歡上她了,我覺得寫得特別好。那部小說我買了三本放家里。
還有像類似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我認為非常重要,你無法回避它。因為抑郁癥自殺的美國當代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寫過一部1300頁的長篇叫《無盡的玩笑》,是美國后現代派文學在21世紀的代表作,我也收到書里了,這樣的書讀著挺累,沒有太多的快樂,但是很智慧。這樣的作品有文學航標的作用。
再比如美國作家理查德·鮑爾斯,他寫了一系列科技小說,把科技前沿和人類處境結合起來,比如《回聲制造者》《上層林冠》。為什么我選擇這些作家?是因為我們需要通過看待他們周邊的環境和角度來琢磨我們自己的寫作。一個有心的作家,一定會從中受到啟發,找到自己的道路。
舒晉瑜:那么在梳理過程中,有沒有發現優秀的作家作品共同之處?
邱華棟:好小說的特點恰恰在于千差萬別。牡丹是這種開法,梅花是那種開法,花的大小、味道、形態不一樣,它們有不同的美。也許我不能把小說標準說得很明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但它確實存在著水平的經線。每個作家都在時代的時間和空間中發現和創造屬于自己的文學世界。
舒晉瑜:大量的閱讀給您的寫作帶來什么?
邱華棟:簡而言之,一個是寫作技法,比如結構、比如說對人性的深度理解。弗洛伊德這樣的精神分析學家影響了意識流作家的產生,那么在傳統的寫實小說里,看不到意識流對更復雜的人性的表現,要通過現代小說才能體會到;其次是這些作家怎么看待自己的傳統。詹姆斯·喬伊斯是從英語文化和文學中成長起來的,他怎么看待愛爾蘭文化、西歐文化以及希臘、羅馬西方文化的根源?我也常常問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怎么看待我們的漢唐文化、怎么看待我們的諸子時代?從傳統文化中學習,怎么創造出新的作品而不是單純地模仿?我們在中國的語境里能不能寫出好作品,作品能不能在中西方文學中互相溝通?比如說福克納的《喧嘩也騷動》寫的是美國南方的現實和歷史,但是我們一看就懂。所以這里面對于怎樣處理自己民族的文化經驗有很多啟發。只有在文明借鑒和文學借鑒中,我們才有更多的思路。
【訪談者簡介】舒晉瑜,供職于光明日報報業集團中華讀書報社。著有《中國女性作家訪談錄》《風骨:當代學人的追憶與思索》《深度對話魯獎作家》《深度對話茅獎作家》《以筆為旗:與軍旅作家對話》《說吧,從頭說起——舒晉瑜文學訪談錄》等。曾獲中國第六屆報人散文獎、第四屆豐子愷散文獎。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