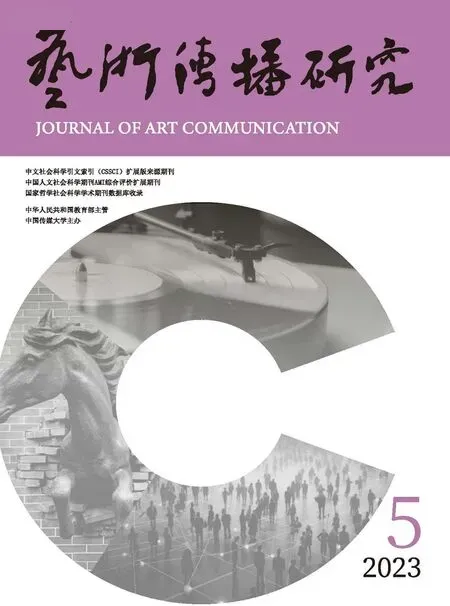晚清海外文學經典在華傳播策略及啟示
——以《巴黎茶花女遺事》為例
張雪花
在西方,“經典”(classics)一詞來源于拉丁文,是指知識領域內具有典范性、權威性,對本國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價值的著作。哈羅德·布魯姆認為,經典是指出現于敏感、感傷和崇高的文學年代并受到認可的作家作品;(1)[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卡爾維諾將產生了某些特殊影響的作品視為經典;(2)[意]伊塔洛·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典》,黃燦然、李桂蜜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博爾赫斯則將經典視為一個持續的過程。(3)[阿根廷]豪·路·博爾赫斯:《作家們的作家》,倪華迪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頁。總之,文藝經典是普遍的藝術法則和生產、傳播、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凝聚著時代的文化成果及其對現實生活的價值,能夠集中反映文化的本質和價值理想,蘊含著豐富的社會與歷史意義。在本文的語境中,海外文學經典是指自國外傳入中國并引起過重要反響的漢譯世界文學作品。19世紀中后期,西方用堅船利炮敲開了中國的大門,與之相隨的是從器物層到制度層再到文化層的全面輸入,當然也包括文學藝術在內。在此背景下,1899年,林紓譯《巴黎茶花女遺事》的問世不僅“揭開了中國翻譯文學的新紀元”(4)孟昭毅、李載道主編《中國翻譯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頁。,也拉開了“林譯小說”的序幕,影響了其后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故成為晚清時期獨特的文化現象。學界對這一現象的研究成果豐碩,涉及梳理、挖掘該書版本和出版方面的資料,總結譯者的翻譯策略,研究其文學成就和影響等方面。在林譯《巴黎茶花女遺事》生成為一種文學經典的過程中,其文本價值因素雖然占據了主要地位,但圍繞該書所進行的各種傳播活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些傳播活動擴大了該書的社會接受范圍,取得了良好的銷售成績,并催生了“茶花女”熱潮的出現,推進了其在中國的經典化進程。本研究在挖掘和梳理相關文獻的基礎上,試圖揭示該書在晚清時期的傳播策略,以進一步理解海外文學藝術作品在中國的經典化發展。研究發現,包括“西國之《紅樓夢》”的言情小說定位、多層面廣告宣傳、立體化搭建的傳播網絡等在內的傳播策略,對該書在中國文學史上經典地位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這對中國經典的海外傳播亦具有借鑒價值。
一、晚清時期《巴黎茶花女遺事》在華出版傳播概況
1848年,法國作家亞歷山大·小仲馬(Alexandre Dumas,fils)出版了《茶花女》一書,其后這一文學經典不斷被改編,體裁涉及話劇、歌劇、芭蕾舞劇、連環漫畫乃至動畫,并被翻譯成英語、西班牙語、俄語、德語、匈牙利語等。1899年,該書被林紓翻譯為《巴黎茶花女遺事》在中國出版,成為中國近代第一部極具影響力的翻譯小說,對小說在中國文學和社會中地位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5)阿英:《關于〈巴黎茶花女遺事〉》,《世界文學》1961年第10期。據統計,其在晚清時期的版本主要有福州畏廬本、素隱書屋本、玉情瑤怨館校刻本、文明書局本、廣智書局本等。(6)陳瑜:《情之嬗變:清末民初〈茶花女〉在中國的翻譯與改寫》,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頁。
福州畏廬本(1899年)為其最早版本,是由私人資助的雕版印刷“原板”,沿用了傳統的出版方式。這種“傳統”一方面體現在由林紓好友魏瀚私人出資,交匠人吳玉田刻梓出版的方式;另一方面體現在版式、裝幀、紙張等諸方面。此版為袖珍本,高18厘米,寬11厘米;全書120頁,每半頁9行,每行20字;版心鐫有“巴黎茶花女遺事”,下注頁數。(7)參見張旭、車樹昇編著《林紓年譜長編》,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頁。從裝幀設計來看,該版為毛邊紙本,字跡清晰,封面為白紙書簽,扉頁淺綠色,印有林紓手書“巴黎茶花女遺事 冷紅生自署”,封底有林紓自寫的“己亥正月 板藏畏廬”字樣,卷末刻有“福州吳玉田鐫字”。據稱該版當時僅印100部,流傳甚稀,但這已為該譯作以后的傳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素隱書屋本(1899年)為鉛印本,即昌言報館本、汪康年本。《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快速、大批量地傳播始于該本。造就這一傳播效應的主要因素在于:汪康年通過林紓友人高夢旦獲得版權后,使用較為先進的印刷技術,以最快的速度批量生產該書,還持續性地在報刊上推出廣告促銷,長達數天,綜合采用多種傳播方式,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目前,在現有資料中無法獲知該版確切的印刷數量,但據學者考證,當在數千本以上,是晚清時期最為暢銷的翻譯小說。(8)張天星:《汪康年鉛印林譯〈茶花女〉考論》,《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此外,該書封面署“巴黎茶花女遺事 書經存案 翻刻必究”字樣,背頁印“己亥夏素隱書屋 托昌言報館印”兩行豎字,是近代版權意識的較早體現。(9)潘建國:《物質技術視閾中的文學景觀——近代出版與小說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頁。
玉情瑤怨館本(1901年)為木刻本,刻工尤精,素樸古雅,頗受部分傳統人士及收藏家喜愛。很長一段時間里,學界對該本的主要出版情況無由得知:阿英較早提及這一點,認為該本“究為誰氏所刊,現在還未能查清”(10)阿英:《關于〈巴黎茶花女遺事〉》,《世界文學》1961年第10期。;張靜廬則以該本為汪康年本(11)參見潘建國:《物質技術視閾中的文學景觀——近代出版與小說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頁。,鄭逸梅持相同看法(12)同上。,皆未有具體佐證;陳寅恪指其為湖南譚氏家刻(13)參見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6頁。,然無其細節。直到謝冬榮以新見私人章印等文獻考證該刊本主持者為湘人譚延闿,玉情瑤怨館系其藏書之所(14)謝冬榮:《文津書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年版,第102頁。,才證明了陳寅恪的論斷,終為此本定論。
文明書局本目前有1903年版和1906年版兩種。文明書局以“慎選東西各國有用之書編譯印行,以睿民智而端學術”為創辦宗旨,是中國最早引進并實施珂羅版印刷的書局,尤擅圖像印刷。《茶花女遺事》恰為“西國有用之書”,契合了該書局的選題需求。同時,該書局版本也具有明顯的自身特色——1906年版新附亞猛、馬克的肖像照與《茶花女小傳》,此前并無。這個版本的肖像在長相、著裝、氣質等方面充滿異域色彩,生動逼真,從視覺上印證了人物的真實性;小傳概述茶花女的一生事跡,語言簡潔且明確指出其安葬之地,給人以“故事即真事”的感覺,增強了傳播效果。陳寅恪年輕時游歷海外,曾專程去巴黎拜訪茶花女墓地并寫詩記之,(15)參見謝冬榮:《文津書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年版,第102頁。可見該本影響之大。
廣智書局本(1903年)為鉛印本。該書局名稱取“廣為傳播智識”之意,以翻譯出版當時西方新學術、新思想著作為主。梁啟超作為書局的實際控制人,將翻譯小說(尤其是政治小說)視為開拓國民視野和構造救國救民政治理想的工具。《茶花女》作為法國文學名著,也被納入“傳播智識”的范圍,列為“小說新集”第一種。(16)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22頁。該本首冠小仲馬照片,次則林紓照片,內有插圖數幅,開本很小,利于收藏。(17)參見鄭逸梅:《蕓編指痕》,北方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頁。從傳播視角看,該本由維新派的書局出版,帶有較強的傳播新知識的目的。具體來看,該本對該書來源(作者、譯者)的強調,以及用照片、插圖增加閱讀趣味等做法,皆有利于向大眾普及外來文化。
總體來看,該書在晚清時期的出版經歷了從木刻本到鉛印本的變遷,體現出明顯的近代特征,即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渡性。經由多家民營書局采用當時先進的出版技術和推廣手段,該書催生了轟動一時的“茶花女”現象,并成為“林譯小說”和晚清翻譯文學的起點,對中國文學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起到了重要作用(18)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5頁。。更進一步說,晚清時期,以《巴黎茶花女遺事》為代表的翻譯文學,使中國文學開始納入現代世界文學譜系,成為“世界文學共同體”的組成部分。
二、晚清時期《巴黎茶花女遺事》在華傳播策略
《巴黎茶花女遺事》自1899年在華首次出版后,很快成為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的經典。該書“中國人見所未見,不脛走萬本”(19)陳衍:《林紓傳》,《國學專刊》1927年第1卷第4期。,形成了“一時紙貴洛陽,風行海內”的局面,(20)鄒振環:《20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頁。其傳播之盛況可見一斑。用傳播學經典的“5W”理論(21)“5W”即指的是傳播過程的五個基本要素:“誰”(Who)、“說了什么”(Says what)、“通過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對誰”(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參見[美]哈羅德·拉斯維爾著:《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何道寬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頁。來解讀可以發現,除了文本因素,這種盛況產生的緣由還在于傳播者對該作品的傳播定位(“誰”“對誰”“說了什么”)、實施的傳播手段和對傳播網絡的立體化構建(“通過什么渠道”)等,這些傳播策略擴大了該書的傳播范圍,提升了傳播的有效性。
(一)言情小說:“西國之《紅樓夢》”的傳播定位
《巴黎茶花女遺事》在傳播過程中,以“豁人心目”和“消悶”兩個功能建構了自身作為“西國之《紅樓夢》”的形象。換句話說,該書以開啟民智、休閑游戲為定位,其傳播一方面迎合了西學東漸的時代潮流,開啟了翻譯文學的新篇章,另一方面也順應了中國傳統小說的消閑功能,以“情跡之奇”和“文法之妙”深入人心。
晚清時期的中國面臨嚴重的社會危機,代表當時先進科學技術的西學之東漸便成為一時潮流,開啟民智亦成為先見者的共識,在各個領域延展開來。其在文學領域則是以這部法國作品的漢譯為重要開端。譯者林紓將翻譯與啟蒙直接聯系起來,說“吾謂欲開民智,必立學堂;學堂功緩,不如立會演說;演說又不易舉,終之唯有譯書”(22)林紓:《譯林序》,《譯林》1901年第1期。,且認為自己年事已高,所能做的便是“肆其日力,以譯小說”(23)同上。,向青年人傳輸新思想,以助他們實現救國的理想。小說評論家邱煒萲也高度評價小說在“謀開吾民之智慧”方面的“絕大隱力”,更將林紓引為同道:“又聞先生(林紓)宿昔持論,謂欲開中國之民智,道在多譯……小說始。”(24)參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頁。在為該書所做的廣告中,汪康年也精準地抓住了這一點,屢次強調其“豁人心目且于西國俗尚亦可略見一斑”“如一粒粟中現大千世界”的功能和“西國著名小說家”的來源。這不僅迎合了當時有遠見的同胞學習西方文化的心理需求,也使讀者意識到該書開拓見識的重要作用,從而產生閱讀的興趣。由此,茶花女形象與西方文學中的“戀愛自由”“理性”“個人主義”“平等”“進化”等思想一起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深深影響了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開拓了中國傳統言情小說“才子佳人”之外的另一種言情模式。進一步來講,可以說以該書為代表的林譯小說,與嚴復所譯的西方文化典籍一起喚醒了一大批民族精英,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做了最初的啟蒙工作。
這一時期的小說在文學體系中的地位處于上升階段,但依然以消閑功能為主,《巴黎茶花女遺事》的暢銷也與該書休閑“消悶”的精準定位相關。林紓翻譯該書就帶有“可破岑寂”的動機(25)參見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頁。,其后在給汪康年的信中又說明該書系“游戲之作”,從譯者的角度肯定該書的產生確有定位于消閑解悶的因素在內。該書的銷售者吳德瀟曾寫信給汪康年:“《茶花女遺事》,此間可銷廿冊……如有新譯奇書可消悶及增拓識見者,乞早寄。”(26)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454頁。此信不僅說明吳是該書的推銷者之一,還印證了該書兼具“消悶”和“增拓識見”兩個功能。正是基于“消悶”這一功能,有關該書的廣告主要內容為強調其情節的變幻和感情的纏綿,如其廣告語中常可見“情節變幻,意緒悱惻”“文法之妙,情跡之奇”“情節變幻”“譯筆尤佳”“事跡新奇,筆墨精妙”等表達。該書作為一種消遣性的通俗言情小說的定位,為近代讀者所接受,如陳衍、吳東園、高旭等紛紛發表讀后感言,寫出“事到無聊說因果,汧國夫人是前身”(27)陳衍:《陳衍讀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頁。“小玉自知病不起,紅顏命薄乃如此”(28)吳東園:《法京巴黎茶花女史馬克格尼爾行》,轉見林薇:《百年沉浮——林紓研究綜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頁。等詩句,將茶花女比擬為唐傳奇中的李娃、霍小玉等女性人物。這種接受還進一步體現在其后出現的許多仿作和擬作上,如“儂更有情”的《愛之花》、鐘心青的《新茶花》《續〈新茶花〉》(戲曲)、徐枕亞的《玉梨魂》、蘇曼殊的《碎簪記》等。對該書消悶休閑功能的強調,使其為更多的普通市民讀者所歡迎,并成為近代文學言情小說之開端。
另外,相關廣告對該書“豁人心目”和“情節變幻”特點的強調,成功構建了該書“西國之《紅樓夢》”的傳播形象。林紓在翻譯該書之前喪妻,心情郁悶;譯書過程中,林紓與合譯者往往為內容所動,相對而哭。(29)吳辰:《林紓:不懂外語的翻譯大家》,《海南日報》2020年7月6日第B15版。林紓也曾自述:“為之擲筆哭者三數。”(30)林紓:《露漱格蘭小傳·序》,轉見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25頁。該書甫一面世,就引來了社會各階層的反響,他們不約而同地將其比為中國的《紅樓夢》,將亞猛、馬克的愛情與寶黛相比較,進而納入到中國的言情傳統中來。邱煒萲以其凄惻,抓住了該書的“情”的主題:“以華文之典料,寫歐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費苦心,好語穿珠,哀感頑艷,讀者但見馬克之花魂,亞猛之淚漬”(31)參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頁。——從“哀感頑艷”“花魂”“淚漬”等字眼來看,“西方之《紅樓夢》”的比擬呼之欲出。金松岑明確提出“《巴黎茶花女遺事》,今人謂之外國《紅樓夢》”(32)金松岑:《論寫情小說于新社會之關系》,《新小說》1905年第2卷第5期。,將該書列入“寫情小說”的范圍。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徐維則等人。這一點在后人的研究中亦得到確認——“人們把《巴黎茶花女遺事》稱為‘外國的《紅樓夢》’”(33)孔立:《風行一時的“林譯小說”》,載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頁。。也就是說,林紓將自己的悲情與該書的悲情相合拍,以傳統文辭包裹著具有“愛情”“自由”等思想內核的故事,使其在傳播過程中以“西國之《紅樓夢》”的形象引起了當時讀書人在情感上的強烈共鳴,進而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
以開啟民智為翻譯西方文學的目的,以情節的變幻作為消閑游戲的注腳,從而建構起該書“西國之《紅樓夢》”的形象——《巴黎茶花女遺事》在傳播過程中的這一精準定位不僅使其順利打開了銷路,也為其文學史地位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二)報刊廣告:集束、預售和連推的傳播手段
為打開《巴黎茶花女遺事》的銷路,出版人在《游戲報》《新聞報》《中外日報》《申報》等報刊上以廣告進行宣傳,并綜合采用多種促銷手段。比如,在投放方式上,廣告采取“告白”的方式,為該書的出版和銷售預熱,吸引讀者的注意,引發其閱讀的興趣;在投放范圍上,以集束式的廣告為特點,集合多家報刊,達到擴大宣傳的目的;在投放時間上,以連推的方式持續數天,加深讀者的印象,擴大接受范圍,由此激起更多讀者的購買欲望。
作為報人,汪康年深諳營銷之道,在該書發排印刷之前,就在報刊上刊登預熱廣告,為之后的銷售造勢。1899年4月24日,有關該書的廣告第一次出現在《中外日報》上:“巴黎茶花女小說,最情節變幻,意緒悱惻。并經福建某君譯出付刊,現本館特向譯書之人用巨貲購得,另用鉛字排印,發各省銷售,并附新譯《包探案》《長生術》二種,不日出書,如有喜閱者,請至本館及各書坊購取可也。昌言報館白。”據查證,至同年5月11日,該廣告至少連登了12次。(34)張天星:《汪康年鉛印林譯〈茶花女〉考論》,《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在19、20世紀交接之際西學東漸的時代背景下,該廣告用“巴黎”“巨貲”等字眼吸引讀者的目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由于林紓譯該書本系“游戲筆墨”(35)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9頁。,意不在利,故上述廣告“用巨貲購得”與“譯書人不受酬貲”的實情不符。于是,在林紓、高鳳謙的強烈要求下,汪康年自1899年5月26日起,在《中外日報》上對此進行糾正:“此書閩中某君所譯,本館現行重印,并擬以巨貲酬譯者。承某君高義,既不受酬貲,又將本館所償板價捐入福州蠶桑公學。特此聲明并致謝忱。昌言報館白。”這則告白連續刊登了5天,為該書增添了“公益”色彩,無形中又增強了傳播效應。這種效應一直持續到1900年——《清議報》第69期也刊登了同樣的內容。可見,出版人采用“告白”的預售方式,以精選的用詞激發讀者的好奇心,為該書的大規模銷售和傳播預熱、造勢,為其“洛陽紙貴”的暢銷局面提供了厚實的鋪墊。
集束式的廣告推廣也是使該書成為暢銷經典的傳播手段之一。換句話說,汪康年作為報人,利用身份、資源之便利,同時在多家報紙上持續推出廣告,“集束”地進行營銷,產生了“廣而告之”的宣傳效果,擴大了小說的接受范圍,提高了該書的銷售數量。據不完全統計,晚清時期,刊登該書廣告的報刊有《中外日報》《游戲報》《新聞報》《國民日日報》《世界繁華報》《字林滬報》《申報》《清議報》等,廣告的主要內容包括小說特點、印刷方式、紙張質量、銷售價格、銷售地點、出版單位等。此外,除《中外日報》,同一廣告也常同時刊登于《新聞報》《游戲報》《世界繁華報》《字林滬報》等報上。其中,《中外日報》為清末改良派報紙,由汪康年主辦,銷售最多時達萬份;《游戲報》為中國近代第一種休閑文藝小報,由李伯元主編;《新聞報》為中外合資,標榜“經濟獨立”“無黨無偏”……這些報刊的立場不一、風格多樣,但都刊登了該小說的宣傳廣告,以集束的方式為《巴黎茶花女遺事》帶來了大范圍快速傳播的局面。林紓本人亦認同這一效果:“當日汪穰卿舍人為余刊《茶花女遺事》……風行一時。”(36)江中柱等編《林紓集》(第六冊),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0頁。可見,這種在多家報刊媒體上幾乎同時刊登廣告的“集束”推廣方式有著不可小覷的傳播能力。
不僅如此,出版者連續投放廣告也有利于形成連鎖效應,給讀者造成該書熱銷的印象,從而激發其購買意愿。下面以《中外日報》為例。該報自1899年5月26日起,連續3天在頭版登出該書的《發售告白》:“茶花女一書情節變幻,譯筆尤佳,現已印出并附新譯《包探案》《長生術》二書。每部白紙實價三角竹紙二角伍分,不折不扣,如欲購者,請向昌言報館及各書坊購取可。昌言報館代白。”至6月1日,該報的頭版廣告變成了《譯印茶花女遺事》:“是書為西國著名小說家所撰。書中敘茶花女遺事歷歷如繪,其文法之妙,情跡之奇尤出人意表。加以譯筆甚佳,閱之非獨豁人耳目且于西國俗尚亦可略見一斑。洵為小說中出色當行之作,非尋常小說所可同日語也。現與新譯《包探案》《長生術》二種合印出售,每部白紙價洋三角,竹紙價二角伍分,不折不扣。如欲購者,請向昌言報館及各書坊購取可也。昌言報館代白。”這一版本更加突出了對該書內容的描繪,進一步體現了廣告主的意圖。不僅如此,這則廣告在《游戲報》上還至少持續登到了6月9日。緊接著,6月10日,該書廣告又以“贈書鳴謝”的方式出現在《申報》上:“昌言報館惠贈《茶花女遺事》及《包探案》《長生術》三種,翻閱一過,事跡新奇,筆墨精妙,如一粒粟中現大千世界,不能以海外之尋常小說目之也。志之以達雅貺。”由此看出,持續的廣告投放帶來了連鎖效應,促進了該書的傳播。
晚清時期,出版者就是這樣用“預熱”的方式為該書的出版和銷售造勢的。商人以《中外日報》為主,以《游戲報》《新聞報》《世界繁華報》《申報》等為輔,持續投放廣告,搭建了一個以報刊廣告為主要傳播手段的新式促銷網絡,給讀者營造了該書“暢銷”的氛圍,推動了該書的銷售和流傳。
(三)立體構建:借力而為、人際與組織融合的傳播網絡
傳播渠道的暢通及傳播網絡的搭建,也是《巴黎茶花女遺事》得以熱銷的重要因素。該書的傳播網絡是由幾個方面構建起來的,包括出版人汪康年“借力而為”打造的順暢的銷售渠道、以林紓為中心的人際傳播、以昌言報館和冶春后社為代表的組織傳播等。
因襲舊例,汪康年利用廣布全國的銷售處為該書搭建了較為暢通的傳播渠道。《昌言報》(1898年8月17日—11月19日)由《時務報》改名而來,汪康年為報館總理,共出版有10期。《時務報》(汪康年擔任總經理)是清末維新派最重要、影響最大的報紙,發行量多時達1.7萬份。這一銷量的達成,有賴于其遍布全國的代售處創造的廣闊傳播空間。1897年7月,《時務報》的派報處(代售處)已出現在70個縣市,共109處,涵蓋直隸、山東、山西、河南、云南、貴州、陜西、甘肅、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份。(37)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第176頁。1898年8月,汪康年遵張之洞之意,將《時務報》改為《昌言報》,《時務日報》改為《中外日報》,(38)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頁。職員多用舊人,銷售渠道亦襲舊例。到1899年5月26日《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在《中外日報》上以“昌言報館”的名義預熱時,《昌言報》由于嚴重的財務危機已停刊達半年之久。(39)潘建國:《物質技術視閾中的文學景觀——近代出版與小說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頁。為“津貼館中經費”以填補虧空并籌措復刊,汪康年積極籌印該書,并以所積累的各種渠道進行銷售。換句話說,該書的銷售因襲了出版人從《時務報》到《昌言報》、從《時務日報》到《中外日報》積累的銷售網和經驗。僅以同年5月21日《中外日報》上的“昌言報告白”為例:“至外埠各處,惟蘭州電局、濟南洋務局、南京陳寓、安慶支應局、壽州文德堂、鎮江裕興康、揚州電局、淮安陳寓、清江善后局、通州森昌、蘇州吳寓、昆山振記、臺州張宅、建寧電局等處……”此處所列舉的內容盡管不夠完整,但所提及的派報處至少分布到了14個縣市,可以想見實際的銷售網絡遠不只此。因此,汪康年借力而為,以昌言報館的名義,沿用了辦《時務報》以來遍布全國的銷售網點(代售處),為《巴黎茶花女遺事》的暢銷打通了售賣渠道,搭建了傳播的網絡基礎。
除了搭建銷售渠道外,以林紓為中心的人際交往活動也促進了該書傳播網絡的形成。從本質上說,林紓的相關人際交往體現為一種文化傳播(40)文化傳播是“人們社會交往活動過程產生于社區、群體及所有人與人之間共存關系之內的一種文化互動現象”。——羅紫初主編《出版學基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頁。活動。林紓交友廣泛,以他為中心參與傳播的人數眾多,涵蓋了與他合作的口譯者(王壽昌)以及諸多文化名人、文化團體等,其間就形成了一個關系密切的傳播網絡。這些名人既包括嚴復、康有為等文化大家,也包括高鳳謙、高鳳岐、張元濟、汪康年等出版名家,后者背后的昌言報館、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機構也為其提供了廣闊的傳播空間。下面以王壽昌為例詳述。他是林紓翻譯該書的合作者、林譯小說最早的口譯者,曾留學法國,精通法文,《茶花女》即為他從法國帶回的文學經典之一 ——有林紓自序為證:“曉齋主人歸自巴黎,與冷紅生談,巴黎小說家均出自名手,生請述之。主人因道,仲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馬克格尼爾遺事》尤為小仲馬極筆,暇輒述以授冷紅生。冷紅生涉筆記之。”(41)[法]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林紓、王壽昌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頁。這說明:王壽昌與林紓關系密切,主動向其推薦了《茶花女》一書;王提出了“口譯筆述”的合作方式,開啟了林譯小說的翻譯模式。可以說,是林、王二人的合作催生了這部近代中國翻譯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此外,林紓與高鳳岐同科中舉,關系親密,進而與其弟高鳳謙(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相熟,引為同好;高鳳謙與汪康年交往,推薦該書由汪康年在上海鉛印銷售;汪康年與吳德瀟、黃篤誠交好,將該書寄給二人閱讀或銷售。由此,“林紓—高鳳岐—高鳳謙—汪康年—吳德瀟、黃篤誠”這種社會個體之間的交際活動也實現了對該書的傳播,使其擴大了傳播范圍,進而更加暢銷。
作為文化傳播的另一種方式,組織傳播也積極推進了該書傳播網絡的建立,促進了傳播的深入、快速進行。根據文化學派的觀點,組織是社會文化的組合。(42)參見[美]凱瑟琳·米勒:《組織傳播(第二版)》,袁軍等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頁。組織分為正規組織和非正規組織兩種。在這一點上,該書的傳播以出版主體昌言報館和文化團體揚州冶春后社為主要典型。昌言報館是一個正規的新聞出版機構,在組織架構、人員職責和對外交流等方面承繼了《時務報》的主要班底,以“指陳利害、開擴見聞”為辦刊宗旨,講究據實而言,報道中外時局及通商事務。應該說,《巴黎茶花女遺事》汪康年本的預熱、出版、銷售、傳播都是以“昌言報館”的名義有組織地進行的,這才得以快速地在社會上引發了“茶花女”效應。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汪刻本出版之前的畏廬本由林紓友人魏瀚出資,只印了100部,分送林、王、魏三家親友,傳播范圍比較有限。昌言報館的這種組織傳播的效果后來延續到商務印書館時期“林譯小說”的名牌效應,可見其威力。在歷史上,文學作品的傳播以非正規的組織傳播較為常見,通常涉及一些較為松散的文學團體或社團等。冶春后社是揚州的著名文學社團,其于19、20世紀之交的活動記錄了揚州逐步摒棄舊制、走向現代的轉型狀況,具有典型的近代色彩。(43)王資鑫:《冶春后社》,載揚州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揚州文史資料·第23輯》,揚州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2003年版,第224頁。該社團的成員宣古愚、趙倚樓、陳懋森、陳霞章、張丹斧等一批揚州名士先后閱讀“茶花女”并賦詩交流,其中趙倚樓動情最深,請宣古愚繪茶花女寫真小像,向冶春同社諸友征詩題詠,并發起創作《茶花女村居圖》卷。卷中繪圖、作序、詠詩、題跋者皆揚州地方一時名彥,最早的作于1899年,最晚的作于1949年,時間跨度達半個世紀。當然,晚清時期的占其中多半,按裝裱順序,其作者依次為吉亮工、宣古愚、趙倚樓、臧谷、陳霞章、張丹斧、陳璧、周潁孝、陳懋森、孔慶镕、王椿、周樹年、包安保、周無方、關笠亭,計15人。(44)木子:《揚州名士歌詠“茶花女”》,《揚州晚報》2013年3月23日第B01版。由此可見,冶春后社有關該書的閱讀、交流活動,引領了揚州的“茶花女”熱潮,大大促進了該書在揚州的傳播。
這一時期,“借力而為”的銷售渠道為該書的銷售和傳播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圍繞林紓形成的人際交往網絡為該書的批量生產和大規模銷售打下了傳播基礎,以昌言報館和冶春后社為代表的組織傳播則擴大了該書的傳播范圍和社會影響,促進了“茶花女”文化熱潮的出現。
三、晚清時期《巴黎茶花女遺事》傳播的現代啟示
晚清時期《巴黎茶花女遺事》的傳播,影響著國人對“西方”和“文學”的認知,激起了人們對“情”與“禮”的重新思考,進而參與了“五四”知識界以“啟蒙”與“革命”為中心的現代化道路選擇。(45)盧文婷:《〈巴黎茶花女遺事〉的翻譯與傳播策略——兼談“五四”愛情浪漫主義話語建構》,載張光芒主編《中國現代文學論叢》(第十六卷第一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72頁。在今天看來,該書獨特的傳播策略在經典的傳播和建構方面,以及中國文學藝術經典的海外傳播方面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借鑒價值。
(一)精準定位受眾,擴大傳播范圍
在當初西學東漸的時代潮流下,小仲馬的《茶花女》以林譯《巴黎茶花女遺事》的面貌進入中國,以中國傳統的文辭典韻講述提倡戀愛自由的西方愛情故事,并通過印刷技術得以廣泛傳播,形成了廣為人知的“茶花女”現象。該書的傳播構建了“西國之《紅樓夢》”的文化形象,以“舊瓶裝新酒”的言情小說模式為中國的大量讀者所接受。這說明,文學文本本身并不能獨立地完成跨文化傳播的重要使命,對它的接受是讀者對文本背后的歷史、文化的系統認知的結果。
在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如何在世界文化傳播格局中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無疑是海外傳播領域的重要課題。對此,十分值得研究的問題包括:如何選擇位于傳受雙方共同經驗范圍之內的作品;如何選擇最契合接受方狀況的模式和話語;如何在傳播的信息功能和娛樂功能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如何做到依據傳播的雙向性和循環性,始終把受眾的需求置于首位,利用受眾的反饋推動中國文學藝術經典的持續有效的傳播;等等。
(二)綜合多種傳播手段,有效利用海外媒介
整體來看,晚清時期的圖書傳播廣告以價格促銷為主,呈現單一化的特點;(46)劉俊冉:《晚清海外圖書在華廣告傳播策略與啟示——以〈大英百科全書〉為例》,《出版發行研究》2021年第1期。《巴黎茶花女遺事》的傳播則明顯不同,它綜合利用多種手段,達到了有效促銷的目的。這些手段包括:在報紙上為圖書進行市場預熱和造勢,吸引讀者的注意,引發閱讀和購買的動機;同一時期在多家報紙上進行銷售宣傳,以集束式的廣告擴大傳播范圍,形成規模效應,給人帶來“暢銷”的印象;以連推的方式持續數天乃至經年刊登廣告,連續加深印象,形成連鎖效應,加大傳播力度;等等。
新媒體時代,網絡使信息傳播的速度更快、時效性更強,且傳播成本更低,因此,文學藝術作品的傳播也應轉變觀念和模式,綜合利用多個平臺,結合紙質、網絡等傳播媒介,采取多種傳播方式,在傳播范圍、傳播時間等方面形成規模、連鎖效應,從而提高傳播的效度。比如美國《路燈》、德國《膠囊》和日本《火鍋子》等雜志,以及“紙托邦”等海外網絡平臺長期刊登中國小說,起到了良好的海外傳播作用。通過與它們進行聯合營銷,有助于中國文化產品進一步打開海外銷售市場、促銷并擴大傳播范圍和影響。
(三)構筑多種傳播渠道,催生中國經典的海外暢銷版
晚清時期,《巴黎茶花女遺事》的傳播借力而為,因襲了《時務報》以來的傳播渠道,并結合了人際傳播與組織傳播的方式,立體化地構建了卓有成效的傳播網絡,營造了暢銷的氛圍,由此使大規模的快速傳播成為可能。當前中國文學藝術的海外傳播,也一直存在著傳播渠道不暢通的問題。受制于這一點,“借船出海”是目前最好的選擇。(47)馬新強:《多維視角下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策略》,《上海翻譯》2020年第2期。也就是說,與海外文化企業的合作仍然是中國文藝海外傳播的首要選擇。這種模式一方面有利于縮短周期、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借助海外同業成熟的出版發行渠道去推廣作品。此外,電子化閱讀時代已經到來,電子讀物制作簡單、易于獲取、便攜且廉價,在降低出版成本的同時,也可以減少讀者的獲取成本。因此,開發文藝App,制作電子書、有聲讀物等,也是出版方在紙質出版之外的迫切需求。更具體地說,可利用國內外已經成熟的網絡社交平臺,如“推特”(Twitter,現已更名為X)、“臉書”(Facebook)、“照片墻”(Instagram)、“狄鐸”(Tiktok)、微信、抖音、快手等,開設相關的中國文化宣傳賬號,構建包括文字、圖像、影音在內的多模態推廣平臺——這是構筑多種傳播渠道的有力措施。同時,還應積極拓展營銷渠道,構建暢通的合作渠道,盡可能擴大傳播活動的視野,創造有利于大規模快速傳播的條件,推動中國經典海外暢銷版的產生。
結論
經典是文化內容的載體,也是文化傳播的媒介,更是文化交流的連接點。晚清時期,林譯《巴黎茶花女遺事》以“西國之《紅樓夢》”的傳播定位,綜合預熱、連推、集束等報刊廣告的傳播手段,融合多種傳播方式搭建了立體化的傳播網絡從而暢銷,塑造了近代翻譯文學的經典,增強了海外文學經典在中國的傳播效應。這一文學/文藝/文化傳播現象亦具有當下性——尤其是隨著我國綜合國力增強,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塑造和建構中國形象也成為學界越發需要研究與考慮的重要問題。在文藝經典的海外傳播方面,我們至少可以就此思考如下具體的問題:如何找到契合不同國家民眾的各種話語模式,精準定位,打造“中國的《茶花女》”之類的中國經典的海外形象;如何構筑傳播渠道,搭建良好的傳播網絡,為中國文藝的海外傳播創造更為廣闊的空間;如何綜合運用多種傳播手段,催生中國經典的海外暢銷版;等等。可以說,在通過文藝經典的傳播讓世界了解今日中國的變化,提高國家的文化軟實力方面,《巴黎茶花女遺事》的傳播恰好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