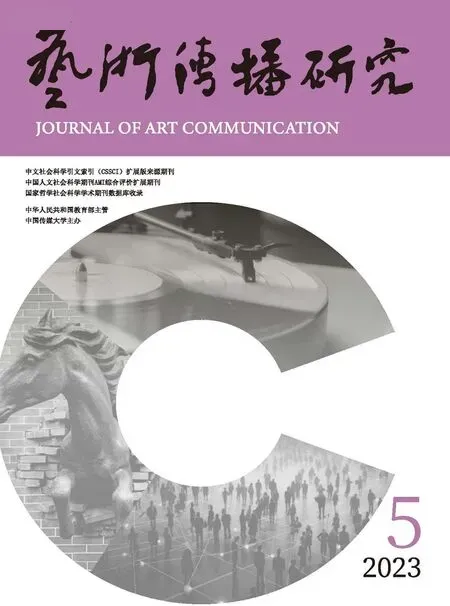中國本土唱片在發端期產生贗品的前因后果
柴俊為
2023年是中國本土唱片誕生120周年。1903年3月18日,在上海“金谷香西餐館”(1)位于四馬路(今福州路)湖北路口。的一個房間里,誕生了第一張中國本土唱片的母盤——費雷德·蓋茨伯格率領的英國留聲機公司(the Gramophone &Typewriter Ltd.,簡稱G&T)錄音團隊,接下來在中國總共錄制了470張母盤。這些母盤被運往德國漢諾威的工廠制成唱片,首版以“克萊姆峰”(Gramophone,現又譯“留聲機”)品牌上市銷售。因此,國內館藏目錄對這批唱片多記有“德商”字樣。但令人遺憾的是,這批唱片作為首批在中國本土錄制的戲曲音樂唱片,目前看來,絕大多數可能是“贗品”,即“偽托”——其署名的表演者并非其實際的表演者。現有證據確鑿可以甄別的,涉及小叫天、汪桂芬、孫菊仙、周春奎、汪笑儂、白文奎、小連生、三麻子(王洪壽)、小子和、郭秀華、劉永春、林步青等人物。
顯然,這既不應該也不可能是英國留聲機公司遠東之行的初衷。該公司這一次旅行錄音,除在中國采錄之外,還在印度、日本、新加坡、泰國、緬甸等地錄制了大量的民族音樂唱片,而就目前關于這些國家的唱片的研究看,尚未見類似的現象。那么,為什么單單在中國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呢?
長期以來,這個問題少有學者關注。誠然,有的研究關注到了偽托當時個別名伶,特別是譚鑫培、孫菊仙等人的唱片,但仍把絕大部分“克萊姆峰”的唱片默認為真品,以為“蓋茨伯格和徐乾麟所錄制的錄音,是第一次收錄當時上海的著名演員和歌女”(2)[德]史通文:《在娛樂與革命之間:留聲機、唱片和上海的音樂工業的初期(1878—1937)》,王維江、呂澍譯,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66-67頁。,很少認識到冒名頂替、以假亂真曾是當時洋行所生產的唱片的一個系統性缺陷。這個缺陷既緣于西方商人的傲慢,亦緣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社會中買辦階層的所作所為;而得到國際著名品牌“克萊姆峰”的背書,正是這一缺陷得以擴散的關鍵。
一、重新解讀“上海之行”
蓋茨伯格1942年在紐約出版的回憶錄《音樂走四方》(TheMusicGoesRound)數十年來多次再版,其中,關于他在上海和香港的回憶的段落以及他的部分日記,為研究東方唱片史的學者較多地引用。不過,這些史料里有兩個問題似未引起足夠的關注。
第一是蓋茨伯格對他所錄制的中國戲劇(曲)音樂表現出了明顯的反感。對此,今天的讀者當然可以用“文化差異”這個理由來解讀,然而只要比較該書中對印度、日本甚至緬甸的戲劇音樂的描述,就會發現原因可能不完全如此。固然,蓋茨伯格在該書中對印度和日本的某些音樂也表現出相當的不適應——比如關于印度音樂,他曾表示“我的音樂訓練的根基被動搖了”,(3)F.W.Gaisberg,The Music Goes Round(New York:The Macmilian Company,1942),p.54.而面對“狂言”這一日本的藝術體裁,他居然直說“對我來講,聽起來就像驢叫”,(4)同上書,第61頁。不過,這種負面評論在書中相對來說依然是局部的、特定的;他在這部回憶錄中對印度、日本的音樂和唱片業的發展也都有總結性的反思。而談到上海和香港,他的評價全部是負面的、刻薄的,比如“中國人演唱時用盡全力咆哮”,“他們的音樂理念是巨大的碰撞和轟鳴”,“她們的聲音猶如小貓的哀鳴”,(5)同上書,第63頁。除此之外似乎別無話說。對于一名有著相當音樂修養的作者來說,這樣的評價差異背后,除了文化因素外應當還有其他的原因,譬如對其他民族的精神世界缺少理解的意愿,又如他所遇見的演員的水平、修養及其所繼承的風格是否真的代表了中國戲劇戲曲的最高水準。
第二個問題或許更為關鍵,即蓋茨伯格團隊在上海錄音時,其采錄程序及酬勞制度均異于在其他國家的慣例。
這次遠東之行,錄音團隊在各地的工作程序本來是差不多的:每到一地,均由當地的中間人(主要是英裔人士)帶領,尋找合適的藝人、劇團,然后觀摩其表演,隨后制定錄音計劃,再進行采錄。在加爾各答,由于該公司當地分支機構的英裔印度職員對印度音樂毫無興趣,蓋茨伯格還專門找了當地的警察陪同去“哈里森路的各種重要娛樂場所和劇院”,又去當地富豪家參加晚宴,觀看少女表演的歌舞(“Nautch”),然后,選了一位著名的歌手古拉·揚(Goura Jan)來錄音,她每晚的出場費是300盧比。此后,又約到了當時有“最好的(印度)古典歌手”之稱的揚基·拜伊(Janki Bai),錄音費高達3000盧比。(6)F.W.Gaisberg,The Music Goes Round(New York:The Macmilian Company,1942),pp.55-57.團隊在印度大約花了6周時間,錄制了500多個母版。在日本的時間更長——蓋茨伯格是“1903年新年的那一周”(7)同上書,第59頁。到達橫濱灣的,而他的日記顯示,直到2月13日他還在為日本藝妓錄音。采錄小組在東京一開始就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參觀劇院和茶樓,并進行試音。蓋茨伯格回憶說,他們“擬定了一個相當全面的民族音樂錄制清單”(8)同上。,最后錄制了600張各種類型的日本傳統音樂唱片,支付的費用高低不等,每段在5美元到30美元之間,一般是20美元。后來,該團隊離開中國后到達緬甸,也是先觀摩了名為“ZAT”的當地雜劇演出,然后錄制了40張成套的唱片。
對比之下,蓋茨伯格在中國上海的工作則頗有異樣,這主要表現在兩點:速度快和價格低。在日程方面,1903年3月16日,他們與英商“謀得利洋行”(The important music-house of Moutrie &Co.(9)同上書,第62頁。)的中間人見面,商定由他去安排演員;次日,在洋行為他們安排的西菜館布置錄音設備;第三天即開始錄音,僅用9天時間就完成了325張唱片的錄制——以當時的技術條件來說,“效率”高得有些驚人。在酬勞方面,竟然不分劇種、不分演員優劣,一律每段4美元,這個價格也低于團隊在日本、印度所出的最低價。
這部回憶錄沒有記載團隊到達上海的日期,也沒有記載在上海觀摩演出、挑選演員的詳情。其中的一則日記表明,他對前來錄音的演員及其帶來的節目并不了解,以至于第一天只錄了10段,不得不中止:
3月18日,星期三。我們錄制了第一張唱片。大約來了15個中國人,包括伴奏樂隊。中國人演唱時用盡全力咆哮,每晚只能唱兩首曲子,然后嗓子就沙啞了……
第一天,在制作了10張唱片后,我們不得不停下來。喧囂讓我的頭腦麻痹,無法思考。(10)同上。
拋開一些明顯帶有傲慢和偏見的修辭不談,這里很引人注意的一個信息點是:謀得利洋行安排的演員演唱,使蓋茨伯格大為意外,不得不停止錄音以解決技術問題。假設蓋茨伯格事先對演員和演出有所了解,接觸過后來姓名被寫在片心上的名伶,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問題;而如果親自與名伶的管事(類似經紀人)進行過談判,他也會知道4美元一段的價格是請不到名角的。兩年之后,名伶陸續應邀參加錄音的價格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11)參見柴俊為:《中國戲曲唱片贗品概述》,載傅謹主編《京劇文獻的發掘、整理與研究——第八屆京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國戲劇出版社2021年版,第589頁。
必須指出,“謀得利洋行”主營“注重樂器洋琴,話匣僅系一種副業”(12)退庵:《話匣與伶人之關系》(下),《時事新報》1928年7月30日第14版。。用現在的話說,它主要的身份是一家外貿樂器行,雖與音樂有關系,但并不是生產和銷售“音樂錄音”的公司,何況當時的中國也不存在專業的錄音公司。那么,為什么蓋茨伯格會認為它是一家“重要的音樂室”呢?這,應該就涉及了該錄音團隊在上海被“安排”(arrangement)的關鍵環節。而由這次“安排”所形成的錄制銷售模式,直接影響了之后十余年的中國唱片業。
二、圓盤唱片到來前的中國留聲機市場
從商業角度考察,可以發現這次“安排”的快速完成與當時中國蠟筒留聲機的銷售模式有直接關系。現有的許多記述表明,在圓盤唱片錄音來到上海之前,中國已經有留聲機銷售——筆者最近發現的一篇1928年的報道說得更詳細:
話匣又名留聲機器,三十年前已有之,其時有法人那潑者首先在吾國發售,假南順泰為發行所,惟所制造之機器殊為草率,如鐘表有發條,推之能動而已,傳聲者系蠟筒……(13)退庵:《話匣與伶人之關系》(上),《時事新報》1928年7月29日第14版。
按“三十年前已有之”,則最遲1898年就有了。我們看到,目前殘存的戲曲蠟筒實物雖由不同的洋行、商號錄制,但很多是百代公司出品的空白蠟筒,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法人那潑者首先在吾國發售”的說法。當然,蓋茨伯格到上海時,銷售蠟筒留聲機的已遠不只有法國商人。在歐美,留聲機一開始主要是作為商用的聽寫機銷售的,在家庭娛樂方面的價值開發得比較晚。早期的蠟筒不能批量復制,所以最初并沒有真正的“唱片商品”可以供應。對一般的藝術消費者而言,既然沒有音樂內容提供,留聲機就難以推廣。歐美的商業錄音活動始于1889年,最早開發這項業務的是愛迪生公司,但該公司僅堅持了8個月即退出,直到1895年左右才重回錄音生產。與愛迪生公司差不多同時且能夠持續開展商業錄音業務的是哥倫比亞公司,后者堪稱世界商業錄音的奠基者之一(14)參見Tim Brooks,“Columbia Recordsinthe 1890s:Founding the Record Industry,”ARSC Journal,(1978):6-7.。該公司除了供家庭娛樂之外,還著力推廣一項風靡了多年的點唱機業務。遺憾的是,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當時沒有出現這樣敢于冒險的先驅者,為了銷售留聲機,洋行經營者開發了一項“只賺不賠”的小生意:
……其時尚未發明今日復印流傳之方法,如欲購買,將機器之價格及所需蠟筒之多寡,預先訂定價目后,方由該公司雇清音前來收音,其價值頗廉,如雇清音來唱一日,代價三元左右,而一日至少可收至十余筒,每一蠟筒僅值小銀元二三角而已。然每售一筒必須收音一次,亦太費事矣。(15)退庵:《話匣與伶人之關系》(上),《時事新報》1928年7月29日第14版。
“清音”又稱“堂名”,源于昆曲清唱,但到了清末的上海,已淪為一種半業余的打唱班,專應婚喪嫁娶上門清唱,另外商號開張、節日祭神等活動亦多請清音班湊熱鬧。清音班只應清唱、演奏,不能化妝登臺,營業特性正合留聲機灌音,但其中不少人的藝術水準相當平庸。
從為數不多的現存戲曲蠟筒可以看出,經營這種灌音業務的不只一家。但這種為銷售留聲機所錄制的蠟筒,也很難說是正規的“音樂產品”,它更像一種代客加工服務。這與哥倫比亞唱片公司開創的那種有品牌、有版權、有目錄(相對標準化)且能夠小批量復制的商業錄音還是有根本的區別。不過,這種“代客錄音”業務,恰好為蓋茨伯格的上海之行(以及此后中國商業唱片的發展)準備了一個“便利”條件和一個“陷阱”。
所謂“便利”條件,就是聚集了一個以清音班為主的灌音圈子。我們在現存的蠟筒和不同品牌的贗品唱片里,會聽到一些相同的嗓音,并且經常反復灌制同一個唱段。在蓋茨伯格錄制的唱片里,有一張寫作《一支令·前段》(16)模版號E1513,目錄號G.C.12506。,署名“周春奎”,另一張寫作《三支令·后段》(17)模版號E1514,目錄號G.C.12507。,署名“孫菊仙”,實際是同一人所唱。此人的特點是一嘴的南方字音。這兩張合起來是一段戲,即京劇《天水關》中諸葛亮“派將”,給魏延、馬岱分別下了一支令箭,又給關興和張苞下了一支令箭,俗稱“三支令”。此人大概很得意自己這段演唱,1905年又在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灌了一遍,用的名字是“裘處”,表明是票友身份;同年,他又用這段在勝利公司分別灌了一張10英寸和一張12英寸片——10英寸片一人到底,署名“白文奎”;12英寸片比較完整,加上了魏延、馬岱“接令”的配唱,署名“楊處、小金紅、馬飛珠”(18)模版號、目錄號9167。。次年,海因里希·布蒙(Heinrich Bumb)到上海,此演員又出現在“撥加(Beka)唱片”的錄音現場,演唱中仍有這一段,復以“裘處”署名(19)筆者懷疑此人即為裘姓票友,勝利公司署“楊處”可能是筆誤。。像這樣的事情絕非孤例,甚至一些知名的演員也加入過這個圈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馮二狗。馮二狗是名旦小子和(馮子和)的兄長,其丑角的聲價雖然在林步青、姜善珍、何家聲等名丑之下,不過早年有嗓,能唱,除本工以外,在《十八扯》等戲里學老生、小生均有是處,尤其學孫菊仙“幾可亂真”(20)羅亮生:《戲曲唱片史話》,李名正整理,載中國戲曲志上海卷編輯部編《上海戲曲史料薈萃》(第1輯),上海藝術研究所1986年印制,第99頁。,勝利唱片有他學孫菊仙的《雪杯圓》。此外,他還能唱蘇灘、本灘、小熱昏等,均有唱片存世。因此,他可稱是早期錄音圈的大忙人,大量的唱片里都有他的聲音。勞弗(Berthold Laufer)代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NH)1901年9月在上海錄制(21)1901年9月至1902年,德國人類學家和歷史地理學家勞弗代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來中國考察,在上海和北京錄制了一批戲曲、曲藝及民間音樂蠟筒,其中有400個蠟筒目前保存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傳統音樂檔案館。的現存蠟筒中也有他的節目,比如梆子《翠屏山》中的潘老丈(22)Collected by Berthold Laufer,China,Shanghai and Peking,1901-1902,SCY2895,https://media.dlib.indiana.edu/media_objects/3f462n38f.、海和尚(23)同上,SCY2914-2915,https://media.dlib.indiana.edu/media_objects/3f462n38f.,南無調《和尚采鮮花》(24)同上,SCY2921,https://media.dlib.indiana.edu/media_objects/3f462n38f.等。以他為代表可見,這批演員當時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灌音經驗。
所謂“陷阱”,就是用這批演員來冒充名伶。當時,與美國的自動點唱機業務有點類似,中國乃至亞洲其他一些地區出現了一種“人工點唱機”——留聲機小販:
唱機形式……一種是裝置喇叭的,聲浪較響,便于大處靜聽;一種是用橡皮帶頭,一組分支好幾副……每人納了相當(的)聽費,他就會給你一副塞入耳內,開唱時你就能聽到蠟筒上所放出的戲曲聲音來了。這一類大都是走江湖的所置,專走鄉村小鎮的處所,欣賞的孩童居多。(25)丁慕琴:《唱片漫談》,《大美電臺周報》第3期(1946年1月24日),第3頁。
而這些留聲機小販播放的蠟筒,其內容幾乎都在假冒當紅的名角:
當時人們對這新出現的玩意兒,不免帶些好奇的心理,其所以能夠吸引人們的興趣,就在于這些攤桌上除設置有留聲機(備有五六根橡皮管供人塞在兩耳收聽的聽筒)一座外,還陳列著許多灌有京劇名角所唱的蠟筒,每一紙殼上都有標簽,寫明汪桂芬的《文昭關》,小叫天的《賣馬》,或孫菊仙的《硃砂痣》等。人們雖明知俱是假,好在每聽一次只要化八文錢,能過一次戲癮,也就不在乎了。(26)羅亮生:《戲曲唱片史話》,李名正整理,載中國戲曲志上海卷編輯部編《上海戲曲史料薈萃》(第1輯),上海藝術研究所1986年印制,第99頁。
綜上可見,在蓋茨伯格到來之前,上海的一些洋行及其買辦人員已經制造了一套“錄音造假模式”。
三、南順泰洋行、謀得利洋行與徐乾麟
蓋茨伯格要想不跌入這個贗品陷阱,除非有兩方面的條件。一方面,他自己要了解當時在當地留聲機銷售領域中的這套運作“底細”。另一方面,遇到的合作者要有見識、有資源、有基本的商業道德——這就需要合作方能認識到圓盤唱片的前景,把眼光放長遠,不做那種“三元錢”成本、“賣一制一”的作坊式生意,還必須掌握梨園界的資源,能約到且愿意去約真正的名家。遺憾的是,這些條件都不具備——蓋茨伯格的合作者是英商謀得利公司。
《時事新報》的文章說,“西人在華營話匣業者,以南順泰為最早,其次即謀得利琴行”(27)退庵:《話匣與伶人之關系》(上),《時事新報》1928年7月29日第14版。。南順泰洋行位于新開河浜,是一家德商,它和謀得利都跟徐乾麟有關系。徐乾麟從1882年起即擔任謀得利洋行的華人買辦,同時又是南順泰的執事(28)佚名:《英美租界公堂會訊案》,《申報》1901年4月7日第3版。。上海的這套留聲機經營模式,他顯然是熟悉的。
蓋茨伯格在當年3月16日的日記中說:“我們與一位河南路的買辦(中間人)George Jailing[他的中文名字叫Shing Chong(音譯)]作了安排,由他來組織藝術家。”(29)F.W.Gaisberg,The Music Goes Round(New York:The Macmilian Company,1942),p.62.這里的“George Jailing”是否是徐乾麟,中外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畢竟這兩個名字都與徐乾麟常用的英文名C.L.Zeen不符。不過,作為謀得利洋行唯一的華人買辦,在這種與華人及中國文化相關的業務中,徐乾麟是決策的主導者,這一點在學界是無異議的。
國外的一些學者把徐乾麟,以及后來協助勝利公司錄音的“Yuen Sing Foong 先生”誤認為是“京劇愛好者”“票友”,以為他們“在上海的娛樂圈有廣泛的人脈”(30)Christina Lubinski and Andreas Steen,“Traveling Entrepreneurs,Traveling Sounds:The Early Gramophone Business in India and China,”Itinerario:European Journal of Qverseas History 41,no.2(2017):282.,通過他們“才能為物克多公司爭取到中國最好的人才”(31)同上文,第287頁。,筆者不知其有何依據。《時事新報》的文章坦言,“該行買辦徐乾麟先生與伶界素無往來”(32)退庵:《話匣與伶人之關系》(上),《時事新報》1928年7月29日第14版。。要知道,清音班與戲班的性質不同。清音自古就是半業余性質的演出團體,營業方式是“開門接生意”,上海的有些清音班干脆設于沿街,有人上門來約就去唱。因此,請他們去錄清唱幾乎沒有門檻。而專業演員的主業是戲院(當時叫茶園)演出,雖然觀客上園子看戲也沒有戲票資金之外的門檻,但是請他們(特別是名角)外出應堂會或參加票房清唱等活動,包括后來的錄音活動,則必須有人脈,另外還得“懂行”。在蓋茨伯格錄音的幾年以后,百代公司在北京由譚派名票喬藎臣作買辦,高亭公司聘羅亮生為顧問,蓓開公司聘用劇評家梅花館主等,都是這個道理。另外,徐乾麟等人明顯也不是“京劇愛好者”或“票友”。蓋茨伯格的日記說,他的一位朋友來參觀錄音,問唱的是否屬于情歌,買辦回答“不是,他是在唱自己的祖母”(No,he is singing about his grandmother)。(33)F.W.Gaisberg,The Music Goes Round(New York:The Macmilian Company,1942),p.63.筆者查閱“克萊姆峰”上海唱片的全部目錄,未發現哪一段的內容與“祖母”有關,而在傳統戲曲里也幾乎找不到有“哀歌”祖母的唱段,所以這段記載極有可能反映了買辦自己因聽不懂而信口開河。羅亮生曾直言:“該行華人經理徐乾麟認為對唱片錄音何必要頂真,只要雇些打唱班(即堂名)的人來唱,寫上名角的名字,既便當又省費,而且一樣可以行銷。”(34)羅亮生:《戲曲唱片史話》,李名正整理,載中國戲曲志上海卷編輯部編《上海戲曲史料薈萃》(第1輯),上海藝術研究所1986年印制,第99頁。這種灌片理念足見此類買辦對戲曲藝術是沒有感情的。像上述《三支令》的例子,一個人唱同一出戲,竟可以分別假冒“孫菊仙”和“白文奎”兩位名角;在1905年喬治·切尼的錄音中,他們又把真的孫菊仙和清音班所唱的錄音同時署為“孫菊仙”;謀得利主持的后三次錄音中,有一名清音老生現存近90段錄音,先后或同時被署以“雙處”“時慧寶”“馬昆山”“馬處”等四五個名字(35)柴俊為:《雙處及其唱片真偽考辨》,《中國京劇》2023年第8期。……這些隨心所欲的做法,充分顯示徐乾麟和他的下屬是戲曲的外行,京劇愛好者必不至于如此荒唐,至少也可以做得略微像樣一些。
筆者梳理這些細節主要是想說明,無論蓋茨伯格是否愿意,以謀得利洋行當時的人脈資源和業務知識,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幫蓋茨伯格約來真正的名角錄制300多張母盤。蓋茨伯格在上海之所以錄得快、價格又低,就是因為謀得利“安排”了清音班唱蠟筒的熟手們。何況徐乾麟也向《時事新報》坦承“最初所制蠟片(36)所謂“蠟片”,當指錄音使用的母盤。最初,一個母盤只能復制一個模版,1902年以后,新技術使得一個錄音母盤已可以復制多個模版,唱片的產量因此大幅提高。,即雇當地清音所唱”。(37)退庵:《話匣與伶人之關系》(上),《時事新報》1928年7月29日第14版。然而,蓋茨伯格未必有興趣了解其中底細,謀得利也未必明確告訴他這些人都是用來冒充名角的。當時,西方的留聲機業正處于法律大戰的漩渦,公司方面如果了解真相,應該也不太可能冒這樣的侵權風險。
四、“謀得利-克萊姆峰模式”
盡管蓋茨伯格的上海之行掉入“贗品陷阱”,在中國唱片業發展史上留下了較為不堪的一幕,但就當時的市場反應而言,這些贗品的銷售情況居然不錯。雖然音樂內容的藝術品質一言難盡,但是產品的可選性、耐用性、便捷性、新鮮感相比之前的“可錄式”蠟筒都大幅提升了,所以吸引力不言而喻。據說,470個華語模版一共壓制了36 000張唱片,除了在中國銷售,海外的巴黎、布魯塞爾、蘇門答臘等地也都有經銷商詢問訂貨。(38)[德]史通文:《在娛樂與革命之間:留聲機、唱片和上海的音樂工業的初期(1878—1937)》,王維江、呂澍譯,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頁。
銷售上的成功很快引來了投資競爭。1906年1月,撥加(Beka)公司的旅行錄音小組剛到香港就聽到了這樣的消息:
哥倫比亞留聲機公司剛剛完成了最新的錄音——據說有1 000段,支付了50 000美元的費用。 “物克多”“克萊姆峰”以及“新樂風”(Zonophon-Records)和“高亭”在(香港地區)……都有代表。(39)John Want,“The Great Beka Expedition,1905-6,”The Talking Machine Review,No.41(1976):729-733.
從文獻價值方面看,“克萊姆峰”的贗品也確有意義,不過只是一種“歪打正著”的意義:中國傳統戲曲尤其是京劇、梆子等所謂“亂彈”劇種的特點,決定了它的“平庸”演員與著名演員之間除了藝術修養與技巧水平的差別之外,還有一種因從民間藝術、廣場藝術逐漸向城市戲劇、劇場藝術發展而形成的歷史性差異。早期比較原始、粗糙的藝術風格和戲路常常保存在一些底層演員甚至票友的身上;而這些早期唱片與名演員的交集更少,這種歷史的陳舊風貌也就保留得更多——這個問題容筆者另做專題研究時詳述。但顯然,這并不能抵消“克萊姆峰”唱片在中國唱片歷史發展中的顯著負面影響。
不講商業誠信,欺騙消費者,侵犯名演員權益……這些問題自不待言,“克萊姆峰”唱片最根本的問題是,把原先流行在中國洋行間的那種“賣一制一”的小作坊式欺詐給工業化、國際化了。這種“商業欺詐”在這樣的跨國企業及其著名品牌的背書下迅速擴張,十余年間,爭相加入中國市場的歐美唱片企業除了百代公司之外,哥倫比亞(Columbia)、勝利(Victor)、高亭(利喴,Oden)、撥加(Beka)等公司或多或少都在中國生產過贗品。(40)柴俊為:《中國戲曲唱片贗品概述》,載傅謹主編《京劇文獻的發掘、整理與研究——第八屆京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國戲劇出版社2021年版,第585-598頁。可以說,當時中國的唱片錄制一時間形成了一種“謀得利-克萊姆峰模式”。
民國以降,不少研究者因不明底細,往往把此類贗品誤解為特定的“高仿”。比如在關于孫菊仙唱片真偽的爭議中,劇評家們紛紛猜測是學孫菊仙較有成就的馮二狗、雙處、時慧寶、呂月樵等假冒孫菊仙。這種思路可能引導當代學者產生了更深的誤解:
一開始,勝利和謀得利公司(或者說買辦徐乾麟)試圖利用他(按:指譚鑫培)的名字獲利。他們請了幾個學了譚派唱腔的票友來上海的錄音棚錄音,然后貼上“譚鑫培唱×××”的標簽……(41)[德]史通文:《在娛樂與革命之間:留聲機、唱片和上海的音樂工業的初期(1878—1937)》,王維江、呂澍譯,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頁。
實際上,當時除百代公司完全拒絕“謀得利-克萊姆峰模式”之外,同業其他公司幾乎都采用了這個模式。在現存的大量唱片中,我們既可以發現同一個人的錄音寫成兩三個甚至更多名角的名字的情況,又可以發現同一名角分別被幾人假冒的情況,所以很可能根本無所謂假冒者是不是學了“×派唱腔”的。一個比較夸張的例子是,1907年錄音的利喴蘇灘唱片,其中署名林步青、張筱棣、周鳳林的均為女子蘇灘之葉菊蓀一人所唱,僅筆者所見即多達48面,實際當遠遠不止(42)這批唱片的目錄及考證依據,參見柴俊為:《中國戲曲唱片贗品概述》,載傅謹主編《京劇文獻的發掘、整理與研究——第八屆京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第594-596頁。——造假已經造到連男聲、女聲都不在乎的地步,遑論流派風格。
這種冒充名角的做法形成一種行業痼疾之后,至少造成了兩大不良后果。
第一,錯失歷史機遇。舉個極端的例子,當時京劇界的三大代表人物汪(桂芬)、譚(鑫培)、孫(菊仙)之中,汪壽命最短,于1908年6月10日去世。據目前所知,汪的最后一次公開演出是1907年9月的福壽堂義演。此次義演由田際云、李毓臣、喬藎臣等發起,“汪桂芬頭一個贊成”(43)佚名:《記汪桂芬在福壽堂演義務戲事》(一),《順天時報》1907年9月6日第5版。,他第一天唱了《取成都》,第二天唱了《群英會》,第三天的《戰長沙》即未參演。從時間上看,如果早一點采取“百代模式”(44)柴俊為:《中國戲曲唱片贗品概述》,載傅謹主編《京劇文獻的發掘、整理與研究——第八屆京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國戲劇出版社2021年版,第586-587頁。,哥倫比亞、勝利、撥加都有機會填補“后三鼎甲”的聲音缺失。遺憾的是,這三家公司第一次到中國,都是緊隨蓋茨伯格的足跡,從香港(或廣州)到上海,而沒有到京城的計劃。當然,汪桂芬的例子包含了假設,畢竟就個例而言,即使后續有更多的公司按照“百代模式”誠實經營,以汪桂芬的怪脾氣,他仍然可能不去錄音。但是,從概率上講,由于絕大多數公司沿襲了“謀得利-克萊姆峰模式”,中國唱片業在其最初的十年里失去的就肯定不止一個“汪桂芬”。
第二,浪費頗多資源。中國唱片業起步的十年,有大量的資金和母版重復消耗在低質量的演唱上。如前文所述,以清音班為主的那個“錄音圈”人數有限,錄制的重復率極高。在中國唱片資源最稀缺的那些年灌制唱片最多的,不是當時的名伶,而是名不見經傳的半業余演唱者。
使情況更為復雜的是,這一模式在得到市場反饋和資本加持后,很快產生了新的“變異”。1904至1905年在上海錄音的哥倫比亞公司,花了數月的時間才錄了1 000個模版,錄制速度明顯降低。我們在存世不多的相關唱片實物中看到,它們雖然還是以清音(堂名)演唱為主的贗品,但是也有林步青(《打寧波會館》《跑馬賦》等)、時慧寶(《教子》《瓊林宴》)、劉永春(《鍘美案》)、汪笑儂(《瓜種蘭因》《黨人碑》)、三麻子(《舉鼎觀畫》)等名伶的真品。也就是說,在“克萊姆峰”之后,其他廠家在造假的基礎上,也開始盡財力、人力所及,邀請一些名角錄音了。很快,這一“變異”也傳到了謀得利。緊跟哥倫比亞公司來華的勝利(Victor,時稱物克多)公司與“克萊姆峰”為關聯企業,所以其錄音師喬治·切尼到上海之后也找謀得利代理(45)哥倫比亞公司在美國跟勝利公司是死對頭,后者的總裁曾用詭計挖走前者生產圓盤唱片的子公司“環球唱片”。后者又與“克萊姆峰”是關聯企業,1904年以后,雙方制定協議:“克萊姆峰”品牌專注于印度及遠東其他地區業務,中國區的業務歸勝利公司。因此,“克萊姆峰”的部分華語唱片此后以“物克多”品牌再版銷售。約請名角的新舉措一定程度上也是老對手相互競爭的結果。:
謀得利第一次請名伶收音時,因該行買辦徐乾麟先生與伶界素無往來,頗感困難。后有金谷香西菜館西崽某某與小連生(即潘月樵)交好,經其介紹,得與徐乾麟相識,小連生乃為徐君在伶界中竭力宣傳,又拉攏同業前往清唱,故第一次得度收音成功,小連生之力居多也。(46)退庵:《話匣與伶人之關系》(上),《時事新報》1928年7月29日第14版。
必須指出,此文為謀得利、徐乾麟辯護的立場鮮明,敘述中時空倒錯、夸大其詞等問題在所難免,但其提到的第一次為物克多錄音時邀請名角卻是事實。我們現在在充斥著大量贗品的當年的唱片中,可以找到汪笑儂、林步青以及真小桂芬(張桂芬),包括后來爭議不止的孫菊仙等少數名家的部分真品。
不能否認,這一“變異”客觀上對后來中國唱片的逐步轉型和文獻保存有一定的正面影響。雖然現存的1905年唱片中能確認的名角非常有限,但是此后約請名角的數量漸漸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哥倫比亞和物克多在中國的最后一次錄音中,真品數量都比最初有較大的提升。然而糟糕的是,這種“魚龍混雜”的出版行為,給后世留下了大量無解的文獻難題。
這種難題在“克萊姆峰”的唱片里已經存在。從現存的唱片來看,該品牌的唱片并非全是“當地清音所唱”,(47)退庵:《話匣與伶人之關系》(上),《時事新報》1928年7月29日第14版。其中有十來張是女聲,除“林黛玉”之外,片心署名都有“妓女”字樣。當時,在茶樓、書場有大量的妓女賣唱,她們在蠟筒時代就已步入“錄音圈”,比如“勞弗蠟筒”中即有大量的妓女演唱錄音——這應該是出于國外錄音團隊要求兼錄男女聲的要求,然而他們或許不完全了解:中國戲曲的聲音性別,并不取決于演員的生理性別。“克萊姆峰”的這些“妓女”唱片現在很難斷定真偽,畢竟除了沒有公認的真品可供比對之外,這些賣唱女子也不像名伶那樣有劇評、傳記等旁證可以參考,甚至都無法用演唱水準去衡量——即使唱得很糟,也可能是真品,因為妓女唱曲并非專業,跟名伶不同,其唱工高低跟名氣沒有必然的聯系。
另外,羅亮生曾指認徐乾麟經手的謀得利錄音包括筱榮祥等人的演唱:
那次錄音所邀的角色中如馮二狗,他學孫菊仙幾乎可以亂真。其他如筱榮祥、孫瑞堂以及在堂名唱老生名的阿狗(忘其姓)等也都是以唱工出名的。(48)羅亮生:《戲曲唱片史話》,李名正整理,載中國戲曲志上海卷編輯部編《上海戲曲史料薈萃》(第1輯),上海藝術研究所1986年印制,第99頁。
羅亮生先生的口述并沒有指明是哪一次錄音。從上下文的表面意思來看,似乎是指勝利唱片的那次。勝利公司的三次錄音,現在未見到完整目錄,已發現的唱片中并無筱榮祥,唯有“克萊姆峰”唱片中有11張,其中《洪羊洞》一片還有1905年再版的勝利版(49)目錄號6836。。也就是說,羅先生說的“那次錄音”很可能就是1903年蓋茨伯格的錄音;然而,“克萊姆峰”的唱片又沒有馮二狗、孫瑞堂的名字,因此也可能是把徐乾麟主導的多次錄音混為一談了。當然,還有一種更極端的可能性,即他們也被用來冒充名伶,無法辨識了。(50)根據目前掌握的造假規律看,似乎不太可能。名演員被用來造假的例子極為特殊,容另文詳述。
等到名角加入之后,這類文獻難題就更多、更復雜了。比如持續近一個世紀的“孫菊仙唱片真偽”爭議就是一樁離奇的學術公案。雙方當事人在世時,一個聲明“我孫某人從不灌片”,一個指認“我給你灌過唱片”,不對簿公堂,只打口水仗。究其癥結,就在于謀得利在“克萊姆峰”和“勝利”兩個品牌上都偽造過孫菊仙唱片,所以即使有真品,在爭論時也難以取信眾人。如此一來,在中國最大的戲曲劇種——京劇的鼎盛時代,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后三鼎甲”中,汪桂芬唱片均屬贗品,孫菊仙唱片真偽爭論不休,近一個世紀來只有譚鑫培的“七張半”百代唱片堪稱確鑿可信的聲音資料。
如今,還有當時的大量唱片處于“死無對證”的狀態。近些年,筆者根據公認的百代唱片真品,結合史料文獻等旁證,逐步辨析了一些標署名角如孫菊仙、劉永春、“小桂芬”、雙處、林步青等的唱片的真偽。與以往的研究相比,文獻數字化的普及,使早期唱片的真偽研究取得了比較大的進展,也讓我們看到了進一步研究的可能性;特別是近來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可望為驗證唱片、推進相關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但是,接觸早期唱片文獻越多,研究越深入,也越容易發現有許多早期聲音文獻是“無解”的,可供比對、參考的資料更少——涉及梆子、粵劇、潮劇等劇種。若沒有可靠的資料作為參照,人工智能恐怕也回天乏術。這不能不說是“謀得利-克萊姆峰模式”留在中國聲音文化史上的巨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