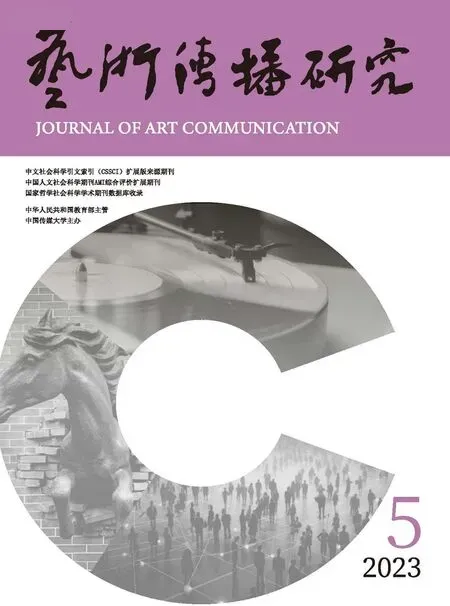習近平文化思想在藝術傳播領域的生動實踐評述
李明剛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新時代的文化建設,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內涵十分豐富、論述極為深刻,是新時代黨領導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堅定文化自信作為文化建設的前提;提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為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內容;提出“兩個結合”作為文化建設的方法;提出全球文明倡議推動人類文明發展。(1)參見陳金龍、何希賢:《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貢獻》,《光明日報》2023年10月17日第6版。這些提法都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貢獻,為中國式現代化發出了文化動員令。為深入領會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論價值和指南意義,我們不妨從考察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在我國新時代藝術生產和傳播領域的生動呈現入手。
一、“文以載道”:中國式現代化的文藝使命
文藝是中國文化陣線的重要方面,是引領廣大人民精神生活、維系中華民族認同和展現國家形象的有力工具。中國素有“文以載道”的傳統,雖然“文”的形式在不同時代各有千秋,“道”的詮釋也因時代所需而不斷演變,但無論如何,文藝在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近代以來,文學藝術與中國社會革命同步共生,因而也在革命的各個階段承載著重要的文化使命。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重要里程碑。在這篇經典文獻的指引下,誕生了優秀的小說如《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創業史》《紅巖》等,優秀的劇目如《白毛女》《洪湖赤衛隊》《江姐》《紅色娘子軍》等,極大地鼓舞了廣大人民群眾投身革命事業和新中國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則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背景下,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第二座重要里程碑。習近平總書記在這篇講話中指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長期而艱巨的偉大事業。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實現這個偉大事業,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這樣的高度認識文藝的地位和作用,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這篇講話在文藝界引發了熱烈反響,激勵廣大文藝工作者扎根基層,深入生活,感受時代脈搏,傾聽群眾心聲,為百姓發聲,為人民代言,為時代抒懷,更加堅定地把塑造新時代的中國人民形象和展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作為重要的文化使命和崇高的職業理想。自這篇重要講話發表以來,我們看到已有更多的文藝工作者通過描繪新時代的英雄群像,謳歌新時代的進步典型,書寫新時代的中國風貌,以高度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藝術化地呈現了中國人民在現代化歷程中的奮斗形象、精神圖譜和價值追求。這些優秀的藝術新作,不僅滿足了中國人民的精神需求,展現了以文化人、凝心聚魂的功能,還能遠播海外,廣受青睞——換言之,它們既是中國人民獲取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也參與了世界文化的互動和人類文明的交流互鑒,產生的文化反響無疑是積極而持久的。
擔負新時代建設文化強國的使命,需要廣大文藝工作者高揚主旋律,唱響正氣歌,努力發揚創新、進取精神,在對傳統文脈的賡續和對外來文化的吸收中探索并創造出新的文脈。“我們應當繼續尊崇傳統藝術或經典藝術,但務必注重發掘其對于當代生活的創造性能量……也就是要從無論哪一種藝術形態中激發起走向未來的當代生活所需要的創生感來。”(2)王一川:《什么樣的藝術才能承擔文化使命?》,《民族藝術研究》2018年第2期。新時代的中國文藝,需要在傳承中華文脈和對傳統經典的深度“再造”中尋找并踐行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徑。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也不僅要守護好祖國的文化遺產,更要重新發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使之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種重要文化支撐和精神動力,并由此形成獨樹一幟的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當然,強調中國風格并不是要盲目排外,而是要處理好一個“化”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貫通古今、融通中外。中國古代藝術中就能見到不少外來文化的影子:音樂方面如龜茲樂、高麗樂、天竺樂,繪畫方面如王維,雕塑方面如楊慧之等。這也讓筆者想起被譽為“民族魂”的魯迅先生在談到其創作的起點時,自述“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3)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載《魯迅全集》第5卷,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53頁。。事實上,通過考察魯迅林林總總的各類藏書,我們可以看出他對外國文學和世界文明的深度關注和廣泛吸納,并為他廣博的興趣和駁雜的知識結構所驚嘆,但是,當我們走進他的文本,卻又很難看得出特定某位作家的影子。究其原因,就在于魯迅具有一種超凡的“化”的能力,用劉思源的話說,就是魯迅有一種強大的“暗功夫”(4)參見孫郁:《魯迅的暗功夫》,《文藝爭鳴》2015年第5期。,這種功夫使他形成了一種獨具民族特色和現代思想的藝術風格。“五四”以后成長起來的作家,無論是左翼還是“現代派”,其早期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歐化”色彩,但到了歐陽山的《高干大》、黃谷柳的《蝦球傳》、孫犁的《荷花淀》、何其芳的《星火集》等,“西方影子”就已漸漸淡化、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頗有中國現實色彩的民族化的藝術形式和中國化的藝術氣質。因此說,在古今中外的匯通中實現新的文藝價值,實現審美以及敘事體系的轉換是完全可行的。進入新時代以來,也確有一系列文藝佳作借助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傳播技術,講述了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人民的新故事,充分展示中國文藝在“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上的使命擔當,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二、“新文脈”的探索:從“經典”到“紅色”
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需要物質建設和精神力量的雙重驅動。關于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在五千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我們要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5)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11月30日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參見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59-260頁。
文藝能夠為一個時代貢獻豐富的精神力量。在對許多歷史階段的回望中,我們皆能見到文藝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與西方文化相比,中華文化具有顯著的連續性,從詩經、楚辭、漢賦,到唐詩、宋詞直至近現代文學,可謂高峰迭起、精品紛呈。中華文脈延綿不絕,展現出中華文化的雄渾底蘊——這些寶貴遺產都應該成為而且能夠成為新時代藝術創作的精神資源。限于篇幅,這里僅重點圍繞“五四”以來的“新文脈”談談筆者的感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對五四精神時代價值的研究,深入揭示新時代發揚五四精神的意義和要求。要結合五四運動以來一百年的歷史,深入研究五四運動倡導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思想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意義,把研究五四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統一起來,同研究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統一起來,使之成為激勵人民奮勇前進的精神力量。”(6)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4月19日主持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參見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頁。在響應這一號召的作品中,電視劇《覺醒年代》以精心設計的藝術形式,通過生動的人物形象和歷史敘事,對“中國為什么要選擇馬克思主義”這個重大問題的回答作了尤為鮮活的展現。該劇通過對歷史的藝術重現,意趣橫生地展露了“五四”先驅和中國共產黨的先行者當年的英姿與風采,達成了歷史真實、藝術真實與時代精神的充分契合。劇中蔡元培的沉穩、寬厚,胡適的務實、溫和,李大釗的憨厚、樸實,還有陳獨秀的魄力與激烈個性,不僅讓觀眾感受到文化先驅或革命先驅強烈的信仰與人格的力量,也展現了他們人性化和人情味的一面,深深地觸動觀眾的心靈。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作為革命家的救世情懷,陳延年、陳喬年、鄧中夏作為革命青年的熱忱信念,陳獨秀父子三人“愛恨交加”的親情,李大釗、趙紉蘭真摯深沉的愛情,《新青年》同人并肩作戰的曠世情誼……《覺醒年代》將這些極富張力和個性的復雜形象生動地進行了呈現。劇中的革命領袖和文化名人形象突破以往的“理念性”處理手法,變成了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既嚴肅又活潑的“凡夫俗子”。他們既有作為革命者的舍生忘死,亦有作為亂世普通人的滄桑境遇。這樣的處理,不僅打破了青年受眾對早期文學家和革命家的刻板印象,讓他們“親密”接觸了課本之外那更具歷史深度和人性溫度的開路人形象,更會在很大程度上正向影響這一代青年對歷史的認知,有效地激發他們對時代、青春和信仰的積極思考。遙遠的“五四新青年”的信仰與奮斗故事,在一個世紀之后再次實現了與青年心理的深度聯結,由此亦足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闡述的感召力與穿透力。《覺醒年代》可謂中國式宏大敘事的一次“藝術覺醒”,難怪有評論者表示:“傳統與現代、啟蒙與革命、政治與文化、學術自由與民族興亡、人道主義與階級斗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自由解放與民主富強……所有這些一百多年來纏繞著中國人的問題,都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了深入探討。雖然并非所有的疑問都得到了最終解答,但它們對觀眾思想的沖擊和激蕩,依然體現了電視劇穿透百年的思想深度和強度。”(7)尹鴻、楊慧:《歷史與美學的統一:重大歷史題材創作方法論探索——以〈覺醒年代〉為例》,《中國電視》2021年第6期。
黨的十八大以來,還有越來越多的改編自紅色經典的影視作品以其富有創造力的形式和充滿時代感的審美意蘊,成為激勵人民奮勇前進的精神力量。紅色經典亦有其不容置疑的現代性,因為現代性本身就是一個流動性很強的概念。“紅色經典的確立取決于結構性的元素,如強烈的意識形態功能需求和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意識的現代轉換……當現代性發展選擇了激進的革命方向時,‘紅色經典’的言說形式和表述結構(就)與現代性敘事具有了同源性。”(8)伍丹、楊經建:《“紅色經典”與中國式現代性建構》,《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從《永不消逝的電波》等作品的傳播效果來看,紅色經典的內在元素顯然為其在新時代被“重新發現”并得到新的傳播提供了合理性。
在古代文脈方面,從近年來廣受贊譽的《中國詩詞大會》《國家寶藏》《經典詠流傳》《典籍里的中國》等文化類綜藝節目,以及昆曲《瞿秋白》、京劇《安國夫人》等藝術作品來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兩個結合”的思想無疑是探索中華傳統文化在新時代轉化之方法的最高指南。新時代的中國藝術生產應立足民族傳統文化,主動吸納當代的藝術手段和傳播技術,通過充滿趣味性、知識性、人生理想和情懷的策劃去演繹中國精神,展示富有中華民族性格的審美眼光與審美追求,讓充滿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的傳統文化藝術元素在新時代綻放新的光芒,從而獲得持久的活力和價值。
三、匯通古今:中國故事與中華氣象
圍繞如何引導人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在宣傳和闡釋中國特色時的“四個講清楚”,其中就包括“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9)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講話的要點,參見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頁。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包含許多世界一流的文學和藝術經典,這種深厚的文化積淀理應成為新時代文藝創作的珍貴源泉。
新時代的傳統,應該帶有新時代的特質,這種特質應該能體現在兼具文明主體性和交互性的新的民族藝術形式之中。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如果一個民族被視為是一個‘文明體’,乃至革命的‘文明體’的話,這也就意味著它必須是持續變化、不斷自我創造、不斷再形成的;也就是說,盡管它有自己的內核,但是這個內核必須是不斷生成的,其中包含了各種各樣的要素,而不能被簡單還原為單一要素,如此它才能夠擁有不斷擴大、包容、生生不息的力量。”(10)參見汪暉、賀桂梅、毛尖:《民族形式與革命的“文明”論》,《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年第2期。這方面,我們或許可以從歌德對中國傳統的開放態度中獲得某種參考。在19世紀20年代提出“世界文學”概念的歌德,對中國文藝作品獨有的風格尤為欣賞,不僅讀過小說和雜劇如《花箋記》《風月好逑傳》《玉嬌梨》《趙氏孤兒》,甚至還親自翻譯了部分宮闈詩。在他看來,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與西方人并無差異,讓他感到親切,但又表現得比西方人“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沒有強烈的情欲和飛騰動蕩的詩興”。歌德在中國文學作品中感受到與他的作品如《赫爾曼與竇綠臺》和英國小說的類似之處,他特別贊賞中國古典藝術天人合一的觀念,以及詩情畫意、含蓄蘊藉的表達和平易純良的道德倫理。他當然也知道這些傳奇在中國遠非一流的作品,而且在西方的“遠祖還生活在野森林的時代就有這類作品了”,但仍強調“對其它(他)一切文學我們都應只用歷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還有可取之處,就把它吸收過來”。(11)參見[德]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114頁。歌德的話讓我們又一次確信,文藝創作者不僅要注重民族性,更要形成匯通中外古今的世界視野。
同時,雖然藝術在展示和探索人性方面是世界性的,但藝術作品的風格卻天然帶有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唐弢先生曾以魯迅和老舍的作品為例,將中國現代文學的民族風格概括為三個重要特征:風俗畫、含蓄、傳神。(12)參見唐弢:《西方影響與民族風格——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一個輪廓》,《文藝研究》1982年第6期。這三個特點不僅適用于現代文學的早期,在近年來“現象級”的藝術作品中也有廣泛運用。仍以《覺醒年代》為例,劇中蔡元培風雪中的“三顧茅廬”、《新青年》“三駕馬車”在泥濘小道上的搭肩行走、毛澤東的雨中奔跑……這些畫面所用臺詞很少,主要借助含蓄的意境,傳神地表現先驅們的精神風貌,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再如《長安三萬里》,從詩詞選用到畫面設計,從形象的建構到氣質的呈現,從情景設置到性格塑造,從詩人個體命運到國家興衰,從私人情誼到家國情懷,由表及里,絲絲入扣,讓人仿佛身臨其境。故事雖然發生在唐代,但聯結了現代的情緒——通過藝術性的創造,讓傳統文脈在當代延續和發揚。該片最終在多個角度實現了突破,比如突破了取材的局限,將視野從神話傳說轉移到古典詩詞這類以往較少被觸及的嚴肅文學,再如突破了舊有敘事方式,以動漫的形式探尋盛唐的輝煌歷史。它將享譽世界的詩人的人生與國家命運相聯系,將優美的中國古典詩詞與飽含民族風格和地方韻味的風俗畫面相結合,立體地展現了詩畫典籍中那種獨一無二的中國文化魅力。它吸收了中國美學和藝術理論的寶貴遺產,讓觀眾了解到熟悉的中國詩人和詩詞背后那遙遠的歷史和“陌生”的故事,不僅可以喚起觀眾對博大精深、有著輝煌歷史的中華文化的自豪感和認同感,還可以極大地激發觀眾對其的熱愛,乃至主動再傳播的意愿。該片在形象設計上也有所突破,從多個方面融入了中華美學精神,造型上著力展現“時代精神”與“中國氣派”,特別是人物造型上采用唐俑特有的雄壯身型,豐神俊朗、瀟灑飄逸又剛健有加,傳神地描繪出了盛唐景象和中華氣韻,對西方某些影視作品“病態化”“猥瑣化”“陰暗化”展示中國人形象的做法也無疑是一次有力的藝術回應。
新時代的內外環境的巨大變化,召喚藝術的創造性表達。在以短視頻為代表的碎片化視聽的“包圍”中,以傳統詩詞學作為線索貫穿作品的《長安三萬里》之所以取得如此良好的傳播效果,根子上還是在于將中華傳統文化與觀眾的成長環境、生活習慣、欣賞趣味、情感訴求、價值觀念進行了深度契合——這是一種對中華美學精神的發揚和對傳統文化的深度“再造”。中國的“00后”“10后”成長于新媒體的浪潮中,這個背景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文化觀念——其文化趣味較之前輩更傾向于諸如游戲、“國漫”、“古風”、“國潮”等方面的“泛文化”類作品。事實證明,《長安三萬里》上映后,掀起了“李白熱”“詩詞熱”,“國風”服飾和相關文旅活動也繼續升溫。此類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帶著觀眾走進歷史,由此喚起或強化民族意識和對本國文化的尊重、信賴與熱愛,傳遞對現實生活的啟發和對未來發展的精神力量。這種烙上了中國符碼的藝術表達,雖是古代題材也不妨礙闡釋時代精神,其文化育人的效果不可小覷。可見,在了解受眾的精神追求潛質,以其喜聞樂見的藝術手法展現中華文化的魅力方面,文藝工作者顯然需要繼續深入探索。
中國藝術歸根結底要服務于中國的現實生活,所以對中國故事的講述還應該善于表達社會價值訴求。在經歷了幾次文化“斷層”之后,傳統的和諧仁愛觀念的影響力一度減弱,各種西方思潮伴隨著市場機制涌入,強烈沖擊了中國人的家庭價值觀念和家庭倫理觀念,鄉土和親情文化也趨于消逝,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式的家庭思維亟待重新建構,這就需要我們把視野轉回東方,帶著當代文明卓越的一面回到我們自身的優秀傳統中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家風”的重要性,這一點在文學藝術中得到了積極的回應。比如,梁曉聲的小說《人世間》以平民的視角,記錄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變遷和發展,以周家三代曲折而堅韌的生存史,展示了知青下鄉、工人南下、恢復高考、國企改革、“下海”潮、留學潮等時代風云中個體的際遇和選擇,喚起了至少一代人的集體記憶。該作品中,肖國慶患病臥軌時“六小君子”仗義出手扶助其女兒上學,鄭娟變賣家產幫助友人,周秉昆亦展現其責任感與孝心……這些具有“自然化”的感性的民眾形象悄然叩問著許多人的內心。這些藝術形象并非擁有完美人格,但骨子里有著傳統道義的精髓,體現了崇善向美的情義擔當和家國情懷,這無疑是當今時代特別需要的。正如評論家所指出的:“《人世間》呈現出中國式心性現實主義美學范式的幾方面表現:真善交融、典型傳神、地緣化育和時勢造人、褒貶皆有、流溯風格。這對當前和今后各文藝門類敘事類文藝創作將起到示范作用。”(13)王一川:《中國式心性現實主義范式的成熟道路——兼以〈人世間〉為個案》,《中國文藝評論》2022年第4期。該作品改編成電視劇后,亦受到了全平臺和全年齡層的歡迎,它對中華傳統親情倫理和家庭責任的藝術化歌頌,對一些掙扎在倫理危機中的觀眾起到了潤物無聲的導向作用。另外,該劇在港澳臺地區和海外觀眾當中也引發了一定的共鳴,甚至被迪士尼買下海外版權,這也佐證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今日世界的倫理道德重構中能夠發揮特定的作用。要之,從《人世間》等作品的生產和傳播來看,中國現代文藝在五四時期和20世紀80年代兩次大規模地“以西方為師”之后,已經可喜地來到了一個創造和開拓的新起點。從人物構型到精神氣質,從審美體系到價值觀念,從心性智慧到美學精神,當下的中國藝術正在努力實現與中國古典文脈的多元接通。我們在舞劇《天路》《敦煌》《只此青綠》等當中也能看到這種衷心的藝術追求,限于篇幅,不再展開。
四、走向世界:從中國形象到中國智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工作者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讓外國民眾通過欣賞中國作家藝術家的作品來深化對中國的認識、增進對中國的了解。要向世界宣傳推介我國優秀文化藝術,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理解。”(14)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參見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105頁。“展形象,就是要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15)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8月21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講話的要點,參見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39-340頁。“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16)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12月11日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參見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159頁。筆者由此感悟到,講好中國故事已成為關系國家前途和人類命運的大事之一。當前西方影視作品中仍可見刻意對中國形象予以妖魔化和奇觀化的做法;面對這種老套且不公的陋象,中國必須要給出文藝上的回應,不僅要讓世界知道 “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17)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參見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28頁。。當然,我們也很高興地看到,中國藝術以此為目標,在展示自我的本來形象方面進行了積極的實踐。僅以影視領域來看,近十年來對中國英雄群像的塑造便頗有代表性——既有革命戰爭和當代武裝行動中的行伍英雄(如《智取威虎山》《戰狼》《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長津湖》等),也有拯救人類的未來英雄(如《流浪地球》《三體》等),更有來自各個行業的“身邊”英雄(如《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烈火英雄》《中國機長》《緊急救援》《中國醫生》等)。這些英雄群像“真實、鮮活、生動,傳遞著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的信仰之光”(18)丁亞平:《英雄與人民:中國電影的形象塑造和歷史觀念的建構》,《電影藝術》2021年第4期。,其中展示出的獨特的信仰、倫理和文化,有別于以往好萊塢式的英雄形象,其體現出的救世情懷、家國理想、奉獻精神,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了強大的精神能量,也積極參與塑造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社會治理模式近年來也得到了生動的藝術呈現,例子有扶貧題材電視劇《山海情》《一個都不能少》,環保題材電視劇《我的金山銀山》《綠水青山帶笑顏》,少數民族地區發展題材電視劇《楓葉紅了》《索瑪花開》《一步千年》等。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涉及少數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除了運用常見的體裁,還吸納了少數民族群眾喜聞樂見的歌舞形式——這種跨媒介的敘事和傳播鮮活地反映了新時代中國風土人情的存續和發展,描繪出民間社會生活的新姿態,從而廣受歡迎。同時,這類作品中帶有鮮明地方色彩的、樸素又不失哲理的關于家園建設的人物對白,不僅展現了中華兒女熱愛家園、吃苦耐勞的傳統品質和改天換地的決心與勇氣,還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被視為一種以藝術家熟悉的貼近日常生活的敘述方式,用人民的口吻進行的對“中國道路”和“中國未來”的間接而堅定的表達。
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我們也看到,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本就有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中國也在不斷追求文明的交流互鑒。以文學為例,五千年的中國文學史本身就建立在與域外交流對話的基礎之上,從而海納百川,走向輝煌。近代中國積貧積弱,文學也曾經有過低潮,此后遂經歷了“拿來主義”時期,一度顯現“歐化”色彩,但這種色彩最終又逐步淡化和消褪,取而代之的是富有中國現實色彩和民族風格的文學形態。中國文學在從過去“仰視”外部的狀態逐步回到“平視”世界文學的位置后,也為世界文學的發展繁榮增添著越來越豐沛的力量。一批“50后”“60后”作家率先走向世界,“70后”“80后”的創作也越來越受到海外讀者關注,中國作家的作品正在不斷被翻譯、輸出,獲得了較好的國際評價,更有《流浪地球》《三體》等藝術精品在海外文壇閃亮登場。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風起云涌,中國除了繼續在國際舞臺上扮演重要的政治和經濟角色之外,更迫切需要提升文化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這就需要我們盡可能發揚文化的主體性,鼓勵自己的文藝成果更多地參與世界層面的交流互動,進而更好地提供解決現實和未來問題的中國方案,展示中國文化的智慧與魅力。
與西方借助資本力量對文化生產和傳播予以壟斷帶來的表面強勢效果相比,我國還須加強文化傳播的共同體建設。仍以文學領域為例,有學者指出:“科幻文化不應成為少數國家或少數群體的幻想特權,而應是多元主體能用以表達態度、影響他者和促成對話的工具。它不能成為優勢國家和優勢階層的‘后花園’,而應該是向所有世界公民敞開的‘公共領域’;它也絕不能成為世界政治經濟結構性不平等的延伸,而應當反過來去矯正這種全面失衡的格局;它不應是各自為營的分散格局,而應當是匯聚共同關切和共同智慧的‘幻想共同體’。”(19)吳福仲、張錚、林天強:《誰在定義未來——被壟斷的科幻文化與“未來定義權”的提出》,《南京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基于此,中國藝術應該以也正在以積極的姿態參與更加公正平等的國際文化秩序的構建。《三體》的成功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僅在于獲得“雨果獎”,更在于開啟了中國文學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注和對人類生存發展的探索,其對人類處境和生存的深切關懷與深度叩問彰顯的正是中國智慧。可以說,《三體》不僅是科幻文學作品參與世界文明對話的榜樣,也是藝術作品發力于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典型案例。
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藝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洞察時代風云,把握時代大勢,站在人類發展前沿,積極探索關系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為應對當今世界面臨的全球性挑戰、解決人類面臨的共性問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20)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4月23日主持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參見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15頁。中國不僅要在世界藝術版圖中回到應有的位置,更要在世界文明的交流和開拓上發揮應有的作用,彰顯屬于“中國文化”這個厚重稱呼的意義和價值——這些都需要文化創造與傳播力量的不斷加強。從全球文化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包括科幻藝術在內的中國文化藝術產業也需要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切實做好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通過傳播共同體的構建,提升自身的競爭力和話語權,進而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出去”,為人類文明的健康和永續發展做出更加卓越的貢獻,立下更加耀眼的功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