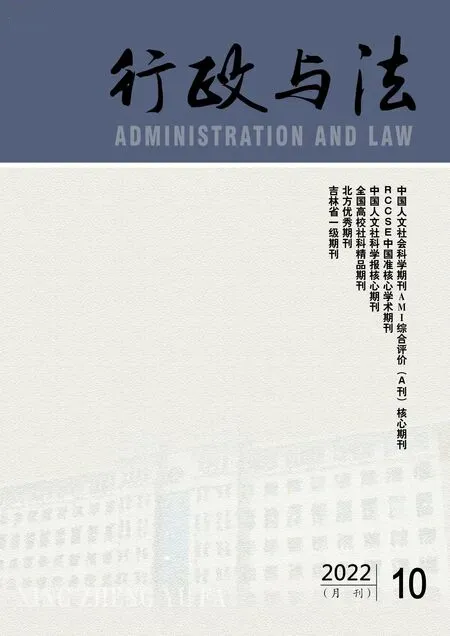風險管理視角下預防性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重大風險認定的審視
2022-11-01 06:55:36何倫鳳
行政與法
2022年10期
關鍵詞:環境
□ 何倫鳳,曾 睿
(福建農林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2)
伴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風險負外部性特征日趨明顯,尤其體現在生態環境領域。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的目標,這喻示著我國生態環境法治需實現從后果控制到風險預防、從環境管制到生態善治的轉型。2015年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一條規定了預防性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突破了“無損害即無救濟”訴訟救濟理念桎梏,使我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邁出環境保護的前瞻性步伐。但因看到,目前我國預防性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實踐成效尚不明顯,總體面臨著“制度空置與告訴無門并存,糾紛處理與風險不減俱在”的尷尬處境。在學界,有學者分別從預防性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預防性司法救濟、程序規則、責任適用規則、責任承擔方式等方面進行詳細論述,但對“重大風險”認定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也有學者從規范闡釋的視角提出了預防性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風險的認定路徑;還有學者從技術規范、程序控制的視角提出了預防性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風險”的解決路徑;亦有學者從舉證規則的視角對“重大風險”的證明簡化提供了合理進路。實務中,由于環境風險具有不確定性、潛伏性、非現實損害性等特點,“重大風險”認定仍呈現出明顯的“重大風險”意涵不明、證明標準模糊、舉證責任有待明確、認定主體專業性不足等問題,這已成為掣肘我國預防性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發展的主要原因。……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老年保健(2021年12期)2021-08-24 03:30:40
中國傳媒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1年1期)2021-06-09 08:43:00
中國生殖健康(2020年6期)2020-02-01 06:28:50
新世紀智能(英語備考)(2019年12期)2020-01-13 06:07:18
瘋狂英語·新策略(2019年9期)2019-10-17 01:51:34
中國生殖健康(2019年11期)2019-01-07 01:28:02
中國生殖健康(2018年6期)2018-11-06 07:09:28
濰坊學院學報(2017年2期)2017-04-20 08:44:31
中國環境監察(2016年5期)2016-10-24 05:25:52
中國商論(2016年33期)2016-03-01 01:5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