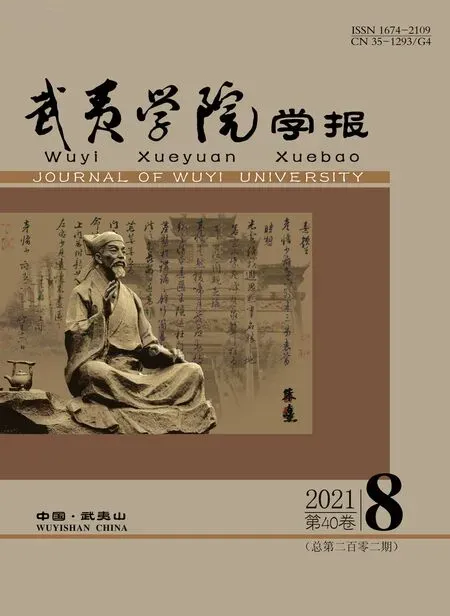就業質量對農民工生活幸福感的影響
——基于泉州的調查數據
林 曄,周畢芬
(福建農林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2)
農民工群體作為外來人口參與城市建設與發展的同時,也在逐步融入務工所在城市,成為城市居民的一員,此外近年來農民工群體開始出現家庭化遷移的趨勢,進城農民工群體不斷膨脹,因此對農民工群體與所在城市的適應性與社會融合程度的研究成為了針對農民工群體的研究中的熱門,而生活幸福感也是衡量農民工群體社會融合水平與市民化程度,以及農民工群體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但農民工群體生活幸福感的影響因素也是千差萬別。本文從就業質量視角出發,研究就業質量對農民工生活幸福感的影響,并從就業方面提升農民工的生活幸福感,促進農民工更好地適應離鄉務工生活提出政策建議。
一、文獻綜述及研究假設
(一)文獻綜述
生活幸福感是衡量農民工群體社會融合水平與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指標,主觀幸福感與生活幸福感屬于詞義相同的不同表達,許多學者也將生活滿意度與主觀幸福感劃為等同[2-3],研究中兩者可以互為替代變量[4],本文中提及的生活幸福感、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為同一概念。學者們從各個角度考慮了農民工生活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包括未來預期收入[5]、收入與工作時間[6]、社會資本[7-8]等。吳奇峰等[9]的研究表明隨著市場化的深入,社會資本對農民工生活幸福感的積極影響沒有改變。此外生活幸福感也是衡量農民工心理健康的一項標準,盧海陽等[10]總結了2006年至2016年國內外關于城鄉流動人口健康狀況的研究情況,發現國內外對農民工健康研究的主要方向為農民工健康狀況的現狀以及測度農民工健康狀況的指標體系、影響因素與健康后果,其中生活滿意度是國內學者衡量農民工心理健康的主要指標。程菲等[11]從消極情緒和包含生活滿意度在內的積極情緒兩個維度評估了農民工的心理健康狀況,并分析了其決定因素,包括人口因素,移民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和文化因素,此外還發現經濟狀況和文化適應的改善對農民工生活幸福感無負向影響。龔晶等[12]認為,社會保障制度對農民工生活滿意度的提高作用并不明顯,相反,由于費用種類的增加,農民工經濟負擔增加。
在就業質量的研究方面,主要以工作滿意度、工資水平、單位福利等作為衡量指標。王瓊等[13]認為,自歐盟發布《2001年歐洲就業報告》并提出就業質量概念后,學界對就業質量的測量指標達成了以下共識:第一個維度是收入是否充足,即就業者的收入是否能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第二個維度則是工作穩定性,穩定的工作才能帶來穩定的收入,而與用人單位是否簽訂勞動合同以及勞動期限可視作是否擁有穩定工作的一項指標;第三個維度是工作相關的社會保障,即單位代繳的各種社會保險與住房公積金;第四個維度則是工作對人心理上的影響,比如超時工作會給勞動者身心帶來巨大的傷害。但就業質量的衡量也不僅限于以上維度,陳萬明等[14]認為就業質量的評價指標可以包含工作環境、工作條件、工作激勵、勞動關系與個人情感。如何提升農民工就業質量也是學界的熱門研究,有從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等角度提升農民工就業質量的研究,鄧睿[15]研究了工會身份對農民工就業質量的影響,結果表明,成為工會的一員有助于增加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增加簽訂長期固定勞動合同的可能性,并對其參加城市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產生積極影響。
(二)研究假設
1.收入水平會正向影響農民工生活幸福感
農民工外出務工的最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穩定的收入來源,但農民工的學歷普遍不高,因此大多數農民工會選擇體力勞動的工作,此類工作一般需要大量的體力與工作時間,農民工的平均工作時間遠遠超過國家《勞動合同法》規定的標準,而業余生活比較單調[16]。農民工大部分時間都處于工作狀態中,工作帶給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感受也是最強烈的,較多的工作時間和單調的業余生活表明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和就業環境并不樂觀。農民工需要工作所獲得的收入維持個人或家庭的開支,收入水平會直接影響農民工個人或家庭的生活質量,因此收入水平會顯著影響農民工對生活的主觀評價。
2.工作穩定性會正向影響農民工生活幸福感
需要能維持生計并且長久的收入,就需要一份穩定的工作,而簽訂勞動合同則保證了農民工在合同期內的勞動權益,幫助農民工與雇傭單位建立長期勞動關系。卿石松等[17]的研究發現勞務派遣和零散工就業人員的幸福感低于受雇于固定雇主的就業人員,但也有研究表明簽訂勞動合同對農民工的生活幸福感具有負面影響[18]。國內外有學者認為,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代表了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間穩定的勞動關系,以及長期的合同期限保證了勞動者收入的穩定[13,19],保障了農民工的勞動權利,使農民工獲得了穩定的工作與收入來源,減輕了失業的焦慮,因此本文使用“近2年內是否簽訂過新的勞動合同”作為工作穩定性的指標,并假設工作穩定性對生活幸福感應有正向影響。
3.社會保障會負向影響農民工生活幸福感
1.3 差異表達基因篩選 利用R軟件limma包[10]篩選差異表達基因,得到腎透明細胞癌與正常腎組織間差異表達基因用于共表達網絡的構建,篩選條件為:FDR<0.05,| log2 FC|≥1.0,其中FC為fold change即兩組間差異表達倍數。
除了支付薪水,用人單位還需依法為農民工繳納各種社會保險,使外來務工者能擁有與城鎮本地職工相當的社會保障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但各項社會保險的繳納金額會占用一部分個人所得收入,而農民工群體往往對社會保險的作用缺少準確的認識,認為多種社會保險的繳納占用了太多的收入,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社會保障會負向影響農民工生活幸福感。
4.負面的工作體驗會對農民工的生活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
負面的工作體驗包括會給農民工在工作中遇到的帶來心理壓力的事件,例如長時間工作、拖欠工資以及在工作或是日常生活場合遇到的歧視。工資與整體工作滿意度是正相關關系[20],而拖欠工資會使農民工面臨經濟困難,雖然中等收入與高收入者之間生活幸福感的差異并不明顯[21],但農民工階層的收入效益還未達到遞減的水平,且低收入者生活幸福感明顯較低。此外近年來出現了農民工家庭化遷移趨勢,家庭主要勞動力的收入是家庭經濟狀況的最重要的支撐,工資拖欠會加重農民工的生活負擔,尤其是缺少存款的外來務工者將會難以為繼。同時強制加班相當于延長了工作時間,長時間的工作容易使人產生厭倦與疲憊情緒,這種情緒容易被帶入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成為心理壓力。工作歧視也會對農民工的心理健康帶來嚴重壓力,被歧視個體會因此降低對自我的評價,失去信心,甚至降低定居意愿,因此本文假設:工資拖欠、強制加班與工作歧視這類負面工作體驗會對農民工的生活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
二、數據來源、模型構建與變量設定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自課題組于2017年在福建地區開展的針對進城農民工的就業與市民化調研。通過隨機抽樣的方法,對福建地區的農民工群體發放問卷。泉州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典型城市之一,全市范圍內中小企業居多,民營企業占有較大份額是其產業特點,從而吸引了很多省內外的勞動者前來務工,農民工群體數量龐大,研究泉州地區農民工群體的調研數據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選用在泉州地區回收的382份有效問卷數據。
(二)模型構建
因被解釋變量為有序分類變量,采用有序probit回歸進行估計,遂建立數學模型:

其中happyi代表被解釋變量生活幸福感,i代表個體樣本,incomei為個體樣本的收入水平變量,stabi為個體樣本的工作穩定性變量,sociali為個體樣本的社會保障變量,nagai為個體樣本的工作負面影響變量,Xi為個體樣本的各項控制變量,β0、β1、β2、β3、β4為系數,εi為誤差項。
(三)變量設定
本文的變量設定如表1所示,被解釋變量為生活幸福感,生活幸福感評價由1-5個等級組成,分別為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受訪者根據自身情況對照調查問卷對自己的生活幸福感進行自評,其中“1”為“非常不幸福”,“2”為“不幸福”,“3”為“一般”,“4”為“幸福”,“5”為“非常幸福”。

表1 變量設定與描述統計Tab.1 Variable setting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就業質量的指標分為四個維度:收入水平、工作穩定性、社會保障與工作負面影響。收入水平的代表變量為月均收入以及工資收入的自評滿意度,月均收入取對數納入模型,而工資收入滿意度與生活幸福感的分級相同,同樣分為5個等級。工作穩定性的代表變量為“近2年內是否簽訂過新的勞動合同”,“0”為“沒有簽訂”,“1”為“近2年內有簽訂過新的勞動合同”。社會保障維度包含6個變量: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住房補貼,均為0-1變量,“0”代表“單位沒有為其辦理”,“1”代表“單位有為其辦理”。工作負面影響包含工資拖欠、強迫加班、工作歧視,均用0-1變量表達,“0”為“不存在此現象”,“1”為“存在此現象”。控制變量為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性別為0-1變量,“0”表示“女性”,“1”表示“男性”,年齡為連續變量,文化程度分為5個等級,從低到高分別是:“小學及其以下”“初中”“高中(中專)”“大專”“本科及以上”,婚姻狀況“0”為“未婚”,“1”為“已婚”。
三、實證結果分析
模型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模型1到模型4分別單獨檢驗了收入水平、工作穩定性、社會保障、工作負面影響四個維度對生活幸福感的影響,模型5檢驗了在同一模型中就業質量的4個維度對生活幸福感的影響,5個模型均加入了控制變量。

表2 有序probit回歸結果Tab.2 Ordered probit regression results
回歸結果表明,工資收入滿意度無論在模型1還是模型5中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在1%的水平上顯著,系數為正(已進行過多重共線性檢驗,vif值低于2),但月收入對數卻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收入對農民工生活幸福感的正向影響的假設得到了證實,但此影響與農民工對工資收入的主觀評價息息相關。農民工的收入直接與其生活質量掛鉤,因此收入是否充足對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影響顯著,但農民工進城務工期間其消費水平相比農村必然有所提高,但由于個體收入分配到生活各方面支出的差異,收入的多少并不能簡單影響農民工的生活幸福感,反而是農民工對工資收入評價的影響更為顯著。相對收入對農民工生活幸福感的影響也非常顯著,但系數較小[22]。農民工進城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就業機會的獲得,其次才是絕對收入的追求[23]。但是,隨著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往往偏向于高技能勞動力,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出現了一些挑戰。中國的產業升級已經領先于勞動力的技能水平,但是目前的勞動力結構表明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仍然在勞動密集型產業[24]。而城市發展不僅需要高技能勞動力,低技能勞動力也在城市建設與發展中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例如作為第三產業逐步發展壯大的服務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二者具有互補性[25]。如果城市只偏向高技能勞動力而抑制低技能勞動力,將不利于消費性服務業的供給,影響城市競爭力。因此,城市在推進產業升級的同時,更應該考慮現有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對低技能勞動力群體的就業機會與收入水平有更多的保障措施。
工作穩定性的代表變量在模型2與模型5中均未顯著,工作穩定性對農民工生活幸福感的影響的假設沒能通過檢驗。農民工因自身條件限制對工作缺乏選擇的余地,并且缺少勞動合同對自身權益保障的認識,在樣本中僅54%的受訪對象與用人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而在更換工作的過程中往往沒有簽訂新的勞動合同,因此工作穩定性并未對其主觀幸福感造成影響。對農民工基本權利的保障,以及普及勞動合同對勞動者的重要性依然任重道遠。
根據模型3與模型5的結果,社會保障維度中的醫療保險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在1%的水平上顯著,工傷保險在模型3中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系數為負,而其他社會保險包括住房補貼的檢驗結果并不顯著,甚至多數出現系數為負的結果。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減輕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就醫負擔,使得疾病與傷痛不會成為壓垮擁有醫療保險的農民工的重擔,但工傷保險以及其他社會保障在模型5中系數多為負數,且顯著性結果均未通過,說明社會保障雖然能夠發揮為農民工提供生活保障的作用,但種類繁多的社會保障反而令農民工感到生活上的負擔,并不能提升生活幸福感,側面印證了龔晶等[12]的研究結論:社會保障種類的增多對農民工身心健康的提升作用不大,反而會因為費用種類繁多而造成農民工的經濟負擔產生更大的壓力。
工作負面影響維度中,強迫加班與拖欠工資均未通過檢驗,只有工作歧視在模型4與模型5中在1%水平上顯著,其系數為負。在工作與生活中遇到的職業歧視會嚴重打擊農民工的自尊,影響對其的自我評價。工作負面影響的假設在實驗中未得到完全支持,僅工作歧視一項在結果中表示顯著影響,結果表明相比工資拖欠與強迫加班,工作歧視對農民工生活幸福感自評的負向影響更顯著。工作干擾家庭與工作績效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與離職傾向存在顯著的正相關[26],強迫加班相當于延長工時,減少了工作者的非工作生活時間,使其難以通過休息恢復工作時消耗的體力,并且減少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的參與,但農民工群體工作時間過長是普遍現象,或許在主觀意識上已接受過長的工作時間為一種常態而不是異常,因此未影響其生活幸福感自評。拖欠工資的不顯著結果其原因可能是農民工家庭中的收入來源不唯一,家庭中存在復數的工作人口(例如配偶、子女),雖然工資拖欠會對家庭收入產生影響,但因為不是只有一人參與工作,收入來源不至于斷絕,因此拖欠工資對生活幸福感的影響并不顯著。
四、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以下結論:首先,收入水平會正向影響農民工的生活幸福感,相比具體的工資數目,對工資收入的滿意度是影響農民工生活幸福感的關鍵因素;其次,工作穩定性并不影響農民工生活幸福感,而社會保障維度中,僅醫療保險能提升農民工的生活幸福感;最后,工作負面影響維度中僅工作歧視對生活幸福感有顯著負面影響。
根據研究結論,本文認為,政府應該著力做好為各技能水平農民工提供就業機會的同時,繼續保障和提高低技能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同勞動合同一樣,社會保障也是政府必須保護的農民工基本權利,目前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依然不甚理想,政府必須保護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簽訂正規勞動合同的權利,用人單位代繳的各類社會保險也不能隨意停繳,因此政府需要加強對用人單位的監管,堅決禁止用人單位強迫加班和拖欠工資以及其他違反《勞動合同法》的行為,并更多地向農民工群體宣傳勞動合同與社會保障在就業與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農民工群體對此類權益的重視程度。而對于農民工在工作與生活中遇到的歧視,建議政府積極宣傳農民工對城市的貢獻,減少農民工在就業與生活中受到的職業歧視,提升農民工生活幸福感,使其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