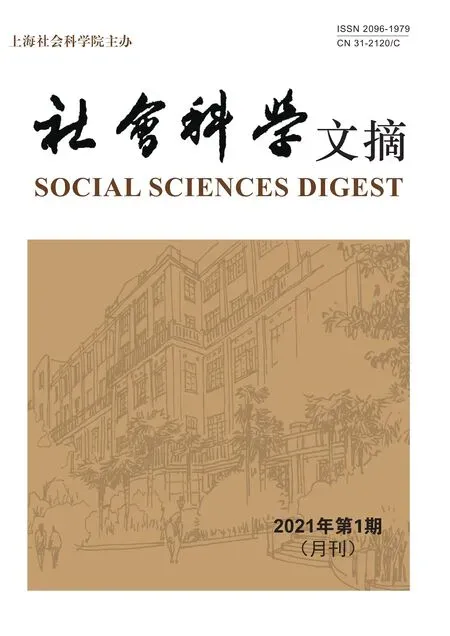作為紀念物的數字移動媒介:德布雷視野下的媒介與遺產傳承
中國中小城市正經歷著快速的城市化建設和居民的頻繁移動,城市遺產保護的議題也隨之日漸升溫。“遺產熱”現象常被解釋為新媒介沖擊下對地方的應激保護。這種對“遺產熱”的解釋預設了穩定不變的地方與媒介技術及其所帶來的變動新世界的對立,將信息的跨地域傳播當作媒介的唯一向度。德布雷的媒介學提醒我們留意媒介的時間傳承維度,指出媒介在文明傳承中的意義。這一審視媒介的新視角和對文明傳承的新闡釋,為我們提供了考察當前城市遺產的另一路徑,也提醒學者在文明延續的脈絡中重新理解媒介的變革。面對當前智能手機等數字移動媒介日益普及的現實,本文將梳理德布雷對媒介與遺產傳承的理解,據此探討新的媒介狀況下遺產傳承的變化,并挖掘數字移動媒介在其中的重要意義。
傳承文明的媒介
(一)作為媒介的紀念物與城市遺產
在德布雷的媒介學中,媒介是“特定技術和社會條件下象征傳遞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是文明發展的前提和文明延續的必要條件,而不只是對現實世界的符號再現,或是傳統生活的技術優化。這一意義上的媒介在人類文明之初就早已存在:由骨骼、石頭等做成的紀念物是最初的記憶媒介,以其物質象征和抽象符號代替缺席的過去。德布雷強調記憶媒介的物質性,指出物理載體與集體組織在傳承中具有與內容符號同等重要的地位。通過組織化的物質載體的中介作用和持續的中介過程,過往的歷史及其文化價值才得以固定并持久留存。
本文所講的城市遺產,便是城市中集合多種歷史紀念物的整體。歷史建筑憑借建筑實體作為標記工具和儲存載體相對持久的特性,在無意中固定城市歷史的某些瞬間并將其帶到當下。除了建筑上的裝飾圖案、雕刻文字等抽象符號,建筑材料、建筑樣式等也代表著特定時代。這些象征由物理的建筑材料所攜帶,在時代變遷的痕跡疊加中成為歷史紀念物。城市遺產中的節慶儀式或日常習俗等傳統活動,同樣也在周期性、組織化的反復實踐中使某些事件或人物為當前所銘記。可以說,媒介學視野下的歷史建筑、習俗儀式等遺產,本身就是文明傳承的媒介載體,對遺產的研究便是對記憶媒介的研究、對文明傳承的研究。
以歷史建筑和傳統活動為城市歷史的紀念物和記憶媒介,也帶來對“地方”的新理解。紀念物以固定或周期反復的土地標記,為其所依附的土地劃定特殊意義,構成城市遺產的特殊地方。地方的特殊意義產生于紀念物這一記憶技術及其對集體的延續性集合,而非隔絕于媒介之外的先驗存在。媒介作為象征技術從一開始就是地方意義的必要構成,而非威脅其穩定安全的洪水猛獸。紀念物作為媒介聯系同時代和代際之間的集體關系,而城市遺產的地方意義就存在于這些關系的交織中。由記憶媒介產生的地方并非封閉、穩定的,而一直都處于與外界的開放聯系和持續變動之中。
(二)視頻圈的即時主義與遺產膨脹
從傳承媒介的角度上來看,城市遺產在當前新技術變革中受到的威脅,與其說是信息網絡帶來的全球化和移動性對穩定封閉本土的沖擊,不如說是來自記憶媒介,即文明延續條件的改變。德布雷用“媒介圈”的概念闡述不同主導媒介形成的生態環境:技術革命帶來人類社會新的主導媒介,將文明過渡到新的媒介圈,形成新的記憶方式和時代精神。新舊媒介圈之間交錯融合,重新組織了社會的不同力量。
從“話語圈”“圖文圈”到“視頻圈”,人類文明傳承的主導媒介從沉重的石頭雕刻和反復的神話儀式轉向相紙、磁帶等。德布雷指出,人們日益面臨“傳承危機”,并將其歸咎于主導媒介的“非物質化”。在以電視等視聽媒介主導的視頻圈中,輕便的記錄載體可以快速廣泛散播和復制流通,但也更加脆弱和短壽。信息流通的加速使人們不再主動走向難以移動的石頭,在其上雕刻以便記憶。相反,紙張與電子屏幕輕易地將世界實時帶到用戶面前,載體的移動替代了人的移動,符號信息取代了物質載體的象征性,即時取代了記憶和歷史意識。
這種即時主義的時間,是視頻圈的時代特征。電視的實時直播以急速的信息套疊消解了碎片事件之間的關系序列和時間深度。一方面,電視是“留住生命的最好儀器”,人們可以利用視頻回放,逆轉時光流淌的方向。另一方面,信息隨時制造事件,也隨時代之以新事件,作為“間接實踐”、要求延遲與偏移的歷史反思不復存在。人們不再花時間記憶,而是被當下的時間所占有。即時可見的圖像過度充實,導致以往通過神圣象征物為集體所共同想象、紀念的文化意義,失去了立足之地。
與視頻圈的即時主義相對應的,是遺產數量的日益膨脹和人們對遺產的熱衷。遺產因記錄的便捷而越來越多,同時人們在技術的疾速前進中,又返回對古代文化的熱衷,如紀念活動的盛行。德布雷將這種遺產的膨脹與追求歸因于在技術高速發展的不穩定中對內心精神平衡的保持,而精神平衡的達成依賴于藝術品的“文化遺產效用”:藝術美學被推崇為人類共同信仰的價值觀念和聯系紐帶。對藝術古董、展館建筑和紀念活動的崇拜和追求,成了集體文化特性的替代黏合劑,人們在藝術品的圣物堆積中進行集體精神療傷。
然而,這種以藝術品為遺產的復古主義追求,已然滲入了視頻圈的時代特征。人們側重保留了遺產的符號和視覺形式,對包裝和衍生品的講究超過了對遺產本身含義的重視。遺產在體積日益膨脹的同時,其意義也在日漸消沉。人們對遺產的渴望實為時髦的符號消費,遺產從本能記憶變為應用記憶,成為失去背景淵源的粉末。
視頻圈下的“遺產熱”在延續紀念習慣、追求集體特性的同時,已然改變了遺產的含義。紀念物被認為是可見的、可展示的甚至可被復制流通的物品或商品,其作為傳承媒介所中介的歷史深度和族群價值退居次位。人們習慣以空間傳播的方式來保證文化傳承,以消費當下的方式確認集體特性。紀念物作為古老的媒介穿越視頻圈,也以視頻圈的即時主義和注重視覺展示的新傳承觀念,延續本土歷史和集體特色。
數字移動媒介時代的城市遺產
德布雷的論述并未涉及新近興起且日益占據主導地位的數字移動媒介,但其基于傳承媒介對遺產的討論,正為探討當前更為復雜的媒介圈及城市遺產提供了區別于媒體研究、遺產研究等的新思路,促使我們從遺產傳承入手考察數字移動媒介。下文筆者結合當前城市遺產的新狀況,梳理數字移動媒介所帶來的不同于視頻圈的新特征。
(一)紀念物與數字移動媒介:移動設備的地理聯系
在智能手機、移動互聯網快速普及的中國,城市遺產幾乎已無法與數字移動媒介相隔離。博物館將藏品進行數字化并在互聯網上展示,人們可以隨時隨地欣賞。數字互動裝置被引入歷史建筑空間,人們借助線上場景,對城市遺產有了更多維度的身體參與。數字媒介不只將遺產的形態外貌在屏幕上展示,也以其物質設備嵌入用戶所在的物理空間,改變人們身處城市遺產時的具身感知,甚至改變遺產的形態,參與建筑和儀式的持續維護和增刪修改。
與此同時,城市遺產也影響著數字移動媒介的信息組織和呈現。移動媒介帶有地理定位裝置,設備所在的地理位置成為其組織邏輯。這種地理邏輯基于特定位置,也涉及該位置上存在的事物及其社會文化意義,與歷史建筑、儀式活動等相關聯。手機程序依據用戶地理定位周邊的歷史建筑排布、儀式進程等向用戶推送相關信息,增強現實(AR)游戲依據手機攝像頭實時“看到”的文物來組織情節。城市遺產作為組織方式影響移動媒介的數字場景,在帶入地理邏輯之外也因其象征的時間深度而帶入歷史的邏輯,改變數字移動媒介的信息架構和用戶的操作實踐。
作為古老媒介的遺產與新興數字移動媒介的互動展現出區別于德布雷所述的新形態,現場的互動體驗成為到訪城市遺產時的重要方面。新舊媒介的相互影響不限于將遺產作為內容的推廣包裝,或視頻圈的符號消費在遺產熱潮上的投射,而是兩者實體化的相互嵌入,作為各自的物質構成,也作為相互組織的程序、邏輯。新舊媒介在物質設備、組織機構等不同層面的持續變動,共同構成人們動態的時空感知。希爾瓦指出,當數字移動媒介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人們就處于數字空間與物理空間持續接合的“混合空間”。在遺產的語境中,這種空間正由歷史建筑與數字移動媒介等的互動所形成。
當前城市遺產展現出來的“混合空間”和互動體驗,得益于數字移動媒介對所處地理位置敏感的特性。一方面,移動媒介作為物質設備,實質改變遺產的地理空間布置,重新組織到訪者的所見與所知所感;另一方面,移動媒介可以感知設備所在地點及其文化脈絡,并以此作為組織邏輯,指導信息的呈現與數字空間的建構。數字移動媒介不再一味著重于遠程傳播,而是依據地理脈絡而組織實時且實地的信息,展現設備在物理地點中的存在,同時也在與遺產的物質互動中,重新凸顯載體的物質實體。
(二)數字移動媒介的記憶:身體存檔與算法驅動
以手機為代表的新興數字移動媒介,一方面以其輕便特性延續了視頻圈的即時主義,促使不斷更新的信息流走向移動中的“我”。然而,手機并未完全取代人的移動,媒介設備反而隨人的移動而移動,隨人的身體實踐而生產符號信息。手機改變了信息的組織方式和人們保存痕跡、記憶事件的方式。
數字移動媒介允許、鼓勵用戶的記錄和分享,使攜帶手機的普通公眾成了記錄者,通過手機應用隨時生產個人的記錄,并在集體中分享。這些記錄離不開公眾個人的身體參與:身體必須位居某一地方,手指需要觸摸屏幕,身體部位的外形或數據也可能出現在記錄中。如樊·迪克所說,身體實踐成為數字媒介記憶的一部分。當信息向“我”移動時,“我”也在主動生產著記憶,“我”的身體參與記憶的生產。
用戶的位置、移動軌跡等種種信息,也時刻為數字移動媒介所感知、記錄。人的身體實踐,經過手機算法而被轉化為數字數據。這些轉化可以在用戶無意識的情況下持續進行,使下意識的身體動作也被記錄在案,成為記憶的一部分。這些記錄包裹于算法的暗箱之中,難以為普通用戶所操控。加上移動媒介對周圍環境的感知和記錄,多種層次的時空數據形成由機器組織且持續更新的數據庫,形成自動化的生活檔案。
萊茲琴斯基將數字媒介這種超越人類的話語實踐、無法被解構為公眾認識的算法特性歸納為一種“物質性”。編程算法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本質指導文本內容的形成,形成了數字驅動的過往存檔,如今也成為人們回溯過往、指導未來的記載資源,如個人在身體數據的存檔中監控健康問題、認識自己,數字地圖的街景影像存檔服務于城市生活。此時,數字移動媒介脫離人的思想控制又緊隨人的身體實踐,在與人類話語的區分上形成其獨立存在。
數字移動媒介的新記憶方式,將可被記錄的事物從權力機構關切的事件,擴展到普通個體的瑣碎日常,記錄視角也從權力機構的篩選變為多元視角的集合,甚至是維利里奧所說的機器“無目光的視覺”。這種記錄一切、隨時存儲的方式,不同于視頻圈中遠方事件向被動觀眾的即時可見和更替,而是在公眾自身的身體參與中持續積累數據,經過算法的分析、加工,以可以為人所理解的方式再次呈現不同時間層次。
數字的集體檔案記載新近的過往,也成為對新近事件的紀念媒介。數字紀念物與歷史建筑、文物、習俗儀式等紀念物和紀念組織并置于人們的生活世界并相互呼應,共同構成將當前與過去聯系以確認集體特征的文明遺產。
作為紀念物的數字移動媒介:重新浮現的物質性與新傳承
數字移動媒介展現出其作為實體存在的重要意義,及其與物質世界的緊密關聯。一方面,移動媒介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環境成為媒介信息生產、呈現的組織邏輯,形成設備與周遭物理空間的隨時聯系。另一方面,數字媒介因算法的自主運行而呈現脫離人類的自動化,作為與人相區別而又相聯系的實體而存在。德布雷曾指出電子視聽媒介的物質載體失去了與符號并置的象征意義,數字移動媒介則重新強調其物質性:載體的物理存在和算法組織規定其存儲和呈現的符號內容,物理設備在與地理空間、與人的身體的關聯中時時提醒人們它的物質性質和形態。
“物質性轉向”是近年來人文研究領域涌現的新趨勢,學者們從“物”的視角切入關注媒介傳播的基礎設施、技術系統、實踐過程等。德布雷所說的物質,更多側重于媒介多層次的實體,區別于抽象符號和精神思想,包含載體材料、組織機構及它們之間的互動。本文所說的數字移動媒介的物質性,同樣涉及設備的物理材料和實體化的組織制度。不過,在數字移動媒介中,物質性的重新浮現并非重新恢復不可復制的物理本體,而更多強調媒介設備存在于物理環境的實在及算法脫離于用戶意識的獨立制度。
憑借重新浮現的物質性,數字移動媒介作為主導媒介組織起新的媒介圈,突出新的痕跡存儲方式和對文明的新傳承。城市遺產展現出對公眾身體參與及互動體驗的強調。人們在“混合空間”中體驗城市遺產,與過去世界相聯系;人類的實踐痕跡隨時向數據檔案轉化,持續進行著遺產的再創造。盡管這些參與體驗仍不乏娛樂消費的意味,但已不限于對遺產視覺形式的保存和重現。遺產在與數字移動媒介的互動中繼續積累當前世界的痕跡,制作新的紀念物和紀念儀式,延續文明活力,也不斷確認由眾人持續重塑的集體特性。
在這一新的傳承狀態中,數字移動媒介成為歷史紀念物之一,為當前的文明傳承提供現在與過往的聯系和對遺產的持續創造。數字移動媒介支持參觀者與居民以多種方式與城市遺產、與過去相聯系;同時移動媒介持續記錄公眾身體實踐與物理環境的數據,使其成為近期事件的檔案和紀念媒介。在這些對當前與長期過去、新近過去不同時間的聯系中,數字移動媒介成為傳承的媒介,成為缺席過去的代表,與歷史建筑、儀式習俗等一樣構成城市遺產。數字移動媒介也以其持續建構的特性不斷對遺產進行改造,更新現在與過往的聯系。
對文明傳承與遺產的關注為我們打開了考察、理解數字移動媒介的另一視角。媒介既連接這里與那里形成網絡,也連接過去與現在形成延續性。數字移動媒介在傳播信息的同時也對信息進行記錄和存儲,在依據地理邏輯組織信息時也加入地理的歷史脈絡,成為人們與過往聯系的方式,展露出它在人類社會及其文明傳承中的重要意義。當前中國關于遺產議題的熱潮也與這一新的媒介圈相關,數字移動媒介的嵌入使得城市遺產并非遙遠之物,人們在多種歷史紀念物中參與、體驗歷史。媒介學的視角提醒我們重視媒介在時間維度的傳承,也為媒介研究者與遺產研究者共同致力于遺產保護及文明傳承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