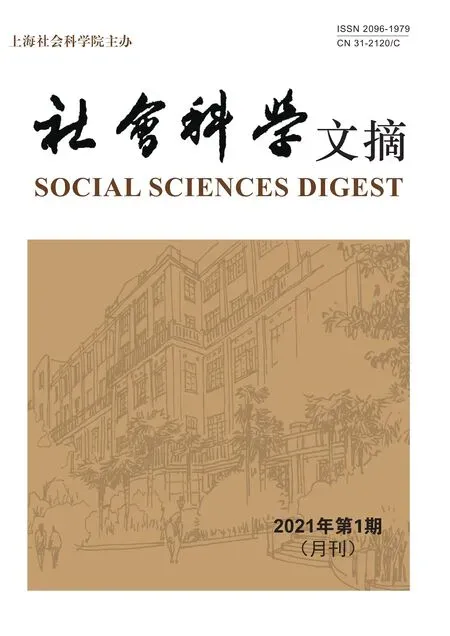知識普及、意義斗爭與思想實驗
——中國當代科幻小說中的科普敘述
一
“最好的時代”——對中國科幻文學前景的這份樂觀的判斷——已經得到了出版數據和文化現象的有力支持。劉慈欣《三體》和郝景芳《北京折疊》先后獲得“雨果獎”,根據劉慈欣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流浪地球》在網絡中被譽為科幻電影元年的標桿作品,再用“兒童文學”之類的標簽固定科幻小說顯然不妥。在科幻小說迅速發展的同時,科學普及的話題也急劇升溫。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需要更多的知識普及,在科技創新及其應用日益滲入日常生活的趨勢中,科普工作受到了高度的重視。然而,同樣分享著科學的發展、同步升溫的科幻和科普,彼此間卻似乎失去了熱絡的互動。評論界承認,當前的科幻更像是在有意地疏遠科普。“以邏輯哲理、技術景觀等人文視角為出發點,已成為當下不少科幻小說家探討科幻中的科學的思考模式。我們很難看到把科普作為創作主動機的科幻小說。”科幻小說主流脫離科普背景成了21世紀中國科普創作的新特點。可是,歷史檢索所呈現的卻截然相反。
“我國的科學幻想小說,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在‘科學普及’這面光輝的旗幟下涌現出來的。”科學技術想象與知識普及手拉手的和諧場景,從清末延續到了20世紀80年代。文學曾經記錄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大潮洶涌澎湃所造成的沖擊。在這種背景之下,科學普及的工作很自然地陷入了困境。此時的科幻創作所面臨的,還多了一重意識形態的影響。科幻、科普就此相揖別。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我們有很多科幻小說家,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已經能寫很優秀很好看的故事了,但在他們的小說中,卻很難再看到普及科學的意識了”。
二
科普,尤其是以科幻這種文藝形式出現的科普,真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嗎?在當前文化語境中,科普是否還需要科幻?這個問題完全可以轉化為“科普需要怎樣的科幻”,或者“科幻應該怎樣科普”。
科普就是自然科學技術知識的普及,這是為大眾所熟知和接受的基本定義。在西方,“科學家”和“普及”作為術語的現代使用出現在19世紀前半葉。在中國當代科幻小說所置身的語境中,科普“源自俄文Популяция научных знаний,意為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科學知識的普及化)。1950年‘全國科普協會’成立,這個詞開始在中國大陸通行”。傳播科學知識并使其為專業工作者之外的人群所了解,科普的任務并不難以理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向科學進軍”的熱潮中,承擔科學普及任務是科幻小說的榮光。用文學的藝術方式普及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寄托著作家對國家建設的美好憧憬,這不是什么難題。相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自然科學知識要穩固得多。那么,交給文學的任務似乎就是裝飾,讓科學知識的受眾“不生厭倦”就是科幻小說的功績。
肩負著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普及科學知識重任的科幻小說創作者們,很快發現困難比預想的更大。科學技術的知識、原理和邏輯不像小姑娘那樣好打扮,它們嚴肅、木訥、不肯配合。強調科幻小說必須尊重科學的真理性以免墮入巫術和幻覺世界的觀點,始終影響著中國當代科幻的科普敘述。“科學小說中的科學成分乃是科學幻想,也即科學的邏輯推理的構思,它必須同整本小說的文學構思相結合……這種結合,不是相加或雜交,而是有機的綜合與重疊,是真實與幻想的綜合重疊。”問題是怎么“有機”,怎么“綜合”?
肯定科幻和科普相互成就、“在新中國的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創造了不大不小的輝煌”的同時,也要看到20世紀50—60年代的科幻小說創作者們對自己的科普性敘述不滿意。鄭文光坦承,“文學的功能和科學的內容,這兩者的有機結合是不容易做到的”,自己的《從地球到火星》《太陽探險記》等作品都無法完全擺脫“把科學知識塞進一個小說框架的毛病”。科幻作家肖建亨感慨:“無論哪一篇作品,總逃脫不了這么一關:白發蒼蒼的老教授,或帶著眼鏡的年輕的工程師,或者是一位無事不曉、無事不知的老爺爺給孩子們上起課來了。于是,誤會——然后謎底終于揭開;奇遇——然后來個參觀;或者干脆就是一個從頭到尾的參觀記——一個毫無知識的‘小傻瓜’,或是一位對樣樣都表示好奇的記者,和一個無事不曉的老教授一問一答地講起科學來了。參觀記、誤會法、揭開謎底的辦法,就成了我們大家都想躲開,但卻無法躲開的創作套子。”童恩正的意見與肖建亨無二:“現在某些科學幻想小說,似乎已經將情節化成了一個簡單的三段式,即第一,提出一個懸念;第二,一個新聞記者(或無知的當事人,或求知欲望很強的小孩,視情況而定)追求答案,遇到一些更古怪的事物,激起更強的好奇心;第三,科學家爺爺(或教授、工程師,視情況而定)解釋原委,于是疑團冰釋,誤會頓消。”科普敘述的前提是科技知識的正確性和完整性,可科幻敘述往往正想在既有的科技確定性上實現突破,它喜歡的是未成事實的可能性,不太在意這種想象是否正確。科普的“確鑿無疑”和科幻的“無中生有”難以共商大事,方程式和想象也無法琴瑟和鳴。
然而,這還不是科幻小說中科普敘述最困難的地方。
三
科幻的科普敘述面臨著諸多困難,部分研究者提議將兩者分開,使科幻從科普的任務中解脫出來,可更嚴峻的問題在于,“如何普”的問題沒能解決,“科普”所“普”的究竟是什么也存疑。科普的常規理解,就是使客觀正確的科學技術知識在大眾中得以普及,現在這個知識傳遞鏈條的每個環節似乎都不那么確定。即使假設科幻小說承擔科普的敘述問題得到解決,為何科幻小說的科普一定“普”的是科學技術?即便照抄方程式,就能保證科普敘述的正確?怎么認定科學技術知識的普及一定秉持客觀?
中國當代科幻小說從事科學知識普及,與“向科學進軍”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但并不能就此斷言,科幻小說中的“科普”,甚至“科普”本身,就只是在普及科學技術知識,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史也說明了這一點。中國科幻小說誕生于近代危機中的中國,已經決定了看似客觀的自然科學知識普及必然與特定的價值觀念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小說是為了讓科學更為便捷地為大眾所接受,而為大眾所接受,又是為了啟民智,“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進而救亡圖存。科學技術知識的原理和邏輯的確不因人的意志而改變,但離開人與社會,它隨即失去意義。活躍于20世紀50—60年代的科幻和科普作家,在科技普及總是與特定的觀念相結合這點上,沒多大異議。“科普”中的“科”,包括自然科學知識之外的知識,“科普”所要普及的內容,自然沒有正確的保證,也沒有保證正確的必要。
越來越清晰的是,公眾對自然科學知識的懷疑難以斷絕。除了文化素質整體性提升的大趨勢外,至少還有三種觀念的影響:一是“沒有一種科學解釋是永遠真實的”,二是“所有的現象……都可以通過合理但不一定完美的自信來預測”,三是“沒有一個科學家能從自然現象中,就人類的價值觀或生存的意義總結出任何東西”。科學總是在推翻過去中獲得進步,誰也無法擔保現今的某條鐵律在未來不被推翻。當然,以相對主義之名取消現有科學技術知識的正確性同樣不可取,堅持理性的立場和啟蒙的勇氣仍然十分關鍵。與其強調每次科普的科學知識都絕對正確,不如保持開放的求真意識。
科幻小說中的科普敘述總會潛在地預估讀者的興趣方向,這是它與純科普作品的明顯差別之一。作為文化系統運作的科學傳播,至少包括了生產、表現、消費、規制、認同選擇等諸多環節,科學傳播和“組織、身份認同、空間、情感、職業生涯、未來,以及許多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緊密聯系……涉及集體和文化的建構”,“各種各樣的傳播實踐構成了既相互依賴又具有自主性的復雜網絡”。科幻小說的科普敘述中,“普什么”也是權衡和選擇的結果,“客觀”終究還要看是誰的“客觀”。
四
處于開放文化環境中的科普,“不是知識的流傳,而是意義的斗爭”,“在研究科普時,我們的關注點應該是意義而非信息”。科幻小說中的科普敘述,普及的不僅是科技知識,還有人文觀念;不僅是單向的傳授,還是多方的平衡;不僅是知識的搬運,還是意義的生產;不僅是客觀的介紹,還是認同的探尋。保留科幻和科普相互成就的可能,離不開啟蒙意識。
現代科技的發展帶來的不僅是便捷、舒適、污染或沉溺,還帶來了知識不確定性的驟增。期待科幻中的科普敘述傳遞確鑿無疑的知識,已經難以與這個時代的科學發展水平及其科普需求相匹配,“小靈通”的時代已經落幕。啟蒙理性尚未填補放逐神后留下的空白,自己對理性近乎極致的推崇和樂觀就招來了后現代主義洶涌的反擊。處于現代與后現代疊加語境的21世紀以來的中國科幻小說,包含了“知識的流傳和意義的斗爭”的科普敘述,在尚未也不能卸下啟蒙者的身份之時,還要適應“闡釋者”的角色變化,或者說必須在“闡釋”中啟蒙。“‘闡釋者’角色這一隱喻,是對典型的后現代型知識分子策略的最佳描述。闡釋者角色由形成解釋性話語的活動構成,這些解釋性話語以某種共同體傳統為基礎,它的目的就是讓形成于此一共同體傳統之中的話語,能夠被形成于彼一共同體傳統之中的知識系統所理解。”著力于知識話語之間的轉譯和相互理解,是確定知識的傳播導向一種思考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建構,從而跨越專業人員之間甚至是專業人員和公眾的區隔。何夕的《傷心者》突顯了科學專業性與大眾理解之間的難度,但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創作,也一直在為突破這種屏障貢獻著文學想象的努力。《三體》的引人矚目不在于黑暗森林、二向箔、“水滴”、思想鋼印等的現實可能性,而在于它在堅持理性想象的基礎上致力于建構一種我們都可能置身其中的意義系統;物理學知識的欠缺不能遮蔽《北京折疊》的價值,它的思考包括了如何認知現實、如何評價自身所處的社會、如何評價自身等問題;韓松筆下的地鐵、高鐵世界晦澀且詭譎,卻是對現有社會制度和文化認同的警示。“對科學素質的理解不僅應該包括對科學的所知和對科學如何運作的理解,更為重要的是,還包括把這個理解與人們自己的生活和周圍世界聯系起來的能力。”知識硬傷只要不把科幻小說改造成奇幻小說,那么科幻小說中的科普敘事就可以在科學發展、意義斗爭與認同探尋的不確定性中啟航。
21世紀以來中國科幻小說的科普敘述,其重心已經從“結束具體問題”轉向“打開某個問題”。只要有勇氣運用理智,科學的發展還將給啟蒙注入不竭的動力。科學的迷人之處不僅在于解決技術問題,它的真正影響更在于“一種心靈態度,一種思考問題和探究問題的一般方式”。在未來豐富的可能性面前,科幻小說科普功能的實踐需要融科學知識傳播、認同觀念探尋和思維方式更新于一體,而“思想實驗”正是一種積極的反應。
五
“思想實驗”源于現代物理學概念。“現代物理學中有一種所謂的Gedankenexperiment傳統,這個詞是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發明的,其字面意思是‘思想實驗’,用來描述一種在頭腦中進行的實驗:物理學家設想出一套精確的實驗條件,或建立一系列有明確定義的假設,試圖邏輯地推斷出實驗結果。”沒有儀器和數據,依靠前提設定下的想象和推演產生新穎的內容,這是科幻小說的強項。在托馬斯·斯科提亞看來,科幻小說“擔負著一項光榮的使命,那就是向人類展示可能的未來,辨識歷史進程中關鍵的節點。科幻小說在充當文學上的思想實驗的同時,也就實現了這一功能。它至少可以充當一種潛在的催化劑,教給我們思考未來的復雜技巧”,因此,科幻小說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實驗的專業制造者”。科幻小說“思想實驗”的功能和特色,曾經在不同側面上得到了理解,如“科幻小說應該被理解為認知性陌生化的文學”,科幻小說“常常暗含了對當下的批評和當今社會趨勢下未來可能發展結果的猜想”,海因萊因甚至想用“推測性小說”替代“科幻小說”,而中國的科幻小說研究者也認同這樣的理念。吳巖說,“強調用道德和倫理對可能性進行判斷,這些恰恰也是科幻文學的內容運作方式”。“科幻可以成為科學引進的調節物,更可以成為思想實驗的偉大場所。”在“思想實驗”的可能性探索中,啟蒙實踐得到延續。
“思想實驗”是啟蒙之問的縱深化推演,自然帶有價值認同色彩。認同的探索或異于既有的現狀,或向未來敞開,自然科學知識和人文社會觀念伴隨著思想實驗的推進而得到傳播。王晉康在《十字》中倡導“低烈度縱火理論”,主張讓初級病毒逐步傳播從而使人類整體逐步適應并實現真正免疫,雖然此過程中不免有個體犧牲,但這正是作為造物主的“上帝”“只關愛群體而不關愛個體”的“大愛之所在”。這樣的觀念顯然與大眾所理解的人文關懷形成差異。陳楸帆《荒潮》的賽博格時代敘事語境中,對是否只有人類才擁有靈魂、是否只有生物才能進化、是否人類的進步必須要付出靈魂為代價等問題的可能性探討,與生態治理新方案、資本跨境滲透、冷戰思維留存、地方宗族勢力、女性/底層人物之認同抗爭的展開奇異地交織在一起。劉慈欣《三體》更是由眾多思想實驗縫織而成,這些想象彼此融匯、撞擊,織就了小說思想的張力。人類社會日常倫理失序的危機推演出了豐富的內涵:“自由意志加要求真相,意味著無視真理”;表層的生命維持與深層的美好生活是二而一的整體;“自由政府反而成為生命自由的最大障礙”。當然,思想實驗的重心在于可能性的探討,在于捕捉地平線上的曙光,而非完成思想的某種閉合。結合科技新發展,發現即將來臨的可能,突破既有的觀念束縛,“思想實驗”的魅力正在其中。“實驗”不保證正確,但不能因為觀念的風險而放棄探究,未來科幻小說的“思想實驗”大可“走出人文主義的執念”,“放棄對古典的人文主義觀念的迷思,去重新構想一個未來的、全新的社會樣態”。走出執念,就意味著保持科技時代中使用理性的勇氣,重新審視自身及自身所處的世界,探尋知識和思想的新的意義空間,這是未來科幻小說科普敘述應有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