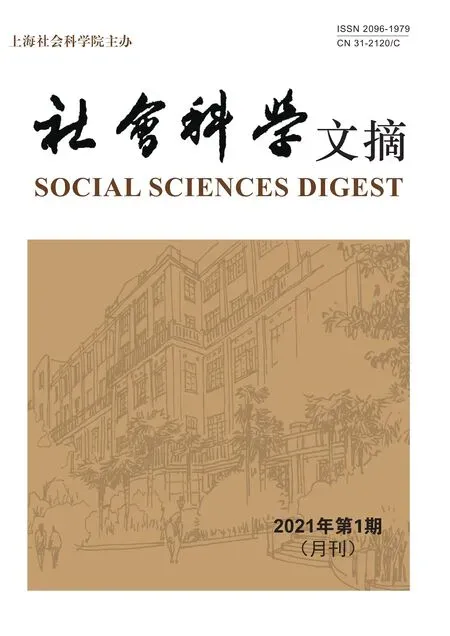《民法典》的四大倫理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譽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通過民法典,我們可以透視當代中國社會的倫理精神。
《民法典》之底線倫理
民法給人的感覺,主要就是財產法,但翻開《民法典》,筆者首先看到的是“人”,而不是“財產”。民法典的主旋律便是人文關懷。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對于民法調整對象的規定是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財產關系在人身關系之前,價值重心在“物”。《民法典》總則把這個順序調過來了,把民法的調整對象規定為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人身關系放在了財產關系之前,體現了貴人輕物的價值取向。第二,人格權編獨立成編在體系上改變了傳統大陸法系“重物輕人”的結構,在價值上確認了人格權在諸種權利中的重要地位,在實踐上回應了社會發展尤其是科學技術發展所帶來的對人格利益的保護問題,從根本上滿足了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三,在人格權編中,人格尊嚴的保護問題是最為基本的、重要的、迫切的問題,對自然人隱私權和個人信息的保護是人格權的重要內容。
回歸“人法”本位的《民法典》確認和維護了作為社會的道德底線的人格尊嚴。應該說,每個社會個體都可以向社會和國家提出必須無條件予以滿足的要求,即社會和國家要把人當人看,不能僅僅將其當作工具來使用。這個要求是最根本的,也是不可取消的,因為人格尊嚴具有壓倒一切的道德分量。社會和國家不能拒絕,只能滿足并加以保護。這種滿足和保護,通過憲法,以基本權利的方式落實下來,通過《民法典》,以人格權利的方式確認下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民法典》是人民權利的宣言書。
人格尊嚴何以成為《民法典》所確認的社會生活的道德底線?
第一,只有自然人才是尊嚴的主體。所謂的自然人,是指具有人類生命基因的有生命的個體。也就是說,自然人的確立只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必須是一個由人類基因組所表達的生命形式,二是必須是一個活著的個體。“自然人”的定義界定了尊嚴主體的范圍,既避免了對尊嚴主體定義過寬之弊,又避免了對尊嚴主體定義過窄之弊。
第二,自然人的尊嚴由人“類”的尊嚴和個體的尊嚴兩個層次構成。(1)所謂“類”的尊嚴,是人之為人應有的、有別于動物等其他生命形式的形象和存在方式。自然人是凝結了自然進化和人類創造的成果結晶,仿佛是鬼斧神工和人類勞動共同鍛造的藝術品,其珍貴程度無可比擬,值得我們肯定和珍惜。(2)所謂個體的尊嚴是指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傳記的作者,這個地位是不可取代的。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傳記的唯一作者,只有這樣才能成為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才能超越身體的所與性和偶然性,通過支配身體、財富和精神,彰顯出人的自由本質。在這個意義上,個體的尊嚴是指本人就是人生傳記的作者的地位是不可替代和不可動搖的,對這個地位的尊重,是個體尊嚴的價值來源。
第三,尊嚴的價值具有內在性、絕對性和普遍性三個特征。(1)尊嚴的價值是內在的,也就是說,尊嚴本身就是好的。只有具有內在價值的東西才能成為其他價值的根據,只有具有內在價值的東西也才能成為衡量其他事物的價值的標準。(2)尊嚴的價值具有絕對性。具有內在價值的東西有很多,但不一定都具有絕對性,譬如,生命、財產、榮譽等都是可以剝奪的,但尊嚴卻是絕對不能被剝奪的。尊嚴的絕對性意味著不可限制、不可替代、不可交換。(3)普遍性。人的尊嚴不是少數人的尊嚴或統治者的尊嚴,尊嚴的榮光落實于每一個具體的個體身上。無論在性別、民族、種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等方面有何差異,只要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即可以以其人的資格而擁有這樣一種地位。可見,在現代文明社會里,如果要確立一個確定無疑的價值支點,那就是自然人的尊嚴。
如果上述分析是合理的,那么,《民法典》通過人格權編獨立成編的結構設計和諸多人格權的確認,無異于畫定了社會生活的“人格尊嚴”的道德底線。
《民法典》之市場倫理
《民法典》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大法,既要適應和體現市場經濟的內在道德,又要適應和體現市場經濟所嵌入其中的社會道德。所謂市場經濟的內在道德,是指市場交易之所以成為交易的內在道德規定性。沒有這種規定性,市場交易就不成其為市場交易,或者市場的主要功能就無法實現。所謂外在道德,是指市場經濟所嵌入其中的社會道德,這是具體形態的市場社會的道德要求。違背了這種要求,市場交易雖然還是交易,但不是一個好的交易,譬如性交易、毒品交易、武器交易等。《民法典》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法,既體現了市場經濟的內在道德,又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德風貌。
《民法典》總則編第7條規定了誠信原則,即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第8條規定了守法與公序良俗原則,即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其中誠信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內在道德要求,公序良俗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外在道德要求。
第一,誠信原則是市場的內在道德。市場經濟的商品交換是通過貨幣和契約的中間環節進行的,否則就不可能形成有規模的市場經濟,而市場交換由于存在著時間和空間上的某種分離,蘊含了極大的交易風險,要想有效地降低和避免這種交易風險,契約無疑成了人們最理想的選擇。可見,市場離不開兩種東西,一是貨幣,一是契約。沒有貨幣和契約的中介,一個跨時空的交易就是不可能的,而貨幣和契約的本質是一種信用機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沒有誠信原則,就沒有交易,就沒有市場。誠信原則是市場經濟的構成性規則,是任何市場經濟,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無論是何種文化背景下的市場經濟,都必須具備的。
第二,公序良俗是市場的外在道德。(1)任何交易都是具體的人在特定時空所發生的具體關系。除了要遵守誠信的內在道德之外,這個交易活動還要遵守交易主體所在共同體的文化傳統和公共秩序。其載體就是習俗。如果說,內在道德是普遍的,那么外在道德就是具體地內在于共同體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2)如果說誠實守信與公序良俗是交易倫理的內在與外在的關系,那么公序與良俗就是目的與規范的關系。所有社會規范都以維護“公序”為共同目的,由此才有了不同社會規范之間的協調和轉化。良俗也因此可以沉淀為道德,轉化為法律。(3)風俗與善良的形與神的關系。風俗是指長期相沿積久而成的風尚、習俗。風俗的種類及其表現形式繁復多樣、良莠不齊,而良俗就是從這些良莠不齊的風俗中,依據社會的道德要求檢選而出的。檢選風俗之良莠的標準,可以是國家提出和推行的主流意識形態,譬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可以是社會知識精英所提煉和概括出來的具有系統化、邏輯化、體系化的道德規范體系;還可以是人們在日常的生產生活經驗中自發形成的道德常識。
第三,民法法典化的價值取向,就是編纂一部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有助于凝結價值共識,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的民法典。翻開《民法典》,我們也能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需要的道德共識。這主要體現在《民法典》的立法目的上,即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也體現在公序良俗的入法上,譬如《民法總則》第8條、第10條、第143條都有公序良俗的規定。我們之所以強調公序良俗入法的意義,是因為它體現了《民法典》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實質上也內含了特定的社會主義價值取向和特殊的民族倫理。
《民法典》之關懷倫理
翻開《民法典》,我們還能感受到對弱者的悲憫和關懷。第一,民事主體制度中,為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設定了監護制度;第二,合同編中對格式合同中不利于弱者的免責條款有嚴格限制,在合同解釋存在兩種以上可能時,選擇其中有利于弱者的那一種規定;第三,婚姻家庭編對婦女、老人和兒童進行特別保護;繼承編中規定為無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額;第四,在侵權責任編里,尤其是關于侵權責任歸責原則的過錯推定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規定,使我們更強烈地感受到了對弱者的同情和關懷。
在傳統觀念中,民法是強者的法律,為什么《民法典》會表現出對弱者的關注和同情呢?
第一,“人設”變了。傳統民法上的人都是“強而智”的人。他們自利而理性、謹慎而精明、自主而負責。這樣的“人設”要的是尊重,而不是關懷。問題是,人是一個脆弱性和堅韌性二重屬性的統一體,人可能沒有想象的那么強大,那么有理性,那么有韌性。經驗告訴我們,脆弱性貫穿了人生的整個生命周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法作為生活的百科全書,當把眼光從抽象的市場主體轉移到現實的生活主體時,也不得不修正自己的“人設”。
第二,平等的訴求變了。傳統民法上的主體資格是平等的,權利能力就是這樣一個抽象的裝置,它把現實生活中的所有差異都抽象掉了,剩下的只是幽靈般的沒差別的原子人。傳統民法號稱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所謂的“平等”就是這種抽象人的形式平等。但現實生活中,差異無處不在,在各種差異中,弱者與強者的差異恐怕是最普遍也是最根本的差異。因此,在同等情況同樣對待的平等訴求之外,不同情況區別對待的平等訴求也應被重視,這是一種實質的平等觀。如何差別對待弱者和強者的問題,自然成為“生活的百科全書”的《民法典》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三,對弱者的傾斜保護。差別對待就是要對弱者予以傾斜保護。弱者總是相對于強者而言的,他們是這樣一群人,他們或者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或者缺乏獲取生活資料的能力,或者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和救濟,總之,他們無力通過自己的努力擺脫面臨的困境,如果不能得到政府和社會的同情和幫助,他們就會陷入被強者欺負的不利地位。因此,法律在通過權利和義務的形式進行利益分配時,會對這群人特別予以關照,以保護他們的權益。社會法自然是通過對弱者的傾斜保護來實現社會的平等訴求,民法也不能與這樣的價值訴求相悖離,也需要在強弱之間,適當地節制強者的任意,保護弱者的利益。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倫理。
《民法典》對弱者的關注和同情不是偶然的,它體現了當代社會從強者倫理到弱者倫理的轉向。為什么會出現個轉向?第一,脆弱性是人類存在的普遍特征。這一特征在現代人類社會所發生的諸如世界大戰以及大規模流行病之類的慘痛經歷中被凸顯出來。第二,傳統社會是身份社會,強者與弱者的地位是固化的,其中下層的弱者被標簽化和污名化,在倫理學里自然沒有地位。而現代社會里,傳統的固態社會轉向了液態社會,弱者是個流動的標識,每個人在某種特定的關系中都可能處于劣勢。這樣,弱者脫去了價值的標簽,被還原為一個事實,而且是一個倫理學不得不面對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事實。第三,風險社會的來臨,凸顯了人的脆弱性。在這個社會里,每個人在風險面前都可能是弱者;隨時都可能成為處于風險中的弱者;每個事件都可能使一個人難以承受其后果。所以,只能以社會依賴與互助的形式來分擔這個風險,由此,風險社會的倫理學必然是強調脆弱性和保護弱者的倫理學。
《民法典》之生態倫理
翻開《民法典》,在煙火氣之外,我們還能感受到清新的自然氣息,由此,《民法典》被稱“綠色民法典”。第一,《民法典》總則編第9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這是將綠色原則確立為民事活動的基本原則。第二,《民法典》各分編中,直接涉及資源環境保護的條款達18條之多,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物權編中確立了物權的生態邊界。二是在合同編中,規定了對合同履行的生態邊界。三是侵權責任編以7個條文全面規定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可見,《民法典》之為“綠色”,實非虛言。
1.透過“綠色民法典”,我們看到的物是什么?近代民法上的“物”是可分割、可支配、可交換的具有經濟價值的東西。中國《民法典》上的“物”自然具有這些特征,但我們也看到了“物”的另一個綠色面向:民法上的“物”同時也是生態環境資源的一部分。這些作為生態資源一部分的物不但是難以分割的,而且具有經濟價值之外的生態價值。由此,從生態共同體的理念出發,一個“綠色的民法典”的物權制度不但要從個人權利保護角度解決“物”的歸屬、利用問題,也要從生態公共利益的角度顧及生態環境資源的歸屬、利用問題,從而不但確立手持可分割、可支配、有效用的獨立物的私有權人,還要確認那些江河大地、雪山高原、森林草原之類不可分割的生態資源的國家和集體的看護者;一個“綠色的民法典”不但要關注“物”的經濟價值,也不能忽略其生態價值。問題是,雖然一個物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都是人類生存所必需,但是它們卻不能一體得以實現,經濟價值的實現往往是以消滅其生態價值為前提的,反之亦然。表現在《民法典》上,就是要整合物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并以此為價值依據,確立財產占有與流轉的綠色邊界。
2.財產占有與流轉的綠色邊界在哪里?生態共同體的理念要現實化,成為人們的自覺活動,需要通過制度的中介。由于《民法典》涉及人的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無疑應該成為最重要的制度中介。由此,《民法典》不但要保護“物”的經濟價值,強調“物”在經濟上的有用性,并以此建立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制度,也要保護“物”的生態價值,并因此作出解決這樣兩種價值沖突的制度安排,包括:對傳統民法所有權的絕對性進行必要的限制;確保使用權人對這些資源的開發利用也要承擔環境保護的義務;確保我們在簽訂合同、履行合同的時候,必須同時考慮環境保護方面的問題。
3.透過“綠色民法典”,看到了中國倫理精神的走向。可以說,“綠色民法典”給我們打開了“由近及遠”的倫理發展的畫卷,使我們看到了道德共同體的邊界不斷拓展,道德關懷的對象不斷擴大,道德經驗和知識不斷普遍化的進程。這種由于道德應用范圍的擴展所引起的倫理形態的變化過程,我們概括為從族群倫理到全球倫理再到生態倫理的過程。按照羅爾斯頓(Holmes Rolston Ⅲ)的說法,人類起初只是承擔對家庭和鄰人的義務,往外依次為對社區、對國家和對全人類的義務,還有對后代的義務,再往外推是自然界,包括動物、植物、大地的義務。西爾凡(Richard Sylvan)和普蘭伍德(Val Plumwood)十分貼切地用“樹的年輪”來指稱這個由近及遠的演變過程。這個由近及遠的過程如果用色譜來表達,就是從黃到綠的過程,這也是《民法典》被貼上綠色標簽的內在邏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