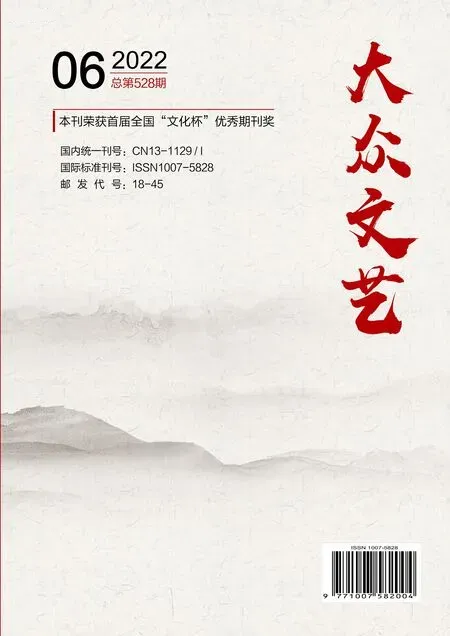多重敘事與讀者思維
——論電影《時時刻刻》對小說《達洛維夫人》的雙重突圍
(武漢大學,湖北武漢 430072)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對文學藝術的評價不高,在他看來,自然萬物的存在是摹仿理念的結果,文學藝術又是摹仿自然世界的結果,因此,文學藝術就像“影子的影子”,和“真實隔著三層”。但是,《時時刻刻》作為一部對經典意識流小說雙重改編的電影作品,應該屬于一部對模仿的模仿作品,卻在跨藝術媒介傳播中取得成功。學界對此研究鮮有涉及,本文意圖從敘事層面,分析小說/電影《時時刻刻》如何吸收伍爾夫創作理念,并運用多重敘事塑造出故事的整一性;同時,理解擁有讀者和創作者雙重身份的坎寧安,怎樣在保留原作的大體框架下,還能提供潛意識之外的多種解讀,在心靈困境的大背景下給出明確的脫困方向。
一、敘事的整一性與多重性
(一)龐雜視角的搬演局限
發表于1925年的《達洛維夫人》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長篇代表作之一,小說以一戰后的英國為背景,事無巨細地講述了上層社會婦女克拉麗莎·達洛維籌備宴會的一天,通過全知視角提煉出人物內心的無意義感。描繪主觀情緒是伍爾夫的創作欲望,人物則是其書寫的載體和動力,她常常拋開謀篇布局的束縛,盡可能刻畫心理視角。
小說看似圍繞達洛維夫人舉辦宴會的單一故事情節展開,但除卻書名中的“主角”外,讀者能知悉任何一個在書中出現的人物想法。龐雜視角的背后,有伍爾夫“描述生與死、理智與瘋狂”的渴望,延伸出數不盡的情節脈絡。作者意識通過旁觀者“入侵”了敘事過程,停頓和分支會不時出現在行文中。在小說開頭,一個貨車司機也能對達洛維夫人發表一番感慨,他沒有再次出現,當這片刻的描寫打斷了正在行進的情節,并衍生出毫不相關的事件來。
枝蔓繁多的敘事造就了深度和廣度,但也很難在一時間擁有廣泛的受眾。在影像時代,作品思想的獨特魅力被熒幕發掘,瑪琳·格里斯就于1997年執導了《黛洛維夫人》。這部電影按照原著進行編排,只對少數情節做出改動,試圖完全通過蒙太奇再現視覺上的意識流。內心獨白、閃回,以及多視角的轉場在影片中經常出現。可以說,這部以孤獨為基調的電影,是對伍爾夫原著的視覺化、立體化。但不可否認,除了伍爾夫的忠實讀者,這樣的改編無法吸引更多觀眾直觀體會原著思想,任意穿梭的全知視角可能帶來表達混亂,持續的敘述口吻也會讓影片變得枯燥。
(二)多重敘事的承接
西方敘事理論自亞里士多德開始便強調情節的“整一性”,這一特質隨創作不斷演進。但“在當代西方敘事學中,傳統的情節整一性遭到了質疑和解構”。伍爾夫的小說意在記錄哲理層面的“瞬間”,這打破了傳統的整一性,時不時“出現各種離題或者偏題”。
多年后,小說家兼編劇邁克爾·坎寧安以此為靈感,創作了小說《時時刻刻》,并于2002年搬上熒幕。影片上映后摘得諸多獎項,除了兩位影后精彩演繹的加持,坎寧安在原著基礎上的再創作功不可沒。聚焦電影的成功時,也需關注他如何讓小說兼具文學性和視覺化特征,如何從非線性的垂直方向,重新整理了原著的多重性,使新的整一性應運而生。
兩部作品的“多重性”并非指“敘事的多角度”,并不意在“通過互相間有交集的人物的視點來講述同一時空”。這種敘事往往十分隱蔽,人物看似在推進各自的故事線,事實上圍繞著同一個事件推進。而《達洛維夫人》雖時空統一,但描繪的是一個個相互獨立的精神世界,各個情節并行推進,但并不交匯,人物僅有短暫的重合。
《時時刻刻》則是將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三個女性交織在一起:一戰后,弗吉尼亞·伍爾夫書寫著達洛維夫人的命運,也在思考自己是否要從精神折磨中解脫。二戰后,美國的家庭主婦布朗太太生活美滿,將迎來自己第二個孩子,可發現自己與小說《達洛維夫人》中人物有著相似的困境,她不愿被剝奪獨立的空間,想用自殺來逃離索然生活。二十世紀末,出版社編輯克拉麗莎為年輕時的戀人理查德籌備宴會。理查德在身患艾滋后厭世,但因克拉麗莎的挽留而茍延殘喘。三個分別身處20世紀的早、中、晚期的女人被時空隔開,在大部分時間里,只通過“達洛維夫人”這個意象來進行單向交匯。可以說這里的“多重性”與《達洛維夫人》相似,都試圖構建作品中的“平行空間”,凸顯相似困境下抉擇的差異。
(三)重新安置“整一性”
兩者都在多重敘事上下足功夫,但呈現效果截然不同。這是因為《達洛維夫人》與《時時刻刻》“多重性”有著微妙的不同:前者采用“雙重情節”發掘隱性的對照;后者則采用套層結構來構建“多重情節”,最終達到的的整合效果也是顯性的。
原著的“雙重情節”藏在瑣碎的旁觀者視角中。從著墨多少和人物命運來看,作品被伍爾夫刻意地分成了兩個世界:除了因宴會而聚的克拉麗莎、彼得、莎麗等人,也花了大量篇幅來單獨描寫詩人塞普蒂莫斯,講述他在戰爭創傷下崩潰過程。詩人與達洛維一家沒有任何來往,不屬同一個階級,亦沒有往事牽連,他與主角圈子的聯系只建立在一個個偶然的共享空間里,比如他與克拉麗莎同時看向一輛出故障的車。這條支線不與主線直接沖突,延伸至結尾,塞普蒂莫斯的自殺才通過傳聞與達洛維夫人發生短暫的交匯,死亡闖進了她的宴會。
克拉麗莎與詩人的最終抉擇也像是硬幣的兩面。自殺的念頭始終在克拉麗莎的腦海里徘徊,因此一個陌生人也給她帶來極大的震動,她思量這個人自殺的原因,設身處地思索死亡對自己的意義。但克拉麗莎還是“太熱愛生活了”,因此伍爾夫塑造了更為敏感絕望的塞普蒂莫斯,來代替克拉麗莎一步步走向死亡。兩人未曾謀面,但又在平行的內心世界里相互理解。
近似平行的“雙重”結構必然產生比較關系,這是一種類似于二分法的對比。雖然作者對生和死的選擇沒有褒貶,給出了人物極大的尊重。但主次分明的結構,難免會令讀者根據自己的價值觀選擇其中的一方。同時,設置塞普蒂莫斯這一次要情節的意義也讓人困惑:它是否僅僅為了陪襯主要情節而存在?或是為了讓克拉麗莎看到一種向死而生的力量?在對比的陰影下,主次情節被迫歸順于相對一致的話題,產生了兩難的抉擇。
《時時刻刻》并不像《黛洛維夫人》那樣按原著安排對比關系,而是將作者伍爾夫與她筆下的人物并置,形成獨立又包容的套層結構,情節一分為三,“雙重”也變為了“多重”。除了上文提到的“整一性效益”,三個相對獨立的故事還可以打破二維局限,構成了疊唱的立體圖景。
在三個故事里,伍爾夫這一線提綱挈領。一方面,因為真實的伍爾夫總謹慎地安排筆下人物的結局,坎寧安也就站在作者視角,圍繞“達洛維夫人是否會死去”這個線索推進全片:勞拉困在女性無形的束縛里,理查德在艾滋病陰影下茍活,克拉麗莎則用固執的照顧挽留別人也禁錮自己。他們究竟是被留下的達洛維夫人?還是擁抱死亡的塞普蒂莫斯?這給了觀眾無盡的懸念。另一方面,伍爾夫的意識通過畫外音無形融入了敘事轉場,貫穿其他兩個故事:無人打擾的勞拉捧起《達洛維夫人》,伍爾夫的聲音隨著她閱讀的動作出現,書中人物、作者與勞拉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她終將死去的這個事實是否重要?
其他兩條平行線也有自身的獨立價值,而非作為主線的陪襯或解釋。兩個女性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擇,并構成了實實在在的人際關系:理查德跳樓后敘事仍在推進,正是在這剩下的十多分鐘里,克拉麗莎與勞拉打破了平行的敘事時空,超出觀眾的預期走入了同一個畫框,在相互安慰后繼續生活。這一點超越了原本的單向聯系,共同的敘事空間讓情節更為連貫真實、出乎意料,這兩個女人也不再僅僅是書中符號的外化,觀眾也就能真正聚焦“人物如何突圍”這條主線。借助相對整一的多重敘述,既平衡了完整的敘事節奏,也在固定時空里延展了主線。
二、讀者思維的引申與突圍
談及伍爾夫,在意識流小說作家的身份之外,評論家都會格外關注她的女性特質,將其作品歸入20世紀浩蕩的女性思潮中。這一點是有理可據的:在她的另一篇小說《一間自己的房間》中,伍爾夫以“婦女和小說”立論,用幽默口吻鼓勵女性在文學領域爭取自由的創作空間,在社會中獲得獨立的經濟地位。《達洛維夫人》中的克拉麗莎放棄了年輕時自由浪漫的性格,逐漸變成舉辦宴會的工具,這是作者女性意識的投射和反思。后世研究因而多從婦女受家庭、社會壓制的角度來闡述作品。
“羅蘭·巴特在他的書中宣稱‘作者已死’。然而‘作者死亡’則是‘讀者誕生’的代名詞”。這里的“讀者”既指后世文論者,又指的是邁克爾·坎寧安。他既是讀者又是創作者,面對伍爾夫著作提出的既有迷惘,他代表多個時代與其遙相呼應,也從再創作角度進行突圍。
(一)性別身份的包容
伍爾夫在“婦女”和“作家”兩層身份的夾縫中左右為難。她雖然對女性身份極為敏感,但她又無意讓女性主題壓倒創作的獨特性,并常常對作品中的性別意識加以反思。“(婦女作家們)也意識到她們自己的性別的特殊性,熱衷于形成一種她們自己的藝術形式....各種各樣的意識——自我意識、種族意識、性別意識、文化意識——它們與藝術無關,卻插到作家和作品之間。”
伍爾夫渴望找到一個自在的性別身份來對待創作,在不少作品中,都表露了“雙性同體”的創作傾向。她跳出年齡和性別的限制,在《奧蘭多》中塑造了一個雌雄同體的貴族,奧蘭多的性別在四百年中多次轉換,并始終帶著兩種性別記憶和認知進入新的生活。“伍爾夫的‘雙性同體’是在努力讓兩種對立的力量保持均衡,而不倒向任何一邊。完全的‘女性’和完全的‘男性’同樣危險”。這一點在《達洛維夫人》中體現地十分隱晦:克拉麗莎與塞普蒂莫斯共通的精神困境與男女性別的劃分形成對抗。同時,讀者僅能通過片刻回憶,猜測深愛彼得的克拉麗莎在年輕時,也與友人莎麗保持曖昧關系。
但坎寧安的《時時刻刻》把隱性的關系凸顯出來,影片中的三個女人都保持異性和同性的關系:平日極為冷淡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對姐姐卻格外依戀;勞拉和身患癌癥的女鄰居有一個互不言說的吻;克拉麗莎則與同性伴侶共度十四年。因此,小說和影片中所展現的同性吸引,并非僅僅因坎寧安本人對同性戀和少數群體的關注,而更多的是他對伍爾夫作品中時時閃現的“雙性同體”的融合傾向。
(二)避免“個人化”傾向
伍爾夫也努力平衡個人化思想與作品獨立性,盡力避免意識流衍生出的另一個問題:幾乎所有人物的心靈都相仿。她曾在《一位作家的日記》中曾反思個人化的創作方法:文學會被“那個該死的利己主義的自我”徹底毀壞,這個自我“把一部書的趣味、主題、情景、人物都狹隘化了,來反映作者個人”。意識流小說的個人化色彩極為濃重,當每個角色的想法肆意涌出,作者的身影也就時時刻刻投射在他們身上,這可能使作品的主題和人物都狹隘化。
《達洛維夫人》中角色的心理都有一定相似性:他們都分辨不清真實的自我,厭棄當下無意義的生活,但逃離的終點處都站著死亡。可以說筆下人人既是“達洛維夫人”,又是伍爾夫本人的翻版。為了盡力規避這種自我循環,伍爾夫展現不同的階級生活,以突出困境的不可復制:上層社會的克拉麗莎享受并痛苦于女主人身份;中產階級塞普蒂莫斯徘徊在好友戰死的幽靈旁,不辨真假;游蕩者彼得厭惡虛偽做派,卻仍要回到宴會上謀出路。這樣一來在不同的階級視角下,危機的原因就呈現各種形態。
但《時時刻刻》選擇在時代分野上做文章,利用空間構建差異,將差異再次放大。在“人人都是達洛維夫人”的內核下,坎寧安以不同情境作為切入點:伍爾夫處在一戰的陰霾下,也苦惱于不被社會普遍認同的女性作家身份,個人困境的背后是西方人普遍的迷惘;對勞拉“自我”的剝奪,既是這一時期給婦女分派的社會任務所致,也是因她的丈夫經歷過動蕩不安的二戰,渴望一個穩定合意的家庭;二十世紀末克拉麗莎的困境則一方面來自對社會的迎合,一方面緣于理查德的艾滋病,指出性解放運動留下的惡果,也反映現代社會的虛假病態。
坎寧安對宏觀背景和個人視角的融合,讓“達洛維夫人”成為一個形容詞,屏幕外的觀眾不由得反問,自己是否深陷這種困境里?這與伍爾夫的本意不謀而合:“‘非個人化’創作態度將有助于擴大作家的視野……她們將會超越個人的、政治的關系,看到詩人試圖解決得更為廣泛的問題——關于我們的命運以及人生之意義的各種問題”。
(三)原著困境的嘗試解答
伍爾夫創作《達洛維夫人》,是想借其短短一天對完整的人生意義進行思索。但與其說她把“死亡”作為解放自我的方法,倒不如說她僅僅向讀者拋出了一個問題,答案是懸置的。《時時刻刻》沿襲了對死亡的探討,同時以一個讀者的視角,給出了“時間”和“死亡”這兩個層面的回答。
坎寧安格外強調“時間”,而片名本身就是對伍爾夫問題的嘗試作答。影片中的三個女人無論在干什么,意義都轉瞬即逝,無意義感“時時刻刻”存在。一天之所以可以代表一生,因為重復不僅存在于當下和過去,也將發生在未來。克拉麗莎擺脫不了“達洛維夫人”的外號,既是被當下的生活困住了,更是被無法改變的自我困住了。影片讓靜止的人生與永恒流動的時間形成交叉,把“無意義”描述出來,進而提出更為具體的問題:人們要如何面對永恒重復的生活?
面對永恒,死亡是最終選擇,伍爾夫筆下的三位主角雖然對此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斷,他們或埋頭現實,或茍延殘喘,或縱身一躍,但都認為痛苦是無法掙脫的,就算心靈相通,他們也始終無法相互體諒。在小說之外,死亡也是作者伍爾夫留給自己的結局,隱隱暗示著人們始終被命運推搡和安排的無力感。
《時時刻刻》則聚焦小說中“死亡中有著擁抱”的微弱希望,把“向死而生”的道理放大。通過剪輯,它打破了人物困境的屏障,在不同選擇間架起的橋梁。片尾處,勞拉和克拉麗莎終于相逢,弗吉尼亞也能對丈夫吼出自己的痛苦,都讓互相遮掩、互不理解的沖突擺在人們面前,盡管這些短暫的交匯可能無法改變什么,但終究好過消極的避而不談。選擇離開的人能向愛人袒露痛苦,被留下的人則能在現實中慰藉彼此。
影片是有目標的,伍爾夫夫婦痛苦卻坦白的傾訴,克拉麗莎女兒對勞拉的擁抱都試圖讓觀眾理解:人們應如何在認清生活本質后,繼續去熱愛它?站在這個角度,克拉麗莎能放下理查德,勞拉遠走他鄉去追尋平靜,觀眾也能通過影片,意識到要努力在生活的無意義中發掘生命的意義,在無限的困境中,尋找有限的精神自由。
本文認為坎寧安的《時時刻刻》不僅符合大眾電影要求的敘事整一性,展現了西方世界的精神風貌,也通過“非線性”手段將原著中隱性的雙重對比,變為不分主次的多重平行對照。同時,坎寧安脫開了伍爾夫時期的困境,站在讀者立場,關注到了“雙性同體”的傾向和“非個人化”意圖,向大眾拋出問題,也能給出更多的解答可能,作出雙向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