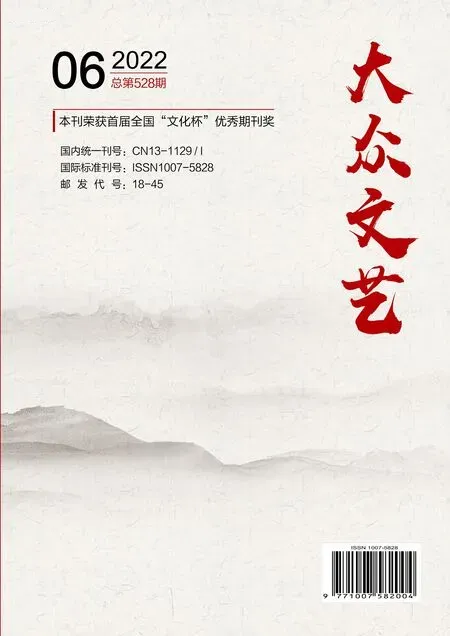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非遺”女性傳承人研究的問題和反思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加拿大圣約翰斯市 A1B 3X8)
無論是在學界還是民間,談論起非遺,人們普遍認為非遺能夠弘揚族群文化,為人類群體帶來整體利益。然而,大量保護記錄工作已淪為僵尸式的博物館呈現,國際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動員,除了旅游開發外,是否真的為人類群體帶來了整體利益,尚無法得到驗證。關于非遺的批判,植根于西方霸權對世界各區域發展的殖民主義式的想象和預設。這種對“鄉愁”“原始”“原生態”的崇拜、倡導和旅游開發,建立在西方已完成和正在享用的現代化之上,卻不公平地對待了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其他欠發達地區,已受到眾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警惕。
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研究和保護已在全球如火如荼地開展了近20年,中國依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指引文件,現已有五批、1709項(包含擴展項)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42項進入世界級非遺名錄。非遺保護及名錄制度在全球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收獲了大量質疑,其中就包括性別議題在非遺領域中的邊緣化。為了糾正這種現象,國內外有關女性傳承人的研究相繼出現。筆者撰寫的《裕固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女性傳承人研究》(2013),是第一篇以非遺“女性傳承人”作為具體研究對象和題目的學位論文。隨后幾年內,相繼產生了十多篇專門研究非遺女性傳承人和非遺中性別問題的學位論文和文章,包括湘西苗族鼓舞女性傳承人(2016)、南寧平話師公戲女性傳承人(2016)、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下的女性傳承人創業探析(2020)等。
中國學者普遍發現,非遺女性傳承人在數量上整體處于弱勢地位。截至2018年5月,五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共計3068人,其中女性740人,占比24.1%。其中,民間醫藥,傳統舞蹈,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等幾個非遺大類中,男性占有絕對比例,似乎有禁止女性參與的傾向,形成了“性別屏障”。非遺制度實施中顯示出的性別問題遠比男女傳承人數量上的差距更為復雜。學界研究表明,不論是出于主動還是被動,女性傳承人天然具有維護本族群原真性文化的優勢。較為封閉地區的少數民族婦女因為早婚、多子女,她們的活動范圍僅限于當地社區和家庭,對外界知之甚少。但是,正是由于這種保守和“無知”,使她們在傳承本民族文化上占據著巨大優勢。同時,在民間美術的學習過程中,男性往往接受開放性的體力型或消費型民間美術的學習,與外界接觸頻繁,更多地對技藝習俗進行創新模仿,而女性不常有在學習或物質消費的過程中產生自身區域文化轉移的機會,多接受較為內斂甚至封閉的民間美術品類學習。這種男性的民間美術私人創造被稱作“仿式”“變式”,而女性參與的私人創造則被稱作“首式”“原式”。
這種對“本真”的堅守和對創新的保守固然使女性天然成為文化傳統的傳承人,但女性并不理所應當堅守文化傳統。比如在印度,女性被認為代表著以精神、傳統、本土與女性為符號的“家”。“……女性在國族主義新父權之下,被期望穿著特定的服飾及保持其他傳統,以背負代表本土的精神與民族主體性。……當男人走向‘世界’時,他們要求女人留在‘家’中。”在西方殖民主義對印度民族情感的傷害和剝削下,只要印度女性(不論是否出于自身意愿)仍然在“家”穿著民族服飾,保持民族傳統,實踐民俗儀式,印度人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自豪就不曾被殖民主義和全球化所消滅。可以看出,保存傳統的角色定位并不總能給女性帶來正面影響,相反,有可能加強女性低下的地位,并將女性囚困在“傳統”的話語里。同理,在非遺化的過程中,民俗的性質已經改變。“這種日常之外的非遺化可能迫使女性重新展現社會的原有秩序,并將其限定在原有的社會地位上。”
在不同民族中存在的或輕或重的父權認知,也影響著女性傳承人的傳承。穆斯林社區普遍具有男性主宰、女性依附的性別觀念,認為女性要維護夫權,聽從男人的規勸和安排等。外出展示、舞臺表演或演唱等非遺傳承活動被認為不符合回族女性的性別規范,成為家庭不穩定的因素,因此,這些傳承活動在一些自主傳承意識淡薄的女性中得不到相應的支持和參與。“她們在講述自己的手藝如何走向產業和市場的時候,首先都會把功勞推給自己的丈夫(丈夫并不在場),她們認為由于丈夫的開明和支持,自己才能參與到市場中。”這些例子表明,女性傳承的非遺活動常常受到家庭阻撓和社區非議。若不是因為這些女性傳承人增加了家庭中的經濟貢獻,她們將不被允許繼續從事這些非遺活動。這意味著,與此同時,大量沒有經濟效益的女性傳承活動已被限制和禁止。
由于獨特的身體、心理特征以及其所處的社會分工與經濟地位,女性在手工技藝類非遺的傳承人中占據較大比例,如山西侯馬刺繡、洮州回族刺繡、魯錦、壯錦等。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刺繡手藝的評價往往與一位婦女是否賢惠勤勞相關,是考量婦女道德節操的標準。土族女性出嫁時,“夸富宴”像工藝博覽會一樣展示新嫁娘琳瑯滿目的繡品嫁妝,土族盤繡成為社區評價的公共物品。但是,刺繡作為一種主要由女性傳承的技藝,具有一定悖論,尤其是當刺繡產品的主要用途是婚禮等儀式節慶時。以回族洮州刺繡為例,當地婚俗中保留著必須陪嫁刺繡物品的習俗。當婚慶需要大量的刺繡作品,以體現女性的巧手和作為女性價值的刺繡技藝被商品化。非遺化和市場化的推進又使更多的女性參與到了這種商品化的刺繡活動中,這造成一部分(已婚)女性的經濟解放,但同時,卻使得當地群眾通過刺繡來判斷一個女性稱不稱職、通過婚姻和生育來圓滿一個女性生命歷程的族群觀念得到加強,進而影響到當地未婚女性和整個回族女性的生活和生存環境。
因此,我們應當注意,非遺項目性別化保護雖然可以有針對性地發展女性的強項,但也限制了女性的多元發展,使更多的女性傳承人止步于傳統技藝,將女性禁錮于家庭和社區之中,“困在”鄉愁和傳統角色之中。比如,“繡娘”“舞娘”等稱謂本身就含有濃重的性別指示(歧視),很難說不是對固有性別模式的一種強化。擅于進行理論批判的民俗學家已經發現,當人們的認知仍停留在過度禮贊傳統和“鄉愁”的階段時,一種值得提倡的活態的生活世界觀應該能夠解決當下的現實問題。筆者認為,與其將“非遺”神圣化為一種改變整個人類文化生態的必由途徑,不如更加實用一些,探討在非遺制度下的個人是否因此受益,并獲得怎樣的收益。因此,我們要看的不是在非遺的框架下保存了多少“遺產”,記錄了多少可能再也聽不懂的歌謠,而是要研究非遺在現代日常生活中對“人”的現實意義。
“文化”不是性別不平等的正當理由,保護一個族群(的文化遺產)不能通過犧牲其中的一部分人(比如女性)來實現。女性天生具有保持傳統的優勢和特性,但是她們并不因此是傳統當之無愧的“守護者”,尤其是當傳統扼殺了女性其他可能性,讓其只停留在傳統角色上時。過度強調手工技藝類非遺對女性的吸納,有可能成為固化女性性別特征的手段之一。我們要防止以“保護和開發民族文化遺產”為借口產生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誤解、歪曲或濫用,防止倚重男權的性別偏好與性別歧視彰顯和抬頭,提防因片面強調民族文化的“完整性”而固守性別歧視的文化內容。
中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旨在從根本上解放自然人,使人(不論男女)都具有充分發展的選擇,成為終極的自由人。提高婦女地位,促進性別平等,是全世界女性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夢想,也是建黨一百年的中國共產黨終極的革命任務。非遺女性傳承人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非遺不僅僅是經濟制度,更是可能改變女性生存環境和社會地位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但是,非遺理念的引入和制度實施必然會在中國大地上產生在地化和水土不服的問題。切記不可回避性別不平等與女性受壓迫的根本原因,避免以“非遺保護”的名義限制女性的可能性和發展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