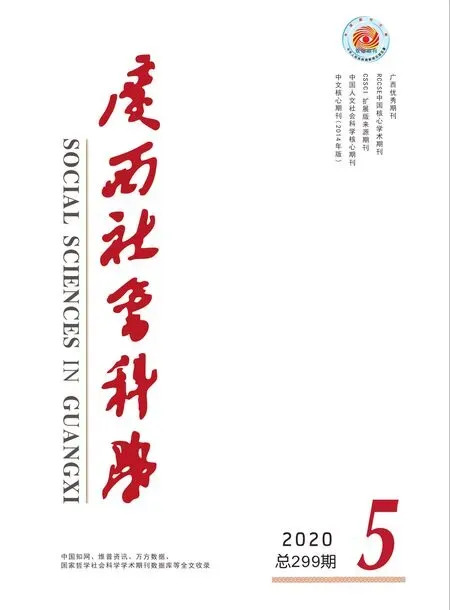民族志知識重構與女性藝術
2020-03-13 04:48:27張曉佳
廣西社會科學
2020年5期
張曉佳
(1.上海外國語大學 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083;2.復旦大學 新聞學院,上海 200483)
人類學試圖通過對大量文化產品的分析來了解社會結構及其象征再生產,物品是文化產品之一,是人類學家尋求社會秩序及其表征機制的一種媒介。通過這些產品,讓社會表述自己,在世界中尋找意義。而藝術人類學定位于立足從藝術的角度研究人的學科,力求破除西方中心論思想的束縛,實現全景式的人類學藝術(史)景觀。新式的藝術人類學研究強調對人類藝術活動當中的藝術行為和人的在場進行整體關照[1]。女性主義民族志在廣義上將婦女從事的藝術工作中的文化、性別和經濟相互關聯起來。大量女性主義民族志作品中呈現出女性的聲音,她們向人類學家講述自己的生活,并聲稱這些解讀和女性主義者的學術視角一般具有有效性。女性的解釋常常挑戰并與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語境相悖,終結了人類學和民族志中女性的歷史性“沉默”[2]。本文從兩種女性藝術作品形式,即婦女紡織及其商品化、婦女與染布藝術,解讀女性經驗對民族志知識重構作出的貢獻,認為除文本形式表述創新外還體現在兩個方面:理論層面的政治化訴求引發的知識建構,實踐層面的經濟、文化日常性。
一、女性主義民族志理論的政治化
Strathern發現,在人類學和女權主義之間的關系中存在一種“尷尬”,她對作為女性研究者在研究中尋找女權主義空間的經驗進行了批判。……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名作欣賞(2021年24期)2021-08-30 07:02:24
兒童繪本(2018年22期)2018-12-13 23:14:52
讀者·校園版(2018年13期)2018-06-19 06:20:12
Coco薇(2016年2期)2016-03-22 16:58:59
讀者(2016年7期)2016-03-11 12:14:36
文學教育(2016年27期)2016-02-28 02:35:09
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年4期)2015-06-23 08:50:19
爆笑show(2014年10期)2014-12-18 22:27:48
語文知識(2014年7期)2014-02-28 22:00:18
中國現當代社會文化學術沙龍輯錄(2011年0期)2011-10-27 02: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