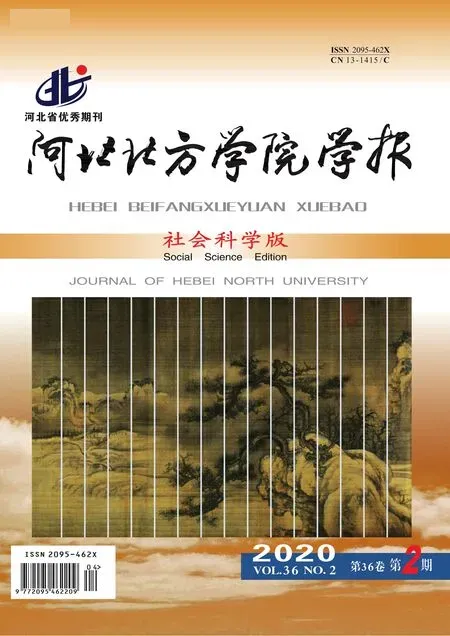身體演出視域中的“罪與罰”
——評麥家《人生海海》
王 雨 晴
(寶雞文理學院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陜西 寶雞 721013)
麥家創作出《解密》《暗算》與《風聲》等一系列諜戰題材作品,并以充滿懸念的故事情節、縝密緊張的推理和奇特的天才人物敘述備受肯定。新作《人生海海》仍是關于英雄的故事,但從“造神”到“推翻神”這截然相反的舉動映射了英雄歸來后的窘迫和面臨的懲戒。“受傷”的身體成為主場并由此打開故事敘述的闕口,通過精神歸鄉祈求達到作者以及作品人物的雙重“救贖”。以“我”對上校故事的講述體現個性化敘述,同時也顯示出作者對歷史的介入。在對駁雜人性以及身體秘密的破譯中,“罪與罰”的主題浮出水面。
一、革命時期英雄身體的“罪與罰”
古希臘時代,對身體美學的崇尚包含了對統治者和造物主偉大神力的肯定。反觀中國,身心二分法才是主流觀念和真理。身體的自我主宰力一直潛伏在歷史地表之下,但其政治功能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承擔著重要的角色。古往今來,在中國人眼中身體同政治和文化緊密相連并產生連鎖反應,更在一定程度上被賦予隱喻色彩。五四啟蒙時期,身體作為個性解放的重要象征符號來完成其與社會話語的合作。文化革命時期,知識分子上山下鄉改造,通過親身實踐與土地接觸來達到精神上的凈化,也與主流價值觀念遙相呼應。身體成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權利博弈的砝碼,與主體間的依附關系發生微妙的斷裂。《人生海海》中,革命時期的英雄上校以身體為籌碼打入敵人內部,在獲取情報的同時也蒙受了恥辱,日后對其身體罪惡的審判成為必然。
英雄上校蔣正南在村子里有一個眾所周知的綽號——太監,廣為流傳的說法是他在戰爭時期被敵人物理閹割而留下這終身恥辱。但事實迥然不同,還有更難以啟齒的身體秘密使上校不為此作過多辯解。這種被認為閹割的焦慮換作任何人都難以承受,而上校用強大的人格面具換來表面云淡風輕的生活。榮格在談到人格面具時認為,其“目的在于給人一個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承認,也可被稱為順從原型”[1]。偽裝是保守秘密的盾牌,但同時盾牌越強大,暴露后的殺傷力也越難以預測。上校的身體在革命歷史的斗爭中卷入權力爭奪的泥沼,在“罪”與“恥”的交織中愈發沉重。上海的暗店里,上校為接近女鬼佬獲取情報和小媽發生關系,致使女鬼佬心生懷疑和妒忌而在他身上繡字并拍照。隨后上校的“風流”名聲又使他猶如被豢養的寵物般被女漢奸囚禁到北京,并為其提供屈辱的性服務。這些恥辱經歷難以被他曾立下的戰功消解,與此相反的是戰績越輝煌,這“恥”越加深。“罪可以通過懺悔來洗刷,恥卻不能。”[2]上校選擇用人格面具躲避與守護這致命的秘密,但沒有宗教的皈依、寄托和凈化,懺悔也變得無計可施。再加上當初在性上的不節制,這一切都使他的身體徹底帶上罪惡的因子。“他這輩子最后悔的事大概就是沒有用自己的技術把肚皮上的字涂掉,發了瘋都惦記著,想涂掉。”[3]257尊嚴的崇高感失效,“知恥”的內在拷問心靈,使上校首先承受的是“自罰”,即強烈的負罪心理。從村民對他是太監謠言的散播,到聲勢浩大的批判會被當眾扒下褲子以至于瘋癲,外界懲戒以主流話語的規訓機制為主,使這副肉身背負沉重的“罰”。文化大革命時期,上校被冠上“人民公敵”和“十惡不赦”的頭銜進行批斗。從始至終,上校的身體都陷入革命斗爭的撕裂和爭搶中,沒有固定歸屬。從小媽不允許上校同暗店其她女性接觸想據其為己有,到女鬼佬在其身上繡字表明她對上校身體的所屬權,再到女漢奸以奴隸的方式將上校囚禁北京,這一系列權力與身體的交接置換,種種“通奸”的過程足以構成上校的“罪”。無論他日后殺多少鬼子,在抗美援朝期間立下多少功勞,這種被浸滿恥辱的“罪”都難以抹去。
十七年文學里,《紅巖》中所塑造的英雄群像以鋼鐵般的革命意志在渣滓洞忍受各種非人的酷刑而引起轟動。同樣以身體所屬權被剝奪來換取革命的勝利,捍衛自身的信念,上校的身體以特殊方式打入敵人內部并衍生出“罪”,身體成為主流話語警示的媒介,在經歷曾經的屈辱與不堪后,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同時,這種罰也頗具吊詭性。因為身體不得已以工具形式發生反叛,但心靈從未被敵人規訓,肉體與心靈的分離卻成為了懲戒的原因。“對于中國的思想者來說,自我操控不是來源于肌肉,而是來源于‘心’。”[4]但革命時期心靈的皈依與否被擱置,身體懲戒卻變得更為重要。批斗、示眾和發瘋成為上校必然面對的懲罰。這種“罪”主要緣于曾經成為敵人的肉體俘虜以及沒有加入革命話語的中心。《青春之歌》中林道靜前期小布爾喬亞式的敘事曾遭到激烈批判,隨后林加入革命的洪流中,通過“才子佳人”轉換為“英雄美人”的宏大話語敘事才使人物獲得合法性和肯定。英雄的身體需要在主流話語和革命中尋求意義與歸屬價值。人物被卷入歷史和革命的漩渦中呈現出一種粘稠與扭結的狀態,但又唇齒相依。身體不僅加入這場戰爭,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承擔著媒介和催化的作用。“這種被民族主義所‘制造’的身體卻是以‘恥辱’和男性尊嚴的喪失為代價的。”[5]由此,麥家在作品中突顯出男性身體也能被征用這一觀念,并討論被迫放逐的身體能否得到承認和正視。與此同時,在這個故事中欲望的交織也不可忽略,如果上校在“性”上稍加克制,隨后事態的發展是否能減輕這種身體上的“罪過”也未可知。身體的歸屬權從最初成為各種權力交鋒的爭奪點到被納入主流話語的規則下,其間道德的拷問、心靈的恥辱以及社會的懲罰都會產生巨大的張力。
二、繁復人性中的“罪與罰”
和革命時期英雄身體的“罪與罰”相對應的是繁復人性中的罪惡因子。革命年代政治風云席卷全國,權力相交更迭,尤其是“文革”使外在的秩序規則遭到嚴重破壞,朝不保夕與提心吊膽的日子成為滋生罪惡的溫床,使在場的每一人都難逃罪與罰的懲戒。現代文學的產生和發展也與“暴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王德威曾談到魯迅和沈從文關于“砍頭”的話題:“回溯魯迅自述的創作緣起,我們可說他在砍頭一景中,不僅看到中國人的無知與無恥,也更感到個體生命符號系統的崩裂,而此一崩裂足使社會文化意義停止運作。”[6]可見,身體遭受摧殘的奇觀被賦予了文化象征意義。這種暴力帶來的不僅是震憾的感官體驗,更多的是對隨身體而消逝的個體價值意義的慨嘆。反觀《人生海海》,雖沒有震顫人心的殺戮場景,但對上校身體的懲戒以及由其身體引發的屈辱和報復,都展現了人性中殘忍的眾生相。上校身體的秘密是村民最大的疑惑和好奇,在近乎密閉的鄉村話語空間里,流言以或夸張或變異的方式在人群中蓬勃生長。它不僅是村民茶余飯后的談資,更成為一種畸形的癖好,并以“窺探”的形式被交流、討論甚至咀嚼。“群體是刺激因素的奴隸。”[7]某一話題的傳染性和暗示性能使人群立即沸騰,同時呈現出具有“統一目標”的集體假象,也使每一個看客成為罪惡的參與者。“當大是大非的教條轉化為瑣碎的家常倫理,當堂而皇之的革命遭遇卑劣的人性時,一切都變得如此粘滯曖昧。”[8]
作品中最能體現“罪與罰”的個體便是“我”爺爺。他既有溫暖的亮色,同時又彰顯出人性中的弱點。為了洗清父親是雞奸犯的嫌疑,爺爺和公安局做了交易,通過揭發上校的藏匿地點換取大字報上對父親白紙黑字的澄清說明。這次背叛致使上校受到囚禁、凌辱直至瘋癲,成為爺爺直到死亡都無法擺脫的“罪惡”夢魘。英雄事跡在民間倫理面前脆弱得不堪一擊,成為必要時刻無謂的犧牲品。爺爺的余生在驚恐和懺悔中度過,變得神經而敏感,最后上吊自殺。懲罰沒有結束,父親延續了纏繞爺爺的精神世界,在潛意識中和死鬼進行激烈的搏斗。“上校是被活人逼瘋的,他是被死鬼嚇傻的”[3]318,這種道德的審問和煎熬雖然接受了“罰”,卻是一種被動式的,以至于使人陷入無休止的矛盾痛苦和心靈混亂。勇于接受“罰”,以反思、追問和懺悔的方式達到內心的平靜與舒展是文學所永恒倡導的。父親與爺爺的自責和懺悔是一種倫理上的承擔,相比之下,林阿姨試圖拯救自己和上校的作法都凸現出“罰”的真正意義。抗美援朝時期,林阿姨向上校求愛,但上校因為自己身體曾經遭受的恥辱無法接受這份感情。內科醫生以卑劣的方式在夜晚得到林阿姨的身體卻嫁禍給上校,使得林阿姨以為自己的身體已經屬于上校。在遭到上校拒絕后,萬念俱滅下她向上級告發上校強奸,從而中了內科醫生設計的圈套,兩人結下致命的誤會。上校因此被開除軍籍,開啟了一段動蕩的人生。如果說對上校的“污蔑”是林阿姨的“罪”,那么林阿姨在上校瘋癲后守護他直到去世便是虔誠地接受了這份“罰”。她曾經是上校跌宕起伏人生的直接導致者,現在又是開啟上校新生活的拯救者。在后來的漫長歲月中,兩人相濡以沫,互相陪伴。簡單的柴米油鹽里消解了曾經“罰”所帶來的沉重窒息感和蠱惑感,并轉化為愛的話語。這種救贖是共生的,從而使林阿姨避免成為第二個爺爺。
“閱讀麥家需要有一種游戲精神,而理解麥家也許還需要有一種抽象的沖動。”[9]在《人生海海》中也不乏狡黠的人性,如行跡頑劣且人品不正的小瞎子只因會阿諛奉承而在文革期間“翻身”成為領導者,誣陷上校和父親是雞奸犯,并在一切都塵埃落定后仍心懷怨念。這種“翻身”后的暴力和丑惡嘴臉在劉震云《故鄉天下黃花》中也有所顯示:趙刺猬與癩和尚的獸欲被通過暴力取得的權力所激發,人性的猙獰面貌昭然若揭。在那個動亂且秩序崩潰的時期,忠誠與服從是成為標桿和掌權者所必備的條件。同時,麥家在這部作品中也將崇高的文字從神壇上請下來,呈現出陌生與丑陋的面孔,如大公報上的字和小瞎子用電腦敲打出來的字,尤其是刻在上校身體的字都成為罪惡的幫兇。
人性隨著世事變遷和趨利避害的本能而愈加駁雜,“罪”和“罰”也不能被簡化為承接關系。上校鐘愛的黑白兩只貓有著獨特的隱喻,幽微的人性絕不是明亮和黑暗的二元對立,而更多存在于兩者交互的陰影中,它們相互對抗、轉化與融合。人是社會關系的產物,在人生浩瀚的洪流中總會不同程度地與他人產生沖突或對抗,甚至形成高危關系。作為對“罪”的彌補和悔過,如何承擔“罰”以及深入內心反省并擺脫由“罪”產生的非理性困惑,都體現出人類能真正為自己行為負全責的勇氣和態度。
三、精神歸鄉中“罪與罰”的完成
在文學史上,故鄉以某種原質性的存在或隱或顯地影響作家的創作,構建獨特的人生和家國想象。魯迅筆下的魯鎮、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及蕭紅呼蘭河畔的小城等,都不僅簡單地意味著某個地理空間,更是作家敘述的原點和精神的起點。麥家曾坦言《人生海海》的創作是他與故鄉的和解:作家在精神歸鄉中尋找對自我身份的確認,作品人物也在“歸鄉”中通過承擔“罰”來尋求心靈救贖。《人生海海》的前兩部都以“我”的視角來呈現英雄上校的故事,或直接對話,或詢問他人,或偷聽。第三部同樣以“我”來反觀家族歷史,這在莫言、格非和蘇童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所展現,體現了作家介入歷史的欲望。麥家此次嘗試的家族敘事延續了先鋒主義的解構形式,但沒有掉入后現代語境中“欲和亡”的話語漩渦。雖有頹敗色彩,但終究給人一種千帆過盡的溫暖。在這個“歸鄉”的時空容器中,上校與“我”以及神性與人性都承擔著不同程度的罪與罰。
“我”的離鄉更多是被迫的逃離,逃離爺爺因揭發上校所犯下的“罪”導致的連坐。從少年到步入老年,“我”的再次歸鄉體現出一種對“罰”的承擔。因為家族是一個統一的生命體,其內在的創傷體驗以血脈相連的方式延續,也為“我”此次歸鄉尋求救贖增添一份寓言的特色。麥家在小說中令“我”與上校之間也形成了一種內在的同構關系。在整個話語敘述的空間中,上校的身體是故事起承轉合的關鍵,它以“秘密”的形式存在,并以“解密”的方式結束。從戰場歸來時他的身上已經攜帶罪惡的因子,不為倫理道德容忍。這次“歸鄉”經歷的誣陷和批斗與自我心靈救贖相悖,強制性的約束在帶來懲戒的同時也加深心靈的創傷。“因為這個小說其實和革命、暴力、創傷是糾纏不清的。”[10]顯赫的功勛被秩序混亂的革命時期拋棄與消解,身體的規訓成為必須,并承載著沉痛的政治意義。真正充滿原始強力的“罰”應是人心的自覺承擔、懺悔和頓悟,而絕非只是身體外部的刑罰。麥家在此也呼喚身與心的內在統一性,但社會的懲戒機制不會因人曾經的付出與犧牲而判別,身體經歷的既定事實也不容任何辯解。林阿姨將遍體鱗傷的瘋癲上校帶離村莊,再離去的上校沒有了往日的意氣風發,變成一個只有7歲智商的細心養蠶的孩童。從最初誓死捍衛自己身體秘密到主動顯示給“我”看,這實為諷刺。同時,上校的“再離去”也承接起“我”的歸來。從異國返回故鄉的“我”看到家鄉的斷壁殘垣,一切物是人非都已成過眼云煙,但家族曾經給上校帶來的傷害難以從時間的洪流中抹去。被放逐和漂泊的個體命運也使這種尋求精神救贖成為必然。“我”去探望再離去的上校和林阿姨,在近距離的接觸中看到鶴發童顏但失去了智者面貌的上校再也沒有戰場上的叱咤風云,卻是一身安然。印在上校身上罪惡的文字被林阿姨再創造出一幅畫,“罰”的意義也伴隨著離鄉以及愛人的陪伴消解了。“我”歸來目睹了父親承受著背叛的原罪而耗光了所有力氣,這種對罪惡的懺悔同樣存在于“我”身上,“罰”的深刻性以超越代際的形式一直存在。
回鄉后觀望到故鄉的衰落與物是人非,也承接起“我”的再離去。尋夢、救贖和對“罰”的擔當構成了這次歸鄉的意義,同時也是“我”再次離鄉的基礎。在魯迅的《故鄉》里,“我”從對封建宗法制度的叛逃到歸鄉尋找精神皈依,但現實的荒涼和根深蒂固的封建積習讓“我”望而卻步,理想與現實產生斷裂和剝離。在不同語境空間的歸鄉中,麥家為其鍍上一層溫暖的底色。誠如書名《人生海海》,“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了生活后依然熱愛生活”[3]310。“我”既是故事的參與者又是觀望者,隨著一切塵埃落定,“我”也接受成長和洗禮。上校再離開村莊更多的是離開這個空間帶來的創傷和懲罰,秩序顛倒的村莊和上校后半生的精神失常隱喻著“罰”和“贖罪”。上校用后半生償還來自身體上刻字的恥辱,“我”的離鄉是被迫以另一種形式“逃避”爺爺背叛的原罪。相同的是,兩者都被放逐到這個世界之外。通過講述,敘述者“我”也與上校一同經歷與成長。兩者雖在時間上錯位,但卻形成一種內在的同構關系。
從“我”少年離去到長大后還鄉直至再離去,其間的懺悔和領悟顯現出成長小說的特征。前半部分上校的故事與后半部分“我”的故事殊途同歸,都在還鄉中實現了對“罰”的承擔和心靈皈依,在時間和空間上都使“罪與罰”的主題更加立體。作家以及主人公的精神歸鄉不僅成為對記憶的緬懷,更是尋求精神救贖與再次出發的動力和勇氣。伴隨著現代化和物質文明的發展,精神歸鄉越來越成為作家在面對精神焦慮與擔憂,以及在主流舞臺表達受挫后的庇護所。英雄從戰場歸來返回民間,聚光的舞臺落幕后該如何適應這個異質性的話語場域,成為麥家思考的一個問題。《人生海海》兼容歷史以及現實生活,展現的辯證英雄主義更多地夾雜著罪過、笑柄以及溫暖的底色。
作家對革命的想象和還原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主題之一,體現出其站在后現代的語境中對歷史的“祛魅”。麥家在《人生海海》中融合了繁復的人性和革命暴力,并以上校身體為秘密軸心演繹著獨特的罪與罰的故事。身體視域下的鄉土話語敘述空間打開了麥家講述革命歷史的新視角,也呈現出萬花筒般的世界。其間家族故事、村莊變遷以及人性的駁雜一一得到展現,并在精神歸鄉中尋找救贖之道。“在歷史、生命以及文本即將終結的時候,所有的親歷、轉述都顯現出某種纏繞在個體生命之中的混沌、模糊。”[11]在這個消費快餐以及信息爆炸的時代,傳統的道德面臨著濃縮和擠壓的危險。麥家在此試圖尋找解決途徑,包括對“罰”的主動承擔,從而成為一個大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