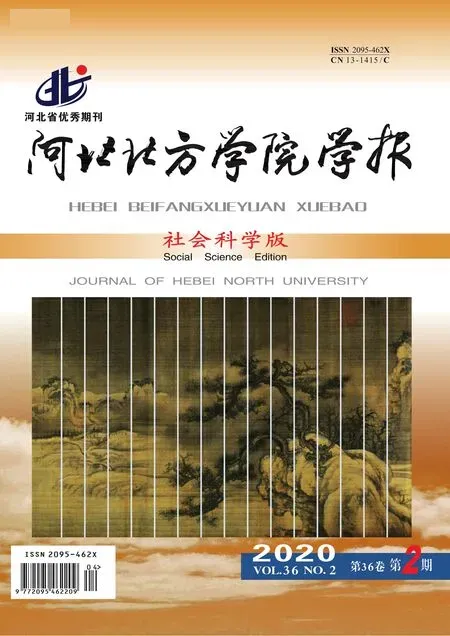五代太常卿太常博士考論
馮 盛
(武漢大學 歷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太常寺,禮樂之司也,始設于北齊,唐沿置。太常卿與太常博士作為太常寺之屬官,在國家禮制運行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目前,學界對唐代太常卿與太常博士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對其設置沿革、入仕遷轉及職能演進等問題已有較為深入的探討①。然而就筆者所見,有關五代時期太常卿與太常博士的研究尚付闕如。事實上,厘清五代時期太常卿與太常博士的設置情況及職能演進,不僅有助于深化對中晚唐以來官職分離現象的認識,同時可為北宋前期太常官制的研究奠定基礎。下文將梳理五代時期太常卿與太常博士的設置脈絡,觀察兩者職能的變化,以討論其階官化進程對宋代官制產生的重要影響。
一、太常卿的設置與職掌
太常卿,始置于南梁,北齊時設為太常寺長官,隋唐兩代皆沿置。在唐代,太常卿為正三品,“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凡國有大禮,則贊相禮儀;有司攝事,為之亞獻”,“若大祭祀,則先省其牲器。凡大卜占國之大事及祭祀卜則日,皆往蒞之于太廟南門之外”[1]394。按此記載,太常卿在大型祭祀中掌“贊襄禮儀”事,主管禮儀事務。據任爽觀察,中晚唐時太常卿的職能不再僅停留于掌事務的層面,亦參與禮制的撰定[2]。《舊唐書》曾載,高宗儀鳳二年(677)因《顯慶禮》“多有事不師古”,朝廷特命太常卿裴明禮、太常少卿韋萬石與博士賀敱、賀紀、韋叔夏和裴守真等“參會古今禮文”[3]818,撰定儀制。德宗貞元二年(786)十一月王皇后崩,“遂命太常卿鄭叔則”撰擬皇后喪禮儀制[4]685。貞元七年(791),太常卿裴郁上奏議定禘祫之禮,“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后,故得合食有序”[3]1001。除了擬定儀制外,太常卿亦負責為皇帝定謚。哀帝天祐二年(902)正月“甲子,太常卿王溥上大行皇帝謚號、廟號”[3]789,但由于王溥所定之謚為美謚而引發朱溫不滿,王溥很快被罷官。繼任者張廷范改王溥所擬之謚,重新定大行皇帝謚號為“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襄宗”[4]19。
及至五代,太常卿的職能基本包含行禮與制禮兩個層面。唐代太常卿在郊廟和社稷等大型祭祀活動中擔任禮儀官,負責“贊襄禮儀”[1]394。五代時,太常卿除了繼續贊襄導引大型祭祀活動外,還常常代表朝廷赴藩鎮行加恩禮。為了拉攏地方割據勢力,朝廷往往會授其榮銜以顯示朝廷對其恩寵優渥,而掌禮儀事務的太常卿自然成為赴藩鎮主持行禮儀式的不二人選。后晉天福二年(937)十一月,“命太常卿程遜、兵部員外郎韋棁充吳越國王加恩使”[5]1009。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太常卿往往冒著生命危險遠赴藩鎮主持行禮,太常卿程遜此行不順,回程時即“遭風水而溺焉”[5]1280,不幸遇難。
五代太常卿的制禮職能首先表現在為皇帝及其先祖擬定謚號。由于五代時期政權更迭頻繁,太常卿除了保留在唐代為大行皇帝定謚的職責外,還需負責擬定皇帝先祖謚號。后唐代梁后,太常卿盧質建議“立廟追謚”唐哀帝,為其上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6]650。石敬瑭建梁后因追尊親廟,特命太常卿梁文矩“奏定四廟謚號、廟號、陵號”[5]1002;郭威建周后沿襲了前代故事,亦命“太常卿邊蔚上追尊四廟謚議”[5]1472。其次,太常卿掌撰廟用樂舞之事。后唐莊宗同光二年(924),太常卿李燕奉旨擬定太廟樂舞名,“懿祖室曰《昭德之舞》,獻祖室曰《文明之舞》,太祖室曰《應天之舞》,昭宗室曰《永平之舞》”[5]425;后漢高祖天福十二年(947)閏七月,權太常卿張昭定祭祀太祖高皇帝時“依舊奏《武德之舞》”,祀世祖光武皇帝時“依舊奏《大武之舞》”;在太廟酌獻文祖明元皇帝室、德祖恭僖皇帝室、德祖恭僖皇帝室與顯祖章圣皇帝室時,分別奏“《靈長之舞》、《積善之舞》、《顯仁之舞》與《章慶之舞》”[5]1336。
更為重要的是,太常卿還常常負責編定敕令與禮書。后梁開平三年(909),太祖朱溫命太常卿李燕與御史蕭頃、中書舍人張兗、大理卿王鄯等考辨前代敕令并撰擬本朝典制,1年后李燕等“重刊定律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目錄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請目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5]1694。后唐時,明宗認為唐人鄭余慶所編《書儀》與古禮不合,特命太常卿劉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劉岳與太常博士段颙及田敏等重新編訂禮書,后人稱其書“猶時有《禮》之遺制”[6]632-633。據筆者統計,五代時期先后曾有26位官員正任或兼任太常卿(表1)。

表1 五代太常卿(含兼任)設置表
由表1可見,除竇儼曾任“判太常寺事”外[7],其他各官兼任太常卿時皆授“判太常卿事”一職。宋人李昉曾言,唐代“丞郎兼判他局者”,“或官高則言判某官事,或官卑則言知某官事,或未即真則言權知某官事,或言檢校某官事”[8]403。而表1中本官品秩低于太常卿卻任“判太常卿事”者為數不少,如后晉高祖天福四年(939)四月甲申,因太常卿程遜出使吳越行冊封禮未歸,晉廷曾命“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棁“權判太常卿”[5]1028;后漢高祖天福十二年(947),吏部侍郎張昭曾權判太常卿事[5]1337;后周太祖廣順三年(953)十月庚戌,“以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田敏權判太常卿”[5]1449等。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及尚書左丞官品皆低于太常卿,而猶言“判太常卿事”。由此看來,李昉所言之唐制于五代時或已廢而不行。或許在時人看來,“判”字已經沒有表明“官高領某低職”的含義③。
二、太常博士的設置與職掌
博士之官始見于秦漢,迨及曹魏,別置太常博士,參議朝廷禮儀典章之事,其后歷代因之。據《唐六典》載,太常博士4人,“掌辨五禮之儀式,奉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鄉導贊其儀。凡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行而為之褒貶”[1]396。但有唐一代太常博士的員額并不固定,如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曾減太常博士為3員,至憲宗朝又增太常博士為6員[9]。
五代之初,受戰亂影響,太常博士的員額亦曾縮減。后唐莊宗同光元年(923)十一月戊申,中書門下以“朝廷兵革雖寧,支費猶闕”為由,奏請諸寺監“置卿、少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二員,余官并停”。太常寺由于掌邦國大禮,許另置丞一員,莊宗從之[10]323。時論以為,莊宗既自詡中興唐室,“宜恢廓”舊制,不當因省官而“驟茲自弱”[5]419。不久之后,后唐又恢復了太常博士4員的舊制。據史載,明宗長興三年(932)正月,“太常卿劉岳奏:‘先奉勅,刪定鄭余慶《書儀》者,臣與太子賓客馬縞,太常博士段颙、田敏、路航、李居浣,太常丞陳觀等,同共詳定,其書送納中書門下’”[10]267。
以現存史料所見,上述4人中唯段颙任太常博士最早,任期最長。明宗天成四年(929)九月,段颙已為太常博士并參與朝廷關于派遣官員祭祀宗廟的討論[5]554。后唐末帝清泰三年(936)九月,車駕將過徽陵,“太常博士段颙奏:‘河陽路當徽陵,今車駕經由,合親朝謁’”,請末帝親謁徽陵[10]59。后晉和后漢時,段颙仍居太常博士一職,并兩次尋檢前代宗廟故事,奏請新朝建本朝親廟及禮儀制度:晉天福二年(937),請晉高祖石敬瑭立七廟;漢天福十三年(947),復請“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外,“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更立六廟”[10]30。
受史料所限,很難爬梳出五代時期歷任太常博士的任職時間及人物事跡,從零星的記載中可窺得五代時期部分太常博士的任職情況:后唐莊宗時期,劉昫曾任太常博士[5]1172;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王丕任太常博士,奉詔令尋檢前代故事,為太常卿定謚提供參考[5]1894-1896;天成三年(928),呂朋龜任太常博士,詳檢故實,奏請立景宗皇帝宗廟于陵園[10]39;后晉天福中,賈緯任太常博士,“以史才自負,銳于編述,不樂曲臺之任”,又改為“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撰”[6]658。由是可見,至后漢時太常博士的基本職權仍為“掌辨五禮之儀式,奉先王之法制,通變隨時而損益”[1]396。
后周時期,太常博士的職權在議禮以備顧問的基礎上有所擴大,顯德二年(955)八月,朝廷下詔“今后諸處祠祭,應有牲牢、香幣、饌料、供具等,仰委本司官吏躬親檢校,務在精至。行事儀式,依附《禮經》,大祠祭合用樂者,仍須祀前教習。凡關祀事,宜令太常博士及監察御史用心點檢,稍或因循,必行朝典”[5]1582。可見,凡有關祀祭之事,無論是行禮儀式還是祭物貢品,皆由太常博士與監察御史一同點檢,務必保證祀儀符合朝廷擬定規范,太常博士除掌行禮與損益禮制外,還兼具監察祀儀之責。顯德五年(958),御史臺奏請“諸祠祭有同日享祀,監祭使具狀申御史中丞,請差官祀。若是無官可差,監祭使牒太常博士通攝”[10]58-59,至此太常博士又有“通攝祠祭”之權。
三、太常卿與太常博士的階官化
職事官階官化是指唐代以來隨著新設的使職逐漸取代了原本職事官的職能,原先的職事官僅發揮階官的作用,用來表明官員的品秩與俸祿。早在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李勣“轉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11]3819。“同中書門下三品”這一使職意味著李勣可以出席政事堂和參與宰相政務。因這一使職并不帶品階,所以李勣的品階與俸祿實際上由太常卿來決定。由于“同中書門下三品”這一使職所承擔的工作遠比太常卿所掌之職更為重要,因此或可推斷李勣的工作重心當在處理國家機務而非禮樂之事。武則天執政時曾仿李勣故事,任命武承嗣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11]83;唐睿宗時期,姜皎“遷太常卿,監修國史”[5]2336;玄宗時,朝廷曾命“太常卿、廣州事嶺南經略使李朝隱為嶺南道采訪使”[12]。在上述諸例中,當某一官員兼任太常卿與其他使職時,往往其所領之使職為工作重心,而太常卿大多只發揮標志其品秩的作用。五代至北宋前期,由于“職事官體系之內,存在著分化不一的狀況”[13],任太常卿者既可掌邦國禮樂之事,亦可以此為階官另掌他職。如后唐明宗時,以太常卿崔協“判吏部尚書銓事”[5]499;宋太祖乾德元年,以太常卿邊光范權知襄州事[8]82。隨著太常卿在北宋前期徹底蛻變為階官,“判太常寺”這一差遣成為此后太常寺長官的身份象征,一直沿用至元豐改制前。
相較于太常卿,太常博士的階官化進程開始較晚,這與唐后期太常博士與太常禮院權力的擴大密切相關[14]127-156。后周世宗年間是太常博士向階官轉化的重要時期,顯德五年(958)夏四月丙辰,“太常博士、權知宿州軍州事趙礪除名,坐推劾弛慢也”[5]1572。顯而易見,趙礪此時實任“權知宿州軍州事”,太常博士可視為其階官,只不過趙礪曾實任太常博士。顯德四年(957)五月,朝廷認為“法書行用多時”繁細難會、重疊層出,特命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編集新格,勒成部帙”[10]148-149,太常博士趙礪亦參與其中。編修典故乃太常博士“掌辨五禮之儀式,奉先王之法制,通變隨時而損益”之責[1]396,故此時太常博士于趙礪而言仍為職事官,至趙礪領“權知宿州軍州事”差遣后方僅作階官之用。據此可見,太常博士的階官化進程與后周中央委派朝官任地方職務有關。隨著太常博士在北宋前期徹底蛻變為階官,“判太常禮院”和“知太常禮院”等差遣產生,“禮儀機構遂有了徹底使職化的結果”[14]145。
五代時期,太常卿與太常博士的職權不斷擴大,太常卿除掌“贊襄禮儀”外,亦掌編修敕令和禮書以及擬定皇帝謚號與廟用樂舞之事,而太常博士在“掌辨五禮之儀式,奉先王之法制,通變隨時而損益”之外,還獲得了監察祀儀與“通攝祠祭”之權。更為重要的是,隨著職事官制度的不斷瓦解,太常卿與太常博士逐漸由職事官蛻變為階官,發揮“寓祿秩、敘位著”[15]的作用。
注 釋:
① 相關研究參見任爽《唐代禮制研究》,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郁賢皓、胡可先《唐九卿考》卷二《太常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55-153;王巖《唐代太常博士考論》,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于俊利《論唐代禮官的地位升降與職權變化》,《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一期。
② 《五代會要》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百二十三頁)《廟樂》小注載:“太子賓客,判太常寺事趙光輔撰”。而《舊五代史》卷八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一千零七十一頁)載,后晉天福七年八月己巳,“以太子賓客趙元輔權判太常卿事,充山陵禮儀使”。就現存史料而言,趙光輔與趙元輔是否為同一人,其官職為“判太常寺事”還是“判太常卿事”,尚無法給出確切答案。
③ 孫國棟認為,唐代職名用“判”還是用“知”并不取決于官品高低,“‘判’著重兼理他官的職務,‘知’則著重兼辦某一特定的事務。所以‘判’稱‘判某官’或‘判某官事’……‘知’則‘知某事’”,見《唐宋史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二百五十九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