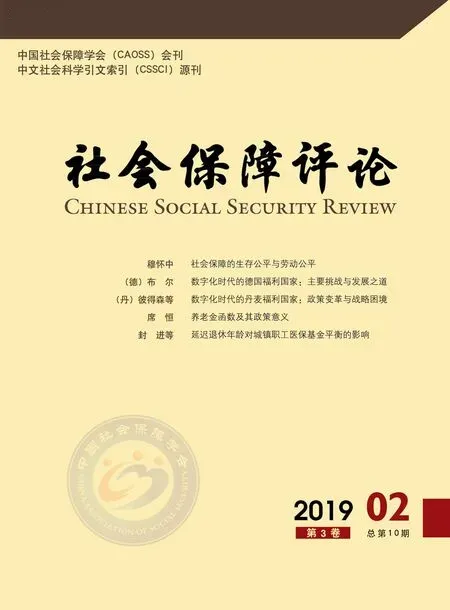數(shù)字化時(shí)代的德國(guó)福利國(guó)家:主要挑戰(zhàn)與發(fā)展之道
(德)丹尼爾·布爾
一、導(dǎo)言
工業(yè)4.0這個(gè)術(shù)語(yǔ)已經(jīng)成為未來(lái)工業(yè)生產(chǎn)的代名詞,它囊括了信息物理系統(tǒng)(Cyber-Physical System)、物聯(lián)網(wǎng)(IoT)、云計(jì)算、認(rèn)知計(jì)算以及人工智能等創(chuàng)新技術(shù)。工業(yè)4.0通常被稱為第四次工業(yè)革命,這一概念與旨在通過(guò)更高效的生產(chǎn)流程、新型商業(yè)模式、客戶導(dǎo)向的制造方法以及行業(yè)與服務(wù)不斷深化的融合來(lái)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目標(biāo)有關(guān)。然而,“4.0”是一個(gè)既具有顛覆性又代表漸進(jìn)性的“代碼”(Cipher)。一方面,數(shù)字化確實(shí)有利于推動(dòng)產(chǎn)生新的商業(yè)模式、價(jià)值鏈網(wǎng)絡(luò)以及新的工作和機(jī)構(gòu),同時(shí)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越來(lái)越多的工作崗位和傳統(tǒng)商業(yè)模式也會(huì)萎縮;另一方面,正如我們過(guò)去已經(jīng)注意到的那樣,這些發(fā)展將更具漸進(jìn)性,比如在工業(yè)4.0(信息物理系統(tǒng))之前,有工業(yè)3.0、工業(yè)2.0和工業(yè)1.0①工業(yè)1.0 是指第一次工業(yè)革命,即蒸汽機(jī)時(shí)代,它是以18世紀(jì)60年代至19世紀(jì)中期掀起的通過(guò)水力和蒸汽機(jī)實(shí)現(xiàn)的工廠機(jī)械化為典型特征;工業(yè)2.0 是指第二次工業(yè)革命,即電氣化時(shí)代,它是以19世紀(jì)后半期至20世紀(jì)初的電力廣泛應(yīng)用為標(biāo)志;工業(yè)3.0 則是指第三次工業(yè)革命,即信息化時(shí)代,它是以20世紀(jì)后半期出現(xiàn)的、基于可編程邏輯控制器(PLC)的生產(chǎn)工藝自動(dòng)化為特征。。
西歐福利國(guó)家的歷史與發(fā)展現(xiàn)狀清晰表明,技術(shù)與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對(duì)其福利體制構(gòu)成挑戰(zhàn)②參見(jiàn)Daniel Buhr, et al., On the Way to Welfare 4.0? Digitalis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Labour Market, Health Care and Innovation Policy: A European Comparison, Berli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6.。從本質(zhì)上來(lái)看,數(shù)字化的發(fā)展將對(duì)福利國(guó)家的現(xiàn)代化產(chǎn)生兩種不同的影響,分別是外部影響和內(nèi)部影響。首先,這種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正在創(chuàng)造一個(gè)工業(yè)生產(chǎn)的新時(shí)代——工業(yè)4.0。工業(yè)4.0通過(guò)改變生產(chǎn)方式、信息通訊技術(shù)的傳播模式并廣泛使用自動(dòng)化技術(shù),從而對(duì)勞動(dòng)者特別是雇員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這些來(lái)自外部的變化和挑戰(zhàn)將需要調(diào)整福利國(guó)家的制度體系予以應(yīng)對(duì)③Werner Eichhorst, Ulf Rinne, Digital Challenges for the Welfare State, IZA Policy Paper, 2017.,這可以稱之為對(duì)福利國(guó)家的外部現(xiàn)代化效應(yīng)(External Modernization Effect)。其次,福利國(guó)家再分配體制的數(shù)字化正在引發(fā)內(nèi)部現(xiàn)代化效應(yīng)(Internal Modernization Effect)。它們一方面與福利服務(wù)的數(shù)字化管理有關(guān),比如互聯(lián)網(wǎng)的激增和寬帶的廣泛應(yīng)用;另一方面,內(nèi)部現(xiàn)代化還包括發(fā)展數(shù)字化在信息處理領(lǐng)域所需的技能和能力以推動(dòng)社會(huì)和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參與等。總之,福利國(guó)家如何應(yīng)對(duì)新的社會(huì)不平等(即所謂的數(shù)字鴻溝),以及可以找到何種解決方案來(lái)處理數(shù)字化所帶來(lái)的影響等問(wèn)題均與此密切相關(guān)。
德國(guó)至今一直在走一條外部現(xiàn)代化的道路,這與保守型福利國(guó)家④參見(jiàn)G?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和協(xié)調(diào)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 CME)⑤Peter Hall, David Soskice,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Peter Hall,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2001.的功能邏輯是一致的。德國(guó)在應(yīng)對(duì)生產(chǎn)和工作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方面的兩項(xiàng)主要政策可以證明這一點(diǎn),即“工業(yè)4.0”和“工作4.0”。兩者都遵循通過(guò)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進(jìn)行三方?jīng)Q策的原則,并尋求協(xié)會(huì)、工會(huì)和相關(guān)政府部門之間通力合作。因此,在政策發(fā)展領(lǐng)域,德國(guó)屬于典型的協(xié)調(diào)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CME),它與美國(guó)的自由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Liberal Market Economy, LME)形成鮮明對(duì)比⑥D(zhuǎn)aniel Buhr, Rolf Frankenberger, "Emerging Varieties of Incorporated Capitalism.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Business and Politics, 2014, 16(3).。
二、資本主義的類型
根據(jù)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領(lǐng)域的一系列重要文獻(xiàn),我們可以區(qū)分資本主義的各種類型⑦Peter Hall, David Soskice,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Peter Hall,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2001.,它們因制度結(jié)構(gòu)和“制度互補(bǔ)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程度的不同而異⑧Masahiko Aoki, "The Contingent Governance of Teams: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4, 35(3).。所謂“制度互補(bǔ)性”,是指某一制度的邊際收益在另一個(gè)制度存在時(shí)增加。根據(jù)這一理論,“當(dāng)某些制度形式共同存在時(shí),其可以相互促進(jìn),并有助于改善資本主義特定制度結(jié)構(gòu)、類型或模式的功能、連貫性或穩(wěn)定性”①Bruno Amable,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apitalism,"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16, 12(1).。
Hall和Soskice提出了5個(gè)領(lǐng)域的制度安排,分別是勞資關(guān)系、職業(yè)培訓(xùn)與教育、金融與公司治理、企業(yè)間關(guān)系和員工協(xié)調(diào)。一般認(rèn)為,可以根據(jù)經(jīng)濟(jì)秩序(或更確切地說(shuō)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在這5個(gè)領(lǐng)域中的具體制度模式來(lái)對(duì)其進(jìn)行比較。某些制度模式比其他模式提供了更可行的環(huán)境,更有利于創(chuàng)造某些類型的產(chǎn)品和服務(wù),因?yàn)檫@些產(chǎn)品和服務(wù)需要特定形式的技能、知識(shí)、基礎(chǔ)設(shè)施、科技或?qū)Y本進(jìn)行調(diào)配的能力。根據(jù)上述分析框架,Hall和Soskice進(jìn)一步提出了兩種理想類型的資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即自由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LME)和協(xié)調(diào)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CME)。其中,美國(guó)、英國(guó)、澳大利亞等被認(rèn)為是最接近自由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國(guó)家,而德國(guó)、瑞典、奧地利等國(guó)家被認(rèn)為更接近于協(xié)調(diào)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類型。在這兩種類型中,企業(yè)往往會(huì)以不同的方式與各自的制度環(huán)境進(jìn)行協(xié)調(diào)。一般情況下,在自由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企業(yè)往往通過(guò)等級(jí)制度和競(jìng)爭(zhēng)性市場(chǎng)機(jī)制來(lái)進(jìn)行協(xié)調(diào),而協(xié)調(diào)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的企業(yè)則更傾向于使用網(wǎng)絡(luò)和行業(yè)協(xié)會(huì)等非市場(chǎng)性治理機(jī)制②Peter Hall, David Soskice,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Peter Hall,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2001.。
Hall和Soskice使用“制度互補(bǔ)性”概念解釋了上述兩種資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比較優(yōu)勢(shì)。其中,自由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在采用激進(jìn)式創(chuàng)新戰(zhàn)略的行業(yè)(如軟件業(yè))中具有優(yōu)勢(shì)。因?yàn)樵谶@種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類型中,自由化的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工會(huì)與雇主協(xié)會(huì)合作不足(薪酬談判碎片化)、等級(jí)式的管理理念以及基于資本市場(chǎng)的企業(yè)融資方式等特征,使得生產(chǎn)要素可以進(jìn)行靈活分配。相反,協(xié)調(diào)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則在依賴現(xiàn)有產(chǎn)品組合進(jìn)行漸進(jìn)式創(chuàng)新的行業(yè)(如制造業(yè))中更具優(yōu)勢(shì),這種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基礎(chǔ)是:共同決策、強(qiáng)大的工會(huì)和雇主協(xié)會(huì)密切合作(行業(yè)層面的薪酬談判)、受監(jiān)管的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以防止人員培訓(xùn)和教育中的沉沒(méi)成本、基于銀行的融資方式。因此,這些制度安排的最佳“契合”,即所謂制度互補(bǔ),帶來(lái)了兩種資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模式的“優(yōu)越表現(xiàn)”,其基礎(chǔ)是可以從這種互補(bǔ)性中獲益的企業(yè)。
Buhr和Frankenberger通過(guò)分析“專制統(tǒng)治下的治理、資本主義以及國(guó)家與市場(chǎng)之間的關(guān)系”③Daniel Buhr, Rolf Frankenberger, "Emerging Varieties of Incorporated Capitalism.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Business and Politics, 2014, 16(3).,從而將上述理論進(jìn)一步擴(kuò)展到其他政權(quán)類型。其認(rèn)為,專制政權(quán)依賴于產(chǎn)出合法性(Output Legitimacy),從而依賴于權(quán)力分配和收入來(lái)源。這種“組合型資本主義”(Incorporated Capitalism)基于以下假設(shè):因?yàn)殒?zhèn)壓成本高昂,所以專制政體需要一個(gè)合法性來(lái)源,以便精英們能夠繼續(xù)掌權(quán)。為實(shí)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他們需要可持續(xù)的收入來(lái)源(如租金、稅收)以重新分配于基礎(chǔ)設(shè)施等公共產(chǎn)品,以及養(yǎng)老、醫(yī)療、教育等領(lǐng)域。因此,這些政權(quán)需要穩(wěn)定的權(quán)力基礎(chǔ),而這個(gè)權(quán)力基礎(chǔ)是通過(guò)拉攏和吸收經(jīng)濟(jì)精英、軍事精英等所有相關(guān)精英并通過(guò)構(gòu)建雙贏的局面而建立起來(lái)的。社會(huì)的越多部分以這種方式融入政權(quán),政權(quán)的領(lǐng)導(dǎo)地位就越穩(wěn)固。除了市場(chǎng)、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或社團(tuán)主義等現(xiàn)有治理模式之外,Buhr和Frankenberger還提出了另外兩種相關(guān)模式,即吸納和強(qiáng)制。據(jù)此,組合型資本主義模式又可進(jìn)一步劃分為兩個(gè)獨(dú)立的子類型,即世襲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Patrimonial Market Economy, PME)和官僚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Bureaucratic Market Economy, BME)。其中,世襲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的合作主要是通過(guò)個(gè)人渠道進(jìn)行的,而官僚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的合作則是在議會(huì)、政黨、工會(huì)、協(xié)會(huì)以及官僚機(jī)構(gòu)和行政機(jī)構(gòu)等一系列正式機(jī)構(gòu)內(nèi)組織的。合作基于這樣一種假設(shè):行動(dòng)者或群體相信這些機(jī)構(gòu)和意識(shí)形態(tài),只要他們是其中的一員或者能夠?qū)Q策產(chǎn)生重要影響并從中獲利。因此,官僚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的合作并不像在世襲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那樣通過(guò)人際關(guān)系的“庇護(hù)網(wǎng)絡(luò)”進(jìn)行,而是使用官僚主義、新形式的合作生產(chǎn)、參與和賦權(quán),以便將大部分社會(huì)群體融入到共同選擇的過(guò)程中。比如,擴(kuò)大福利項(xiàng)目的范圍可以反過(guò)來(lái)增加政權(quán)的合法性和穩(wěn)定性①Daniel Buhr, Rolf Frankenberger, "Emerging Varieties of Incorporated Capitalism.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Business and Politics, 2014, 16(3).。

表1 資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類型
德國(guó)可被稱為協(xié)調(diào)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典型代表。協(xié)調(diào)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傾向于在相對(duì)合作的經(jīng)濟(jì)主體之間發(fā)展長(zhǎng)期關(guān)系(如長(zhǎng)期勞動(dòng)關(guān)系、長(zhǎng)期資本等)。就德國(guó)而言,高水平的工作保障,加上良好的培訓(xùn)和晉升記錄,以工作委員會(huì)為基礎(chǔ)的制度化員工參與,以及工會(huì)與雇主協(xié)會(huì)之間的合作關(guān)系形成了某種類型的制度互補(bǔ),這種制度互補(bǔ)可以從供應(yīng)商、買家、金融家、雇主和雇員之間長(zhǎng)期穩(wěn)定的關(guān)系和高度信任中看到。總而言之,協(xié)調(diào)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往往擅長(zhǎng)流程創(chuàng)新以及在成熟的制造業(yè)中生產(chǎn)高質(zhì)量、高附加值的產(chǎn)品,這些行業(yè)的特點(diǎn)是擁有大量所謂的“隱形冠軍”,其基礎(chǔ)是具有強(qiáng)烈出口導(dǎo)向的中小企業(yè)(Small and Mediums-Sized Enterprises, SME)。這些中小企業(yè)形成了強(qiáng)大的行業(yè)協(xié)會(huì)并由這些協(xié)會(huì)很好地代表,如德國(guó)機(jī)械設(shè)備制造業(yè)聯(lián)合會(huì)(VDMA)、德國(guó)電氣和電子工業(yè)協(xié)會(huì)(ZVEI)、德國(guó)標(biāo)準(zhǔn)化研究所(DIN)。通過(guò)這些協(xié)會(huì),大小企業(yè)在社會(huì)和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方面攜手合作。正是這套具體的正式制度,構(gòu)成了德國(guó)在生產(chǎn)和政策制定領(lǐng)域的獨(dú)特路徑。這一路徑可以說(shuō)更具漸進(jìn)性,遵循在正式場(chǎng)合(如共同決策機(jī)制、協(xié)會(huì)、標(biāo)準(zhǔn)化委員會(huì)或者像工業(yè)4.0平臺(tái)這樣的特定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協(xié)商的理念對(duì)現(xiàn)有制度逐步進(jìn)行改變。
三、工業(yè)4.0與德國(guó)的制度變革
在德國(guó),關(guān)于數(shù)字化及其對(duì)經(jīng)濟(jì)影響的討論早已開(kāi)始。然而,最初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是技術(shù)領(lǐng)域①參見(jiàn)Daniel Buhr, Social Innovation Policy for Industry 4.0, Bon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5.。早在2006年,德國(guó)聯(lián)邦政府就已提出一項(xiàng)包含具體目標(biāo)的中期戰(zhàn)略,旨在實(shí)施一項(xiàng)綜合創(chuàng)新政策。在《德國(guó)2020高技術(shù)戰(zhàn)略》(High-Tech Strategy 2020)這一后續(xù)計(jì)劃中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此前計(jì)劃的“影子”。其中,工業(yè)4.0也被列入未來(lái)各種項(xiàng)目之中,其目標(biāo)是將德國(guó)打造成為長(zhǎng)期領(lǐng)先的數(shù)字設(shè)備、工藝和產(chǎn)品供應(yīng)國(guó)與生產(chǎn)基地②Peter Ittermann, Jonathan Niehaus, "Industrie 4.0 und Wandel von Industriearbeit.überblick über Forschungsstand und Trendbestimmungen," in Hartmut Hirsch-Kreinsen, et al.(eds.), Digitalisierung Industrieller Arbeit, Baden-Baden, 2015.。因此,德國(guó)聯(lián)邦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以技術(shù)為中心的研究計(jì)劃,以保持德國(guó)工業(yè)的“技術(shù)領(lǐng)先地位”,如 “工業(yè)4.0自動(dòng)化”(德國(guó)聯(lián)邦經(jīng)濟(jì)與能源部投入4000萬(wàn)歐元)、“工業(yè)4.0——為未來(lái)生產(chǎn)而創(chuàng)新”(基金總額約為1.2億歐元)名下德國(guó)聯(lián)邦教育及研究部(BMBF)實(shí)施的各種計(jì)劃。德國(guó)聯(lián)邦教育及研究部在工業(yè)4.0領(lǐng)域研究的另一個(gè)重點(diǎn)是“智能技術(shù)系統(tǒng)(OWL)”。這是一個(gè)卓越的集群,在此集群中,技術(shù)領(lǐng)先的企業(yè)和研究機(jī)構(gòu)合作開(kāi)發(fā)新的技術(shù)平臺(tái)。自2012年以來(lái),該合作在區(qū)域一級(jí)得到了資助。上述舉措以聯(lián)邦政府的《2014—2017年數(shù)字化議程》(Digital Agenda 2014—2017)為框架,該議程是涵蓋數(shù)字化各個(gè)方面的跨部門戰(zhàn)略,涉及寬帶的安裝、工作場(chǎng)所的數(shù)字化、IT安全和工業(yè)4.0等主題。此外,德國(guó)巴登-符騰堡州、柏林、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等聯(lián)邦州也在支持各種示范工廠、卓越研究中心和企業(yè)項(xiàng)目,這些州正在致力于生產(chǎn)技術(shù)的開(kāi)發(fā)及其實(shí)際應(yīng)用①參見(jiàn)Daniel Buhr, Thomas Stehnken, Industry 4.0 and European Innovation Policy: Big Plans, Small Steps, Bon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8.。
德國(guó)聯(lián)邦政府很早就關(guān)注了數(shù)字化領(lǐng)域在社會(huì)層面和技術(shù)方面的發(fā)展,并為創(chuàng)新進(jìn)程中的主要參與者制定了合作框架,且最初的重點(diǎn)是技術(shù)發(fā)展。從那時(shí)起,其中的一些舉措就與“工業(yè)4.0平臺(tái)”聯(lián)系在一起,這些舉措非常符合主導(dǎo)性市場(chǎng)理念和已被證明的中觀的社團(tuán)主義邏輯。
工業(yè)4.0是《2020高科技戰(zhàn)略行動(dòng)計(jì)劃》(Action Plan High-tech Strategy 2020)中所確定的未來(lái)發(fā)展項(xiàng)目之一。因此,德國(guó)聯(lián)邦政府強(qiáng)調(diào)了該領(lǐng) 域在社會(huì)和技術(shù)層面的迅速發(fā)展,并為所有創(chuàng)新參與者提供了合作框架。由下屬于德國(guó)聯(lián)邦教育及研究部的經(jīng)濟(jì)與科學(xué)研究聯(lián)盟所成立的工業(yè)4.0工作小組提出了成功進(jìn)入第四個(gè)工業(yè)時(shí)代的要求。2012年10月,該工作小組提交了題為《工業(yè)4.0未來(lái)項(xiàng)目的實(shí)施建議》的報(bào)告。三個(gè)代表著超過(guò)6000家公司的協(xié)會(huì),即德國(guó)機(jī)械設(shè)備制造業(yè)聯(lián)合會(huì)(VDMA)、德國(guó)電氣和電子工業(yè)協(xié)會(huì)(ZVEI)以及德國(guó)信息技術(shù)、通訊、新媒體協(xié)會(huì)(BITKOM),對(duì)工業(yè)4.0計(jì)劃的完善提出了進(jìn)一步的修改意見(jiàn),并于2013年4月簽訂了一項(xiàng)跨協(xié)會(huì)的合作協(xié)議,即工業(yè)4.0平臺(tái)。2013年漢諾威工業(yè)博覽會(huì)上,德國(guó)正式宣布推出該平臺(tái)。2015年4月,該平臺(tái)進(jìn)一步拓展,納入了更多公司、協(xié)會(huì)、工會(huì)、科研機(jī)構(gòu)和政治性團(tuán)體。德國(guó)聯(lián)邦經(jīng)濟(jì)與能源部(BMWi)和聯(lián)邦教育及研究部與來(lái)自商界、科學(xué)界和工會(huì)領(lǐng)域的高級(jí)代表一起監(jiān)管該平臺(tái)。
工業(yè)4.0平臺(tái)旨在為所有利益攸關(guān)方提供共同建議,這是建立一致而可靠的框架的基礎(chǔ)。因此,該平臺(tái)計(jì)劃在競(jìng)爭(zhēng)開(kāi)始前的階段建立聯(lián)盟和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以支持德國(guó)企業(yè)技術(shù)和活力的發(fā)展。該平臺(tái)還旨在了解制造業(yè)的相關(guān)發(fā)展趨勢(shì),并將這些信息整合起來(lái),以形成對(duì)工業(yè)4.0的統(tǒng)一全面理解。這意味著該平臺(tái)不會(huì)在實(shí)際運(yùn)營(yíng)中進(jìn)行市場(chǎng)活動(dòng),比如運(yùn)營(yíng)展示中心、開(kāi)展研究項(xiàng)目或公司主導(dǎo)的項(xiàng)目,但它會(huì)主動(dòng)發(fā)起和支持這些活動(dòng)。同樣,在標(biāo)準(zhǔn)化領(lǐng)域,該平臺(tái)也不會(huì)制定具體標(biāo)準(zhǔn),因?yàn)閭鹘y(tǒng)上是由德國(guó)標(biāo)準(zhǔn)化學(xué)會(huì)(DIN)、德國(guó)工程師協(xié)會(huì)(VDI)等協(xié)會(huì)來(lái)制定標(biāo)準(zhǔn)的,其他強(qiáng)有力的(部門)機(jī)構(gòu)(如德國(guó)機(jī)械設(shè)備制造業(yè)聯(lián)合會(huì)、德國(guó)電氣和電子工業(yè)協(xié)會(huì)以及德國(guó)信息技術(shù)、通訊、新媒體協(xié)會(huì)等)也參與其中。然而,該平臺(tái)確實(shí)也指出標(biāo)準(zhǔn)和規(guī)范方面需要完善的地方,并積極對(duì)國(guó)家和國(guó)際委員會(huì)的工作提出建議。
在專項(xiàng)主題小組中工作的專家,其任務(wù)是提出解決標(biāo)準(zhǔn)化、規(guī)范化、網(wǎng)絡(luò)系統(tǒng)安全、法律框架、研究和工作安排等領(lǐng)域問(wèn)題的可操作方法。企業(yè)代表指導(dǎo)委員會(huì)負(fù)責(zé)制訂策略,以在技術(shù)上落實(shí)工作小組的成果。由來(lái)自政界、行業(yè)團(tuán)體、科學(xué)界、工會(huì)、聯(lián)邦部門和聯(lián)邦各州代表組成的戰(zhàn)略委員會(huì)負(fù)責(zé)政治管理,戰(zhàn)略委員會(huì)進(jìn)一步擴(kuò)大了關(guān)于工業(yè)4.0影響的社會(huì)討論。

圖1 工業(yè)4.0 平臺(tái)的治理結(jié)構(gòu)
四、工作4.0與德國(guó)的制度調(diào)整
2016年11月,德國(guó)聯(lián)邦勞動(dòng)和社會(huì)事務(wù)部發(fā)布了《工作4.0白皮書》。這是一個(gè)為期18個(gè)月的對(duì)話進(jìn)程的結(jié)果。該白皮書描述了德國(guó)勞動(dòng)領(lǐng)域面臨的挑戰(zhàn),并在政治辯論中加入了政策建議。對(duì)話的參與者包括廣泛的利益攸關(guān)方,如學(xué)術(shù)界、工會(huì)、雇主組織以及公眾。通過(guò)創(chuàng)造“工作4.0”這一術(shù)語(yǔ),這場(chǎng)辯論有意與業(yè)已流行的“工業(yè)4.0”討論聯(lián)系在一起,前者并不是為了與后者相對(duì)應(yīng),而是一種補(bǔ)充。工作4.0反映了德國(guó)政策制定者越來(lái)越廣泛的共識(shí),即工作領(lǐng)域的變化將不可避免地對(duì)福利國(guó)家和社會(huì)保障體系產(chǎn)生影響。雖然制造業(yè)工人在過(guò)去10年甚至更長(zhǎng)時(shí)間里一直在經(jīng)歷數(shù)字化,但許多白領(lǐng)專業(yè)人士(如健康顧問(wèn)或法律顧問(wèn))現(xiàn)在才意識(shí)到他們目前的工作可能會(huì)在未來(lái)幾年發(fā)生根本性變化。對(duì)于整整一代年輕人而言,項(xiàng)目式就業(yè)、遠(yuǎn)程工作以及工作與休閑之間日益模糊的界限將成為其工作生涯的常態(tài)。2015年4月,聯(lián)邦勞動(dòng)和社會(huì)事務(wù)部發(fā)布了一份《綠皮書》,啟動(dòng)了咨詢程序。《綠皮書》提出了具體問(wèn)題,而隨后出版的《工作4.0白皮書》應(yīng)該對(duì)這些問(wèn)題給予具體解答。為此,聯(lián)邦勞動(dòng)和社會(huì)事務(wù)部采取了一系列行動(dòng),比如邀請(qǐng)協(xié)會(huì)、工會(huì)和企業(yè)提交解決方案,舉辦專門的工作坊和相關(guān)活動(dòng),委托學(xué)術(shù)研究,通過(guò)“Futurale”電影節(jié)等平臺(tái)在地方一級(jí)直接與公眾對(duì)話從而了解民意等等。其中最重要的討論議題是: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和社會(huì)變革時(shí)代,我們?nèi)绾尾拍鼙3稚踔良訌?qiáng)對(duì)優(yōu)質(zhì)工作和體面勞動(dòng)的愿景?最終,形成了一份近300頁(yè)對(duì)未來(lái)工作進(jìn)行全面評(píng)估的報(bào)告——《工作4.0白皮書》,該報(bào)告勾勒了“數(shù)字化變革時(shí)代優(yōu)質(zhì)工作”的愿景,而這一愿景是建立在德國(guó)傳統(tǒng)的共同決策和共同參與等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模式的基礎(chǔ)之上①參見(jiàn)Wolfgang Schroeder, et al., Shaping Digitalisation: Industry 4.0, Work 4.0, Regulation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Berli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7.。
白皮書闡述了當(dāng)前工作領(lǐng)域轉(zhuǎn)型的主要趨勢(shì)及其相應(yīng)的驅(qū)動(dòng)因素,同時(shí)也仔細(xì)研究了工作4.0面臨的主要挑戰(zhàn)。企業(yè)、員工、社會(huì)伙伴、工會(huì)、聯(lián)邦與州層面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利益相關(guān)者等群體現(xiàn)在需要采取行動(dòng),應(yīng)對(duì)這些挑戰(zhàn)。在此,重點(diǎn)是磋商過(guò)程中提出的6個(gè)關(guān)鍵問(wèn)題,這些問(wèn)題概述了技術(shù)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工作條件之間存在緊張關(guān)系的主要領(lǐng)域②BMAS (eds.) , Wei?buch Arbeiten 4.0, https://www.bmas.de/SharedDocs/Downloads/DE/PDF-Publikationen/a883-weissbuch.pdf, 2016.。
第一,數(shù)字化是否會(huì)使每個(gè)人在未來(lái)都盡可能地?fù)碛幸环莨ぷ鳎咳绻沁@樣,那么需要符合什么條件?
第二,“數(shù)字平臺(tái)”等新商業(yè)模式對(duì)未來(lái)工作有何影響?
第三,如果數(shù)據(jù)的收集和使用變得越來(lái)越重要,那么如何保障員工享有數(shù)據(jù)保護(hù)的合法權(quán)利?
第四,如果將來(lái)人類和機(jī)器更緊密地合作,機(jī)器將如何幫助人們?cè)鰪?qiáng)工作的能力?
第五,工作正變得更加靈活。但是,就工作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而言,哪些解決方案可能會(huì)改善員工的選擇?
第六,未來(lái)的現(xiàn)代公司將會(huì)是什么樣子?它可能在所有方面都不像傳統(tǒng)公司,但為員工參與和社會(huì)保障提供便利?
《工作4.0白皮書》勾勒了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中體面勞動(dòng)和優(yōu)質(zhì)工作的愿景,并基于“社會(huì)”(協(xié)調(diào)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概念,為結(jié)論和政策選擇奠定了規(guī)范基礎(chǔ)。因此,在一個(gè)創(chuàng)新和民主的社會(huì)中,制度性的共同決策(Mitbestimmung)和員工個(gè)體參與的新形式之間并不被認(rèn)為是相互矛盾的,而是互補(bǔ)性的,也是創(chuàng)新與民主型企業(yè)的特征。鑒于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工作4.0白皮書》指出,在早期階段為提高技能和改善個(gè)人發(fā)展前景進(jìn)行投資至關(guān)重要。這種支持應(yīng)側(cè)重于預(yù)防,即不應(yīng)僅針對(duì)低技能勞動(dòng)者,也不能只在工作生涯后期或裁員之前發(fā)揮作用,而是應(yīng)該遵循更為廣泛的策略。在這種邏輯下,白皮書提出的另一個(gè)建議是逐步將當(dāng)前的失業(yè)保險(xiǎn)轉(zhuǎn)變?yōu)榫蜆I(yè)保險(xiǎn),以便為工人提供更多的預(yù)防性支持。這種預(yù)防性支持措施的一個(gè)重要元素是有權(quán)獲得關(guān)于終身教育、培訓(xùn)和提高技能的獨(dú)立建議,這在某種程度上遵循了現(xiàn)有職業(yè)教育和培訓(xùn)機(jī)構(gòu)的做法,因此得到了德國(guó)勞動(dòng)和社會(huì)事務(wù)部的積極倡導(dǎo)。

表2 工作4.0 對(duì)話進(jìn)程的重要事件
工作4.0對(duì)話表明,工作的新要求、技術(shù)和社會(huì)變革以及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的變化導(dǎo)致了新問(wèn)題和新挑戰(zhàn)。如何利用數(shù)字技術(shù)使工作更輕松——尤其是對(duì)年齡較大的員工和殘障人士?我們可以創(chuàng)造哪些新的工作時(shí)間模式來(lái)滿足企業(yè)的需求以及員工對(duì)其工作時(shí)間有更多控制權(quán)的需求?①BMAS (eds.), Darum geht's Der Dialogprozess Arbeiten 4.0, http://www.arbeitenviernull.de/dialogprozess/darum-gehts.html, 2019.
根據(jù)行業(yè)和公司的不同,這些挑戰(zhàn)和問(wèn)題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緊急程度。 對(duì)于企業(yè)或社會(huì)而言,并沒(méi)有現(xiàn)成的藍(lán)圖可以使工作4.0成功。然而,有些嘗試和想法應(yīng)該在受保護(hù)的空間中進(jìn)行實(shí)驗(yàn),從中學(xué)習(xí)和改進(jìn)。這些機(jī)會(huì)表明了嘗試新方法和創(chuàng)造新空間的必要性,這可以讓管理層和員工共同努力,從而更好地探索創(chuàng)新的工作理念。
對(duì)話過(guò)程的這些發(fā)現(xiàn)需要在實(shí)踐中進(jìn)行檢驗(yàn)②參見(jiàn)Kerstin Jürgens, et al., Arbeit Transformieren! Denkanst??e der Kommission ?Arbeit der Zukunft?, Bielefeld, 2017.。因此,聯(lián)邦勞動(dòng)和社會(huì)事務(wù)部希望鼓勵(lì)和支持企業(yè)建立內(nèi)部創(chuàng)新空間(Innovation Space),以測(cè)試新創(chuàng)意的潛力。與此同時(shí),企業(yè)之間應(yīng)該保持聯(lián)系并互相學(xué)習(xí)。為了支持企業(yè)之間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構(gòu)建和相互交流,聯(lián)邦勞動(dòng)和社會(huì)事務(wù)部創(chuàng)建了在線平臺(tái)(www.experimentierr?ume.de),企業(yè)可以在此平臺(tái)上展示自己的創(chuàng)新空間并了解彼此的項(xiàng)目。為了推動(dòng)這一進(jìn)程,該部將通過(guò)提供資金和咨詢服務(wù)來(lái)支持創(chuàng)建創(chuàng)新空間。在這些創(chuàng)新空間中,企業(yè)和公共部門可以邁出走向未來(lái)工作的第一步。
五、結(jié)論
通過(guò)分析生產(chǎn)和工作領(lǐng)域數(shù)字化的主要政策發(fā)展歷程,我們?nèi)匀豢梢园l(fā)現(xiàn)德國(guó)協(xié)調(diào)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所留下的鮮明“遺產(chǎn)”,即強(qiáng)大的正式機(jī)構(gòu)和通過(guò)平臺(tái)搭建的協(xié)作網(wǎng)絡(luò),并以此制定社會(huì)政策和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雖然德國(guó)關(guān)于數(shù)字化的爭(zhēng)論長(zhǎng)期以來(lái)只局限于技術(shù)和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但無(wú)論是“工業(yè)4.0”還是“工作4.0”,都更加關(guān)注工作條件等社會(huì)問(wèn)題。當(dāng)涉及新的工作形式時(shí),社會(huì)伙伴在諸如合法就業(yè)狀況、社會(huì)保護(hù)、共同決策和利益代表等關(guān)鍵問(wèn)題上的分歧似乎要大得多。工會(huì)開(kāi)始形成自己的立場(chǎng),并早早地提出了積極的建議。然而,關(guān)于進(jìn)一步發(fā)展德國(guó)的工業(yè)區(qū)位,工會(huì)和行業(yè)協(xié)會(huì)達(dá)成了廣泛的共識(shí)①參見(jiàn)Wolfgang Schroeder, et al., Shaping Digitalisation: Industry 4.0, Work 4.0, Regulation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Berli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7.。
總之,在形塑工作條件的過(guò)程中,社會(huì)伙伴關(guān)系、共同決策以及民主參與仍然是德國(guó)社會(huì)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核心要素。這是危機(jī)時(shí)期的一股穩(wěn)定力量,也是德國(guó)在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中取得成功的要素。與其他國(guó)家相比,德國(guó)的社會(huì)伙伴(雇主和雇員)普遍對(duì)數(shù)字化采取了積極態(tài)度,“尤其是工會(huì),從一開(kāi)始就沒(méi)有像現(xiàn)代路德派(Luddites)那樣試圖阻礙數(shù)字化。他們重視數(shù)字化帶來(lái)的機(jī)遇,但也沒(méi)有忽視其中必須應(yīng)對(duì)的風(fēng)險(xiǎn)。”②參見(jiàn)Wolfgang Schroeder, et al., Shaping Digitalisation: Industry 4.0, Work 4.0, Regulation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Berli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7.
因此,工作4.0對(duì)話的一個(gè)主要成果是發(fā)現(xiàn)需要加強(qiáng)社會(huì)伙伴之間和企業(yè)層面的談判,以便成功應(yīng)對(duì)數(shù)字化的結(jié)構(gòu)性變革。然而,這需要穩(wěn)定德國(guó)的集體談判機(jī)制、為勞動(dòng)者參與其組織建立更廣泛的基礎(chǔ)、為工作與員工委員會(huì)提供充足的權(quán)利和資源,以及維護(hù)企業(yè)共同決策的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與歐洲標(biāo)準(zhǔn)。聯(lián)邦勞動(dòng)和社會(huì)事務(wù)部一直建議視是否存在集體協(xié)議,在適用一般立法框架方面提供更大的靈活性。此外,該部正計(jì)劃推動(dòng)建立工作委員會(huì),并建議提高工作委員會(huì)在數(shù)字工作領(lǐng)域參與共同決策的能力。同時(shí),與社會(huì)伙伴一道,德國(guó)勞動(dòng)和社會(huì)事務(wù)部在進(jìn)一步完善福利國(guó)家制度中的主要目標(biāo)是穩(wěn)定就業(yè)能力,并為人們工作生涯的各種轉(zhuǎn)換提供便利。再者,該部還建議建立長(zhǎng)期性的個(gè)人賬戶(個(gè)人活動(dòng)賬戶),每個(gè)人在其工作生涯開(kāi)始時(shí)設(shè)立該賬戶并注入基礎(chǔ)“資本”,然后通過(guò)就業(yè)或個(gè)人繳費(fèi)賺取“積分”,這些積分可用于接受教育、提高技能、創(chuàng)業(yè)或離職休假。同時(shí),它也可以作為個(gè)人能夠向其繳費(fèi)的長(zhǎng)期賬戶進(jìn)行管理。除了工作4.0對(duì)話之外,德國(guó)所有的社會(huì)伙伴都需要就福利國(guó)家及其社會(huì)保障體系的未來(lái)達(dá)成社會(huì)共識(shí)。根據(jù)工作4.0的對(duì)話進(jìn)程,將有5個(gè)方面的核心問(wèn)題需要處理:一是收入與社會(huì)保障;二是獲得優(yōu)質(zhì)工作的機(jī)會(huì);三是多樣化成為新常態(tài),即構(gòu)建以生命階段為策略而非死板的工作模式;四是保持工作質(zhì)量;五是將共同決策、參與和企業(yè)文化視為一個(gè)整體①BMAS (eds.), Darum geht's Der Dialogprozess Arbeiten 4.0, http://www.arbeitenviernull.de/dialogprozess/darum-gehts.html, 2019.。
總體而言,工會(huì)和雇主協(xié)會(huì)等關(guān)鍵角色的系統(tǒng)參與以及社團(tuán)主義機(jī)制的復(fù)興似乎是一個(gè)很有前途的戰(zhàn)略。然而,縱觀時(shí)間軸,德國(guó)顯然至今一直在走外部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主要關(guān)注技術(shù)和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這有些出乎意料,因?yàn)榈聡?guó)已經(jīng)建立了適當(dāng)?shù)恼胶头钦綑C(jī)構(gòu)(社團(tuán)主義),本可以嘗試采取更全面的方法。此外,協(xié)調(diào)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制度結(jié)構(gòu)現(xiàn)在也需要證明其在合作基礎(chǔ)上塑造數(shù)字化的能力。
- 社會(huì)保障評(píng)論的其它文章
- 收入保持與工傷保險(xiǎn)補(bǔ)償給付體系之調(diào)整
- 住房公積金制度何去何從:存廢之爭(zhēng)、定位重思與改革方向
- 社區(qū)老年服務(wù)供需動(dòng)態(tài)變化與平衡性研究
——基于CLHLS 2005—2014的數(shù)據(jù) - 延遲退休年齡對(duì)城鎮(zhèn)職工醫(yī)保基金平衡的影響
——基于政策模擬的研究 - 城鄉(xiāng)居民養(yǎng)老保險(xiǎn)對(duì)代際收入轉(zhuǎn)移的影響:基于CLHLS 2005—2014的縱貫分析
- 共享、融合與創(chuàng)新:城鎮(zhèn)低收入群體多層次養(yǎng)老保險(xiǎn)體系設(shè)計(j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