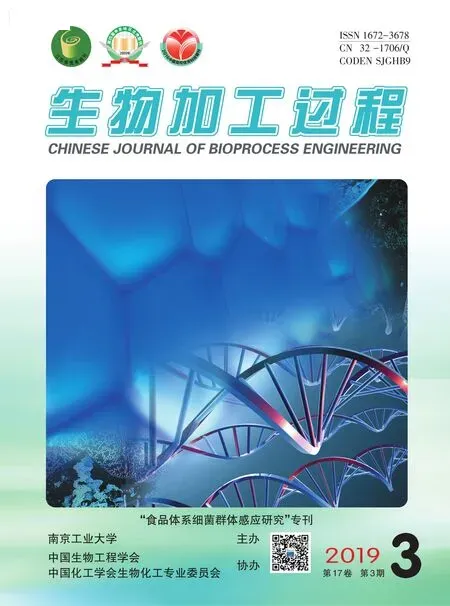細菌群體感應對細菌生物膜形成與調控的研究進展
董汝月,于曉倩,曾名湧,劉尊英
(中國海洋大學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山東青島266003)
Rending等[1]根據信號分子的性質及感應模式的不同,將細菌群體感應(quorum sensing,QS)系統分為4類:① LuxI/R型信號系統。除黃色黏球菌和哈氏弧菌(Vibrioharveyi)外,大部分的革蘭氏陰性菌的QS都是由這個系統調控,該系統以N-酰基高絲氨酸內酯(N-acyl-homoserine lactones,AHLs)作為信號分子。AHLs由LuxI酶合成,在細胞內不斷累積后利用特定的傳輸系統向外運輸,其數量達到一定閾值后就會與相應的受體蛋白LuxR結合進而啟動下游基因的表達(圖1)。研究發現,在部分革蘭氏陰性菌中,LasR、CarR、ExpR、Rh1R和TraR也屬于AHLs受體蛋白[2]。

圖1 LuxI/R型信號系統[1] Fig.1 LuxI/R quorum-sensing system[1]

圖3 LuxS/AI-2型信號系統[1] Fig.3 LuxS/AI-2 quorum-sensing system[1]
②小分子多肽介導的信號系統。主要存在于革蘭氏陽性菌中,在該系統中主要利用修飾后的小分子多肽(auto-inducing peptides,AIPs)作為信號分子,AIPs不能自由穿透細胞壁,需通過ABC轉運系統(ATP-binding cassette)才能到達細胞外發揮作用。AIPs濃度達到一定閾值時會與細胞膜上的雙組分磷酸蛋白激酶信號識別系統結合,引發激酶的組氨酸磷酸化并使細胞內受體蛋白的天冬氨酸磷酸化,然后再與特定靶位結合后啟動目的基因的表達[3](圖2)。

圖2 AIP介導的信號系統[3] Fig.2 AIP quorum-sensing system[3]
③LuxS/AI-2型信號系統。除了細菌種內的QS交流外,還存在一種用于種間交流的AI-2(autoinducer-2,AI-2)型群體感應系統(圖3)。AI-2分子被認為是一類呋喃酮酰硼酸二酯(furanosyl borate diester),其前體為4,5-二羥基-2,3-戊二酮(DPD),在該系統中,當AI-2在菌體外積累到一定閾值時會與LuxP受體蛋白結合,再通過與激酶蛋白LuxQ反應啟動相關基因的表達[4]。
④AI-3/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型信號系統。人們對于該系統中的信號分子AI-3研究得很少,該信號分子是表達腸出血性大腸桿菌毒力因子的信號分子,然而該分子結構尚未明確[5],該系統的諸多功能仍在探索中(圖4)。

圖4 AI-3/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型信號系統[1] Fig.4 AI-3 quorum-sensing system[1]

圖5 生物膜形成過程 Fig.5 The biofilm life cycle
1 細菌生物膜的形成過程
細菌生物膜的形成一般包括4個階段(圖5)[6]。第一階段為細菌初始黏附。浮游的細菌借助鞭毛的運動、流體動力或布朗運動到達載體表面;第二階段為細菌微集落形成。吸附到載體表面的細菌在繁殖過程中通過調節基因表達,分泌出胞外聚合物如多糖、蛋白質、胞外DNA等黏附于載體表面形成微集落;第三階段為生物膜成熟。細菌通過生長和繁殖形成復雜的三維結構的生物膜;第四階段為生物膜的分散。生物膜中的胞外聚合物分解,單個細菌脫離生物膜,進入周圍環境中,進入下一個生物膜周期[7]。細菌生物膜形成的不同階段與群體感應密切相關,受群體感應系統的調控。
1.1 細菌初始黏附
在生物膜形成的初始階段,微生物細胞可以通過它們的附屬物(例如柱狀物和鞭毛)附著到表面,也可以利用其他物理作用,如范德華力/靜電相互作用等附著到其上。Yarwood 等[8]研究發現,細菌的初始黏附與細菌群體感應有關,在金黃色葡萄球菌中,agr群體感應系統控制幾種與宿主基質接觸的表面黏附素,這些包括纖維蛋白原和纖連蛋白結合蛋白。在某些條件下,agr突變體比野生型菌株更容易黏附在生物和非生物表面[9]。Cole等[10]發現,胃腸道病原體幽門螺桿菌具有涉及附著的群體感應luxS的同系物,并發現luxS突變體的黏附能力要比野生型菌株高2倍。
1.2 生物膜微集落的形成與成熟
細菌吸附到載體表面后,在繁殖過程中通過調節基因表達,分泌出細胞外聚合物,這些聚合物黏附到載體上形成生物膜微集落[7]。Hentzer等[11]研究表明,細菌的運動性、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ar polymeric substance,EPS)形成和鼠李糖脂形成會影響生物膜結構。EPS是生物膜中的主要組分,EPS占總生物膜質量的50%~80%,研究表明在生物膜成熟階段,對EPS的形成很重要的某些基因產物被表達,而群體感應系統是EPS生成的一個重要調控機制[12]。Borlee等[13]發現第二信使環二鳥苷酸(c-di-GMP)能夠正向調節EPS基質組分的產生。Starkey等[14]在銅綠假單胞菌中發現細胞內高水平的c-di-GMP能夠通過促進EPS基質形成來促進生物膜生長,而較低水平的c-di-GMP促進浮游細菌的活力。Huber等[15]發現群感應系統cep可以調控cepI/R洋蔥伯克霍爾德菌H111菌生物膜的成熟。在具有cepI或cepR突變的菌株中,它可以形成生物膜中的微集落,而野生型菌株則形成成熟的生物膜。Labbate等[16]和Lynch 等[17]研究發現:基于酰基HSL的群體感應影響革蘭氏陰性細菌Serratialiquefaciens、嗜水氣單胞菌的生物膜成熟,攜帶ahyI突變的菌株形成比野生型菌株結構分化更小的生物膜,ahyI突變體也顯示出生物膜相關活力計數的逐漸減少,且這種表現可以通過添加外源丁酰基HSL使其恢復。Yang等[18]研究發現細菌產生的AHL顯著增加了硅藻生物膜的生物量和EPS產量。
1.3 生物膜的分散
在生物膜分散階段,生物膜內的微生物細胞快速增殖和分散,以便從生物膜中離開成為浮游形式,有利于細菌轉移到新的部位從而實現傳播感染[19]。Le等[20]發現,金黃色葡萄球菌的agr系統突變株的生物膜形成能力增強,同樣的agr系統可以使成熟的生物膜解離,金黃色葡萄球菌的agr系統可以通過上調類似去污劑的多肽酶和核酸酶的表達來促進生物膜解離。在生物膜分散階段,群體感應系統仍可調控生物膜解離速度而加速細菌分散、感染。
2 生物膜形成調控策略研究
由于QS系統參與細菌生物膜形成的不同階段,故細菌生物膜形成調控策略不僅包括通過直接手段(如生物膜降解酶)去除生物被膜,還包括通過抑制QS系統來間接調控生物膜的形成,下面簡要介紹幾種常見的生物膜形成調控策略。
2.1 抑制細菌群體感應信號分子的產生
該策略通過干擾細菌信號分子的合成途徑,抑制信號分子的合成,從而達到調控細菌生物膜形成的目的。信號分子大體分為4類:①N-酰基高絲氨酸內酯(acyl-homoserine lactones,AHLs)及其衍生物類,即AI-1類,這類信號分子主要作用于革蘭陰性細菌;②氨基酸和修飾后短肽類(autoinducing peptide,AIPs),這類信號分子主要作用于革蘭陽性細菌;③呋喃硼酸酯類(furanostlborate-diester),即AI-2類,它是一類種間信號分子;④其他信號分子,哈維氏弧菌產生的第三類自誘導分子13-碳羥基酮(13-carbon hydroxyl ketone),即CAI-1[21]。QS信號分子的產生是以某類物質為底物,然后經各種酶共同催化合成。因此,理論上可以通過破壞底物或抑制酶活性來阻斷信號分子的合成[22]。由S-腺苷甲硫氨酸(SAM)衍生的AI-1和AI-2類信號分子,經過5′-甲基硫代腺苷/S-腺苷高半胱氨酸核苷酶(MTAN/Pfs)催化5′-甲基硫代腺苷(MTA)或S-腺苷高半胱氨酸(SAH)水解使其脫腺苷化,在這一過程中,任一產物的積累都會抑制AI-1或AI-2的產生。近年來的詳細晶體學研究已經闡明了大腸桿菌SAH/MTA核苷酶結合位點的完整結構和幾何結構,從而實現了更多的互補抑制劑設計。Gutierrez等[23]研究發現羥基化吡咯烷作為一種SAH/MTA抑制劑能夠抑制自誘導物的產生。Schauder等[24]發現BuT-DAD Me-Immucillin-A能夠抑制2種菌AI-2的產生,并導致生物膜形成顯著減少。同樣,Dong等[25]發現Triclosan(二氯苯氧氯酚)通過抑制烯酰基 ACP還原酶而抑制銅綠假單胞菌N-丁酰基-L-高絲氨酸內酯(C4-HSL)合成。此外,植物中含有的天然小分子物質也可以干擾信號分子的產生。Truchado等[26]研究表明,富含黃烷酮的天然橙提取物(主要是柚皮苷、新橙皮苷和橙皮苷)可通過減少AHLs的產生來降低小腸炎耶爾森氏菌的活性并抑制生物膜的形成。
2.2 降解細菌群體感應信號分子
另一種基于QS的調控策略是通過產生信號分子降解酶降解信號分子,使細菌的QS系統不能感知信號分子,從而無法啟動相關基因的表達,以此調控生物膜形成。如細菌中有許多降解 AHLs 的群體感應淬滅酶,研究發現有4種類型的酶具有降解AHLs信號的能力:AHL-內酯酶和脫羧酶,能夠水解信號分子內酯環;另外2種為AHL-酰基酶和脫氨酶,能夠裂解信號分子酰基側鏈[12]。Romero等[27]發現魚類病原體Tenacibaculummaritimum形成生物膜依賴短鏈C4-HSL,并且可通過酰基轉移酶降解長鏈C10-HSL,從而影響其生物膜的形成能力。Chevrot等[28]發現由植物產生的γ-氨基丁酸能夠激活根瘤農桿菌的內酯酶(AttM)活性,進而降解AHL信號,減弱QS依賴性感染過程。Schipper等[29]在原核QS猝滅系統中添加了由一組基因bpiB編碼的“內酯酶”,在Nitrobactersp.中檢測到編碼BpiB01、BpiB04和BpiB07的3個同系物,這些基因負責抑制生物膜的形成。Vinoj等[30]發現由地衣芽孢桿菌DAHB1表達的AHL-內酯酶(AiiA)具有廣譜AHL底物特異性。純化的重組AiiA在蓋玻片試驗中抑制了弧菌生物膜的發育,并顯著減弱了循環水產養殖系統中蝦的感染和死亡率。
2.3 使用群體感應抑制劑
群體感應抑制劑(quorum sensing inhibitor,QSI)一般為信號分子類似物,通過與信號分子受體蛋白競爭性結合,并使受體蛋白失活,進而阻斷QS系統而調控生物模的形成。最早發現的群體感應抑制劑是從海洋紅藻Deliseapulchra中提取的一種 AHLs 類似物——鹵化呋喃酮(halogenated furanones),該物質可以破壞費氏弧菌的QS行為[31]。最早研究的(5Z)-4-溴-5-(溴亞甲基)-3-丁基-2(5H)-呋喃酮可抑制大腸桿菌中的群集和生物膜形成。Ren等[32]通過DNA微陣列分析發現,天然的溴化呋喃酮所抑制的大多數基因是參與趨化性/運動性和鞭毛合成。Roy等[33]發現,在鼠傷寒沙門氏菌中,具有2~6個碳原子側鏈的合成呋喃酮能夠顯著抑制生物膜形成。He等[34]發現呋喃酮化合物C-30與變形鏈球菌在牙齒表面形成生物膜有關,這種化合物會降低與細菌黏附和生物膜積累相關的基因的表達,從而使生物膜變薄,并發現其他種類鏈球菌的生物膜形成被呋喃酮C-56抑制[35]。Kalaiarasan等[36]研究發現,合成的2種抗QS化合物N-(4- (4-氟苯胺)丁酰基)-L-高絲氨酸內酯(FABHL)和N-(4-(4-氯苯胺)丁酰基) - L-高絲氨酸內酯(CABHL)可以通過抗QS系統來抑制生物膜形成。在植物中同樣存在與信號分子結構類似的物質,可以干擾信號分子的產生,從而干擾生物膜的形成。Siddiqui等[37]發現胡椒提取物可抑制AHLs的產生,并且抑制由銅綠假單胞菌和細菌聚生體引起的生物膜形成和EPS產生。
2.4 群體感應抑制劑與抗生素協同作用
生物膜內的細菌在生物膜胞外基質的保護下可以更好地抵抗殺菌物質。因此,破壞生物膜可能會增強細菌對殺菌物質的敏感性。Bahari 等[38]報道了添加姜黃素顯著降低了阿奇霉素和慶大霉素對銅綠假單胞菌的最低抑菌濃度(MIC),且阿奇霉素比慶大霉素和姜黃素對生物膜形成和運動性表現出更大的抑制。Zeng等[39]發現抗生素氨芐青霉素和黃芩苷對銅綠假單胞菌生物膜抑制具有協同作用。Mahdiun等[40]發現鉍 -乙二硫醇和妥布霉素可以協同降低銅綠假單胞菌中信號分子的產生和生物膜的形成。Brackman等[41]發現妥布霉素和黃芩苷水合物聯合作用可有效減少肺部感染伯克霍爾德氏菌的微生物群體負荷,且病原菌的生物膜不能維持。
2.5 使用生物膜降解酶
生物膜調控除了基于QS的調控策略外,生物膜EPS降解酶也越來越受到重視。EPS主要成分為多糖、蛋白質、糖蛋白、脂質、磷脂、糖脂和核酸。根據EPS不同的成分,可以將生物膜降解酶分為多糖降解酶、蛋白水解酶和胞外DNA降解酶。多糖降解酶一般包括淀粉酶、海藻酸裂解酶、纖維素酶和溶菌酶。Araújo等[42]發現β-葡聚糖酶與季銨鹽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銨(CTAB)協同作用可去除銅綠假單胞菌60%的生物膜。Huang等[43]發現蛋白酶在去除生物膜方面更有效。Lefebvre等[44]發現,絲氨酸蛋白酶可分別降解綠膿桿菌和金黃色葡萄球菌77%和70%的生物膜。Ye等[46]研究發現,將脫氧核糖核酸酶I(DNase I)固定在鈦(Ti)表面上可顯著降低變形鏈球菌(變形鏈球菌)和金黃色葡萄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在載體上的黏附和生物膜形成。Kim等[45]研究發現DNase I可以顯著抑制大腸桿菌生物膜形成并能顯著降解已形成的成熟生物膜。生物膜降解酶的使用可以替代或減少化學殺菌劑的使用,從而有效提高產品安全性。
3 結語與展望
QS系統是細菌主要的調控和交流機制,細菌利用其可以方便地感知周圍環境中自身或其他細菌的濃度變化,并借此來調控細菌內某些特定基因的表達。細菌生物膜使細菌具有更強的耐藥性,對人類安全產生嚴重威脅,而群體感應作為調控生物膜形成的重要機制之一,了解細菌生物膜形成過程中QS的具體調控過程和調控策略可以有效的去除和控制生物膜及相關感染。與化學合成的群體感應抑制劑相比,植物中提取的QSI安全性更高,并且群體感應抑制劑與抗菌劑的協同作用可以更好地減少藥物的應用。最近生物膜中主要成分EPS的研究越來越多,特別是高效、綠色的酶制劑的應用發展前景也非常廣闊,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新的理論不斷被提出,我們有理由相信,將來可以更好地解決細菌生物膜這一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