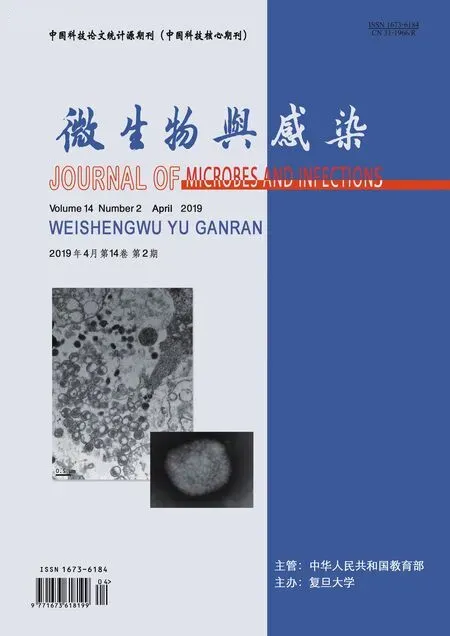腸道黏膜免疫與炎癥小體的研究進展
黃佳銘,楊冬雪,李曉曦,楊碩
1. 南京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免疫學系, 南京 211100; 2. 南京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
1 腸道免疫
腸道是機體主要消化器官,也是機體重要免疫器官,處于機體免疫防御的最前線。腸黏膜是機體與病原發生相互作用的主要場所,腸道中有大量腸道菌群定植,它們與宿主共生,在腸道免疫中發揮重要作用[1]。根據目前研究結果,腸道免疫系統主要由腸道菌群、腸道上皮細胞(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IEC)、腸上皮內淋巴細胞(intraepithelial lymphocyte,IEL)、固有層淋巴細胞(lamina propria lymphocyte,LPL)及派氏淋巴結(Peyer’s patch,PP)等構成(圖1)。
1.1 腸道菌群
腸道微生物群是人類胃腸道中發現的微生物或有機體的集合,包括細菌、古菌、真菌、原生動物和病毒[2]。腸道菌群有數萬億個共生微生物,主要包括5個細菌門:厚壁菌門、擬桿菌門、放線菌門、變形桿菌門和梭狀菌門, 其中擬桿菌和厚壁菌占腸道總菌群的90%左右(分別占25%和65%)。腸道菌群在不同腸段中定植的種類存在差異,小腸中梭狀菌、鏈球菌和乳酸桿菌等為優勢菌群,而盲腸、結腸和直腸中的優勢菌群是厚壁菌和擬桿菌[1]。腸道微生物群不僅對機體吸收營養物質至關重要,還有助于抵御其他病原菌入侵,并為免疫系統正常發育提供必需的條件[3]。有研究比較了菌群移植前后實驗動物消化道的狀態,發現無菌動物胃腸道蠕動減慢,小腸絨毛增長,腸壁變薄,相關淋巴組織不發達,上皮淋巴細胞、黏膜中IgA+漿細胞和CD4+T細胞減少,抗原呈遞細胞的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物(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Ⅱ分子表達下降。重新移植菌群后,腸道收縮加快,絨毛變短,血管增生,淋巴細胞聚集到黏膜,淋巴細胞對抗原的反應速度和強度均增加,腸道免疫功能顯著增強[4]。有研究報道,腸道菌群可分泌信號分子,促進黏膜免疫系統中免疫細胞數量增加和分化,并誘導黏液及抗菌肽等分子表達[5]。腸道微生物的顯著變化會調控天然免疫和適應性免疫細胞的發育[6],進而影響腸道內穩態及機體免疫系統功能。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菌群失調與許多疾病的發生密切相關,如肥胖、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腸易激惹綜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自身免疫病、過敏、自閉癥、抑郁癥及老年性癡呆等。腸道菌群失調可增加腸道中游離氨基酸,特別是脯氨酸,艱難梭菌(Clostridiumdifficile)可利用這些氨基酸作為能量來源,促進艱難梭菌感染,造成嚴重腹瀉,甚至引起死亡[7]。腸道菌群紊亂導致物質代謝異常,可引發心血管疾病。膳食膽堿、磷脂酰膽堿或甜菜堿依賴腸道菌群的代謝產物——氧化三甲胺(trimetlylamine oxide,TMAO),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風險。主要來源于雞蛋、牛奶、肝臟、紅色肉類、魚類等的磷脂酰膽堿,在腸道中首先被腸道菌群代謝生成三甲胺,三甲胺在肝臟黃素單加氧酶的作用下形成TMAO,進而通過調節巨噬細胞表面清道夫受體的表達水平,參與動脈粥樣硬化過程[8]。因此,腸道菌群不僅調節腸道黏膜免疫,對機體其他系統功能的有效發揮也有重要幫助。

In small intestine, there are various different types of cells localized in the gut epithelium along the crypt-villus axis, in which each type of epithelial cells plays unique role in maintaining intestinal homeostasis. Enterocytes, the most prominent cell type of the intestinal epithelium, are responsible for nutrient and water absorption and also produce antimicrobial peptides such as RegIIIγ, β-defensins, cathelicidins to defend against invading pathogens. Paneth cells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crypt produce amounts of specific antimicrobial peptides (lysozyme, α-defensins, sPLA2). M cells are localized in the follicle-associated epithelium (FAE) overlying Peyer’s patches and can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antigen uptake and passage to underlying immune cells. Goblet cells secret mucin and promote luminal antigens transfer to dendritic cells. Endocrine cells are stimulated by antigens to produce transmitter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digestive function of intestine system and regulate intestinal immune function. In addition,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immune cells distributed in the intestinal epithelium and lamina propria of the intestine, such as macrophages, neutrophils, dendritic cells, monocytes, lymphocytes and plasma cells, etc, which form a complex network to monitor the intestinal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as the first line of host defense against threats from the microbiome. Moreover, plenty of microbiota in intestine are not only the threat to host, but also play key roles as one of the components of intestinal mucosal immune system. Intestinal microbiota can competitively inhibit the coloniza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n the intestine,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stinal mucosal immune system, and regulate intestinal epithelial function by secreting metabolites.
圖1腸道免疫系統主要構成
Fig.1Thecomponentsofintestinalmucosalimmunesystem
1.2 腸道上皮細胞
腸道上皮細胞是參與腸道黏膜免疫的主要功能細胞,主要包括吸收性柱狀上皮細胞、杯狀細胞、潘氏細胞、內分泌細胞、M細胞等。它們呈單層緊密排列,組成腸道上皮組織并覆蓋于黏膜表面,除能消化吸收腸道營養及形成黏膜物理屏障阻礙細菌入侵外,還參與漿細胞分泌的IgA抗體轉運、抗原呈遞、細胞因子分泌等免疫活動。腸道上皮細胞中腸細胞占80%以上,其表面的微絨毛結構增大了與外界物質接觸的表面積,同時刷狀緣表面表達分泌多種蛋白質降解酶,可對腸腔中的蛋白質等進行充分降解和吸收[9]。腸細胞之間形成緊密連接,構成腸道黏膜的主要物理屏障,且在腸道細菌刺激下,腸細胞可分泌大量抗菌物質如RegⅢγ、β-defensin、抗菌肽等,直接殺滅細菌進而控制腸道菌群穩態[10]。杯狀細胞是維持上皮細胞屏障功能的一群特化細胞,在腸道黏膜免疫中有重要功能。杯狀細胞可分泌多種黏液蛋白,組成腸道上皮組織黏液屏障,通過疏水作用結合腸道細菌抗原蛋白,進而限制其侵入腸黏膜[11]。潘氏細胞位于腸道隱窩底部,主要功能是分泌抗菌分子殺滅入侵細菌;此外,潘氏細胞緊鄰腸道干細胞,可分泌WNT信號分子和乳酸代謝分子等,對腸道干細胞增殖和分化有重要調節作用。因此,潘氏細胞對腸道發育和腸道黏膜防御至關重要[10]。腸道上皮還存在內分泌細胞,這些細胞在抗原刺激下會釋放小分子遞質(如5-羥色胺、組胺、促胰液素、膽囊收縮素-促胰酶素),刺激腸道神經和免疫細胞發揮功能,可幫助腸道蠕動,促進腸道消化吸收營養物質,還可調節腸道黏膜免疫防御[5]。M細胞是一種存在于腸道上皮組織中特化的抗原轉運細胞,其細胞表面無微絨毛結構,不分泌消化酶和黏液,因此抗原物質更容易通過M細胞進入腸黏膜派氏淋巴結中,被樹突細胞攝取、加工并呈遞給T細胞,進而激活免疫應答和促進漿細胞分泌IgA抗體來防御入侵腸道細菌[12]。此外,大量研究表明,腸道上皮細胞在腸道細菌刺激下會產生大量免疫效應分子,如炎癥和趨化因子——白細胞介素18(interleukin 18,IL-18)、IL-6、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人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等,對腸道免疫細胞的招募、增殖、活化和免疫應答發生具有重要作用[4]。由此可見,腸道上皮細胞既能促進機體對食物營養物質的吸收,也能形成物理屏障阻礙腸道細菌侵入腸黏膜,還能作為連接天然免疫與適應性免疫應答的橋梁,其多元化角色對維持腸道微環境穩態平衡至關重要[13]。
1.3 腸道免疫細胞
腸上皮內淋巴細胞和固有層淋巴細胞是腸道主要免疫細胞。腸上皮內淋巴細胞是機體內最大的淋巴細胞群,約90%是CD3+T細胞,其中一半為CD3+CD8+T細胞,可通過Fas受體誘導細胞凋亡來清除入侵病原,并分泌細胞因子調節腸道上皮細胞和固有層淋巴細胞功能,目前對其功能的研究還在探索中[14]。固有層白細胞主要包括樹突細胞、分泌IgA的漿細胞、T細胞和固有淋巴樣細胞(innate lymphoid cell,ILC)等[13]。
樹突細胞是專職抗原呈遞細胞之一。小鼠腸道中的樹突細胞亞群高表達CD11c和MHCⅡ分子,但不表達IgG高親和力受體CD64[15]。定居在腸道固有層的樹突細胞為CD103-CX3CR1+亞群,其樹突能在腸道上皮細胞間隙延伸至腸腔攝取抗原,主要發揮抗原加工和呈遞功能。另一種樹突細胞為CD103+CX3CR1-亞群,可進一步分為CD11b+CD8α-和CD11b-CD8α+兩種小亞群[16]。有研究發現, CD103+CD11b+和CD103+CD8α+亞群可遷移至派氏淋巴結和腸系膜淋巴結(mesenteric lymph node,mLN)中,促進初始T細胞分化、成熟和免疫耐受形成,在腸道黏膜免疫中發揮重要作用[16]。
腸道固有層存在大量B細胞,細胞膜表面主要表達分泌型IgA。雖然IgM是B細胞首先產生的免疫球蛋白,但B細胞在淋巴組織生發中心受到抗原刺激和濾泡輔助T細胞(follicular helper T,Tfh)作用,會發生抗體類別轉換(class-switch recombination,CSR),產生IgG、IgA和IgE。在腸道特定的免疫微環境中,如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factor β,TGF-β)及IL-10等細胞因子大量存在,促進B細胞分化為分泌型IgA漿細胞,其分泌的IgA通過腸道上皮細胞轉運進入腸腔,通過抗體中和作用來控制腸道細菌侵入。因此,IgA分泌型B細胞對腸道菌群調節和腸道黏膜免疫防御有極為重要的作用[14]。
腸道T細胞廣泛分布于派氏淋巴結、腸系膜淋巴結、固有層及腸道上皮組織內。T細胞根據其表面受體的不同分為γδT細胞與αβT細胞,在腸道免疫中均有重要作用。有研究發現,大腸埃希菌可激活γδT細胞產生細胞因子γ干擾素(interferon γ,IFN-γ),IFN-γ進一步刺激巨噬細胞釋放IL-15,促進γδT 細胞在感染部位聚集和激活,進而誘發抗感染免疫[17]。此外,γδT 細胞激活可釋放炎癥因子IL-17,IL-17在腸道免疫中有重要作用,可招募中性粒細胞抵抗腸道細菌感染[18]。αβT細胞對抗原識別具有特異性,在腸道樹突細胞作用下,初始T細胞(na?ve T cell,Tn)可激活分化成不同T細胞亞群,主要包括Th1、Th2、Th17、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Treg)和CD8+NKT細胞等,這些T細胞在腸道黏膜免疫防御中均有重要功能。Th1細胞可分泌IFN-γ和TNF-α等炎癥因子來促進抗感染,從而抵御腸道細菌侵入[19]。Th2細胞主要分泌IL-4、IL-5、IL-10等免疫效應分子,可誘導IgA型B細胞產生,進而釋放大量IgA以保護腸道黏膜[20]。Th17細胞可釋放IL-17、IL-22、IL-21、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等多種炎癥因子,不僅可招募中性粒細胞和單核巨噬細胞清除腸道細菌感染,還可促進腸道上皮細胞分泌抗菌肽直接殺滅細菌,并促進腸道上皮細胞的損傷修復[21]。Treg細胞具有免疫抑制作用,通常可抑制效應T細胞的過度增殖和活化,進而減輕過強免疫炎癥反應帶來的免疫病理損傷[22]。在腸道固有層中,Treg細胞主要通過產生IL-10、TGF-β等細胞因子來負調控效應T細胞的過度激活。因此,Treg細胞對維持腸道內穩態和抑制腸道炎癥的發生具有重要作用[23]。CD8+NKT細胞也參與腸道黏膜免疫反應。有研究發現,口服假結核耶爾森菌后可誘導CD8+T細胞在固有層聚集,進而控制腸道局部感染進程[24]。健康人腸道中的T細胞在腸道黏膜免疫和腸道內穩態維持過程中發揮著積極作用,然而IBD患者體內由于腸道免疫功能紊亂,T細胞常處于過度激活狀態。有研究表明,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e)和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患者腸道和外周血中T細胞顯著增多,且患者炎癥部位T細胞呈現Th17和Th1細胞共有特征,可同時分泌IL-17和IFN-γ炎癥因子[25],因此針對T細胞的治療方法將是臨床腸炎研究的重要方向。
ILC是近年來發現的一類重要的天然免疫細胞亞群,具有天然免疫和獲得性免疫細胞雙重特征。其與天然免疫細胞類似,可被病原迅速激活,但產生的效應分子與Th細胞相同。根據其分泌的細胞因子可分為4類,即ILC1、ILC2、ILC3和ILCreg細胞,與T細胞中的Th1、Th2、Th17及Treg相對應,在腸道黏膜免疫中發揮重要作用[26]。ILC1細胞在小腸和結腸中均有分布,產生IFN-γ、TNF-α等細胞因子,激活腸道抗感染反應[27]。ILC2細胞主要分泌IL-5、IL-13,在腸道抗寄生蟲反應中有重要作用[28]。ILC3細胞產生IL-17和IL-22,可保護腸道上皮,抵抗感染發生[29]。ILCreg是新近鑒別的可分泌IL-10抑炎性細胞因子的ILC,可調節腸道穩態,抑制腸道炎癥發生[14]。ILC在腸道細菌刺激后會產生大量細胞因子,如TNF-α、IFN-γ、IL-17等,進而激發免疫炎癥以清除病原體,但腸道中的ILC過度活化也會導致腸道炎癥,引起炎性腸道疾病發生[30]。
2 炎癥小體與腸道黏膜免疫
腸道免疫的誘導物包括食物和腸道微生物中的刺激分子和病原蛋白。天然免疫反應是機體阻礙病原入侵、清除有害物質、維持腸道免疫穩態的重要防御機制。作為病原感受器,分布于腸道上皮細胞的天然免疫模式識別受體(pattern-recognition receptor,PRR)如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TLR)、Nod樣受體(NOD-like receptor,NLR)、RIG-Ⅰ 樣受體(RIG-Ⅰ-like receptor,RLR)等中,可識別病原相關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PAMP)配體,激活下游信號通路和分子事件,誘導抗感染細胞因子及其他腸道黏膜免疫防御分子的表達,促進黏膜免疫反應發生[31]。目前,已發現多個IBD致病或易感基因為天然免疫分子,如NOD2、ATG16L、TLR9、NLRP3等[32]。研究表明,PRR在機體其他組織區域中的免疫作用多集中在促炎癥效應,在腸道中則不同,分布于腸道上皮細胞的PRR不僅可誘導炎癥招募免疫細胞,還可誘導上皮細胞釋放抗菌分子并直接引起上皮細胞死亡來清除入侵病原,因此腸道上皮細胞PRR對防御腸道菌群入侵和維持腸道內環境穩定具有獨特而強大的作用。炎癥小體是一類重要的NLR類PRR,是多蛋白組成的大分子復合體,其功能異常與許多感染和免疫疾病發生有關[33]。近年來研究表明, IBD、IBS等腸道免疫相關疾病與炎癥小體的非正常活化有密切關系,炎癥小體在腸道黏膜免疫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
2.1 炎癥小體
炎癥小體也稱炎性小體,為一種多蛋白復合體,是天然免疫系統的重要組成。根據核心分子不同,主要分為NLR和 AIM2樣受體(AIM2-like receptor,ALR)家族[11]。目前研究較多的炎癥小體主要包括NLRP3、NLRP1、NLRC4、NLRP6、NLRP12和AIM2(圖2)。炎癥小體能識別外源性的PAMP或內源性的危險相關分子模式(danger-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DAMP)[34],參與病原感染免疫防御及細胞損傷和代謝異常等導致的炎癥反應。炎癥小體激活后可促進蛋白酶Caspase-1和Caspase-11(人為Caspase-4/5)的激活,激活的Caspase可誘導IL-1和IL-18前體剪切而成熟。大量研究表明,炎癥小體激活產生的IL-1β和IL-18具有廣泛的生物學功能,在免疫和炎癥反應中起重要作用。其中IL-1是一種多功能細胞因子,在局部可誘導IL-6、IL-8、CCL2等細胞因子表達,幫助中性粒細胞及單核細胞遷移至感染和損傷部位,激活炎癥反應[14]。此外,IL-1也可促進樹突細胞、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的活化[35],且在免疫應答反應中增強T細胞的激活[4],與其他細胞因子協同作用可促進Th17細胞形成[36]。IL-1在腸道炎癥中的作用已被許多研究報道,阻斷IL-1可改善梭狀芽胞桿菌相關性結腸炎和沙門菌誘導的腸炎,提示IL-1在IBD中是一種促炎細胞因子,發揮炎癥損傷病理作用[37]。炎癥小體下游的另一效應因子IL-18不僅可激活單核細胞[26],還能誘導T細胞產生IFN-γ,被認為是一種促Th1分化細胞因子[28]。在一定條件下,IL-18也可激活γδT細胞驅動IL-17產生[38]。在腸道未發生感染和炎癥穩態的情況下,腸道上皮細胞是IL-18的主要來源[39],其釋放的IL-18被認為具有促進腸上皮修復、增殖和成熟的功能[29]。最近研究發現, Caspase激活還可切割Gasdermin D 蛋白(GSDMD),引起炎性死亡或細胞焦亡(pyroptosis)發生,這種新鑒定出的細胞死亡方式是一種“炎性細胞程序化死亡”。GSDMD被蛋白酶Caspase切割后,其N端結構域片段釋放并寡聚化,隨后結合到細胞膜上形成10~15 nm的孔洞,進一步促進成熟IL-1β和IL-18釋放,激活炎癥反應[40]。此外,GSDMD蛋白的N端片段寡聚化形成的孔洞會引起細胞滲透壓失衡和細胞膨脹,導致炎性死亡或細胞焦亡發生[32]。已有研究表明,細胞焦亡可破壞病原感染的細胞,抑制病原在細胞內的復制,并促進IL-1β和IL-18釋放,激活炎癥反應,引起針對相關病原的免疫應答發生,進而刺激機體免疫系統對病原感染的清除[20]。雖然細胞焦亡可保護機體免受病原感染的侵襲,但如果過度激活,會導致致命的膿毒癥發生[41]。有研究顯示,GSDMD缺失會削弱機體對腸道細菌和腸道病毒的清除[42],但其在腸道免疫中的具體角色仍需深入研究。

Inflammasomes are multiprotein complexes, mainly including NLRP1, NLRP3, NLRC4, NLRP6, and NLRP12, as well as AIM2 identified so far.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inflammasomes consist of core proteins, adaptor proteins, caspase and some regulatory proteins. The core protein usually contains leucine-rich repeat (LRR) domains, nucleotide-binding and oligomerization (NACHT) domains, a protease caspase activation and recruitment domain (CARD) or pyrin domain (PYD). However, the core protein of AIM2 inflammasome has a HIN-200 domain in its C-terminus that can bind to DNA. After sensing signal stimulation, inflammasome will assemble and recruit the protease caspase-1 and caspase-11 through CARD domain, then subsequently auto-activate caspase to form P20/P10 protease complex. The activated caspase not only converts pro-IL-18, pro-IL-1β to mature form, but also cleaves gasdermin D (GSDMD) to induce pyroptosis, thus promoting inflammation. Additionally, some inflammasomes such as NLRP3, NLRP6, NLRP12 contain PYD domain instead of CARD domain to recruit apoptosis-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s (ASCs), followed by recruitment of caspase through CARD domain of ASC.
圖2炎癥小體
Fig.2Inflammasomes
2.2 NLRP3炎癥小體與腸道
NLRP3是炎癥小體家族中的最主要一員,可被細菌毒素、ATP、線粒體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及尿素結晶等多種病原和體內危險信號分子激活,是抗感染免疫和炎癥性疾病發生過程中的重要角色[43]。在未發生感染和炎癥穩態的情況下,腸道中NLRP3的表達水平較低,一旦激活后會在腸道免疫細胞中上調表達,隨后組裝激活蛋白酶Caspase-1,促進IL-1β和IL-18前體的切割成熟,引發炎癥反應[11]。臨床流行病學研究發現,人染色體1q44下游NLRP3的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突變與克羅恩病發生相關[44]。在瑞典進行的一項研究分析了482例克羅恩病患者的SNP位點,發現CARD8和NALP3位點突變與克羅恩病發病的相關性最大,且有偏好男性的傾向[45]。除與腸道炎癥病理作用相關外,NLRP3在生理狀態下可保護腸道免受病原體侵害,其誘導的炎癥反應可激活免疫應答,控制腸道細菌感染[46]。NLRP3炎癥小體不僅參與IBD的發生,還有研究發現其異常激活與腸道腫瘤的形成密切相關[47]。已知動物脂肪的飽和脂肪酸可作為NLRP3炎癥小體激活反應的刺激物,引起內質網應激反應[48],而大豆蛋白等可抑制NLRP3炎癥小體異常激活[49](圖3)。
2.3 NLRC4炎癥小體與腸道
NLRC4炎癥小體可被致病性革蘭陰性沙門菌的細胞內鞭毛蛋白和Ⅲ型分泌系統(type III secretion system,T3SS)組分激活[50]。NLRC4炎癥小體激活后,會促進IL-1β和IL-18前體的成熟分泌,并引起細胞焦亡的發生[50]。NLRC4炎癥小體在維持腸道穩態平衡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腸道上皮細胞中的NLRC4炎癥小體激活可引起上皮細胞焦亡,導致細菌感染的細胞脫落,阻礙腸道細菌對腸道黏膜的侵襲,還可促進上皮細胞分泌IL-18,對腸道黏膜完整性有重要保護作用[51]。然而,NLRC4炎癥小體過度激活也可能導致嚴重的上皮破壞和病理損傷[52]。此外,NLRC4炎癥小體還參與p53下游凋亡通路[53],但其在腸道腫瘤發生中的作用還需進一步探索(圖3)。
2.4 NLRP6炎癥小體與腸道
NLRP6最初被稱為PYPAF5,在腎、肝、肺、大腸和小腸中高表達。腸道中NLRP6主要表達于腸道上皮細胞,如杯狀細胞,其對腸道黏膜自我更新修復和黏液蛋白分泌至關重要[54]。近年來研究表明,NLRP6通過多種機制參與調控宿主對病原的防御和腸道內穩態,包括炎癥小體效應、免疫信號通路激活、自噬作用等[55]。NLRP6能通過下游效應分子IL-18促進上皮細胞修復和分泌抗菌肽,且能通過自噬促進腸上皮黏液層形成[55]。NLRP6還可防御腸道病毒感染,相關研究表明腸道中NLRP6可作為病毒傳感器來調節腸道抗病毒反應[56]。由于NLRP6在腸道中作用重要,其表達受多種因素調節,如腸道菌群可調節NLRP6表達[57],水缺乏引起的應激效應也可通過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來抑制NLRP6表達[58]。對NLRP6活性調控因子的研究發現,膽汁酸衍生物牛磺酸可作為NLRP6信號通路的正調控因子,而精胺和組胺可作為負調控因子[57]。目前,關于NLRP6在人類胃腸道疾病中的作用數據很少,亟待進一步探索與研究(圖3)。
2.5 NLRP12炎癥小體與腸道
NLRP12炎癥小體功能異常與IBD發生有密切關系,但其對腸道黏膜免疫的調節作用復雜,涉及宿主基因組、微生物菌群和炎癥反應的動態交互作用。通過比較同卵雙胞胎和其他患者,發現NLRP12在人類潰瘍性結腸炎中表達較低。小鼠研究發現,NLRP12缺乏會引起結腸炎癥增加,并導致菌群多樣性發生改變,如腸道益生菌Lachnospiraceae減少,結腸炎相關的Erysipelotrichaceae顯著增加[59]。NLRP12缺陷引起的菌群失衡及結腸炎癥狀可被炎性因子抗體治療或益生菌Lachnospiraceae干預治療所逆轉[59]。將無特定病原體(specific pathogen free,SPF)級小鼠糞便移植到無菌NLRP12缺陷小鼠中,可引起后者異常免疫信號的抑制和結腸炎癥狀的逆轉,與此同時對NLRP12缺陷小鼠中炎癥因子進行阻斷可逆轉菌群的失調[59]。這些研究結果表明,NLRP12在腸道中對腸道菌群和黏膜免疫系統有雙重調節作用,為認識、研究和治療IBD提供了新的思路(圖3)。
2.6 AIM2炎癥小體與腸道
AIM2是干擾素誘導基因HIN-200家族的成員之一,是一種胞質DNA感受器[60]。AIM2炎癥小體在腸道多種細胞中表達,包括巨噬細胞、淋巴細胞、上皮細胞等。相關研究表明,腸道微生物DNA可激活AIM2炎癥小體,后者的激活進一步誘導IL-1β和IL-18產生。AIM2炎癥小體產生的IL-18與上皮細胞或免疫細胞的IL-18受體結合,誘導抗菌肽分子表達,因此其可通過抗菌肽調節腸道微生態,對維持腸道穩態及抵御病原體入侵起關鍵作用[61]。AIM2還與輻射引起的腸炎有關,缺乏AIM2的小鼠由于蛋白酶Caspase介導的腸道上皮細胞焦亡作用削弱而減輕了輻射誘導的腸道損傷[61]。AIM2也參與結直腸癌的發生,AIM2基因突變在遺傳性非息肉病性結直腸癌患者中已被發現[62]。小鼠研究表明,非造血細胞來源的AIM2通過不同于其炎癥小體的調控機制(如抑制過度AKT激活和WNT信號異常),調節腸道干細胞不受控制的增殖,防止腸道腫瘤發生[63]。綜上,AIM2也許可作為干預腸道疾病的治療靶點,但相關臨床研究還需深入[64](圖3)。

Upon pathogen invading into the epithelial cells, inflammasomes in the epithelium, such as NLRP6, NLRC4 and AIM2, will be activated to secret cytokine IL-18, which subsequently stimulates intestinal epithelial or immune cells to produce IL-22. IL-22 acts o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to induce the production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s and proteins required for the intestinal epithelial repair. Activation of inflammasomes in epithelial cells can also cause pyroptosis, which is activated and assembled by GSDMD protein to form membrane pores, leading to cell swelling and death. Pyroptosis can release the invading bacteria of epithelial cells and stimulate immune response to enhance mucosal immune defense. NLRP6 inflammasome in goblet cells not only promotes IL-18 secretion and pyroptosis, but also facilitates mucin protein secretion by regulating autophagy to protect intestinal epithelial integrity. NLRP12 inflammasome mainly perturbs immune signaling pathways of immune cells and inhibits excessive inflammatory responses. NLRP3 inflammasome plays roles in the immune cells of lamina propria, which can activate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promote mucosal immune defense in the homeostatic state, but cause inflammatory pathological damage in the excessive infection state.
圖3炎癥小體和腸道黏膜免疫
Fig.3Inflammasomesandintestinalmucosalimmunity
2.7 Gasdermin 家族與腸道
Gasdermin是一類保守蛋白家族,包括GSDMA、GSDMB、GSDMC、GSDMD、GSDME和DFNB59,大多數已被證明具有成孔活性[65],主要在免疫細胞中表達[66]。近年來研究較多的是GSDMD,它可通過“經典”和“非經典”途徑激活,導致細胞焦亡[40],已被確定為蛋白酶Caspase-1和Caspase-11(人為蛋白酶Caspase-4/5)的直接下游靶點[65]。GSDMD被裂解后其N端釋放并寡聚結合到胞膜上,形成細胞焦亡過程中質膜上的功能性孔隙,引起膜的腫脹和破裂[67],還與釋放IL-1β和IL-18有關[67]。GSDMD如果過度激活,會導致致命的膿毒癥發生。有研究表明,GSDMD可插入富含心磷脂的細菌膜中,發揮殺菌作用[40]。其在腸道黏膜免疫中也可能發揮重要作用,參與細菌感染的上皮細胞的脫落[51]及對腸道病毒的清除[68],但具體作用仍需深入研究。此外,有研究發現GSDMA、GSDMC、GSDMD在消化道腫瘤樣本中均沉默表達,很可能在消化道腫瘤發生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69](圖3)。
3 結語
在宿主與微生物共同進化的漫漫時間長河里,腸道免疫系統進化出復雜但有效的策略來應對外界病原的挑戰。最近大量研究表明,炎癥小體在腸道免疫中的作用至關重要,但作用機制遠未闡明。近年來,Gasdermin家族的發現為炎癥小體的腸道免疫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線索,但仍需進一步探索。腸道黏膜免疫研究方興未艾,深入研究腸道免疫系統的作用機制對攻克相關疾病、造福人類健康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