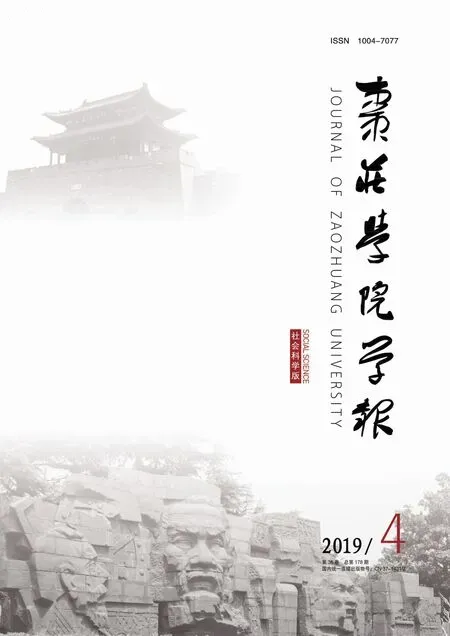歷史情懷與自由倫理批評
——評路文彬《中西文學倫理之辯》
胡莎
(1.北京語言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83;2.華北科技學院,北京 東燕郊 101601)
出于對人們生存現狀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情觀照和期待,路文彬教授致力于文學倫理研究和批判,探索倫理視野中的當代文學世界,數十年筆耕不輟,著作等身,日前又出版學術新作《中西文學倫理之辯》,該著作從“主體與服從”“自由與個體”“反抗與崇高”“善惡與正義”“男權與女權”等方面展開了富有前瞻性和建構意義的理論體系闡述;從學理角度辨別和厘清了常見的文學倫理認知誤區,突顯文學倫理建構主體本質存在及人倫和諧關系的社會功用和價值,并再度喚起我們生活感知與倫理思考在自由層面知行合一的初心。
托馬斯·曼曾在《自由的問題》一文中指出了:“不要由于別人不能成為我們所希望的人而憤怒,因為我們自己也難以成為自己所希望的人。”我們承受著無限生命之重,似乎并不自由快樂。路文彬教授獨辟蹊徑,對此問題做出了如下回應:“我們源于命運,卻又成就著命運。我們因為不自由,所以懂得了自由。總是有限給予著我們無限,這就是存在的真實境遇,命運永遠是通過約束來解放我們的。設若沒有有限與約束的話,我們可能壓根就無從認識自身的存在。”事實上,我們擁有怎樣的自由倫理觀,就生活著怎樣的命運。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偏重感性審美、關注“形而下”,導致中國文學至今不能以足夠的理性對待自由的問題。從古代儒道文化到現代啟蒙文學,再到當代文學,中國文學受縛于自由倫理,一直存在著自由倫理缺失、誤讀以及失范的問題。
不論是道家以“忘己”的方式踐行著自由,還是儒家以“克己”的形式接近著自由,都是以主體的實質性放逐為代價的。也就是說,無論秉持謹小慎微抑或灑脫超然的心態,實際上是出于順應外界的茍且享樂,有賴于外在力量的接納,無需激發和釋放主體自我內在力量進行自由反抗。可見,反抗作為所有存在主體對于命運的責任性應答和自由力量顯現的途徑,在中國儒道文化中是缺場的。同時“作為一種矯正或回歸,反抗乃是記憶的實踐。反抗本身其實就是對于遺忘的反抗。自由乃是通往真理的道路,基于自由渴望的反抗正是在這一點上證明了自身的真理屬性。”安提戈涅和竇娥的個案從主體實踐層面表明,“個體的實質不是被塑造出來的,乃是以自身的自由意志創造出來的”。如果沒有對于本質及其價值的清醒認知,沒有到達一定的精神高度,便不可能有堅定付諸行動的反抗。古希臘安提戈涅的反抗正是對于自己女性本質訴求的服從。安提戈涅不僅用生命捍衛了自我的本質,更為重要的是,她同時憑借這種犧牲使克瑞昂終于認識到了自己過錯,帶來了希望。相比而言,中國的竇娥由于傳統文化的自由倫理局限性,無法上升到安提戈涅的自由精神高度。
而中國近現代的啟蒙者們雖然已經開始認識到自由的價值,但是其深度卻是遠遠不夠的。于是我們在《傷逝》中不無失望地發現,子君雖然有著毫不妥協的自由意志,可是她依然畏懼于外在的未知世界,并沒有領會到自由的真諦。涓生最終拋卻了愛情責任重負,則表明了茍活者對于生命責任的無知和放棄,無以領會愛情的要義。他們更無法認識到痛苦與幸福的不可分離。唯有認識并肯定痛苦的價值,我們才能從超越幸福的角度重新思量人生的目的和啟示。而《玩偶之家》的娜拉在自由真理的引領下,勇于告別安逸的日子,奔向完全未知的世界,即覺醒之后的行動,投身到那個等待她認知、發掘的新世界。對于自由的態度,以及作家對于自由、責任和命運內在聯系的認知,是子君與娜拉之間本質性差異的原因所在。
近觀中國新時期當代文學,《愛,是不能忘記的》《綠化樹》《黑駿馬》《人生》等經典之作無疑都存在致命的缺憾,那就是由于缺乏了對生命意義和人類命運的主體性思考,這些當代作家們沒有深刻認識到愛與拯救的自由價值,致使正義和崇高、責任與愛在中國當代寫作中嚴重缺場。
我們作為社會中的個體,離不開社會群體生活,然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現代人處在一種‘他’所想所說的東西都是任何人所想所說的境地,他并未獲得不受他人干擾、獨立思考表達自己思想的能力”。要知道,“自由的魅力來自于差異”(鮑曼語),沒有差異便沒有自由,如果社會群體代替了個體思考,那么個體將不再是思考主體,一旦缺乏自己獨立人格和判斷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眾所周知,我們的傳統非常強調記憶的重要性,從古代入私塾背誦三字經,到科舉考試以四書五經為綱,再到現在中考,高考,以及《詩詞大會》《最強大腦》等電視娛樂節目,無一不在向我們著強調記憶背誦的重要性。可是我們在無休止的背誦中失去了很多,我們的大腦思辨能力一再降低水準,我們被迫記憶各種瑣碎的事實,所表達出來的情感和思想,更多的是為了適應甚至討好社會風俗或者輿論觀點。事實上,我們已被不自由的偽情感重重包圍著。即使我們要做出發自內心的自由選擇,也需要克服多重的阻力。
面對這個令人們感到棘手的問題,路文彬在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的關鍵在于,作為主體,他必須能夠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選擇。”“自由對于主體固然是重要的,但主體對于自由的意識也許是更加重要的。主體需要自由,然而設若缺少對于這種自由的認識,主體便難以承當一個真正主體所需承當的責任。最終,這個主體將極有可能會因此喪失他的自由。”而一旦喪失了主體自由,那么責任將由于沒有真實的根基作為支撐,良知因此無法同責任統一起來。這樣一來,主體將缺失自我的位屬,沒有未來和歷史,僅有當下;主體對于他者生命的愛與關懷、對他者困境的共同分擔將被漠視,主體自由倫理中蘊含的痛苦甚至犧牲的本意也會被消弭。而真正的孤獨者與眾不同。他能強烈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同時又沒有迷失在群體的喧囂中,而是超越于這個群體,并清醒洞見到自己對于這個群體的責任。不僅如此,真正的孤獨者由于借助了自由意志,從精神層面親近和認同痛苦的真正本質,進而理解到幸福的真正本質。因此,他并不拘囿于膚淺的幸福主義論調——對痛苦和沉重持厭棄甚至畏懼的態度。相反,他泰然自若從不絕望,“最終得以找到自我的和平”并實現了內心世界的豐盈和提升。
正如作者在書中所強調的:愛包容著恨,正如幸福包容著痛苦。幸福主義已使我們陷入認知的迷途,只有以自由名義承擔起反抗庸俗的責任,我們的文學才得以回歸本質,實現文學命運的救贖。路文彬教授這部著作的問世,無疑彰顯了他充滿愛與自由的歷史情懷和精英姿態,真誠而倔強地前行在文學倫理人格建構與完善的漫漫長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