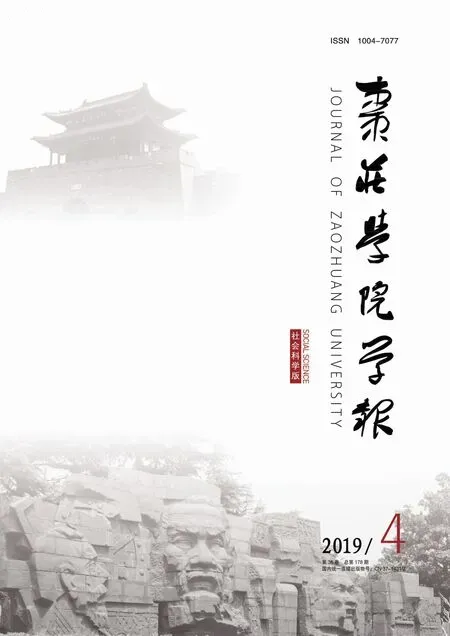論徐則臣中短篇小說中的謎題敘事
高媛
(山東理工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 淄博 255000)
徐則臣是中國大陸“70后”作家的重要代表,曾寫作《耶路撒冷》《北上》等多部較有分量的長篇小說。與此同時,他筆耕數十年,創作大量中短篇小說,在真假參半、虛實兼備的北京、花街、鵝橋、左山以及小葫蘆街等文學地理空間中,展現不同人物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欲。在其諸多中短篇作品中,“設謎”是作者常用的情節敘述手法,謎團既是推動小說情節發展的關鍵要素,亦是吸引讀者閱讀的重要內容。
一般說來,通俗小說會把“提出問題,延緩提供答案”作為結構文本的重要手段。問題主要包含兩類,亦催生出對應的兩種小說類型:涉及因果關系的問題,諸如“誰干的”是傳統偵探故事的內核,涉及時間的問題,諸如“后來會怎樣”則是探險故事的核心問題。[1](P14)徐則臣的中短篇寫作,也借鑒了這一藝術手段,以“謎”入文,使文本中的謎題呈現為兩種不同形態。
一、得解之謎:言在此而意在彼
在多數小說寫作中,謎題設置對應著解謎行為的發生,它一方面統攝表層情節結構發展,使其在設謎——解謎的深層敘事邏輯中順敘進行,另一方面則賦予小說神秘的懸疑色彩。徐則臣的中短篇小說,試圖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帶有細節性的謎題,以此剝落籠罩在生活世事之上的平淡面紗,再現復雜的人物過往經歷。平靜的花街上,修鞋的老默孤獨死去,在眾人的平淡生活里掀起波瀾。在遺書中,他把僅有的兩萬元存款留給豆腐店老板的兒子良生,透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神秘意味(《花街》)。海陵鎮上,老邁得已被人忘卻姓名的七奶奶,在近乎失智的狀態中,聽人轉述丈夫的侄子汝方死前念叨著“秦娥”一詞,突然抽搐,似乎要發病,讓人驚異(《憶秦娥》)。
在現實的謎題敘事之余,作者的筆觸一轉,將人物的舊日經歷寫入小說。良生的母親麻婆孤身帶著他來到花街,隨后被豆腐店老板藍麻子接納組建家庭。七奶奶與汝方的嬸侄關系,中間隔著長期在外做生意、一回家即暴斃的叔叔徐七。在歷史的故事追溯中,人物的謎樣行為似乎早已獲得答案。隨著良生與母親爭吵,母親早年的妓女身份以及父親的不義拋棄都得以顯露,他與老默之間可能存在的父子血緣正是確鑿的謎底。經歷了回光返照的七奶奶,念叨著“我等了七十一年,他終于肯叫我的名字了”[2]離世,重演了《伏羲伏羲》中王菊豆和楊天青的悲劇,亦為人生中最后的謎畫上句號。小說以謎題結構作品,在揭示謎底之余,更多將其思想意蘊置于人物的現實行為表現之中,老默來到花街后,日日光顧豆腐店,將早年的拋棄行為轉化為無言的癡守懺悔,七奶奶與汝方相互愛戀卻囿于宗法及世俗壓力難以相守,只能在獨處時回憶過往。
徐則臣作品中的謎題設置多關涉事物的因果聯系,設置方式因文本內容產生差異,謎題既可能是草蛇灰線的伏筆,亦會成為旁逸斜出的點綴,部分甚至僅存在小說中的某個細節里。在對謎題進行處理時,作者并非事無巨細地交待前因后果,而是有意在作品中減少關涉謎題的描寫,將其轉換為“隱藏的材料或曰省略的敘述”,以意味深長的沉默,“對故事的明晰部分產生顯而易見的影響”“并且刺激讀者的好奇心、希望和想象”[3](P95)。
在貫穿小說始終的伏筆式謎題中,《長途》一篇頗為典型。小說開端處,敘述者“我”帶著DV準備拍攝叔叔的長途跑車生活,卻發現他已成為水上運送貨物的船老大。“叔叔為何放棄心愛的汽車”,是小說起始預留的一個不起眼的謎題。運貨途中,叔叔搭載了一位瘸腿女性秦來,二人表現出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近至叔叔寧愿放棄拉貨也要搭載秦來,遠則為雙方溝通寥寥,“我”對秦來的試探亦使叔叔如臨大敵。雙方的關系在這種亦親亦疏的狀態中成為新的謎題。除此之外,小說中還穿插著叔叔講述的六個長途跑車故事,既與人物的水上經歷應和,也暗藏著叔叔的心機,最后一個故事將謎題全部揭破。在這段被他轉嫁到別人身上的肇事逃逸經歷中,秦來即是被撞瘸的陌生女孩,也成為叔叔此后放棄開車、主動搭載的直接原因。小說將一個陸上的車禍故事包裹成謎,轉移到水中飄搖的貨船之上,以叔叔隱秘的懺悔和贖罪行為,完成兩場融合在一起的長途故事講述,也寄寓著“再堅硬的仇恨和報復都會被時間打磨掉寒光,石頭失去棱角,終成為暖玉”[4](P141)的希望。
《鴨子是怎樣飛上天的》《刑具制造者》等作品亦采用同樣的伏筆式謎題設置方式。在前者中,年午的“鴨子飛上天”故事似乎對“我”的鴨子丟失做出合理解釋,但他一次次送到“我”家的野鴨以及最終躋身為“我”爸爸的事實,反而為鴨子失蹤提供了新的答案。作品中孩童的孤獨無措以及無力抵抗壓抑現實的悲劇頗為典型。后者里一出場即三天沒睡覺“做生意”的大班,最終在一眾戴著父親潛心研制的新枷鎖的反賊中出現,“生意”的真面目——革命得以彰顯,父親間接將其送上斷頭臺的人生荒誕感更難以言喻。
旁逸斜出的點綴式謎題,看似是小說的情節插曲,發生在次要人物身上,卻都在最終暗合了主要人物的命運際遇,強化了小說的主題思想表達。《如果大雪封門》《石頭、剪刀、布》以及《一號投遞線和憂傷》都包含這類謎題設置。在《如果大雪封門》中,離鄉的養鴿少年林慧聰留在北京的最后愿望即是看一場大雪,可是在等雪的過程中,他的鴿子不時失蹤與死亡,成為難以破解的謎題。同住的行健與米蘿雖有嫌疑,卻從未露出馬腳,直到“我”發現他們偷偷把鴿子送給一位陌生女性。真相大白的輕松并未如期而至,隨之而來的大雪以及鴿子死亡也帶來陌生女性無錢醫治重病被迫還鄉的消息,與看完雪即回鄉的林慧聰殊途同歸。底層“京漂”人物的殘酷生活境遇借助“鴿子”意象得到完整還原,其生計選擇(貼小廣告、養鴿)、生活細節以及京郊環境,都在養鴿、丟鴿、收鴿、送鴿的故事中體現。
與此類似的還有《石頭、剪刀、布》,飯店老板老吉的長期住院不歸之謎背后,隱藏著這個男人的不告而別真相,做出同樣選擇的,也包括老板娘小田的前幾任戀人兼合伙人。小說結尾處,“我”作為小田的新希望,享受過女性的柔情蜜意后,仍走上了前幾位男性的老路,在關鍵時刻背棄老板娘,回歸自己的舊日生活。部分男性的貪圖享樂、不負責任等劣根性成為小說著力批判的內容。《一號投遞線和憂傷》之中,身為投遞員的“我”努力探究單身女性陳禾的生活狀態之謎,毫不留情地揭穿她自己給自己寄信的把戲,戳破她所營造的“有人在關心我”心理幻想,卻未料到在觸及他人的痛苦時,自己以及其他都市人的孤獨感同樣強烈。
同時,小說中的部分謎題,體現在部分僅為敘述者“我”所知的細節中:《棄嬰》中如玉丟棄的男嬰,正是她與村長不正當關系的佐證;《大水》中,沉禾的妻子不幫丈夫拉架,與鄰居年五似乎交往過密的行為之謎,都在最終她與年五私奔的結局中得到驗證;《失聲》中丈夫過失致人死亡的姚丹,拒絕鄰居好意仍要維持家庭生計,等在黑暗中門口的明滅煙頭,在“我”的眼中,即是對其選擇的無聲證明。
除了對因果關系的謎題運用,徐則臣還在小說中設置了一系列時間謎題,將小說的情節推進動力轉化為“然后發生了什么”這一讀者閱讀訴求。《紙馬》里的敘述者“我”,因手藝出眾,也為了家庭生計,在鄰居葬禮上搖紙馬。但在送葬途中,承諾在家陪伴病重母親的侏儒哥哥卻出現了,使我開始擔心“家中母親如何”這一問題,也在無形中將其轉化為小說的情節謎題。緊隨其后,哥哥心愛的嗩吶、“我”懷中的紙馬、母親的病癥表現以及葬禮的過程描寫等內容交錯且重復出現,既寫出光棍兄弟倆的貧寒家境以及僅存樂趣,也不斷強化“母親在家如何”這一謎題所產生的懸念。小說結尾處,哥哥受送葬人群中慫恿,即將碰觸身邊的女孩達到人生“高峰”“我”卻聽到報信孩子帶來的母親倒地不起的消息,謎題的結局昭然若揭,也將兄弟二人拉回殘酷的現實。
除此之外,在北京這一地域空間的文學敘事中,尋找戀人胡方域的女孩居延面臨著“能否找到”的人生謎題(《居延》),有著八旗血統的上海女孩王琦瑤也在思索著能否見到“富豪爺爺”的重要問題(《浮世繪》)。前者中的尋找,因為居延的逐步成長與獨立變得無足輕重。謎題讓位于人物的經歷敘述,雖獲得破解,但只是為完成人物的心理轉變書寫。較之于謎的結果,人物努力破解謎題的過程及其中的人情冷暖,反而成為小說著力描寫的內容。后者的同名主人公王琦瑤,復刻了《長恨歌》中女性的選擇和命運,在與多位男性產生身體以及情感糾葛后,錯過了似謎一般的爺爺的真實境況——常年臥床且貧苦無依,也徹底失去了“飛上枝頭變鳳凰”的希望。
E·M·福斯特曾指出:“情節屬于小說那個講求邏輯、訴諸智識的層面;它需要謎團,不過這些謎團在后文中一定要解決”[4](P85)。這些在后文得以解答的各異謎題,存在于徐則臣的中短篇小說之中,不再像其在偵探小說等類型文本中,聚焦于“人物如何通過努力破解謎題”的過程,而多以水到渠成的方式被人物獲知答案,并在看似波瀾不驚的敘述中產生令讀者回味的藝術魅力。其原因即在于,小說中謎底的揭破,并非單純實現“真相大白”的敘事目的,從而滿足讀者對于事實的簡單探求,而是逸出謎題本身,暗示人物的行為,影響人物的命運,透射出現實社會中的都市底層人群、村鎮街道居民的人生百味體驗。基于此,得解的謎題在完成小說常規設謎——解謎情節模式之余,更多促成了“言此意彼”的效果達成。
二、懸置之謎:言有盡而意無窮
與文本中已獲確定性解答的謎題相比,始終處于無解狀態的謎題也在徐則臣的多部作品中出現。它們如同前者,扮演推動小說情節發展的重要角色,卻在關涉真相的時刻被懸置,使小說留有“空白”。這些謎題以單一或交錯的形態,產生于情節發展的不同階段,雖可供讀者進行多重讀解,仍賦予作品獨特的神秘韻味。
單一形態的懸置之謎可能出現在情節鏈條的任意一環,在徐則臣筆下,最為典型的是開端以及結尾部分。開端部分的未解謎題,本應類似于前文所述的伏筆式謎題,統攝整篇作品,但在逐步產生裂隙的文本敘述中,其位置和導向都發生偏移,最終促使無解狀態的生成。
小說《西夏》為投奔“我”的陌生啞女西夏設置了謎一樣的身份,以大量篇幅表現“我”為了探究西夏經歷所嘗試的種種努力。但臨近結尾處,西夏即將自陳身份,真相馬上可以大白,“我”卻主動放棄為其醫治啞疾的機會。因為“我”內心的恐懼作祟,擔心西夏的未知過往會導致雙方的分離結局,只能采取拒斥態度逃避現實。“我”的人為干預終止了真相顯露的進程,使小說重點從“西夏是誰”這一謎題,轉移到都市生活中陌生人共處“同一屋檐下”的可能性探究,也暴露出部分現代人在熟悉狀態中拒絕改變和失去的脆弱心理狀態。
《六耳獼猴》以馮年化身為六耳獼猴、被耍猴人玩弄的重復夢境,在開端設謎——馮年為什么總做同樣的夢?雖則主人公及其身邊人物提供不同解釋,諸如工作壓力、異性渴求、家庭幻想等,但并無確定性結論。看似多解的謎題在本質上仍處于無解狀態,反而體現出“京漂”小人物的現實生活處境以及多重心理壓力。
出現在結尾部分的懸置之謎,失去破解可能,只能將人物命運和情節進程定格在特定瞬間,小說敘述亦戛然而止。這類謎題使小說形成一種“沒有結局的結尾”[5](P145),也體現出作者的創作意圖:“對一個短篇小說來說,故事的確切結局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蘊的結局”,基于此,創作者“可以對故事保持必要的沉默”[6](P115)。
《我們的老海》中,前去海邊看望情人的“我”,被情人的丈夫海生發現私情,受到其不斷升級的報復,幾乎要殞命于大海。但出人意料的是,最終海生將“我”推上游泳圈,然后自己消失在大海之中。“海生為何要救我”變成無解謎題。《容小蓮》里的女性容小蓮,生活被異地丈夫、年幼兒子、周末情人、苛刻婆婆以及天真小叔子包圍,既要解決家中小叔子誤殺致人死亡的危機,又要面對單位查賬引發的情人失蹤問題。在小叔子伏法、情人被查后,人物從瑣事中抽身,卻發現兒子失蹤了。“兒子去哪兒了”是人物必須面對的現實謎題,在小說未能給出答案的情況下,極易導致人物生活支離破碎。兩部小說的主人公,人生際遇都呈現出同樣的下滑態勢,卻在小說結尾處,一反彈,一墜落,被懸置的謎題決定命運。
不同于上述設置單一謎題的作品,《最后一個獵人》《古代的黃昏》等作品采取“謎中謎”的方式,以舊謎題引發新謎題、新謎題解決/影響舊謎題等手段結構情節。需要注意的是,作品中的部分謎題并未獲得解答。正是因為這種未解狀態,人物命運及情節發展“留白”,為小說營造豐厚悠遠的審美意蘊。
身為“最后一個獵人”的杜老槍,在禁槍期間被人舉報用槍,面臨牢獄之災。“是誰舉報”是小說的核心謎題,多次出現于作品之中。他需要繳納足額罰款,在“借錢比賺錢還難”的現實境況中,女兒袖袖如何籌措錢財是暗藏的新謎題。直到以物質換取袖袖身體的男子前來“要債”,新謎題在杜家得解。男子被憤怒的杜老槍打死,又在“我”父親的言語掩飾中“變成”“舉報的人”。于不知情的旁觀者而言,杜老槍成功找到舉報者加以報復,破解了小說中的唯一謎題。但對少數知情者來說,得解的新謎題與未解的舊謎題被并置在一起,卻未能解決任何現實問題:舉報者未知又搭上了袖袖。戛然而止的結尾所留下的空白,按照現實邏輯發展,極有可能是杜老槍繼續服刑,袖袖為籌措錢財的努力付諸東流,更有可能還要繼續。人物在無解的謎題影響下,陷入新的悲劇境地。
《古代的黃昏》是一部多重謎題相套的作品。鵝橋的大戶林家已經漸趨衰敗,宅里潛藏著各色謎題,遠至幾年前的少爺被毒身亡之謎,近到剛發生的太太白貓被害之謎。種種跡象暗示謎題復雜交錯:家中管家與少奶奶曾有私情,管家毒打“不能生育”的妻子,為少爺看病的醫生杳無音訊,管家之妻偷買砒霜……多重矛盾爆發后,真相得以顯露:管家為了家產和少奶奶毒殺少爺,繼而暗害太太未果,管家之妻為了子嗣給少奶奶下毒,卻在無意中害死丈夫。看似清晰的敘事在結尾時產生新的謎題:少奶奶講述的小少爺身世真假難辨,在少爺與管家兩個當事人已死的境況中,“父親是誰”的答案,更像是少奶奶自保的護身符,可靠性大打折扣。未解的身世謎題在真假、是非乃至實虛之間游移,使小說保持一種神秘且混沌的風味。
與這類無解的謎題不同,徐則臣的部分中短篇小說中的謎題,呈現出似是而非的不確定性。它們貫穿情節發展始終,表現為晦暗不明的懸置狀態,確證或消解小說中已經發生過的情節內容,使小說一直保持著謎樣氛圍。在以這類謎題為主的作品中,人物的缺席、情節的斷裂時有發生,意義的無從探究亦是常態,類似于敘事充滿“空缺”[7](P116)的新潮小說。
《鵝橋》一篇中,帶著已逝父親“回到鵝橋”的囑托,“我”百般尋找終于抵達,卻發現當地人對“我”這個“水中影子是直的”外鄉人帶有冷漠的敵意,只有小水姑娘友好熱情。“我”向當地人打聽父親在此的經歷,多數鵝橋人不自然地否定他的存在,唯有精神有問題的“神經七”言語錯亂地還原“父親年少到此隨即拐跑當地姑娘”的事實。但細究人物的精神狀態,故事本身更像是不可靠敘事,“父親在鵝橋經歷了什么”這一問題變成“父親是否到過鵝橋”“我”也在探究未果的情況下離開鵝橋。謎底固然可被解讀為“外鄉青年帶走本地姑娘,引發當地人憤怒以致諱莫如深”,但當地人的“影子說”“神經七”的瘋癲言行,又使這一結論含混且曖昧不清。
同樣具有謎樣氛圍的《養蜂場旅館》,表現“我”的記憶與經歷差異謎題。“我”在左山散心時住進陌生的養蜂場旅館,卻發現房間似曾相識,老板娘小艾也認識“我”。她以種種舉動不斷提醒“我”8年前的故事:“我”傾心于她,把她從女孩變成母親。這與“我”的前女友搖搖的言說不謀而合,但絲毫沒有存在于“我”的記憶中。她還拿出錄音帶證明自己話語的可靠性,在她的誘導下,“我”試圖相信8年前確有其事,并與她鴛夢重溫。在這一過程中,老板在門口親眼目睹二人親熱,發出一聲“啊”,與錄音帶中那聲不知道是誰發出的“啊”重合。“舊事是否發生”是“我”到左山時即存在的謎。如果像兩位女性言之鑿鑿那般發生,那“我”的記憶空白,其實正呼應了《褐色鳥群》中“記憶是靠不住的”論斷。如果“我”的記憶沒有問題,那搖搖與小艾二人近乎一致的話語,以及“我”莫名的熟悉感,又能夠將一個謎題拆解為多個,并具多重解釋。
作為創作者曾計劃的《虛構的旅程》[8](P3)系列中的作品,兩篇小說都以人物探訪某地為情節線索,借助似是而非的謎題連綴起人物的過去和現在。《鵝橋》中“我”與父親重疊在一起,離開時,“神經七”誤以為“我”又把小水帶走,《養蜂場旅館》中時隔8年重演的場景及“啊”聲。重復的意象、事件將線性時間置換為循環時間,與謎題共同營造神秘的小說氛圍。
無解、多解乃至意味不明的懸置謎題,在小說文本中留下待解的“空白”,為作品提供豐富的闡釋空間。這些沒有明確答案的謎題,給予讀者多重讀解的機會,使他們尋找存在于文本中的“蛛絲馬跡”,揣度可能的謎底,最終得出多樣的結論。與此同時,個體的生活經驗、特定地域的變遷故事乃至社會歷史的轉折進程等內容,被包含于小說的謎題敘事中,也會隨讀解被讀者強化,凸顯小說中懸置謎題“言不盡意”的特點。
得解謎題與懸置謎題二者并存于徐則臣的小說之中,既以現實謎題的揭示反映生活的不同形態,亦以日常謎題的無解將“人世的榫隙和斷層”以及“可以發現和言說之外的沉默部分”[9](P2)公之于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