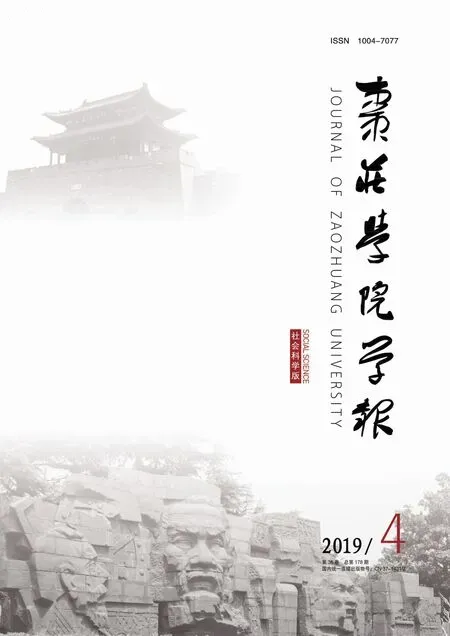葉啟勛的書籍生活和情感世界
胡晨光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875)
論起典籍傳藏,多以江浙為代表;湖南地處偏遠,不常被人推重。傅增湘說:“嘗觀古來言藏書者,咸爭推吳越故家,而楚蜀之地,乃寂寂無聞。”[1](P3)民國年間,以葉德輝為代表的葉氏家族,在湖南藏書界異軍突起。葉啟勛是葉德輝的侄子,家風浸染之下,葉啟勛繼承了葉德輝喜好藏書的品格,著有《拾經樓·書錄》三卷,紀其所藏善本圖書百余部,傅增湘為之作序。在書錄題跋中,葉啟勛不僅關注典籍的文獻價值,考訂書籍的版本、批校、流傳,且記述了許多與時代、家族、書籍生活相關的掌故,使之具有獨到的文化價值。
葉啟勛兄弟三人,兄啟蕃、弟啟發,同好購藏典籍。其弟葉啟發藏書樓號為華鄂堂,藏書志名《華鄂堂讀書小識》,兩家藏書初未分彼此[2](P3)。葉啟勛子葉云奎說:“迫于生計,伯父啟蕃外出求職,以擅長珠算得任會計;叔父啟發擅長國畫,得任教員;父親則得日本《漢學雜志》和南京金陵大學《國學季刊》約稿,而收藏古籍工作未嘗一日稍停。”[3](P493)另據《二葉書錄》,兄弟三人的善本書籍多為葉啟勛購入,則葉啟勛為兄弟三人中收藏典籍的主力。
葉啟勛的諸篇題識寫定之后曾公開發表,1934年《圖書館學季刊》發布《本刊所載〈拾經樓群書題識目錄〉》[4](P420),其中已有題識四十余篇。1937年,葉氏將《拾經樓·書錄》刻印于長沙;1940年時,《拾經樓·書續錄》成書二卷,達二三萬字,李小緣曾許為之分期刊布[5](P135),惜未見下文。啟勛弟啟發說:“己卯三月,定兄取劫余未盡之書編成書錄,更取所作各書之題跋訂為《拾經樓·書后錄》。”[6](P170)可知在1939年時,葉啟勛還曾編訂藏書目錄,亦未見流傳。因此,我們在討論他的書籍生活時,現存的《拾經樓·書錄》是最為主要的材料。
近年以來,隨著學界對湖湘文化的關注,針對葉啟勛的相關研究漸多。姜慶剛、晏選軍等學者發布了葉啟勛同李小緣、商承祚、柳詒徵等學人來往的書信[7][8][9]。張憲榮和楊琦則重點關注了葉氏兄弟所撰《二葉書錄》的特點和價值[10](P86~95)。堯育飛所撰數篇文章揭示了葉啟勛的生平經歷和學術貢獻[11][12][13],且他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傅增湘舊藏《長沙葉定侯家藏書紀略》一書抄錄發布[14](P191~206),為學人研究葉啟勛藏書提供了新材料。以上研究對我們了解葉啟勛其人其事均有重要貢獻。但少有學者關注葉啟勛具體的藏書活動、心態和情感,本文擬以葉啟勛所撰《拾經樓·書錄》為中心,勾稽其書籍生活和情感世界,求教于方家。
一、葉啟勛的典籍購藏
受家族影響,葉啟勛很小的時候即注重購入典籍,他說:“余年才志學,即從廠肆游。”1916年,葉氏17歲,時周鑾詒藏書散出,他與友人秦更年分得之。1930年時,葉啟勛31歲,他寫到:“本抱殘守缺之心,為啟先待后之計,歷十三寒暑,得四萬卷有奇。”[15](P76)再至1937年《拾經樓·書錄》撰成刊刻時,葉啟勛自稱“十數年間,聚書十萬卷有奇”。則僅在1930至1937這七八年間,葉啟勛就購入典籍六萬卷。
(一)購藏方式
有學者總結 “購書之方式也往往因人因時而殊異。然舉其大概,仍有一定之式:以購書對象論,或字書肆、賈客,或自藏家、民間;以購書類型論,或專注新籍,或鐘情舊典,間或新舊兼蓄;以購書方式論,或自買,或代買,或大宗收購,或零星蓄積;以購書所得論,或系刻意尋覓,一朝釋懷,或系不期而遇,喜出望外,如此等等,難以盡舉。”[16](P235~236)據《拾經樓·書錄》所記,葉啟勛購藏典籍有得之書肆、書賈、藏書之家等方式,他鐘情舊典,以自買為主,兼有大宗收購和零星蓄積。
《拾經樓·書錄》記載,長沙的玉泉街舊書肆是葉啟勛經常尋覓圖書之處。他的藏書中,有些書就是從書攤上不經意間得來,如在“冷書攤中”得趙之謙的《從古堂款識學》[15](P70),又在“冷書攤頭購得明成化癸巳先族祖文莊公刻《詠史古樂府》”[15](P138)。
但更多的好書還是直接來自于書賈處。葉啟勛不惜重金、廣搜舊籍的名聲傳揚在外,書賈常持書上門或持書單邀請葉氏往購其書。如明刻本《韓詩外傳》題記載:“三月十日,估人從湘潭舊家獲大批書籍歸,約余往觀。”[15](P17)1935年時,葉氏曾得北宋刊小字本《說文解字》,記得書過程:“乙亥夏五,湘鄉估人持書一單求售,約余往觀。”[15](P17)時代變動,藏書難守,舊藏書家之書,也常為葉氏所得,如于賀長齡后人處得李鼎元手批《水經注》[15](P54),于黃國瑾家得朱彝尊、黃丕烈舊藏明抄本《牡丹百詠集》[14](P202)。
“不期而遇”之外,他特別關注何紹基的舊藏,可謂“刻意尋覓”,在坊肆、書賈處見之,不惜重金購求,何氏后人何詒愷亦趨葉啟勛之門求售。故葉氏所藏善本書中,何氏舊藏甚多。據葉啟發所記,1929年時,兄弟二人購藏何紹基舊藏已超過五千卷:
有清道咸之間,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以書名重海內,而其藏書之富,人多不知,殆以一善掩眾長也……丙寅、丁卯之間,太史曾孫詒愷移寓省垣,染阿芙蓉癖甚深,又沉溺醉鄉,陸續舉其先世所藏者售金以資所費。余兄弟每于估人手見其家藏舊本,必傾囊金購歸。先后所得,以宋槧《宣和圖譜》《韻補》《夢溪筆談》,毛抄《重續千字文》為最,其余元明舊槧、批校稿本不下五千卷也。[15](P76)
何紹基以書法聞名,其藏書罕有人關注。何氏后人移居長沙,嗜好鴉片,不能守書,其書遂輾轉為葉啟勛兄弟所得。當然,葉啟勛購求圖書的方式有可能是諸多方式的綜合,舊藏家之書散落坊肆或為書賈整體購去,再為葉啟勛所得,也是常見的情況。在葉啟勛的典籍購藏活動中,少見請人代購,多為親自購買。
(二)與書賈的博弈
同其他商品的流通一樣,在圖書市場的交易中,買方和賣方也常要經歷一番博弈。葉啟勛在藏書界浸潤多年,自然要同書商常有往來。葉啟勛的筆下的書商多沒有留下姓名,多以“書估”“估人”代稱,其形象或陰險狡黠,或敏而好學,躍然紙上。試舉一例,王鳴韶為王鳴盛之弟,有《鶴谿文稿》手稿。葉啟勛先于袁芳瑛處得此書之一半,而書賈處持有另一半。“書估知余必欲得此以成完璧,始頗居奇,遷延月余,以殘冊無人過問,卒為余有”[15](P154),葉啟勛知曉書估居奇遷延的原因和目的,但不急于入手,最終書估因書為殘本難以售出,不得不售予葉啟勛。更多的情況是每逢珍本,書賈常以葉啟勛之面色定書之價格,“估人之黠者,每以余之面色定價之高下。此書余一見而心怦怦動矣,估人遂堅持原價,不肯減少”[15](P129)。更有狡黠的書賈不知書之價值,僅見葉啟勛來購,便知書非普本,刻意提高價格。葉啟勛對此深有體會,但惜書之情,不忍交臂失之。如購明本《居士集》時,“當時持此書求售,人無知者,余擬以賤價獲之。不欲書估見余欲售,始知為秘帙,居奇昂價。余重其希見,乃以重價收之”[15](P118)。
有經驗的書商多熟悉典籍的版本和價值,以為交易時的憑借。故有時藏家和書賈眼力精疏,在書籍交易時十分重要,稍有不慎,就會處于下風。1916年時,葉啟勛在書賈處見彭文勤手校古香樓抄本《默記》,因書賈不知彭文勤之名,葉氏得以賤值二十金得之[15](P78)。又如因書賈“不知半恕道人為蕘圃別號”,且不識其筆跡,葉氏得以番銀四十餅購得明刊本《巽隱程先生集》[15](P142)。
有時書賈居奇過甚,索價極貴,葉氏不得不采取非常規辦法,仿明人王延喆事,排印流布之以降其價。明嘉靖王延喆刻本《史記》題識記:“憶余庚申歲,有持影宋抄本唐馬總《通歷》求鬻者,聞出縣人袁漱六太守芳暎家中,其先固蘭陵孫星衍淵如觀察舊藏本也,索直極昂,且不肯示人。余頗惡其居奇,乃假歸,集從父兄弟竭一晝夜之力,抄寫其副,急以活字排印二百部,而以原書還之。厥后活字印本坊肆風行,其人知而賤售從兄某,今得之矣。距求售時才月余耳。”[15](P38)當然,此法不甚光明正大,不足為人效仿。
亦有好學的書賈,買賣達成之后仍向葉啟勛求教的。有一柳姓書賈,持一汲古閣刊毛扆校本《春渚紀聞》,二十金售于葉啟勛。成交之后,“柳謂余曰:‘京估某曾見過,以無毛印疑之,今已售汝,曷告我以真假?’”[15](P85)葉啟勛回復說自己曾在涵芬樓見毛扆校本《鮑照集》,以字跡推斷,此本確為毛扆手校。
二、葉啟勛的藏讀習慣
藏書家在長期的書籍生活形成了一定的藏書和讀書習俗,在這之中體現著藏書家的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
(一)重裝典籍
葉啟勛對所藏善本,常進行重裝。一種情況是書籍破損或分割,必須重新裝訂才能方便閱讀和保存。許多殘缺之卷在經葉啟勛之搜訪和重裝之后,得以破鏡重圓。如宋刊明印本《臨川先生文集》,“此書紙背間多朱墨字跡,蓋其時用公牘廢紙所印。原書裝二十冊,以嘉靖極薄綿紙襯訂,余因其破口蟲傷重裝,將原襯紙撤去。惜紙背字跡因重裝不能辨認,并識之以諗后之讀是書者。”[15](P85)再如王鳴盛之弟王鳴韶的《鶴谿文集》手稿,1916年時,葉啟勛先于袁芳瑛家得其半,三年后,再于書賈處得另一半,“因為編次,重加裝訂”[15](P154)。葉氏重裝修補之舉,不僅保證了典籍的價值,也延續了典籍的生命,其《鶴谿文集》一書至今仍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
還有一種情況是善本需重裝之以示珍貴。如宋刊宋印本《韻補》(是書湖南圖書館鑒定為元刻本,可備一說),葉啟勛“以番餅百元得之,手自裝池,以為吾家鎮庫之寶。”[15](P31)翁方綱手校舊抄本《瀛涯勝覽》,葉啟勛“特重加裝飾,以待來者,知所寶重焉”[15](P56)。
(二)節日讀書并作題記
據《拾經樓·書錄》所載,葉啟勛常在特殊節時取書閱讀并作題記。以他書籍生活中相對安定的1926和1927兩年為例:
1926年,正月人日,讀明刻本《鐔金文集》并跋之[15](P144),中秋,讀趙之謙手稿本《從古堂款識學》并跋之[15](P70);重九日,讀《昌谷集》并跋之[15](P111);臘八日,讀《杜樊川集》并跋之[15](P110)。
1927年元旦,讀汲古閣影宋精抄本《重續千字文》[15](P34);正月人日,讀《后山詩注》并跋之[15](P122);元宵節,讀翁方綱、何紹基批校本《寶真齋法書贊》并跋之[15](P78);中秋節,讀明刻本《寇忠愍公詩集》并跋之[15](P133);臘八節,讀明抄本《猗覺寮雜記》并跋之[15](P79)。
以上所舉均是重要的傳統節日,葉啟勛在歡慶時節并不像多數年青人一般陷入歡娛,而是取閱藏書并作題跋,可見他對典籍和文化的癡迷和追求。除了在節日之外,生辰之時,葉啟勛也常聚友朋,同集家中,賞鑒藏書。1929年,葉啟勛自道州何氏得翁方綱、丁杰、錢馥校本《寶刻叢編》,生辰之日“友人聚集同觀,午后泚筆記之”[15](P64)。1931年生辰日,葉氏宴集好友“雷丈民蘇、許丈季純、徐子紹周”[15](P27),于拾經樓西簃,同觀張穆、何紹基批校之王筠《說文釋例》稿本。
此外,葉啟勛還有邀請名士共同鑒賞藏書的習慣,葉運奎說:“座上客有雷氏三兄弟和徐氏兩兄弟等……一月數聚或連聚數日,習以為常,始終不懈。”[3](P491)
三、葉啟勛的藏書心態
周少川先生曾總結私家藏書心態的類型有文化認同的心理、以讀書為樂的意識、“遺金滿籝,不如一經”的心態、藏書私密、祈求永保的心態、藏書公開的心態等數種[17](P134~146)。葉啟勛以讀書、藏書為樂,購書不惜重金,守書時輕易不外借,可見他愛書、惜書和藏書私密的心態。
(一)以讀書、藏書為樂
以藏書、讀書為樂的心態,使葉氏擁讀藏書便不知外界之苦,“時嚴寒大雪,呵凍書之,不覺其苦也”[15](P120)。再如讀《谷山筆麈》,他記:“嚴寒大雪,圍爐書此,時憂禍頻仍,幾忘其為遁世之民,書能養性,固如是耶?”[15](P90)他在《拾經樓·書錄序》中說:“唯余而立之年,半以書相依如命,流離顛沛,伴侶皆書,嗜之篤,緣之慳。”[15](P5)顛沛流離之中,葉啟勛以書籍為伴侶,以摩挲賞玩藏書為生平快事。
在時代變動使得“日以讀書為樂”都成為奢望時,葉啟勛對此表示出無比的遺憾。1933年時,葉啟勛得趙啟霖手批陳奐《毛詩傳疏》。他翻閱其書,見“《疏》中考證改正處頗多,校字離句甚為精博,想見前輩好學之勤劬,讀經之審慎”,故感慨到:“方今經學沉晦,禮教綱常且潰決不可收拾,且兵戈水火又一再相乘,求如曩時二三老儒不聞禍亂,日以讀書為樂者,殆如鈞天之夢,不可期遇矣。展讀斯篇,不禁為之掩卷三嘆已也。”[15](P19~20)時易勢移,舊學典籍承載的傳統學問已經不再為追求新潮的士人所沉迷。葉氏在新學崛起的年代抱殘守缺,以讀書藏書為樂,頗有乾嘉諸老之風。
(二)惜書甚于惜金
葉啟勛購書多不惜重金,如葉啟發見有人持宋刊本《宣和書譜》求售,索值三百金,馳書上海請示葉啟勛,葉啟勛“亟復書如值償之,然未信其真為宋刊,第以歷來收藏家志目罕見記載,雖重值勿惜也”[15](P72)。葉啟勛竟肯在未信其書真為宋版的情況下,豪擲三百金,可見其惜書甚于惜金。又如曾經方功惠、李希圣收藏的明刊本《古廉李先生詩集》一書,葉氏記其入藏過程:“先是,有人持此書至書坊求售,坊賈中固無一陶蘊輝、錢聽默之流能識古書者,因其蟲蝕過甚,群鄙夷置之。持書者為湘鄉人,初至會城,不識途徑,僅聞人言有葉某者,好書有癖,致奇書不惜重價。偶從坊間相值,遂導余至其寓所,且言坊賈之無識,并出此書。告余為其先祖亦元先生舊藏,前有亦元先生手跋,因欲留為世守,而迫于生計,故僅留手跡而去其書。其先則得之巴陵方氏者,與曩時世父考功君所言一一吻合。余亟以番餅百元易之。”[15](P144)葉德輝曾告知方功惠、李希圣藏書的淵源,故當李希圣后人持書來售時,葉啟勛亟購之,且其所記“初至會城,不識途徑”一語頗為得意,似稱自己才是城內有見識、有資格購進此善本之人。同時該題記也點出了在當時的書籍貿易圈中,葉啟勛“好書有癖,致奇書不惜重價”的形象已經被廣泛認可、流傳。
另一方面,葉啟勛常在書錄題跋中記載得書的價格以彰顯自己的惜書之情。1926年,葉啟勛得汲古閣影宋精抄本《重續千字文》,記得書之事:“去歲臘八,余從估人手見之,堅索白金二百,遷延月余,乃以五十餅金得之。當毛斧季售書潘稼堂太史時,其《秘本書目》記云‘精抄之書,每本有費四兩之外者,今不敢多開’。所謂‘裁衣不值緞子價’也,在當年抄時豈料有今日哉?事逾數百寒暑,今日之價已數倍之,又豈毛氏所能料及哉?”[15](P34)。1927年,以50餅金得明汲古閣影元抄本《文則》一冊,并說:“今此書毛《目》所估抄價只八錢耳,余乃以五十餅金易之,數十倍于毛氏估價。”[15](P163)葉啟勛以自己購書的花費同毛氏《秘本書目》所載相比,襯托得書價格之高,其意在彰顯自己購書不惜重金,表明自己對書籍的熱愛。
(三)藏書私密
時局動蕩,經歷坎坷,葉啟勛知書籍傳藏不易,故嗜書之情更篤,雖“自詡達觀”,但藏書私密的心態使其輕易不肯外借、出讓其藏書。葉啟勛獲得北宋本《說文解字》后,時“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邵元沖夫人張默君,由省政府派人陪同來看此書”,葉啟勛以“是否宋本尚不能定告之”[3](P492),拒絕了觀書之請。1940年時,金陵大學的圖書館學家李小緣曾致信打探:“長沙告捷以后,日趨穩定,我兄府上藏書幸早下鄉,不知近狀若何,現移何處,儲藏如愿轉讓,弟甚愿效微勞,是否有意及之乎?”[5](P134)李小緣有意代收其所藏,葉啟勛亦未許之。面對各方的壓力,葉啟勛輕易不肯外借、出讓其藏書,體現了他私密藏書的心態。
在葉氏的書籍交游中,他的做法也偏向謹慎。《拾經樓·書錄》中出現最多的葉氏書友是秦更年,以秦更年為例,可見葉啟勛嗜書之深。1916年周鑾詒散出之書中,有明趙氏仿宋本《玉臺新詠》,為葉啟勛所得。秦更年堅請相讓,葉啟勛“固未之允”。1927年春,葉德輝過世,葉啟勛前往上海避亂,秦更年“復申前議”,葉氏“未忍卻篋”。1930年,葉啟勛徙家至上海,秦更年“仍未能忘情此書,知余攜之行笥,強讓未可,割愛不能,遂請假觀數日”[15](P156)。至于不肯借書的緣由,葉啟勛自述到:“世父死丁卯春月之難,藏書散失幾盡,從兄某則因家計,將所得斥賣罄盡,惟余此部,得保守于喪亂之余”[15](P156)。故珍密之書,不肯出讓外借。
再以《廣川書跋》一書為例,友人藏文征明抄本《廣川書跋》,葉啟勛“擬乞得之”,以補藏書之闕,結果“友人靳未許也”[15](P75)。從友人的反應中或許可以推見葉啟勛平時的做法。葉啟勛后得秦氏雁里草堂抄本《廣川書跋》,李盛鐸之子李家滂來訪,“見而贊賞,堅請相讓”,葉啟勛亦“靳未之許,卒至面赤而去,遂秘之篋笥,不敢示人”[15](P76)。秦更年亦兩次來借校此書,葉啟勛均未出借,僅囑葉啟發以一刊本臨校之贈予秦更年。
當然,這并不是意味著葉氏與諸藏友之間斷絕書籍往來,如葉啟勛曾“從友人秦曼青許見黃復翁手校元本《詩外傳》。適行篋中攜有此本,因假歸以綠筆臨錄一通,并影摹諸家校藏印記及題跋,附訂于首”[15](P19),即葉氏與秦更年亦互有借鈔借校之舉。他在題識中多處記載自己不肯外借、出讓典籍,源自于動亂時代保藏圖書的不易,其意在彰顯書之珍貴以及自己的惜書之情。其后人見之,更應寶重其書。
四、葉啟勛的情感寄寓
私家藏書具有自覺自愿的特點,透過藏書家們艱苦卓絕的不懈努力,可以挖掘出他們的文化心態和情感寄寓。在葉啟勛孜孜不倦地購求、守護、傳承典籍的背后,寄托著對伯父葉德輝的懷念,對家學傳承的堅守,也垂訓著葉氏后人。
(一)追憶世父
葉德輝曾在蘇州寄詩“阿十持本日對讎,抱經思適能同擅”[18](P238)稱許葉啟勛、葉啟發兄弟。葉氏兄弟能在湖南藏書界產生影響,與早年間葉德輝的指點不無關系。葉啟發說:“仲兄定侯及余方在髫齡,即侍硯側。先世父時即以各書版刻之原委、校勘之異同相指示。余兄弟習聞訓言,漸知購藏典籍。”[6](P169)
葉啟勛能夠接觸學界名流如張元濟、傅增湘,得以拓寬眼界,也多借葉德輝之力。在1921年時,葉啟勛前往上海,獲觀涵芬樓藏書,“辛酉夏,余道過滬上,時大伯父由蘇適來,因率余往觀涵芬樓藏書,中有舊抄《鹿皮子集》,假之取讀”[15](P133)。即便是在葉德輝過世之后,葉啟勛避亂上海期間,也獲觀書涵芬樓,即“夏初,余避亂滬上,從海鹽張菊生年伯元濟許假觀涵芬樓藏書”[15](P115)。1934年時,傅增湘南游衡山,道經長沙,葉啟勛執年家子禮相見。返程時,傅氏往觀葉氏兄弟藏書并選定十余部珍貴典籍,由葉啟勛撰成題識寄給他,即傅氏所藏《長沙葉定侯家藏書紀略》。傅增湘還在葉啟勛《拾經樓·書錄》書成后為他作序,序中頗多贊許之詞。
作為其后人,葉啟勛常常在題跋中流露出對世父的懷念。《李文公集》題記中說:“回憶平時每得一書,必經世父鑒定跋尾,今世父殉道,不能起而請益,并以知莫氏之誤,書此能不凄然乎?”[15](P109)再如葉德輝擬刻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自莫棠和傅增湘處各得一種,囑葉啟勛校訂之。葉啟勛記:“丁卯春正,余禮廬抱痛,閉戶勘書,先世父遂以二書俾余,囑為校記,擬付手民。未及其半而湘亂作,先世父殉道,余遁寓海濱。既痛哲人之云亡,復悲先澤之或泯,江天在望,徒喚奈何。”[15](P88)字里行間,表現出對葉德輝的追憶。葉啟勛、葉啟發在題跋中反復言及葉德輝的指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人傳承葉德輝學術的欲望和標榜。
葉德輝在世時,葉啟勛曾參與校刻《書林清話》。葉啟勛的《四庫全書目錄版本考》一書即是在葉德輝的指示下創作。葉啟發說,葉德輝過世后,“余兄弟避亂申江,攜大伯父手稿于行笥中,故交門友見者,無不慫恿付之梓民。”[19](P759)另外,據姜慶剛發布的葉啟勛和李小緣的往來書信,葉啟勛處還藏有葉德輝的未刊稿數種,并“擬為先伯編訂年譜”。可見葉啟勛在表彰葉德輝的學問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
(二)傳承家學
長沙葉氏自敘是葉清臣、葉夢得、葉盛等人的后人。在書錄題跋中,葉啟勛有意將自己書寫為葉氏家學的傳承人,在為葉德輝校刻《郋園讀書志》后,他在《郋園讀書志跋》[19](P757)中追述了家學淵源,將先人藏書治學的傳統、葉德輝的教誨和自己的藏書喜好接續書之,同劉肇隅、葉啟崟、葉啟發等人的《郋園讀書志》序跋相比,葉啟勛所作跋文頗有追溯自身學術淵源、傳承家族學問的意味。
在典籍購藏方面,很多藏書家對家族前輩、鄉邦先賢的書籍都相當看重,以之為學術傳承的途徑和代表。葉德輝即有意收藏葉氏先賢之書并校刻之。葉啟勛時,家族遭逢巨變,時代動亂,他更重視先世遺書,以示不忘所自。葉啟勛曾刻意搜求原觀古堂舊藏和觀古堂所無之書。每得觀古堂藏書,追憶舊事,感慨良多。1933年得觀古堂舊藏明影宋抄本葉氏先祖葉夢得的《建康集》,葉啟勛記:
此則藏之觀古堂中,為子孫青箱世守之業。丁卯三月,先世父被難,典籍散亡。此書余從冷書攤頭購歸,亦似冥冥中有默加呵護者。楚弓三篋,亡來已久,一旦頓還舊觀,展卷相對,如見故人。特世父云亡,寒暑屢易,追懷疇昔,感痛系之。惟先世父得此書于庚子冬至后一日,是年五月為余生辰。綜此三十四年間,余家變故相乘,余雖屢經憂患而酷好典籍,相依如命。此書幾經展轉,別六載而仍歸于余,抑天公欲破余之癖,故予而故靳也耶?抑長恩有靈,祖先之眷戀余小子也耶?[15](P127)
1900年即葉啟勛出生之年,葉德輝購入此書,并從盛宣懷藏抄本補全,后匯刻入《石林遺書》。1927年時,該書隨著葉氏家族變動而流散。1933年,葉啟勛自書攤尋得此書,展卷閱讀,感慨良多,甚至有“長恩有靈”“祖先眷顧”之句。在《拾經樓·書錄》完成后,葉氏序中記“非敢問世,以示楹書之世守耳”,足見葉啟勛傳承祖先遺書和家族學問的堅守。
(三)垂訓后人
藏書家常在書志題跋中垂訓后人,訓誡他們珍惜祖宗藏書、好學勤勉,以求學問綿延、家族興盛。葉啟勛在明抄本《東坡先生志林》題記中記:“辛未七月,文安后人詒愷持來此書,索值至百元。彼固不知書,第以先人所遺,故要高價耳。取閱向書之有少河手跋者,乃知此書無名氏題字亦少河手跡,固即目中所載之書也,亟償值藏之。蓋自也是翁后,又遞經大興朱氏椒花吟舫、道州何氏東洲草堂珍藏矣。兩家皆無印記,特志其顛末,以示子孫,知所寶重焉。”[15](P84)何紹基家族衰落,其孫持書求售,但并不確知其書淵源。葉啟勛梳理是書的流傳故實,垂訓其子孫寶重其書,頗有引以為戒的意味。圖書的收聚和傳承殊為不易,書籍不僅為后人治學求仕提供了支撐,先輩們保藏圖書的行為就是極好的家庭教育素材。葉氏先祖葉盛就注重蓄書之舉的氣度和德行,他得知藏書故家長洲虞氏家道中落,不僅不強取其書,而且舉薦虞氏后人為官,傳為佳話。葉啟勛在題跋中也多次表露出對良好家風的重視。1926年冬,葉啟勛得藏書家王時敏的手稿本《王西廬家書》一卷。王時敏在家書中常論及季振宜和錢曾的“峭刻詭譎”。葉啟勛對比王時敏和季、錢二人的身后遭遇,感慨“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強調家族教育和家風的重要。他說:
遵王為牧齋族子,生平受其提攜,得附士林。后乘牧齋之喪,率族人爭產,逼河東夫人縊死,其人狗彘不若,乃知西廬有先見之明……書中敘述家常,宅心仁厚,其于親故貧窘之際,猶時時眷戀于懷,如聞當時父子絮語。其教戒諸子有“為善乃受實用”,勖勉諸兒“事事務存寬厚,念念勿蒙邪曲,培養元氣,少答天意”諸語,尤見其居心慈善,不墜家風,宜乎子孫科第蟬聯,及身享高壽大名,晚景無不如愿。彼季滄葦、錢遵王諸人雖事事經營,惟恐失利,而身后書籍、字畫,轉瞬化為煙云,子孫繼起無達人,生前遺行,至今為人指斥。亦可見余慶余殃,其理信不爽也。[15](P153)
葉氏對王時敏寄語兒輩的教戒勖勉深以為然,但令人唏噓的是,數月之后,葉德輝被殺、藏書星散。經歷了家族變故、顛沛流離的葉啟勛,更知圖書保藏不易,1927年8月,他在明成化刊本《李文公集》題記中告誡子孫:“鄉邦遺澤,由吳而湘,由湘而吳,楚弓楚得,吾子孫其永寶之。”[15](P109)
葉啟勛在書錄中,多有言及葉德輝之子葉啟倬處。在葉盛手校明聞人詮本《舊唐書》書錄中,葉啟勛記:
此書出郡故藏書家,索值頗昂。從兄某知其為先人手澤,而又不惜財物,不欲致之。及歸余插架,又欲乾沒以去。余于從兄弟輩為最小,遂不敢爭,亦不愿爭也,卒為所奪。未幾,從兄某豪于摴蒱之戲,盡散其藏書,余仍從估人手得之。嘗考歸安陸運使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沈下賢集》葉石君跋”崇禎戊寅得沈亞之集,為林宗乾沒,近來林宗物故,書籍星散,宋元刻本盡廢于狂童敗婦之手。予生平不欺其心,自信書籍必不若林宗死后之慘”云。案林宗公以后娶妻,故致二子失愛以憂死,士論少之。而從兄某以腰纏萬貫,吝不資先世父以行,致死丁卯之難,為清流所不齒,卒之及身而書籍星散,且負債累累。然則欺心之人,天理報施,固未嘗或爽,其然豈其然乎?因跋是史,以垂訓云。[15](P44~45)
葉啟勛在題跋中多處表示葉德輝之子葉啟倬沉迷賭博、售賣藏書、吝惜財物、學問粗疏,不能繼承先世遺志,此處更暗指葉德輝“死丁卯之難”是因葉啟倬不愿出資供葉德輝前往日本。葉啟勛引用祖先葉盛的跋文,借對從兄的控訴,垂訓其子孫為人端正、不可欺心。葉啟勛筆下,葉德輝之子的形象可以用“吝惜財物、不學無術”來概括,因此有學者認為,“雖葉德輝生前極為自負,嘗稱‘湘中一省人物,不及輝之一家’,葉德輝三子,長子葉杞早夭,次子啟倬、三子啟慕,皆不賢肖,而能繼其家學者,實為其弟葉德炯之子葉啟勛、葉啟發二人而已。”[20](P372)
五、余論
20世紀30年代后期,長沙時局動蕩,葉啟勛的藏書活動受到了極大影響。1939年長沙大火和1944年日軍占領長沙給拾經樓藏書造成極大損失。葉啟發云:“中日戰起,東北淪亡,繼而蘇、皖、鄂、贛先后喪失,長沙日有鋒鏑之警,舟車阻塞,避地無方,余兄弟未得盡舉藏書移至鄉野。迄至十月,湘垣大火,拾經樓、華鄂堂均成灰燼,典籍之未攜出者,同罹浩劫。”[6](P170)1940年時,葉啟勛致書商承祚,提及“倭寇肆虐,長沙首被火焚,家藏典冊一部分遂罹劫灰,手卷諸稿同為余燼”。另據葉運奎述,日軍占領長沙期間,曾派人四處搜尋葉啟勛的蹤跡;長沙光復以后,又有人趁機挑釁,想要占有其書。葉啟勛將書籍用皮箱裝好,藏于草藥鋪。“長沙解放以后,父親深感購書難,收藏難,保全更難,像此類珍貴書籍,不宜私家收藏,經全家商定于1951年全部捐獻國家,現存湖南圖書館。”[3](P493)《長沙市志》載:“1951年,其子葉闿運代表父親將拾經樓珍善本書100余種,3000多冊,2.3萬余卷,悉數捐贈給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現絕大部分珍藏于湖南省圖書館善本書庫”[21](P578),其中不乏宋元珍本、稿抄批校本。據湖南圖書館的尋霖介紹,葉啟勛、葉啟發兄弟藏書全帙捐藏于湖南圖書館,至今為其鎮館之寶[22](P138~144)。
要指出的是,葉啟勛并非只知賞鑒、不求治學的“賞鑒派”藏書家。他曾參與編寫《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工作,據統計,“撰寫提要359篇,其中經部110篇”[23](P344)。他還創作有《說文系傳引經考證》《說文重文小篆考》《釋家字義》《通志堂經解目錄考證》《四庫全書目錄版本考》等學術作品,部分刊載于《金陵學報》《圖書館學季刊》等刊物。在時局動蕩不安,學術風氣轉向的情況下,葉氏恪守以目錄版本學、小學為主的家學,保存典籍,為文化傳承貢獻了力量。很多葉啟勛式的末代藏書家,在動亂的戰爭年代,不惜一切購求、保存、傳承珍貴典籍,又將之捐獻公藏,使其至今能為人利用。他們雖然沒有親赴戰場,但在文化領域,他們保藏典籍、傳承學術的努力同樣值得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