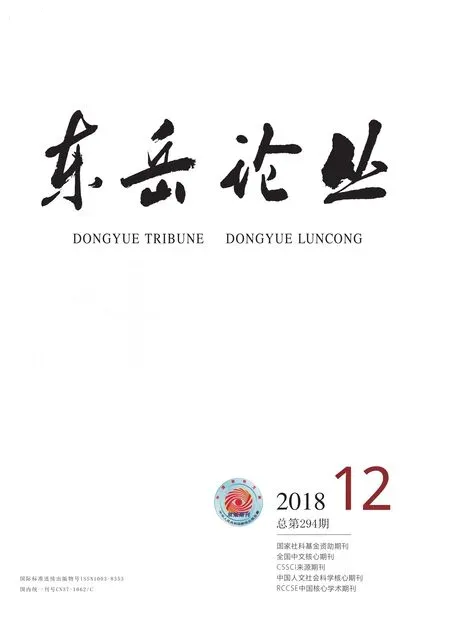近代“天下大同”重塑的經學路徑
2019-01-05 02:34:52刁春輝
東岳論叢
2018年12期
關鍵詞:孔子
刁春輝
(山東大學 儒學高等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100)
錢穆先生在評述周秦時代時說:“在當時中國人眼光里,中國即是整個的世界,即是整個的天下,中國人便等于這世界中整個的人類。[注]《錢賓四先生全集·中國文化史導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7頁。也就是說,依周秦時人們的地理認知,四夷與諸夏即構成了整個天下,也即整個世界,周時是一封建列國的天下,而秦時則是一郡縣的天下。天下始終是以中國為中心向四圍延展的圖景。這種認知即使在后來人們對于地理范圍的認知不斷擴大,擴及西亞、歐洲、非洲,以至于到晚明,從《坤輿萬國全圖》來看,中國人對世界地理已經開始有了初步認知,但這些地理認識并沒有對中國的天下秩序構成沖擊——一方面是因為沒有直接形成亡國風險,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此秩序背后的文化價值支撐沒有被懷疑否定過,中國始終是禮義文明的代表。
不過近代以后,特別是甲午后,保國保種保教成為迫切的任務,中國人所認可的天下秩序從現實上和觀念中都崩塌了。作為天下觀直接學術支撐的經學,也面臨著調整自身理論的需要,若不能有效應對,則中國的存在在制度上與文化上都會陷入危險之中。
通觀近代,針對天下的大同觀,從經學上試圖解決此問題的也大致可分三路徑,此處分別以廖平、康有為和沈艾孫為代表。廖平以禮學,康有為以公羊學為代表的《春秋》學,沈艾孫主要以四書為闡述路徑。……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學生天地(B版)(2022年9期)2022-11-01 03:29:40
中國漫畫(2022年3期)2022-04-19 12:59:10
家教世界·創新閱讀(2021年6期)2021-08-23 06:58:17
家教世界·創新閱讀(2021年5期)2021-06-24 14:09:11
家教世界(2021年16期)2021-06-21 08:45:56
快樂語文(2021年9期)2021-05-06 02:19:38
學生天地(2020年18期)2020-08-25 09:29:34
小學生優秀作文(趣味閱讀)(2017年5期)2017-04-14 08:46:15
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1期)2014-11-23 10:20:44
現代語文(教學研究)(2014年10期)2014-09-25 11: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