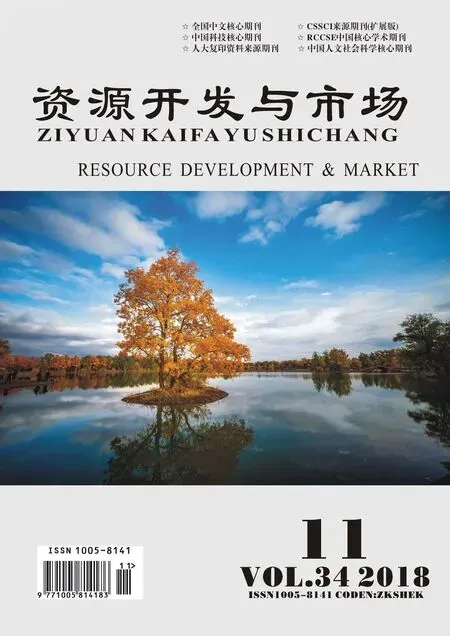遺產旅游地居民環境行為、環境后果對生活質量感知的影響
(湖南師范大學 旅游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生態環境是遺產地旅游業永續發展的重要基礎,有效保護生態環境、實現遺產旅游地可持續發展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難題。社區居民作為重要的利益相關者,是遺產旅游地生態環境的直接和長期受眾群體,他們的環境態度和行為對旅游地生態環境的保護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旅游產業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當地居民生活質量、維持旅游地生態環境的可持續。因此,尋求實現旅游業可持續發展和提高遺產旅游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平衡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界對環境行為和居民生活質量關系的研究成果逐漸豐富。國外學者既探討了居民滿意度對其環境行為的顯著影響[1,2],又反向分析了環境行為對居民滿意度的影響[3]。如Heinz等利用理性選擇模型證實生活滿意度對環境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2];Marta等以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納達城市為例,研究發現居民環境行為和環境意識對他們的主觀幸福感產生積極的正向影響或沒有顯著影響,但不存在負面影響[4]。國內學者對兩者關系的研究側重于將主觀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作為一個心理因素來探討對居民環境行為產生的影響[5]。如楊奎臣等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3)”數據,分析了社會公平感、主觀幸福感對居民環境行為的影響機制,結果顯示居民主觀幸福感對私域的親環境行為產生正向影響,而對公域的親環境行為有顯著的負向作用[6]。綜上所述,國內學者雖然開始關注環境行為與生活質量之間的關系,但研究深度有待深化、研究角度也有待拓展,基于旅游目的地居民視角的研究仍鮮見。本文以遺產旅游地武陵源的居民為樣本,探究他們的環境行為與生活質量的內在關系。同時,引入居民環境后果感知變量,深入分析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以期為提高旅游目的地居民生活質量和維持目的地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參考。
1 研究設計
1.1 案例地概況
武陵源風景名勝區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包括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天子山、楊家界等景區。1992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是我國首批世界自然遺產、國家5A級景區和世界地質公園。景區內約有340戶居民,共968人;景區周邊約有2361戶,共7151人。武陵源風景區在發展旅游業的過程中一度面臨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困局,199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亮出“黃牌”警告,因此保護生態環境迫在眉睫。為加強景區生態環境的綜合治理,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當地政府實施了生態移民搬遷、拆遷保護等工程。同時,政府提出要將移民搬遷、景區質量提升等與人民的幸福生活有機結合,全面提升居民幸福感與滿足感。
1.2 問卷設計
本研究在檢索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擬定了居民環境行為、環境后果感知和生活質量感知量表,綜合咨詢專家意見和實地預調研對問卷的題項進行了篩選和調整,最終確定了包含居民基本信息在內的33個題項。問卷第一部分為遺產旅游地居民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4個題項。第二部分為居民環境行為量表,根據孫巖、Schmit等[7,8]的研究共歸納了20個題項,并劃分為生態管理行為(B1—B9)、消費行為(B10—B14)、公民行為(B15—B18)和說服行為(B19—B20)4個層次。部分題項根據武陵源的實際情況進行調研,其中“捐款幫助當地保護環境或為當地的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做過貢獻”題項的測量依據為居民參與的天子山環境整治(籌資、志愿進行花草苗木綠化和“全民清潔日”活動)、“志愿者撿拾小街小巷垃圾活動”、“我要環保”公益活動、“守望青山碧水”環保公益活動、“綠色出行”環保活動等;題項“關注政府的環境政策和措施”、“主動關注媒體報道中的環境問題或環保信息”的測量依據為居民閱讀或咨詢《環保法》等環境法規政策的宣傳資料、武陵源區環境質量公報,觀看環保公益廣告、宣傳牌、環境監測演示活動等。題項均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形式,1—5分別表示“從未做到”、“偶爾做到”、“約半做到”、“大多做到”和“每次做到”。第三部分為居民環境后果感知量表,借鑒王凱、張玉玲等[9,10]的研究成果,共設計了8個題項,劃分為自然環境后果感知(C1—C5)和人文環境后果感知(C6—C8)2個層次;所用題項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形式,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第四部分為居民生活質量感知量表,以主觀生活質量感知“滿意度”來測量,題項設置為“您目前對您的生活總體滿意程度”;題項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形式,1代表“非常不滿意”,5代表“非常滿意”。2018年3月12—31日開展正式調研,分別選取武陵源袁家界、天子山和高云3個地區的居民進行抽樣調查。共發放問卷450份,回收359份,有效問卷325份,整體有效率90.5%。
1.3 研究假設
環境行為與生活質量感知間存在相互影響的循環機制。環境行為屬于親社會行為的一種,親社會行為能增強人們的生活滿意度[11],而生活滿意度的提升又可促進居民實施更多的環境行為[12]。Schmitt等研究證實居民環境行為能對生活滿意度產生積極的影響[8];張玉玲、王凱等研究發現,居民環境后果感知對環境行為具有正向的影響[9,10]。隨著環境污染等問題的加重,居民主觀生活質量的滿意度也會隨之降低。鄭君君等發現主觀感知的環境污染程度會對居民的生活滿意度產生負面影響[13]。借鑒以上文獻,主要提出以下假設:H1——環境行為正向影響旅游地居民生活質量感知;H2——環境后果感知負向影響旅游地居民生活質量感知;H3——環境行為能緩解環境后果感知對旅游地居民生活質量感知產生的消極影響。
環境行為屬于親社會行為的范疇,親社會行為的某些特征可延伸到環境行為。研究表明,成本性越高的親社會行為產生的滿意度或幸福感更強烈[14],而居民環境行為的實施需要付出不同程度的成本(如時間、金錢或精力等)。其次,不同環境行為的可觀察性程度不同。如洗刷過程中關閉水龍頭是相對私密的,不易被他人觀察到;而參加當地的環保活動則公開性較強,容易被他人觀察到。研究發現,觀察性越強的親社會行為能通過提高自身的聲譽,更有效地促進滿意度或幸福感[15]。此外,環境行為的社會互動性也不盡相同。社會關系是人類生存必須具備的,但有的環境行為的社會互動性不強,不太可能增加社會聯系(如電器不使用時關閉);其他某些環境行為則具有較強的社會聯系(如主動和他人探討環境問題)。Csikszentmihalyi等研究表明,與他人進行社會交往時所獲得的滿意度或幸福感要比獨處或獨立工作高[16]。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假設:H4——環境行為的成本性越高對旅游地居民生活質量感知的正向影響越強烈;H5——環境行為的可觀察性越高對旅游地居民生活質量感知的正向影響越強烈;H6——環境行為的社會互動性越強對旅游地居民生活質量感知的正向影響越強烈。
2 結果與分析
2.1 樣本描述
樣本人口統計學特征:本次調研中人口統計學特征分別包含性別、年齡、月收入和文化程度4個方面(表1)。其中,受訪居民中男女比例相當;年齡主要集中在21—40歲和41—60歲兩個階段,共占81.9%;人均月收入≥3001元的占比最大,為41.3%;學歷以初中、高中(含中專)為主。

表1 樣本的人口統計學特征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通過計算各變量的均值得出,4類環境行為的均值依次為生態管理行為(3.49)>消費行為(3.42)>說服行為(2.93)>公民行為(2.84)。表明旅游地居民最常做的環境行為類型是生態管理行為,其次是消費行為和說服行為,公民行為實施得最少。其中,生態管理行為、消費行為超過了中間值3(“約半做到”),實施頻次相對較好,而說服行為和公民行為的實施頻次不高。在環境后果感知中,人文環境后果感知的均值(4.04)大于自然環境后果感知的均值(3.77),兩者均超過了中間值,說明武陵源居民對環境的感知較為敏感,且對人文環境變化的感知更加強烈。武陵源居民的生活質量感知均值為3.18,處于基本滿意的中間狀態。
2.2 信度、效度檢驗及驗證性因子分析
問卷總體信度的Cronbach′α系數檢驗值為0.894,居民環境行為和環境后果感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檢驗值分別為0.931和0.943,表明問卷的內在信度較理想。由表2可知,所有題項的因子載荷值均大于0.5,且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P<0.001),說明各題項對潛變量有較強的解釋力度,即問卷有較好的效度;組合信度在0.712—0.936之間,均大于0.7,表明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良好;平均方差提取值均大于0.5,各潛變量具有較好的聚合效度。

表2 驗證性因子分析
注:***表示顯著性水平為P<0.001。
2.3 假設檢驗
環境行為、環境后果感知與生活質量感知分析: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對居民環境行為、環境后果感知和生活質量感知的關系進行分析。為檢驗假設H1、H2和H3,設置了3個模型。模型一和模型二分別以4類環境行為和2類環境后果感知作為自變量,以生活質量感知作為因變量;模型三則將環境行為和環境后果感知同時作為自變量,生活質量感知作為因變量。由表3可知,在模型一中居民生態管理行為、消費行為、公民行為和說服行為均正向影響生活質量感知,且除說服行為外,均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P<0.05),表明遺產旅游地居民實施環境行為能提高其生活質量感知,增強生活滿意度,其影響程度依次為生態管理行為>消費行為>公民行為>說服行為。調研發現,武陵源景區居民實施環境行為能提高其生活滿意度的外在驅動力之一是政府等管理部門的惠民政策,如景區內居民出行均可免費乘坐景區公共環保車等。模型二中,居民自然環境后果感知和人文環境后果感知均顯著負向影響生活質量感知,表明遺產旅游地居民的環境后果感知會抑制生活滿意度的提升,人文環境后果感知的抑制作用略強于自然環境。當居民環境行為和環境后果感知同時作為生活質量感知的影響因子(模型三)時,結果表明環境行為仍然正向影響生活質量感知,而環境后果感知仍負向抑制生活質量感知,兩者均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通過對比3個模型發現,居民環境行為和環境后果感知同時存在時對生活質量感知產生的影響比兩者單獨對其產生的影響稍強。上述研究結論證明,假設H1和H2成立。

表3 模型回歸結果
注:**表示P<0.01;*表示P<0.05。
為了檢驗假設H3——環境行為能緩解環境后果感知對旅游地居民生活質量感知產生的消極影響。本研究首先檢驗了居民的環境后果感知對其環境行為的影響,建立以環境后果感知和環境行為為自變量和因變量的回歸模型,結果顯示,居民的環境后果感知顯著正向影響其環境行為(系數為0.201—0.314,P<0.05)。結合表3研究結果,居民環境后果感知與環境行為呈正相關,與生活質量感知呈負相關;而居民環境行為與生活質量感知呈正相關。因此,檢驗居民實施環境行為能否作為中介緩解環境后果感知對生活質量感知的消極影響。借鑒Hayes等[17,18]檢驗中介效應的Bootstrap方法對其進行驗證,結果顯示,中介效應在95%的置信區間上顯著,環境后果感知經過環境行為到生活質量感知的中介效應分別為-0.117和-0.121(95%CI=[0.0476,0.0825],95%CI=[0.0563,0.0795],P<0.001)。由此可知,旅游地居民主動實施環境行為能緩解環境后果感知對生活質量感知產生的消極影響,假設H3成立。
環境行為成本性、可觀察性及社會互動性分析:為進一步分析居民的不同環境行為對生活質量感知的影響程度,將調查問卷中的20項居民環境行為與生活質量感知逐一進行回歸。建立與模型三相類似的回歸模型,自變量為單項環境行為和環境后果感知,因變量為生活質量感知,回歸結果見表4。從表4中可知,除B6(垃圾分類投放)環境行為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外,其余19項居民環境行為均對生活質量感知產生正向的積極影響,其影響程度各不相同,系數值在0.009—0.193之間。

表4 回歸系數及標準化結果
注:**表示P<0.01;*表示P<0.05。
假設這種不同的影響程度不是隨機出現,而是與環境行為的成本性、可觀察性和社會互動性相關聯(即假設H4、H5和H6)。為了檢驗這三個假設,本研究參考Schmitt等[8]的研究方法,設置1—5級的李克特量表,邀請相關領域的9位專家,對20項環境行為的成本性(1表示“無需付出成本”,5表示“付出很高的成本”)、可觀察性(1表示“完全觀察不到”,5表示“極易觀察到”)和社會互動性(1表示“無建立社會關系的可能”,5表示“一定能建立社會關系”)分別進行打分。檢驗打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0.764,說明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為了使所得數據與回歸系數都處在同一個數量級別上進行分析,運用“z-score標準化”方法將數據轉化為無量綱化測評值,數據標準化處理后得到的結果見表4。
本文將遺產旅游地居民各類環境行為對生活質量感知的回歸系數與其成本性、可觀察性和社會互動性之間的關系繪制成散點圖(圖1)。
從圖1可見,居民環境行為的成本性與回歸系數的相關性最大(r=0.043),其次是可觀察性(r=0.017),社會互動性的相關性最小(r=0.014)。即遺產旅游地居民環境行為的成本性越高,對生活質量感知產生的影響越大;可觀察性越高,對生活質量感知產生的影響越大;社會互動性越強,對生活質量感知產生的影響越大。因此,假設H4、H5和H6得到了驗證。由于某些環境行為可能存在成本性、可觀察性和社會互動性并存的情況,本研究將3個影響因子同時作為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僅有成本性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系數=0.037,p=0.01),可觀察性(系數=0.011,p=0.35)和社會互動性(系數=0.005,p=0.52)均未通過檢驗。由此可知,成本性能更深刻地影響旅游地居民環境行為與生活質量感知正相關的關系,而可觀察性和社會互動性則相對較弱。究其原因,武陵源遺產旅游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居民收入均不高,當地居民更重視基本生活需求,而對高級需求關注較少。因此,居民實施高成本的環境行為(特別是高經濟成本)比高社會互動性的環境行為獲得更多的滿足感,更容易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感知。
3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武陵源遺產旅游地的社區居民為研究對象,對其環境行為、環境后果感知與生活質量感知的關系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和啟示:①在4類環境行為中,旅游地居民實施生態管理行為的頻次最高,其次為消費行為,公民行為和說服行為的實施頻次較低。居民的環境后果感知較敏感,且對人文環境后果的感知程度略強于自然環境后果。因此,在推動武陵源居民實施環境行為時,要針對公民行為和說服行為等弱項,在居民社區、學校等公共區域積極開展環境教育,讓遺產旅游地居民能充分認識自身的環境責任,為推動全民參與環境行為奠定堅實基礎。實際上,現階段遺產旅游地居民的環保意識還有待增強,需要政府管理部門的合理引導,如制定有關環境行為的獎懲政策等。②遺產旅游地居民環境行為正向影響生活質量感知,環境行為的實施能促進他們生活滿意度的提升。環境后果感知顯著負向影響遺產旅游地居民的生活質量感知,但居民主動實施環境行為能緩解環境后果感知對生活質量感知產生的消極影響。因此,遺產旅游地在注重旅游發展的同時,應加強環境綜合治理工作,制定合理的旅游發展和管理政策,轉變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傳統旅游發展模式;堅持綠色和低碳發展方式,實現保護生態環境和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的雙贏。此外,引導居民實施積極的環境行為,營造有利于居民實施環境行為的外界條件,如提供便利的公共設施、建立健全法律法規等。③遺產旅游地居民環境行為的成本性越高、可觀察性越高、社會互動性越強,對生活質量感知的影響就越強烈。其中,成本性影響最大,其次是可觀察性,社會互動性影響最小。因此,當地政府部門需對高成本性的環境行為(需要花費較多時間、精力或金錢才能完成的環境行為)給予一定的獎勵,以鼓勵這些積極行為的實施,如種植樹木、購買環保型汽車、企業研發或引進低碳技術等;推動居民參與環境行為的社會體系,調動政府、社會團體和環保組織等積極開展志愿者服務、環保公益和公眾信訪投訴等活動,激發社區居民的環境責任感,促使他們在實施環境行為的同時,拓寬人際交往,提高生活滿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