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保護的現實困境與制度創新
——以“南京虐童案”為例
胡杰容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北京,102249)
一、問題提出
兒童不僅是家庭的成員,也是國家公民。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兒童作為獨立的權利主體,享有生存、受保護、發展和參與四項最基本的權利。其中,受保護的權利是指保護兒童在受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任何負責照管兒童的人照料時,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傷害或凌辱、忽視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1]狹義的兒童保護主要是指預防和干預兒童虐待和忽視的集體行動,即國家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包括社會救助、法庭命令、法律訴訟、社會服務和替代養護等措施,對受到和可能受到暴力、忽視、遺棄、虐待和其他形式傷害的兒童提供的一系列旨在救助、保護和服務的措施,使兒童能夠在安全的環境中成長。[2]中國是《兒童權利公約》的最早締約國之一,頒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強調對兒童進行家庭、學校、社會和司法保護。
近年來,屢屢曝光的兒童虐待案件說明我國在兒童保護方面尚存在空白。其中,2015年4月初發生的“南京虐童案”引起司法干預,并經過媒體的持續報道,得到廣泛的社會關注。案件的始末是南京江北區一小學二年級男生施小寶,因為沒有完成養母李某布置的課外作業并且撒謊,遭到李某的毆打,學校老師發現傷情后報警。南京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介入調查,并將施虐者李某以涉嫌故意傷害罪刑事拘留。經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后,浦口區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李某故意傷害罪,并處有期徒刑六個月。①
這起案件被作為一起刑事案件,得到了司法機關的介入。在司法干預過程中,養母李某以故意傷害罪被定罪服刑,其兒童虐待行為受到了刑事懲戒,似乎司法正義得以維護。但從兒童權利的視角來看,這起案件也是關涉多方主體價值觀念和利益立場的兒童保護事件。當國家公權在介入家庭領域中的兒童保護時,必然觸及案件發生的社會文化脈絡,包括當事人之間的情理關系;也要具體而充分地考慮到兒童與家庭之間已經形成的依戀關系、兒童的生活安置和未來發展等問題。司法干預的出發點是兒童保護,但是否真正做到維護兒童利益最大化、是否達到維護兒童權利的效果尚需深思。本研究將結合這起典型的兒童虐待干預案例,從兒童權利的視角,分析當前我國兒童保護的現實困境和隱含的重重張力。在此基礎上,試圖討論在中國本土文化背景下,在預防和干預兒童虐待的實踐中,如何實現國家、父母、兒童三方權利的相對平衡,真正有效維護兒童權利、滿足兒童需要。
二、兒童保護中的困境與沖突
(一) 是兒童虐待還是體罰管教
在最廣泛意義上,所有對兒童故意傷害的行為都構成兒童虐待(child maltreatment),無論是對兒童的苛刻、過分嚴厲、拒絕、忽視、剝奪,還是暴力和虐待(child abuse)。[3]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兒童虐待(child abuse)是指對兒童有撫養監管義務及操縱權的人,做出足以對兒童的健康、生存、生長發育及尊嚴造成實際的或潛在的傷害行為,包括各種形式的身體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視或經濟性剝削。[4]這一狹義的兒童虐待界定強調:在不同的施虐主體中,父母是重要的施虐者;在多種虐待形式中,身體虐待是常見的主要形式。在“南京虐童案”中,養母李某因為教育問題多次打罵施小寶,直至2015年3月底,再次因學習和行為習慣問題,她嚴厲責打小寶,造成一級輕傷。如果參照兒童虐待的界定,顯然她的行為構成兒童虐待。我國法律對虐待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規定相對嚴格,不僅在主觀方面強調主觀故意,而且在客觀方面要求虐待行為情節嚴重,具有經常性、持續性和嚴重后果。在維護家庭團結的立法意圖下,虐待案屬于自訴案件,不告不管。但在兒童虐待案件中,一是兒童作為限制行為能力的人,無力提起訴訟;二是“家丑不可外揚”等親親相隱的家庭倫理觀使得當事人不愿提起訴訟。因此,對兒童虐待案件,國家介入顯得尤為必要。但本案中,司法機關從打擊與懲戒犯罪出發,將李某行為的性質認定為故意傷害行為,并以故意傷害罪論處。顯然,李某毆打施小寶的行為不同于一般的故意傷害行為,而與兒童虐待問題緊密相關。在這個意義上,司法機關對李某的行為定性沒有觸及行為的本質特點。
案發后,李某反復強調,她責打施小寶是為了督促他改正惡習,她的行為屬于體罰管教,并堅決否認虐待孩子,拒絕認罪甚至企圖撞墻自殺。②③但從兒童福利專業人士的角度看,當事人李某的行為已然構成兒童虐待。到底體罰管教是不是兒童虐待,專業的界定與普通人的看法存在明顯分歧,即使是遭受責罰的兒童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模棱兩可。研究發現,兒童對于父母虐待行為的合法性持雙重態度,一方面,他們在理智上對父母的虐待行為合理化,另一方面,在情感上表現出不接受。[5]52這意味著受虐兒童對父母責罰行為存在認知與情感之間的張力。在本案中,李某的行為為何難以被認定為兒童虐待?為什么在中國即使是如此嚴厲的體罰管教也難以被認定為兒童虐待?
首先,對兒童虐待的認識與一定的兒童觀緊密相連。人們怎樣對待兒童源于怎樣看待兒童,對兒童地位的不同看法直接影響了人們對待兒童的方式。兒童是家庭的私產與父母的附屬品,還是國家的公民與獨立的權利主體?如果兒童被視為家庭的私產和父母的附屬,父母即使再嚴厲地體罰管教孩子,也是個人行為。反之,如果將兒童作為獨立的權利主體,享有國家法律賦予的受保護權,體罰責打兒童則可能構成侵犯兒童受保護權。在這一意義上,對兒童虐待的界定是建立在某種兒童觀的基礎上的。
其次,對兒童虐待的界定要結合一定的社會文化脈絡。兒童虐待是一個文化敏感性的概念。在導致對兒童虐待認識差異的多種邏輯根源中,文化觀念和價值取向是重要的影響因素。[6]28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為,“棍棒底下出孝子”,將體罰責罵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教養方式。因此,人們不認為體罰孩子是侵犯他們的權利,而是認為“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才見怪”。在這樣的思想觀念下,體罰成為管教孩子的一種重要方式,似乎愛之愈深,責之愈嚴。盡管當今人們的家庭教育觀念和兒童教養方式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從親子權力關系上看,強調家長權威的父權中心主義文化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一些家長依然認為,打罵孩子只是“體罰管教”而不是“兒童虐待”。體罰管教是否可認定為兒童虐待,與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家庭權力關系具有直接關聯。
最后,兒童虐待的界定要經歷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社會建構論認為,各種社會現實是在主體間性的互動中,社會行動者之間實現共享性理解的結果;是經由溝通、對話甚至利益沖突與斗爭達成共識的產物。[7]從兒童虐待概念在美國的確立過程看,1960年前,雖然兒童受虐現象客觀存在,但直到1962年,美國丹佛的兒科醫生亨利·坎普(Henry Kempe)等人出版了《受虐兒童綜合癥》一書后,在醫療、司法和社會服務等不同專業團體的共同推動下,聯邦政府于1974年制定的《兒童虐待預防和干預法案》才確立了兒童虐待的最基本定義。[6]26這說明兒童虐待要成為一種表現為客觀外在性的社會現實,需要人們的思想認知、價值信念等發生變化,需要不同社會群體的共同努力,透過對相關行動新的意義賦予,實現共享性理解。
正是因為兒童虐待的界定與一定社會文化背景下人們的兒童觀和教養觀密切相關,所以,不同群體對兒童虐待的界定存在較大分歧,對體罰管教是否是兒童虐待存有異議。在“南京虐童案”中,對李某體罰小寶的行為,司法機關認為是故意傷害,當事人認為只是管教失當,而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和世界衛生組織對兒童虐待的界定,她的行為顯然侵犯了兒童的受保護權,構成兒童虐待。在一定程度上,“南京虐童案”折射了兒童保護實踐中對兒童虐待行為認知和定性上存在著張力。
(二) 是司法正義還是社會恢復
從歐美國家的實踐看,司法、醫務、教育和社工等不同專業共同參與兒童虐待的干預,尤其是司法和社工專業。然而,不同專業在價值理念、干預方法、考慮重點上存在差異,這在兒童保護實踐中常常是引發爭議的問題。從“南京虐童案”的處理來看,強調司法介入,而忽視社會服務,整個干預過程包含著司法正義和社會恢復之間的張力。
首先,司法正義與情理脈絡之間具有一定的張力。本案中,養母李某和生母張某之間是感情篤厚的表姐妹,施小寶與李某之間已經建立了深厚的依戀關系和歸屬感。④這種情理脈絡可以成為妥善解決問題、維護兒童利益可資利用的資源和優勢。但司法機關沒有重視施小寶、張某與李某之間的關系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和被告人,他們不是利益和情感對立的雙方當事人。其司法干預過程強調維護司法正義,拒絕當事人提出的刑事諒解書和刑事和解書,也不愿傾聽受虐兒童的心聲。這種干預固然達到了懲戒與威懾違法行為的目的,但卻使當事人的情理關系和社會團結遭到破壞。本案中,面對養母判刑入獄,生母萬分愧疚,甚至跪地道歉。⑤⑥這即體現了國家公權力介入兒童保護領域時,司法正義與情理脈絡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
其次,司法正義與社會恢復之間存在張力。涂爾干認為,違法犯罪行為侵犯的是社會整合,壓制型法律以集體意識為主導來維系社會的機械團結,而恢復型法律體現的是以功能依賴來維護社會的有機團結。[8]恰如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所指出的,刑事司法模式建立在適當報應和懲罰罪犯基礎上,通過一種規訓技術,對案主進行分類管理和監管訓練,試圖改造主體,保衛社會。這種模式強調司法正義,但卻不利于社會關系結構和功能的恢復,甚至對其具有破壞性效果。而社會恢復模式強調在矯正治療和恢復補償等非懲罰性的司法理念指引下,通過輔導、矯治、教育、安置、能力建設、恢復關系、補償過錯等措施,一方面實現主體塑造,另一方面恢復社會關系和社會團結功能,減少糾紛和預防犯罪,最終達到保護社會的目的。[9]本案的司法干預具有刑事司法模式的特點,將維護司法正義放在首位,不重視被告人與受害人之間已經形成的親子關系,更不重視被告人李某的教養觀念行為的矯正、家庭撫育功能的維護,忽視了社會連帶關系的維護及其家庭撫育功能的修復。
(三) 是兒童權利還是其他主體權利
兒童保護涉及兒童、父母、社會和國家等多重權利主體,不同主體之間可能發生權利沖突。在“南京虐童案”中,兒童受保護權和父母監護權、兒童受保護權和社會監督權、父母監護權和政府干預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沖突。
1. 兒童受保護權與父母監護權的沖突
兒童的受保護權和父母的監護權都是我國法律規定的合法正當權利。對兒童的受保護權,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條明確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創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環境,依法履行對未成年人的監護職責和撫養義務。禁止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遺棄未成年人。”[10]父母對子女的教育監護既是一種職責,也是一種權利。我國《婚姻法》第二十三條明確規定:“父母有保護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權利和義務。”[11]《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一條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該關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狀況和行為習慣,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適當的方法教育和影響未成年人,引導未成年人進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預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煙、酗酒、流浪、沉迷網絡以及賭博、吸毒、賣淫等行為。”[10]但由于權利主體的利益沖突和立法者的價值模糊,導致相關的法律規定并不明晰。例如,對父母監護權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對什么是父母適當的管教行為或適當的教育方法沒有具體規定,對父母行使監護權時兒童人身受保護的權利如何體現也沒有明確規范,這些語焉不詳的地方成為父母監護權與兒童受保護權之間的沖突空間。[12]那么,在維護兒童的受保護權時,如何同時保障父母對子女的教育監護權?
2. 兒童受保護權與社會監督權的沖突
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個人隱私。[10]在“南京虐童案”中,媒體的頻繁報道和案件的公開審理,完全曝光了小寶的身世及其他隱私。媒體采訪時,小寶屢屢被問及案件相關的細節和感受。在網絡空間里,他成為網民談論消費的對象,并被貼上“被虐待兒童”的標簽。作為一起典型的兒童虐待事件,社會和媒體的廣泛關注是在行使合法監督權,但在推動兒童權利保護的同時,也深深傷害了兒童的隱私權,嚴重干擾其正常生活,實質是一種二次傷害。社會行使監督權時,如何保障兒童不被二次傷害?
3. 父母監護權和政府干預之間的沖突
在父母、兒童和國家三者的權利與義務關系上,兒童不僅受父母監護,也受國家保護。《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國家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當父母監護行為失當時,國家有保障未成年子女權利的義務,有監督父母等監護人行為的權利。[10]但在何種程度上,父母的監護行為可認定為失當?在何種情形下,國家可進行干預?當父母和國家的認知判斷發生分歧時,如何處理?我國相關法律并無具體明確規定。因此,父母對兒童的監護權與國家對兒童的保護權可能產生沖突。
(四) 是兒童受保護權還是兒童其他權利
1. 兒童受保護權與參與權之間的張力
受保護權和參與權是兒童權利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尊重兒童觀點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即任何事情涉及兒童,均應聽取兒童的意見。為了維護這一原則、保障兒童參與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二條明確規定,締約國應確保能夠形成自己看法的兒童有權對影響兒童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對兒童的意見應按照其年齡和成熟程度給以適當的重視。兒童特別享有機會在影響到兒童的任何司法和行政訴訟中闡述見解,以符合國家法律的訴訟規則的方式,直接或通過代表或適當機構陳述意見。[1]在“南京虐童案”中,雖然小寶強烈要求回到南京養父母家、希望繼續由養母撫養監護,但仍然被帶回生父母家。對兒童的生活安置沒有充分考慮他本人的意愿,這一司法干預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兒童受保護權與兒童參與權之間的張力。
2. 兒童受保護權與發展權之間的沖突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提出,尊重兒童基本權利的原則,所有兒童都享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應最大限度地確保兒童的生存和發展。[1]但兒童發展權的維護與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不可分離,在生活安置上,維護兒童的受保護權和發展權,有時處于一種兩難困境。從“南京虐童案”來看,小寶的生父母是安徽農民,家庭經濟壓力大,經濟撫養能力有限,因此主動將小寶送給李某撫養。而李某夫妻社會經濟地位高,是典型的中產家庭,他們為小寶提供了優越的生活環境和良好的教育機會。更重要的是,小寶已經與李某建立了親密的依戀關系。如果李某能夠改變教育方法,將小寶交由李某撫養,在精神、情感、物質等方面,可能更有利于小寶的發展。在小寶的生活安置上,司法機關從維護兒童受保護權出發,裁定由其生父母監護。這種安排不僅忽視了小寶與養母之間已經建立的情感關聯,而且不利于兒童發展權的維護。根據媒體報道,小寶離開南京回到家鄉后,難以融入當地生活,學習成績下降。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和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兒童利益最大化、尊重兒童基本權利、無歧視、尊重兒童觀點為四項基本原則,強調保護兒童生存、發展、受保護和參與四項基本權利。但在兒童保護的干預中,不同權利主體之間可能發生權利沖突,甚至兒童權利內部也可能出現張力。僅僅從“南京虐童案”的司法實踐來看,維護了兒童的受保護權,卻忽視了兒童的發展權和參與權,難以體現兒童利益最大化、尊重兒童基本權利、尊重兒童觀點的原則,很難說這是理想的兒童保護行動。
三、加強兒童保護的制度創新
對兒童虐待與體罰管教的認知分歧、司法正義和社會恢復之間的張力、兒童權利維護的多重沖突,構成了兒童保護實踐的現實困境。走出困境,消解張力,促進兒童權利維護的平衡,需要加強兒童保護的制度創新。
(一) 推動兒童虐待的社會問題化,提升對兒童虐待的共同定義
雖然兒童虐待問題現實存在,兒童受虐致傷致死的事件屢屢見諸報端。但在我國“兒童虐待”至今未被建構為一個社會問題,客觀存在的兒童虐待現象還缺乏不同社會群體和社會力量的持續關注和集體建構。社會問題具有客觀現實性和主觀建構性,它的存在不僅依其是否客觀存在,而且取決于它是否得到了行動者的關注,是否被行動者主觀上接受為社會問題。在一定意義上,社會問題是對社會現象的主觀定義和社會建構的結果。更重要的是,社會問題的形成是一個問題化的過程,是多方行動者在主體間性互動的基礎上進行磋商與對話,逐漸達成一種共同接受的認識與問題解決方案的活動。其中包含著各社會群體對社會現象的不同認識與回應,及其圍繞問題認識與社會回應展開的協商、沖突,直至形成對議題的共同定義。[13]在這個意義上,只有推動社會對兒童虐待的普遍關注,并整合不同的利益、價值、認知的人們對這類現象的理解與定義,才能將兒童虐待現象社會問題化。當社會普遍認識到打罵孩子不是私人領域的個人行為,而是侵犯兒童權利的行為,甚至成為社會問題時,才能形成人們對兒童虐待問題的普遍共識,才能引起宏觀政策和微觀實踐兩方面的行動。
兒童虐待是一個文化敏感性的概念,對它的界定要結合一定的文化和社會處境。正如蘇珊·比賽爾(Susan Bissell)所言,對兒童保護的界定必須充分理解兒童及其文化和處境,否則會導致片面武斷的界定,而這種武斷界定可能使得我們無法恰當地理解兒童保護風險的發生,也可能違背兒童權利,只有基于文化自覺和情境自覺的兒童保護實踐才更加有效。[14]正如電影《刮痧》所反映的那樣,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同樣的行動被賦予不同的意義,中國文化認為刮痧是一種中醫傳統的診療技術,而美國文化認定為兒童虐待。對兒童虐待的定義既不能以父權中心主義文化為借口,掩蓋兒童虐待的事實,也要充分考慮本土文化和具體情境因素,提出切合中國本土情境的兒童虐待定義。
(二) 倡導支持家庭的兒童福利政策,推動兒童、父母、國家之間的權利平衡
對兒童虐待的預防和干預包含了國家干預、家庭價值、父母親職權和兒童權利等不同的要素,如何平衡這些要素是兒童保護需要考慮的焦點。兒童保護以一定的兒童福利政策為依托,兒童福利政策集中體現了對兒童撫養和照顧的政府干預。在宏觀兒童福利政策上,強調政府干預需要平衡兒童、國家、父母三者之間的關系,國家干預應該重視家庭需要、優勢和資源,通過支持家庭兒童撫育功能的發揮,來預防和干預兒童虐待。
不同的兒童福利政策模式體現了國家介入兒童保護的程度和方式不同。根據兒童、父母和政府多重主體之間的關系,福克斯·哈丁(Fox Harding)比較了自由放任主義、國家父權主義、父母權利中心和兒童權利中心四種不同類型的兒童福利政策。自由放任主義的兒童福利政策認為,兒童照顧是家長的權責,應該最大限度地限制國家介入。而國家父權主義強調,國家公權享有維護兒童權益的職責和干預家庭的合法性,當發生兒童虐待的風險時,國家應該積極主動介入,甚至提供替代性照顧。父母權利中心模式主張,國家應該尊重父母的監護權,只對兒童撫養功能失調的家庭提供有限的干預。兒童權利中心模式從兒童的獨立性與主體性出發,強調維護兒童權利。[15]西方兒童福利的發展已經進入“兒童保護和家庭支持融合時期”,尊重家庭及父母權利成為主導的政策取向,國家干預體現為支持和提升家庭的兒童撫育功能。[16]以美國的兒童福利政策為例,其發展取向越來越強調家庭價值、尊重父母權利與適度政府干預介入,以體現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之間的協調、政府干預背景下兒童權利和父母權利之間的平衡,其實質是國家干預主義前提下,對家庭為本理念的理性回歸。[17]概言之,兒童問題連接著兒童、家庭和國家,要平衡父母權威、政府干預和兒童權利三者的關系,兒童福利政策不僅要保護兒童合法權利,還要尊重父母的權威和家庭的撫幼功能。
我國的兒童福利政策正在逐漸從殘補式走向適度普惠制,兒童虐待問題的處置也走向有限的國家干預。自“南京餓死女童案”后,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民政部聯合頒行了《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八種情形可以依法撤銷父母的監護權。[18]這使得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對父母等監護人侵害兒童權利行為的司法干預被激活,[10]表明兒童虐待問題被納入國家干預范圍。2016年國務院頒行的《關于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將因家庭監護缺失或監護不當遭受虐待、遺棄、意外傷害、不法侵害等導致人身安全遭到威脅或侵害的兒童,納入困境兒童保護機制范圍內,[19]民政部建立了《受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指引》。但在工作實踐中,會盡力促進家庭完整與融合,撤銷監護人監護資格非常嚴謹慎重,只有萬不得已才將兒童帶離家庭。這表明我國的兒童保護實踐依然非常強調家庭的兒童照顧職責和撫養功能。
如果兒童福利體系不能整合家庭生活背景中擁有的豐富性和優勢,這個福利體系就不能有效地對脆弱兒童和困境家庭的需要做出回應。除了保護兒童安全外,維護永久并穩定的家庭聯系同樣是兒童的需求,要保證兒童是在穩定、持續、永久的家庭環境中撫養長大,需要通過提供家庭支持預防兒童虐待風險,促進兒童的積極發展。[20]在我國,傳統的家本位文化依然相對強大,家庭價值和資源不可忽視。具有中國文化敏感性的兒童福利政策應該以家庭為本,一方面,強調父母是兒童撫育的權責主體,家庭是兒童成長的最佳環境;另一方面,在父母親職權和國家干預的關系上,政府與父母不是一種對立關系,政府不是替代而是支持家庭更好地發揮兒童撫育的功能,推行一種支持家庭的兒童福利政策。
(三) 整合家庭服務和兒童保護,提升家庭兒童照顧功能
兒童保護包括宏觀政策和微觀模式兩個層次,在強調兒童、國家、家庭三者權利平衡的兒童福利政策框架下,需要推動兒童保護和家庭服務相融合的兒童虐待干預模式。即以家庭為干預單位,通過家庭維護服務和家庭重整服務,對受虐兒童及其父母都開展輔導,維系適當的親情連結,改善父母撫養行為,修復和維護家庭的兒童照顧功能,最終維護兒童權利,滿足兒童需要。
兒童保護和家庭服務是西方兒童虐待問題的兩種干預模式。前者是政府對兒童撫養角色失當的父母采取司法途徑為主的干預形式,政府通過轉移或者取代父母監護權來實現保護兒童,容易導致政府與家長陷入對立沖突中。后者將兒童虐待視為家庭結構功能失調的表現,政府干預主要是通過與家長合作、提供家庭支持服務,幫助家庭恢復兒童撫育功能。[21]在兒童權利的話語下,西方兒童保護模式呈現出綜融趨勢,即注重發揮兒童及其系統的優勢和資源,強調“父母參與”“伙伴關系”,明確國家、社會、家庭等不同主體的福利責任。[22]即使是兒童保護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國,也逐漸走向兒童保護模式和家庭服務模式的整合。從1980年的《收養支持和兒童福利法案》(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 of 1980)開始,美國聯邦政府先后建立了“家庭維護與支持服務項目”(Family Preservation and Support Services Program)和“促進家庭安全穩定項目”(Promoting Safe and Stable Families Program),通過了《收養和安全家庭法案》(Adoption and Safe Families Act of 1997)和《維護兒童和家庭安全法案》(Keeping Children and Families Safe Act of 2003)。這些舉措確立了家庭服務在美國兒童福利制度體系中的地位,標志著美國從片面武斷地強調兒童保護,轉向同時強調家庭服務和兒童保護。[23]
在中國,從當前來看,提升兒童虐待干預方法的文化敏感性,應該以家庭為干預單位,為家庭提供支持、資源和服務等,發揮兒童家庭系統的優勢和功能。在我國臺灣地區,兒童保護的“家庭干預計劃”包括家庭功能與兒童安全評估、親職教育、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兒童安置評估及其他社會福利服務方案。兒童虐待的干預主要通過家庭維護服務和家庭重整服務來促進家庭兒童撫育功能的恢復與提升。通過社會工作專業評估,當兒童繼續留在家庭內沒有風險時,可提供家庭維護服務;當面臨高度風險時,可先將兒童進行寄養安置,提供家庭重整服務,以促進兒童回歸家庭。[24]雖然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服務針對發生兒童虐待風險的程度不同,但都是以維持親子依戀關系、降低外部干預對親情關系和家庭倫理的破壞、恢復和提升家庭的兒童照顧功能及最大限度維護兒童利益為目標。
(四) 推動社會工作專業的介入,以跨界合作尋求司法正義與社會恢復之間的平衡
兒童虐待問題需要司法干預和法律權威來懲戒施虐行為、維護兒童權利,但兒童身心健康成長、家庭撫養功能的發揮還需要專業社工的參與,通過跨專業、跨部門的合作,達到司法正義和社會恢復之間的平衡。切實維護兒童權利,滿足兒童需要,更需要發揮社會工作專業在兒童保護中的重要作用。
在兒童虐待的干預過程中,社會工作專業承擔著重要的職責。首先,舉報初查。在強制舉報制度下,接到學校、醫生、社工、鄰居、基層的舉報后,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要展開調查,篩查是否存在兒童虐待問題。其次,調查評估。兒童受虐風險和兒童保護需求的調查和評估需要社工的參與。兒童虐待風險發生的原因及其如何降低風險發生率,兒童及其家庭是否有緊急需要,家庭具有哪些優勢和資源,是否需要申請緊急保護,需要社工的調查評估和專業判斷。再次,制定兒童保護計劃。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要召集家庭成員、律師、兒童及其他有密切關聯的人員,為兒童及其家庭制定服務計劃,商議具體明確的兒童保護方案,以確定給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務的內容和類型、兒童安置與撫養的方式等。最后,執行兒童保護計劃。專業社會工作者依據兒童保護計劃為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務,包括通過鏈接與整合資源,幫助家庭解決經濟困難來改善兒童成長環境;通過家庭咨詢輔導、親職教育,提升父母撫養方式和教養觀念;通過兒童托育等服務,來補充父母職責;通過協調家庭關系、疏導兒童和家長情緒,解決家庭和兒童所面臨的問題。
在我國,2016年第六次婦女兒童工作會議提出,建立并運行監測預防、強制報告、應急處置、評估幫扶、監護干預五位一體的兒童保護機制,這一制度體系的順利運行需要社工專業的參與及其與司法部門的密切合作。第一,監測預防機制要求強化家庭監護責任,專業社會工作者可以為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導和定期隨訪等服務,幫助他們改善兒童撫養方式,提升其監護能力。第二,強制報告機制要求學校、醫院、村居、社工機構主動報告,社工機構負有發現報告的義務。第三,應急處置機制下,警察依法對監護不當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批評訓誡,對兒童虐待行為開展刑事偵查,專業社會工作者須參與兒童虐待的現場處置。第四,通過評估幫扶機制,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接受委托對兒童安全處境、生活保障、家庭監護、身心狀況等開展評估,并提出兒童虐待的干預措施,開展家長的教育輔導和兒童的身心康復服務等。第五,監護干預機制中,當存在兒童虐待的高風險,需要委托監護、臨時監護或者轉移父母監護權時,司法部門需要參考社會工作專業人員的社會調查報告和風險評估報告,以裁定是否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是否必須轉移父母監護權、哪種安置方式更切合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由此可見,社工專業的高度介入并與司法部門密切合作是我國兒童保護機制的重要內容。

①案件過程根據央視網法治在線報道整理,“南京虐童案”一審庭審紀實 [EB/OL].[2015-10-16]. http://news.cntv.cn/2015/10/16/VIDE1444972678893820.shtml.
②南京本地寶報道, “南京虐童案”9月28日開審養母李征琴拒認罪[EB/OL].[2015-09-28]. http://nj.bendibao.com/news/2015928/57703_3.shtm.
③“南京虐童案”養母企圖撞墻自殺法院決定對其逮捕[EB/OL].[2015-09-29]. http://nj.bendibao.com/news/2015929/ 57751.shtm.
④新華網報道,南京虐童案涉事男童:不恨養母都是為了我好[EB/OL].[2016-03-23]. 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6-03/23/c_128824578.htm.
⑤中國青年報報道,南京虐童案孩子生母:判決結果太不近人情了[EB/OL].[2015-10-11]. http://zqb.cyol.com/html/2015-10/11/nw.D110000zgqnb_20151011_4-04.htm.
⑥南京本地寶報道南京虐童案養母出獄,生母下跪道歉大喊對不起[EB/OL].[2016-03-13].http://nj.bendibao.com/news/2016313/60703.s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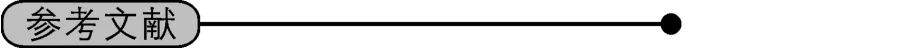
[1]兒童權利公約[EB/OL].[2017-8-30]. http://www.un.org/chinese/children/issue/crc.shtml.
[2]尚曉援. 兒童保護制度的基本要素[J]. 社會福利(理論版), 2014(8): 2-5.
[3]CICCHETTI D, CARLSON V. Child maltreatment: 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4.
[4]WHO. Report of the consultation on child abuse prevention[R].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 5-16.
[5]祝玉紅. 聆聽與尊重: 兒童權利視角下對兒童虐待經驗的探索性研究[J]. 中國青年研究, 2013(4): 50-54.
[6]喬東平, 謝倩雯. 中西方“兒童虐待”認識差異的邏輯根源[J]. 江蘇社會科學, 2015(1): 25-32.
[7]彼特·博格,托馬斯·盧克曼. 知識社會學——社會實體的建構[M]. 鄒理民,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1:27-34.
[8]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M].渠敬東,譯.北京: 三聯書店,2000:48-74.
[9]郭偉和. 走在社會恢復和治理技術之間——中國司法社會工作的實踐策略述評[J]. 社會建設, 2015(4): 38-48.
[10]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主席令第六十號)[EB/OL].[2016-03-14]. http://www.gov.cn/zhengce/2006-12/29/content_2602198.htm.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正)[EB/OL]. (2001-05-30).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1-05/30/content_5136774.htm.
[12]李靜, 宋佳. 家庭兒童虐待中的權利沖突及其法律控制[J]. 廣西社會科學, 2015(12): 121-126.
[13]葛忠明, 遲興臣. 社會問題: 過程及其實踐的空間[J]. 文史哲,2003(5): 138-143.
[14]BISSELL S, BOYDEN J, COOK P, MYERS W. Rethinking Child Protection from a rights perspective: some observations for discussion. [EB/OL]. [2018-01-20]. https://www.researchgate.net/scientific-contributions/2053964005_Susan_Bissell.
[15]KIRTON DEREK. Child social work policy and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2009: 7.
[16]喬東平, 謝倩雯. 西方兒童福利理念和政策演變及對中國的啟示[J]. 東岳論叢, 2014(11): 116-122.
[17]滿小歐, 李月娥. 美國兒童福利政策變革與兒童保護制度——從“自由放任”到“回歸家庭”[J]. 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2014(2): 94-98.
[18]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等. 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EB/OL]. (2014-12-29).http://www.kids21.cn/zcwj/201412/t20141229_308405.htm.
[19]國務院. 關于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EB/OL]. (2016-06-16).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6/16/content_5082800.htm.
[20]JENSON J, FRASER M. Social policy for children and family a risk and resilience perspectiv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Inc. 2006: 23.
[21]GILBERT N. Combating child abus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trends [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5.
[22]劉玉蘭, 彭華民. 西方兒童保護社會工作的理論轉型與實踐重構[J]. 社會工作與管理, 2017(3): 5-11.
[23]胡杰容. 家庭維護服務: 美國實踐與中國意義[J]. 澳門理工學報, 2013(2): 149-155.
[24]沈黎, 呂靜淑. 臺灣兒童保護服務的實踐與啟示[J]. 當代青年研究, 2014(5): 7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