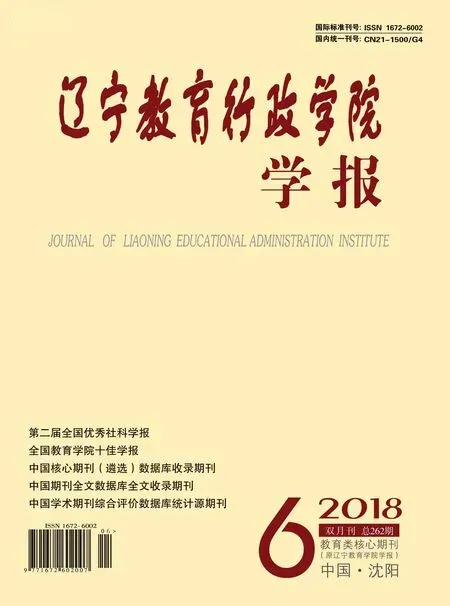王紹蘭《管子地員篇注》探賾
郝繼東
沈陽師范大學,遼寧 沈陽 110034
《地員篇》位于今本《管子》卷18中,第58篇,前一篇是《度地篇》,與此為上下承接關系;后一篇為《弟子職》,與本篇關系不大。《地員篇》和《度地篇》《水地篇》《地圖篇》一道,構成《管子》關于地理學的核心理論,闡述了土壤地理、水文地理、植物地理等方面的知識。自唐以來,就有人作過探索研究,主要留意于標點注釋方面。清代《地員篇》的研究仍以校釋為主,何如璋、王念孫、孫詒讓、張佩綸、王紹蘭、丁士涵、俞樾、方苞、張文虎等人對此都有過注釋,其中尤以張佩綸、王紹蘭、丁士涵三人對《地員篇》貢獻較大。而王紹蘭有《管子地員篇注》,成為對《地員篇》進行專門研究的第一人。
王紹蘭(1760~1835),字畹馨,號南陔,自號思維居士,浙江蕭山城廂鎮人。為清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其研究方向以儀禮、說文為主,兼及子史。在《管子》研究方面,他主要有《管子說》《弟子職古本考注》《管子地員篇注》三種。但其著述大多未刊,散佚較多,現存《管子地員篇注》,收錄于《續修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中。①
一、文獻概述
王紹蘭《管子地員篇注》共4卷,前有自敘、張佩綸敘及胡燏棻識三序,大致說明了《地員篇注》的成書原因及過程。
據自敘,王紹蘭罷官在家后,多以研習舊籍遣日,至《管子地員篇》,見其博大宏深,“天之所生,地之所載,罔不畢述。讀既終篇,目為瞠者久之。喜其足資多識。”②(P561)而當世所傳之尹知章注淺薄疏陋,少有發明。“因博采古今通人所說,條分句解,可簡則簡,可繁則繁,疑者闕焉。自惟瞀無能管窺萬一,積日成帙,釐為四卷,將欲總括大恉,又無能畢肖形容,惟《宙合篇》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至于無間不可名而由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今既取《宙合》之言以稱《地員》之美,其殆庶幾乎。”②(P561)自敘闡述了《管子地員篇注》成書的原因:一是《地員篇》博大宏深,可以供讀者廣博見識;二是《地員篇》之舊注淺陋而粗疏,特別是尹知章的注釋多為后學所詬病,有必要進行全面的梳理。另外,《地員篇》的內容是地理生態植被的總結,對農業生產有非常高的實用價值,歷經千百年之后,至清時仍有很大的實用意義。而事實上是,由于語言文字上的差異和植物土壤名稱的變遷,再加上舊注存在錯誤,《地員篇》的當下實用功能難以實現。
關于《地員篇注》的成書過程,胡燏棻敘有比較清晰的描述。“余既刊南陔先生所為《說文段注訂補》已,又求其《地員注》,久而后得之。……蓋先生所著《說文集注》數百卷,為書過冗,無意問世。既萃其精者為《段注訂補》,復頗綴入是書,以存其所自得,非獨為《地員》發也。……正偽發微,精博幽窅,遠非舊注所及,表章羽翼之力,亦以勤矣。余悼先生書多不傳,斯注脫于兵火,文多壞滅,因復為補正,核而刊之,使好《地員》之學者得以尋焉。”②(P563)胡氏之言表達了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王紹蘭的《地員篇注》乃其所刊布;二是說明該書的內容是王紹蘭《說文集注》精編為《段注訂補》之后所剩材料綴編而成,并不專為注解《地員篇》而發。另外,王紹蘭校釋文字得到了胡氏的好評,即所謂“正偽發微,精博幽窅”。
郭沫若等著《管子集校》,亦參照了王紹蘭的《地員篇注》,并對該書有所微辭。首先郭氏之書記載了王氏《地員篇注》的成書及刊行時間;其次對王書加以評價:“說頗滋蔓。”③(P19)其實,如果綜合胡燏棻和郭沫若二人對王氏《地員篇注》的看法,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王氏《地員篇注》撰寫的初衷不是為校釋《地員篇》,而是《說文集注》衍生的產物,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地員篇注》,就難免會有“滋蔓”之病。再者,如果我們用傳統考據學觀點來看,《地員篇注》擺脫不了“滋蔓”之論;若以生態學或溯源考證的觀點看,《地員篇注》也不失為一本實用之書,起碼為后學理解《地員篇》所見土壤物種等名稱的來源有相當大的好處。
二、文獻主要成就
王紹蘭所撰《管子地員篇注》,主要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釋義
作為一部校釋著作,釋義是第一位的。有清以來,考據學大興,學者對字詞的訓詁考證蔚為大觀。王紹蘭生活于乾嘉時期,正是考據流行之時,必然會受到考據學風的影響。如其對“蔓山”的解釋:
蔓之言曼也。《魯頌·閟宮篇》“孔曼且碩”,毛《傳》:“曼,長也。”《爾雅·釋詁》:“延,長也。”謂山形曼延而長。《說文》:“蔓,葛屬。”《周南·葛覃篇》“葛之覃兮”,毛《傳》:“覃,延也。”鄭《箋》:“葛,延蔓于谷中。”《唐風·葛生篇》“葛生蒙楚,蘝蔓于野”,毛《傳》:“葛生延而蒙楚,蘝生蔓于野。”《北山經》有蔓聯之山,此蔓山亦其比矣。②(P597)
“蔓”的語義來自于“曼”,即有蔓延綿長之意,是聲訓的結果。王紹蘭引用《詩經》《爾雅》《說文》《山海經》為書證,充分證明了“蔓山”乃蔓延連綿之山,而非長滿藤蔓之山。后世學者引用皆以此為據,如郭沫若等人的《管子集校》即以王氏此注為準,③(P912)黎翔鳳的《管子校注》亦同。④(P1087)唯夏緯英校釋與此略異,夏氏認為“蔓山”應為“巒山”,“巒”“蔓”音近,“巒山”當是蔓延的山。⑤(P16-17)夏氏所釋乃由音近而來,其釋義仍為蔓延之山,與王氏殊途同歸,但不若王氏的解釋來得直接明了。
(二)考源
一般來說,清代以考據學為核心的學術思想多以字詞為根本,以小學為主要手段,推尋字詞之詁,而很少涉及詞語之語源。王紹蘭的《地員篇注》卻與此有所不同,乃追尋名物形成之源,由始至終,理清事物命名的脈絡,以便讀者更好地掌握某一物種的歷時演變和名稱的變化。這種校釋方式也是由該書的性質所決定的,即《地員篇》的校釋不單純是文字問題,而是生態學、地理學的問題,故校釋時就不僅僅以文字釋義為主,而更多地加入了名物考源的成分。除上文提到的“蔓山”來源于“曼”義之外,再如對“駢石”的解釋:
駢讀若駢肋之駢。《說文》:“駢,駕二馬也。從馬并聲。”《左氏僖二十三年傳》“聞其駢肋”,《注》:“駢肋,合干。”《晉語》作“骿肋”,韋昭注:“骿,并干也。”《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釋文》:“駢,《廣雅》云‘并也’,李頤云‘併也’,司馬彪云‘駢拇謂足拇指連第二指也’,崔譔云‘諸指連大指也’。”駢拇猶駢肋也,《白虎通·圣人篇》引《傳》曰“帝嚳駢齒”,《御覽》卷三百六十八引《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又引《孝經·鉤命決》曰“夫子駢齒”,駢齒猶駢拇也。然則駢之言并也。山之下多石,其石兩兩并連,故云駢石,而不可得泉矣。②(P600)
“駢”為形聲字,從語源的角度講,它的讀音和意義是來源于“并”字的。我們從王紹蘭的說解中也看到了這一點,而且我們了解了“駢”不僅僅用于“駢石”,而且還用于“駢肋”“駢齒”“駢拇”等詞組中,可見其語用的廣泛性。
(三)辨誤
在自敘中,王紹蘭便指出“世所傳尹知章《注》淺陋疏略,罕所發明”。宋明以來,尹《注》一直受到研究者的指責。特別是清代以來,隨著考據的深入,尹《注》訛誤的發現越來越多,學者幾近于不批尹而不成書的地步。王紹蘭《地員篇注》或辨尹《注》之誤,或補尹《注》之闕,成為校釋的一項重要內容。茲舉“山之材”例如下:
尹《注》:“材”猶“旁”也。紹蘭按:“材”無“旁”義。下云“山之側”,此亦不得言“旁”。“材”蓋“”之偽。《玉篇》“”同“椒”,則此謂山之椒也。《楚詞·離騷》“馳椒丘且焉止息”,王逸《注》:“土高四墮曰椒。”《漢書·外戚傳》“釋輿馬于山椒兮”,孟康曰:“山椒,山陵也。”《廣雅·釋丘》:“四隤曰陵。”是孟康解“椒”為“陵”,與“四隤曰陵”之義正合。然則“山之椒”謂山四下隤阤處。《文選·月賦》“菊散芳于山椒”,李善以“山椒”為“山頂”,失之。②(P605)
(四)解物
《地員篇》是生態地理植物的大集合,詳細記述了當時的地理、水文、植物、生產等方面的名物制度。作為一本解讀《地員篇》的著作,《地員篇注》就需要對上述這些名物制度等方面的知識加以說解,而說解的前提條件是作者必須將現有的名物制度與漢代以前的制度相對接。無論如何,都需要作者擁有豐富的生態學、地理學、植物學等方面的知識,并且也有貫通古今名物制度的能力。這也正是王紹蘭《地員篇注》不同于一般《管子》考據著作的一個特點。
關于名物制度的說解,王氏《地員篇注》較為常見,如上面所舉“駢石”“蔓山”之類。茲再舉一例:
魚腸 竹類。《初學記》卷二十八引梁簡文帝《修竹賦》:“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竹得稱草者,《說文》:“竹,冬生草也。”《爾雅》竹之類皆列《釋草》。《西山經》“高山其草多竹”,《中山經》“荊山其草多竹,大堯之山其草多竹,師母之山其草多竹,夫夫之山其草多竹”,皆其證也。②(P602)
“魚腸”是竹類,有《初學記》所引為證,竹子歸為草類,有《說文》《爾雅》《山海經》為書證。以上關于名物的解釋,在《地員篇注》中很普遍。王紹蘭對每一事物的說解形式各不相同,但都切中要害,指出現如今人們容易產生疑問之處。
總之,鑒于《地員篇》的特殊內容,王紹蘭校釋過程中除了運用考據學方法之外,探本尋源,解名釋物是常用的手段。最后形成的《地員篇注》有不同于清代考據者《管子》研究成果的內容,故而有些傳統學者對此深為不齒,但我們應看到王紹蘭在《管子》研究中所做出的寶貴貢獻,至少使我們能夠跳出狹隘的考據學視野,真正認識到貼近生活現實的學問之模樣,切實使《管子》為現實生活生產服務。
三、文獻特點
《地員篇》內容之豐富,王紹蘭借用《宙合篇》譽其為“有橐天地”。確實,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在《地員篇》中皆有敘述。王紹蘭為《地員篇》之博大宏深而折服,又意識到尹《注》之淺陋,于是博采古今通人之說,條分縷析,可繁可簡可闕,成《管子地員篇注》4卷。通觀全書,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考證翔實
郭沫若認為王氏《地員篇注》“說頗滋蔓”,可以說有一定的道理。但筆者認為,“滋蔓”之病并不只有王氏之書存在,以考據方法形成的成果很大程度上都存在這樣的問題。考證之繁復是清代學者之共同特征,我們沒必要對《地員篇注》過多指責。郭氏等人另一個失誤在于將王氏此書列為考據著作加以考察,而未能認識到此書乃水文地理生態學方面的實用之書,因而得出不確的判斷。
筆者認為,《地員篇注》整體上說是一個考證詳實的著作。胡燏棻在敘言中對王紹蘭此著有所評價:“先生精名物訓故,其說經大氐網羅百家巨細貫綜,浩渺無涯。斯注陳義尤繁富,一字之證,幾累萬言。若釋瀆田則辨及溝洫,釋粟秫則辨及麻縻,至于丘陵墳衍之名,草木鱗介之屬,尤徧引《爾雅》、《山海經》諸書,窮原竟委,務于博侈,往往非《地員》本義。”②(P563)前幾句指出王氏之注翔實,證據博宏;后幾句又說務于博而失卻《地員》本義,這也可能是郭氏等人“滋蔓”之論的來源吧。但我們認為,詳盡之說或過侈之論都是可以接受的。
前面我們在引用王紹蘭自敘時提到,《地員篇注》撰寫的原意是對其《說文集注》抽繹,即抽出《說文集注》中有關生態地理方面的內容,圍繞《地員篇》而成書。從這一動機上看,王氏《地員篇注》就與真正意義上的考據學著作存在差異,所以他注重的是生態地理物產等的歷時變化,并將其詳細的記錄下來,這種引證雖最初是以《地員篇》內容為出發點的,但敘述過程及結果不一定以此為標準,如果我們站在地理水文農業指導書這一角度來看問題,翔實甚至滋蔓到是著作的特征或者優點。
比如對“李”的說解,引用了《爾雅》、郭璞《爾雅注》、邵晉涵《爾雅正義》《廣韻》引《爾雅》《齊民要術》所引、陶弘景注《本草》《廣雅》《論語》所引、《太平御覽》所引、《史記》《漢書》《荊州土地記》《風土記》《西京雜記》、西晉傅元賦、古歌辭等共1700余字,介紹了李樹的名稱、來源、種子、種類(如麥李、爵李、車下李、郁李、雀李、奧李、赤李,等等),并說明了各種李樹的出產地及不同稱呼的由來。特別是在說解的最后還說明了“瓜田李下”“李代桃僵”的出處和含義,這樣關于李樹的知識在這條注中便一覽無遺了。②(P643-645)
作為一部“足資多識”的普及性著作,我們沒有必要對《地員篇注》在學術的嚴謹上做過多的苛求。苛求的結果會蒙蔽了該書知識全面系統的優點,而放大了其學術不足的缺點。因此,筆者認為王紹蘭的《地員篇注》在考證方面有詳盡而全面的特點,可以說對閱讀此書的人帶來很大的便利。
(二)推本溯源
前面所引胡敘提到一句“窮原竟委”,是一個客觀的評價。《地員篇》所寫之時,離王紹蘭時代已有千余年,其間名物制度、社會人文環境、地貌生態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有前代學者對此做出的注釋,使后人能夠借助淺陋的說解而大致了解前代的知識,但對此進行系統的梳理是大勢所趨。王紹蘭正是這一任務的擔當者,他以將古今名物制度系聯為目的,博采古今學者之注釋,披尋本源,古今一貫,撰成《地員篇注》。因此,對名物制度本源及流傳的抒寫與闡釋,正是王紹蘭《地員篇注》的又一大亮點。
在關于對“桃”的說解中,其中有一類稱為“櫻桃”,關于“櫻桃”命名的由來及文獻的記載,王紹蘭有詳盡的敘述。櫻桃最初之名為含桃,見于《禮記·月令》之文,后在《史記》中就出現現用名。含桃也稱函桃,櫻桃亦稱桃,“含”與“函”“櫻”與“”互為異體,皆可訓為“小”,所以四者為一物,即今稱櫻桃也。由以上可知,櫻桃命名來源于含桃,是小桃之義,另外古之含桃、函桃、桃與今之櫻桃,皆一物也。②(P641-642)
《地員篇注》中這樣的事例也很多見。比如還在“桃”這一條中接著記述了以“桃”喻“逃”的社會習俗和“二桃殺三士”的歷史故事。另外,王紹蘭所引書證往往是一個由遠及近的歷史脈絡,以《說文》《爾雅》《山海經》為先,次及《史記》《漢書》,再及后代作品。可見,王紹蘭的說解除了詳實之外,更注重對事物命名的追溯,善于找到古今事物之間的聯系,由本及末,由源至流,使讀者既拓展了見聞,又對名物制度有了歷時的認識。
四、文獻價值和影響
王紹蘭《管子地員篇注》能夠在后世產生影響,并不僅僅因為它是詮釋《管子》的作品,而更為主要的原因是它建立起來的溝通古今名物制度的話語場,使后人對身邊的物產有所認識。筆者認為,作為一部詮釋性著作,應遵循其應有的學術規則,《地員篇注》基本做到了;作為一本溝通古今的實用工具書,也應考慮受者的知識性及趣味性,《地員篇注》也做到了。那么,《地員篇注》必將對后世產生一定的影響,無論是在《管子》注釋方面,還是在對生態地理的記載方面。
首先,《地員篇注》為《管子》研究提供了便利。《地員篇》是《管子》的組成部分,是《管子》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王紹蘭的校釋是對前人《地員篇》研究成果的總結,并結合自己研究心得而形成的。郭沫若雖然認為王氏之書“滋蔓”,但仍于《地員篇》部分的集校中大量引用其說解,更體現了王紹蘭在《地員篇》注釋中的地位。另外,夏緯英的《管子地員篇校釋》、黎翔鳳的《管子校注》也對王氏之書加以引用,同樣說明了這個道理。
其次,為古代生態學、地理學、植物學研究提供了資料。《地員篇》本身集中反映了《管子》地學思想、植物學、生態學等方面的知識,是《管子》學說中非常實用的內容,如地形、地貌、土質結構、植物種類、水文等,其分類之細甚是空前。由于年代久遠,流傳過程中的種種訛變,《管子》包括《地員篇》出現了令人難以卒讀之處,后人對其整理工作繼踵而至,無論如何,這些學者的解釋都對《管子》的研究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也為后人讀懂《管子》創造了條件。王紹蘭的《地員篇注》正是理解《地員篇》的依據,將近兩千年的古代生態學、地理學、植物學知識和當下知識聯系起來,使學者更易理解,同時也為當世及后代的地理學研究者們提供了寶貴的研究材料。
再次,對后代普及科學知識的讀物的撰寫提供了思路。一般來說,科普讀物注重的是知識性和趣味性,既要通過讀物傳播豐富的知識,又要兼顧讀者的閱讀興趣。《地員篇注》就在這兩個方面進行了很好的嘗試。《地員篇注》說解了大量的名物,而不局限于《地員篇》所提到的,通過連類而及的方式,將相關的知識濃縮在條目中,即每一條目所含的信息量比較大,正如胡燏棻稱道的“窮原竟委,務于博侈”。
總之,王紹蘭之《地員篇注》對后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也得到了一些學者的好評。張佩綸在《地員篇》上也有相當的研究,⑥他寫給王氏《地員篇注》的敘曾稱贊道:“節解而支分,句釋而字詁,其義訓衷于《爾雅》、《說文》,頗足證明管書,砭補尹《注》,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決是非以定準裁。”②(P562)因此,當選擇一個正確的角度來看待王紹蘭的《地員篇注》時,我們就會為其取得如此成就而喝彩,也為后學能擁有這樣的參考資料而慶幸。
注釋:
①見《續修四庫全書》第97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王紹蘭.管子地員篇注[M].《續修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第97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③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管子集校引用校釋書目提要[M].管子集校,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
④黎翔鳳.管子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⑤夏緯英.管子地員篇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⑥張佩綸有《白帖引管子》(不分卷)、《抄太平御覽引管》(不分卷)、《管子學》(12卷)、《管子識語》(不分卷)等著作,從夏緯英《管子地員篇校釋》、黎翔鳳《管子校注》、郭沫若《管子集校》所引來看,張佩綸在《地員篇》的研究上是相當有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