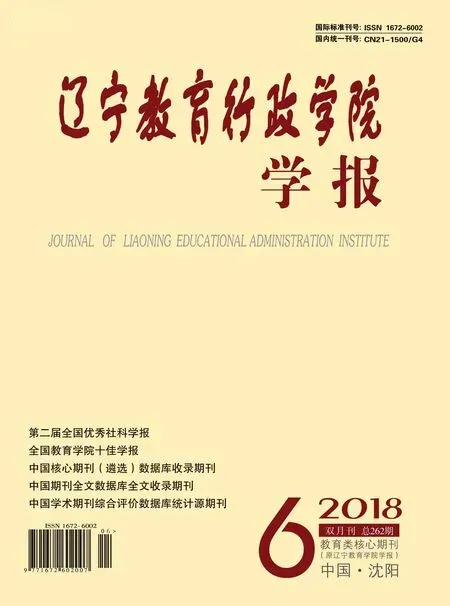論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為
——兼論“醉駕型”犯罪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合理性
姜 夢
首都師范大學,北京 100089
在“醉駕型”犯罪之中,我國刑事司法實務界有判處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慣例。前段時間,發生于安徽省的“陳運醉駕案”終審被判處死刑,但被最高人民法院發回后改判無期徒刑,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而在“醉駕”類犯罪當中,處罰的基礎是刑法上的“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由于該理論在我國刑法實務與學術界是否得到承認尚存爭議,因此,對牽涉“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相關類型的犯罪,在對其解讀時亦常常存在困難。
一、域外刑法對原因自由行為的規范
基于責任原則之下,“實行行為與責任能力必須同在”這一原則是刑事處罰可罰性的基礎,因此,當實行行為進行時、責任能力已經在客觀上確實減弱的情況下,不尋找此種情形下的處罰邏輯,就會破壞責任原則之下的可罰性基礎,由此而誕生的“原因自由行為”一直為域外刑法學理論所關注和探討。
最早能夠找到的類似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論述,源自于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當中的內容,其指出:“將飲酒行為視為罪惡中,忽視其對責任能力作用,在此情形中得以加重處罰之事由。”②[P24]而后,這一問題又經托馬斯·阿奎那和普芬道夫進行過討論,并最終由克萊恩施羅德確定以“原因自由行為”作為概念標志以表達使用。③[P600]而在該概念為學界所接受并廣泛使用后,對于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同樣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19世紀中葉,在薩維尼等法學家的力主之下,《德國刑法典》并未對于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進行詳盡的規定。④[P25~26]但是,這種過分苛求責任主義的觀點逐步為司法實踐認識到與公眾觀念上的不符,更是在刑罰導向上使得法律引導公民為自險無責任能力的行為。因此,責任理論開始異化,主張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逐漸變得有力,進而發展至今已成為通說觀點。④[P25~26]
現代大陸法系各國刑法典對于原因自由行為的規范并不相同,比如,《意大利刑法典》上對于原因自由行為基本上在總則規范當中予以明確,該國法律規范對于原因自由行為的規定大致為:當陷入風險的原因是由于行為人自身可控制的行為所引起的,則不能以行為時無責任能力而尋求罪責的減輕。但是,產生于偶然事件或者不可抗力的醉酒、使用麻醉藥品的狀態,而導致危險行為最終發生的,要減輕行為人的罪責。但是,對于主動自陷無責任能力的行為,能夠證明自陷無責任能力是為事后所脫罪借口的,刑罰得以加重,并且對于行為人屬于慣常醉酒的情形而言,由于經常陷入醉酒狀態,對于嚴重的后果而言有預見性,因此,在慣常醉酒狀態下實施的犯罪行為,刑罰同樣予以加重。⑤[P32~33]
《德國刑法典》對于原因自由行為采取了分則立法的模式,《德國刑法典》第323條a表述為:“(1)行為人故意地或者過失地通過酒精飲料或者其他醉人的藥物使自己處于昏醉狀態的,處5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錢刑,如果他在該狀態中實施違法的行為卻因為他由于昏醉已是責任無能力或者因為沒有排除責任無能力而因此不能處罰他的話;(2)其刑罰不得重于對在昏醉中所實施的行為所威嚇的刑罰;(3)該行為只有根據要求、授權或者刑罰要求才予追究,如果昏醉中的行為只有根據請求、授權或者刑罰要求才能予以追究的話。”⑥[P195]
瑞士對于原因自由行為采取了總分則相結合的立法模式,《瑞士聯邦刑法典》第12條規定為:“(例外情況)如果嚴重之精神障礙或意識錯亂是由行為人自己故意造成,并在此等狀態下實施犯罪行為的,不適用第10條(責任能力、無責任能力)和第11條(限制責任能力)的規定。”⑦[P4]該法第263條規定為:“(在自己造成的無責任能力情況下實施的犯罪)1.因自己造成醉酒或麻醉,且在此等情形下犯重罪或輕罪的,處6個月以下監禁刑或罰金。2.行為人在此等情形下實施了只規定科處重懲役的犯罪的,處監禁刑。”⑦[P86]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域外刑法學理論上對原因自由行為的探討留下了相對豐富的學術資料,但大陸法系刑事司法實務對于原因自由行為而言,其態度是比較曖昧不清的,在接受原因自由行為的問題上,大陸法系的刑事司法實務界仍然比較保守。比如,德國聯邦最高法院1996年8月22日的判決對于酒后闖入過境檢查處撞死兩名官員的行為,該判決對于原因自由行為而言持有相對意義上的否定態度,僅肯定了部分過失的行為,而否認對于危害道路交通和無證駕駛兩個行為的故意行為,特別是否定了在原因自由行為當中構成要件的延伸。⑧[P91~93]
二、關于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探討
雖然大陸法系許多國家在刑法典中均部分承認了原因自由行為理論,但是,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尚不能明確地解釋其為如醉酒等喪失罪責能力的狀況下提供可罰性的依據。大陸法系的許多學者同樣對于原因自由行為理論提供的可罰性依據進行了探討,具體來說是以下兩個方面:
(一)構成要件行為(實行行為)為根基的可罰性論
在“行為與責任必須同時存在”的責任主義語境之下,討論原因自由行為必須建立在如何解釋“同時存在”這一命題。由于醉酒或陷入心智缺失的狀態后,顯然已不具備認識事物的前提,故而必然不能具備責任能力,因此,責任能力(認識)在客觀上只可能存在于因醉酒或其他原因造成心智缺失之前。基于這一客觀事實出發而形成的考慮,如果需要尋找“行為與責任必須同時存在”的理據,就只有將構成要件行為適當地提前(實行行為提前),才能夠尋找到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依據。具體來說,刑法學家主要認同的理由存在于“原因行為時的責任理論”與“類間接正犯”的理論二者。
“原因行為時的責任理論”,是指“具備責任能力的原因行為是追究責任的對象,如果能夠肯定原因行為同結果行為(結果)之間存在一定的構成要件關系的,即可對原因行為追究刑事責任”。⑨[P36]而“類間接正犯”理論是指將陷入心智缺乏而造成責任能力缺失的情況,與間接正犯中“利用無責任者為犯罪行為”進行比較,試圖援引間接正犯的可罰性根據反過來適用于原因自由行為當中。由于二者均是試圖將原因自由行為的責任處罰對象(即構成要件行為)對于常見的犯罪構成而言適當提前,因此,均是擴張了構成要件行為的范圍,是試圖在構成要件層面的基礎上來解決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問題。
但是,筆者認為,無論是“原因行為時的責任理論”,還是“類間接正犯”理論,均存在其致命性的硬傷。具體來說,“原因行為時的責任理論”的問題在于,行為人所為的原因行為在這一理論的框架下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刑法的處罰對象,但是,這些行為本身可能根本不具備違法性。通俗地說,行為人即便是大量飲酒,或者服用精神類藥品等等行為,均不是刑法所禁止的行為。德國刑法學家洛克辛教授就指出:“反對行為構成模式的一種主要論點在于,對一種結果故意進行的原因設定,還沒有表現為法律所要求的那種構成的行為(Tatbestandshandlung)。”③[P601]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強行將這一類行為納入主觀目的性的思考中進行評價,進而以其行為所具有的、可能的目的性來評價為犯罪行為的對象,有嚴重的不當擴張構成要件范圍的嫌疑,構成要件本身的客觀性主導地位,事實上,也可能已經不復存在,并且也會喪失構成要件的規范屬性與犯罪圈的厘定屬性。另外,這樣一種對于所謂的“原因”的追索,事實上是首先設定了結果的必罰,而后再尋找責任最后存在的節點,并直接“不分青紅皂白”地將這個節點作為處罰的基點的,顯然與犯罪論整體上證成犯罪的邏輯不通。如果始終堅持客觀主義的刑法理論并堅持“違法是客觀的”這一基本立場,這樣的對構成要件行為(實行行為)進行的任意擴張,很難令人接受。
與之相對,“類間接正犯”理論同樣具有很嚴重的問題。具體來說,“類間接正犯”還是援引的間接正犯的理論而尋求的處罰邏輯,但問題在于:首先,間接正犯本身即是一種對犯罪構成的修正,而原因自由行為本身還沒有完全地離開基礎的犯罪論層面。根據筆者的觀察,在以“違法——責任”為框架的基礎的犯罪構成當中,特別是在違法的階層之上,并不能夠存在對犯罪構成行為就可以大肆進行修正的情形。換言之,修正的犯罪構成應當至少是在犯罪構成完全結束之后的問題,而不應該在基礎的犯罪構成還沒有能夠盡善盡美的前提之下,就直接援引修正的犯罪構成來解釋基礎的犯罪構成的問題,這種對“犯罪構成的提前修正”同樣有肆意之嫌。其次,間接正犯理論本身恐怕尚不能完全解釋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問題,具體來說,“類間接正犯”的理論只是注重了間接正犯理論當中間接正犯的“工具性”這一面,而未能注意到間接正犯理論當中“教唆性——支配性”的另一面,其后果是造成“類間接正犯”體系的片面性。如果行為人在醉酒之后完全喪失了責任能力,按照“類間接正犯”的邏輯,行為人應當負完全的刑事責任。但間接正犯在很多時候只能存在至教唆的程度,如果未能夠達到對實行行為人的支配,則很難承認間接正犯。換言之,當行為人自陷無責任能力、心智缺失的程度尚未達到意識完全喪失、但意識已經有所減弱的程度之下,行為人不能按照“類間接正犯”的邏輯來成立原因自由行為處罰,同時,原因自由行為本身更構不成一個教唆行為,使得行為人再承擔教唆的罪責,在這種情況之下,行為人就只能被減輕甚至免除刑事責任。這與客觀公正顯然不符。⑩[P258~259]
(二)責任修正理論
由于在構成要件的層面上,需求可罰性根基的嘗試并不能夠盡善盡美,因此,也存在對立的責任層面上的修正理論來尋求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根基。具體來說,責任修正理論與構成要件模式之間共同的認識前提還是“實行行為與責任能力必須共存”這一前提,但對于實行行為本身并不加以改動,而是在責任的層面上,責任修正理論認為,對原因自由行為下的行為人的責任能力是一種修正。換言之,刑法在原因自由行為當中,例外地承認了客觀上、實際生活的認識上不具備責任能力的行為人具有責任能力。這是對于責任概念本身進行的一個修正,因此,在責任的層面上,為原因自由行為本身尋求到了可罰性根基。
責任修正理論的提出同樣備受質疑,具體來說是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責任修正理論同樣是對犯罪論本體進行的修正,在基礎的犯罪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進行的修正同樣是肆意的;其次,責任修正理論動搖了故意與過失同構成要件行為之間的關系,③[P600]并且有動搖了“故意”這一概念的嫌疑;再次,責任修正理論同實際的、客觀的責任意識是完全對沖的,沒有認識到原因行為同結果行為之間的關聯性,更沒有注重對于原因行為本身的評價,其評價的對象還是在客觀上無責任能力下實施的、觸犯構成要件的行為本身;最后,對于這一責任修正理論在實定法(總則)與習慣法(與總則相關的判例)上,均找不到相對應的法規與判決的必要支持,這一所謂的對罪責的修正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嫌疑。③[P600]
筆者認為,上述對于責任修正理論的批評有一定道理,但該理論仍然可行。
第一,針對責任修正理論是對于犯罪論本體進行修正、基礎的犯罪構成與犯罪論尚未完結的情況下的修正這一質疑。筆者認為,這一批評對于維護犯罪論本體,特別是積極的犯罪構成的穩定而言,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是,筆者同樣認為,基于原因自由行為已經屬于犯罪論進入到責任是否予以排除的臨界點上進行考慮的問題,原因自由行為之前,所有的積極的犯罪構成均已基本完成且不存在明顯的修正之處(特別是故意和過失已經判斷完畢),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在原因自由行為之后的責任階層當中開始對犯罪構成進行必要的修正,相比較直接修正犯罪構成要件階層而言,是一種代價較小的對犯罪論階層的修正。且這種修正是基于對樸素的公平正義的理解而必然進行的一種結果,修正的階層越靠后,對犯罪論的影響自然也就越小,是對犯罪論特別是基礎的犯罪構成的“最小傷害”。
第二,針對動搖故意與過失概念本身的質疑。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將故意與過失作為優先階層判斷,并試圖在優先層級上建立與實行行為之間關聯的一種認識而產生的結果,對于故意或者說認識的一種例外性的承認,并不一定會動搖故意本身的概念,且從原因自由行為的概念上考慮,認識仍然可能在原因行為時無可爭議的存在,而這種認識與控制能力本身隨著原因行為的延展,雖然在客觀上消落,但在法律上仍可以被認為是行為人應當提高對自我的控制的一種要求,而認為應當加強對此種情況下行為人的自我監督。筆者認為,這并不會導致故意與過失這一概念的瓦解,相反會強化故意與過失概念當中,行為人的自我控制的意志屬性這一面,對故意與過失概念本身而言,反而是一種增強。
第三,針對后兩項質疑,筆者認為,對于批評責任修正理論仍然是處罰的構成要件行為本身這一問題,是沒有真正地認清原因自由行為的處罰,根據仍然是站在客觀主義刑法的立場之上。客觀主義刑法的立場之下,實行行為有故意規制與犯罪圈公示,這兩個重要的屬性。肆意地修正一個屬于客觀的、公示屬性的實行行為顯然不妥當。因此,建立在實行行為本身不能夠動搖的前提之下,修正相對主觀化較強的責任階層還是妥當的。而對于實定法依據的問題,德、日刑法典總則雖然可能在一定的時期之內缺乏足夠的依據,但這并不能夠成為阻卻責任理論本身的依據,相反,法律及判例大量地為原因自由行為提供可罰性依據,無論在構成要件層面上的修正,還是責任層面上的修正,其實均已不存在違反“罪刑法定”原則這一層面上的問題。
當然,對于修正責任階層,也有觀點提出了處罰原因自由行為的故意,需要具備“二重的故意”這一理據。⑽[P258~259]同樣,我國學者陳興良教授也指出“在存在雙重故意的情況下,即醉酒是故意的,對于結果發生也是故意的,認定為故意犯罪當然沒有問題。在存在雙重過失的情況下,即醉酒是過失的,對結果發生也是過失的,認定為過失犯罪也沒有問題。在故意醉酒后過失造成結果,或者過失醉酒后故意造成結果的情況,我認為應當根據對結果的心理態度分別認定為過失犯罪或者故意犯罪”。?[P183]但是,這樣一種認識卻可能存在著真正的、動搖故意概念的風險。換言之,在自陷無責任能力的前提之下,考慮著例外地承認存在責任能力,還有政策性和公正性的支持,雖然例外地修正了故意的概念,但基于對犯罪論本體的最小傷害還能夠為公眾所接受;因此,在已經過失地陷入到無責任能力的前提之下,即便因醉酒、精神疾病發作等原因導致對結果的追求的產生,倘若還以故意犯罪追究責任,顯然對于公民本身而言,已陷入到巨大的風險當中,公民本身在責任層面上盡到的可防范的義務只能存在于尚可控制自身意識之時,不可能強求公民在已喪失意識之后再產生對結果的不追求,這顯然不切實際。換言之,責任修正理論能夠被承認,不僅僅是因為其是對基礎的犯罪構成的“最小傷害”,其可罰性的原因還在于未能盡到防范自險無責任能力的發生,從而觸及了刑律上對于罪責的延伸條款而成立了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
三、我國刑法上的原因自由行為
我國《刑法》第18條第4款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這一條款被我國部分學者視為是我國刑法承認原因自由行為的法理之一。周光權教授曾特別指出:“醉酒的人通常是在某種程度上減弱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但并非完全喪失這種能力。行為人以酗酒壯膽作案,即便犯罪時辨認、控制能力降低,也必須受到懲處……如果行為人已經預見自己醉酒后會陷入喪失辨認、控制能力的病理性醉酒的境地,而故意飲酒,最后造成犯罪結果的,則應當根據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確定責任。”①[P171]
根據周光權教授對此部分的解讀可以發現,事實上我國《刑法》第18條第4款之規定存在兩個方面的探討。一是,我國刑法的立法者認為,行為人雖然醉酒當時喪失了一部分的辨識能力,但并未喪失全部的辨識能力,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的行為仍然有成立責任的可罰性空間,故而肯定了在醉酒狀況下行為人負刑事責任的能力。二是,當行為人自陷無責任能力之時,行為人的行為因原因自由行為而入罪,亦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不過,即便是按照對我國《刑法》第18條第4款之規定進行“兩面性”的解讀,亦可以發覺這樣一種解釋的方法其結果上是我國刑法系不承認原因自由行為的基本法理。換句話說,在“實行行為與責任同在”的語境下,原因自由行為理論本身的探討,在于首先確認行為人已不具備責任能力,在這一前提之下,進而才考慮以“原因自由行為”這樣的概念架構來尋求處罰的邏輯合理性。而我國《刑法》解決這一前提的方法是立法者首先肯定了在該前提之下,行為人具備責任能力,從而肯定承擔刑事責任。這一對《刑法》第18條第4款之解讀,也在事實上與我國刑法學界拋棄原因自由理論的呼聲不謀而合了,?[P49~57]其結果都是拒絕適用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邏輯框架。這樣一種解釋看似既不違反“實行行為與責任同在”的基礎處罰法理,更解決了原因自由行為之下的理論窘境,看似有極強的合理之處。
但這樣對我國《刑法》第18條第4款的“兩面性”解讀、甚至于在實質上是“拋棄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做法,在具體案例當中可能會導致顯失公正的情形發生。比如,行為人酒力很差,只喝一杯就會有嗜睡、乏力等嚴重的醉酒反應;而該行為人在攜帶其未成年的子女、參加某次聚會時,被不知道其攜帶了未成年子女的他人所惡作劇,在其飲料中倒入了一杯高度白酒,行為人喝了該飲料后果然出現醉酒反應,在回家的路上其未成年的子女恰巧無意落入水中,而此時行為人因醉酒竟躺在路旁呼呼大睡(即:在過失醉酒的狀況下發生的不作為犯罪)。在這一案例中,顯然惡作劇者適用間接正犯的理論有極大的不合適。且在我國《刑法》第18條第4款并未對“醉酒”限定在故意醉酒的前提之下,如果拒絕適用“原因自由行為”的理論,而以對我國《刑法》第18條第4款的錯誤的“兩面性”解讀的話,那么,其結果必然是行為人應當因不作為行為而明顯地構成故意殺人罪。但很顯然在整個的案例當中,行為人在正常狀況下根本不可能不想營救自己的子女,完全不可能放任子女死亡的結果發生。其不營救子女的原因,只能是因為醉酒導致的認識能力和意志能力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強行地要求行為人承擔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顯然有違社會的一般認識與樸素的公平正義觀。更何況,事實上在整個案例中,行為人實際的罪過,可能僅僅只是在攜帶未成年人參加聚會的情況下,喝下所謂的“飲料”時未能及時、審慎地察覺出該飲料可能暗含的酒精成分,造成了對未成年子女的管控能力下降。這樣一種主觀上的罪過,顯然具有意外事件的成分,至多只能停留于過失的層面之上。但由于行為人罪過的產生時,與實行行為完全分離,實行行為的產生完全位于主觀罪過之后,因此,在酒精辨識上的錯誤根本不能夠成為行為人主觀罪過為過失的處罰理由,這樣在“兩面性”的解讀之下,行為人實際上還是只能承擔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這很不合適。
筆者認為,想要解釋我國《刑法》第18條第4款之規定,依舊只能以原因自由行為理論本身來尋求解釋的空間。換言之,如果單純地將《刑法》第18條第4款認為是“兩面性”地承認了醉酒狀況下行為人在客觀上就具備責任能力,而將《刑法》第18條第4款作為法律的提示性規定進行理解,在實際的處罰邏輯上會常常陷入困境。因此,理解《刑法》第18條第4款之相關規定,只能是認為醉酒的人犯罪的,在我國刑法上例外地承認了具備責任能力。換言之,《刑法》第18條第4款在實質上并非是法律的提示性規定,我國法律也不能因此而被理解成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肯定行為人在客觀上、實際上就具備責任能力,而只能適用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認識,認定該條款系對責任能力的修正條款或者擬制條款。即采用“責任修正”的理論對本條款進行解讀。
采用“責任修正”的理論對《刑法》第18條第4款進行解讀具備一定的理論優勢,首先,它在客觀上保證了犯罪論體系的基本穩定,而使得犯罪論的運轉體系同社會實踐的一般認知相同,不使犯罪的認定與社會認知過分分離。其次,最大限度地保證了處罰的公正性,在理論上對于“實行行為如何同責任能力同在”的問題,在邏輯上進行了盡可能盡善盡美的安排。最后,采用“責任修正”的理論在我國更是避免了“無法律規定或先例”的問題,使得“責任修正”的理論在我國可以找到實定法上的依據,避免了原因自由行為在認定中對于“責任修正”理論找不到實定法上依據的尷尬。
四、以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看“醉駕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合理性探討
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意見(法發[2009]17號)》中指出:
“刑法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行為人明知酒后駕車違法、醉酒駕車會危害公共安全,卻無視法律醉酒駕車,特別是在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造成重大傷亡,說明行為人主觀上對持續發生的危害結果持放任態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對此類醉酒駕車造成重大傷亡的,應依法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2009年9月8日公布的兩起醉酒駕車犯罪案件中,被告人黎景全和被告人孫偉銘都是在嚴重醉酒狀態下駕車肇事,連續沖撞,造成重大傷亡。其中,黎景全駕車肇事后,不顧傷者及勸阻他的眾多村民的安危,繼續駕車行駛,致2人死亡,1人輕傷;孫偉銘長期無證駕駛,多次違反交通法規,在醉酒駕車與其他車輛追尾后,為逃逸繼續駕車超限速行駛,先后與4輛正常行駛的轎車相撞,造成4人死亡、1人重傷。被告人黎景全和被告人孫偉銘在醉酒駕車發生交通事故后,繼續駕車沖撞行駛,其主觀上對他人傷亡的危害結果明顯持放任態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二被告人的行為均已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根據該意見,我國刑事司法實務界確立了在醉駕導致嚴重車禍、造成公共安全和人員的重大損失的情形下,判處行為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審判趨勢。對于這一趨勢,理論界與司法實務界均作出了許多解釋。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方文軍曾撰文指出:
“行為人醉酒駕車肇事,一次性撞擊造成特別嚴重的傷亡后果,說明行為人醉駕程度嚴重,基本喪失對車輛的控制能力,且多屬于嚴重超速行駛,對公共安全的危險程度高,故應當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這種意見有一定合理性……《意見》以黎景全案和孫偉銘案作了說明。這兩個案例的被告人都是在嚴重醉酒狀態下駕車肇事,連續沖撞,造成重大傷亡,說明二人主觀上對他人傷亡的危害結果持放任態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故二人的行為均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當說,對于類似孫偉銘案、黎景全案這種有連續沖撞行為的案件,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基本形成共識……對于行為人高度醉酒后明顯控車能力不足,又有超速、逆行、闖紅燈等其他違法情節,肇事時一次性多點撞擊,造成重大傷亡的,鑒于這種情形下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放任心態的理由較充分,故可以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如果行為人醉酒后沒有明顯降低控車能力,肇事前也沒有其他交通違法情節,因一時疏忽而違章肇事,即使肇事時一次性有兩個或多個撞擊點,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的,也不宜簡單地為了體現嚴懲而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該認定為交通肇事罪的還是應當依法認定。”?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對于這一司法認定趨勢的解讀,仍然是基于對《刑法》第18條第4款之“兩面性”解讀之下的結果。換言之,論者仍然認為,行為人在醉酒的狀態下,仍然具備責任能力,故而確立了對其可罰的地位。可是,《意見》又指出:“一般情況下,醉酒駕車構成本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并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結果的發生,屬于間接故意犯罪,行為的主觀惡性與以制造事端為目的而惡意駕車撞人并造成重大傷亡后果的直接故意犯罪有所不同,因此,在決定刑罰時,也應當有所區別。此外,醉酒狀態下駕車,行為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實際有所減弱,量刑時也應酌情考慮。”?又在量刑的階段,似是而非地承認行為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實際有所減弱,如果按照“兩面性”解讀來看,顯然在統一性上難以令人滿意。
但是,基于前文已經論述了認為《刑法》第18條第4款“兩面性”認識的錯誤問題,在此可不做重復論述。但援引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而言,是否具備對于現在司法實踐操作的合理解讀?筆者的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具體來說,責任修正理論下的原因自由行為,可以承認的是行為人在自陷無責任能力的情況之下,對于進行實行行為時,例外地肯定了存在責任能力,而這種責任能力不必然一定在醉駕當中是故意或者過失。換言之,行為人在喝酒前已認識到自己有可能會在之后去鬧市區開車并喪失控車能力,仍然選擇自陷無能力的前提之下,考慮對其責任上非難是合理的(但非難的不能是喝酒行為本身),從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害后果,在事實上成為了行為人已喪失控車能力的重要證據,進而有承認行為人有危害公共安全故意(放任)之空間。而相反的一點是,倘若行為人在酒后尚未完全喪失控車能力,也就說明行為人尚具備一定的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適用原因自由行為,但對未造成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可以適用交通肇事的罰則,考慮行為人在主觀上仍有“過于自信”而成立的空間;或者根本沒有適用原因自由行為的必要,因為行為人的責任能力仍在承擔刑事責任能力的底線以上。
當然,我國學界也有學者提出觀點認為,可以參考德國模式在刑法分則當中就特別罪名承認原因自由行為理論。?[P109~114]但筆者認為,基于筆者前文已論述的就我國《刑法》第18條第4款的解讀而言,我國《刑法》在事實上,已有承認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特別條款,按照此認識來看,在分則當中再對原因自由行為理論進行明確,雖然有盡到法律提示性義務的需求,但多屬于“疊床架屋”,只需要加深對于現有條文的理解即可完成,而沒有在分則中重復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必要。
筆者認為,對于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基礎,應當按照責任模式(責任修正理論)進行理解。同時,我國《刑法》第18條第4款已可以被認為是承認原因自由行為的基礎,在此前提之下,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意見》的內容,同樣具備合理性。
注釋:
①周光權.刑法總論(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②胡印富.論原因自由行為[J].法制與社會,2011(12).
③克勞斯·洛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一卷)[M].王世洲,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④何慶仁.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困境與詮釋[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2).
⑤黃風.意大利刑法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⑥馮軍.德國刑法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⑦徐久生.瑞士聯邦刑法典[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
⑧克勞斯·洛克辛.德國最高法院判例刑法總論[M].何慶仁,蔡桂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⑨鐘連福.德國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為理論[J].德國研究,2005.
⑩山口厚.刑法總論(第二版)[M].付立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陳興良.規范刑法學(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梁云寶.犯罪論視域下的“原因自由行為”理論之否定[J].法學,2012(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意見[EB/OL].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網,(2010-02-10)[2018-01-20].http://www.court.gov.cn/shenpan-xiangqing-79.htm l
?方文軍.醉駕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條件[N].人民法院報,2014-05-14(6).
?于改之.論外國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為[J].山東大學學報,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