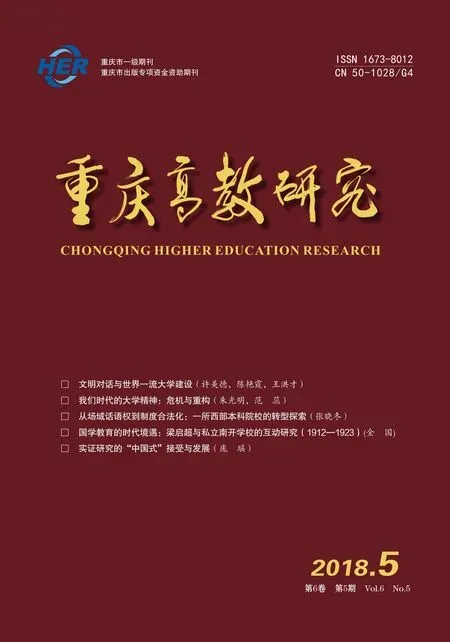國學教育的時代境遇:梁啟超與私立南開學校的互動研究(1912—1923)
金 國
(常州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院,常州 213164)
圍繞國學教育,20世紀20年代前后,梁啟超與私立南開學校①私立南開學校是嚴修、張伯苓所辦學校的統稱,包括私立南開中學、私立南開大學等。(下文簡稱“私立南開”)有過短暫的互動往來。于梁啟超而言,在與私立南開的互動中,寄托了其對傳統國學的“發明整理”;于私立南開而言,這一互動往來帶來了私立學校發展所需的“名人效應”。關于梁啟超與私立南開的互動,亦有諸多學者關注。《陶行知、梁啟超、張學良與南開學校》(夏嘉、應之,1987)、《梁啟超與南開》(王彥力,2013)等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梳理了梁啟超與私立南開的淵源。《梁啟超的私立大學夢》(尤小立,2014)更是聚焦梁啟超在私立南開創辦的文化學院,探討了文化學院創辦失敗的原因。盡管如此,本文亦有進一步探討、研究的空間與必要。
大體來說,本文主要聚焦或關注如下內容:一是梁啟超與私立南開學校的早期互動。現有成果中多將梁啟超與私立南開互動的起始時間定為1915年。事實上,在此之前,梁啟超就與嚴修有過短暫的接觸,雖然接觸時間不長,卻奠定了梁啟超在私立南開開展國學教育的良好基礎,而這些在現有研究成果中卻常被忽略。二是文化學院失敗原因的分析。現有成果雖有涉及失敗原因的分析,所得結論亦有一定的道理,但本文試圖將文化學院的創辦納入近代中國私立大學國學教育的時代背景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嘗試以新的視角,歸因文化學院何以創辦失敗。梁啟超與私立南開的互動雖然短暫,但富有深意,它是近代中國私立大學國學教育時代境遇的縮影與寫照。希望本文有助于豐富和深化對近代國學教育時代命運的理解和認知。
一、國學教育基礎的奠定:從私人情誼到學校教育的公共交往
現有成果中,一般提及梁啟超與私立南開的互動,要么是從1915年梁啟超“欲與學校方面多所聯系”[1]開始,要么是從1921年私立南開大學邀請梁啟超參加開學典禮算起。其實,梁啟超與私立南開頗有淵源,而這淵源始于私立南開的創始人嚴修、張伯苓與梁啟超的互動往來。查閱《嚴修年譜》,早在1912年10月12日,嚴修就曾拜訪梁啟超,但稍顯遺憾的是“談未數語,客絡繹而至,不能盡其辭,輒先辭出,異日再來”[2]281。此時的梁啟超剛剛結束長達14年的流亡生涯,從日本歸國不久。鑒于梁啟超的聲望,訪客絡繹不絕。這次見面是否為二人首次見面,不作考證,但從相關記載來看,對于因訪客太多而中途“夭折”的拜訪,嚴修也頗感遺憾。盡管如此,但梁啟超與私立南開的互動自此便拉開序幕。
梁啟超與私立南開的早期互動并非圍繞國學教育,而是基于與私立南開學校創始人嚴修、張伯苓之間的個人情誼而展開的私人交往互動。據《嚴修日記》《張伯苓年譜長編》記載,梁啟超與嚴修相識應早于張伯苓。因此,1915年1月20日,嚴修在北京北海為介紹梁啟超事,致函張伯苓[3]129。1 月30 日,嚴修約請梁啟超、張伯苓等,梁啟超相贈《歐洲戰役史》[2]332。自此,梁啟超與嚴修、張伯苓3人之間的互動交往日漸頻繁,私人情誼也日漸深厚。基于此,嚴修于1915年11月6日,致函梁啟超,力勸其戒“樗蒲之好”,乃因“吾國人崇拜先生者眾矣。演而以為仿,行而以為表,所系甚鉅也”[2]347-348。
隨著嚴修、張伯苓與梁啟超之間的私人情誼日趨熟稔,梁啟超與私立南開的互動漸由基于私人情誼的私人交往轉至學校發展的公共交往。梁啟超也逐漸參與到私立南開學校的辦學中來,并受邀參與私立南開學校的相關活動。1917年1月31日,梁啟超受邀到南開學校演講。演講中,梁啟超表達了對私立南開的贊許之情以及盼與南開互動的迫切愿望:“鄙人旅居津門時,即希令子弟來斯學校,并期來此參觀,以冀得悉貴校詳情,而與學校方面多所聯絡。蓋國中興學多年,明效尚未大著,使全國學校能悉如南開之盛名,則誠中國前途之大幸。職此之故,接洽之心,益為迫切。”與此同時,梁啟超也勉勵南開學子擔負起社會的期望:“現今國內對于貴校學生,甚希望大有作為于社會,并望貴校榮譽日與俱長。負斯責者,是在諸君。”[3]178對于此次演講,周恩來曾在《梁任公先生演說詞志》中有所記載,并給予高度評價,稱其演講“氣度雍容,言若金石,入人腦海”[3]179。顯然,梁啟超的演講深得南開學子的贊許。但是,較為可惜的是,這樣的演講在梁啟超與私立南開的早期互動中并不多見。對于忙于政治事務的梁啟超而言,走進學校演講也實為難得。
梁啟超之所以愿意接受邀請并在私立南開發表演講,或者說梁啟超之所以愿意與私立南開(包括與嚴修、張伯苓)保持互動,其原因概與如下因素有關:其一,基于共同的教育改革的認知。在教育改革的認知上,梁啟超與嚴修有共識。諸如在科舉改革上,梁啟超對嚴修的舉措頗為贊賞。1897年,時任貴州學政的嚴修奏請清政府開設“經濟特科”,梁啟超對此高度評價并贊許道:“此亦足稍新耳目,蓋實新政最初之起點。”[4]32在梁啟超看來,“興學校、養人才,以強中國,惟變科舉為第一義。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4]27。應該說,梁啟超與嚴修在科舉改革上的共識,為后來二人之間的往來互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其二,基于私立南開辦學質量的認可。私立南開因開辦中學而享有盛譽。蔡元培稱贊南開中學為“國中知名之學校”[5]。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克伯屈在其日記中稱張伯苓“是中國中學教育的先驅者,是一個國際知名的人”[3]191,從側面肯定了南開中學的辦學質量。鑒于對南開中學辦學質量的高度認可,梁啟超也樂于與私立南開展開互動,用梁啟超自己的話來說,“接洽之心,益為迫切”。也基于此,梁啟超將其子送入私立南開。
當然,作為互動的另一方,私立南開是樂見梁啟超參與到學校辦學中來的。私立學校的辦學經費主要來自于學費和社會捐助。因此,梁啟超與私立南開互動所帶來的“名人效應”是嚴修、張伯苓所需的辦學資源。借由“名人效應”,私立南開可獲得更多的社會關注,以利于吸引更多數量、更高質量的生源以及社會捐贈,確保辦學經費的穩定獲取。這在私立南開與梁啟超的后續互動中有更為具體的體現。
隨著張伯苓、嚴修先后赴美以及梁啟超啟程赴歐游歷,梁啟超與私立南開的早期互動告一段落。盡管如此,這一短暫的“互動交往史”卻為后來梁啟超試圖與私立南開合作,共同開辦國學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國學教育的展開:重心轉移與文化學院的籌建
自1918年12月梁啟超計劃赴歐至1920年3月歸國,一年有余的歐洲游歷對于梁啟超的人生經歷而言,具有轉折性意義。就社會活動重心來說,歐洲之旅強化了梁啟超由政治到對中國古典文化重新闡釋的重心轉移。
自1912年從日本歸國之后,梁啟超積極參與政治,并為袁世凱舉旗吶喊。因此,梁啟超深受袁世凱的賞識,繼而出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當袁世凱暴露稱帝野心,梁啟超繼而策劃武力討伐袁世凱。在此以后,梁啟超還出任過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等職。1917年11月,隨著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段祺瑞政府垮臺,梁啟超也隨即辭職。政潮中的浮沉,致使梁啟超萌生退隱官場政治之意。在游歷歐洲之前,梁啟超曾與友人懺悔“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并“相約以后決然放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6]562-563。時值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即將召開,梁啟超想乘此機會走出國門,一來“求一點學問”,二來打算將“我們的苦冤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以求“盡一二分國民責任”[7]。由此,梁啟超于1918年底前往歐洲考察。在歐洲一年有余的實地考察,使梁啟超的文化價值取向發生了重要變化,改變了其竭力引進西方思想文化的追求,轉而要以西方的辯證思維和科學研究方法重新詮釋中國古典文化,使中國文化在創新中走向現代[8]。因此,梁啟超社會活動的重心也發生了轉移,將“大半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古代的著述和講學上”[9]。
基于此,創辦大學也成為梁啟超在歐洲游歷過程中謀劃的歸國事項之一。1920年1月12日,張君勱致函黃溯初述及梁啟超的歸國計劃,其中就包括興辦大學事項。不過在張君勱看來,開辦大學實屬不易,“與其自辦大學,不如運動各省籌辦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輸精神,何必負辦學之責任乎”[6]576-577。如張君勱所言,20世紀20年代前后私立大學辦學并非易事,但從函件可知梁啟超對于辦學還是抱有相當之興趣和期待。梁啟超在赴歐之前曾被推舉為中國公學校長,旅歐歸來,曾有意接替校長王敬芳接管中國公學。但鑒于蔣百里的建議(認為梁啟超只宜任教,而不宜出任校長),以及中國公學辦學經費籌措的現實壓力,梁啟超最終放棄出任校長一職,而由張東蓀代理校長(名義校長為王敬芳)兼教務長[10]69。然而,梁啟超所寄托希望的中國公學辦學并不順利。接連爆發的風潮以及改制大學所需經費的短缺使得張東蓀對于中國公學的未來持悲觀態度,以致萌生退意[10]71-72。為此,梁啟超曾致函蔣百里、張東蓀等,表明對于風潮以及辦學的態度:“鄙意謂但使勉強可辦得下去,則此校斷不宜舍棄。搏沙(筆者注:王敬芳)無論如何總屬我輩,有事可以商量,最多再鬧風潮一兩次,愈鬧一次則阻力愈減一分,在吾輩持之以毅而已。”[6]603對于中國公學,梁啟超的態度是明確的,即希望盡最大努力維持辦學。在隨后的信函中,梁啟超進一步要求蔣百里等“要盡其力所能及,將此校辦好”[6]606。
在勉勵張君勱、蔣百里等在中國公學的繼續辦學之外,梁啟超也在試圖謀劃拓展國學教育“根據地”。因此,梁啟超強化了與私立南開的互動。1921年1月6日,梁啟超受邀頒發南開大學各組網球比賽優勝獎品以及足球第一隊獎[3]273。1921年9月1日,梁啟超應邀在南開演講大學之責任。9月12日,梁啟超受聘講授中國史,題為《中國歷史研究法》,并從該日始授課,課時為每周一、三、五下午四時至六時,且該課為文、理、商三科必修科目。據記載,第一次講課聽講約數百人之多,天津各校教員、學生來旁聽者頗眾[3]283-284。1921年11月21日,梁啟超在南開大學講演《市民與銀行》,就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停止兌現影響市面金融問題發表講話,除歷史課學生外,還有南開中學學生及校外人員聽講[3]288。
鑒于梁啟超與私立南開的密切往來以及迫于生計的現實考慮,1921年11月26日,蔣百里致函梁啟超談及與私立南開共同辦學的想法:“先生于近日內,何妨與南開確定一辦法,將先生之歷史講義亦歸為講座之一,而再約漱溟(筆者注:梁漱溟)也擔任一座,震(筆者注:蔣百里)與君勱(筆者注:張君勱)、東蓀(筆者注:張東蓀)每各擔一座,每座講演之期為四個月,文書口頭研究之期為六個月,因每座專為內部學生不收外人,則由學校酌送束脩,大約連買書費在內得萬六千金即足(若四人則更少矣)。若能公開,更添收一部聽講生則其效益宏矣。此事似尚輕而易舉,而為震與君勱當前目下之生活問題,亦可同時解決,豈非一舉數得。”[6]604
1921年12月,梁啟超致函張東蓀、蔣百里、舒新城等,報告與張伯苓所談在南開辦學事宜:“南開事絕無問題,伯苓之著急過于吾輩。每見必詢消息,我幾無以應對。昨日講義完了時,彼又來問君勱行止,我告以二十日內必到,彼重托設法,勿俾他處截留,我已允為盡力。此公辦事權限分明(我從數小事看得極清),我已與彼言,若將文科全部交我,我當負責任,彼歡欣鼓舞已極。對于此事當經一次吾黨會議后積極進行。百里所言立辦自由講座之說,我頗懷疑,鄙意先將此文科立定后再圖進取。我與伯苓商,本是明年暑假后計劃(但我輩若預備齊全,則寒假后進行一部分,亦未始不可),鄙意君勱當主任,百里、東蓀、宰平(筆者注:林宰平)各任一門(宰平未與切商,諒必可來)。能找到梁漱溟最佳,更輔之以我,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萬丈。我的計劃對于南開文科,原定預算外,由我設法為之歲募數千(諒不難辦到),則我輩對于此科之關系愈深,而基礎愈固(此科當然旁通理、商兩科,則根底植于全校矣)……南開文科辦三年后,令全國學校文史兩門教授皆仰本科供給,其所益不已多耶?”[6]606-607
從梁啟超的致函中可知張伯苓對于梁啟超的建議是“歡欣鼓舞”的。梁啟超與私立南開的合作對于雙方來說都有益處。一方面,對于梁啟超而言,可以通過借助南開文科培植國學人才。當然,這其中亦有借助國學人才的培養,壯大派系力量之意。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私立南開也希望借助梁啟超的盛名促進辦學。不管是嚴修抑或張伯苓均深知辦學的“名人效應”,因此在實際辦學過程中,尤其是在辦學經費的募捐過程中希望憑借梁啟超的聲望籌集更多辦學經費。諸如1921年10月30日,南開學校董事會召開會議,決定將來擬請梁啟超撰寫捐啟序言[3]287。事實上,梁啟超也為私立南開大學慷慨撰寫了《為南開大學勸捐啟》。
基于此,1922年1月17日,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蔣百里等就在南開大學籌建文化學院會晤張伯苓。當然,張伯苓是樂見其成的。按照籌建計劃,將由梁啟超自任文化學院院長,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梁啟超未能擔任中國公學校長的遺憾。當然,創建文化學院僅有理想是不行的,還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為此,梁啟超發表《為創辦文化學院事求助于國中同志》一文,謀求社會力量襄助辦學。關于成立文化學院的目的,梁啟超在該文中強調:“我國儒家之人生哲學,為陶養人格至善之鵠,全世界無論何國,無論何派之學說,未見其比,在今日有發揮光大之必要。”除此之外,梁啟超也述及了“現在學校制度有種種缺點”,并以此糾偏,實行半學校半書院的辦學組織形式。該文也明確了文化學院在“教導以外擬辦諸事”,包括:(1)整理重要古籍,校勘、訓譯、編訂,令盡人能讀且樂讀;(2)將舊籍或新著翻譯歐文;(2)編寫學校用之國史、國文及人生哲學教本等[6]633。
文化學院籌建計劃一經公布,引起了社會關注以及私立南開的高度重視。據《梁啟超年譜長編》記載:“先生創辦文化學院的計劃和征求贊助的啟事,遍達各處后,名流中復書慨愿捐助者頗不乏人,學生中因仰望而致書愿來受教者也大有人在。”[6]634《南開周刊》對此亦有報道:“自梁任公先生與學校方面共議在本校大學部成立東方文化研究院①關于梁啟超所籌建的辦學機構,目前有兩種不同的名稱,分別是東方文化研究院與文化學院。本文以梁啟超發表的《為創辦文化學院事求助于國中同志》一文中的名稱為準。后,一般有志東方學術研究者,莫不引頸高呼,期此世界獨一之研究院早成立;而學校方面半年來亦積極與梁任公籌劃一切,如募經常費,敦請當代大學者張君勱、蔣百里諸先生來院講學等,不遺余力。”[3]316
按照梁啟超的計劃,文化學院擬在1923年秋季開學。但遺憾的是,此項計劃最終未能實現,這對于私立南開以及20世紀20年代的國學教育而言,均是極大的損失。
三、無疾而終的國學教育:失敗原因
關于文化學院計劃最終夭折的原因,學界大體有兩種意見:一是認為“大概仍是經費的困難”[6]634;二是認為主要因為“梁啟超對于私立大學創辦的雄心很大,實缺乏確定的規劃”[11]。以上諸原因,固然是導致文化學院失敗的重要因素,但不管是因為經費的原因,抑或梁啟超的個人因素,均未將文化學院計劃的失敗放在近代私立大學創辦的時代背景以及國學教育的時代境遇層面上加以考察。
從文化學院公布的創辦計劃來看,授課者多是梁啟超的門生,因此師資應不是文化學院創辦面臨的最大問題。辦學經費的籌集才是創辦文化學院亟須考慮的核心議題。按計劃,文化學院所需最低限度經費包括:建筑費4萬元,購置圖書費2萬元,頭兩年經費共4萬元。盡管文化學院設在“南開大學新校址中,一切學課與南開保相當之聯絡關系”,但“文化學院簡單之建筑終不可少,即此亦非三、四萬不可”,可現實捐贈情況卻是,雖然響應者不乏其人,但“所得者尚不及十分之二也”[6]633-634。就20世紀20年代前后私立大學②本文所指私立大學是指國人自辦的私立專門以上學校,具體包括私立大學與私立專門學校,不含教會學校。創辦的時代背景而言,創辦者不僅需要發布創建計劃,還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籌措辦學經費。
從教育政策層面來說,政府雖鼓勵私立大學的創辦與發展,但除了在相關政策上支持和鼓勵外,并無辦學經費上的資助。在政府看來,私立大學(包括其他私立學校)雖然重要,但終究是扮演“輔助國立大學教育高等人才”[12]的角色。從社會背景來說,自袁世凱去世之后,派別紛爭、地方武裝沖突不斷。“在民國期間,舉凡地方性和地區性,以致全國規模的長期和短期的武裝沖突,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有數十百次之多。”[13]文化學院所在的平津地區,在1920—1922年就爆發了兩次大規模戰爭:一是1920年7月爆發的直皖戰爭;二是1922年4月爆發的直奉戰爭。兩次戰爭對于平津地區辦學生態的破壞是顯而易見的。再從社會民眾的公共精神來說,資助興學的社會氛圍尚未形成,也不利于私人辦學。這也是司徒雷登為什么能夠體諒張伯苓辦學不易的原因之所在,因為相比之下“美國人習慣于響應國內和國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張伯苓沒有這些優越條件”[14]。
基于此,想要創辦并維持私立學校的生存,則必然需要傾注大量的精力和時間,以獲取辦學資源。查閱1922—1923年的《梁啟超年譜長編》可知,在此期間梁啟超的精力并非完全用在文化學院的創辦上。除講學、著述、辦報外,中國公學依然是梁啟超著力關心的重要事項,所耗精力頗多。而與文化學院相關事項,在《梁啟超年譜長編》中則較少提及,可見文化學院并未成為梁啟超在此階段主要顧及的對象,或者說在諸多事務當中,文化學院的重要性尚未達到梁啟超所要著力考慮的程度。在中國公學因辦學經費岌岌可危的窘境之下,梁啟超難有精力顧及文化學院的創辦以及辦學經費的籌措。這是文化學院創辦失敗的重要原因,而現有成果中鮮有涉及。
當然,文化學院創辦失敗也與國學教育在近代中國私立大學中的時代境遇有關。與國立大學相比,私立大學在專業設置方面顯得更為務實,常會選擇一些實用性較強且易于就業的專業。如此專業設置也導致了私立大學中的國學教育處境堪憂。
就專業設置而言,私立高校中少有國學相關專業。以1918年為例,經政府立案認可的私立大學中,僅武昌私立中華大學設有“文科哲學門”,私立中國大學設有“文預科”[15]179-180。而立案認可的私立專門學校中尚未見國學相關專業的設立[15]187-190。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國立大學中,多有設置國學相關專業,諸如國立北京大學、山西大學、南京高師、武昌高師,以及后來成立的東南大學等均設有國學相關專業,清華學校還因辦有國學研究院而享有盛名。因有充足的辦學經費,梁啟超亦有底氣將清華國學院打造成國學重鎮[16]。因屬國立大學,東南大學也才有可能成為國學研究的重要陣地,其所創辦的《學衡》雜志影響深遠,以至成為學術流派。在私立大學的辦學中,國學并非其首選專業,尤其在私立大學初創時期更是如此。中國公學即是例證。中國公學除了辦理中學外,還“附設師范、理化、英文、算學等專科,以應時需”[17]。民國之后,在孫中山、黃興等支持下增設政、法、商專門科,三科之中,商科發展最好,直至1925年中國公學才添設哲學系。
此外,即使私立大學中設有國學相關專業,也多慘淡經營。私立大學中,專門以國學教育而著稱的當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下文簡稱“無錫國專”)。無錫國專創辦于20世紀20年代,其規模不大,但卻在當時的國學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無錫國專之所以能夠維持辦學,離不開施肇曾的大力資助,并承擔了無錫國專初創時期的全部開辦經費[18]。即便如此,隨著戰爭對辦學環境的破壞,以及辦學規模的擴大,無錫國專也曾瀕臨停辦。無錫國專如此,遑論其他私立大學。無錫國專實屬個案,普遍的情況卻是,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西學的大量輸入,傳統文化乃至國學教育招致巨大沖擊。在此背景下,私立大學中的國學教育在科系競爭中往往處于弱勢,常常讓位于實用性學科。以私立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創辦為例,鑒于校長林文慶“對于國學,提倡不遺余力”,廈門大學于1925年冬才開始著手籌辦國學研究院。1926年10月10日,國學研究院成立,校長林文慶親任院長,沈兼士、林語堂分任研究院主任、院總秘書,實際工作由沈兼士負責[19]。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創辦可謂轟動一時,然而不幸的是,卻因此爆發了學生風潮。關于風潮的緣起與經過,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具體討論,不過按照顧頡剛的說法,“廈大的風潮,起于理科與文科的傾軋,而成于魯迅先生的辭職”[20]。魯迅亦認為,在廈門大學“理科也很忌文科,正與北大一樣”[21]。在這場文科與理科的競爭中,最終以國學研究院停辦的方式結束。
四、結 語
不管是梁啟超在私立南開大學創辦的文化學院,抑或廈門大學成立的國學研究院,其實是近代中國私立大學中國學教育時代境遇的縮影與寫照,它受制于私立大學自身的性質與辦學模式,也受制于實用主義盛行的時代背景。當然,除此之外,國學教育在私立大學中的式微也與西學的引入而導致的學科分化密切相關。國學教育不再“是從整體性上掌握的一門學問”[22],而是嵌套在現代學科分類體系之中。具體來說,現代學科體系中的歷史、哲學、語言學、文學等在一定程度上也留存了傳統國學的相關內容。國學作為整體之學遭到了現代學科分類的挑戰,陳獨秀對此就曾批評道:“當今所謂國學大家,胡適之所長是哲學史,章太炎所長是歷史學和文字音韻學,羅叔蘊所長是金石考古學,王靜庵所長是文學。除這些學問外,我們實在不明白什么是國學。”[23]在此背景之下,依然有私立大學不單開設國學相關專業,甚至專門成立國學研究院。然而,鑒于私立大學本身的性質以及實用主義思潮的侵襲,國學教育在近代私立大學的命運可想而知。近代中國私立大學中的國學教育是近代國學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對私立大學中國學教育的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國學教育在近代社會的時代命運,也有助于為現代國學教育的開展提供歷史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