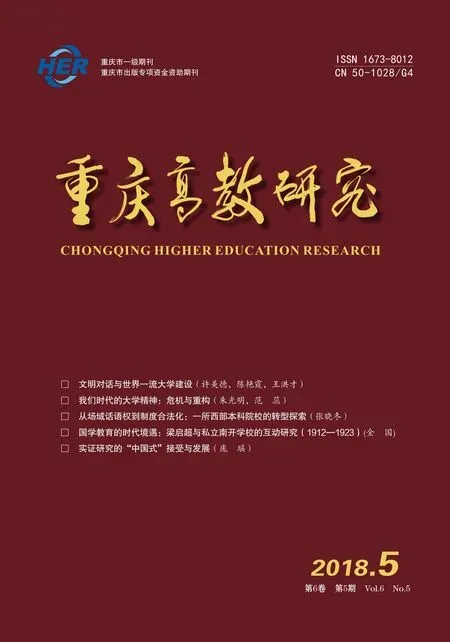我們時代的大學精神:危機與重構
——基于雅斯貝爾斯陶冶思想的啟發
朱光明,范 蕊
(安徽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所,合肥 230039)
卡爾·西奧多·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是一位視野極其寬廣的哲學家,也是一位極具人文情懷的教育思想家,他給人的印象是冷靜、孤傲,體現了精神貴族所特有的理性氣質。他的這種冷靜、甘于寂寞的學者風范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缺乏的。雅斯貝爾斯非常關注教育,他的陶冶思想及對人的精神狀況的關注,對我們當今時代的大學教育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雅斯貝爾斯陶冶觀中的精神貴族
(一)人是自由的精神存在
伽達默爾指出:“人類教化的一般本質就是使自身成為一個普遍的精神存在。”[1]“教化”就是德文中的“Bildung”,也被譯為“陶冶”,不僅有“教育”和“文化”之義,而且還是一種教育與文化的過程和產物,是“某種潛在的、內在的和尚未完成的東西變成現實的、外在的和確定的有機的自我實現過程”[2]。雅斯貝爾斯認為,陶冶是人的生活方式,是人的第二天性[3]105。陶冶活動是一種包含著對人類生存狀況思考的教育方式,它使得教育成為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并與人的成長緊密相連。最為關鍵的是,人的完整發展始終是陶冶最為關心的問題,因此,可以說,陶冶鑄造了人的本質,正是在陶冶的過程中,人的內在精神才被真正喚醒。
雅斯貝爾斯所生活的時代,人的精神面臨著政治和技術的雙重影響,從而出現了自由的危機。一方面是技術時代到來對人類生存的影響。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指出:“與技術時代的出現同時或更早,已經發生了一種奇特的世界現象,即精神和心理的衰退遍及世界……歐洲人通過科學和發現造成的技術革命,僅僅是精神災難的物質基礎和加速原因。”[4]158-159另一方面,納粹黨上臺之后,國家社會主義成為主流思想,個人的生存狀況與精神狀態在技術時代與高壓統治下陷入危機。他看到個人喪失了自由,淪為時代精神的附庸,成為達到某一目的的純粹手段。
雅斯貝爾斯認為自由是人的原初現實,人只有在意志的生存經驗中才能發現自由的意義,人雖不能證明自由,但卻能通過自身的意志行為實現自由[5]。他的生存學說意在強調海德格爾此在中人的精神體驗存在,并將這種精神體驗叫作生存。雅斯貝爾斯將精神視為大全的樣態之一。他認為,精神是構成人生活處境的要素之一,是理念的支撐和動力。人類因為其肉體而受到物質世界中各種條件的約束,但人類意識的不斷覺醒催生了一個超越物質世界有限性的精神世界的出現,人類便在這一精神世界中證明著自身的存在。雅斯貝爾斯將人看作一個精神存在,教育的關鍵在于對人內在精神的培育。同時,一個民族的教育方式,也決定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層次。
(二)理想人格之精神貴族
雅斯貝爾斯將人本身看作是精神存在,陶冶是通向精神世界的途徑。他指出,陶冶不是占有知識,而是習得精神內容的代名詞[3]104。
雅斯貝爾斯對平均化教育進行了批判,認為被平均化的知識導致了精神的貧乏①在《什么是教育》與《時代的精神狀況》兩本書中,雅斯貝爾斯都表達了對在教育平均化過程中群眾精神狀況的擔憂。例如,他在《時代的精神狀況》中寫到(136頁):“大多數人的教化傾向于迎合普通人的需要。精神因其散漫于群眾之中而衰亡,知識則由于被合理化地處理到一切淺薄的理解力均能接受的程度而貧困化了。”。在覺察到這一危機后,他提出“精神貴族”這一理想人格,而作為特殊學校的大學應該以培養這樣的人為目標。“精神貴族”作為時代的珍品,指的是擁有飽滿的精神狀態、出眾的個人能力且品德高尚的少數人。這些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人成為蕓蕓眾生實現自身價值的榜樣。在雅斯貝爾斯看來,進入大學學習的年輕人便是全國民眾中的精神貴族[3]147。這一理想人格既是對大學生成長的要求,也是對大學人才培養規格的一種見解。
精神的生活意味著不以某些外在或世俗的名利為目標,而是為了學術而學術。雖然雅斯貝爾斯這一思想被人認為帶有精英教育色彩,但卻符合布魯貝克所提出的高等教育認識論的觀點①布魯貝克在《高等教育哲學》的第一章“高深學問”中講到:強調認識論的人,在他們的高等教育哲學中趨向于把以“閑逸的好奇”這種精神追求作為目的(13頁)。。雅斯貝爾斯認為,大學應該兼顧職業學校、文化中心和研究機構三重身份[6]67。但是無論扮演何種角色,大學應該走的是一條實現精神生活與教學、研究并重的道路。
1.追求科學理性
人類對知識的迫切追求是自發的,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只有以對求知欲的滿足為終極目標,才會產生源源不斷的動力。雅斯貝爾斯指出,真理意識的培養需要人類后天的陶冶,探究的熱情由原始的知識引導,在持續的陶冶中,理性得以成長并逐漸突破自身的狹隘,消除一切狂熱。由此,人們不僅獲得了具有內涵的知識,還獲得了相應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就大學教育而言,理性的展現表現為一種基本科學態度的養成,只有將真理當成信仰,在研究中才能始終站在客觀的立場,以嚴謹的態度對待知識,這就要求培養一種批判的精神。因此,大學教育應該認識到,專業教育的功能不能局限于傳授知識與技能訓練,還在于它能夠啟發學生形成科學的態度。雅斯貝爾斯認為,好的大學教師必須成為研究者,科研和教學的結合是大學至高無上且不可替代的基本原則,比起單純地對學生進行知識的灌輸,教師真正要做的是引導學生接觸科學的精神,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真正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6]73。這一點不僅是在研究中,在對學生進行職業訓練時也應該得到體現,職業培養不是一種單純技能的傳授,而應該是學術和科學思維能力的培養與提升,培養的重點應該是活躍的頭腦、領會問題并提出疑問的能力以及方法的掌握[6]74。倘若大學以教授學生封閉的知識體系為目標,那么當知識體系不斷豐富、更新、淘汰時,學生所獲得的原本的框架就不再適用,此時學生的知識體系就會面臨崩塌的危機。
所以,在雅斯貝爾斯看來,大學并不是給學生某一固定的知識,也不應用某個特定的理論、價值觀去塑造學生的思想,而是應該倡導對真、善、美的探尋,用理性的態度去滋養學生的精神世界,其中哲學在這一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雅斯貝爾斯認為,哲學之思開啟了精神之眼,對真理探索這樣的精神活動離不開哲學式的思辨,哲學教學是歷史傳承必經的步驟,其功能是傳播真理[3]162。但他同時強調,哲學是不能教的,只能靠自身的悟性去參悟人生與世界[3]160,而大學教學的關鍵在于通過對哲學知識的傳授來使學生學會主動對日常生活進行哲學式的思考。反觀當今哲學在大學中的境況,哲學被劃分為獨立的學科,對哲學的學習更多的是一種對哲學史的回顧,其他與哲學相關性較小的專業則將哲學看成是一種如空中樓閣般虛無縹緲之物,將其束之高閣,甚至在以實用性、工具性的評判標準下,哲學作為無“用”之物而被忽略。
2.堅持自由交流
雅斯貝爾斯認為,大學應該給學者們提供條件使得他們能夠與同行的學者和學生一起開展直接的討論和交流[6]97。這種交流并不局限于形式,主要是一種精神的交流,但思想的表述和觀念的有效性都以真理為根基。交流不僅僅是研究成果的展示,抑或是觀點的宣講,而是一種以尊重為前提的相互質疑與溝通。偶爾發生辯論,但辯論中并不夾雜私人目的,而是一切以真理為最高標準。因此,雅斯貝爾斯在比較了3種教育形式(經院式教育、師徒式教育和蘇格拉底式教育)之后,認為理想中的大學教育方式應該是蘇格拉底式的。因為在蘇格拉底式教育方式中并不存在權威者抑或是主導者,教師與學生是兩個平等交流的主體,真理是唯一的權威,師生之間的精神交流在這樣的教育形式中才有實現的可能。真理本質上是可傳達的東西,真理源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只要真理是深刻的,它就是可傳達的,因而真理必然帶有交往的性質[5]。大學生作為成年人,可以而且理應為自己負責。大學要做的便是給學生以自由,自由使大學中的交往成為可能。
在雅斯貝爾斯看來,大學作為一個整體,永遠都不可能被一種精神統一起來,倘若只有一種思想大行其道,而其他人要么頗以為然要么漠不關心,或者是將思想上的分歧上升至權力派別的爭斗,最終以權斗的方式來實現一派對另一派的思想統治。諸如此類情況的出現是對大學精神致命的打擊。大學應該做的是為各種思想的闡發提供平等的機會,這是學術自由的表現。大學精神的活躍開始于各類圈子之間的精神交流。縱觀中國歷史,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造就了中國思想史上的高峰,諸子百家的思想成為后世思想的肇始。南宋時期的“鵝湖之會”,被稱為中國哲學史上一次堪稱典范的學術討論會,主客觀唯心之爭也給中國哲學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因此,大學中的每個人都應關注交往的方式,除隔絕外界的閉門造車導致思想上的狹隘之外,學術會議如果普遍表現為只闡述而不交流,那么這種無思想火花的交流方式也算不上精神的交往。
3.恪守學術精神
在雅斯貝爾斯看來,大學的功能是要成為一個時代的心智良知。大學與社會的關系在不斷變化,從開始大學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來維護學術自由,被稱為“象牙塔”,到后來社會對大學給予物質和法律上的支持,社會因素開始影響大學,大學開始履行為社會服務的職能。但雅斯貝爾斯指出,政治和社會兩個方面的影響足以改變大學的面目,大學敗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外界的大眾教育的壓力做毫無原則的妥協[6]176。雅斯貝爾斯提醒人們,大學對知識大門的失守是極其危險的事情,也是大學成為社會附庸的第一步。大學的精神和要義就是在知識整體觀念的指引之下,各學科之間彼此獨立而又相互合作。因此,從知識的整體性出發,某一固定的學科并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領域,大學應秉持同一性的理念,避免學科領域的割裂,促進跨學科合作以及知識的拓展與深化。除大學已有的知識以外,大學有責任吸納新的素材和技能,以統一的理念加以整合,大學不是封閉的領域,哪里出現知識的需求,大學就有責任在這個領域提煉知識和傳授知識。
在知識整體性的理念之下,大學應該堅守真理探究的理想,恪守學術精神。大學需要學術自由,但只有在學術目的和對真理的忠誠被考慮進來的地方,學術自由才會存在。也就是說,學術自由是以真理為標準的一種謹慎的態度而非不經思考的信口雌黃。以布迪厄的社會實踐邏輯來看,在學術場域,大學學術既需要以資本的形式生成,也需要學術資本促進學術的再生產,大學學術應遵循學術資本的生成邏輯。如果學術資本的生成缺乏理性的領導,學術資本就成為經濟利益和利潤的代名詞。在學術場域中,人們的習性可以被看作“學術慣習”,這一慣習表現為學術人身上的學術生存心態,源于學術場域不斷對學術人的形塑,學術人只有通過學術慣習的塑造和影響,才能在學術資本生成中產生合乎實踐理性的行為[7]。因此,大學要發揮時代精神的領袖作用,維護學術自由,維持學術高水平——這應是大學存在之根本。
二、我們時代大學精神的危機
我們時代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社會流行觀念在網絡技術和媒介助力下,深深影響了我們大學的精神狀態。
(一)快餐文化成為時代意識的精神此在
尼爾·波茲曼認為,文化交流中的媒介對于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質重心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影響[8]11。雅斯貝爾斯早就注意到他那個時代的印刷物——報紙在媒介宣傳中的主宰作用。人們通過快速瀏覽報紙代替了書籍等優秀閱讀材料,簡短的文章不再引起人們的沉思與反省,雅斯貝爾斯敏銳地觀察到社會讀物的改變,借此表達對社會普遍精神狀況的擔憂。僅信息載體的改變這一點就已經反映出公眾對信息接受能力的衰退與注意力的短暫。公眾注意力在獵奇心理的引導下,偏好于轟動而又新奇的事物。大眾傳播媒介為迎合市場需求而愈發變得形式大于內容,導致信息的加速更新,而公眾在信息的快速更迭中獲得短暫的滿足之后又轉而尋求新的刺激。
他這一洞察同樣適合我們今天的網絡閱讀。網絡以碎片化的內容、便捷的獲取方式成為繼報紙、電視等傳播媒介之后的又一新興媒介,加之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普及,使得淺閱讀成為一種普遍的閱讀方式,這也逐漸形成一種快餐式的文化。面對數以萬計的不加甄別的信息,很少有人花時間去弄清真假,更何況大多信息與己毫無干系,加上主流媒體對信息的選擇性推送(如微博“熱搜”的背后操作)使得公眾被迫接受片面化的信息,同時也被這些信息所占據和撫慰。這些共同導致了公眾記憶時間的短暫。加上刻意的用詞,信息內容極具誘導性,公眾輿論也成為一種新的暴力手段。公共網絡平臺的匿名評論區淪為情緒發泄之地,謾罵、惡意評論等充斥著戾氣的言論隨處可見。在那里,人們無須為自己的言論負責,詆毀所要付出的代價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甚至會掀起一場網絡罵戰,無謂地消耗許多時間和精力。
這種快餐式文化體現出一種娛樂至上的精神。在這種環境下,每個無名者都被當作工具,公眾生活演變成單純的娛樂,人們上一秒還在對惡性事件的發生感到憤憤不平,下一秒就在搞笑或惡搞視頻中遺忘了剛才的憤怒,人們習慣于這種情緒的快速轉換,最后以至于變得沒了情緒也沒了看法。這樣的生活狀態侵入大學校園后,對大學生的精神追求造成了消極的影響。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手機里的新奇事兒總是比專業知識有趣得多,而理想、追求等本為青年人談論的事情卻成為學生們的忌諱。學生們投身于虛擬的世界來佯裝自己的無暇思考,用“活在當下”來為自己的放縱懶散尋找合適的理由。
(二)消費主義成為社會發展的流行趨勢
雖然社會物質越來越豐富,但是受商業社會的刺激或誘惑,人們的消費欲望越來越強烈。根據鮑德里亞的總結,“消費社會”的特點是:在空洞的、大量的了解符號的基礎上,否定真相[9]12。同時他也認為,消費世紀是異化的世紀,是資本符號下整個加速了的生活力進程的結果[9]224。在這樣的消費社會中,商品邏輯得到普及,“消費”本身成為目的。加之營銷手段的不斷更新并在社會生活中引起潮流,導致了商品的符號化,即商品的真正價值不再是使用價值,而是它所象征的身份和地位。商品的符號象征為社會所認可,在狂熱的消費浪潮中,符號實現了其強大的社會統治力。在符號的迷惑下,人們拒絕認清消費的真相,個人存在也在這樣的符號消費過程中被消解,當消費者一味追求商品的虛假的符號價值來滿足他們虛假的需要時,在商品神性面前,消費者變成了溫順的奴隸[10]。
商業化在消費主義的推波助瀾下蔓延至教育領域,表現為人們對教育的消費建立在對它所具有的符號意義的消費之上,即教育本身具有了符號化的意味[10]。在消費社會里,似乎一切事物都可以被當作商品,教育也不例外。接受教育成為個人資本積累的一種手段,市場需要什么樣的教育,大學就提供什么樣的教育商品。商業化的思維模式把價值衡量標準引向了教育投資回報率,如專業的選擇以專業未來的收益為考量標準。滿足個人的身心發展、實現自我價值等這些教育最本質的價值被降格為教育的附庸。此外,教育真正受到追捧的主要原因是它為人們提供了社會游戲的入場券,教育變成一個身份象征的符號,人們在通過對各類教育的分級中標注了教育的符號價值。當接受教育只是等同于鍍金,那么教育將會貶值,當大學選擇放棄科學研究、拋棄全人教育而去迎合消費市場,將自己降格為職業培訓場所時,最后的結果不僅會導致教育質量的普遍下降,而且教育本質也將成為問題。
(三)現代犬儒主義成為主要的生存狀態
最近,人們常用一個網絡新詞“佛系”或“佛系青年”來描述現代青年人的一種精神狀態或態度,所謂“佛系”就是一種怎么都行、不大走心、看淡一切的活法和生活方式。這一詞語反映出現代犬儒主義的價值取向。犬儒主義原本是古希臘時期四大派別之一,安提西尼為創始人,第歐根尼為該學派的典型代表。在第歐根尼那里,對自我的肯定超越了一切解釋世界的合法性方式,這個個體存在的“佯狂”承認沒有任何權威是神圣的,也沒有任何權威本身是無懈可擊的[11]。不同于古代犬儒主義,現代犬儒主義獲得了與之前完全不同的意義,它是以“極致利己”為人生信念,以不相信人性善念為道德理念,以委曲求全、得過且過為處世態度的一種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和實踐話語[12]。因此,現代犬儒主義者一面表達著對現實社會價值標準的不滿,一面在認識到自身對現存標準的無能為力時又尋求與這些標準的妥協,表現出對一切標準、規則的附和與遵從,至于對錯,既不關心也不在乎,于是犬儒主義成為一種行為哲學。
現代犬儒主義對教育領域的影響體現在:第一,現代教育哲學犬儒化。這樣的教育哲學有能量而沒有深度,有目標而沒有目的,有理智而沒有理性,犧牲深度而求諸表面,貶低生命而乞靈于技術,從而廢黜了教育所具有的一切理想主義的品質,墮落于徹底的現實主義與功利主義[11]。教育哲學上的犬儒化可以看作是對高等教育認識論哲學的一種違背,是教育理想與社會現實矛盾沖突下的產物,即人們既認識到自己是一種自由的精神存在,同時又深感置身于社會之中自身力量的渺小無力。這種個人追求與社會標準的對立,造成了公眾對個人生存及教育價值的迷茫。第二,以這樣的哲學觀培養出來的學生是一個“庸人”,即一個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個只對物質和日常事務感興趣的人[13]143。學生在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匱乏下,通過對自身價值的否定、對自我人格的消解,導致道德意識的淡薄、甚至是道德虛無,出現一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以及將自己當作商品出賣的做法。此外,大學生拒絕對自身存在狀態進行思考,對未來的生活秉持悲觀消極的態度,不敢直面現實,而是采取一種逃避的方式,將自己的精神意識附著在外物的感官刺激之中,將自己的存在隱藏在眾人之中,避免主動在公眾場合發表意見,但對軼事、緋聞卻積極充當“吃瓜群眾”。在面對他人的指責與批判、個人又不得不凸顯時,則一貫采取防御態度,表現出一種不聽、不想、不反思的精神狀態。
三、我們時代大學精神的重構
雅斯貝爾斯對精神狀況的關注以及精神貴族這一理想人格的提出,對追求真理這一根本任務的重申等,給當下教育領域內的精神危機留下諸多啟示。“人不僅生存著,而且知道自己生存著。”[14]51人類對自身的認識是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對人的存在意義及主體性地位的意識,是自我精神覺醒的第一步。而大學對年輕一代的成長尤其是精神的培養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大學責任的重拾
教育不是一項孤軍奮戰就可以完成的任務,大學教育無法離開社會而獨立發展,現代大學走出“象牙塔”,開始發揮服務社會的職能。盡管這是大學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大學應在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保持警惕,把握好同市場的距離。不論是根據社會發展需要調整專業設置還是為社會生產提供相應人才,大學都應認識到服務社會并不等同于迎合大眾。大學的發展倘若完全交由社會決定,對社會發展給教育領域帶來的諸多負面影響視若無睹,那樣大學終將淪為經濟發展下的犧牲品。大學對一個人、一個民族人格的塑造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以至于雅斯貝爾斯認為教育比軍隊更重要。因此,在對社會風氣的糾正中,大學應該成為時代的精神領袖,以自治的態度、科學的嚴謹態度、哲學式的思辨去陶冶每個學生的精神,引領他們實現內在的自由。
大學應代表社會的良心,對“人”本質的追問、對什么是“真”的探討,不應在社會的洪流中被遺忘與拋棄。大學代表著知識的尊嚴,倘若大學一旦為政權所用,便會成為某種思想的宣傳陣地,那時思想的凋謝標志著大學靈魂的死亡。回顧二戰法西斯上臺之后,大學的那段經歷便可知道。作為社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在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愈益重要,愈發多元。如今,大學同社會、市場的關系日益密切,大學的培養目標要契合市場需要成為大學教育的發展趨勢。但無論大學扮演何種角色,對真理的追求、對人精神狀況的關切將成為大學最重要的職能。大學應是社會文化的引領者與矯正者,大學對大眾文化的一味迎合是大學自輕自賤的表現。
大學是精神貴族的聚集,它扛起人類精神的大旗,維護著人性的高貴。正如艾倫·布盧姆所言,在一個以理性為基礎的國家,大學是政體的廟堂,它致力于運用最純粹的理性,喚起人們心中的敬畏——一種自由而平等的人類聯合體當之無愧的敬畏[15]2。
(二)學術理想的堅守
“一所大學的性格是由它的教授們所決定的。每所大學都要仰仗它所招來的那一類人。”[6]147教育的純粹的精神氣質在教師身上的最主要體現就是廣大教師應當將教育當作自己的崇高使命而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看作是一種“規范性”活動,以及一種善的和道德的行為[16]。大學教師肩負著教育一代代青年人的使命,不同于初高中階段,教師扮演著等同于家長的角色。大學教師面對的是一群正值芳華、有想法、有激情的年輕人,正因為受教育者的這一特點,在教師與學生的關系上,就像尼采的師生倫理觀念,學生應該是教師這一創造者的伙伴,是一個共同的創造者。教師對于學生而言是“欄桿”而不是拐杖[17]。
大學教師更應該是一名富有創造力的研究者而不是單純的教書匠。大學教師作為學者的身份出現在大眾視野,這一形象的樹立也為教師的個人發展提供了平臺,大學因其多元化的特質使得不同風格的教師得以共存。一個教師的受歡迎程度應該與其學術水平、人格魅力以及道德修養等方面相關,而且越是在求真的時代,教師的受歡迎程度越應取決于他的學術能力。如果一名大學教師的“走紅”既不是因為他的學術能力,也不是因為他的個人魅力,而僅僅是外貌、時髦等原因時,這意味著學術理想在大學中的失落。當一名研究者淪落到靠外貌來吸引學生時,這將是一件極其可悲的事情。老子在《道德經》中告誡人們:“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唯獨真正的精神貴族才會培養出更多的精神貴族。教育者在社會風氣的不斷侵襲下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習慣于講授而不研究,甚至將學術看作是謀求職業前途的工具抑或是不費力地迎合學生喜好的工具而常常夸夸其談。連教育者自己都對自身使命產生懷疑時,那便是大學精神狀況最大的危機。因此,在這一浮躁的時代,教育者要做的是用自己的思考去引導學生對生活境況的反思,用自己的學術理想感染學生對自身精神狀況的關注。
(三)積極自由的追求
“自由”是人類探討的永恒話題,對“人”境遇的思考總是與“自由”聯系在一起。弗洛姆在對“自由”進行探究之后,將“自由”劃分為兩種: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大學生的普遍生活狀態可以用這兩種自由來說明:單純的沒有束縛的自由是一種消極自由,內在精神的無所依靠導致了對外在事物的依附與沉迷,學生處于一邊獲得自由一邊又急于逃避自由的矛盾之中;積極自由表現為個性的保持、思想的獨立以及理性的批判。
淺閱讀導致批判能力的普遍喪失,并不是沒有提出質疑的機會而是連思考都干脆放棄。書籍的備受冷落是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閱讀應是一個接受、判斷、交流、成長的過程,而這一過程需要通過書籍來實現。當今淺閱讀將閱讀簡化為單純的信息獲取,碎片化的閱讀方式導致思維上的不連貫和心態上的躁郁不安。真正的閱讀需要大塊的時間去咀嚼、去品味,以維持穩定的心理狀態去投入、去判斷。閱讀書籍,特別是經典書籍,被迫讓人冷靜下來,否則看到的僅僅是一堆文字符號,它需要智力去理解,需要時間去沉思。經典所蘊含的智慧結晶不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失去存在的價值,尤其是在人類所面臨的共同話題面前,前人的思考或許會是自身困境的答案。
“自由”不等于不被打擾,更不是隔離,若重拾經典是一種與前人的精神交流,那么現實世界中的交往也是積極自由實現的條件,個人精神的充實有時需要激烈的碰撞,堅持己見是一種畏懼改變的表現。只有向別人開放自己,將自己的想法展現在別人面前,在雙方的相互傾聽與思考當中,才能突破個人觀念中的狹隘,走向更加廣闊的天地。這樣的交往是一種自由的交往,即建立在彼此尊重、相互傾聽基礎上的溝通。一個積極自由的人往往擁有一種穩定的心理狀態,即使在面對外部沖擊時,依然能夠自持。正如《逍遙游》中所言,“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這便是獨立,與孤獨不同,個人精神的獨立往往體現在與人的交往之中。
四、結 語
無論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是扮演職業訓練場、教育科研基地抑或是其他新的角色,大學發展的落腳點始終在于“人”的發展。大學之所以被如此看重,正是因為大學教育本質上是對人精神的養護。大學因“精神貴族”的聚集而變得高貴,這一高貴閃爍著人類理性的光芒。就整個社會而言,年輕一代的精神狀態影響著整個社會的風氣,而年輕人精神的養成恰恰需要陶冶。一個社會若喪失了精神,任憑商業、媒體等因素對教育的浸染,使得學術商業化、功利化傾向嚴重,高等教育變成交易的商品,其最終會導致大眾文化的庸俗。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大學培養出的一代代青年始終與卓越無緣,更談不上超越。睿智的公眾是由學術和文化的蓬勃發展與熱烈討論造就的[13]143。面對我們時代的精神危機,只有大學肩負起對青年人精神滋養的使命,才能培養出一代代精神富足的“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