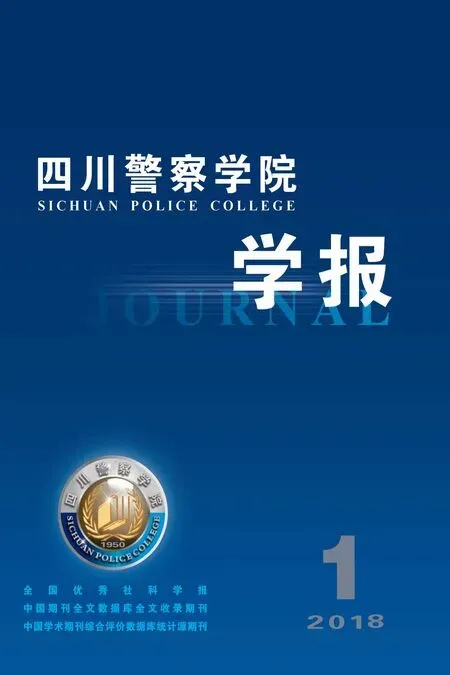犯罪性中止行為處理路徑新探
陶秋林
(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 100872)
中止行為被視為刑法的鼓勵行為[1],但是中止行為也可能造成損害,在某些情形下,中止行為會造成新的法益的損害,甚至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問題是新的法益損害應當如何被歸因與歸責?對于造成法益損害的中止行為如何處理?如下文案例:
案例一[2]:甲將A鎖在屋內并打開煤氣后,心生悔恨時發現別無他法,只能拿起石頭砸破了價值昂貴的防盜門,防止了A煤氣中毒死亡。甲的砸破門的行為如何處理?
案例二[3]:乙為報復B,故意放火欲燒其房屋,但是火勢漸兇之時怕事情鬧大,不得已只能通過損壞B的鄰居的墻壁撲滅了大火,B因此得救,乙損壞該鄰居墻壁的行為如何處理?
案例三[4]:丙以殺人的故意向C腿上注射毒劑,但因C不斷哀求而心生憐憫,立刻截斷了C的一條腿防止毒劑的蔓延,從而成功的避免了C的死亡。丙的截腿行為如何處理?
在討論犯罪性中止行為的處理之前,有必要對該行為的概念與構成先予以分析。
一、犯罪性中止行為的概念
中止行為既有效防止了實行行為更嚴重法益侵害結果的出現(有效的中止行為),又造成了新的法益損害(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如何認識這種現象,還值得考慮[5]。有學者指出,“行為人出于特定的犯罪故意實施犯罪行為,在犯罪行為實行終了后,法定犯罪結果發生前,行為人采取積極措施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行為造成了損害,其行為本身又符合另一犯罪的客觀構成要件”,宜將之稱為“中止行為之罪”[6]。但是筆者認為,其一,“中止行為之罪”的概念注意到了該行為的損害性,但是忽視了“中止性”才是該行為的本質;其二,對行為的定義應當符合行為的定性,“中止行為之罪”的定義隱喻該行為應當定性為犯罪行為,但是該中止行為存在適用正當化事由排除違法性或有責性的空間。應當認為,前一犯罪行為的實施者出于自動性采取的后一行為首先符合了中止行為的特征——中止意圖和中止有效性——故本質上屬于“中止行為”;但是該行為同時又造成了新的法益損害并且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因此具有“犯罪性”。所以將該行為定義為“犯罪性中止行為”更加科學——既能充分肯定該行為的有益性,又沒有忽略該行為的損害性。
行為人在實行行為終了后出于中止意圖實施了中止行為,但異于通常情況,此時的中止行為造成了新的法益損害并且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可稱之為“犯罪性中止行為”。而對這一特殊中止行為如何處理,學界存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觀點。對于現有理論的梳理與分析,有助于我們反思和構建更加合理的處理模式。現有涉及犯罪性中止行為有三種代表性學說:正當化事由說,獨立處罰說和中止犯競合說。
二、犯罪性中止行為處理的理論現狀及評析
(一)正當化事由說及其不足
考慮到行為人行為防止了更嚴重侵害結果的產生,所以當中止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時,無論是違法性還是有責性,都實質區別于通常的犯罪行為。有學者主張,犯罪性中止行為在符合相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被認定為正當行為。例如大谷實教授認為,“在中止行為本身構成犯罪的場合,如以使他人瓦斯中毒死亡的故意將他人房間充滿了瓦斯,但為了中止而毀壞玻璃窗時,這種行為當然構成獨立的犯罪。但有考慮緊急避險或缺乏期待可能性的余地”[7]。張明楷教授也指出,第一,中止行為本身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可以將其作為獨立的犯罪處理;第二,如果中止行為又符合正當化事由條件時(如可以認定避險行為或無期待可能性等),不認為是犯罪[8]。根據正當化事由說,犯罪性中止行為可以被正當化,即排除違法性(緊急避險)或者有責性(期待無可能)。
正當化事由說承認犯罪性中止具有適用正當化事由排除犯罪性的可能,充分評價了犯罪性中止行為之積極有益的一面。但是可以看出該理論對犯罪性中止行為與通常侵害法益的行為進行了同等考量,并沒有重視犯罪性中止行為的特殊性——若無自身實行行為對法益侵害的惹起則無中止之損害。所以該理論面臨兩點不足:第一,正因為前行為對法益侵害的惹起才存在后中止行為之“犯罪性”,所以在適用緊急避險規則之前,需要探討“自招他人危險”的法理,例如這樣的問題需要得到解答:自招他人的危險可以被認定為緊急避險嗎?正當化事由說不假思索的適用緊急避險,沒有充分回答上面的問題,無法讓受害者遭受的“雙重侵害”得到妥善處理;第二,正當化事由說認為存在期待可能性適用空間的主張,存在不足,因為該主張沒有深入分析期待可能性適用的條件,事實上,隨著刑法過失理論、歸責理論及風險理論的發展,期待可能性理論在當下刑法中適用的范圍越來越小、條件越來越嚴格,并非所有法益沖突的局面均可以被認定為沒有期待可能性,犯罪性中止行為時法益沖突并非極其強烈,更何況行為人自身就存在前實行行為之罪責,所以該行為能否期待可能性理論,本身就存在很大疑問。需要進一步探討。
(二)獨立處罰說及其缺陷
與正當化事由說對立的獨立處罰說主張,對行為人的實行行為單獨定罪后,對犯罪性中止行為也認定為犯罪處理,大塚仁教授認為,“中止行為本身符合其他罪的構成要件時,可以作為獨立犯罪被處罰”[9]。正如在案例二中,根據日本刑法第260條損壞建筑物的規定[10],為撲滅自己放的火而推翻了鄰人墻壁的行為,可以認定為損壞他人建筑物罪,此時判處行為人放火罪與損壞他人建筑物罪數罪并罰。
雖然前述正當化事由說主張對犯罪性中止行為“正當化”,因為沒有嚴格規范緊急避險和期待可能性的適用而有輕縱行為人之嫌,但是獨立處罰說對犯罪性中止行為徑行定罪處罰的理論,存在對行為人苛責過重和對有效中止行為未作評價的問題。其一,行為人真誠悔過并積極采取中止行為防止了侵害結果的發生,不得已損害了建筑物時卻被數罪并罰,是否過于強調了行為無價值而忽視了中止的有效性這一正當結果。換言之,對防止造成更加嚴重結果的中止行為定罪處罰的做法,使得行為人遭受過重之刑罰。其二,對造成損害的中止行為一律定罪處罰,實際上不當增加了構成中止行為的條件、提高了中止犯減免處罰的認定標準——中止行為不得造成法益損害否則即為犯罪行為。這種做法不但違法了第24條鼓勵行為人及時中止的刑法目的,而且會導致行為人在產生了中止意圖之時,預想到自己采取中止行為如果損害了另一法益卻可能構成新的犯罪而放棄中止行為的實施,不利于行為人自動回歸法秩序,不利于行為人及時中止其犯罪行為。
(三)中止犯競合說之不當
前面兩種觀點主要來自于日本學界,而源自德國競合論的中止犯競合論主張,“所謂中止犯與既遂犯的競合,是指犯罪人出于特定的犯意,實施預謀的犯罪行為,后來自動中止了業已實施的預備或實行行為,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了預期危害結果的發生,構成預謀的犯罪的中止犯,但同時卻又構成另一犯罪的既遂犯。”[11]根據該說可以認為,幾乎所有造成一定損害的犯罪中止,都是“中止犯與既遂犯的競合”。正如本文案例三:丙注射毒藥行為并及時中止,構成故意殺人罪之犯罪中止,為防止C死亡而截斷腿的行為被認定為故意傷害罪的既遂,成立二者之競合并按照吸收原則,最終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的犯罪中止。
然而,中止犯競合說存在不妥當之處。首先,中止犯競合說作為德國競合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立足于德國刑法的規定:對于犯罪中止免除處罰。但這樣就產生了對造成損害的犯罪中止也免除處罰的刑罰不均衡的問題,因此德國學者提出了中止犯的競合理論予以平衡。但是我國刑法規定,造成損害的中止犯,應當減輕處罰,沒有造成損害的中止犯,才應當免除處罰,刑法已經構建了合理的中止犯處罰模式,因此筆者認為,中止犯競合說不能適用于我國中止犯的案件,自然也不能適用于犯罪性中止行為的案件處理。其次,中止犯競合說運用競合理論解決了實行行為及其造成的損害的問題,但是犯罪性中止情形并非此實行行為及其損害的歸因歸責關系,而是犯罪性中止行為自身及其造成的損害結果如何處理的問題,中止犯競合說并沒能解決本文所探討的如何處理犯罪性中止行為這一難題。
由上可見,對犯罪性中止行為的處理,現有理論主張適用緊急避險或期待可能性予以正當化,沒有具體分析緊急避險的適用條件和探究期待可能性適用之“不可能”,未免過于“縱容”行為人;而徑行適用分則法條予以定罪處罰,又對行為人過于苛責,未免導致行為人欲行中止之時躊躇不前;競合理論因為不符合我國刑法具體規定而存在不當之處。所以,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取長補短、克服缺陷,探求犯罪性中止行為的處理新路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犯罪性中止行為的妥當處理
不可否認,犯罪性中止行為面臨法益沖突和衡量,如果符合相應條件則具有適用緊急避險排除違法性的空間,但是應當結合自招危險等理論進行合理適用。下文根據犯罪性中止行為的特殊性而具體分析緊急避險適用的條件,同時明確何種情形才能將其認定為避險行為。
(一)緊急避險的合理適用
我國刑法允許為了他人的法益而緊急避險,所以當行為人不得已實施了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損害了新的法益,但卻防止了實行行為侵害結果的發生,可以考慮緊急避險的適用。如果要將犯罪性中止行為認定為緊急避險,則不僅需要分析一般性的條件,而且也需要結合該行為的特殊性具體分析適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1.適用緊急避險的可能性。
(1)自招他人危險屬于“現實危險”嗎?值得討論的是,行為人的行為造成了他人面臨遭受損害的危險中,行為人能否實施緊急避險,也就是自招的針對他人危險的情形該如何處理?在德日刑法中,該情形被適用自招危險理論予以判斷是否構成緊急避險,但是在英美刑法中存在不同的觀點,“緊急避難不得是被辯護人創造的(應是自然力量),”[12]“脅迫不適用于一個人意圖或輕率地使自己處于很可能使自己受脅迫的狀態。”[13]正如學者所言,自招危險緊急避險存在這樣一種矛盾——實施行為導致危險情勢出現的可譴責性和自然留存的自我救助的避險權利[14]。筆者認為,犯罪性中止情形即屬自招他人危險的一種情形,因此該行為能否被認定為緊急避險也會面臨上述同樣的問題。
理論上自招危險可以分為自招本人的危險和自招他人的危險,對于自招危險,學界有否定說、肯定說、二分說和相當說等理論。當危險由本人導致的時候,有學者提出行為人具有可譴責的余地[15]。筆者不贊同這個觀點,正如張明楷教授主張,“對自己招致的針對他人的危險,應允許緊急避險”[16]。學者王駿也指出,行為人為了避免重罪自然要實施避險,因此自招他人危險符合緊急避險條件的情形,沒有理由不允許實行緊急避險[17]。因為首先,雖然他人危險的是由于行為人的故意或過失導致的,但是行為人為了防止出現更嚴重的損害結果,而采取損害另一較小法益的行為保全了更大法益的情形,應當肯定其結果價值,換言之,在自招危險情形中,也可以存在比犧牲法益更值得保護的保全利益[18];其次,行為人實施犯罪性中止行為時,避險目的是存在的。“避險目的包括以下兩個層次:一是直接目的是給第三人造成損害,將危險轉嫁……二是根本目的是避免危險的威脅”[19]。所以自招他人危險后,實施了“避免危險”的犯罪性中止行為人,存在損害較小法益以實現保全更大法益的避險目的;最后,犯罪性中止行為適用緊急避險,并不會“縱容”犯罪。因為自招他人危險的實行行為仍然會作為犯罪處理(中止犯);而行為人損害新的法益的行為,并非完全免除責任,可以要求行為人承擔賠償責任。
(2)緊急避險的另一個條件是危險正在發生。存在疑問的是,在行為人自身的實行行為創設了被害人法益處于受侵害之狀態,能否承認此狀態是緊急避險條件之一的“面臨緊迫的危險”?換言之,行為人創設之風險是否屬于緊急避險之危險源?
行為人采取的犯罪性中止行為,倘若確為面臨前行為造成的緊迫危險情境下而做出,那么符合條件應當被認定為緊急避險。原因有二,其一我國緊急避險之危險來源可以包括大自然的不可抗力,動物的侵害,人的行為等等,在犯罪性中止情況下,行為人先前之實行行為使得被害人的法益處于現實侵害或遭受侵害的危險之中,可以認為危險正在發生。其二,面臨緊迫的危險意味著一種現實的環境情勢,造成這一情勢的因素無需考慮[20]。筆者贊同這一觀點,犯罪性中止的案件中,行為人實行行為導致被害人法益處于危險之中,如果存在這樣一種“面臨緊迫的危險”的現實環境情勢,那么應當認為符合緊急避險的現實危險條件。
(3)如何認識犯罪性中止行為的“不得已”?在犯罪性中止案件中,行為人通常的辯解是別無他法,為了防止自己導致更嚴重的結果只能采取另一個具有損害性的行為。對于此種情形,可以做這樣的認識:所謂不得已,是指危險迫近刻不容緩,行為人除選擇采取緊急避險外,已無其他方法可以排除危險的情況,才可以實行避險[21]。行為人如果不這么做,最終的結局會是嚴重危害結果的發生,而這種結果無論是被害人還是行為人都難以承受的,犯罪性中止案件中也存在這樣一種“不得已”,行為人的辯解可以被采納。
(4)如何認識犯罪性中止行為人的避險意識?行為人的避險意識分為避險認識和避險意志。犯罪性中止行為人能夠認識到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面臨危險,避險認識很容易判斷。但是關于避險意志,部分學者仍然對行為人存在雙重“行為惡”而有所顧慮,認為行為人不但前實行行為已經違反刑法規范,而且后所實施的中止行為也背離了法秩序。但是此種觀點立足于事實性評價的層面而沒有運用刑法的規范性思維進行分析,存在不當之處。在不得已而實施犯罪性中止行為的情況中,行為人并非是可以形成反對動機而不為的“行為惡”,行為人為了避免他人的更重要法益遭受進一步損害而不惜“違法”也要中止自己的犯罪,已經表明行為人具有避險意志[22]。行為人的“決意”侵害新的法益,于法規范的遵守而言,不僅不是再一次的背離,而反而是行為人堅守法秩序的避險意識的體現。
(5)限度要件的判定具有特殊性。我國刑法通說認為,緊急避險的限度要件是避險行為沒有超過必須要限度,造成不應有的損害[23]。犯罪性中止案件也需要嚴格限制新法益的損害限度。根據學者彭文華的觀點,緊急避險限度的價值判斷,實質上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客觀判斷,即將造成的損害與避免的損害進行客觀比較,這往往是判斷緊急避險限度的前提和基礎;二是價值判斷,即綜合一切影響兩種損害的社會價值的主客觀因素,分別加以分析,并就緊急避險的整體社會價值作出最終判斷[24]。筆者贊同此觀點,在犯罪性中止案件中,需要綜合進行客觀判斷和價值判斷,對犯罪性中止行為的避險限度進行分析考量。如果犯罪性中止行為符合避險條件,那么可以適用緊急避險規則。而且將該行為認定為緊急避險,無論是基于現實需要、功利主義違法觀還是法秩序的規范指引角度考量都具有合理性。
2.適用緊急避險的合理性。
(1)犯罪性中止有適用緊急避險的現實需要。首先,行為人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大幅降低。犯罪性中止情形中,行為人意圖實施的行為是出于自動中止前行為造成的危險,已經表明行為人的違反法規范行為的自我糾正,而且其主觀惡性也大為降低。其次,行為人的中止行為雖然造成了新的法益的損害。但是因為緊急情況下別無他法,只有損害該法益才能避免更大損害的發生,社會危害性大大降低,正如學者William J.Chambliss和Thomas F.Courtless指出,“這樣的辯護總是成功的:在極端必要情況中(緊急避難和脅迫),行為違法了刑法是為了避免更大的公眾損害”[25];再則,行為人實施該行為是行為人中止意識的體現,也是行為人避險意識的外化,人身危險性也充分降低;最后,行為人損害了較小法益保全了更大法益,于被害人是有益的,于社會整體利益也是有益的。客觀上損失了較小法益而挽救了較大法益的情形,不應作為犯罪處理,符合緊急避險條件的應當排除其違法性。
(2)功利主義違法觀的提倡。規則功利主義在處理不同利益博弈情形時,并非固守某一條文而是強調選擇最恰當的條文規范予以適用[26]。正如案例一甲為救助躺在充滿煤氣房間中的乙而砸破窗戶的案例中,不得損害他人財產是《刑法》第275條的規定,但在緊急情況下,這項規則(不得損害他人財產)就讓位于《刑法》第21條規定的緊急避險,功利主義違法觀基于客觀情狀對行為和結果進行評價,符合刑法保護法益的目的。對符合條件的犯罪性中止行為適用緊急避險規則可以消除行為人實施中止行為的后顧之憂,不會因為害怕觸犯新罪而猶豫不決。
(3)法秩序的規范指引。雖然我國刑法分則規定了不同犯罪的構成要件,但是我國刑法總則也設定了完善的排除違法性或者有責性的規則。某些場合行為人的行為可能在要件上齊備,但是法規范并非僅僅是積極的成罪判斷,例外的,也會存在排除違法性或免責的規則[27]。德日刑法通過排除違法性或者排除有責性對該當行為予以正當化,英美刑法則提供這樣的排除犯罪性的路徑,即當特定案件中被告人實施了非法行為之后,如果聲稱存在更重要的正當事由(Justification)或辯解(Excuse),可以使得該行為合法化(Lawful)[28]。所以無論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建立了對表面違法而實質正當行為進行合法化的路徑。犯罪性中止行為雖然表面上符合構成要件,但如果符合避險條件則會實質性的屬于避險行為。而且需要重視的是,學者Komesar指出的法律實施是為了保護應該保護但是同時又極易受到侵害的對象,往往這種對象又傾向于引起人們的忽視[29]。如果對犯罪性中止行為成立避險的可能性不加考察,將導致法秩序指引功能缺失甚至是錯位。
(二)期待可能性免責的困境
除緊急避險的適用之外,期待可能性似乎也能為犯罪性中止行為之正當化提供理論支撐。事實上部分學者(如正當化事由論者)也支持這樣的觀點:犯罪性中止行為人可以被認為沒有期待可能性而排除其有責性。但具體研究期待可能性被限制適用這一外部環境,和犯罪性中止行為自身特性后,筆者認為應該否定期待可能性理論之于犯罪性中止案件的適用的做法。
而且如今無論德國學界還是實務界,都已經淡化了期待可能性理論的討論和適用[30]。德國諸多學者都列舉了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弊端:違反立法權、司法權的權力分配原則,違反刑法明確性原則和導致刑法軟弱化[31]。當然,如果存在生命法益無法衡量時的緊急避險情狀,期待可能性的適用可以得到肯定。日本刑法學界最初將該理論體系定位于超法規的責任阻卻事由,“然而,這一理論并未為司法實務界完全接受”[32]。現今期待可能性理論在日本的適用空間極大縮限,“最高法院盡管沒有明確拒絕期待可能性理論,但是也不是持積極態度。期待可能性理論的作用,之后再下級法院的判決中也逐漸減小”[33]。同時適用標準仍然沒有建立,何時使用、如何適用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平野龍一教授提出,“只在極為例外的場合才沒有上述的期待可能性”[34],主張對期待可能性理論的適用進行嚴格限制,而這一“極為例外”的場合,可以認為是生命法益沖突時緊急避險的情形。在英美法系存在獨特法庭規則,對行為人是否可以期待實施合法行為做出了精密的判斷。根據學者Laurie L.Levenson的觀點:普通法系僅僅允許脅迫之類的完全免責辯護事由存在于死亡威脅或者嚴重的身體傷害的威脅下,或者同樣嚴重的威脅發生在緊急避難情形中[35]。雖然英美法系沒有提出類似期待可能性的理論,但在英美刑法中存在一種有效的法庭上的事實反訴(Factual Counterclaim),該反訴的主要內容即為行為人沒有可選擇的合法行為[36]。所以筆者認為,英美刑法對被告人處于緊急避難和脅迫情形下的處理,存在與德日刑法處理無期待可能性之相同的情形。正如學者George E.Dix和M.Michael Sharlot指出的,當一個案件確實出現了,被認為在緊急情形下或者脅迫的過程中,迫于生命受到威脅而且當時沒有合理和合法行為實現的可能性時,刑事懲罰法將會越過這個案件,刑法在這類案件中對可憐的被告人保持了沉默(In Silence)[37]。更深入探討的話,被告人只有在極其苛刻的條件下——例如被人用槍逼迫運輸毒品,因為當時無論如何也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合法行為(Law-abiding),所以犯罪行為可以被法律承認為正當(Justice)[38]。所以英美刑法同樣將“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合法行為”這一免責事由嚴格限定在生命法益沖突的情形。我國臺灣地區學者柯耀程和林鈺雄將其體系定位于調節性刑罰恕免事由,而不作為普遍性的刑罰恕免事由[39]。應當認為這一定位是科學的。臺灣實務界也對期待可能性理論的適用保持謹慎態度,對于“期待可能性理論”并沒有直接排除,然而也沒有在判例中出現過[40]。所以臺灣學者認為,無期待可能性只能在罕見個案中以“調節性刑罰恕免事由”出現,正如林山田教授指出的,期待可能性理論充其量只能夠被當作一個節制原則[41],而非一般性免責事由。
筆者對我國期待可能性研究的熱點指數和研究關注度指數進行了統計。我國學者于1979年發表了第一篇描述“期待可能性”理論的論文[42],結合圖1可知,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期待可能性理論成為學術新研究點,之后從2002年到2008年,期待可能性理論的研究迅猛發展(從年發文量20篇到年發文量140篇左右)。結合圖2主題為“期待可能性”文獻發表年度分布圖可知,在此期間該主題的論文發表數量直線上升,直到2011-2012年(修正案八發布)達到論文發表數量最高峰(年發文量接近150篇)。 與此同時,期待可能性理論研究熱度自2009年達到最高峰后開始了持續平緩下降,發表論文數量自2012年后也逐漸降低,說明期待可能性理論研究回歸理性,或者說期待可能性理論相關問題經過了充分研究已經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成熟的觀點。例如在期待可能性理論的適用上,大部分學者均主張應該嚴格限制該理論的適用[43]。

圖1 我國“期待可能性”研究關注度指數圖
例如有學者指出,只有窮盡刑法規范(包括司法解釋)明文規定的所有出罪事由及其類規定以及刑法理論中定型的出罪事由之后,認為仍然有出罪必要,才能考慮適用期待不可能的標準進行判斷[44]。謝望原教授指出,“刑法第16條包含了心理受強制從而失去意志自由的情形。換言之,《刑法》第16條包含了除緊急避險外所有無期待可能性的情形”[45]。亦即僅存在于刑法中緊急避險和不可抗力以及意外事件之中,嚴格限制通過期待可能性對行為人進行免責的空間。類似的觀點還有,期待可能性并不能在任何法益沖突的情況中存在,而只能在生命法益間的緊急避險中得以適用[46],期待可能性理論在緊急避險中的適用范圍被進一步縮限。結合上述理論,筆者贊同期待可能性只能在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和極其罕見的生命法益間的緊急避險中得以適用,犯罪性中止行為既不屬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從通常情形中分析而非個別特例),將之與極其罕見的生命法益間的緊急避險相比,犯罪性中止行為也是處于更為緩和的情境中,所以行為人實施的犯罪性中止行為不能被認為存在期待不可能。
結合上述分析可知,各國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的適用處于不斷限縮狀態,期待可能性被認為只能適用于極其罕見的生命法益沖突的緊急避險案件中,犯罪性中止案件并不能適用期待可能性理論排除有責性。但是犯罪性中止行為具有適用緊急避險排除違法性的可能。當行為人面臨已經出現的緊迫危險,不得已只能通過實施犯罪行中止行為損害較小法益保護更大法益時,如果沒有超過必要限度符合緊急避險條件的,更宜適用緊急避險規則排除行為的違法性。

圖2 我國“期待可能性”文獻發表年度分布圖
四、結論與處理模式
(一)犯罪性中止行為處理的結論
綜合全文論述可知,期待可能性理論不適用于犯罪性中止行為的處理。“刑罰之根本性的正當性基礎,在于它有助于阻止將來對于應受保護的利益的侵害”[47]。所以如果行為人為了中止犯罪而不得不實施侵害其他法益的行為,仍然可以適用緊急避險排除違法性。除此之外,其他的犯罪性中止情形應當按照相應犯罪定罪處罰。
(二)犯罪性中止行為處理模式
犯罪性中止行為探討的前提是:其一,行為人出于防止結果發生的中止意思而實施中止行為;其二,中止行為客觀上足以防止既遂結果的發生;其三,以消除實行行為所引起的既遂危險或預備行為所引起的實行危險為內容;其四,以既遂結果的未發生為終極形態[48]。與其同時,犯罪性中止行為因其特殊性——以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中止行為中止實行行為之罪。所以其處理模式也與普通的中止犯有所不同:
1.符合緊急避險的情形。當犯罪性中止行為符合緊急避險的情形,適用緊急避險原則。行為人的犯罪性中止行為構成緊急避險時,對于造成的新的法益損害,行為人應承擔民事責任。
此時整個案件的處理模式是,行為人實行行為及其損害結果構成相應犯罪的犯罪中止,行為人中止行為符合緊急避險,但是對于中止行為造成的新的法益損害,承擔民事責任,最后模式為:中止犯+民事責任。
2.不符合緊急避險的情形。當犯罪性中止行為不符合緊急避險情形,應認定該行為構成犯罪。正如無正當辯解(正當化事由)的違法且有責的行為 “刑罰注定了是正當的,立法者必須規定此時適用什么和何種刑罰,司法者應當施加這種適當的懲罰”[49]。當犯罪性中止行為沒有滿足緊急避險的條件時,應當根據行為人實施犯罪性中止行為時的罪過心理認定構成相應的犯罪。
(1)過失犯罪。William Dienstein教授指出,犯罪是這么兩種情形:違反了刑法禁止的行為,以及沒有盡到刑法要求的注意[50]。當行為人實施了不謹慎的犯罪性中止行為且分則規定須處罰時,因為行為人的中止行為不符合緊急避險,而又符合相應過失犯罪的構成要件,應當對犯罪性中止定罪處罰。此時整個案件的處理模式是,行為人實行行為及其損害結果構成相應犯罪的犯罪中止,行為人中止行為構成過失犯罪,最后模式為:“中止犯+過失犯罪=數罪并罰”。
(2)故意犯罪。因為行為人的中止行為不符合緊急避險,但符合了相應故意犯罪的構成要件,應當對犯罪性中止行為定罪處罰。此時整個案件的處理模式是,行為人實行行為及其損害結果構成相應犯罪的犯罪中止,行為人中止行為構成故意犯罪,最后模式為:“中止犯+故意犯罪=數罪并罰”。

圖3 犯罪性中止行為的處理模式
[1]李立眾.犯罪未完成形態適用[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2:160.
[2][日]大谷實.刑法講義總論[M].黎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403.
[3][日]大塚仁.刑法概說(總論)[M].馮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224.
[4]馬克昌.犯罪通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482.
[5]張明楷.未遂犯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成文堂,1998:433.
[6]高立勇.中止行為之罪及其處理[J].人民檢察,2010,(8):61.
[7][日]大谷實.刑法講義總論[M].黎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403.
[8]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371.
[9][日]大塚仁.刑法概說(總論)[M].馮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224.
[10]日本刑法典[M].張明楷,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95.
[11]馬克昌.犯罪通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482.
[12]D.Scott Broyles,Criminal Law in the USA,Netherland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p.74.
[13]Kate E.Bloch&Kevin C.McMunigal,Criminal law:A Contemporary Approach:Cases,Statutes,and Problems,New York:Aspen Publishers,2005,p.546.
[14]張 寶,侯華生.論自招危險之緊急避險的判斷路徑[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3,(9):32.
[15]謝雄偉.自招危險的緊急避險適用研究[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2):285.
[16]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219.
[17]王 駿.刑法中的正當化事由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202-203.
[18]黎 宏.緊急避險法律性質研究[J].清華法學,2007,(1):52.
[19]陳興良.刑法總論精釋(第二版)[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289.
[20]陳 璇.自招危險情形下的緊急避險問題研究[J].江西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7,(1):71-72.
[21]謝望原.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2):124.
[22]時延安.大陸與臺灣違法論之比較研究——以違法性的本質為中心[J].刑法論叢,2013,(1):486.
[23]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40.
[24]彭文華.緊急避險限度的適當性標準[J].法學,2013,(3):102.
[25]William J.Chambliss,Thomas F.Courtless,Criminal Law,Criminology,and Criminal Justice:A Casebook,California: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92,p.152.
[26]周 祥.規則功利主義違法觀之提倡刑法學派之爭視角的展開[J].清華法學,2013,(1):36.
[27]王 鋼.法外空間及其范圍側重刑法的考察[J].中外法學,2015,(6):1560.
[28]Joan McCord and John H.Laub,Contemporary Masters in Criminology,New York:Plenum Press,1995,p.154.
[29]Neil K.Komesar,Law’s Limits:The Rule of Law and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Righ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87.
[30]劉仁文.刑法的結構與視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61.
[31]方 鵬.德日期待可能性理論比較研究——以超法規責任阻卻事由為視角[J].金陵法律評論,2008,(1):58-59.
[32][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總論[M].王昭武,劉明祥,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64.
[33]黎 宏.日本刑法精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27.
[34][日]平野龍一.刑法的基礎[M].黎宏,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113.
[35]Laurie L.Levenson,The Glannon Guide to Criminal Law:Learning Criminal Law Through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and Analysis(3rd ed.),New York:Wolters Kluwer Law&Business,2012,p.361.
[36]Paul H.Robinson&Michael T.Cahill,Criminal Law (2nd ed.),New York:Wolters Kluwer Law&Business,2012,p.283.
[37]George E.Dix and M.Michael Sharlot,Criminal Law:Cases and Materials (4th ed.),Saint Paul: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6,p.739-741.
[38]Charles P.Nemeth,Criminal Law,Upper Saddle River:Prentice Hall,2004,p.426
[39]柯耀程.刑法概論[M].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7:264-267;林鈺雄.新刑法總則[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90.
[40]張麗卿.期待可能性在臺灣刑法的適用[J].金陵法律評論,2008,(1):118.
[41]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262.
[42]王維平.所謂安樂死的必要條件被認為不是安樂死的刑事案例[J].環球法律評論,1979,(2).
[43]陳興良.期待可能性的體系性地位——以罪責構造的變動為線索的考察[J].中國法學,2008,(5):88-90.
[44]方 鵬.出罪事由的體系和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1:246.
[45]謝望原,季理華.見危不救罪的期待可能性問題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2):78.
[46]劉艷紅.調節性刑罰恕免事由: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功能定位[J].中國法學,2009,(4):120.
[47][德]萊茵荷德·齊佩利烏斯.法哲學[M].金振豹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280.
[48]陳興良,江 溯.判例刑法教程(總則篇)[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136.
[49]William R.Buckley and Cathy J.Okrent,Torts&Personal Injury Law (3rd ed.),New York:Thomson Delmar Learning,2004,p.11.
[50]Joshua Dressler,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 (4th ed.),Danvers:Matthew Bender&Company,2006,p.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