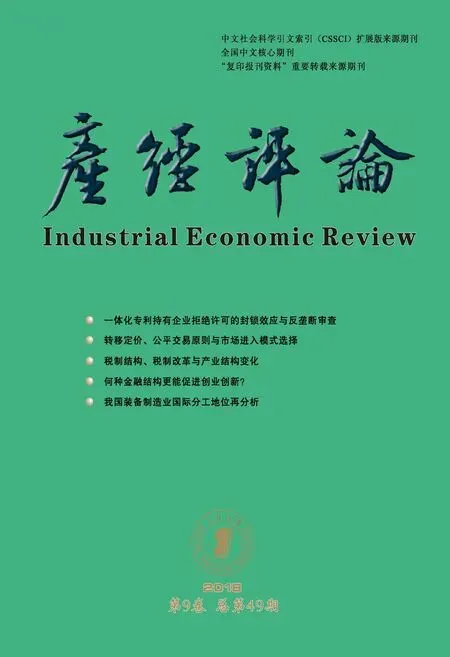文化產業發展助力區域經濟增長的雙重效應
——基于中國省際面板的經驗數據
一 引 言
近些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顯現出一個新特點,即逐步從邊緣產業過渡到支柱產業,且有望成為我國新的經濟增長點(陸立新,2009)[1]。從文化產業的綜合發展情況來看,截至2015年底,納入統計范圍的全國文化單位達29.91萬個,同比增加1.17萬個;從業人員達229.44萬人,同比增加25.42萬人①數據來源:2016年《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從文化產業與經濟之間的關系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2015年我國文化產業實現增加值25829億元,比上年增長7.9%,增速比當期GDP增速高1.5個百分點;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3.82%,比上年提高0.06個百分點;文化產業對當年GDP的整體貢獻高達4.6%。并且,大部分地區文化產業的增長速度高于經濟整體的增長速度,成為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創業的重要產業,以及推動產業結構優化的朝陽產業②數據來源:2016年《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
已有文獻從實證角度探討文化產業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且得到基本一致的結論:文化產業發展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兩者之間呈現正向的線性關系。但既有文獻忽視了文化產業本身的產業結構特征。實際上,文化產業包含的產品通常是較為“高級”的產品,如體育、娛樂、網絡游戲等屬于衣食住行之外的產品,從產業結構角度而言處于產業鏈的中后端。在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居民對于此類產品的需求較低,但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時,居民對此類產品的消費相應增加。Beyers(2002)[2]利用美國的數據證實了上述特征的存在,發現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在文化產品和服務上的支出顯著增加。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可能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上升而愈加顯著,兩者之間很可能是非線性關系。另一方面,Kibbe et al.(1980)[3]較早地探討了文化產業的外溢性問題,并發現這種外溢性對經濟發展具有很大貢獻。而國內既有文獻在探討文化產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普遍忽視了這一特征,這可能導致無法正確判斷兩者的關系或低估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實際影響。
為了檢驗上述特征,重新厘清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形式,本文利用2000-2014的省際面板數據,在非線性視角和空間計量模型的設定下,再次探討了文化產業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發現,文化產業發展確實有助于區域經濟增長,但這種作用是非線性的,即隨著經濟的發展,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同時,得益于文化產業的外溢性特征,當地文化產業的發展對于鄰近省份的經濟增長也具有一定促進作用。深入分析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助力作用和作用形式對于重新認識兩者的關系具有積極意義。
本文的貢獻主要有兩點:一是從產業結構特征入手,發現并檢驗了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呈現出非線性特征,這對于正確理解兩者的關系至關重要;二是借助空間計量模型,檢驗了文化產業促進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發現了文化產業的另一特征。研究立足于實體經濟層面,對我國當前經濟增長提供了有益啟示。一方面,當前我國經濟增速由高速增長過渡到中高速增長,面臨一定下行壓力,并將有可能長時期處于“L”型底部。另一方面,過去我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固定資產投資,而當前我國經濟逐漸轉向高質量發展,改革進入深水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穩金融降杠桿都在進行之中,那么在經濟增速放緩、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點在哪里?實證結果表明,文化產業作為產業鏈的中后端產業,屬于新興的朝陽產業,而產業中心向下游移動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李懷亮等,2010)[4],因此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文化產業覆蓋領域包括體育、娛樂、影視等,大力支持和發展文化產業,有助于促進消費升級,對產業結構升級也具有重要意義(王晗,2016)[5]。
本文后續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文獻綜述,第三部分為模型設定、數據說明,第四部分為實證檢驗及分析,最后為結論及相應的政策啟示。
二 文獻綜述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文化產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探討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相較而言,國外學者更早探討文化產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且普遍認為文化產業發展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例如,Power(2002)[6]利用瑞典的數據實證發現,瑞典文化產業發展對該國經濟增長和勞動力市場穩定均發揮了有益作用;Scott(2004)[7]通過多個國家的數據發現,文化產業發展為收入增加和就業增加貢獻了很大的份額,因而對于政府而言,發展文化產業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
隨著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國內學者也越來越關注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文獻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文獻主要以某一省份或區域為研究范圍來檢驗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王林和顧江(2009)[8]以長三角地區為例,發現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康燦華和戴鈺(2011)[9]則以湖南省為研究對象,發現文化產業發展確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湖南省整體的文化產業發展水平卻比較低。吳承忠與李臻(2013)[10]以長株潭三個城市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了文化產業的核心層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周晶和曹麥(2015)[11]則以北京市為例,發現創意文化產業對國民就業和經濟增長均存在促進作用。闞大學和吳連菊(2015)[12]以江西省為研究對象,從文化的人力資本和產業資本兩個維度檢驗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結果發現文化產業雖然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但經濟意義卻并不顯著,未來具備成長的潛力。
第二類文獻則主要從全國層面來探討文化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1)以全國層面的時間序列數據展開研究,如蔡旺春(2010)[13]探討了文化產業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發現文化產業可以帶動其他關聯產業的發展,并最終起到促進整體經濟增長的作用。李增福和劉萬琪(2011)[14]采用全國的時間序列數據,結合灰色關聯法,分別探討文化產業的核心層、外圈層和相關層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發現文化產業的相關層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馬駿(2014)[15]也利用全國的時間序列數據,發現文化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長期的影響。(2)以全國省際層面的數據展開研究,如石衛東和衛曉星(2013)[16]利用PLS模型檢驗了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帶動作用和間接促進作用,并發現間接作用主要在于提升了人力資本水平、促進了技術創新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杜傳忠等(2014)[17]利用全國30個省的面板數據,發現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確具有促進作用,但區域之間存在差異,東部地區主要通過提升人力資本等間接作用促進經濟增長,而中西部地區主要通過文化產業增加值的直接作用拉動經濟增長。
上述文獻主要圍繞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展開了實證研究,所涉及的方法包括灰色關聯法、投入產出法以及計量研究等。但是大部分文獻在實證檢驗兩者的關系時,采用線性模型,即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不隨時間變化的,這一假定可能與實際情況不符。正如Beyers(2002)[2]研究指出的那樣,美國的消費模式已經發生變化,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居民在文化產品和服務上的支出顯著增加。實際上,從產業結構角度而言,文化產業由邊緣產業逐漸過渡到支柱產業,本身就意味著它在經濟體中的地位和貢獻有所改變。所以兩者之間為線性關系的初始設定可能存在一定問題,或者并不能完全捕捉到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隨時間變化的趨勢和作用。其次,與其他產業不同的是,文化產業發展具有較強的空間溢出效應(Kibbe,1980)[3],王晗(2016)[5]的研究更是認為文化產業的間接效應實際上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文化產業發展的溢出效應意味著一個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可能會對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帶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現有文獻并沒有從空間角度對這一問題作更為深入的探討,忽視這一特征有可能會低估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考慮到現有文獻缺乏對文化產業的產業結構特征作深入分析的實際情況,為了更加準確地研究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本文做了如下改進:首先,將研究范圍從某一特定區域擴大到全國范圍,采用中國2000-2014年省際面板數據來探討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省際面板數據整體樣本量相對于某一省份或者區域的數據而言更加豐富,從而得到的結論也更為全面可信。其次,本文設定了線性模型和非線性模型同時檢驗文化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實證發現,雖然采用線性模型得到的基本結論與既有文獻結論相一致,但是當采用非線性模型時,文化產業發展的一次項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卻不顯著或者不穩定,這意味著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雖然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這種促進作用具有非線性特征,即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隨著發展水平的上升而越來越大,但是線性模型卻無法捕捉出這種特征,從而忽視了文化產業在不同階段下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差異。最后,本文探討了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基于嵌套權重的空間模型,發現文化產業發展不僅有助于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同時對周邊地區的經濟增長也具有顯著促進作用。此外,本文同時采用GDP和人均GDP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度量指標,并結合雙固定效應模型,分別進行了全國和分區域的檢驗,以保證估計結果的穩健性。
三 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一)非線性模型設定
為探討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本文設定如下基準線性面板模型:
lngdpit=β0+β1lncultureit+β2lninvestit+β3tradeit+β4lneducateit+β5lnconsumptionit+β6urbanit+ui+λt+εit
(1)
式(1)中,被解釋變量gdpit表示省份i在時期t的經濟發展水平,本文分別采用GDP和人均GDP來度量。核心解釋變量cultureit表示當地的文化產業發展水平,用各地區文化事業費進行衡量,文化事業費越多意味著當地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越高。其他控制變量,investit表示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用各省歷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度表示;tradeit表示當地的貿易水平,用各省歷年進出口貿易總額表示;educateit表示當地的人力資本水平,用各省歷年教育經費收入水平衡量;consumptionit表示當地居民消費水平;urbanit表示當地的城市化水平。為了使估計結果更加有效,本文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以排除地區間不可觀測因素和時間因素對估計結果的影響。其中ui表示省份i不隨時間變化的不可觀測因素,λt表示時間因素,εit表示誤差項。上述各項數據均作對數處理,這樣既使得數據更加平穩,也有助于緩解數據的共線性和異方差性,從而使得估計結果穩健。
上述模型假定了文化產業發展與地區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線性關系。但這種設定可能存在一定的問題,因為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可能呈現出不同的作用,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可能更加顯著。鑒于此,對模型(1)進行了如下拓展,以便檢驗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非線性作用。
lngdpit=β0+β1lncultureit+β2lncultureit2+β3lninvestit+β4tradeit+β5lneducateit+β6lnconsumptionit+β7urbanit+ui+λt+εit
(2)
與式(1)不同的是,式(2)引入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平方項,以檢驗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非線性影響。除平方項以外,模型的其他變量含義及處理方式與式(1)一致。平方項的引入改變了文化產業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初始模型設定,使得兩者之間的作用關系截然不同。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文化產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越顯著,本文預期β2?0,同時,根據β1可以將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分為三種情況,具體如下。

圖2 不同β1取值下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影響的差異
如圖2所示,在預期β2?0的情況下,若β1?0或=0,則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存在加速效應,即文化發展水平越高,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越大(圖2中a、b);若β10,則意味著文化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先抑制、后改善的“U”型作用(圖2中c)。
(二)空間計量模型設定及權重矩陣
上述模型(1)與(2)所反映的均為文化產業發展對于當地經濟水平的促進作用,但由于文化產業具有較強的空間溢出效應,上述模型無法檢驗文化產業的溢出作用。鑒于此,本文設定了如下模型:
(3)
式(3)中,被解釋變量lngdpit為經濟發展水平;ρWgdpit表示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滯后項,ρ為空間滯后項的系數,W為權重矩陣;Xj, it既包含解釋變量,又包含控制變量,與前文設定一致;Dcultureitθ表示文化產業發展水平的空間滯后,D為對應的權重矩陣,θ為解釋變量空間滯后項的系數;μi為地區固定效應,γt為時間效應;λEVit為擾動項的空間滯后,E為擾動項的空間權重矩陣,λ為對應的系數*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盡管在描述中分別采用了W、D、E來表示權重矩陣,但并不意味著這些權重矩陣一定是不相同的,在本文的研究中,W=D=E,因此在后面的分析中,統一采用W來表示。。該模型為空間計量一般模型,通常有以下具體形式:
(1)若λ=0,則以上模型為空間杜賓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簡稱SDM);
(2)若λ=0且θ=0,則以上模型退化為空間自回歸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on Model,簡稱SAR);
(3)若ρ=0且θ=0,則上述模型退化為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簡稱SEM)。
空間自回歸模型和空間誤差模型都用于度量被解釋變量的空間關聯效應,但前者是指被解釋變量存在直接的空間關聯,后者則表示被解釋變量的空間關聯是由模型之外的因素即誤差項的關聯產生的。空間杜賓模型則不僅能夠度量被解釋變量的空間關聯效應,還能刻畫解釋變量的空間效應。在本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度量經濟發展水平在省份之間的關聯效應(對應于系數ρ或λ),另一方面還需研究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是否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對應于Dcultureit的相應系數)。所以主要采用空間杜賓模型(SDM)作為主要回歸模型。但為了觀察結果的穩健性,同時也報告了空間自回歸模型(SAR)和空間向量誤差模型(SEM)的回歸結果。
進行空間計量的前提是準確度量區域間的空間關系,這需要借助空間權重矩陣。一般而言,空間權重矩陣的形式如下所示,其中,n表示截面的個數,主對角元素w11=w22=…wnn=0(同一區域的距離為0),非主對角元素wij(i≠j)則度量了個體i與j的空間相關關系。

通常空間權重矩陣有鄰接權重、地理權重、經濟距離權重和嵌套權重等多種形式。基于鄰接關系、地理距離和經濟距離的空間權重矩陣均為對稱矩陣,這意味著省份A對省份B的影響與省份B對省份A的影響是一致的。而實際情況未必如此,比如北京對河北的溢出效應與河北對北京的溢出效應就可能是非對稱的。鑒于此,本文的權重矩陣主要采用同時基于鄰接關系和經濟距離的嵌套權重矩陣。關于鄰接權重矩陣、經濟距離矩陣及嵌套權重矩陣的設定方法如下:

表1 權重矩陣的定義、涵義及元素計算方法
(三)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
本文數據涵蓋2000-2014年中國29個省級區域*由于在空間計量的設定下,海南省屬于一個島嶼省份,并沒有直接接壤的省份,故將其剔除。的面板數據,其中西藏由于多項數據缺失故將其剔除。GDP、人均GDP、固定資產投資水平、貿易發展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均來自2001-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各地區文化事業費來自2001-2015年《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為了排除價格因素的干擾,GDP、人均GDP、固定資產投資水平、消費水平以2000年為基期采用相應指數進行了處理,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貿易發展水平以及人力資本水平則使用剔除通貨膨脹的方法進行了相應處理。另有極少數缺失數據,本文采用均值法進行了替代,以保證數據的完整性。本文涉及的各變量中英文名稱及其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 回歸結果及經濟分析
(一)線性視角回歸結果
1.全樣本回歸結果
首先根據模型(1)的設定,對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線性檢驗,檢驗結果列于表3。其中,列(1)、(3)、(5)被解釋變量為GDP,列(2)、(4)、(6)被解釋變量為人均GDP。為了考察結果的穩健性且便于比較,在列(1)、(2)中并未引入控制變量,同時也只控制了省份固定效應,并未控制時間固定效應;在列(3)、(4)中加入控制變量,列(5)、(6)則在上述基礎上繼續引入時間固定效應。實證結果顯示,不管采取哪種實證模型,文化產業發展對GDP和人均GDP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具體而言,文化產業發展增長1個百分點,GDP增長0.0328個百分點,人均GDP增長0.0117個百分點。
從控制變量來看,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貿易、人力資本水平和消費水平對當地經濟水平的提升也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但從絕對量的貢獻上來看,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對整體經濟的促進作用非常顯著,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經濟增長對投資存在較為嚴重的依賴現象。在引入控制變量的雙固定效應模型下,回歸模型的R2達到99%以上,說明整個模型引入的解釋變量可以用來解釋地區經濟增長的99%,不存在嚴重遺漏解釋變量的問題。
注:括號中的為標準誤;*、**、***分別表示顯著性水平為10%、5%和1%。
2.分區域檢驗結果
為了保證結果的穩健性,同時便于比較不同地區之間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差異,將上述樣本劃分為東、中、西三大區域進行檢驗。2011年新區域分類標準將全國分為東部沿海、中部、東北和西部地區四大區域*四大區域的劃分標準:http://www.yqjgdj.gov.cn/art/2014/2/28/art_10246_422856.html。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河北省、山東省、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臺灣省、廣東省、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海南省。中部地區包括: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陜西省、甘肅省、青海省、重慶市、四川省、西藏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貴州省、云南省。,由于東北地區只有三個省份,中部地區只有六個省份,本文將東北地區和中部地區合在一起進行處理。分區域回歸結果見表4。其中列(1)-(3)以GDP作為被解釋變量,列(4)-(6)以人均GDP作為被解釋變量,所有實證模型均為加入控制變量的雙固定效應模型。實證結果進一步表明,不管是在東部、中部及東北還是西部,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從控制變量上來看,盡管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對經濟促進作用非常顯著,但呈現出典型的區域差異,其中西部地區對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的依賴程度最為嚴重。此外,消費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三個地區均非常顯著,但進出口貿易總額、人力資本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在各區域之間發揮的作用也不盡相同,其中人力資本水平在中部及東北地區的作用最小。各個模型的R2均達到99%以上,說明模型擬合優度良好,不存在嚴重的變量遺漏問題。

表4 分區域回歸結果
注:括號中為T統計量; *、**、***分別表示顯著性水平為10%、5%和1%。
(二)非線性視角回歸結果
1.全樣本回歸結果
基于全國樣本和分區域樣本的線性回歸結果充分說明,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這一結論與之前文獻得到的結論相一致。但是,一個重要問題是,上述實證均以線性模型作為基本假定,隱含著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變的,這可能與現實并不符合。因為在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階段,其對文化產業的需求水平也越高,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可能更大。鑒于此,在論證了模型(1)的線性關系之后,重新反思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特征,并對模型(2)進行實證檢驗。在模型(2)中,引入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平方項,以考察兩者之間存在的非線性關系,回歸結果見表5。

表5 非線性視角的基準回歸結果
注:括號中為T統計量; *、**、***分別表示顯著性水平為10%、5%和1%。
從表5可見,在引入了文化產業發展的二次項之后,二次項的回歸系數在各種設定下均顯著為正。并且,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次項系數并不顯著,這意味著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雖然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但其作用形式并非線性,而是體現出非線性特征。二次項系數顯著大于0,與預期的結果一致。這說明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會隨著發展水平的上升逐漸增大,呈現出指數形式的“加速”特征。由于在大部分模型下,文化產業的一次項系數并不顯著,本文傾向于認為其系數β1=0。因此,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的促進作用類似于“U”型曲線的右半部分,即先平穩后“加速階段”(可參見圖2-b)。在引入二次項之后,其他控制變量固定資產投資水平、進出口貿易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仍然顯著為正,與基準線性回歸結果保持一致。這進一步說明本文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2.分區域回歸結果
為了保證結果的穩健性,利用模型(2)進一步檢驗了分區域下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6。結果發現,主要解釋變量文化產業發展的二次項仍然顯著為正,這進一步證實了前述結論。而一次項的回歸系數或者不顯著,或者不穩定。在控制變量中,發現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且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負相關,即越是經濟發展落后的地區(西部),其對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程度越深。總體而言,分區域的回歸結果進一步論證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非線性的。

表6 非線性視角下的分區域檢驗
注:括號中為T統計量; *、**、***分別表示顯著性水平為10%、5%和1%。
(三)文化產業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檢驗
接下來利用空間計量模型實證檢驗文化產業的空間溢出效應,實證結果見表7。其中列(1)-(3)被解釋變量為GDP,列(4)-(6)被解釋變量為人均GDP,列(1)和列(4)采用空間自回歸(SAR)模型,列(2)和列(5)采用空間誤差向量(SEM)模型,列(3)和列(6)采用空間杜賓(SDM)模型。研究結果顯示,ρ與λ均大于0,意味著經濟發展呈現空間正向關聯,即相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也越高,這實際上揭示了我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集聚特征。關注文化產業的空間溢出項Wculture,在兩種經濟指標測度下,Wculture不僅大于0,且在5%水平上顯著,這說明文化產業發展不僅對經濟增長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文化產業的水平項系數顯著為正),也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文化產業的空間項系數顯著為正)。即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僅能夠促進當地經濟水平的發展,同時有助于鄰近且經濟水平接近地區的經濟發展。控制變量影響與之前的分析并沒有多大出入,因此在這里不再贅述。

表7 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
注:括號中為T統計量; *、**、***分別表示顯著性水平為10%、5%和1%。
表7的實證結果表明,既有研究可能低估了文化產業發展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空間計量經濟學引入之前,經濟學研究很少關注各省經濟之間的互動,且通常假設各省的變量相互獨立。如果放松上述假定,即認為各省的變量之間并不是獨立的,那么OLS的估計就是有偏的。事實上,各省經濟之間有著廣泛的聯系,而且通常而言距離越近的省份之間聯系越密切,省份之間的獨立性假定很難成立。因此,本文在考慮鄰近且經濟水平相近地區之間存在互動聯系的基礎上設定模型,發現文化產業存在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
五 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利用2000-2014中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從多個角度測度了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發現前者對后者呈現出非線性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兩大特征。本文研究說明,忽視文化產業發展影響經濟的非線性特征和空間溢出效應,則不僅難以深入分析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形式,同時也會低估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對文化的需求存在差異,文化產業發展反過來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可能存在非線性特征,同時文化產業具有較強的空間溢出性,但既有文獻研究中忽略了上述特征。因此,本文在非線性模型和空間計量模型的設定下,重新探討了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是:(1)文化產業發展對GDP和人均GDP增長均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其作用形式體現為非線性特征。具體而言,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加速促進作用,即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隨著經濟發展而加大。分區域視角下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加速作用依然穩健,且區域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2)文化產業發展不僅能夠直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對地理位置鄰近且經濟水平接近的省份也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即“空間溢出”效應,這意味著發展文化產業可以帶來正的外部效應。(3)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出顯著的空間正向關聯,這意味我國經濟分布體現出集聚特征。(4)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占據重要地位,在落后的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對固定資產投資依賴程度最大。
當前我國經濟正進入增速放緩的“新常態”,在產業轉型升級,經濟逐漸轉向結構優化和高質量,追求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約束條件下,加大對文化產業的投資不僅可以直接提升經濟增長質量,還可以拉動大眾的“文化消費”傾向,促進消費升級,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文化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加速促進作用可能正是來源于此。同時,文化產業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疊加作用。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應當大力并持續發展文化產業,提高文化產品的供給能力,以充分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提速”和“空間溢出”作用。
[1] 陸立新. 文化產業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J]. 統計與決策, 2009, (20): 86-87.
[2] Beyers, W. B.. Culture, Servic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TheServiceIndustriesJournal, 2002, 22(1): 4-43.
[3] Kibbe, B. D., Waskin, L. S., Conklin, W. T.. Creative Workers,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A]//Place and Rol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Societies[C]. Montreal: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80.
[4] 李懷亮, 方英, 王錦慧. 文化產業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研究[J]. 經濟問題, 2010, (2): 26-29.
[5] 王晗. 文化產業發展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J]. 財經問題研究, 2016, (5): 48-53.
[6] Power, D.. “Cultural Industries” in Sweden: An Assessment of Their Place in the Swedish Economy[J].EconomicGeography, 2002, 78(2): 103-127.
[7] Scott, A. J.. Cultural-products Industries and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spects for Growth and Market Contestation in Global Context[J].UrbanAffairsReview, 2004, 39(4): 461-490.
[8] 王林, 顧江. 文化產業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來自長三角地區14個城市的經濟數據[J]. 中南財經大學學報, 2009, (2): 84-88.
[9] 康燦華, 戴鈺. 湖南文化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 湖湘論壇, 2011, (3): 60-63.
[10] 吳承忠, 李臻. 文化產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以長株潭城市圈為例[J]. 城市問題, 2013, (7): 59-63.
[11] 周晶, 曹麥.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以北京市為例[J]. 調研世界, 2015, (6): 17-20.
[12] 闞大學, 呂連菊. 文化產業對地區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基于江西城市動態面板數據[J]. 科技管理研究, 2015, (20): 138-142.
[13] 蔡旺春. 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基于產業結構優化的視角[J]. 中國經濟問題, 2010, (5): 49-55.
[14] 李增福, 劉萬琪. 我國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J]. 產經評論, 2011, 2(5): 5-13.
[15] 馬駿.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研究[J]. 統計與決策, 2014, (20): 149-152.
[16] 施衛東, 衛曉星. 我國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路徑——基于PLS模型的驗證[J]. 經濟管理, 2013, (5): 139-148.
[17] 杜傳忠, 王元明, 王飛. 中國文化產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及其機理分析——基于2001年-2011年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現代管理科學, 2014, (1): 12-14,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