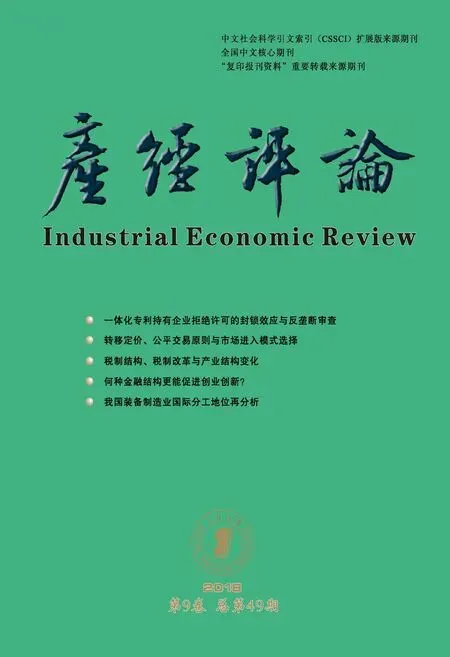農戶層面的農業耕地規模對生產效率的影響
——對我國廣東、江西、河北三省142個農戶的跟蹤調查
一 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顯著促進了我國農業發展(黃季焜,2004)[1]。1978-2015年期間,我國糧食單產從2527公斤/公頃上升到5452公斤/公頃,累計增長近116%,年均增長約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6)[2]。在較長一段時期內,農業穩步持續增產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非農部門轉移,逐漸使得非農收入成為中國農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姜長云,2008)[3]。
一般而言,農民增收的途徑,除了增加家庭生產要素(例如土地、勞動力和資本)投入,更重要的是通過優化生產要素配置和采用先進技術來提高生產效率。在微觀層面,生產效率是指經營主體采用先進生產技術和有效生產要素配置方式以實現產量或收益最大化的能力(Chavas et al., 2005)[4]。農民的生產效率可以從農作物層面、農業層面和農戶層面來考察,農戶層面生產效率與以往文獻中所指的農作物和農業層面的生產效率具有較大差異。具體而言,農作物層面生產效率以特定農作物生產為研究對象,反映的是特定農作物生產過程中農民實現產量或收入最大化的能力。相比而言,農業層面生產效率關注的范圍更廣,但也僅限于農民從事農業生產中實現農業產量或收入最大化的能力。在農民農作物種植結構單一和不從事非農生產的條件下,研究農作物和農業層面生產效率對于引導農民更合理地配置生產要素和采用先進技術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在農民參與非農生產的條件下,僅僅研究農作物和農業層面的生產效率對于引導農民在農業和非農生產之間合理配置生產要素缺乏有效參考價值。農民在同時從事農業和非農生產時,其整個家庭是一個獨立決策單元,任何生產要素配置都將在家庭層面進行決策,而特定農作物生產乃至農業生產的要素配置都僅為家庭決策的一部分。但是,農戶層面生產效率,可以通過把農業和非農生產納入統一框架來反映農民實現家庭總產出和收入最大化的能力。因此,從農戶層面對農民的生產效率進行定量研究對于引導農民合理配置家庭生產要素以獲取最大化產出或收入具有重要實踐指導意義。
規模和生產效率的關系是經濟學文獻中歷久彌新的研究問題。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在農民同時從事農業和非農生產的條件下,農業耕地規模將對農戶層面生產效率產生什么影響?農業耕地規模越大還是越小更有利于農戶層面生產效率提高?科學準確回答上述問題,對于當前中國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以及保障農民家庭收入持續穩定增長具有重要政策含義。為此,本文首先采用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方法估算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水平。技術效率反映了給定生產投入條件下實際產出和潛在最大產出之間的關系,衡量了農民在家庭生產要素不變情況下獲取最大化產出的能力。但是,技術效率未能考慮不同種類農業和非農產出的價格差異。換言之,農民獲取最大產出的能力并不一定反映其獲取最大收入的能力。相比而言,分配效率反映了給定生產條件下實際收入和潛在最大收入之間的關系,衡量了農民在家庭生產要素不變情況下獲取最大收入的能力。在此基礎上,本文構建計量模型定量分析農業耕地規模對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的影響。
下面的內容結構安排是:第二部分為文獻綜述,對國內外農業生產效率估算及其與生產規模關系的相關文獻進行綜述;第三部分建立中國農戶同時參與農業和非農生產條件下的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的理論框架,以及農業耕地規模對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影響的計量模型,并介紹數據來源;第四部分討論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的估算結果,分析農業耕地規模對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影響的計量結果;第五部分為結論和政策啟示。
二 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就農民的生產效率估算展開了探索,主要有兩類估算方法。第一類是直接采用土地、勞動或資本等偏要素生產率,或者全要素生產率作為生產效率的替代變量,這些文獻從不同側面衡量了不同類型農業生產要素的產出能力(申紅芳等,2013)[5]。第二類主要采用參數和非參數方法估算農民的生產效率。其中,參數方法采用計量經濟方法估計隨機前沿生產函數(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進而計算實際產出與潛在最大產出之間的比例作為生產效率的一個替代變量(Feng,2008[6];Tan et al.,2010[7])。相比而言,非參數方法主要是采用DEA方法來估算每一個生產單元的生產效率,從而避免了參數方法需要對隨機前沿生產函數進行嚴格設定的難題(劉萬利和許昆鵬,2011[8];時悅,2007[9];王文剛等,2012[10])。在生產效率的估算對象層面,現有文獻主要是在特定農作物或者農業層面對生產效率進行研究,從農戶層面開展生產效率研究的文獻尚不多。Chavas et al.(2005)[4]和趙建梅等(2013)[11]在考慮農民從事非農生產的條件下,采用DEA方法分別估算岡比亞和中國農民的生產效率,并分析了農戶層面生產效率的影響因素。
圍繞生產規模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國外部分學者考察了農場或土地規模與土地生產率(單產)之間的關系。例如,Sen(1962)[12]最早對印度的研究發現,印度的農場規模和土地生產率呈負向關系。Dyer(1991)[13]研究認為,在落后農業經濟的靜態條件下,農戶種植規模與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是負向的,但是這種負向關系會隨著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而打破。而Kiani(2008)[14]基于巴基斯坦數據的分析結果卻表明,土地生產率與農場規模之間盡管呈現負向關系,但是并不顯著,小規模和大規模農場的土地生產率均高于中等規模農場的土地生產率。國內學者也從這個角度開展了較多研究。例如,辛良杰等(2009)[15]研究發現,農戶土地規模和土地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是非線性的。王建英等(2015)[16]利用對江西省325個水稻種植戶的調查數據研究發現,在地塊層面土地生產率和農戶經營規模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陳杰和蘇群(2016)[17]基于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對中國小麥、稻谷、玉米及大豆生產中土地生產率和土地規模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發現兩者之間的關系受到作物種植結構和地區差異的影響。
與上述研究不同的是,部分學者首先估算了農民的生產效率,在此基礎上建立計量模型來分析農業生產規模對生產效率的影響。例如,Munir et al.(1999)[18]基于對印度旁遮普地區的調查數據,通過計量經濟方法估計隨機前沿生產函數估算農場的技術效率,考察農場規模與技術效率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兩者之間的關系顯著為正。亢霞和劉秀梅(2005)[19]利用1992-2002年中國分省主要糧食作物的投入和產量數據,基于隨機前沿生產函數估算了小麥、玉米、大豆、水稻的技術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結果發現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對糧食產量具有正向影響。李谷成等(2009)[20]在1999-2003年中國湖北省農戶調查數據的基礎上,考察了農戶生產效率與生產規模之間的關系,認為農業生產效率與規模之間存在的負向關系應從更高的視角進行研究。劉天軍和蔡起華(2013)[21]利用陜西省210個獼猴桃農戶的微觀調查數據,基于貝葉斯隨機前沿估計方法分析了不同經營規模農戶的生產技術效率,結果表明經營規模的擴大對農戶生產技術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總體而言,現有文獻對農民生產效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以往研究主要從農作物或農業層面研究農民的生產效率,而從農戶層面定量研究農民生產效率的文獻較少。如前所述,開展農戶層面生產效率的定量研究對于在農民同時從事農業和非農生產條件下引導農民合理配置家庭生產要素以獲取最大化產量或收入具有重要意義。其次,農民的農業生產規模對生產效率,尤其是農戶層面生產效率影響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結論。大多數文獻假定生產規模對生產效率的影響是單調的,較少考慮非單調性關系的可能,少數文獻提出農業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之間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但未用實證方法作進一步考察。
三 方法與數據
(一)生產效率估算
考察生產效率,首先是要區分其與生產率之間的差異。如前所述,生產效率是實際產出或收益與潛在最大產出或收益的比值,反映的是生產者有效利用生產技術或配置生產要素實現最大化產出或收益的能力;而生產率是指實際產出與生產要素投入的比值,反映的是生產要素的產出能力。關于生產效率估算,總體而言有參數和非參數兩類方法。考慮到中國農戶既從事農業生產也從事非農生產的現象普遍存在,本文借鑒Chavas et al.(2005)[4]的做法,采用基于產出的非參數方法估算農民的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本文把效率指數界定在[0,1]的封閉區間。
為了方便表述,首先對相關概念和變量進行定義。假設一個擁有m個勞動力的農戶同時參與農業和非農生產活動。不失一般性,假設該農戶中第i個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和非農生產的時間分別為Ai和Bi,其中i=1,…,m,則A=(A1,…,Am)和B=(B1,…,Bm)分別是農戶投入到農業生產和非農生產的勞動向量。同時,農戶雇傭勞動力H參與農業生產,s代表用于農業生產的物質資本投入。農業產出向量為q;非農產出為Z。假設農業產出價格向量為p*本文假設非農產出的價格為1,因此Z即代表了非農產出水平,也代表了農戶的非農收入水平。。
技術效率反映的是給定生產投入條件下實際產出和潛在最大產出之間的關系,衡量了農民在家庭生產要素不變情況下獲取最大化產出的能力。因此,一個同時參與農業生產和非農生產的農戶,其技術效率指數可以表述如下:
TE(s,A,H,B,q,Z,T)=minθ{θ: (s,A,H,B;q/θ,Z/θ)∈T,θ>0}
(1)
其中,TE是技術效率指數;T是農戶面臨的生產技術集合。因此,(s,A,H,B;q,Z)∈T表示農戶投入(s,A,H,B)可以生產出(q,Z)。如果技術效率TE=1,表示農戶正處于生產技術前沿;如果技術效率TE<1,表示農戶處于生產技術前沿以下,即缺乏技術效率。
由于技術效率沒有考慮不同農業和非農產出的價格差異,因此定義分配效率為給定生產投入條件下實際收入和潛在最大收入之間的關系,以其衡量農民在家庭生產要素不變情況下獲取最大化收入的能力。因此,分配效率指數可以表述如下:
AE(p,s,A,H,B,T)={p′(q/TE)+Z/TE}/R(p,s,A,H,B,T)
(2)
其中,AE是分配效率指數。如果分配效率AE=1,表示利益最大化的農戶關于產出的投入配置是有效率的,否則關于產出的投入配置不是有效率的。需要說明的是,R(·)是給定投入集合的收入函數,具體定義如下:
R(p,s,A,H,B,T)=maxq, Z{p′q+Z:(s,A,H,B;q,Z)∈T}
(3)
(二)農業耕地規模對農戶層面生產效率的影響模型
本文的基本假設是,在農戶同時從事農業生產和非農生產的條件下,其技術采用和生產要素配置決策不局限于特定農作物乃至農業生產,而會不可避免地延伸到非農生產范圍。在農業生產規模較小的情況下,小幅度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可能并不足以形成農業生產的規模效應,而且可能抑制農戶的生產要素(例如,勞動)向技術更優、回報更高的非農生產流動,最終導致農戶層面生產效率降低;但是,當農業生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之后,規模效應逐漸顯現;而且當農業收入成為農戶主要收入來源時,農戶可能會有意識地采用更優的農業生產技術,提高自身在農業生產中的生產要素配置能力,從而使得農業生產規模和生產效率之間呈現正向關系。因此,本文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Efficiency=β0+β1Land+β2(Land×Land)+β3Rent+β4Male+β5Age+β6Educ+β7NHead+
β8Hsize+β9TLabor+β10NLabor+β11Dependency+β12Crop+β13Region+β14Year+u
(4)
式(4)中,Efficiency為農戶層面生產效率,包括技術效率(TE)和分配效率(AE);Land為實際農業耕地面積;Land×Land為農業耕地面積的平方;Rent為轉入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比重;Male為戶主是否為男性的虛擬變量;Age為戶主年齡;Educ為戶主受教育年限;NHead為戶主參加非農生產虛擬變量;Hsize為家庭人口數;TLabor為總勞動力數;NLabor為非農勞動力數;Dependency為撫養比,即非勞動力數量與勞動力數量的比值;Crop為農作物種植結構,包括水稻、玉米、小麥、棉花和蔬菜等主要農作物虛擬變量;Region為地區虛擬變量;Year為年份虛擬變量;β0-β14為待估參數;u為隨機誤差項。
由于生產效率是定義在[0,1]封閉區間的變量,因此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式(4)進行回歸將得到非一致的估計結果。因此,本文將使用Tobit回歸對式(4)進行估計,并使用聚類穩健標準誤控制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性和序列相關性。
(三)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研究數據來自2012-2013年在我國廣東省、江西省和河北省5縣開展的農戶實地調查。具體調查區域為廣東省廉江市、徐聞縣,江西省九江縣,以及河北省河間市、清河縣。按照隨機抽樣原則,每個縣選取2個樣本村,在每個樣本村選取20個農戶。除部分隨機選取的農民不能提供家庭成員從事農業(含耕地規模)和非農生產的完整信息外,共獲得142個有效樣本,樣本有效率達到71%。2012-2013年期間,通過對上述農戶進行跟蹤調查共獲得267個有效觀測值。
實地調查中,與本研究相關的調查內容分為四類:(1)農戶個人及家庭基本特征,包括每個家庭成員的姓名、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及是否勞動力;(2)農業耕地特征,包括農業耕地面積及轉入耕地面積等;(3)農業生產特征,包括種植的農作物類型,及每種農作物種植面積、物質投入、勞動投入(含自投勞動和雇傭勞動)、產量及出售價格等;(4)非農生產特征,包括每個勞動力是否參加非農生產、非農生產時間和收入等。
表1列出了樣本主要特征的描述性結果。總體而言,在有效樣本農戶觀測中,男性占60%以上,平均年齡約53-55歲,受教育年限略高于6年(約為小學水平)。在所有樣本農戶觀測中,幾乎超過50%的農戶均參加非農生產。就家庭特征而言,戶均家庭人口約5人,其中勞動力約4人,其中1.4個勞動力參加非農生產。撫養比,即非勞動力家庭成員與勞動力家庭成員的比值,平均而言為0.3左右。在樣本農戶觀測中,戶均耕地面積大約0.7公頃(即0.7×15=10.5畝),其中轉入耕地面積約占總耕地面積的13%左右。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實地調查數據整理而得。
四 結果與討論
(一)生產效率估算結果
表2列出了本文用于估算生產效率的農業和非農生產的投入產出信息。就農業生產而言,樣本農戶的勞動投入為年均634小時,其中2013年略高于2012年。投入到農業生產中的物質資本年均為7500元左右。相對應地,農業收入年均為23000元左右。在非農生產中,樣本農戶的年均勞動投入約為16個月,而獲得的非農收入為年均44000左右。這說明,對于樣本農戶而言,非農收入幾乎為農業收入的2倍,在農民家庭收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表2 樣本農戶農業和非農業生產的投入產出情況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實地調查數據整理而得。
表3列出了樣本農戶層面生產效率的估算結果。總體而言,樣本農戶的平均技術效率為0.949。其中,江西省九江縣的平均技術效率最低,僅為0.899,而最高的廣東省廉江市為0.976。除了不同地區農戶技術效率存在較大差異外,本文也發現盡管農戶層面技術效率仍然存在一定的改進潛力,但是空間十分有限,因為已有215個樣本農戶觀測是技術有效的,占總樣本農戶觀測的80.2%左右。

表3 樣本農戶生產效率估算結果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實地調查數據整理而得。
相比而言,樣本農戶層面的平均分配效率偏低。如表3所示,分配效率均值僅為0.799,其中河北省清河縣低至0.711,而最高的江西省九江縣也僅為0.861。與此同時,僅43.1%的樣本農戶觀測的分配效率等于1。平均而言,分配非效率解釋了近20%的農戶收入損失,從而說明樣本農戶未能實現收益最大化,存在通過提高分配效率來改善收入水平的空間。
(二)Tobit回歸結果
本文首先采用Tobit回歸考察農戶的農業耕地規模與農戶層面生產效率的關系,同時使用聚類穩健標準誤控制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性和序列相關性。計量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研究結果表明,農戶的農業耕地規模與農戶層面生產效率之間存在顯著的“U”型關系。如表4所示,在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的結果中,農業耕地面積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而農業耕地面積平方項的系數卻均顯著為正。這說明,農業耕地規模與農戶層面生產效率之間的關系是非線性的,即“U”型拋物線。進一步計算各個變量的邊際效應可知,當農業耕地面積為0.526公頃(約8畝)*為了計算農戶層面生產效率最低點的農業耕地面積,首先根據表4中的邊際效應計算技術效率對農業耕地面積的一階偏導數,并令該一階偏導數等于零。由于農業耕地面積及其平方項的邊際效應分別為-0.786和0.747,因此技術效率對農業耕地面積的一階偏導數為-0.786+0.747×2×Land*=0,通過進一步計算可得Land*=0.526公頃。農戶層面分配效率最低點農業耕地面積計算方法與此相同。時,農戶層面技術效率最低。這說明,當農業耕地面積小于0.526公頃時,農戶層面技術效率隨著耕地面積增加而降低;但是當農業耕地面積大于0.526公頃時,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將隨著耕地面積增加而提高。類似地,使農戶層面分配效率最低的農業耕地規模是0.883公頃(約13畝),當農業耕地面積小于0.883公頃時,農戶層面分配效率隨著耕地面積增加而降低;但是當農業耕地面積大于0.883公頃時,農戶層面分配效率將隨著耕地面積增加而提高。

表4 農業耕地規模對農戶層面生產效率影響的Tobit回歸結果
(續上表)

變量技術效率(TE)系數標準誤邊際效應分配效率(AE)系數標準誤邊際效應 撫養比(比值)0132 02430026-0100 0192-0040種植結構: 水稻(種植=1,不種植=0)-01610166-0032-01240135-0050 玉米(種植=1,不種植=0)013802400027-01050124-0042 小麥(種植=1,不種植=0)-00340128-00070250???00800100 棉花(種植=1,不種植=0)0397??01740079-00430130-0017 蔬菜(種植=1,不種植=0)0619???01630123-00160084-0007常數項1251???04230825???0283Sigma0355???00440319???0022偽R平方03240307對數似然值-111606-159120F統計量26144085觀測值267267
注:(1)標準誤為聚類穩健標準誤。(2)模型中均采用了縣市虛擬變量和年份虛擬變量來控制地區和時間效應,但考慮篇幅未在本表報告。(3)*、**和***分別表示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
回歸結果與本文的基本假設是一致的。一方面,小幅度擴大農業耕地規模,農民難以顯著地提高生產技術和要素配置水平、發揮農業生產的規模效應,從而不能顯著促進家庭總產出和總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農業耕地規模擴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農戶對于非農生產的要素投入,從而降低農民從事非農生產獲得的收入。換言之,在非農生產報酬明顯高于農業生產報酬的條件下,小農戶有限地擴大農業耕地規模所增加的農業產出和收入不足以彌補非農生產投入降低而減少的非農產出和收入,這種由有限農業耕地規模擴大導致的家庭生產要素從非農生產回流至農業生產很可能是無效率的。因此,在農業經營主體主要為小農戶的條件下,實施農業規模化經營必須避免掉入農戶層面生產效率陷阱。在增加耕地面積以達到農業規模化經營時,需要滿足兩個條件:(1)耕地面積應大于上述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臨界點處的面積;(2)該面積所對應的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應不小于增加耕地面積之前的效率水平。由于農業耕地面積和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之間均呈現“U”型拋物線關系,并且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在耕地面積在零與臨界點耕地面積之間呈下降趨勢,根據拋物線對稱原理,具有更高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的最小農業耕地面積應與零點對稱。如圖1所示,為了不降低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最低農業耕地面積分別約為1公頃(15畝)和1.8公頃(27畝)。如前所述,由于技術效率衡量的僅僅是農戶獲取最大化產出的能力,而分配效率衡量的是農民獲取最大化收入的能力,因此本文認為農業規模化經營的最低耕地面積應該約為1.8公頃(27畝),否則將會存在農戶層面的分配效率損失。

圖1 農業耕地面積與農戶層面生產效率關系示意圖*由于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受到除農業耕地面積之外的其他因素影響,因此在不影響生產效率與耕地規模關系分析的情況下,在圖中縱坐標不體現具體效率水平。
就戶主特征而言,戶主男性虛擬變量在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的回歸結果中系數均未達到顯著性水平,表明戶主性別因素不會對農戶層面生產效率產生影響。但是,戶主年齡對農戶層面技術效率的影響達到了顯著性水平,表明年齡越大的戶主其技術效率也更高。這可能是因為年齡可以間接反映戶主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和經驗,經驗越豐富的農戶可能具備更好的農業生產技術,從而提高了技術效率。但是,戶主年齡對分配效率的影響并不顯著,說明年齡大的農戶可能對市場價格的敏感性較低,難以根據農業和非農產出的價格變化而調整家庭生產結構。此外,戶主受教育年限對農戶層面生產效率沒有顯著影響。可能的原因是,樣本農戶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不同農戶之間的生產知識、技術水平及資源配置能力等與教育的相關性較低。戶主參加非農生產顯著地提高了農戶層面分配效率,說明參加非農生產可以使農民對市場價格變化更加敏感,從而及時調整家庭生產結構。
家庭特征因素總體上并未體現出對農戶層面生產效率的顯著影響。具體而言,家庭人口數、總勞動力數以及撫養比等三個變量的估計系數均不顯著。但是,家庭非農勞動力人數與農戶層面技術效率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非農勞動力越多的農戶其技術效率也越高。這可能是因為,非農勞動力在參與非農生產中可能獲得更多的先進經營理念,從而對農業生產具有積極影響。此外,農戶的農作物種植結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農戶層面的生產效率。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用兩種方法對上述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第一種方法是采用Probit回歸分析農業耕地規模對農戶層面生產效率是否為1的影響。第二種方法是采用隨機效應Tobit回歸對剔除非重復觀測值得到的平衡面板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無論是Probit回歸還是隨機效應Tobit回歸結果均與表4回歸結果保持了一致。在農戶層面技術效率Probit回歸結果中,農業耕地面積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而其平方項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農戶層面技術效率等于1的概率先隨著農業耕地面積的增加而變小,通過臨界點后隨著農業耕地面積的增加而變大。類似地,分配效率的Probit回歸也得到了高度一致的結果。為了進行隨機效應Tobit回歸,首先對樣本觀測值進行了平衡化處理,剔除了非重復觀測值,得到了250個觀測值的兩年平衡面板數據。在此基礎上,對平衡面板數據進行了隨機效應Tobit回歸,其結果與表4回歸結果一致。農業耕地面積及其平方項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系數大小與表4中相應系數基本一致。上述結果充分說明,本文的計量分析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表5 農業耕地規模對農戶層面生產效率影響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注:(1)括號內為標準誤,其中Probit回歸為聚類穩健標準誤。(2)所有控制變量與表4回歸完全一致,但考慮篇幅未在本表報告。(3)*、**和***分別表示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
五 結論與啟示
本文考慮到我國農民普遍存在同時從事農業和非農生產的情況,先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估算了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接著用Tobit回歸定量研究了農戶的農業耕地規模對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的影響。本文研究數據來自于2012-2013年對我國廣東省、江西省和河北省142個農戶的跟蹤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樣本農戶的平均技術效率為0.949,且改善潛力有限;相比而言,樣本農戶的平均分配效率偏低,均值僅為0.799。計量模型估計結果表明,農戶的農業耕地規模與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均存在顯著的“U”型關系。當農業耕地面積小于0.526公頃時,農戶層面技術效率隨著耕地面積增加而降低;當農業耕地面積大于0.526公頃時,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將隨著耕地面積增加而提高。類似地,當農業耕地面積小于0.833公頃時,農戶層面分配效率隨著耕地面積增加而降低;當農業耕地面積大于0.833公頃時,農戶層面分配效率將隨著耕地面積增加而提高。否則將會存在農戶層面的分配效率損失。此外,戶主個人特征、家庭特征及農作物種植結構也對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有顯著影響。
由上述結論得出以下啟示:第一,由于非農收入逐漸成為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考察農民生產效率不能僅停留在特定農作物或農業層面,應以農民家庭為獨立決策單元。第二,在農民同時從事農業和非農生產條件下,研究農業經營規模對農戶層面生產效率的影響應考慮兩者之間的非線性關系。第三,在農業經營主體主要為小農戶的條件下,實施農業規模化經營中,需避免掉入“農戶層面生產效率陷阱”。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為了不降低農戶層面技術效率和分配效率水平,農業規模化經營的最低耕地面積應約為1.8公頃。
[1] 黃季焜. 我國農業的過去和未來[J]. 管理世界, 2004, (3): 95-104, 111.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中國統計年鑒[M]. 北京: 中國統計出版社, 2016.
[3] 姜長云. 中國農民收入增長趨勢的變化[J]. 中國農村經濟, 2008, (9): 4-12.
[4] Chavas, J., Petrie, R., Roth, M.. Farm Household Productio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he Gambia[J].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 2005, 87(1): 160-179.
[5] 申紅芳, 陳超, 王磊. 世界農業經營規模與農業生產效率研究及其對中國的借鑒[J]. 農村經濟與科技, 2013, 24(12): 14-17.
[6] Feng, S.. Land Rental, Off-farm 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Farm Households in Jiangxi Province, China [J].NJAS-WageningenJournalofLifeSciences, 2008, 55(4): 363-378.
[7] Tan, S., Heerink, N., Kuyvenhoven, A., et al.. Impact of Land Fragmentation on Rice Producers’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South-east China[J].NJAS-WageningenJournalofLifeSciences, 2010, 57(2): 117-123.
[8] 劉萬利, 許昆鵬. 中國農戶生產效率實證研究[J]. 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 2011, (1): 125-128.
[9] 時悅. 農業生產效率變動分析、 分解及調整目標——基于DEA方法的實證研究[J]. 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 6(4): 30-34.
[10] 王文剛, 李汝資, 宋玉祥等. 吉林省區域農地生產效率及其變動特征研究[J]. 地理科學, 2012, (2): 225-231.
[11] 趙建梅, 孔祥智, 孫東升等. 中國農戶兼業經營條件下的生產效率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 2012, (3): 16-26.
[12] Sen, A.. An Aspect of Indian Agriculture[J].EconomicWeekly, 1962, 14(4-6): 243-246.
[13] Dyer, G.. Farm Size-farm Productivity Re-examined: Evidence from Rural Egypt[J].JournalofPeasantStudies, 1991, 19(1): 59-92.
[14] Kiani, A.. Farm Size and Productivity in Pakistan[J].EuropeanJournalofSocialSciences, 2008, 7(2): 42-52.
[15] 辛良杰, 李秀彬, 朱會義等. 農戶土地規模與生產率的關系及其解釋的印證——以吉林省為例[J]. 地理研究, 2009, 28(5): 1276-1284.
[16] 王建英, 陳志鋼, 黃祖輝等. 轉型時期土地生產率與農戶經營規模關系再考察[J]. 管理世界, 2015, (9): 65-81.
[17] 陳杰, 蘇群. 土地生產率視角下的中國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基于2010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 (6): 121-130.
[18] Munir, A., Qureshi, S., Hussain, Z.. Recent Evidence on Farm Size and Land Productivity: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J].PakistanDevelopmentReview, 1999, 38(4): 1135-1153.
[19] 亢霞, 劉秀梅. 我國糧食生產的技術效率分析——基于隨機前沿分析方法[J]. 中國農村觀察, 2005, (4): 25-32.
[20] 李谷成, 馮中朝, 范麗霞. 小農戶真的更加具有效率嗎? 來自湖北省的經驗證據[J]. 經濟學(季刊), 2009, 9(1): 99-128.
[21] 劉天軍, 蔡起華. 不同經營規模農戶的生產技術效率分析——基于陜西省獼猴桃生產基地縣210戶農戶的數據 [J]. 中國農村經濟, 2013, (3): 3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