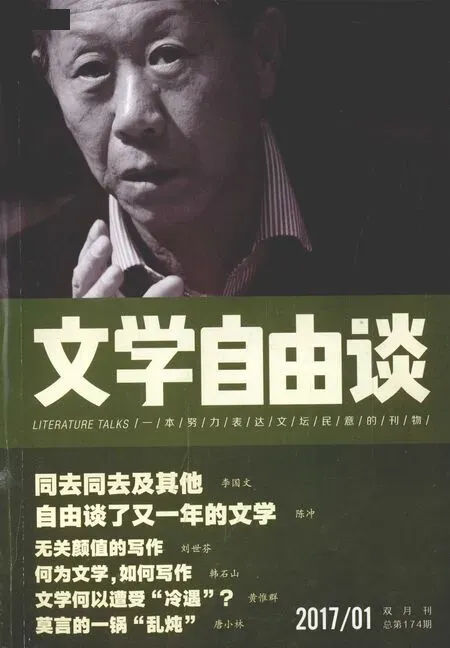為什么我們選擇了“孩子”?
王帥乃
為什么我們選擇了“孩子”?
王帥乃
彭懿的《巴夭人的孩子》在經(jīng)過漫長的醞釀打磨后,一經(jīng)推出便獲得了眾多兒童文學(xué)愛好者的密切關(guān)注,在收獲驕人市場戰(zhàn)績的同時(shí),亦享有著上佳的業(yè)內(nèi)口碑。 “中國第一部原創(chuàng)攝影繪本”并非只是噱頭,它確實(shí)是一個(gè)“講了好故事”又“講好了故事”的優(yōu)秀文本。現(xiàn)在,最熱的一波話題浪潮漸漸過去,是我們靜下心來仔細(xì)品味它的時(shí)候了。
前些天偶然“重遇”奧登的一句話——他對一位想成為“詩人”的年輕人說:“如果寫詩是因?yàn)橛性捯f,那意思不大。如果是為了待在詞語近旁,偷聽它們互相之間的言談,那么至少觸摸到了詩歌的根基。 ”這是在說,當(dāng)我們不再心急于從文本中求得顯在的“意義”,而是觸摸、欣悅于每一個(gè)構(gòu)成文本的符號及其連接方式本身時(shí),不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將更容易靠近文學(xué)、靠近詩。《巴夭人的孩子》在有心人的眼里可以讀出無限意義,尤其是社會(huì)學(xué)、人類學(xué)視角下的后殖民與階級問題,這也確實(shí)是文本有意涉及的層面;但我這里想談的,僅僅是基于文本文字與畫面語符鏈接之上的“孩子”。
《巴夭人的孩子》可以說是全方位地以“孩子”為中心,給予孩子每一個(gè)角度的注視:仰拍、俯拍、遠(yuǎn)景、中景、近景、特寫,單個(gè)孩子的、兩個(gè)伙伴的、一群小家伙的,正臉、側(cè)臉、背對,站著不動(dòng)的、一躍而起的、各種表情的……它從封面就開始了故事的講述,一片瑩綠一葉舟,像是要載著讀者進(jìn)入愛麗絲的幻境——如同“幻想小說”中總會(huì)有一扇區(qū)隔又貫通現(xiàn)實(shí)與幻想世界的界線之門,就像進(jìn)入“納尼亞”的大衣柜、九又四分之三站臺(tái),或《永遠(yuǎn)講不完的故事》里那本叫《永遠(yuǎn)講不完的故事》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