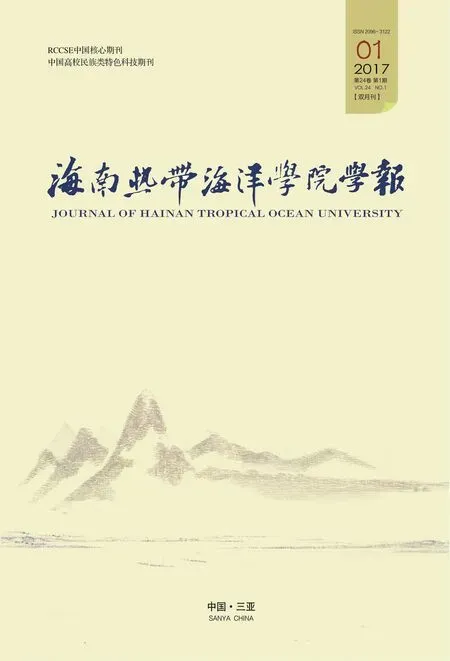社會文化行為研究之逃避自由
——在娛樂至死中隱沒自我
蒿 帆
(陜西理工大學(xué) 文學(xué)院,陜西 漢中 723000)
社會文化行為研究之逃避自由
——在娛樂至死中隱沒自我
蒿 帆
(陜西理工大學(xué) 文學(xué)院,陜西 漢中 723000)
埃里希·弗羅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現(xiàn)代文化和社會危機最要緊的一個方面,即自由對現(xiàn)代人的含義。在自由與民主化的現(xiàn)代社會里,個體化進程飛速發(fā)展。一心追求自由的人因為無法承擔(dān)自由帶來的孤立與無能為力之感選擇了逃避自由。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提出的娛樂的方式成為了人們逃避自由的機制。人們最終以愛的藝術(shù)克服孤立與自由的矛盾,不再逃避,獲得真正積極的自由。審視這些關(guān)于自由的問題,積極擺脫人類成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的窘境,在《愛的藝術(shù)》中探尋解決矛盾的方法,將對現(xiàn)代人的自由發(fā)展和媒介環(huán)境的改善具有深刻的意義。
《逃避自由》;《娛樂至死》;《愛的藝術(shù)》;隱沒;媒介
現(xiàn)代人總是高舉自由的旗幟,崇尚個性化的個人發(fā)展進程。人們想要通過掙脫各種陳舊的束縛去追求個人獨立發(fā)展的自由。但結(jié)果往往適得其反,人們在享受自由帶來的獨立與理性的的同時,也必然承受著自由帶來的孤立、焦慮和無能為力感。現(xiàn)代媒介環(huán)境下信息的泛濫化、輿論的隱匿性與爆炸性更是加重了這種孤獨與疑慮。各種媒介的發(fā)展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在孤獨世界里隱沒自己的方式,那就是娛樂至上。現(xiàn)代社會的媒介環(huán)境與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里所描繪的相比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人們以娛樂至死的方式逃避自由,將自己隱沒于信息的洪流之中,失去自我。只有自發(fā)性的愛才能讓人趨向于合群又不磨滅個性,人們克服孤獨的情感只有一種,那就是愛。愛,是人追求自由的需要,是讓人不再逃避自由的必要條件。
一、 逃避自由的原因:孤獨與恐懼
(一)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
探尋逃避自由的原因,必須從個人的出現(xiàn)和自由的產(chǎn)生入手。我們首先要明白,什么是自由。弗羅姆在《逃避自由》中給自由下了一個定義:“我所謂的概念是: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而且,其含義隨人把自身作為一個獨立和分離的存在物加以認識和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所變化。”[1]16也就是說,自由產(chǎn)生于人類意識到自身與自然的不同,意識到自己與他人的不同,意識愈加強烈,自由愈加蘇醒。人與自然之間隔著一個社會,自然的毫無約束與社會的規(guī)則條例之間是順承的關(guān)系。人在這種順承關(guān)系中找到自己的獨一無二的位置,人就認識和理解了自由。人類的社會歷史就始發(fā)于人類在自身與自然的一體狀態(tài)中,開始意識到自己是獨立存在的個體,是與周圍自然和他人相分離的一個實體之時。這種自由意識的弱小與周圍環(huán)境的強大讓自由一度只是漫長歷史長河中朦朧的感知。人在這種朦朧的感覺中于與自己賴以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始終密切聯(lián)系著,盡管他偶爾或部分地意識到自己是個獨立實體,但他更堅定地認為自己是周圍世界的一部分,與自己身處的世界密不可分。但自我意識的逐漸蘇醒,還是加快了人與自然這個原始紐帶的分離。
“我們可以稱這個個人日益從原始紐帶中脫穎而出的過程為‘個體化’。”[1]16在個體化進程出現(xiàn)之前,人缺乏個體性,卻在“始發(fā)紐帶”的庇護下獲得安全感和引導(dǎo)。“始發(fā)紐帶”導(dǎo)致個人的出現(xiàn),緊隨其后個人的個體化進程展開,人開始逐漸擺脫這個連接母與子或原始共同體成員與其部落及自然的原始紐帶。就成長過程來說,兒童與始發(fā)紐帶斷絕的程度越高,他渴望自由與獨立的愿望就越強烈。一旦個體化全部完成,個人從這些給與他安全感與歸屬感同時也給予禁錮和抑制的紐帶中解放出來,新的問題產(chǎn)生了:個體化進程出現(xiàn)了兩個方面的辯證特征:“個體化進程日益加劇的一方面為自我力量的增長,另一方面是孤獨日益加深。”[1]19-20
(一)缺乏意義與方向的生命
逃避自由需要的產(chǎn)生,是因為人意識到自己在賴以發(fā)生的世界里的孤獨狀態(tài),意識到自己是與他人分離的個體。與世界相比,個人覺得世界無比強大,有壓倒一切的力量和重重的危險。由此他產(chǎn)生了一種無能為力感和焦慮感。“于是,為了克服孤獨與無能為力感,個人便產(chǎn)生了放棄個性的沖動,要把自己完全隱沒在外面的世界里。”[1]20當人選擇了隱沒自己,就等于選擇了逃避。自由的增長過程伴隨著人的發(fā)展過程,一方面自由的增長使個人力量逐漸增強,個人日趨完善,對自然的掌控越來越得心應(yīng)手的過程;一方面孤獨感和不安全感日益加深,對生命的懷疑感加重,個人的無能為力感和微不足道感侵蝕著人對于自由的追求。為什么會產(chǎn)生懷疑,為什么會有無能為力的感受,原因在于人類所依賴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條件的滯后,沒能為人類個體化進程的實現(xiàn)提供保障,沒能為自由的增長提供基礎(chǔ)。這種滯后讓自由成為人類難以忍受的負擔(dān)。“于是,它便等同于懷疑,無異于一種缺乏意義與方向的生命;于是人便產(chǎn)生了逃避這種自由的強烈沖動,或臣服,或與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種關(guān)系,借此擺脫不安全感,哪怕以個人自由為代價,也在所不惜。”[1]25政治上,擺脫了封建統(tǒng)治的人們在現(xiàn)代民主社會的法律和規(guī)則之下,獲得的是有限的自由。揭竿而起的年代已經(jīng)過去,暴力不再是擺脫束縛,獲得自由的途徑。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經(jīng)濟上,資本決定性地位的獲得,意味著人所具備的勞動能力讓人成為奴仆,資本成為了主人。資本的控制下,技術(shù)的進步更加重了人的微不足道感,人類自己發(fā)明的工具強大到使人本身淪為工具的仆人。在規(guī)模化機器的控制下,人被困于固定的位置,失去了人類的部分自由。文化上,流行的趨勢控制著人們的喜好,人們想要追求個性,卻迷失在流行文化的大潮之下,失去自主選擇。也許看上去文化的多樣性給人們提供了無限選擇的可能。但人們得到的卻是一個主流文化主導(dǎo)下的一小部分可供自由選擇。這種社會結(jié)構(gòu)下,人是得到了發(fā)展,但人卻更加孤立無援,人是得到了更多自由,卻又產(chǎn)生新的依賴。社會使人越來越獨立自主,也使人越來越孤獨恐懼。人建造了世界,卻不再是這個他所建造的世界的真正的主人。相反,世界成了它的主人,面對于他自己創(chuàng)造的勞動成果,他成為了仆人,他必須卑躬屈膝地聽命于主人的安排。人已物化為工具,成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人被禁錮于大規(guī)模的機器之下,成為一個齒輪,一個永久地固定在同一位置上的物件。人幻想著自己成為世界的主人,卻淪為世界的奴仆。人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改變了世界,可以自由的發(fā)展,卻一直被世界改變,囿于工具化的特定角色之中。
(三)沉默的螺旋
“我們卻忽略了公眾輿論及‘常識’之類無名權(quán)威的作用,它們的作用非常大,因為我們非常急于與別人對自己的期望保持一致,也同樣非常害怕與眾不同。”[1]76個人活動總想“趨炎附勢”,逃避自由的發(fā)展,總想尋求群體的庇護。在傳播學(xué)中,這種行為產(chǎn)生的惟一結(jié)果就是形成“沉默的螺旋”。個人還是向大多數(shù)人低頭了,即使他是對的。現(xiàn)代社會中,人的自我是喪失了個人的社會自我,是隱沒在角色扮演中的偽自我。這個自我背負了他人的期望和社會的期許,這使得個人在面對自己時也不得不進行偽裝。因為個人無法承受真實自我在社會中追求自由、與眾不同所帶來的負擔(dān)。他們力避免由于自己單獨持有的某些態(tài)度和信念所產(chǎn)生的孤立,所以他們必須全力逃避自由,隱沒自我。
二、 逃避機制:以娛樂至死的方式隱沒自我
(一)酒神精神
希臘人以酒神精神逃避自由。《悲劇的誕生》中尼采提出他在酒神秘儀中人的縱欲自棄的狀態(tài)中看出了希臘人的悲觀主義。“自棄”是希臘人逃避自由的方式,逃避個人自由,回歸“始發(fā)紐帶”是希臘人的終極愿望。因為尼采認為希臘民族與其在日神的外觀下隱藏世界痛苦的真相,不如直面痛苦。“酒神是個體的人自我否定而復(fù)歸世界本體的沖動。”[2]10在尼采看來,酒神的本質(zhì)就在于“個體化原理崩潰之時從人的最內(nèi)在基礎(chǔ)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滿幸福的狂喜”[2]8。只有放棄個人,向世界的本質(zhì)回歸才能具有面對痛苦的勇氣和力量。從尼采認為的熱情肯定生命意志的酒神精神中我們看到的是“擺脫個體化的束縛,回歸自然之母永恒生命的懷抱”[2]9。酒神精神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超脫人生是在醉的現(xiàn)實中蓄意毀掉個人,用一種神秘的統(tǒng)一感解脫個人。人類在不同的發(fā)展階段都存在逃避自由的心理和行為。繁榮一時的希臘文明下強調(diào)的是民族意志,集體概念。個人忘言廢步,在群體中迷狂嬉戲表明自己是共同體成員。個體化狀態(tài)被希臘人認為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和始因,成為了本該鄙棄的事情。希臘民族的整體意志超越一切個人,這是那個特殊時代的特殊需要。
尼采看到了人性在主動否定自我過程中的狂歡,而在尼采之前兩千多年的亞里士多德的理性靈魂說里,人的實踐理性是被動的。“而這種最高最終極的目的就是‘至善’,幸福便是合德性的活動。”[3]亞里士多德對“現(xiàn)世”的重視與尼采相通。不同的是,尼采認為現(xiàn)世是痛苦的,需要以逃避自由的方式直面這種痛苦。而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是屬于現(xiàn)世的人的幸福,“現(xiàn)世人的幸福與人的實踐活動是密切相關(guān)的,存在于人的生活經(jīng)驗和理性能力的行為之中”[3]。從亞里士多德到尼采,歷史走過了兩千多年的旅途,人類也從自由到走向了逃避。
(二)《娛樂至死》與隱沒機制
網(wǎng)絡(luò)中流行文化的傳播最能體現(xiàn)現(xiàn)代人正在以一種娛樂至死的方式一味趨同。明星是流行的典型代表,外貌成為了對一個明星最具說服力的評價標準。清一色的審美趨同,讓“顏值”成為了社會大眾的審美標準。媒介將這種審美價值傳播給廣大受眾,人們同樣選擇將自我隱沒在精致的五官和美麗的外表之下,整容成了人們隱沒自己最好的方式。追求時尚,淹沒于快餐化的時尚更迭中成為現(xiàn)代人逃避自由的方式。現(xiàn)代人放棄自由,將自我隱沒在外界潮流中。將個人退縮在娛樂至死的媒介環(huán)境中試圖通過這種隱沒,消弭個人自我與社會之間的鴻溝,以此克服孤獨和無權(quán)利之感。也就是說,逃避機制源于孤立個人的不安全感。現(xiàn)代人在媒介的權(quán)威主義下放棄個人自我的獨立傾向。總想隱沒于各種媒介尤其是網(wǎng)絡(luò)的大環(huán)境下。“這種機制的更明確的形式在于渴望臣服或主宰,即我們所說的受虐—施虐沖動。”[1]101人們在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guī)則游戲的庸俗網(wǎng)絡(luò)文化中因為一時的享樂而失去了自由,被自己所熱愛的東西禁錮甚至毀滅。尼爾·波茲曼描述到:“這是一個娛樂之城,在這里,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xiàn),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和商業(yè)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jié)果是我們成為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4]4“附庸”二字體現(xiàn)了我們與媒介之間受虐與施虐的共生關(guān)系。我們享受娛樂這件華麗外衣下兇殺、色情、暴力、奇聞異事對于我們眼球和心靈的肆虐。我們心甘情愿的接受甚至主動尋求這種刺激。這種受虐沖動源于人們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所體會到的微不足道感。孤立無援讓獵奇的心理欲望更加強烈,仿佛只有看到這些不平常的事件才能證明自己是多么正常和多么的合群。通過一次次的點擊和分享,我們從受虐者搖身一變成為了施虐著,轉(zhuǎn)身再去影響別人,對他人施虐。網(wǎng)絡(luò)的存在打破了媒介真實與虛構(gòu)的傳統(tǒng)界限。媒介成為了人們生活中新的權(quán)威,人們在此獲取想要的信息。明明是虛構(gòu)的媒介環(huán)境卻因為自己獨特的空間和時間優(yōu)勢部分地展現(xiàn)出真實的世界面貌。人們將自己隱沒在網(wǎng)絡(luò)的屏障之下,不停地說著和做著本在真實世界中難以啟齒的話和無法做到的事。躲在屏幕后方的自我似乎才可以更加灑脫和放肆。在媒介環(huán)境中,道德和輿論以“匿名權(quán)威”的姿態(tài)逐漸取代公開權(quán)威對人們實行的統(tǒng)治。“道德綁架”是公眾對于個人的施虐。“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們不接受這個世界表面所表現(xiàn)出來的東西。”[4]97事實卻恰恰相反,自從十九世紀中期照片和插圖以勃發(fā)之勢入侵符號環(huán)境之后,“偽語境”擾亂了人們的認識和判斷力。復(fù)雜的電子媒介環(huán)境下片段式、碎片式、標題式、圖片式的表達方法讓人們只憑只字片語就做出判斷,在信息不完整甚至是不真實的情況下對當事人進行評判,以道德為借口,以為站在了大多數(shù)的隊伍里就等于占領(lǐng)了道德的高地,對當事人實施語言上的暴力,參與群體施虐的行為。人們總是害怕一句“異言”就使得自己成為網(wǎng)友輿論槍口下新的攻擊目標,總是不敢表達自己,隱藏自己。
如此就引出了逃避機制的另外兩種:破壞欲和機制趨同。“破壞欲是是生命未能得到實現(xiàn)的后果。”[1]131壓力是現(xiàn)代人面臨的嚴重問題,壓力和自由是一對矛盾體。那些使人的生命受到壓抑的個人和社會條件滋生了破壞沖動,于是人們使用網(wǎng)絡(luò)媒介對他人實施語言暴力,惡語相向,傷害別人的同時也在傷害自己,以此發(fā)泄自己的破壞欲。而這些破壞沖動又是人對自己或他人懷有特殊敵視的根源。人們將自己的敵視、嫉妒、反感等負面情緒統(tǒng)統(tǒng)在一道屏幕的掩蓋下肆無忌憚地傾倒。網(wǎng)絡(luò)游戲中虛擬的戰(zhàn)爭和搏斗就是人們發(fā)泄破壞欲的最直接的表現(xiàn)形式。激烈刺激的游戲體驗滿足了人們的破壞沖動。“趨同”更是逃避自由最方便的選擇。這種逃避機制是現(xiàn)代社會大多數(shù)常人所采取的方式。個人不再是他自己,在他人對他的期望下,他被社會的文化模式塑造,于是他變得和所有其他人一樣。“我與世界的鴻溝消失了,意識里的孤獨感和無能為力感也一起消失了。”[1]132個人的想法和感覺并不再是他的思想和感覺,而是由另一個人灌輸?shù)剿哪X子里的外在的東西。
為最便捷的選擇。人們選擇在清一色的大眼睛、高鼻梁、瓜子臉中享受與他人同樣的美麗。人們選擇整容的方式達到別人期望的樣子。“顏值”這個網(wǎng)絡(luò)用語甚至深入到現(xiàn)實生活的話語模式。還有太多的新鮮說法可以直接改變詞語原有的意思,占有著特殊的迎合公眾口味的新的解釋。“粉絲”就是這樣一個在媒介環(huán)境中誕生的新鮮事物。粉絲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文化,帶著部分群體強烈的趨同意識去崇拜同一名偶像。這種崇拜在某些粉絲群體中甚至演變?yōu)橐环N霸占心理和暴力行為。一旦偶像遭受負面評價和質(zhì)疑,粉絲群體就會群起而攻之,人肉搜索帶來的羞辱和謾罵使對方毫無抵抗之力。不同粉絲群體間為了偶像爭吵和大打出手的例子也是時有發(fā)生。“‘公眾’是一種僅僅靠數(shù)量顯示其強大的力量,藝術(shù)家不應(yīng)該去迎合。”[2]50現(xiàn)狀卻不是這樣,公眾成為了最強大的群體,擁有難以想象的影響力和攻擊性。“熱點”“熱門”這樣的詞似乎是為了表現(xiàn)現(xiàn)代社會的“趨同”現(xiàn)象所應(yīng)運而生的。多數(shù)人關(guān)注的“點”是才能成為熱點,引起更多人的興趣,引發(fā)更大范圍的討論。這些“熱門”在不斷的提醒人們,這是公眾關(guān)注的事情,你也應(yīng)該關(guān)注。也去這只是一個幌子,卻真的吸引了受眾,帶著他人的期待滿足了多數(shù)人的趨同心理。“趨同”讓我們放棄了自己的思想,表達的都是被他人植入的意愿。“然而,表達我們思想的權(quán)利,只有在我們能夠有自己的思想時才有意義。”[1]171公眾扮演著具有強大力量的他人的角色,大眾媒介支配著公眾與個人。在大眾媒介的引導(dǎo)下,在公眾的期望中,我們終于喪失了勇氣,失去了自我。個人臣服于公眾的權(quán)威,人們臣服并依賴媒介的力量。言論自由的時代人們需要這么一個平臺,滿足自己受虐和施虐的沖動,破壞的欲望和他人的期望。權(quán)威和破壞欲是消滅個人,趨同只是隱藏個人,將個人隱沒于外界。這三種機制在現(xiàn)代媒介環(huán)境中被人們利用得淋漓盡致。
三、 《愛的藝術(shù)》:克服孤獨的需要和情感
(一)追尋愛的本真
弗羅姆認為:“自發(fā)行為是一種克服恐懼孤獨的方法,同時人也用不著犧牲自我的完整性,……愛是此類自發(fā)性的最核心組成部分。”[1]186人們在消極的自由中將自我隱沒于外界,孤獨并且軟弱。自發(fā)性的愛可以使人獲得積極的自由,趨于合群又不磨滅個性。這種追求自由的愛不是把自我完全消解在另一個人中的那種愛,不具有受虐沖動;也不是強制擁有另一個人的那種愛,不具有施虐沖動。而是在充分保存自我的基礎(chǔ)上,不趨同、不破壞,與他人融為一體的愛。在愛的藝術(shù)中,人是掌握“愛的藝術(shù)”的主體,“《 周易略例明彖》中,魏晉玄學(xué)家王弼曾提出‘物無妄然,必由其理’的說法。這也就是說,事物的存在是以其內(nèi)在的原因為支撐的,否則世界上絕不可能存在無緣無故的事物。”[5]人的存在就是為愛的藝術(shù)明確了主體,人可以在心理和行動中逃避自由,卻無法逃避本身的“此在”性。在愛的實踐中,人可以更加確切地感受自我的存在,從而弱化逃避自由的沖動。在愛的藝術(shù)中,愛的實踐和其他藝術(shù)實踐一樣,需要紀律、集中、耐心,時刻對自己保持清醒。而掌握愛情藝術(shù)的特殊條件就是克服自戀,克服這種態(tài)度下人們貪婪和恐懼,對人和事物抱有開放性的態(tài)度,保持客觀性,以此打破表面深入現(xiàn)象核心。也就是揭開人們隱沒自己的外殼,追尋愛的本真。
(二)假愛情的典型表現(xiàn)
愛的實踐中不乏少見的兩種典型的假愛情的形式值得注意:一種是偶像化的愛情,一種是多愁善感的愛情。偶像化的愛情常被人們稱為是偉大的愛情,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小說和電影里,對愛的對象偶像化的崇拜占據(jù)了愛情關(guān)系的全部。之所以稱之為偉大,是指愛對象的偉大。這種形式的愛在一開始就伴有強烈性和突發(fā)性。“一個沒有達到產(chǎn)生自我感覺高度的人(這種自我感覺的基礎(chǔ)是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揮自己的力量)傾向于把自己所愛的人‘神化’。”[6]69在對愛的對象的崇拜中人們異化了自己的力量,反射自己的力量到所愛之人的身上。這個過程中,人失去了自己而不是在被愛人的身上找尋自己的力量。這個過程伴隨著瘋狂和失望,失望過后就是找尋新的偶像,“偉大”的愛情消逝了。多愁善感式的愛情就像是一場白日夢。“這種愛情的本質(zhì)就是它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而不是存在于與另一個人實實在在的結(jié)合之中。”[6]70在這種想象的愛情中,人們通過消費愛情電影、小說、歌曲等愛情體驗的替代品使自己得到滿足。這些代替品的消費過程滿足了人們對于一切沒有實現(xiàn)的對愛情,對人與人之間親近關(guān)系的向往,是最浮淺的愛情體驗處于多愁善感式愛情中的人們總是想回到過去,他們陷在回憶的漩渦,通過把當下推移到過去的方式使自己獲得愛情的深深的感動。囿于過去就無法享受當下,也無法憧憬未來,這種形式的愛是沒有生命力的愛。
(三)生命自由的升華
愛的能力不是獨立存在,憑空產(chǎn)生的。愛的能力要求人們完全投入,全力以赴,要求激情與活力,理性與責(zé)任,尊重與了解,這是生命自由的升華。“這種能力只能通過在生活的許多其他方面的創(chuàng)造性的和積極的態(tài)度才能獲得。”[6]90生命中愛情之外的范疇里沒有積極性與創(chuàng)造性的人,在愛情方面也不會有這種能力。
人類追求自由,逃避自由,獲得自由的過程是一個個人自我發(fā)展,逐漸強大的過程。自由與生俱來的矛盾——個性的誕生與孤獨之痛苦讓人產(chǎn)生了逃避自由的沖動。現(xiàn)代人處在娛樂業(yè)繁華喧囂的鼎盛狀態(tài)之中,難免會以媒介所提供的方式逃避自由,娛樂至死這種方式是現(xiàn)代人隱沒自我,逃避自由的方式。網(wǎng)絡(luò)暴力、輿論攻擊、道德綁架之種種無一不在提醒著人們:個人的沉默逃避會帶來更大范圍的沉默怪圈,一旦個人放棄自由,他所代表的小群體隨之也會失去自由,進而與其態(tài)度相反的對立群體就會更大程度上去剝奪其自由。正如兩軍交戰(zhàn)中的一方在士氣上已不戰(zhàn)而勝。娛樂至死并不能真正讓人完全永久地隱沒自我,因為人總有厭倦了逃避、清醒地亦或是憤怒之下想為自己說句話的時候。所以,人還是找到了追求自由的答案:愛的藝術(shù)。在愛的藝術(shù)中,人們用自發(fā)性的愛摒棄了沉默懦弱的偽自我,找回了,敢說敢做、敢為人先的真自我;拋棄了被外界期望所切割的部分自我,找回了獨立自主的完整自我。人的理智在愛中蘇醒,人的力量在愛中強大,人最終會找回積極的自由,找回生命的意義。
[1][美]埃里希·弗羅姆.逃避自由[M].劉林海,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
[2][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劇的誕生[M].周國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3]黎紅勤.作為“道德基礎(chǔ)”的理性如何規(guī)范道德——康德“實踐理性”德性論解析與重構(gòu)[J].瓊州學(xué)院學(xué)報,2014(3):74-79.[4][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章艷,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4.
[5]任祥偉.一種哲學(xué)智慧的詮釋:如何通向本體的澄明之境[J].瓊州學(xué)院學(xué)報,2014(4):84-89.
[6][美]艾·弗羅姆.愛的藝術(shù)[M].李健鳴,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7.
(編校:王旭東)
Stud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Behavior: Escape from Freedom —Hidden Oneself in the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HAO Fan
(Faculty of Arts, Sh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723000, China)
InEscapefromFreedom, Erich Fromm pointed out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modern culture and social crisis: the meaning of freedom for modern people. In the free and democratized modern society, the individual process is rapidly developed. Freedom-pursuit man chooses the escape from freedom because they can’t bear the sense of isolation and powerlessness brought by freedom. InAmusingOurselvestoDeath, Neil Postman proposed that amusement becomes mechanism for people to escape from freedom. People will eventually overcome the contradiction of isolation and freedom bytheartofloveand won’t escape and eventual gain the real positive freedom. Observing these freedom issues, actively getting rid of the predicament of man turning into the species of amusing themselves into death, and exploring methods of resolving contradictions in the The Art Of Love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people’s free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odern media environment.
EscapefromFreedom;AmusingOurselvestoDeath;TheArtOfLove; hiding; medium
格式:蒿帆.社會文化行為研究之逃避自由——在娛樂至死中隱沒自我[J].海南熱帶海洋學(xué)院學(xué)報,2017(1):91-95+117.
2016-09-20
陜西理工大學(xué)研究生創(chuàng)新基金項目(SLGYCX1604)
蒿帆(1991-),女,河南南陽人,陜西理工大學(xué)文學(xué)院文藝學(xué)專業(yè)2014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闡釋學(xué)、《文心雕龍》。
I206
A
2096-3122(2017)01-0091-05
10.13307/j.issn.2096-3122.2017.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