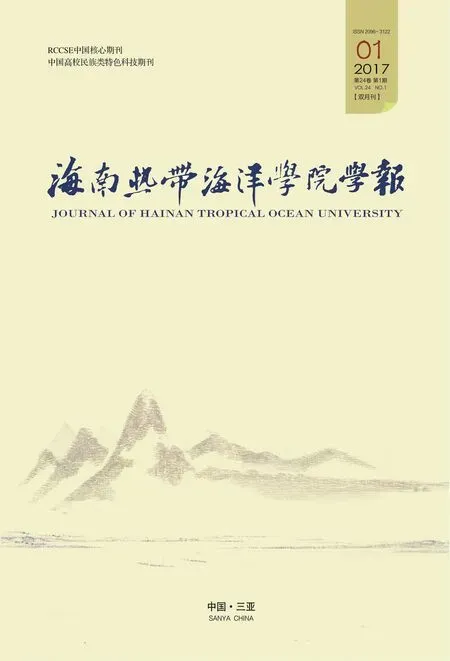神話與魏晉詩歌
葉慶兵
(山東大學 文學院,濟南 250100)
神話與魏晉詩歌
葉慶兵
(山東大學 文學院,濟南 250100)
神話在魏晉詩歌中廣泛地存在,構成魏晉詩歌的重要內容。神話對于魏晉詩歌,在內容、形象、語言、深層涵義以及詩人的個性表達等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和影響。同時,魏晉詩歌也對神話的發展發生作用,促進了神話的仙話化。魏晉詩歌廣泛地運用神話,這與神話自身的豐富意蘊、神話的自然發展、魏晉時期搜奇記異的社會風氣以及魏晉時期特殊的政治環境都有關系。
神話;魏晉詩歌;仙話化
對于魏晉詩歌,研究者們主要關注的是門閥制度、玄學、佛教等的影響,很少有人關注到神話。實際上,魏晉詩歌中存在著非常豐富的神話內容,這些神話對魏晉詩歌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同時,魏晉詩歌對神話的運用,也促使神話面貌發生改變。對魏晉詩歌中的神話內容進行深入細致的考察,既可以加深對于魏晉詩歌的理解,也可以對上古神話在魏晉時期的發展演變有更清楚的認識。
一、 魏晉詩歌中的神話
神話在魏晉詩歌中廣泛存在,并且構成魏晉詩歌的重要內容。一些重要詩人喜用神話,而一些重要的詩歌作品中也往往包含著神話。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含有神話內容的魏晉詩人詩歌主要有:
曹操:《氣出唱》(華陰山)、《氣出唱》(游君山)、《秋胡行》(晨上散關山)、《秋胡行》(愿登太華山)以及《精列》《度關山》《陌上桑》。
曹丕:《秋胡行》(堯任舜禹)、《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
曹植:《惟漢行》《豫章行》《靈芒篇》《五游詠》《仙人篇》《驅車篇》《妾薄命行》《游仙詩》和《升天行》(扶桑之所出)。
嵇康:《答二郭三首》(昔蒙父兄祚)、《五言詩三首》(俗人不可親)、《述志詩》(潛龍育神軀)以及《游仙詩》《代秋胡歌詩七章》《六言詩十章》。
阮籍:《詠懷十三首》其二、《詠懷八十二首》其二、其十八、其二十五、其二十八、其二十九、其三十五、其三十八、其四十五、其五十二、其五十四、其五十八、其七十九、其八十一。
傅玄:《歌》(雷師鳴鐘鼓)、《雜詩》(朱明運將極)、《雜詩》(旸谷發精曜)、《詩》(鸞鳥晞鳳凰)、《擬四愁詩四首》(我所思兮在瀛洲)和《日昇歌》《又答程曉詩》。
張華:《上巳篇》《招隱詩》和《游仙詩四首》(玉佩連浮星)。
陸機:《折楊柳行》《前緩聲歌》《鞠歌行》《順東西門行》《擬迢迢牽牛星詩》。
張載:《詩》(白玉隨天回)、《詩》(十日出湯谷)、《雜詩十首》(朝霞迎白日)、《雜詩十首》(墨蜧躍重淵)、《雜詩》(太昊啟東節)。
王鑒:《七夕觀織女詩》。
李充:《七月七日詩》。
李颙:《羨夏篇》《感冬篇》。
郭璞:《游仙詩十九首》(旸谷吐靈曜)、《游仙詩十九首》(采藥游名山)、《游仙詩十九首》(縱酒濛汜濱)、《詩》(羲和騁丹衢)。
曹毗:《黃帝贊詩》。
謝安:《與王胡之詩》。
陶淵明:《勸農詩》《命子詩》《止酒》《讀<山海經>詩十三首》和《飲酒詩二十首》(羲農去我久)。
以上僅是筆者根據逯欽立先生《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以及諸家詩集的整理校注本所作的粗略統計,并不完備。但是從以上這些詩篇已經可以看出神話在魏晉詩人、詩歌中的廣泛影響了。不僅如此,這些詩歌涉及到的神話內容還非常豐富。
經初步梳理,魏晉詩歌所涉及的神話人物主要有:
1. 伏羲、神農、句芒。如嵇康《答二郭詩三首》:“羲農邈已遠,拊膺獨咨嗟。”[1]487陶淵明《飲酒詩二十首》:“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2]282張華《上巳篇》:“仁風導和氣,勾芒御昊春。”[1]617
2. 高陽、太皞。如李顒《感冬篇》:“高陽攬玄轡,太皞御冬始。”[1]858
3. 西王母、東王父。如曹操《氣出唱》:“遨游八極,乃到昆侖之山,西王母側。”[3]242曹植《仙人篇》:“驅風游四海,東過王母廬。”[3]390嵇康《代秋胡歌詩》:“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1]480張華《游仙詩》:“列坐王母堂,艷體餐瑤華。”[1]621傅玄《歌》:“王母出穴聽,王父吟安廂。”[1]568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十三首》:“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2]398
4. 羲和。如阮籍《詠懷八十二首》其十八:“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3]488《詠懷八十二首》其三十五:“愿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3]508傅玄《日升歌》:“東光升朝陽,羲和初攬轡,六龍并騰驤。”[1]567《又答程曉詩》:“羲和運玉衡,招搖賦朔旬。”[1]570張華《招隱詩》:“羲和策六龍,弭節越崦嵫。”[1]622郭璞《游仙詩》:“手頓羲和轡,足蹈閶闔開。”[1]866
5. 望舒。如傅玄《詩》:“鸞鳥晞鳳凰,望舒繼白日。”[1]572李顒《感冬篇》:“望舒游天策,曜靈協燕紀。”[1]858謝安《與王胡之詩》:“夕翫望舒,入室鳴琴。”[1]906
6. 風神、雨神、雷神。如傅玄《歌》:“雷師鳴鐘鼓,風伯吹笙簧。”[1]568其中雷師即雷神,風伯即風神。又如張載《雜詩十首》:“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1]747飛廉即風神,《楚辭·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注:“飛廉,風伯也。”[4]豐隆即雷神(或曰云神),《淮南子·天文訓》:“季春三月, 豐隆乃出,以將其雨。”高誘注:“豐隆,雷也。”[5]號屏為雨神,《搜神記》:“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一曰玄冥。”[6]
7. 黃帝(軒轅)。如曹植《仙人篇》:“不見軒轅氏,乘龍出鼎湖。”[3]389-390曹毗《黃帝贊詩》:“軒轅應玄期,幼能總百神。體練五靈妙,氣含云露津。摻石曾城岫,鑄鼎荊山濱。豁焉天扉開,飄然跨騰鱗。儀轡灑長風,褰裳躡紫宸。”[1]888
8. 炎帝。如李充《七月七日詩》:“素云巡濛汜,炎帝收離光。”[1]857
9. 堯、舜、鯀、禹。如:曹丕《秋胡行》:“堯任舜禹,當復何為。百獸率舞,鳳凰來儀。”[3]272曹植《豫章行》:“虞舜不逢堯,耕耘處中田。太公未遭文,漁釣終渭川。”[3]401陶淵明《勸農》“舜既躬耕,禹亦稼穡”[2]34。《讀山海經詩十三首》:“何以廢共鯀,重華為之來。”[2]417
10. 應龍。如陸機《鞠歌行》:“朝云升,應龍攀,乘風遠游騰云端。”[7]618
11. 夏后、夸父、共工。如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其二十二:“夏后乘靈輿,夸父為鄧林。”[3]493其二十九:“共工宅玄冥,高臺造青天。”[3]501其五十四:“西北登不周,東南望鄧林。”[3]529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十三首》:“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余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后。”[2]408
12. 恒娥(嫦娥)、玉兔。如嵇康《五言詩三首》:“恒娥進妙藥,毛羽翕光新。”[1]489傅玄《歌》:“兔搗藥月間,安足道。神烏戲云間,安足道。”[1]569
13. 河伯。如曹植《仙人篇》:“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3]389-390
14. 湘娥、宓妃、簡狄。如曹植《仙人篇》:“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3]389曹植《妾薄命行》:“想彼宓妃洛河,退詠漢女湘娥。”[3]392張華《游仙詩四首》:“湘妃詠《涉江》,漢女奏《陽阿》。”[1]621陸機《前緩聲歌》:“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北征瑤臺女,南要湘川娥。”[7]572湘娥即舜之二妃娥皇、女英;宓妃乃洛神;“瑤臺女”為殷之始祖神簡狄。《呂氏春秋·音初》載:“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8]《史記·殷本紀》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9]119
15. 后稷。如陶淵明《勸農》:“哲人伊何,時維后稷。”[2]34
16. 精衛、刑天。如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十三首》:“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夭無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2]410形夭即刑天。
17. 危、欽駓、窫窳、祖江、鵕鶚。如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十三首》:“巨猾肆威暴,欽駓違帝旨。窫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鵕鶚豈足恃?”[2]413詩中巨猾當作臣危,《山海經·海內西經》載:“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發,系之山上木。”[10]285祖江即葆江,《山海經·西山經》載:“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鐘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殺葆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鐘山之東曰崖。欽化為大鶚,其狀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為鵕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則其邑大旱。”[10]42-43
18. 牛郎、織女。如曹丕《燕歌行二首》:“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何梁。”[3]287陸機《擬迢迢牽牛星詩》:“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7]447王鑒《七夕觀織女詩》:“牽牛悲殊館,織女悼離家。一稔期一宵,此期良可嘉。赫奕玄門開,飛閣郁嵯峨。隱隱驅千乘,闐闐越星河。六龍奮瑤轡,文螭負瓊車。火丹秉瑰燭,素女執瓊華。絳旗若吐電,朱蓋如振霞。云韶何嘈嗷,靈鼓鳴相和。亭軒紆高盻,眷予在岌峨。澤因芳露沾,恩附蘭風加。明發相從游,翩翩鸞鷟羅。同游不同觀,念子憂怨多。敬因三祝末,以爾屬皇娥。”[1]854李充《七月七日詩》:“朗月垂玄景,洪漢截皓蒼。牽牛難牽牛,織女守空箱。河廣尚可越,怨此漢無梁。”[1]857
從上面的舉例可以看出,魏晉詩歌中所涉及的神話人物達到了數十個之多,原始神話中的太陽神、月神、風神、雨神、雷神、河神、春神、始祖神、英雄神等都有涉及。這還只是就神話人物而言,實際上,魏晉詩歌中所包含的神話內容還遠不止此。魏晉詩歌中還涉及許多神話中的地名,如旸谷、濛汜、隅谷、崦嵫、閶闔、玄圃、昆侖、九嶷、不周、鼎湖;還有許多神話中的神物,如若木、扶桑、尋木、三青鳥、三珠樹等,它們共同構成了魏晉詩歌中豐富的神話內容。
二、 神話對魏晉詩歌的作用和影響
魏晉詩歌中豐富的神話內容說明神話在魏晉時期是被廣泛傳播和接受的,這在神話研究上也能夠得到印證,郭璞為《山海經》作注就是很好的說明。同時,豐富的神話內容,也必然為魏晉詩歌帶來深遠的影響。
首先,豐富魏晉詩歌的內容。在魏晉詩歌中涌現出了一些直接以神話為描寫內容的作品,最典型的當然是陶淵明的《讀<山海經>詩十三首》。除此之外,曹毗《黃帝贊詩》全篇以黃帝為描寫對象;而陸機《擬迢迢牽牛星詩》、王鑒《七夕觀織女詩》、李充《七月七日詩》等更是形成了專門歌詠牛郎織女故事的系列詩篇。這都可見出神話對魏晉詩歌內容的滋養。
其次,塑造新奇形象,描繪奇異畫面。神話中的人、物本來就有著奇特的形象,當這些神話人、物進入詩歌,也就為詩歌帶來了新奇的形象,并描繪出一幅幅奇特的畫面。如傅玄《雜詩》“旸谷發精曜,九日棲高枝”[1]572,張載《詩》“白玉隨天回,皦皦圓如規。踴躍湯谷中,上登扶桑枝”[1]743,“十日出湯谷,弭節馳萬里。經天曜四海,倏忽潛濛汜”[1]743,都用詩的語言描述了太陽神話,或九日或十日并出,畫面頗為壯觀奇特。又如郭璞《游仙詩》“手頓羲和轡,足蹈閶闔開。東海猶蹄涔,昆侖螻蟻堆”[1]866,場面又是何其壯闊與神奇,不僅詩歌形象源自神話,詩歌大膽的想象和瑰瑋的氣魄也顯然受到神話影響。
第三,促成語言的多樣性。在魏晉詩歌中,雖然有一部分直接以神話為描寫內容的詩歌,但很多詩歌則只是以神話名稱來代稱現實事物,如以望舒代月、羲和代日、豐隆代雷、號屏代雨等。但是由于神話世界的多姿多彩,可以用來代稱一種事物的,往往可以有多種神話對應項,這就給詩人的使用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也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詩歌語言。如同樣是代稱太陽,既可以用羲和、高陽等太陽神的名稱;也可以用神話中太陽的棲居與行經之所,如:扶桑、若木、旸谷、濛汜、隅谷、崦嵫等多種稱謂,這就構成了魏晉詩歌中多姿多彩的太陽形象。以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為例,其中寫到太陽,就出現了羲和、扶桑、若木、旸谷、濛汜、十日、隅谷等多種稱謂。由此可知,神話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語言。
第四,帶來豐富的含義與深刻的精神內容。神話本來就包含著豐富的故事性,神話人物身上帶有固定的精神和品格特征,當詩人在詩歌中運用到神話人物的時候,他們的故事、品格和精神自然而然就會進入詩歌,從而大大豐富了詩歌的內容,也使詩歌含義更加深刻。如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十三首》歌詠精衛,雖然只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這樣簡單的兩句,但是這兩句詩的背后包含著一個無辜被溺、矢志復仇的倔強、堅定的形象。描寫刑天,同樣只有“形(刑)夭(天)無(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兩句,但這背后卻有一個敢于與帝爭神,即使失敗被戮也不肯屈服,仍然要頂天立地斗爭到底的反抗者形象。精衛、刑天的豐富形象和特定精神內涵是從神話中帶來的,倘若沒有神話中的既成故事為背景,這簡單的四句詩根本不可能表達出現在這樣深刻的含義。當然,如果沒有神話,陶淵明根本就寫不出這樣的詩歌。正是由于有了相應的神話背景,陶淵明才可能在簡單的兩句詩中表達出豐富的內容和深刻的精神內涵。
第五,表現詩人獨特的個性、思想和追求。魏晉詩人在神話的運用上表現出不同的喜好,這實際上反映出了詩人們不同的個性、思想和追求。阮籍尤其愛用太陽神話,其《詠懷詩八十二首》中有十四首涉及神話,而這十四首中又有七首用到的是太陽神話,他用到了羲和、扶桑、若木、旸谷、濛汜、十日、隅谷等幾乎所有太陽的別稱。阮籍如此廣泛地運用太陽神話,一定有自己的目的和原因。在這七首涉及太陽神話的詠懷詩中,阮籍所關注的問題其實主要是兩個:一是生命的流逝,如其十八:“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為咸池暉,蒙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3]488其三十五:“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太陽。愿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3]508其五十二:“十日出旸谷,弭節馳萬里。經天耀四海,倐忽潛蒙泛。誰言焱炎久,游沒何行俟。逝者豈長生,亦去荊與杞。”[3]527其八十一:“人生樂長久。百年自言遼。白日隕隅谷。一夕不再朝。豈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飖。”[3]561二是勢路的窮達,如其二十五:“飛泉流玉山,懸車棲扶桑。日月徑千里,素風發微霜。勢路有窮達,咨嗟安可長。”[3]496-497其二十八:“若木耀西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涂,明暗不相侔。窮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3]500阮籍的《詠懷詩》可以說是“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11],其具體所指難以情測,但從這幾首涉及太陽神話的詩歌來看,似乎都在關注生命遠逝,勢路多窮。阮籍本有濟世之志,這從他的《通易論》可見一斑,但他卻處在政治斗爭殘酷的險惡環境中,稍有不慎甚至會有喪生之虞,怎么可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結合這種情況來考慮,阮籍詠懷詩中這幾首涉及太陽神話的詩歌,似乎正是在表達他在此險惡環境中,勢路多窮,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只能蹉跎歲月的傷感,而太陽的東升西落,正能給人日月遠逝最直觀的感受。這或許是阮籍喜用太陽神話的原因所在吧,而豐富多彩太陽神話的使用,無疑也在詩人抒發情感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阮籍,其他詩人在神話的使用上也體現出一定的喜好和個性。如“漢魏五言詩的真正奠基人”[12]曹操就特別喜歡在詩歌中使用西王母形象,曹操運用神話的詩歌主要有《氣出唱》(華陰山)、《氣出唱》(游君山)、《秋胡行》(晨上散關山)、《秋胡行》(愿登太華山)以及《精列》《度關山》《陌上桑》,其中《氣出唱》兩首和《陌上桑》直接寫到西王母,《秋胡行》兩首和《精列》雖然沒有直接寫到西王母,但都寫到了西王母的所在地——昆侖,可見曹操對于西王母神話的熱衷。曹操為什么如此偏好西王母神話?分析這些涉及西王母神話的詩歌,不難發現它們大多體現了詩人同一種情感——對生命遠逝的遺憾和對長壽、永生的渴望。如《氣出唱》(華陰山):“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3]242《氣出唱》(游君山):“常愿主人增年,與天相守。”[3]243《精列》:“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3]244《陌上桑》:“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3]250《山海經·西山經》載:“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郭璞注:“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10]50-51西王母在神話中可以說是掌管死亡的大神,而神話又有西王母和不死藥的傳說。這就難怪曹操要反復提到西王母神話了,曹操正是借西王母神話來表達“人生幾何”“去日苦多”的深層傷感。正是由于西王母神話與曹操的憂生之嗟存在著深層次的契合,曹操才會在詩歌中反復使用這一神話。同時,西王母神話的反復重現,無疑又更突出了曹操這個大英雄對于生命必然逝去的無限惋惜和無可奈何的悲情。與曹操不同,曹丕和曹植很喜歡在詩歌中運用堯、舜的神話傳說,這又顯然表現了兄弟二人的政治抱負和追求。可見,神話與詩人個性的表現、情感的抒發、思想的呈現都有促進的作用,能夠相得益彰。
三、 魏晉詩歌對神話的影響
神話影響魏晉詩歌的同時,魏晉詩歌也在影響著神話。魏晉詩歌對神話的影響,最突出地表現為神話的仙話化,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看出來。
首先,神話人物與仙話人物同現,沒有區別。如曹操《氣出唱》(華陰山):“遨游八極,乃到昆侖之山,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亭。來者為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樂共飲食到黃昏。”[3]242阮籍《詠懷十八十二首》其二十二:“夏后乘靈輿,夸父為鄧林。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沉。鳳凰鳴參差,倫伶發其音。王子好簫管,世世相追尋。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3]493赤松子、王子喬都是著名的仙話中人物,他們得道成仙,能夠永生。在魏晉詩人筆下西王母、夸父等神話人物與仙話中的人物合流,而從思想傾向上來說,所表現的更符合仙話的長生主題,這就顯然是把神話人物仙話化了。
其次,神話世界與仙話世界混一,難以區分。昆侖是我國古代神話中的神秘之所,《山海經》載:“海內昆侖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10]294又載:“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10]47蓬萊在神話中沒有什么地位,它在《山海經》中只出現過一次。但是在仙話中,蓬萊的地位卻非常重要,成為眾仙之所,不死藥的所在地。《史記》載:“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9]313又載:“少君言于上曰:‘祠灶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于是天子始親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9]573-574在魏晉詩歌中,昆侖與蓬萊卻漸漸混而為一。如曹操《精列》:“愿螭龍之駕,思想昆侖居。思想昆侖居。見期于迂怪,志意在蓬萊。”[3]244《秋胡行》(愿登太華山):“愿登泰華山,神人共遠游。經歷昆侖山,到蓬萊。”[3]259可見,神話圣地與仙話圣地依然沒有分別,都成了長生不死的所在。
第三,更為突出的是,神話大量地進入仙話題材的詩歌作品,一些游仙詩卻是以神話人物為主。如曹植《仙人篇》:“仙人攬六箸,對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韓終與王喬,要我于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逾景云,高風吹我軀。回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閶闔正嵯峨,雙闕萬丈余。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驅風游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岳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趣且徐徐。不見昔軒轅,升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3]389-390其詩云“仙人篇”,但其中真正屬于仙話人物的其實只有韓終、王喬、秦女,其他的湘娥、河伯、王母、軒轅等,則都是神話人物。其《游仙》中所寫到的地點,卻主要是鼎湖、扶桑、弱水等神話中的地名。又如張華《游仙詩》云:“列坐王母堂,艷體餐瑤華。湘妃詠《涉江》,秦女奏《陽阿》。”[1]621也以王母、湘妃為歌詠對象。郭璞《游仙詩十九首》其中也有多首寫到姮娥、旸谷、濛汜、尋木、扶桑、羲和、閶闔、昆侖等神話中的人、物。這說明魏晉詩人,完全是把這些神話當作仙話了。
神話的仙話化在很早就開始了,甚至在《山海經》中也摻入了一些仙話的成分,但是像魏晉詩人這樣,直接把二者視為同一,把神話的世界和仙話的世界完全混同,以前恐怕是沒有,至少不會有如此高的程度。同時,魏晉詩歌對神話、仙話不加區分,采神話入游仙詩的行為,無疑又會促進神話仙話化的進一步發展。
四、 神話在魏晉詩歌中大量出現的原因
在前文論述中,筆者曾總結了部分詩人喜用神話的原因。實際上,喜用神話的詩人在歷朝歷代也都有一些,如唐代的李白、李商隱也喜歡在詩歌中運用神話,但是像魏晉一樣,在詩歌中大量運用神話,甚至形成一種風氣,卻是很少見的。神話在魏晉詩歌中大量出現大概有如下一些原因。
首先,這是由神話自身的豐富意蘊決定的。我國上古神話具有豐富的精神內涵,這為魏晉詩人詩歌創作提供了寶貴的藝術資源。如前文所述,曹操可以在上古神話中尋找到西王母以抒發憂生之嗟;阮籍可以憑借羲和神話抒發人生的感慨和對生命流逝的哀嘆;而陶淵明也可以借助精衛、荊軻、刑天等神話人物含蓄地表現自己金剛怒目的一面。但凡詩人有表達的沖動,在神話中能夠找到對應的素材,這不僅是神話在魏晉詩歌中廣泛存在的原因,也是神話能夠進入詩歌的前提條件。神話的豐富意蘊,和詩歌簡練的語言,言簡義豐的藝術追求相契合,這使得神話自然會進入詩歌。
其次,這與神話的自然發展有關。上古神話在先秦兩漢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尤其是發生了神話歷史化以及神話仙話化的演變。神話歷史化對于保存上古神話的原貌是不利的,但是歷史化了的神話卻變得容易接受,促進了神話的廣泛流傳。如堯、舜、禹是魏晉詩歌中頻繁出現的神話人物,在魏晉詩歌中,他們都是上古時期的明君圣王,這正是他們歷史化了的形象。神話的仙話化,又使得神話人物自然而然地進入了游仙詩中。
第三,這也和魏晉時期搜奇記異的社會風氣有關。魏晉時期是神話接受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了郭璞的《山海經注》等整理、研究神話的學術著作,還出現了《搜神記》《神仙傳》《列仙傳》《穆天子傳》《十洲記》等搜奇記異的作品。這些作品搜集的內容,有許多就是上古神話。這種搜奇記異,“發明神道之不誣”的社會風氣下,詩歌作品中廣泛地運用神話也就不奇怪了。
第四,不能不提到的還有魏晉時期特殊的政治環境。魏晉時期政治黑暗,士人始終處于政治高壓之下,極易招致禍端。這種社會氛圍使得士人大多不敢公開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態度。在這種大背景下,充滿奇思異想,與現實毫無瓜葛的神話,當然是一種很好的避禍的選擇,阮籍《詠懷八十二首》中大量地運用神話,或許就有這樣的考慮。另一方面,特殊的社會環境又使得儒家的思想束縛變得松弛,士人們敢于“越名教而任自然”,這又有利于突破儒家“不語怪力亂神”的限制,使神話在魏晉詩歌中大量運用成為可能。
原典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原點和基本方法”[13],本文從魏晉詩歌原典出發,對魏晉詩歌運用神話的情況作了梳理,就神話與魏晉詩歌的相互影響和作用,以及魏晉詩歌大量運用神話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討。實際上,不僅是魏晉詩歌,魏晉的辭賦、魏晉時期興起的志怪小說等文學作品中都有不少神話內容。神話與魏晉文學的關系,目前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關注和研究,日后或許能夠引起專家學者們的注意。倘能如此,拙文亦不失拋磚引玉之意。
[1]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3.
[3]黃節.黃節注漢魏樂府詩六種[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4][宋]洪興祖.楚辭補注[M].黃靈庚,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3.
[5]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106.
[6][晉]干寶.搜神記[M].汪紹楹,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43.
[7]劉運好.陸士衡文集校注[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8]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335.
[9][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3.
[10]袁珂.山海經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曹旭.詩品集注[M].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51.
[12]祖秋陽,木齋.曹操詩歌的分期及其在詩歌史地位的重新認知[J].瓊州學院學報,2016(1):3-8.
[13]木齋.原典:學術研究的基礎原點和基本方法[J].瓊州學院學報,2015(3):1-3.
(編校:李一鳴)
The Study on Myths and Poetry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YE Qing-bing
(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Myths existed widely in the poems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poetry of the time. Myth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and made an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ntents, images, languages and connotations of the poetry. Meanwhile, the poems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also affected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myths and helped in the mythologization of the myths. The widely use of myths in poetry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rich implications, its natural development, the special social climate and political atmosphere.
myths; the poetry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mythologize
格式:葉慶兵.神話與魏晉詩歌[J].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報,2017(1):27-33.
2016-11-25
葉慶兵(1992-),男,安徽太湖人,山東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2014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先秦兩漢文學與文化。
I207.22
A
2096-3122(2017) 01-0027-07
10.13307/j.issn.2096-3122.2017.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