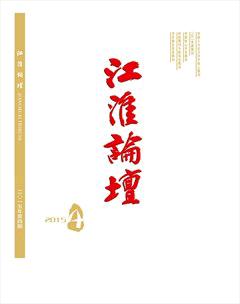戴震與儒學哲理化進程的終結*
陶 清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合肥230051)
戴震與儒學哲理化進程的終結*
陶清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合肥230051)
儒學究竟是維系人心、規范人的社會關系的人生學問,還是由概念辨析、邏輯推理所建構的哲學系統,這是儒學研究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研究所必需思考和直接面對的大問題。戴震直面儒學失卻匡范人心、維系倫常的社會功能以及宋明新儒學“以理殺人”的現實,延續儒學傳統的經典詮釋學的方法,從思想理論上分疏和辨析了儒學作為學問和作為哲學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社會功能和效應,從而提出和完成了終止儒學哲理化進程以回歸其學問特質的歷史性任務。出于思想理論分疏和辨析尤其是學術論戰的需要,戴震的學術思想、特別是通過經典詮釋學所實現的他的學術思想的理論精華和思想貢獻,仍然屬于哲學范疇;但是,戴震哲學以后,以儒家學問為思想理論資源的“道德的形上學”的理論建構和思想實現已無可能。
戴震;儒學;哲理化;宋明新儒學;理與欲
從根本上說,以孔孟為代表的原始儒學,就是道德治理學問。隨著中國社會各種矛盾在歷史進程中的深化和激化,以及各種學術思想和流派為爭奪占有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話語權力而展開的角逐,啟動了儒學思想發展的哲理化進程。其中,孟子出于思想論戰(“辯楊墨”)的需要,過多地討論了“心性”、“善惡”等理論問題,使得原本在孔子那里隱而不顯、懸設喻義的“性與天道”命題浮出水面,開啟了儒學自身哲理化進程的源頭活水;漢唐儒學關于“天”與“性”的反復談論,實乃孟子所開啟、荀子推波助瀾的儒學自身哲理化進程的源頭活水之濫觴;至宋明新儒學,關于“理氣”、“理欲”、“心性”、“知行”條分縷析的概念辨析和因果主導的邏輯推論幾呈汪洋之勢,儒學自身哲理化達致峰巔。明末清初,尤其是明清鼎革的歷史事變,“天崩地坼”的社會現實迫使一大批思想家,特別是其中的儒家學者深刻反思和反躬內省自己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問題;改弦易轍、拒斥理學(宋明新儒學)的路徑依賴以回歸原點,成為當時的哲學思想大家的基本共識。[1]然而,由于明末清初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特別是清初統治者的思想文化禁錮政策實施和當時的哲學思想大家的“明遺民”社會角色的自我選擇,他們的思想對當時的社會運行甚至于學術理論界的影響極其有限。(1)由明末清初哲學思想大家所發軔的、終結(2)儒學哲理化進程以回歸原始儒學本旨的歷史任務,最終由戴震完成。
一、生與死:理想道德懸設與人的生存權利的沖突
原始儒學關于倫理準則和道德規范的文化設計,兼具德性論和規范論的雙重內涵。(3)一方面,它以追求個人的德性完善為目標,主張通過個人的道德修養和踐履及社會角色的準確定位,以個人德性的力量自我實現和確證自己的生命價值和生活意義;另一方面,它又通過善與惡、應當不應當等規范調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力圖在實現個人德性完善的同時實現社會秩序穩定和諧,并以之確證個人德性的功德圓滿。由于兼具德性論和規范論的雙重內涵,原始儒學關于倫理準則和道德規范的文化設計就給人以整體圓融而無偏弊、普適的恒久魅力,以至于人們相信不僅可以據之聽訟斷獄,而且半部《論語》就可以治天下。
然而,兼具德性論和規范論雙重內涵的關于倫理準則和道德規范的文化設計,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因為,作為這種文化設計的前提預設,不僅有理想中的“德性人”,而且還有現實中的“社會人”以及活生生的“生物人”。因此,當告子以“生之為性”質疑,楊朱、墨翟以“為我”、“兼愛”倡說,孟軻不能不強辯力辟:賦予“性”以“善”的片面價值規定性且引入“心”的“善之四端”曲為之說,直至痛斥楊墨為“無君無父”的“禽獸”。戴震認為:孟子力辯楊、墨,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事關重大。因為,“蓋言之謬,非終于言也,將轉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于事,害于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后世也,顯而共見;目之曰賢智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相率趨之以為美言,其入人心深,禍斯民也大,而終莫之或寤。辯惡可已哉!”[2]147在他看來,孟子以前的儒家圣賢無辯論的必要,而在孟子以后,不僅孟子的論敵如楊、墨,而且時人知之不多的老、莊,以至于后來傳入的佛教都廣為人知且更加深入人心。因此,為發明和捍衛儒學的“圣人之道”而進行的辨析論戰,不僅不能夠終止,而且必須進行到底。戴震認為自己有責任自任其重,因為,“茍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古圣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后世之仁人而自遠于仁也”。自任其重以至于“自任以天下之重”(孟軻語)的責任感,知而必言以不辜負圣賢之學的使命感,是一個儒者必須具備的品格;自任其重且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就是戴震對自己作為一個儒家學者的自我定位。(4)
需要指出的是,戴震自我期許的不得不辯,與孟子所謂非好辯乃不得已之辯已不可同日共語。戴震的辯論對象,已不再是儒學之外的學派、學說,而是在儒學內部、自詡接續孟子以后的儒學道統的“真儒”乃至“醇儒”,因此,“辟異端邪說”直至斥為“禽獸”的論戰手法已不可再用,而且只能跟隨對手的方法并引經據典以辨明是非對錯。本來,經典詮釋學即通過對儒學經典如“六經”、“語、孟”的理解和詮釋以闡發自己的觀點和思想的方法,是儒家學者代代傳承的治學和表述方法;其中,辨名析理即通過名詞概念的辨析以闡明義理,包括學者本人的新思想和新觀點,是儒學的經典詮釋學的基本的研究和表述方式。僅此而言,論辨本身對戴震來說并非難事。文字考訂、名物訓詁以至于典章制度的因革變易乃戴氏所長,儒家經典,尤其是“六經”、“四書”也早已熟諳于中,然而,戴震卻踧踖再三、欲言又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戴震如此踟躕,如有大不得已?
顯然,戴震的顧忌與論辨對象有關,更與他指責論辨對象的罪名有關。戴震闡發儒學經典義理的代表作有四篇:《原善》、《孟子私淑錄》、《緒言》和《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只是界定儒道之別,如“老聃、莊周之言尚無欲,君子尚無蔽”之類[3]20;《孟子私淑錄》雖然指出程朱之失、陸王之蔽,但嚴守儒與釋道之辨,而且對于二程、朱熹和張載等宋儒多有回護;《緒言》大致不出《孟子私淑錄》范圍,只是反復強調宋儒言性已失孟子言性本旨,仍肯定“嘗求之老、釋,能卓然覺寤其非者,程子、張子、朱子也”[2]140;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兩篇都是自設問答體,且“問者”直指宋儒、程朱,“答者”總是王顧言他或曲意回護;至《孟子字義疏證》則每答必曰六經、孔孟之是與后儒之非,明確指出由于“宋儒出入于老、釋,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為言”以至于“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為言,其禍甚于申、韓如是也”;[2]160-161不僅如此,“宋以來儒者”以一己意見為“理”而辨理欲,“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為禍又如是也”[2]216。至此,真相終于大白:戴震真正的論辨對象就是宋明新儒學,尤其是其代表人物二程和朱熹,雖然戴震仍尊稱他們為“程子、朱子”。戴震指控其論敵的罪名有二:其一,程朱以“理”代圣人立言卻雜乎老、釋之言,世人被“理”責斥致死卻不能申辯、無人憐憫,因此死于“理”尚且不如死于嚴刑酷法;其二,程朱以一己意見為“理”、飲食男女為“欲”辨理欲,將“理”和“欲”對立起來且是此非彼并利用話語權利以上升至治理方略的高度,因此,即使是正當的本能和欲望的滿足和追求也可能被指責為“自絕于理”[2]216,如此“理欲之辨”實際上就是殘忍的殺人工具。試想:挑戰如此龐大的“神圣家族”、尤其是其中以“真儒”儒學道統繼承者自居的程朱(5),且欲加之以“以理殺人”甚于酷吏枉法殺人的罪名,戴震的顧忌也就不難同情地理解,以至于有論者認定:“《疏證》一書約成于乾隆丙申(1776)末至乾隆丁酉(1777)初,此書乃戴氏哲學著述之絕筆。”[2]145
如果以上詮釋語境可以成立,那么,作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的讀者,我們就無法規避文本本身所直接呈現的生與死的沖突,而且必須和作者一起思考:“理”只是“極好至善的道理”[4],何以能夠與人的生存權利相沖突,以至于成為較之酷法更加殘忍的殺人工具?可以設想:戴震的思考,應與他的生活經驗,尤其是與他的故鄉有聯系的生活經驗有關;然而,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只能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馬克思語),只能通過文本的閱讀理解去體認、去詮釋《孟子字義疏證》且企達與作者的視界融合。
在戴震看來,“理”之所以能夠置人于死地且無人敢憐,是因為理學家以“儒學圣賢”代言人自居卻將“理”字認錯,錯在雜乎老莊、釋氏之言故似是實非、以圣賢名義故世人以非為是。戴震認為:“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2]151“理”,是人認識和把握對象的客觀規定性的范疇,正確認識和把握對象的客觀規定性從而理解其運動變化法則才能保證人的活動的合理性,這就是古代圣賢所謂理;因此“理”既不是一個人的想當然,也不是先天地萬物而獨存的一個物,前者即“私”后者是“蔽”,二者是妨礙真理性認識的大敵,“不過就老、莊、釋氏所謂‘真宰'‘真空'者轉之以言夫理,就老、莊、釋氏之言轉而為六經、孔、孟之言”[2]164。如此一來,一方面造成了學術思想及其傳承的混亂。“老、莊、釋氏以其所謂‘真宰'‘真空'者為‘完全自足',然不能謂天下之人有善而無惡,有智而無愚也,因舉善與智而毀訾之”[2]166。與之相同,程朱所謂“理既完全自足,難于言學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氣為二本而咎形氣。蓋其說雜糅付合而成,令學者眩惑其中,雖六經、孔、孟之言具在,咸習非勝是,不復求通”[2]166。而且,由于宋儒不是像荀子、老莊和釋氏在六經、孔孟之后之外另闡己說,而是將前者雜糅附會而入后者,因此,“六經、孔、孟而下,有荀子矣,有老、莊、釋氏矣,然六經、孔、孟之道猶在也;自宋儒雜荀子及老、莊、釋氏以入六經、孔、孟之書,學者莫知其非,而六經、孔、孟之道亡矣”[2]172。宋儒在儒學的名義下偷運老莊、釋氏較之“異端邪說”對儒學的攻擊危害更大,高舉孔孟旗幟而實行老釋之道,“蓋程子、朱子之學,借階于老、莊、釋氏,故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謂真宰真空者而余無所易”[2]172。易言之,宋儒通過偷梁換柱消解了孔孟之道,無異于在思想理論上戕害了宋以后的儒家學者。
另一方面,“理”字既已認錯,以之規范人的活動也就無合理性可言。作為規范人的活動的“理”乃“同情之理”,是制約人的自然生理需要和情欲合理性的準則;“合理”首先必須“合情”,“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2]152。“同情之理”也就是“天理”即“自然之分理”,“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2]152。人都有自然生理需要和情欲,這是由人的本性的自然屬性層面,即以本能和欲望的形式存在于人身上的自然生理需求所規定的。人的自然生理需要和情欲必須得到滿足,否則不能生存;個人的自然生理需要和情欲的滿足又必須具有合理性,否則就會威脅他人的生存且危及自己的生存。在生與死之間持存一個合理性的尺度,無需反思只需反省體認,“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為好惡之節,是為依乎天理”[2]152。為什么一定要“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這也是因為自己與他人都是人,是人就只能在社會關系中生存,這是由人的本性的社會屬性層面,即以與人交往的形式存在于人身上的社會交往的需要和追求規定的。[5]不在社會關系中存在的人,是抽象的、想象中的“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必須在與他人的關系中獲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在己與人皆謂之情,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2]153。因“以情絜情而無不得其平”,故“圣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2]161;由于以“天理”為先后天地人物而獨存且與“人欲”截然反對、不可兩立的“物”,又由于“人知老、莊、釋氏異于圣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于宋儒,則信以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2]161。因此,以儒家圣賢真理的面目呈現且為希賢希圣的“上位者”治理“下之人”的“治人”手段,“天理”也就不能不成為合理合法且絕對正確的“殺人”工具。“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于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同欲達之于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為言,其禍甚于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之書,豈嘗以理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發為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2]161作為“極好至善的道理”的“天理”,就是這樣合理合法且絕對正確地殺人的。
二、理與欲:關于倫理準則和道德規范的文化設計與人的本性的沖突及和解
戴震指控程朱等宋儒“以理殺人”的罪名之一,是以離經叛道的“一己意見”為“理”和“天理”指導社會實踐,社會上的“上位者”又信奉此“理”和“天理”為古代圣賢之道而以之治“下之人”,因“不通情理”而“不合情理”故不能“合情合理”亦在“情理之中”。從根本上說,儒家只是以“通情達理”調諧社會關系、維系人心倫常的學問而不是以形而上的“理念”范定人們的思維的哲學,即使這種“理念”“完全自足”、“至善極好”,與百姓的“日用飲食”[2]153日常生活世界有何關聯?因此,宋明新儒學家即使沒有直接“以理殺人”,也必須承擔因“理”而置人死地的社會責任,因為“希賢希圣”的“上位者”就是以此“理”“治人”的,從儒學的社會功能和實際效應看,于情于理,理學家們都難辭其咎。
戴震認為:宋明理學家之所以將“理”字認錯以至于造成“以理殺人”的社會惡果,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用老莊、釋氏所謂“完全自足”的“真空”、“真宰”來詮釋“理”,尤其是將“理”界定為先天地人物而獨存的“極好至善的道理”,因此,一切妨礙存養此“理”即與“理”相對而立的“氣”稟所有,統統都在克制棄絕之列。“程子、朱子謂氣稟之外,天與之以理,非生知安行之圣人,未有不污壞其受于天之理者也,學而后此理漸明,復其初之所受”[2]166。“天理”獨存,是程朱與老莊、釋氏所謂“完全自足”的“真空”、“真宰”者同;“學而后此理漸明”,是程朱與老莊、釋氏所謂“絕圣棄智”、“絕仁棄義”的“絕學”者異。然而,既然“復其初”以明“天予之以理”的“學”只是“復其初之所受”,那么,這樣的“學”就不是儒家的學問,而是老莊、釋氏的“絕學無憂”。“試以人之形體與人之德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乎長大;德性始乎蒙昧,終乎圣智。其形體之長大也,資于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非‘復其初';德性資于學問,進而圣智,非‘復其初'明矣。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所清明,異于禽獸之不可開通。然人與人較,其材質等差凡幾?古圣賢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老、莊、釋氏謂有生皆同,故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問學以擴充之。”[2]167這樣,宋明新儒學家實際上也就建構了這樣一種思維取向和定式:凡源于“理”的,就都是好的,都在主敬存養之列;凡生自“氣”的,就都是有害的,因而皆在必去必滅之列。在戴震看來,這樣一種思維取向和定式的典型范式,就是“存天理滅人欲”。戴震認為:正是這種“理”“欲”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支配下的“理欲之辨”,才是宋明新儒學家“以理殺人”的真正原因和根據。[2]216
首先,“理欲之辨”以“正邪”判“理欲”,必然導致建立在因果關系之上的道德分析的邏輯推論:只有滅人欲才能存天理,乃是正義所規定的唯一選擇。其經典依據,就是《樂記》所云:“滅天理而窮人欲”和《中庸》所謂:“君子必慎其獨。”戴震認為這是對儒家經典的誤解。因為,從“理”“欲”的本來關系看,二者同出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的自然屬性層面規定了人生而即有自然生理本能和欲望,而且必須得到滿足和實現;但其滿足和實現不能是無節制的,無節制地窮人欲違悖了自然萬物“節而不過”的“相生養之道”,因此,“滅天理而窮人欲”,實際上是“言性之欲之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為正,人欲為邪也。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2]162這才是通過理欲之辨所揭明的理欲之間真正的本來關系。至于“慎獨”,確實存在著“正邪”之分,卻與“理欲之辨”無關,遑論“存理遏欲”!在戴震看來,人的行為和活動,都是受人的意識(“志意”)支配的。人的意識有“敬肆”之分,人的行為和活動也就有“正邪”之別。“敬者桓自檢柙,肆則反是;正者不牽于私,邪則反是。必敬必正,而意見或偏,猶未能語于得理;雖智足以得理,而不敬則多疏失,不正則盡虛偽。”[2]163因此,以“正邪”判“理欲”的“理欲之辨”,實際上就是以“一己意見”得出的價值判斷規定乃至取消事實判斷,其結論必然荒謬、結果必然惡劣。
其次,“理欲之辨”以“物”代“物則”,必然導致由具體上升到抽象的思維過程的倒置;從具體中抽象出來的思維的抽象物取代客觀實在,“理”也就只能成為不可學知的先天獨存,只能以去害存養的方式葆有。戴震認為:“理”與天地人物的本來關系,就是客觀事物與其運動變化法則的關系;之所以必須以抽象思維的方式去把握法則,因為,把握了法則也就把握了事物及其運動變化的普遍實在性和客觀必然性。他說:“物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則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實體實事,罔非自然,而歸于必然,天地、人物、事為之理得矣。夫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事物之委曲條分,茍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懸,平者之中水,圓者之中規,方者之中矩,然后推諸天下萬世而準。”[2]164實際存在著的事物,都有其運動變化的法則,因此,法則并非獨立于事物的客觀存在,而是事物運動變化所表現和實現的客觀必然性;人的認識是關于這種客觀必然性的認識和把握,以保證自己認識的真理性并指導自己的實踐行動的成功,而不是以這種抽象思維的產物取代認識和誤導實踐。否則,思想理論上的混亂和誤植,一方面必然導致學術思想及其傳承的混亂,因為,“舉凡天地、人物、事為,求其必然不可易,理至明顯也。從而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為之理,而轉其語曰‘理無不在',視之‘如有物焉',將使學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非六經、孔、孟之言難知也,傳注相承,童而習之,不復致思也。”[2]165另一方面,也必然誤導社會治理實踐。對于老莊、釋氏來說,只求“完全自足”、“因舉善與智而毀訾之”[2]166,“既守已自足矣,因毀訾仁義以伸其說”[2]167;一旦訴諸實踐,“實動輒差謬。在老、莊、釋氏固不論差謬與否,而程子、朱子求道之心,久之知其不可恃以衡鑒事物,故終謂其非也”[2]168。由思想理論上的錯誤,必然導致學術思想及其傳承的悖道乖離,必然導致社會治理實踐的禍民害民,這是建立在有物有則的實踐理性基礎之上的事實驗證。儒學作為一門以成功的社會治理實踐為旨歸的學問,就是通過先知知后知、先覺覺后覺的思想傳承方式,以問學培養德性、以擴充塑造品行去成就品學兼優的學者;品學兼優的學者學而優則仕且仕而優則學,則仁政王道行而“斯世因此而見儒者作用,斯民因此而被儒者膏澤”[1]772-773。這就是作為學問的儒學與其他一切學術思想流派和理論體系所不同的特質,也是戴震之所以“吾用是懼,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2]148力辨宋明新儒學確系非儒學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最后,“理”、“欲”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必然在理論上推導出“理氣二本”的理論謬誤,必然在實踐上導致“滅欲存理”的實際禍害。“理”“欲”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與“滅人欲存天理”因果關系的道德分析不同,是一種普遍的價值思維范式,它一方面要求將一切處于相對相關、相互作用著的事物和現象,都置于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框架中去思考;另一方面,它又將一切處于相對相關和相互作用著的對象性關系的兩個方面,武斷地賦予片面的價值規定,表現為邏輯結論預成的獨斷論。戴震指出:在宋明新儒學那里,從自然界的“化”與“神”到人身的“血氣”與“心知”,從天地人物的“形體”與“性”、“陰陽”與“道”到人的身心之間的“欲”與“理”,無不處于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單邊思維的模式之中。[2]169-172這樣一種普遍的價值理性的思維范式,在理論上必然由邏輯推理最終抽象而至“理氣二本”,在實踐上必然因片面地價值規定而預設是非善惡以禍害無話語權力的斯民。
在戴震看來,宋明新儒學的“理”“欲”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之所以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從根本上說,是原點即錯故路徑全非。戴震認為:原始儒學的原點選擇,乃是基于古代圣賢關于人的本性的深刻洞見,基于此見的關于倫理準則和道德規范的文化設計即為儒學之道,循此道以教化材質各異之人以歸于人道,這就是原始儒學原點與路徑相統一的根本,即所謂“性”、“道”、“教”一以貫之之道。在儒學圣賢看來,人與禽獸的區別,不在“知懷生畏死,因而趨利避害”[2]181,也不在于“私于身者,仁其身也;及于身之所親者,仁其所親也”[2]181,因此,“自然”、“仁義”以至于“知覺運動”[2]182均不足以別人獸,但又不能舍棄“自然”、“仁義”、“知覺運動”去別人獸,關鍵在于能否“懿德”,即將人與某些群居動物共有的“德性”轉化成為美好的德行。儒學圣賢基此關于人的本性的深刻洞見,通過文化設計設定的倫理準則和道德規范,以引導和轉化人的“德性”為美好的德行,“此可以明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于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之,以歸于靜,歸于一,而恃人之心知異于禽獸,能不惑乎所行,即為懿德耳”[2]184。不離“自然”、“仁義”、“知覺運動”,籍學問資養,尤其是學以致用致知于行以擴充之,才能以轉化“德性”為美好的德行,將自己由本能和欲望的世界提升至價值和意義的世界,從而通過生物進化基礎之上的文化進化的人的方式把自己與動物區別開來。顯而易見,儒學圣賢如此理欲不即不離、一元統合的思維方式,與宋明新儒學“理”“欲”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確實有著本質的區別。個中緣由,在戴震看來,只因“古圣賢所謂仁義禮智,不求于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而后儒以為別如有物湊泊附著以為性,由雜乎老、莊、釋氏之言,終昧于六經、孔、孟之言故也”[2]184。“理”之于“欲”、或者說源于人的本性的深刻洞見的關于倫理準則和道德規范的文化設計,原本和諧的升華之道,卻因錯誤的思維方式而兩相沖突乃至勢不兩立。因此,消弭沖突、走向和解,關鍵就在于思維方式的轉換。但是,思維方式的轉換并不像脫衣換衣那樣簡單,而需要跟隨對手的思維路徑去探其本源以正本清源。因為,只有源潔才可能流清、本真才可能末實。
三、形而上與形而下:作為哲學的儒學與作為學問的儒學的沖突
揭橥后儒、尤其是宋明新儒學的“理”“欲”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與古圣賢,特別是孔孟原始儒學的理欲不即不離、一元統合的思維方式的本質區別與對立,戴震關于宋明新儒學尤其是程朱“以理殺人”罪責的指控得以坐實。但是,聽訟斷獄于儒家實出于大不得已,息訟空獄才是儒家之所長。因此,個人以為,戴震關于宋明新儒學尤其是程朱“以理殺人”罪責的指控,本不在于故作駭人聽聞語以嘩眾取寵,更不在于宣稱唯我獨是以取程朱而代之,甚至不在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重建思想秩序”[6],而只在于揭明作為哲學的儒學和作為學問的儒學所具有不同的乃至截然反對的社會功效,從而還儒學以學問的本來面目。
在戴震看來,還儒學以學問的本來面目,需從辨明形而上下始。戴震認為:原始儒學也談論形而上與形而下的關系問題,但從未以二元分離乃至對立的方式談論。如“道”與“陰陽”,儒學經典如《易》“直舉陰陽,不聞辨別所以陰陽而始可當道之稱,豈圣人立言皆辭不備哉?一陰一陽,流行不已,夫是之謂道而已”。“六經、孔、孟之書不聞理氣之辨,而后儒創言之,遂以陰陽屬形而下,實失道之名義也。”[2]176-177宋儒之所以將形而上與形而下對立起來而自創“理氣之辨”,而且直逐形而上,如道、太極、理之類,在戴震看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欲借階老莊、釋氏,以言儒學圣賢所未言的“性與天道”。宋儒“考之六經、孔、孟,茫然不得所謂性與天道者,及從事老、莊、釋氏有年,覺彼之所指,獨遺夫理義而不言,是以觸于形而上下之云,太極兩儀之稱,頓然有悟,遂創為理氣之辨,不復能詳審文義。其以理為氣之主宰,如彼以神為氣之主宰也。以理能生氣,如彼以神能生氣也。以理壞于形氣,無人欲之蔽則復其初,如彼以神受形而生,不以物欲累之則復其初也。皆改其所指神識者以指理,徒援彼例此,而實非得之于此。學者轉相傳述,適所以誣圣亂經”。[2]179
宋明新儒學借階老莊、釋氏以言“性與天道”且尊揚形而上而貶抑形而下者,與荀子的論“學”論“性”亦有關聯。荀子論“學”,肯定常人可以學而為圣賢,但又強調學禮義以變化氣質,因為人性本惡,“而于禮義與性,卒視若閡隔不可通”[2]187。因此,“荀子知禮義為圣人之教,而不知禮義亦出于性;知禮義為明于必然,而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極則,適以完其自然也”[2]188。儒學圣賢基于人的本性的深刻洞見的文化設計與常人之性,問學以資益德性且學以致用的擴充德性與學習“禮義”,至此斷為兩截、隔如天淵,儒家“性學”歧而不明。宋明新儒學兼采孟荀、欲合善惡而適以病性,又以理氣清濁、揚濁澄清論學而恰入老莊、釋氏彀中。因“彼荀子見學之不可以已,非本無,何待于學?而程子、朱子亦見學之不可以已,其本有者,何以又待于學?故謂‘為氣質所污壞',以便于言本有者之轉而如本無也。于是性之名移而加之理,而氣化生人生物,適以病性。性譬水之清,因地而污濁,不過從老、莊、釋氏所謂真宰真空者之受形以后,昏昧于欲,而改變其說”。[2]191其實,性之善惡皆權而非經,下學上達與我宰非我(6)路徑相反,豈能兼容調和、綜合創新?“若夫古圣賢之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擴而充之者,豈徒澄清已哉?程子、朱子于老、莊、釋氏既入其室,操其矛矣,然改變其言,以為六經、孔、孟如是,按諸荀子差近之,而非六經、孔、孟也。”[2]192
宋明新儒學既欲借階老莊、釋氏以言古圣賢之所未言,又援引老莊、釋氏之學消解儒學內部之分歧,因此,形而上的尊崇與追逐和形而下貶斥與曲解,而且所有這一切都是以圣賢的名義在儒學內部、名正言順且無所不窮其極地進行著,宋儒已經走上了儒學哲理化的不歸路。在戴震看來,跟隨宋儒的思維路徑以探其本源且通過字義疏證和概念辨析以揭明其失足之處,是必須有人來做的極其重要的工作。但是,通過字義疏證和概念辨析以詮釋儒家經典,追隨圣賢言行以訴諸儒學之道,則是更為重要的工作且只能由真正的儒者擔當。而如此去做的必要和重要的前提,就是如何去思,去思那已言未聞的“性與天道”。[2]147-148
戴震認為:原始儒學并非不談“性與天道”,但是,關于“性與天道”的談論,不是出于驚異好奇而滿足自己的求知欲望,而是出于維系人心、安定社會以自我實現和確證自己的生命價值和生活意義的需要和追求,因而也就不是以純粹理性思而辨之,而是以情絜情實而踐之。如“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2]197。既然人的本性如此,思想者的任務就是為其滿足和實現提供合理性標準,以及合理地滿足和實現自己本性的需求的途徑、方法和手段。“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2]197反之,己所不欲,必施于人;己之所欲,必禁于人,焉能通人情得人心,遑論籍此得天下。
以情絜情,又并非不愛智慧。但是,愛智慧,更需愛他人;否則,蔽于一己聰明而私于一己之欲,也就既不心安也不明智。因為,“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丑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后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為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為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為蔽,蔽則差謬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圣智也。”[2]197也許,作為推動人類歷史前進杠桿的“惡”,也應當加以“不私”、“不偏”、“不蔽”的限定也未可知。可以肯定的是,一個“理”字,即使是完全自足的“絕對理念”,也絕無可能變惡為善。
再如“道”。儒學圣賢視“天”為自然而然,因此也就沒有類似“天之所以為天”之類關于“始基”的反思之必要。戴震認為,原始儒學從不離開“性”而談論“道”,因此,儒學所謂“道”,首先是指“人道”。“人道,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2]199而且,儒學所談論的“道”和“性”,都是談論具體事物及其通過運動變化所實現和所表現出來的普遍實在性和客觀必然性而非抽象概念,因而也就不必擔心邏輯悖論而為談論本身劃定界限;但必須為人盡性達道的行為和活動設定準則,以保證人人都能遂欲達情以盡人道。戴震說:“曰性,曰道,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純粹中正之名。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一事之善,則一事合于天;成性雖殊而其善也則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于必然,適完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道于是乎盡。”[2]200-201在戴震看來,儒學之道實際上也就是人人由之且循之可以自我實現和確證自己的生命價值和生活意義的自由之路,而宋儒之道(“理”)則反是。“古圣賢之所謂道,人倫日用而已矣,于是而求其無失,則仁義禮之名因之而生。非仁義禮有加于道也,于人倫日用行之無失,如是之謂仁,如是之謂義,如是之謂禮而已矣。宋儒合仁義禮而統謂之理,視之‘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此為‘形而上',為‘沖漠無朕';以人倫日用為‘形而下',為‘萬象紛羅'。蓋由老、莊、釋氏之舍人倫日用而別有所謂道,遂轉之以言夫理。在天地,則以陰陽不得謂之道,在人物,則以氣稟不得謂之性,以人倫日用之事不得謂之道。六經、孔、孟之言,無與之合者也。”[2]202-203
戴震認為:辨明原始儒學之“性與天道”與宋明新儒學以“理”言“道”的本質區別的目的,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蓋言之謬,非終于言也,將轉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于事,害于政”[2]147;“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禍于人也大而莫之能覺也;茍莫之能覺也,吾不知民受其禍之所終極”。[2]215如:宋明新儒學以人倫日用、飲食男女為“欲”,即使是正人君子也難免被據“理”而求全責備,似乎不食人間煙火、無情感無欲望如泥塑木雕一般,才是道德化身,“此理欲之辨使君子無完行者,為禍如是也”;以無情無欲之泥塑木雕為君子且非君子即是小人,如此自設標準且“不是……就是……”的單邊思維模式將有情有欲之飲食男女置于生即罪過死則“自絕于理”的生存困境,“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為禍又如是也”。欲望必須得到滿足、情感必須得到實現,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現實的和有血有肉的人天賦即有的自然屬性的規定性,硬要將之與“天理公義”對立起來、非此即彼,那就只能迫使“下之人”開動腦筋運用生存智慧和技巧虛與周旋、欺瞞偽善,“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為欺偽之人,為禍何可勝言也哉”[2]216-217。如此“理欲之辨”一旦為統治階級采信以為社會治理方略,必然為害社會;天下之人盡信程朱為躬行實踐之真儒,則必然禍國殃民。儒家學問一旦因形而上升華為哲學,如宋明新儒學借階老莊和釋氏且深入荀告之歧途的所作所為,禍國殃民的負面效應和惡果也就在所難免。
結語:在《孟子字義疏證》的字里行間,戴震的踧踖躑躅躍然紙上。戴震的顧忌,還不是投鼠忌器,畢竟程朱不是“鼠”,雖然未投之“器”已面目全非;也許因為罪名雖已坐實,但沒有犯罪動機存在的任何證據。以程朱為代表的宋明新儒學,是在孔孟名義下的借階老莊、釋氏,是在力辟異端旗幟下的詮解儒學元典本旨,是在爭奪話語權力的思想交鋒中重建儒學本體的努力,是在人心不古以致人欲橫流歷史環境中扶植綱常以重整人心的奮斗,其間種種酸甜苦辣實不足以與外人道;只是善良的愿望并不能保證一定就有良好的社會效益。理論與實踐之間錯綜復雜、瞬息萬變的互動關系,現實的生存狀況與理論懸設間如隔天淵、巨大反差的沖突,以及諸如正統與異端、破舊與立異、為人與做事以致說理與斥罵、文字與義理、敬其人與惡其言之間說不清道不明又必須說道的“煩惱”、“苦悶”,都使得戴震不得不開口必援引所據、落筆必本諸元典,用心良苦、步步為營,作者彼時的種種喜怒哀樂好惡懼已很難為此時的讀者所絜矩,更無論“視界融合”。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戴震以后,以原始儒學經典、如“六經”和《論語》為思想理論資源,接著抑或照著“孔圣之學”講哲學,已無可能。誠然,借階西哲甚或以西哲為標準和根據,接著甚至照著宋明理學講,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現實的。只是,捫心自問:倘若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欲望尚且不能滿足,極好至善、完全自足的“理”即使是“天理”,對我來說確實既無價值也無意義。
注釋:
(1)這一觀點,已受到葛兆光教授的質疑。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91頁,頁下注①。
(2)本文所謂“終結”,是在“界定”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海德格爾曾經說過:如果有一個銀盤被它的制造者界定為宗教祭祀活動使用的祭器,那么,對于這個銀盤來說,“這個界定終結了這個物”。參見:《海德格爾選集》,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928頁。
(3)關于德性倫理學與規范倫理學的區分和聯系,可參見高國希《當代西方的德性倫理學運動》一文,載《哲學動態》2004年第五期第30-33頁。
(4)戴震的這一標準,與其前輩已有距離。如黃宗羲訓“儒”之義曰:“統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也,圣也。”(《南雷文定》首集卷四,<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唐甄說:“儒之為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何異于匹夫匹婦!”(《潛書·辨儒》)可見在明清學者心目中,做一個儒者并不容易。
(5)可參閱:葛兆光著《中國思想史》第二卷,第212頁;第226-228頁。
(6)指老莊、釋氏之學。參見《孟子字義疏證》第191-192頁。
[1]陶清.明遺民九大家哲學思想研究[M].臺灣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2]戴震.戴震全書·孟子字義疏證(第六冊)[M].合肥:黃山書社,1995.
[3]戴震.戴震全書·原善(第六冊)[M].合肥:黃山書社,1995.(《原善》、《孟子私淑錄》、《緒言》、《孟子字義疏證》,載《戴震全書》第六冊)
[4]朱熹.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88:2549.
[5]陶清.性學研究·中國傳統學問的自我體認和詮釋[M].海口:.南方出版社,2000.
[6]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212,413-424.
(責任編輯吳勇)
B249.6
A
1001-862X(2015)04-0135-008
本刊網址·在線雜志:www.jhlt.net.cn
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儒學的重建”(AHSKY2014D144)
陶清(1955—),安徽懷寧人,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傳統文化及其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