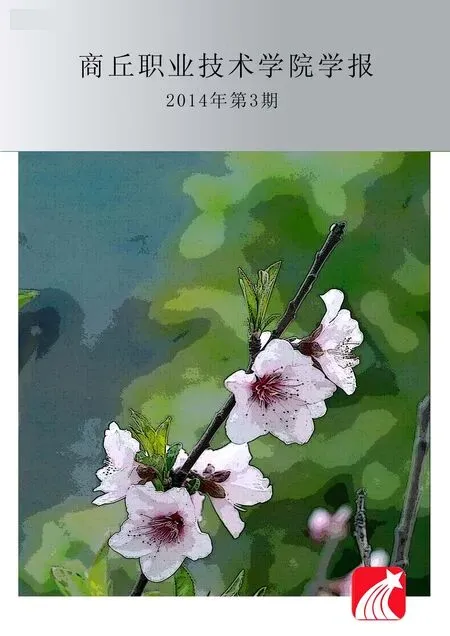佚書《魯連子》的藝術及思想特色
劉 金
(北京語言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83)
魯仲連(又稱魯連子、魯連、魯仲連子),戰國時期齊國人,“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1]2459長久以來人們多依據《戰國策·齊策》和《史記·魯仲連列傳》的記載,把魯仲連當做歷史人物進行品評。但是,對于記載了魯仲連行事、言語的佚書《魯連子》,卻鮮有問津。本文主要對佚書《魯連子》所反映出的魯仲連思想及其行文藝術特色作初步的考察。
一、關于佚書《魯連子》偽書辯
在考察前,必須要對《魯連子》進行偽書辯。《魯連子》是偽書的觀點古已有之。古今人大多從事件發生時間的混亂和史實的誤差兩方面來論證該書是偽書。宋·蘇轍《蘇氏春秋集解》、宋·呂大圭《呂氏春秋或問》、清·邵泰衢《史記疑問》,從史實的角度切入,因佚書《魯連子》中出現了不合歷史實際的明顯錯誤,從而認定該書是偽書[2]。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今人錢穆《先秦諸子系年·魯仲連考》,從時間的角度考證,因佚書中出現個別的史實時間錯雜混亂,而認定為偽[2]。同時,也有部分學者對上述的偽書證據進行反駁,如王德敏、周立升《魯仲連雜考》,利用大量的史料、邏輯思辨和出土文物,針對錢穆先生的質疑,提出了有力的反駁[3]67-68。綜合各家觀點,我們認為斷定《魯連子》是偽書、記載魯仲連的資料是不可靠的論斷,其依據是不足的。余嘉錫先生在《古書通例》中就曾指出:“自漢武以后,九流之學,多失其傳。文士著書,強名諸子,既無門徒講授,故其書皆手自削草,躬加撰集。蓋自是而著述始專……后人習讀漢以后書,又因《隋志》于古書皆題某人撰,妄求其人以實之,遂謂古人著書,亦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于其中雜入后人之詞者,輒指為偽作,而秦、漢以上無完書矣。不知古人著述之體,正不如是也”[4]119。《魯連子》的文本大致也是如此,因而不能因一些時間、史實上的矛盾就認為其為偽書。我們可以說,《魯連子》所載史料,應該是可信的,只是該書在流傳編寫的過程中,有錯字、衍文或是時間顛倒的情況,而有些錯誤則是后人畫蛇添足造成的。
有關《魯連子》佚書的輯佚情況,根據學人考察,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是所輯佚本中“材料最豐,用力最勤”的一部[2],今人張秉楠《稷下鉤沉》則對《魯連子》的史料進行了點校,以享后代。本文對佚書《魯連子》的考察,則依據此二書。
二、佚書《魯連子》的藝術特色——用形象生動的故事說明道理
佚書《魯仲連》按照記述事件的不同,可分25個小節,各個小節的長短不一。“義不帝秦”和“射書救聊過”是篇幅最長、記述最詳實、最能顯示魯仲連風格特點的事件。故事均收錄在《史記·魯仲連列傳》和《戰國策·齊策》中。為了說服新垣衍和趙國不帝秦,魯仲連舉了鮑焦、齊威王同周關系由尊到破裂、醢梁王、魯鄒小國義不帝齊(閔王)以及帝秦檜嚴重威脅到新垣衍財富地位等5個例子;“射書救聊城”同樣是通過列舉古人管仲、曹沫等人的實例來說明不“規小節”、不“惡小恥”才能成榮明立大功,又從齊國上下會全力爭聊城、燕國國內因戰爭而困頓不堪的現實情況出發,對死守聊城的燕將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終說服燕將放棄守城,魯仲連不費一兵一卒憑借口舌為聊城百姓解圍。兩個長篇在列舉事例的同時還穿插精致的說理言論,從而使事件和理論得到了有機的統一,更加增強了說服性。另外的23則都是短小精悍的故事,有的甚至只是一句話的諺語,如:百足之蟲,至斷而不蹶者,持之者眾也。除了最后一則“子曰君子能仁于人”是單純的道理格言,其他24則或用形象生動的小故事,或用歷史人物,或用社會上的軼事佚人來說明一個道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魯仲連用門關來說明何謂“勢數”,用淺顯常見的事例清楚明白地說明了比較玄虛的勢數。這樣就使得整部佚書讀起來輕松易懂,形象深刻。需要指出,作者在文中只是單純敘述這些形象的事例,并不對事件進行褒貶、也不發表自己的觀點言論。但是從記錄的事例來看,這些中性色彩的事例主體比較集中、明晰,還是能夠很清楚地看出魯仲連的思想。
至于佚文中出現的一些無頭無尾的段落,像“契始封商,在太華之陽。松樅高千仭而無枝,非憂王室之無柱也”、陸子謂齊愍王曰“魯費之眾臣,甲舍于襄賁”、朐劇之人辯等,結合其他較完整小節的書寫情況,據推測,應是原文在傳抄的過程中發生了脫落,只剩下了一些殘章。還有一種情況值得我們注意,“義不帝秦”和“射書救聊過”兩節篇幅上明顯同其他尚存完好、首尾連貫的小節有太大的差距,又兩節均存于《史記》和《戰國策》中,所以就此可推論,該兩節在內容上受到了后人的增補潤飾。
三、佚書《魯連子》的思想意蘊——勢數思想
《魯連子》雖然在《漢書·藝文志》中被列為儒家,但是他的思想與儒家有很大的不同。縱觀其說,他有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也有縱橫家游說的影子;他受名家辯術的影響,講求辯術,但卻理論聯系實際,不是一味地空談;他受墨家影響,具有明顯的“兼愛”“非攻”的思想,但最后隱居海上,亦有道家遁世之風[5]34-35。蓋其人志意橫溢,不拘一家學。
馬國翰在序中說,《魯連子》一書的主旨思想“在于勢數,未能純粹合圣賢之義”[6]1159。此說甚是恰當。關于“勢數”的內容,魯連先生見孟嘗君于杏堂之門,對此有著形象的說明:
魯連先生見孟嘗君于杏堂之門。孟嘗君曰:“吾聞先生有勢數,可得聞乎?”連曰:“勢數者,譬若門關,舉之而便節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勝。關非益加重,兩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彼可舉,然后舉之,所謂勢數。”
魯仲連以舉門閂為例,為孟嘗君說明所謂“勢數”就是學會找到事物內在規律,并且懂得利用這個規律。比如舉門插,如果手放在門插的合適地方,便可以一個手指毫不費力地舉起;若沒有放在正確的位置,那么兩只手都舉不動。原因就在于順“勢”而行。事情可行,然后再行動,在行動時懂得找規律、用規律,就是“勢數”。在第二則孟嘗君逐于齊而復返章中,譚拾子以“事之必至,理之固然”來勸諫孟嘗君。譚拾子拿市場早上因物品豐富而人滿,晚上因物品買完而人走為例,來說明事物發展有其必然結果,道理發展有其必然規律,從而讓孟嘗君坦然接受那些因自己失勢而被判自己的齊國士大夫們。
魯仲連的“勢數”思想一方面來自于他的老師“徐劫”。在《玉函山房輯佚書》諸子部中有《徐子》一書,其中記載徐劫以“百戰百勝”之方法說魏太子不要攻齊,但魏太子終因抵不過外界的力量,而不得不攻齊,后戰死。徐劫早已預測到外界會強迫魏太子攻齊,故他對自己勸說的無效采取了一種非常達觀的心態。從這里可以看出,魯仲連老師徐劫的思想有著順事物發展規律的特點。另一方面,“勢數”還受到孟子、荀子的影響。雖然文獻中并沒有直接明顯的例子,但是從孟、荀對“數”的解釋,還可以從中窺探到“勢數”的影子。如《荀子·富國》云:“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義)而有用為人,數也。”《孟子·告子上》云:“今夫弈之為求,小數也”。由此可知,“數”是指小的技術、方法。所謂方法,其實也是需要掌握內在規律。
魯仲連的“勢數”同法家學派的“勢”的觀點是不同的。韓非子在《難勢》中說:
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于自然,則無為言于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
從這里可以看出,“勢”的觀點在戰國時代應該是一個流行詞匯,但是各家對它的解釋不同,在韓非子看來,“勢”就是君主要運用各種手段使自己處于獨尊的地位,用“權勢”來腳注此“勢”應該更確切,也就是利用權勢來保證君主的獨裁統治。韓非子謂“勢必于自然,則無為言于勢矣”可知,魯仲連有遵循規律之意的“勢數”,應該是當時社會上比較流行、人們廣泛接受的一種觀點。
從現存《魯連子》佚書的材料看,魯仲連的“勢數”顯然沒有法家的陰謀權勢,更多的是帶有孟荀的方法、方術之義。但是他又不同于孟子以高唱“仁政德治”來實現“王道”的治國理想,他的順其規律自然發展的觀點更加接近于荀子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那種一切遵循自然態勢變化的觀點。
通過與孟、荀、韓非子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魯仲連的勢數思想繼承并發展了孟、荀儒家一派的注重規律、方法義,沒有韓非子法家派的陰謀權勢,也受到自己的老師——稷下學者——徐劫的影響,同時他的思想、創作也印有戰國時期說客的縱橫風。下面從用人、治國、歷史三個角度看“勢數”的反映。
(一)人才觀
“勢數在”的用人策略就是從現實觀察,找到人才的個性特點,從而做到用人所長,舍其所短。在第一則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章中,魯仲連用“猿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貍,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擋,使曹沫釋其之劍,而操銚耨與農人居垅畝之中,則不如農夫”三個接連比喻說明“物舍其所長,用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的用人觀,最終使孟嘗君心悅誠服地不再逐客。第十七則古善漁者宿沙瞿子章中:
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宿沙非闇于漁道也,彼山非魚之所生也。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以通俗清晰的事例進一步證明人才只有用在合適的地方才會發揮作用。在第十則陳無宇問門客章也體現出要知道人才看重的地方,然后對癥下藥才會發揮作用。“君不能與所輕與士,欲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在位者如果連自己最不重視的財物都不惠及門客,那又有什么資格要求門客在危險之中用生命來捍衛國家呢?可見,如果要門客能夠侍君以至身,那在位者一定要體現出足夠的誠意來待門客,物質享受應該是最好的表達方式。像孟嘗君那樣,為了使門客們有更好的物質享受,寧愿自己節儉。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這點呢?在第十二則人心難知于天章魯仲連提出:“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冬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為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純薦也。”人君所察,主要的一點就是人才的選拔,人君在選拔人才時應清楚此人此時可不可以用,能不能勝任此差以及在某個具體情況下適合不適合任職,只有這樣考慮周全,才能發現人才的內在特點,掌握用人規律,從而不至于出現“冬耕”、“方輪”、“棉墊子”這類違背規律、導致結果惡化的事情出現。
魯仲連人才觀還認為人才要為國家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隨意高談闊論。第八則齊之辯士曰田巴章說得很清楚:
魯連往謂田巴曰:“臣聞堂上之糞不除,郊草不蕓,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則?急者不救則緩者非務。今楚軍南陽,伐高唐,燕人十萬眾在聊城而不去。國亡在旦暮耳,先生將奈何?”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夫危不能為安,亡不能為存,則無為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眾為所貴談,談者其若此,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惡之,愿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聞教。”明曰見徐劫曰:“先生之騎乃飛兔腰褭也,豈特千里駒哉!”于是杜口易業,終身不復談。
面對能爭好辯的田巴,魯連認為對于一個士人來說,他的責任不在于自己的辯論技巧多么的高超,關鍵是要在社會上起到實際的作用,如果口才能夠使國家轉危為安,辯論可以把瀕臨滅亡的國家從死亡線上拉回來,那么這才是真正的士,否則那些空口說談的夸夸之詞,只能似梟鳴,一發聲音就會招致別人的厭惡。魯仲連不僅是這樣說的,在實踐上他真的做到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三則射書救聊章和第六章義不帝秦章,魯仲連憑借自己縝密的思維、高超的辯論手法以及一顆愛國為百姓的仁慈之心,用一張三寸不爛之舌,擋住了秦國的萬乘軍車、說服了燕將放棄聊城使聊城百姓免遭屠城之禍。
(二)治國觀
“勢數”在治國觀上最大的特點就是從實際出發,只要能夠有利于社會國家,便可為我所用。比如第九則楚王成章華之臺章,楚將伍舉利用了魯莊公膽小的畏懼心理,借吳國之威要回了楚王賞賜給魯君的大曲之弓、不琢之璧,這種狐假虎威的行為既使楚君避免了出爾反爾不守信用的惡名,也最終得到了想要之物。作者魯連子對這件事的態度沒有褒貶,這里面雖然有些權詐的成分在,顯示了楚君的狹小肚量,但伍舉確實摸透了對方的心理,為楚君辦事。第十六則弦焊相第章載,續接弓弦那么矰就會射得又高又遠;專諸刺殺吳王僚,闔盧才登機。對于子弒父的行為,魯仲連并未譴責這個非道德的惡劣行為,而是把重點放到了闔閭登機稱霸的結果上,這足見其中的實用主義心態。第十三則衛州共縣章,周厲王被國人趕到彘地,天不可二日但也不可無日,周共伯便攝政監國,等到周厲王克死彘地,周共伯便歸國于太子靖。在作者的敘述里,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并沒有什么講仁義禮智信的大道理、大節操,為了治理國家,共伯暫時出來攝政,國人亦無懷疑等不信任的想法,等到厲王去逝,自然歸政。也許史實并非如此,但是從魯仲連的敘述態度可看出,對于共伯這樣從國家事跡利益出發的行為,作者還是對此肯定的。
(三)歷史觀
“勢數”在歷史觀上的體現就是不拘泥于儒家的教條,凡事以實際為依準行事。第五則魯仲連謂孟嘗君非好士章,魯仲連以“色與馬取于今之世,士何必待古”的觀點來層層誘導使孟嘗君意識到自己對待門客方面還是存在問題的。而不待古之士的觀點和傳統儒家言必稱堯舜禹、夏商湯周公的言行差距甚遠,這點反映出魯仲連并不泥古,而是以發展前進的眼光看待現世。
這里還要提到第二十五則子曰君子能仁于人章:
子曰:“君子能仁于人,不能使人仁于我;能義于人,不能使人義于我。”
這個觀點同《論語》中孔子的觀點如出一轍。在《論語·顏淵》篇中,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家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想自己和他人做事都需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地,但是孔子跟他說,自己可以這樣做到,但是不要強求比人也如此。這節是全軼文25節中最明顯體現儒家思想的例子,就此我們可以推論,《魯連子》一書中還會有大量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只是在流傳過程中亡佚了。
參考文獻:
[1] 司馬遷.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卷(八十三)[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 滕吉慶.《魯連子》輯佚與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中國文獻學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2009.
[3] 王德敏,周立升.魯仲連雜考[J].管子學刊,1987(2).
[4] 余嘉錫.古書通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 石小同.試談魯仲連的“勢數”[J].管子學刊,1994(1).
[6]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