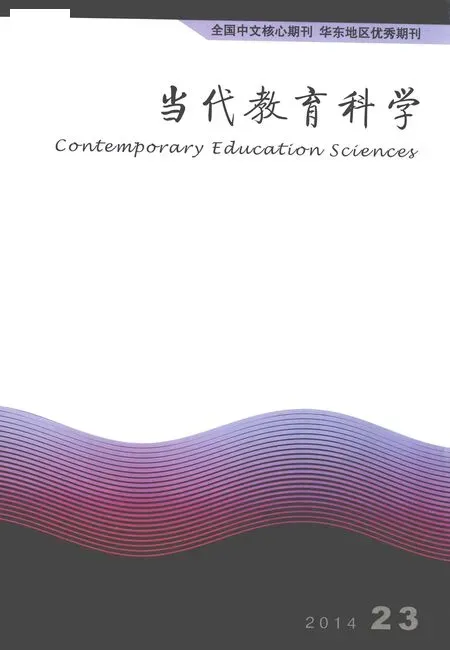論道德教育的四個“二律背反”
●聶曉娜
論道德教育的四個“二律背反”
●聶曉娜
目前諸多德育研究流于對虛假命題的人云亦云而迫切需要理性的反思和提問。文章在目的論、方法論、效果論、本體論四個層層遞進的層面提出困擾當前道德教育的四個二律背反問題:德育目標層面的宏大與低微之爭;德育方法層面的過剩與單一之爭;德育效果層面的有效與無效之爭,德育本體層面的可教與不可教之爭。究問的目的不是想到取代,而是企圖澄明德育的本體性問題,以期回歸德育之本真狀態(tài),助于當下的德育研究。
二律背反;道德教育
二律背反(antinom ies)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提出的哲學基本概念,指雙方各自依據普遍承認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公認為正確的兩個命題之間的矛盾沖突。康德認為道德的普遍法則不可避免地要進入感性經驗,否則就沒有客觀有效性,于是在人的身上必然發(fā)生幸福和德行的二律背反。這種二律背反,同樣發(fā)生在今天的道德教育領域之中。德育領域的四個二律背反相互纏繞,共同構成了道德教育的復雜性。
一、道德教育目標:宏大與低微
當前我們的道德教育的目標究竟是過于宏大,在表述上過于空泛,以至在教育實踐中難以達成,還是這個目標其實非常低微以至失去道德理想,是個問題。從道德教育理想的角度看,今天的德育目標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而從德育實踐能力的角度看,甚至這個較低的目標似乎也難以企及。我們正穿行于德育理想與德育現(xiàn)實的無窮勾斗之中。
當前學校道德教育是規(guī)訓性的,即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告知受教育者“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并要求受教育者按照學校或社會所允諾的道德閾限去行為。規(guī)范本身由于具有國家或社會認可的“合法性”而獲得其不可置疑的權力性。問題的關鍵當然在于規(guī)范的制定即規(guī)范本身是否能夠體現(xiàn)國家或社會意志,但一旦規(guī)范得以制定,規(guī)范本身就游離了審問的范圍而成為不可挑戰(zhàn)的衡準。既然規(guī)范必須基于國家或社會意志,那么對規(guī)范的遵守本身也就是對國家或社會意志的遵守。對于規(guī)范的制定者而言,你之所以要去遵守這些道德規(guī)范,僅僅是你“必須”。所以今天的道德教育從根本上講培養(yǎng)的是學生對于規(guī)范的執(zhí)行能力,而不是對于規(guī)范的理解能力。亞里士多德將德性分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兩種。[1]理智德性主要通過教導產生,道德德性主要通過習慣養(yǎng)成。習慣的養(yǎng)成則必須重視活動的性質。實踐活動的綜合性不僅要求道德主體對于實踐性質的體認,而且也要求道德主體將其體認與具體的道德情境結合起來。也就是說,道德德性的形成不僅要培養(yǎng)道德主體的道德理智,更重要的是培養(yǎng)其實踐智慧。這也正是當下德育最為失察之處。
目前我們培養(yǎng)的受教育者,并非沒有對規(guī)范的認知,而是沒有智慧將這一認知與具體的道德情境結合起來。任何規(guī)范都是抽象的,抽象的規(guī)范不能窮盡具體的道德情境,而德性恰恰就是在具體的道德行動中形成的。所以我們的所謂德育,只是抽象的知識灌輸。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們忽視了道德個體終究是一個具體的社會存在。如果個體反思規(guī)范本身的正當性能力被剝奪,他就只能是一個被動的關于規(guī)范的知識的接受者。他對規(guī)范的所謂遵守就是以所謂遵守來換取相應的功利效果,他對道德規(guī)范的遵從也就只能是一種追求道德功利的理智行為。所謂理智,是個體對于規(guī)范執(zhí)行利弊后果的一種博弈能力。如果違背規(guī)范所產生的非道德效果極具誘惑力,而且個體有能力承擔道德后果(由于其具有承受能力、逃避能力或者后果嚴重不到他能夠承受的水平),那么他就有可能“冒險”去違背規(guī)范。換言之,社會個體不是不想去違背道德規(guī)范,他之所以沒有破壞道德規(guī)范僅僅在于他缺少對道德后果的承受能力。這時候關鍵的問題僅僅在于,“我”并不是“不想”去違背道德規(guī)范,而是因為我“不敢”。這樣一來,規(guī)范究竟是什么其實已經失去了意義,真正起作用的只是道德后果。可想而知的是,假設一個所謂遵紀守法的“好公民”一旦獲得對道德后果的承受能力,結果可想而知。可見,這種所謂“好公民”只是一時的、暫時的好公民,并不是一個真正意義的“好人”。因此,目前德育并不是培養(yǎng)道德主體的德性,而是培養(yǎng)其道德的博奕能力。
這是一個以精明的理智遵守規(guī)范追求道德功利的反理性時代。現(xiàn)代道德教育對于培養(yǎng)理性的“好人”這一終極目的來說,無論其道德規(guī)范目標有多高,其實都過于低下了。它充其量只能培養(yǎng)出“不壞”的人,但不能培養(yǎng)出完美德性的“好人”。它充其量只能培養(yǎng)出“不敢”做壞事的人,但不能培養(yǎng)出不“想”做壞事的人。當代教育似乎只是建立在一個低俗但可靠(low but solid)的基礎上。雖然一個低俗而可靠的道德教育目標比一個完美的道德教育目標更具有達成的現(xiàn)實可能,但即使如此,道德教育工作者們仍抱怨這個目標還是太高了。當代道德教育沒有追求、沒有理想由此可想而知。
對于德育思想工作者而言,道德的理性似乎也在逐次喪失。在我國當前的德育理論界,德目主義還在以各種變式大行其道。雖然德目的分梳在道德知識編排與評價上更為科學和可行,但對德目與承擔德目的載體之間線性關系的過于強調已經放逐了對德目本源的思考,這種所謂的德育顯然不再是本體性的培養(yǎng)“好人”的德育,而僅僅是為了完成一個可行性目標而存在的退而求其次的德育。在這種“德育”思想指導之下的受教育者,由于失去對道德本體的反思能力,由于對于生活道德的決斷不是出于道德自覺而僅僅出于對外在強制性權威的恐懼,而只能落入個體的“他律”狀態(tài)。而道德理性的喪失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偏見和狂熱、蒙昧和迷信,這正是德目論潛藏至深的危險。
當然一個完美的道德教育目標只能是一個烏托邦,但道德教育是一個必要的烏托邦,如果沒有對完美德性的允諾,道德教育的存在將因失去存在的根本而變得毫無意義。作為社會實踐活動的道德教育特別是學校道德教育分理宏大的道德教育目的為可以操作的道德教育目標本無可厚非,但不能忘卻的是任何一個可行的道德教育目標都必須與最宏大的道德教育目的結合起來。在這一點上,值得道德教育思想界沉思。
二、道德教育方法:單一或過剩
當下我們手中所能利用的道德教育方法是太多了,還是太少了?德育理想主義者認為目前的德育方法蕪雜,而德育現(xiàn)實主義者則抱怨德育方法失于實用。這個問題究竟應該如何看待?
整個有關方法論問題討論的關鍵在于方法的抱怨者們對方法的渴求必有其特別之處。方法既然在絕對數量上并不為少,那么對方法的抱怨也就只能是對方法的質量的抱怨,即所謂方法太少了,實質上就是“好”的方法太少了。正是因為“好”的方法的稀缺,所以即使一個很低的道德教育目標也難以達成。所以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好”方法。既然所有的方法的有效性或“好”都在某種意義上寄托于方法使用者的品質,既然我們由于自身的品質不能生產出“好”的方法,那么“好”的道德教育方法的產生也就只能在眾多的方法中進行合理的安排或抉擇。
歸根到底,我們對方法和技術的崇拜源于我們對德育功利化的渴求。我們只是關心技術的有效性問題,但并不關心我們的道德實踐品質。我們可以如何去算計“方法”,但并不關心目的是否正當。韋伯的科學中立論將技術的目的性反思連根拔起,以至技術的危險隱而不彰。技術并不僅僅是一種工具性的東西。海德格爾認為技術的本質是“座架”,作為一種解蔽方式,座架使人走向一種可能性的邊緣,即視座架為一種尺度而閉鎖了人原初的那個無蔽之域。[2]施米特更是從政治哲學的角度批判了韋伯的技術中立論所帶來的道德真空。他說:“現(xiàn)在技術很容易淪為這種或那種需要和欲求的仆役。在現(xiàn)代經濟中,全然非理性的消費方式符合于徹底理性化的生產方式。一種神奇的理性機制永遠都以同樣的認真和精確滿足這樣那樣的需求,無論是對絲綢襯衣的需求,還是對毒氣或其他任何東西的需求。”[3]技術的“背后”究竟隱藏著什么呢?技術何以具有如此之魅惑?技術的信仰啟示著對技術的批判。技術批判正經由形而上學批判達至政治哲學的批判。在法蘭克福學派的大多數批判技術的言論中,技術被認為是一種奴役身體和心靈的工具,但無論如何,把一切人類活動簡約為對自然的工具性宰制都顯得過于抽象和武斷。同樣,海德格爾對現(xiàn)代技術本質的揭示(“座架”,即生活方式)亦沒有完全脫離形而上學的視野從而難于把捉尋覓技術的人類學基礎。在較為晚近的技術批判中,技術不再被視為一種解放的力量(啟蒙哲學)或人性的驅動(法蘭克福學派),而是被視為一種非常關鍵的政治信念建構的現(xiàn)實因素,從而技術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技術手段,而是與自由主義、虛無主義的興起互為因果。技術-經濟思維的價值無涉(韋伯)把一切導向“相對主義”,從而成為虛無主義勃發(fā)的關鍵力量(施特勞斯),而技術在自由制度和法律理論中的專政即技術統(tǒng)治在自由民主制和公共話語中的實踐則導致了“浪漫的生產力”(技術化生產過程的抽象)的普遍化,從而推進了自由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興起(施米特)。技術的問題可謂大矣,德育界尚無從覺知。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技術武裝了人的能力,卻剝奪了人對于目的正當性的反思。當前道德教育是方法論的或技術主義的。方法論的道德教育或技術主義的道德教育只關心“如何做”,而不關心“何以可能”,它只關心操作的程序,而不關心實踐的基礎。這種虛浮無根的道德教育其實只是道德教育的異化狀態(tài)。正如新儒學大師熊十力所言,“學不究體,終成戲論”,那些所謂以嚴肅著稱的學院派研究有可能只是一種“嚴肅的游戲”或如馬克思所言,“醉醺醺的思辨”。當前德育的方法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不是不夠聰明,而是太過于聰明甚至精明了。目前德育思想界好象尚未覺察到這一點。
所以,在層出不窮的方法論的華麗外衣下其實真正掩蓋的是智慧的貧乏。說到底,當前道德教育的問題絕不是方法問題,而是智慧問題;絕不是技術問題,而是觀念問題。當前道德教育智慧的獲得必須基于對古今之爭(古人之“拙”與今人之“巧”)的重新審理。投身道德教育的“知性真誠”表面上充溢著內心的道德涌動,但教育理智的累積絕不意味著教育理性的獲得。古人之所以并不關注于方法,是基于道德理性的完美德性的允諾居于比方法本身更關鍵的位置,此造成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現(xiàn)代人之所以必須關注于方法,是基于道德理智的目標達成是所有道德教育的歸宿,此造成所謂對方法的無節(jié)制追求。古人之所以沒有必要去關注方法,是因為方法服從于它從之出又歸于其的本體;現(xiàn)代人之所以不得不關心方法,是因為方法已經遠離了它的本體而自裁自決。比之于古代追求完美德性的“巨人”,現(xiàn)代人只是工于心計、投機取巧的“侏儒”。
今天的德育在工藝、方法、技術層面太過于精巧,太過于精致,已經失去了中國傳統(tǒng)道德教育“樸”的精神。精之為精,在技巧,樸之為樸,在精神。在今天,我們越是談論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似乎離我們就越遠,我們越是重視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好象越發(fā)厭倦給予我們回報。現(xiàn)代人太精明于算計,太過于聰明,甚至太過于矯揉造作,他有太多的方法但缺少利用方法的智慧。當前教育太缺少古人道德教育“拙”的智慧。當前的道德教育是種“精致的渺小”或者“渺小的精致”。它太追求“精致”了,從目標設置到方法選擇,從經驗累積到模式建構,當前教育所追求的是如何才能做到“科學”即所謂科學的道德教育才是有意義的道德教育。當前道德教育似乎有太多“好”的主意,也有太多“好”的方法,但當前道德教育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好”的。
三、道德教育效果:無效或無效
道德教育“無效論”目前幾近成為一個不證而明的客觀命題。德育“無效論”真的就是德育理論的“生長點”?德育“無效論”真的“有效”?
德育無效論首當其沖且獨一無二地關心的是“效果”問題,并不是道德教育“好壞”的品質問題。而效果好壞的判斷,必須首先審視其所達到的目的的品質,否則所謂效果論將變得毫無意義。當前所謂“無效論”的判斷,恰恰陷于這種無根之境。這是德育隱藏至深的現(xiàn)代性問題。所謂現(xiàn)代性問題,就是刻意取消“高貴”(古代)與“低俗”(現(xiàn)代)的區(qū)別而以所謂效果問題即“進步”與否作為好壞的標準。[4]現(xiàn)代性的實質則在于為了能夠達到欲望滿足的最大化必須進行不斷的革命——“進步”的當然就是“新”的,“新”的恰恰被認為就是“好”的。德育的歷史浪漫主義本末倒置地用所謂“新”本身來判斷一切是否好,而不是用“好”的標準去衡量某種新事物是否對。德育無效論其實正是道德虛無主義的現(xiàn)實表征。德育無效論作為道德虛無主義的現(xiàn)實結果反過來則加強了虛無主義的力量。既然制度和方法的問題才是決定德育品質的關鍵所在,那么對德育本身品質的判斷就變得可有可無了。既然德育自身的品質特別是其目的品質毋需判斷,那么所謂道德教育也就只能流于平面、形式空洞。說到底,對德育無效的哀怨,本質上就是對于技術論和方法論的哀怨。這種哀怨充其量只是一種情緒化的無聊狀態(tài)而已。
德育的歷史主義浪漫派一直堅持這樣一種信念,即世俗大眾都有從善之心,之所以會作惡,實為欲望所蔽,只要不給予其作惡的外部環(huán)境即從制度上或契約上限制人作惡的可能,惡將隨著制度的完美化終將消除。所以,完美制度的建立一直是完美德性的外在保障,這一信念在西方哲學史上一直從柏拉圖延續(xù)至馬克思主義,再到晚近張揚正義的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在這種信念中,完美制度的確立被認為是使人棄惡從善的關鍵,而前者又不得不依賴于制度制作的技術化和程序化。從第一次現(xiàn)代性浪潮的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的進步觀念的提出,到第二次浪潮的盧梭、康德和黑格爾歷史觀念的承續(xù),再到第三次浪潮尼采和海德格爾的歷史主義的完成,技術主義的路線一直貫穿終始。正是歷史主義的迭興,才造成施特勞斯所謂虛無主義化的西方哲學的危機。其實無論是“歷史的狡計”,還是現(xiàn)代性的“共謀”,技術或方法的問題都不可避免地成為完美德性形成的外在技術保障。
有效性問題本質上是個科學問題,有效性的提高則是一個需要借助于科學才可能的問題。德育的有效性問題只有在科學主義的視野內才是可能的。近代科學具有三個顯而易見的特征:精確性、實驗性、專門化。德育有效或無效問題恰恰是以此為尺度的,而對無效性的克服也恰恰是以這三個方面為旨歸的。科學的精確性、實驗性、專門化所實現(xiàn)的并非僅僅是作為理論的科學的嚴格化,而是最終把生命的本質交于技術制作。人以科學來計量,反過來科學也算計了人。海德格爾對此批判道:“技術的統(tǒng)治不僅把一切存在者設立為生產過程中可制造的東西,而且通過市場把生產的產品提供出來。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貫徹意圖的制造范圍內分化為一個在市場上可計算出來的市場價值。這個市場不僅作為世界市場遍布全球,而且作為求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質中進行買賣,并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帶入一種計算行為之中,這種計算行為在并不需要數字的地方,統(tǒng)治得最為頑強。”[5]科學的專門化則使教育由于從屬于工藝和制作而失去整體性、目的性的支撐。對此,雅斯貝斯評論說:“我們的時代在教育問題上的不安以下述情形為征兆:教師們在缺乏任何統(tǒng)一的教育思想的情況下強化著自身的努力;論教育的新書層出不窮;教學技巧持續(xù)地擴充。今天,單個的教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一個自我犧牲的人,但是,由于缺乏一個整體的支撐,他實際上是軟弱無力的。而且,我們的狀況所獨具的特征似乎是,具有實質內容的教育正在瓦解而變成無休止的教學法實驗,這個教育的解體所形成的是種種無關宏旨的可能性。人們?yōu)樽陨砼幍玫淖杂烧谙⒍煽斩礋o效的自由。一種嘗試迅速地為另一種嘗試所取代。教育的內容、目標和方法不時地被改變。這是一個對自身沒有信心的時代,它焦慮地關注著教育,仿佛在這個領域中有可能再次從虛無中創(chuàng)造出某種事物來。”[6]我們并不能否認德育有效論研究的確已對德育實踐有所觸及,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德育有效論研究對于德育的本體性問題尚未觸及。我們究竟在何種意義上認為今天的德育是無效的,至今仍是一個懸案。德育無效論絕非一個純粹事實性的不證而明的問題。
四、道德教育可能:可教或不可教
在德育思想界,美德是否可教的問題尚未得到嚴肅地追問。美德一定可教,似乎只是當前我國德育界的一種堅定的信念,并未得到知識論方面的證明。美德究竟是否可教的問題,對于道德教育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本體性問題。美德不可思議地可學,但并不顯而易見地可教。我們有所謂道德教育,但道德本身是否可教并非由此就是自明的。關于這個問題,德育研究雖已有觸及,但似乎有進一步追問的必要。
美德是否可教的問題是蘇格拉底哲學的經典問題之一。這一明確的提問,來自于哲學家和貴族青年美諾(Meno)的對話。美諾問哲學家,“美德是可傳授的,還是通過實踐獲得的?或者如果它既不是通過實踐獲得的,也不是學來的,而是來自天性或其他途徑?”蘇格拉底說,關于什么是美德,他自己尚一無所知,而當一個人不知道一樣東西的時候,又如何知道它的品質呢?這樣,蘇格拉底把美德是否可教的問題就置換為美德是什么的問題。這兩個問題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
在接下來的對話中,蘇格拉底用他巧妙的“問答法”一步步辯難和引導美諾。原來所謂美德并不是一大堆美德,而是美德的共同本質。美諾總結說,美德就是正義。但正義究竟是美德的一種還是就是美德本身?圓、長方形、正方形等都是圖形,但是它們只是一種圖形。它們又有共同性,那就是都是由線條構成的空間。美德也有著這樣的統(tǒng)一性。美德是高貴的、是有益的,人們總是向往著有益的東西,有的人選擇了壞的,并不是因為他想要壞的,而是他分不清好壞。而要分清楚好壞,就必須借助于道德的知識。而道德是不是知識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哲學家引入了一個倫理學的核心概念“善”,認為美德是一種“善”,如果知識包括了一切的“善”,那么“知識就是美德”。
蘇格拉底和美諾充滿機智的對話經過問題的巧妙置換所得出的“知識即美德”的結論,試圖揭示知識即美德的充要條件。作為必要條件,知識是美德的引導;作為充分條件,有“善”的知識,才會產生“善”的行為。哲學家認為“公正以及別的美德都是明智。公正的行為和一切以美德為基礎的行為都是美的和好的。……只有明智者才會做出美的和好的行為,而不明智者不可能做出這種行為,即使竭力去做,也會做錯。所以,公正的和所有一切美的和好的行為都以美德為基礎,那么,由此可見,公正和所有的美德即是智慧”。而知識、智慧(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這是最高的德性)是可以教的,所以美德可教。
如果美德系于知識,按照蘇格拉底的論述,美德可教。然而,可否假設美德不是知識,卻依然可教,或美德雖是知識,卻根本不可教?美德在蘇格拉底的著名表述里究竟還隱藏著怎樣的“隱微”表達?
對現(xiàn)代人來講,蘇格拉底的論述充滿了疑問。顯然,美德知識未必一定可以導致美德的行為,因為欲望可以其合法性的名義名正言順地抵制理智,也就是說,即使道德主體有道德理智,但現(xiàn)實道德的博奕可使其獲得“知”而不“行”的合法性,因為對現(xiàn)代人來說,欲望比理性更為正當。所以,蘇格拉底在現(xiàn)代性中如果是成立的首先必須基于的條件是人必須是理性的。只有理性的人才可以做到有知識而又有美德行為。再者,如果道德根本不是知識,而是道德情感或道德實踐(如中國傳統(tǒng)哲學所認為的那樣),那么所謂道德的可教性也就是道德是可以教化的。而所謂教化是對心靈的培育,按照心靈的內在品性對心靈品質的提升。既然教化意味著使人處于“美好”之中,是對人完美德性的允諾,那么教化的本質就在于回答“應該如何生活”是必須的,這就決定了道德哲學問題也就是政治哲學問題,或者,道德就是政治性的。
美德雖未必就是知識,但因人的理性和道德的政治性,美德可教。但有否可能美德雖是知識,而未必可教?在杜威看來,倫理知識有“道德的知識”和“關于道德的知識”之分,其分解類似于批判理性主義者波蘭尼的方式,前者類于“個人知識”,而后者類于“客觀知識”。作為客觀知識的“關于道德的知識”是可教的,因為它可以按照可證實的原則選擇、組織和評價。而作為個人知識的“道德的知識”則未必可教,因為它關涉到個人的意志品質和情感體驗。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教人“關于道德的客觀知識”,但個人“道德知識”的形成則依賴于個人的道德實踐感受和實踐能力,即其實踐智慧(亞里士多德)。
因此如果蘇格拉底的著名論述在現(xiàn)代性中依然成立,那么,所謂“關于道德的知識”與“道德的知識”之分就沒有意義。反之,如果倫理學知識的分解是有意義的,那么蘇格拉底的論述就存在著顯而易見的矛盾。這種矛盾性的實質正是倫理學的古今之爭。在古代是可能的道德教育,在今天反倒受到懷疑;在蘇格拉底那里,他通過“隱微”表達所試圖揭示的人的理性和道德的政治性,在現(xiàn)代性中,人們雖然據理力爭來表達對于道德教育的堅守,實質上卻是對人的理性的無望和懷疑。
作為道德哲學的本體問題,道德的可教性問題在古今之爭中其實處于完全不同的意義世界。基于道德理性和實踐智慧(古代),道德作為善是可教的;基于道德欲望和德育活動(現(xiàn)代),道德作為善雖然也被認為是可教的,但由于欲望的正當性,道德的可教性其實被存疑。所以,道德的可教性問題,實質上仍是一個“經典”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現(xiàn)代的問題。設若現(xiàn)代人不能從道德的可教性問題對道德理性和善有所領會,那么所謂道德的可教性追問僅僅是一個勞而無功的虛假命題。而一旦這個問題付諸闕如,所謂道德哲學研究將處于虛浮的無根之境。對此,現(xiàn)代道德教育不得不察。
[1][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5.
[2][5][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M].孫周興選編.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6,944,432.
[3][美]約翰·麥考米克.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批判[M].徐志躍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38.
[4]賀照田.西方現(xiàn)代性的曲折與展開[C].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86.
[6][德]雅斯貝斯.時代的精神狀況[M].王德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95.
(責任編輯:劉丙元)
聶曉娜/山東英才學院學前教育學院講師,教育碩士,研究方向為學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