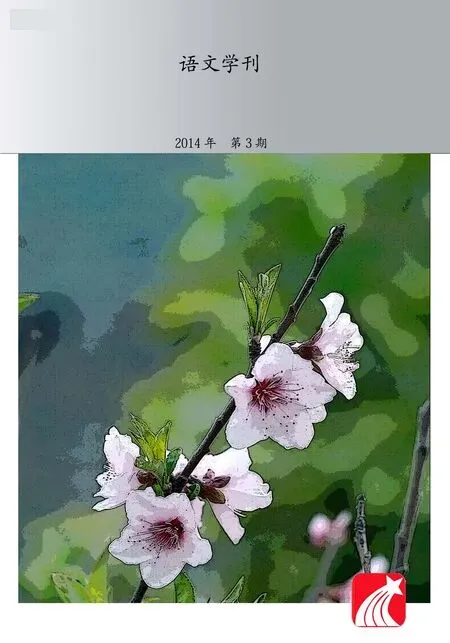論星期五的話語權
——沉默
○ 王錦方 張萌萌
(中國礦業大學 (北京)文法學院,北京 100083)
文學評論界對南非作家J.M.庫切的小說《福》的評論焦點之一就是星期五的沉默。筆者認為之所以討論沉默這個話題,主要基于后殖民研究的重大問題之一,即話語權問題,其次是庫切在小說文本中對讀者的暗示。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關于話語與權力的理論,一針見血地指出權力是通過話語獲得的。要維護權利,就要維護話語權,即通過規則和程序來規范哪些可以言說,哪些需要被沉默。反之,要爭得權利,首要的就是要爭得話語權,這就是現代社會人們普遍關注的言論自由問題。可是,在后殖民的語境下,話語權有意或是無意的被權力控制,星期五的有聲的話語權仍然是被剝奪了,他唯一的話語權就是沉默。
薩義德(Edward Said)曾指出:“歷史總有著各種各樣的沉默與省略,總有著被強加的形塑和被容忍的扭曲。”庫切自己在小說中也多次暗示讀者,星期五把沉默作為一種話語權是小說要表達的核心思想之一。他在小說中把星期五的沉默比作故事的“中心”,故事的“眼”,故事的“嘴”,明顯在暗示讀者,星期五的沉默是這部小說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那么,讀者不禁要考慮的問題就是:誰不讓星期五說話?星期五如何用沉默訴說?這也是本文要探討的后殖民主義在話語權上是如何實現對殖民主義的反撥這一話題的。
一、誰不讓星期五說話
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屬下能說話嗎?》一文中斷言“屬下不能說話”。從話語權力理論的角度看,“屬下”就是沒有話語權的人群,沒有權力來表達自己。另外,根據斯皮瓦克的觀點,屬下又分為不同層次。在小說中,蘇珊的女性身份,可以認為是一種屬下,是沒有話語權的。但是,蘇珊是白人,相對于星期五的地位她有話語權,黑人奴隸星期五則屬于最底層的“不能說話”的下屬。
在《福》中,星期五的沉默被一種黑色的殘忍所象征,給人印象深刻,那就是星期五的舌頭被割掉了。于是,尋找舌頭被割掉的原因就成了找出星期五為什么失語的重要線索。
克魯索認為是“奴隸販子”,“或許那些奴隸販子是摩爾人,……我們怎么會知道真相?”這是蘇珊從克魯索哪里得到的信息。克魯索認為不能得到真相。作為奴隸主,克魯索對于奴隸想說什么,有什么要求,根本不關心。
而蘇珊卻在千方百計地尋找真相,她后來甚至畫了圖畫來讓星期五辨別,他的舌頭是奴隸販子還是奴隸主(克魯索)割掉的,結果一無所獲。蘇珊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說了我的故事之后,如果不交代星期五舌頭的怎么沒的,那就仿佛賣了一本內頁全是空白的書。”她這樣做,只是讓自己的荒島故事更完整罷了。“然而,唯一能說出這段經歷的只有星期五自己的舌頭。”這樣也就注定了,蘇珊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答案了——失去了舌頭的星期五講述失去舌頭的故事,這樣的后現代的悖論注定了星期五的故事就是一個謎,一個精心編織的敘述的扣眼,等待扣子卻不可得。
當蘇珊想教會星期五語言時,英國本土作家Foe指出“蘇珊,你必須捫心自問:割掉星期五的舌頭是奴隸販子的行徑,目的是讓他順從,而我們在喋喋不休地爭論著一些詞的含義,卻吹毛求疵地讓星期五學習這些詞匯,難道這就不是奴隸販子的行徑嗎?”要求星期五沉默而割掉他的舌頭和要求星期五只能按照我們的要求說話,同樣是剝奪他的話語權的行為。行文至此,看來探討誰割掉星期五的舌頭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問題在于誰是話語權擁有者,以及這些擁有者如何的強化自己的權力,打壓反對者,使他們沉默,從而實現自我利益。
福柯認為,言語控制一方面是不允許言說,暴力剝奪話語權,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按當權者的要求說,不能胡說亂說。在小說中,星期五被割掉舌頭只是一種隱喻,底層人,抑或是下屬是不能說話的,即使是有了表達,這種表達也不會被社會主流所重視。既然弱勢群體無法表達自身,那么星期五的沉默是對這種話語權的挑戰,沉默讓所有有關星期五的話語互相矛盾,不攻自破。沉默消解了主體話語權,也抵抗并拒絕了權力者的主體地位。
二、星期五一直在說話
在《福》中,所有的人有意還是無意地都成了星期五沉默的壓迫力量,這個力量就是權利對語言的控制。然而,星期五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自我,在星期五看來,蘇珊、庫魯索以及笛福等人才是“他者”。他向大海撒下了花瓣,吹著自己的曲調,跳著屬于自我的舞蹈。當別人任意編排星期五的身份以及故事的時候,星期五一直都是實實在在的存在著,而且以自己的方式在說話。
看這段描寫:“他從暗處劃了幾百碼,一直劃到長滿海藻的地方,手伸進掛在脖子上的袋子里,取出一把白色的小薄片,撒在水面上。”誰會向長滿海藻的大海撒花瓣?毫無疑問,星期五在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騎著一根圓木,像長滿海藻的大海撒下白色的花瓣,這段似乎唯美的描寫,把星期五一個黑人奴隸的精神世界展現了出來。“……他是有靈魂的。”這里的有靈魂,不妨看做星期五是有自我的,盡管我們看待他是個“他者”——能任意賦予他我們的各種期待以及想象。
星期五的音樂以及舞蹈,同樣是星期五的語言表達,只不過是肢體語言和另外一種聲音語言。蘇珊認為,音樂如果是語言的話,應該能和星期五進行交流,可是當她想當然的認為自己吹奏的七個音符能讓星期五跟著吹奏的時候,才發現星期五在頑固的堅持自己的曲調,只有六個音符的一個曲子。蘇珊與星期五借助音樂的交流失敗了,她“痛苦地意識到,他并不是因為遲鈍才將自己封閉起來,而是拒絕與我有任何交流。”這是對妄圖邊緣化他者,強化自我的有力回擊。“他跳舞的時候仿佛變了一個人。”星期五帶上假發穿上袍子,不停地旋轉,忘了時間,也忘了自己。星期五要擺脫周圍的一切,包括蘇珊。當旋轉的時候,會發現一切都在圍著自己轉,自我成了核心。
通過星期五的撒花瓣,吹笛子,跳舞等行為,很容易發現星期五有自己的靈魂,自己的音樂,自己的舞蹈,自己的世界,完全不是他人描述的那樣一個沒有靈魂的被割掉舌頭的黑人奴隸。星期五的沉默,質疑了殖民文本對被殖民者形象的歪曲。這就解構了那些任意塑造星期五的想法,比如迪福的魯濱孫漂流記》中的形象,以及食人生番,吉普賽人,黑人奴隸等。我們不得不說,星期五一直在訴說,只不過是以一種非主流的方式在訴說,而且以一種當權者所忽視或故意保持沉默的方式在訴說。
三、結 語
當讀者糾結于“誰割掉了星期五的舌頭?”這個問題時,就開始了語言與權力關系的思考,這也是庫切故意設計的一個謎,解謎的過程也就是解構了話語權力體系。殖民者用權力來強化殖民話語權,從而獲得殖民利益。對于被殖民者,一般來說,解構殖民話語就是給予被壓迫者聲音。需要注意的是,庫切卻反其道而行之,反倒讓被壓迫者失聲,保持沉默。這既可以看作是殖民統治之下,黑人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低下,毫無話語權的象征,也可從看做解構殖民者自己的行為過程中不經意間強化被壓迫者的聲音。沉默以一種特有的方式對抗掉了殖民文化霸權,并在這種沉默中用音樂,舞蹈等手段表達了自身的存在與價值。
【參考文獻】
[1]包細簪. 后殖民與后現代的兼收并蓄 ——解析庫切的小說《福》[D].蘇州大學,2009.
[2]高敬,石云龍. 試論后殖民語境下庫切小說《福》中的話語權[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12(10).
[3]黃暉. 敘事主體的衰落與置換——庫切小說《福》的后現代、后殖民解讀[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6(7).
[4]J.M.庫切.福[M].王敬慧,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
[5]劉本英. 話語的顛覆與重構——庫切《福》的后殖民研究[D].大連理工大學,2009.
[6]李燕子.《仇敵》:庫切對魯濱孫漂流記》的解構[D].湖南師范大學,2007.
[7]Raman Selden, etc. 2004.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earson Education.
[8]姚夢澤. 《福》解構寫作的寫作[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
[9]張德明. 從《福》看后殖民文學的表述困境[J].當代外國文學,2010(4).
[10]朱峰. 論蘇珊·巴頓“寫作的焦慮”[J].當代外國文學,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