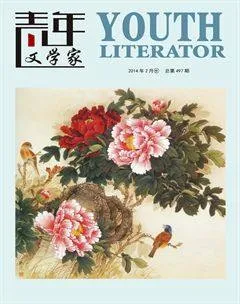淺論張天翼筆下的女性形象
摘 要:張天翼筆下誕生了許多不朽的藝術形象,如鄉紳地主和向上爬的小人物,并且這些人物形象都得到了一定的意義闡釋。其實張天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具有同樣的藝術魅力,如受封建文化毒害的悍婦,偉大而無奈的慈母,具有反抗意識的農村婦女。他冷峻地批判地舊式傳統女性,同時又深刻理解女性生存的艱難,同情女性命運的悲慘,并對女性的反抗意識給予贊美。
關鍵詞:女性形象;悍婦;慈母
作者簡介:明洪慧(1977-),女,漢族,滑縣。鶴壁職業技術學院人文教育學院,講師,碩士學位,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05-0-02
張天翼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多產的作家,從小隨父親漂泊的經歷,使他接觸了多個階層的人物,從而為其寫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張天翼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批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其中鄉紳地主和向上爬的小人物形象成為文學評論界偏愛的對象。但細讀其作品,張天翼筆下的女性形象同樣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
一、自私、變態的悍婦
中國文學作品中塑造了一些面目可憎、行為潑辣的悍婦,她們深受中國封建傳統思想的影響,封建禮教的貞烈觀和三從四德的倫理道德標準制約著她們的行為,封建正統的文化教育在她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她們是封建傳統文化犧牲品的同時,同樣是封建思想的維護者,也成為殺害和她們一樣的女性的劊子手。《善女人》中的主人公長生奶奶是個性最為鮮明的悍婦,“她同時充當寡婦、母親、婆婆和善女人四種角色,并且為了作個虔信佛教的善女人,不惜放棄母子親情,激化婆媳矛盾,最終成為孤家寡人。”[1]她十五歲時嫁給長生后經常受到丈夫的辱罵和毆打,丈夫去世之后,她所接受的貞烈觀使她苦熬多年,把兒子阿大撫養成人,并把自己全部的愛傾注在兒子身上,阿大成家之后,她嫉妒兒子對兒媳的疼愛,看到阿大夫妻二人恩愛幸福,感到心理不平衡。“阿大給那個狐貍精迷住了,連娘都不要了。”于是就對兒媳百般挑剔,長期的情感欲望無法得到正常的釋放,從而形成了心靈和精神上的變態,拿舊的標準去衡量兒媳婦,自己當年做媳婦的時候“一年到頭把顆心提得高高不敢做錯一點,老公還動不動就兜屁股上一腳”,而“現在做媳婦的可爬得比阿婆還高。”最后逼得兒媳婦領著女兒阿巧回了娘家,一個原來完整的家就這樣徹底破碎了。同時,她具有濃厚的封建迷信思想,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來世,為了湊夠修行的五十元錢而費盡心機,她通過老師太把錢借給自己的兒子阿大,收取的利息三分,比借給其他人的要高,為了得到封二爺三分半的利息,寧愿讓出一分錢的利息給老師太,也要逼兒子阿大還債,當看到阿大因無力償還債務而鐵青的臉,她心中也閃現了憐憫和母愛,但是金錢和修行的誘惑力最終讓她拋棄了親情。
張天翼在刻畫長生奶奶這樣的形象時,并沒有局限于簡單的道德評判標準,而是還揭示了其內心的脆弱和無奈及母愛缺失后孤獨。當她飽嘗磨難把兒子養大成人之后,就像債主般地收回報答,認為為兒子付出了太多,兒子就應該給予她對等的回報,她的母愛中夾雜著濃郁的封建專制色彩和自私心理。其實,她這種自私專制的母愛不僅傷害了自己的兒子、兒媳,同時也深深傷害了自己。張天翼還原了長生奶奶作為人的復雜性,并由此對傳統的母親形象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正如夏志清所言:“這位作家在他最佳的小說里,往往保留了人性真相的一種廣度。”[2]
二、矛盾、迷茫的大小姐
五四時期,出身于新興資產階級家庭的大小姐,有著雙重的身份,既是資產階級的一分子,貪圖享樂,同時又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禮,向往平等和自由,新舊思想的激流碰撞使她們處于矛盾、迷茫之中。張天翼以敏銳的眼光準確地重塑了這些女性的形象。
《出走以后》的姑太太是一個在自己七叔思想教化出來的新派人物,丈夫對工人的欺騙和剝削,使她不能容忍,堅決地回到娘家,發誓要和丈夫離婚,但是回到娘家之后,她感到這潮濕、雜亂的環境與她已經習慣的豪華生活相比是那么不協調。當考慮到一家人的生計和前途時,她動搖了,通過七叔的開導,使她最終選擇了回去。正如魯迅所預言“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3]《移行》中的桑華本來有過進步的追求,冒著生命危險進行地下活動,但黑暗的現實與她向往的生活產生強烈的反差,使她離開了革命隊伍,投入了富商的懷抱之中,走向了沉淪。這些資產階級的大小姐富于幻想,憎恨丑惡,但又缺乏斗爭的勇氣和信心,張天翼對這些女性參加革命的勇氣給予了贊賞,同時也對她們的懦弱本質進行了揭露。
三、偉大、無奈的慈母
張天翼把更多的筆墨放在了渾身散發母性光輝的女性身上,盡管她們歷經生活磨難,但她們內心深處仍然是善良寬厚了的,如《奇遇》中的小連兒媽媽,《團圓》中的大根媽。《奇遇》是通過兒童豫子的視角來敘事的,小連兒一家為了生存從鄉下的老家逃到了城里,并且小連兒媽媽不得不狠心丟下小連兒到豫子家里當奶媽,而她的丈夫木三卻用妻子的血汗錢賭博喝酒一,豫子出身富貴,得到了家人甚至小連兒媽媽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健康茁壯地活著,而小連兒因為貧寒的出身,卻無法得到親生母親的照料,終日孤獨地待在陰暗的家中,最終離開了人世。豫子和小連兒形成了一個鮮明對比,并且豫子的存在無時無刻不在提醒小連兒的媽媽她曾經同樣有一個健康的孩子,但這個孩子卻永遠地離開了人世,這所有一切深重地壓迫著她。
《團圓》中的大根媽,在極其困苦的年月里,丈夫長壽為了生計外出打工一年多卻杳無音信,為了保全五個孩子的生命被迫賣淫。一年之后,當長壽回到家中時,盡管大根媽百般隱瞞,但他還是知道了事情真相,此時的他,為了自己的名聲,厲聲斥責為他養育了五個孩子的妻子。在小說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大根媽的身影,也很少聽到她的聲音,她的形象大都是通過大根、長壽及吳三姥姥、連司務這些人來表現的,從他們的行動和言語中,我們可以窺出她為了孩子而忍受屈辱的偉大形象。
《奇遇》和《團圓》中刻畫了兩個偉大卻無奈的母親,在物質匱乏的生活中,為了孩子,不惜出賣肉體,出賣靈魂,為了孩子,她們默默忍受著命運給她們的不幸。張天翼對她們強烈的母愛是崇敬的,所以對她們所受的傷害更加同情。同時在文中和無私的母親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兩個不負責任、冷酷怎么的父親,張在翼在作品中用犀利尖刻的筆鋒對他們進行了無情的批判,使得小說在贊揚母親的無私中,達到了對男性的道德批判。
四、反抗、進步的婦女
在封建制度的統治下,農村婦女處于社會最底層,她們的肉體和心靈飽受侮辱和損害,張天翼將憐憫的目光關注她們,同時也看到了她們的初步反抗意識。《笑》中發新嫂的丈夫楊發新代表鄉人的利益和地主惡霸九爺作對,九爺就以抓土匪的名義抓走了楊發新,發新嫂苦苦哀求九爺放人,九爺表面上答應,但心里鄧盤算著怎樣誘發新嫂,以報復楊發新。發新嫂為了救出楊發新,她出賣了身體,接受了九爺的蹂躪,但九爺卻在清風閣茶館這樣一個最適合消息散布和傳播的公共場所,將發新嫂被他侮辱并以此換錢的交易公之于眾,他想利用可畏的人言殺死發新嫂,發新嫂從哀求、屈服中看到了九爺卑鄙的本性,終于將茶壺摔向九爺,給了九爺憤怒的反擊。
《脊背與奶子》中的任三嫂被族紳長太爺調戲,并以一身的“茨實粉”“沒有蒸透的蒸雞蛋”引發了其占有欲,當長太爺用言語試探她時,遭到了她一頓痛罵“青天白日里你調戲人……真不要臉……”,“畜生!老狗!強盜!雜種!痞子!任剝皮……”[4]。當后來長太爺用玉圈做誘餌,收買任三嫂,再次遭到了拒絕。當長太爺給任三嫂帶上“萬惡滛為首”的罪名,用鞭抽打她時,雖然“完整的皮肉上抽出疙瘩,在疙瘩上抽出血。在打爛的紅肉上面,深深地烙著竹節的印記”,但她不叫,不哭,不掙扎。受過鞭打之后的任三嫂故意用鮮美的外表吸引長太爺,并最后將其推到在爛泥里,而她卻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逃跑計劃,實現了自己一直堅守的愛情。
如果說發新嫂的反抗是被迫的、無奈的,不能真正體現獨立的反抗精神,那么任三嫂的反抗則是自愿的,張天翼在她們身上寄托著對女性美好的希望。同時,也批判了長太爺、九爺這些農村土豪惡霸、地主鄉紳,他們依仗自己手中的權力,草菅人命,無視他人的自尊和生命。
張天翼對舊式傳統的女性無情地進行了批判和否定,但作為一名人道主義作家,他又用更改的頭腦,悲憫的眼光對善良無奈的女性給予了同情甚至贊許。并且在塑造這些女性形象時,張天翼還不斷思索導致女性不幸命運的深層原因,融入了自己對人性的深刻理解。“人是多方面的,是復雜的創造物,要是只用一張臉譜——不論是什么臉譜,那總是寫不到家的。”[5]在審視女性的同時,對男性進行了反觀。也正因為如此,張天翼筆下的女性形象展放出獨特的藝術魅力。
參考文獻:
[1]靳偉娜.張天翼筆下的女性形象分析,河南大學,2006.
[2]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158.
[3]魯迅.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152.
[4]張天翼.華威先生,華夏出版社,2009.49-50.
[5]張天翼.張天翼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