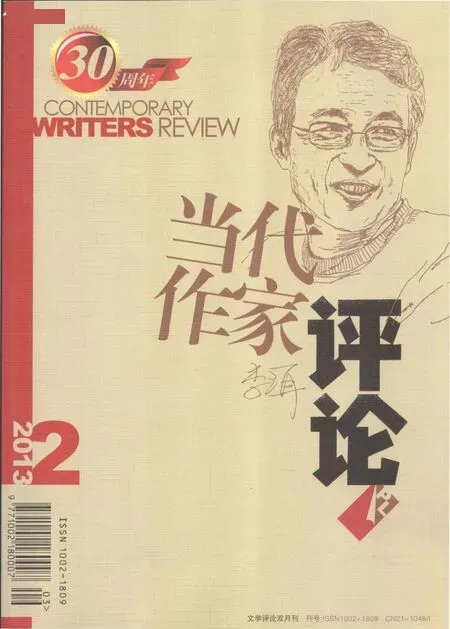詩歌的危機與世界性詩學——美國詩歌二○○○-二○○九(上)*
2013-11-14 08:57:34邁克爾戴維森
當代作家評論
2013年2期
關鍵詞:語言
〔美〕邁克爾·戴維森 著 林 源 譯
作為危機的詩歌
一九一七年,當龐德(Ezra Pound)將回望的目光投向上一個世紀時,他將其視為“相當模糊的、混亂的百年,一個無病呻吟的、矯揉造作的時期”(《回望》)。大家知道,他希望二十世紀的詩歌能“更挺拔,更理智……‘更貼近骨骼’”。新詩要“嚴峻、平白,擺脫情感上的拖沓”,這一定義引發出意象派和客觀派及現代派詩歌的眾多寫法。此時的龐德憑借一個個偽裝和角色、譯文和模仿,朝著丁尼生的詩風和印象派的遺風發出強烈的挑戰,他的這些作品最終形成了《詩章》(The Cantos)。要是我們再回望龐德說過的話,又不知他要對我們時下的寫作作何感想:
概念化寫作對原創性一字不提。相反,概念性寫作故意使用彰顯自我的技巧,強調零創作性、模糊性、借用、剽竊、盜取、偽造,以此作為寫作的不二法門。
——坎尼斯·古德斯密《概念化詩學》
最好的詩歌真的不是寫出來的,而是在幾乎不假思索或沒有感覺的狀態下說出來的。仿佛每天的談話就圍繞著這些旋生旋滅的事物。不妨將此稱為內心的閑話或者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多少有些相互糾纏的話語。
——林覃
要考慮的是:作為探索的詩,作為行動的詩——詩歌循著斷裂的軸來表達意思,這些意思在語義場里構成因素,構成層次,又穿越語義場,充實并繁衍出創造意義的方式。
——金詠梅《句首輕讀音》
沒有營養的詩歌、充滿雜音的詩歌、試圖探索的詩歌——這些話聽上去既不“更挺拔,更理智”,也沒有暗示出龐德所關注的文化復興。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華詩詞(2023年8期)2023-02-06 08:51:28
文苑(2020年4期)2020-05-30 12:35:30
小學生作文(中高年級適用)(2018年3期)2018-04-18 01:24:47
瘋狂英語·新策略(2017年8期)2017-05-31 08:13:46
新聞傳播(2016年10期)2016-09-26 12:15:04
玉溪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1期)2015-08-22 02:51:58
少兒科學周刊·少年版(2015年4期)2015-07-07 21:11:17
語文知識(2014年10期)2014-02-28 22:00:56
中學生英語高中綜合天地(2009年10期)2009-12-29 00:00:00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08年51期)2008-12-31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