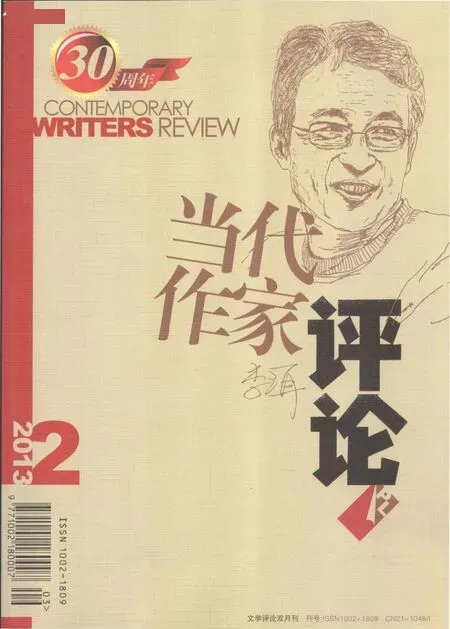為什么要寫長篇小說?——答黎紫書《告別的年代》
2013-11-14 08:57:34董啟章
當代作家評論
2013年2期
董啟章
黎紫書沒有問過我這個問題。至少沒有直接問過。但讀黎紫書的《告別的年代》,幾乎每一頁、每一行都聽到她在問這個問題——為什么要寫長篇?這個問題又同時分為兩個:為什么要寫這部長篇?以及,為什么要寫長篇小說?黎紫書在小說的后記中說,寫長篇是“處心積慮”但同時又“羞于啟齒”的一回事。我十分明白這樣的心情。這絕不是出于不必要的謙虛,但也不是因為自信不足。那更大程度上是時代的使然。我還要說得更直接嗎?其實大家都知道,長篇小說的時代已經過去。所以,上述的問題其實應該是:為什么還要寫長篇?
黎紫書的后記肯定是“處心積慮”的,她肯定把這個問題前前后后想過通透。她一步一步地提出了好幾個寫長篇的理由。由最表面的理由開始,六年前她因為目睹小說家“大哥哥”駱以軍對寫長篇的焦慮(而這焦慮又跟我正在寫長篇有關),自己的寫作心態也慢慢地從游戲變成認真,開始產生“自覺和勇氣去質問自己書寫之目的”。由此而進入更深層的理由:“但認清自己的局限畢竟是一個寫手趨向成熟的必然過程,即便我無力突破,但我卻有了把握去直面自身的局限,并在書寫中逐步揭穿自己。”《告別的年代》這部關乎自身成長經驗的小說,便因此而產生。這解答了“為什么是這部”的問題。再下去便是“為什么是長篇”的問題,她說:“因為那里有足夠的空間讓它們(記憶的玩具箱子里的事物)說出各自的對白。”黎紫書在這里說:“這是今天的我所能想到的寫長篇小說的唯一理由。……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黨課參考(2021年20期)2021-11-04 09:39:46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小哥白尼(軍事科學)(2019年6期)2019-03-14 05:49:56
黨課參考(2018年20期)2018-11-09 08:52:36
中國蜂業(2018年6期)2018-08-01 08:51:14
都市麗人(2015年4期)2015-03-20 13:33:22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